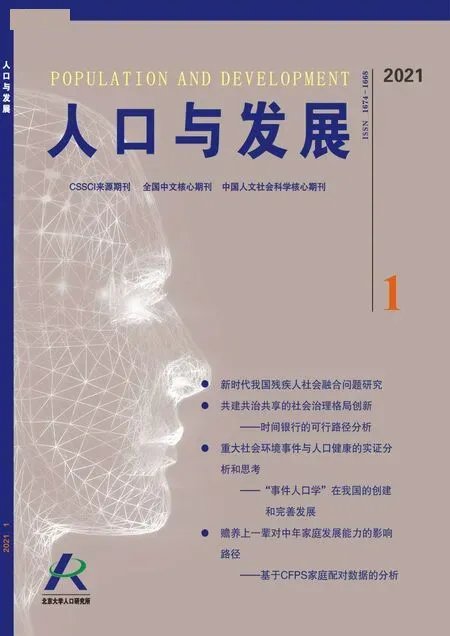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叶静漪,苏晖阳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1 问题的提出
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尊重、关注与保障残疾人群体,推进其社会融合,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全社会人文关怀的温情体现。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为8502万人,其中重度残疾2518万人,中度和轻度残疾人5984万人。(1)参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载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网:http://www.cdpf.org.cn/sjzx/cjrgk/201206/t20120626_387 581.shtml,2020年12月16日最后访问。残疾人群体相对于健全人群体而言,在肢体、语言、听力、精神、智力或多重方面存在某些长期缺损,(2)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的第一条,对残疾人群体的属性进行了相关界定,同时阐明了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生理层面的原因使得残疾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会遇到客观上的障碍,也导致残疾人群体受到精神层面上的忽视甚至歧视,整体社会接纳程度依旧有待提高,难以和健全人一样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数千万残疾人亟待国家和社会更加重点的关注,也亟待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范畴进行专门考量。
由于残疾人群体在生理与心理层面上处于相对欠缺优势的地位,因此需要在多个层面上予以倾斜保障也成为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1945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在序言部分即强调将“人权”和“平等”作为世界人民的基本信念。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人”皆有权平等享受在社会中的一切合理的权利。此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国际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涉及残疾人的重要文件,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我国也一向高度重视对残疾人群体的保障工作,自《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2)》实施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工作和保障更是多见成效,至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为核心,包括各层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内的残疾人权利保障法律体系。
但是我国在残疾人融入社会这一层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残疾人的社会融合,是对残疾人的认识从“救济对象”转变为“权利主体”,以普惠与特惠相结合、一般与特殊保障相结合的原则为指导,遵循“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实现法律、教育、信息、就业及社会保障、媒体、无障碍等方面与社会的充分融合,确保残疾人能够依法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履行义务,获得公正的、必要的机会和资源,正常享受社会福利,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促进残疾人在社会中实现平等全面的发展。那么,在大力推动残疾人社会融合的大背景和总要求下,如何从法律、教育、信息、就业及社会保障、媒体、无障碍等多个角度立体地推动残疾人融合进程?如何激励残疾人主动参与、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平等享有相关权利?如何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充分保障残疾人的身心健康?如何形成更加常态化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保证残疾人事业和社会融合进程高质量推进及发展?如何在这个复杂且动态的过程中,有效促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这都需要对相关理论、思想与实践展开更深层次的梳理与研究,需要更加深入且充分地理解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理论界定与实践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完善新时代残疾人社会融合多领域综合保障机制体系,推动残疾人平等参与和全面融合。
2 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的思想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取得很大进展。深刻理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的思想渊源,需要从三方面掌握其内涵。一是深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中可借鉴的资源。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融贯中西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为更好地推动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看,残疾人的社会融合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的必然要求。辩证唯物主义指出,普遍联系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准则。社会融合充分体现了普遍联系的观点。残疾人作为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也和社会其他群体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推动其社会融合,就是创造条件,消除社会对残疾人融入社会的各方面障碍,使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观点,阐释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国社会对残疾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最开始的感性认识是把残疾人当作需要救济的对象,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渐深入理解残疾人作为权利主体的主体性,更加关注残疾人在政治生活、教育、就业、文化等方面越来越突出的需求,从原先的“救济对象”转变为“权利主体”,这一认识的转变更接近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性。从社会融合的角度促进残疾人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规定为人之为人的真正权利,对于保障残疾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帮助他们融入正常社会,实现其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符合匹配残疾人自身利益和发展规律的重要意义。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集中体现在儒家“仁爱”思想之中。儒家将“仁”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孟子在对“仁”思考中发现了人性内在的“恻隐之心”,并认为人的恻隐之心作为仁之发端,自发推动着人去关爱他人,守望相助。(4)《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记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互助的过程就是推进残疾人社会融合必不可少的交往条件。与此同时,儒家“仁爱”的思想不仅体现在“爱人”(5)《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表明“成人”的过程就是一个“求仁”的过程。,更是具有自反性的“自爱”,即在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具有无限可能的行动主体,残疾人的志向、目标、梦想一样值得全社会给予支持,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每一个人提供自我实现的平等机会。孔子“有教无类”(6)《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曰:‘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影响了后世几千年,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推动残疾人在教育方面的社会融合,能够为其他领域的社会融合奠定丰厚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从上古尧帝到青铜时代,国家便有对于社会特殊群体的关注和扶持。(7)《尚书·尧典》中就记载了以德治国、修己安民的思想,《尚书·大禹谟》首次提出了“政在养民”的思想,《礼记·月令》还存有夏王朝“养幼少,存诸孤”的记载。无论是《尚书》中记录的殷王的“无弱孤有幼”,还是《史记》中对于周文王的“笃仁、敬老、慈少”的记录,抑或是《礼记·王制》中对于救济鳏寡孤独的清楚说明,都能看出古代帝王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注。周朝还设有“保息六政”的政策,即是指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据《周礼》注疏,振穷即对鳏寡孤独残疾实行救济,宽疾即对残疾人等免除役事。“贩穷”,“恤贫”,“宽疾”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中,赈谷应是首要和主要的。周代还有乡师、乡大夫、遂师、遂大夫、族师等各级官员,负责对残疾人等进行救济品的发放。春秋战国时期对残疾人实施居养政策,收养残疾人并负责其起居饮食,并在徭役、赋税方面对残疾人减免义务。(8)《管子·度地》写道:“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痼)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也就是说,仍能从事某些劳作的残疾人也可以减免一半的徭役。战国初期,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主张,社会的和谐需要全体成员相互之间的“兼爱”,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作为平等的主体而与他人交往,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包含残疾人在内的各个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唐代设有“悲田养病坊”,旨在救助老幼废疾无依无靠者。宋代大儒朱熹于乡里建立社仓,以弥补官方赈济之不足,这些都从社会整体视角,为今天残疾人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思考。
从西方哲学思想中可借鉴的资源来看,西方思想家很早便从社会共同体的角度去看待特殊群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幸福而单独存在的,其目的是要实现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9)《理想国》(IV420B)中记载,苏格拉底在与阿德曼托斯交流时讲到“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这意味着需要从总体性的视角去平等看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个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实现自我的社会融合与帮助他人实现社会融合是相统一的。亚里士多德将人性论的规定和社会共同体的属性相关联,认为善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和发展目的,个人对于善(幸福)的追求与城邦的共同善(集体利益)是协调一致的,个人需要在共同体之中追求城邦的整体幸福,这提醒我们要在共享的理念中去与他人相处,并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空间,由此才能实现社会融合。
人具有共同体成员和个体权利主体的双重属性。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关于个人权利的相关论述,为把残疾人理解为“权利主体”奠定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基础。根据格劳秀斯(1583)和霍布斯等人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应当承认人的自我保存权利,在自我保存的前提下需要我们关心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10)格劳秀斯在其所著的《捕获法》中提到,“首先,要允许人们保护自己的生命并且躲避那些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与有害的东西;其次,要允许人们为自己谋求并且保留益于生命之物”。洛克进一步从劳动权和财产权的视角完善了人权理论,为当代残疾人在社会中的平等受教育权和就业权提供了理论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对人的本质、价值和个性的肯定,使得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成为人权的基本要求。法国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天赋人权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博爱,每个人都应享有正常生存、得到尊重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这提醒我们当今要切实关注并实现残疾人在社会各方面的权利,使其在各个领域真正实现与社会的融合,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公共正义(11)公共正义是属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论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罗尔斯相信,在民主社会中,各种价值观之间有可能就公共正义问题通过重叠共识达成一致,以此应对多元价值与公共整合之间的紧张。是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每个人的共同追求。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看,我们不仅要承认和贯彻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公平平等原则,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承认差别原则的合理性,即社会制度应当去尽可能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约翰·罗尔斯,2009)。威尔·金里卡(2005)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也告诉我们,要根据社会现实情况去实现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单就教育领域的残疾人社会融合而言,需要我们思考的便是一方面要保障“起点公平”,确保残疾人群体可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另一方面,要逐步发展到“追寻差异性公平”,关注残疾人个体的学习需求和需要,尊重个体多样性。总之,我们不能抽象地和形式地去思考残疾人的社会融合,而应当设身处地站在其立场上,在各个方面针对性和切身性地助力其实现社会融合,从而达到实质正义。
在新时代,在吸收中外优秀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更需要发展“平等、参与、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残疾人社会融合事业发展得更加壮大。在这里,“平等”指的是非排斥性,不为残疾人的社会参与设置障碍;“参与”强调了残疾人作为社会成员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重要力量的地位;“共享”表明了残疾人作为社会成员分享改革成果和发展红利的正当权利。在贯彻这一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转化为社会正义的理念,将个人道德要求转化为公共领域中的伦理价值规范,同时吸收西方可借鉴的伦理思想资源,伴随实践发展去不断丰富和深化对残疾人社会融合思想基础的认识,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残疾人社会融合理念。
长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为残疾人社会融合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各方面支撑。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也为新时代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推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作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必须着眼于整体,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制度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截瘫伤员说,“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面向未来,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我们更应当坚定树立残疾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的观念,为残疾人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追求进步、施展才华的平台、舞台,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更好环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实现我国残疾人的社会融合。
3 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现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对残疾人事业越来越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观念也从原本注重物质补贴转为更加重视自身能力培养、自身价值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残疾人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深度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重要且坚实的一步。当前,我国残疾人法律保障机制不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对残疾人和善友好的融洽社会氛围也越来越浓厚。但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于残疾人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当前的社会融合发展仍存在着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于残疾人特殊的自身条件,给予其必要的特殊关怀与保障,有利于残疾人更平等地在实质上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
3.1 总体制度保障:法律法规基本覆盖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残疾人公民权利的有力保障,也是推进和落实各项残疾人社会融合工作的必要前提。我国残疾人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主体法律、在具体领域对残疾人权益实施保障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该领域其他规章、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律法规中对残疾人权益保障有关的内容。
残疾人权益保障的主体法律是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18年修订)。在具体领域对残疾人权益实施保障的行政法规包括1994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2017年修订)、2007年颁布的《残疾人就业条例》、2012年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和2017年颂布的《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条例》等。在其他例如民法、刑法、婚姻法、教育法等重要法律规范中也都有涉及残疾人权利保障的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更是主导构建了我国残疾人民事权利保护的制度体系,以实现残疾人与其他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王治江,2020)。
总体来说,我国在残疾人总体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概括指向残疾人权益”到逐步覆盖残疾人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康复等各领域、全方位的法律体系;从只有在法律和行政规章层面对残疾人权益做出的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到地方性法律法规、政策中同样对残疾人权益进行因地制宜的具体化规定的巨大进步。同时,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事业支撑,我国还尝试在法律实施过程和具体司法实践中,积极推动残疾人权益保障落到实处。
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有关残疾人权利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但经过对主要条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对残疾人提供的制度保障,并不是通过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来明确参与残疾人保障工作主体的责任,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执行力,难以得到有力的保障。此外,我国法律法规仍相对注重“扶弱”和“助残”,在为残疾人社会融合创建全面无障碍环境、提供发挥个体潜能平台等方面仍较为缺乏。
3.2 刚性环境建设:设施建设与信息通达
建设适于残疾人生活的无障碍设施,是在物质层面上为残疾人去除障碍,为其平等行使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提供基本前提。自2012年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施行以来,在党委领导、各政府推动、各级残联组织配合、残疾人参与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平等参与、共享融合”的无障碍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以物质环境、信息交流、社区服务无障碍为主的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快速发展。(12)参见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三周年有关情况发布会中的发言:http://www.scio.gov.cn/m/xwfbh/xwbfbh/wqfbh/2015/20150803/tw33183/Document/1443169/1443169.htm,2020年12月16日最后访问。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也强调了要“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提升残疾康复服务质量”。
在“用得上”、“用得起”的基础上,“十四五”期间致力于让残疾人“用得好”。作为无障碍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是服务残疾人的物质载体。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有利于推动残疾人赋权增能、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促进残疾人社会参与,是实现社会权利的重要途径(凌亢等,2017)。2012年以来,住建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无障碍市、县创建工作,在相关责任部门的主导下,逐步明确并贯彻落实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无障碍出行设施标准等各行业标准规范文件。(13)参见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三周年有关情况发布会中的发言:http://www.scio.gov.cn/m/xwfbh/xwbfbh/wqfbh/2015/20150803/tw33183/Document/1443169/1443169.htm,2020年12月16日最后访问。盲人按摩、盲人阅览室等基层残疾人康复、托养和综合服务设施建设规范和标准也进一步推动完善。截至2019年,全国已出台537份省、地市、县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737个地市、县已展开系统化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全国参与无障碍培训的人数达到4.9万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达3261次;有关部门为136万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其中包括15.3万严重贫困的残疾人家庭;并为47.4万残疾人发放了针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燃油专项补贴。(14)
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也得到了全面发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共有2341个,总建设规模达584.5万平方米;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共有1006个,总建设规模达414.2万平方米;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共有887个,总建设规模达251.3万平方米;5.8万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已经实现了危房改造。(15)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残疾人发展统计公报》根据联合国《亚太残疾人十年》的衡量指标,我国许多城市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相较于发达国家同等类型城市已毫不逊色。(16)参见王晓慧:《“亚太残疾人十年”阶段性成果显著将进一步推动国际残疾人事业共同发展》,载华夏时报网,https://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72840,2020年12月21日最后访问。
残疾人信息无障碍建设是在信息文化融合层面上为残疾人去除障碍、消除鸿沟,推动残疾人积极参与数字经济、融入大数据时代、共享数字化生活的基本前提。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残疾人无障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努力破除残疾人群体在信息交流融合上的壁垒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相关主管部门结合行业特点,从专项政策支持、信息无障碍标准体系建设、电信普遍服务推进、信息技术赋能、公益信息服务等方面多管齐下,联合各行业持续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残疾人信息消费成本不断减轻的成效。
2020年9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实施的《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推进我国信息无障碍建设,消除残疾人群体的“数字鸿沟”,通过信息技术赋能,实现社会包容性发展,助力残疾人群体在信息文化层面上实现更好的社会融合效果。在指导意见的推动下,“十四五”时期,“新基建”的建设完善、信息无障碍终端产品供给的提升、互联网无障碍化的普及、信息无障碍产业化的发展等,将有效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与无障碍环节融合发展,这对于破解我国信息无障碍产业规模化不足、信息无障碍终端产品和服务供需对接不畅、市场主体自发参与建设积极性缺乏等问题,将发挥重大作用。
3.3 柔性环境创造:融合发展与社会语境构建
残疾人社会融合是社会环境与自我的双重构建的过程,需要社会为残疾人营造平等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也要求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持有融入社会和环境的积极意识。
健全、丰富的融合教育是残疾人提升自我能力的必要基础,广义的融合教育指所有残疾人都能够完全融入普通的教育系统,包括接受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乃至实现终身学习(吴文彦,厉才茂,2012)。融合教育作为残疾人融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残疾人能够真正“活出精彩人生”的重要保障,其关键地位不可忽视。
近年来,我国特殊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特殊教育经费不断增长,其增长率高于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增长率。(17)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192所,特殊教育在校生达到79.5万人,(1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3.6万名残疾的青壮年文盲接受了国家提供的扫盲教育。(19)
但鉴于融合教育推进的特殊性,在当下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例如:特殊教育建设参与主体较为单一,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力量,无法实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的良好状态;教育教学方法、管理模式的规范过于笼统,缺少细化规定,难以适应新时代下残疾人社会融合的新要求(吴琼星,庞文,2020)。
对此,国家出台的“提升计划”“实施细则”等制度文本对我国特殊教育制度体系做出了有效的补充,且为残疾人获取相应的信息便利也是《残疾人保障法》所规定的“政府责任”(叶静漪,苏晖阳,2020)。新出台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正式确立了“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远程教育为补充”的特殊教育基本方针,建立了我国特殊教育多元教育格局,丰富了特殊教育参与主体。2017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也指出了改革方向,要求积极提高残疾人教育质量、推进融合教育。残疾人社会融合进程在媒体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省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25个、电视手语栏目32个;地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219个、电视手语栏目272个。(20)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残疾人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残联还建立了网络舆情监测平台,推出了依托网络的残疾人服务地图和微服务平台(郑功成,2017)。总体来看,虽然当前公众对残疾人社会融合的认知程度依旧偏低,但随着近年来社会媒体对残疾人群体的报道更加深入,正面友善的媒体报道极大促进了对残疾人友好融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将有利于残疾人群体实现更充分的社会融合效果(程征,周燕群,2020)。
社会保障方面,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便贯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按比例落实残疾人就业,同时用辅助性就业和公益性就业的方式,在支持性就业的探索中,为残疾人就业途径的拓宽、就业增收等提供助力。对于无劳动能力、无抚养人或者扶养人不具有扶养能力、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辅以教育救助、就业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扶贫救助等制度系统,特别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为残疾人民生保障构筑起“包围性”防线。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工作也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的要求下上升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依托于专业康复机构和社区康复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实现了基础康复服务的全覆盖。
4 国外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理念、内涵与实践
4.1 国外残疾人社会融合理念的发展
国外社会融合的概念及其理念定义研究,自20世纪初就已在自杀现象的相关研究当中明确出现(Durkheim,1951),后逐渐延伸至流动人口、移民、婚姻家庭等相关的研究之中。有学者提出社会融合的核心是感知融合,重点观测包括某个个体在某一群体中的归属感以及作为该群体的成员的精神感受(Bollen,Hoyle,1990),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进行研究,称之为“使成员留在他们所在的群体中的力量”(Festinger.L,1950),主要关注于让某个群体关系维系和延续的主观驱动力,后来其关注的侧重从原因机制转向结果变量,将其定义为“所有使得群体成员留在群体中的力量的结果”。1995年在欧盟及地中海国家间启动的“巴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在其推进的过程中提出要统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弱势群体的融合。欧盟也于2003年在关于社会融合的联合报告(The EU Commission Joint Report on Social Inclusion)中对“社会融合”作出了定义,其内涵主要是指向确保背负相关风险或遭受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全面参与社会生活,享有平等的机会和福利,为其更多参与生活和决策提供保证。
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国外开始有学者以社会融合相关理论作为基础,逐步延伸关注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相关话题并展开了研究。美国学者费伊(1955)开发出一个量表,从自我接纳、接纳他人和对他人接纳自己的程度感受三个维度评价接纳群体的社会融合倾向(W.F.Fey,1955),鲍勃·萨佩(1991)做了关于社会排斥和残疾人关系的研究,试图通过借助阐述社会因素的参与导致了残疾人群体权利的实现难度增加,来推动个体型残疾向社会型残疾转变的路径,以达到社会融合的目的(Oliver Michael,1991)。斯梅尔赛(2001)也提出,社会融合处理的是某一个社会单元中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社会联系和互动的范围、频率和效果(如认同感等)的问题(Smelser.N.,Baltes.P.B,2001),该概念可以依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应用于包含残疾人群体在内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单元、群体或组织。此外,不需要改良或者特别设计的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替代了无障碍设计(Barrier-free Design),将服务对象从残疾人扩大至所有人,可以为所有人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便利,这不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被美国等多国的主流和立法所接受。这些相关研究涉及了对残疾人社会融合的较为基础性的研究与分析,但许多特点及特征较之以往有了许多转变,缺乏对于新时期和新形势下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研究。
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残疾人社会融合的重要内容,其惠及面越来越广,可以为残疾人创造出更为友好的社会环境,也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多个国家的重点关注。其理念支持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其一是社会环境的残疾观,世界卫生组织于2001年10月发布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更新了当中对于“残疾”一词的定义,认为残疾不仅是生理缺憾,更是一种包含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复合状态,其相较于1980年发布的《国际缺陷、残疾和障碍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and Handicaps),无论是理念还是应用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革;其二是社会分享说,其认为残疾人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强调通过社会体系中的无障碍环境来促进机会均等的实现;其三是同化论和多元论的结合,从残疾人发展的角度处理残疾问题,关键是从物质环境、信息环境以及体制安排上,排除所有社会因素障碍以保证所有残疾人能够充分参与其中。
另外,自我意识也是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掀起的残疾人“独立生活运动”。不同于医疗模式下“独立生活”的定义即消除功能上的障碍,残疾人开始要求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并逐渐意识到社会因素也是造成他们不能“独立生活”的重要原因,从而摆脱将社会环境视为给定因素的思维定势,呼吁全社会关注消除这种障碍。随后在日本、英国等国家,类似的运动也开展起来(Shapiro JE,1994),其也成为了社会和权利模式残疾观的先声,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残疾人的社会参与,也推动了残疾人社会福利相关观念的更新。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在1974年提出社会排斥(21)英国政府对社会排斥的定义是:“人民或者地区遭受到了失业、低技能、低收入、简陋的住房、高犯罪率、不健康和家庭破裂等问题的综合影响”。社会排斥重要的特点是,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变动的“怪圈”。概念之后,也促使了后来兴起的逆社会排斥的相关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后来在2011年共同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22)参见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https://www.who.int/disabilities/world_report2011-06-09,2020年12月16日最后访问。中也提到,需要“提升公众关于残疾的意识和认知、相互间的尊重和理解有助于形成融合性社会”。
4.2 国外残疾人权利保障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实践
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在此领域探寻通过立法及固定为制度的形式,来明确残疾人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如在国际层面,1982年和1993年,联合国分别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和《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Standard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强调无障碍环境建设在确保残疾人的平等权利的重要意义,第61届联合国大会更是通过了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的第一个人权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随后该公约于2008年5月3日正式生效。国际劳工组织也于1983年通过了《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的公约》(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Employment(Disabled Persons)Convention),对残疾人在职业康复、就业方面的相关权利、原则、政策和措施等进行规定。
在国家层面,美国(23)美国于1990年出台了《美国残疾人法》。、英国(24)英国于1995年颁布了《反残疾人歧视法案》。等国家也纷纷出台了相应法律法规,特别是许多国家在其本国的宪法中明确加入了反对残疾歧视的条款,力图解决伴随残疾出现的隔离和排斥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奥地利、巴西、斐济、芬兰、冈比亚、德国、加纳、马拉维、瑞士、乌干达等国的宪法,都作了反对残疾歧视的规定,对于推动残疾人社会融合起到了重要的法律制度保障作用。西班牙更是在1982年直接以残疾人社会融合为名进行立法,基于西班牙宪法中关于权利及人格尊严的相关条款,以联合国《精神病患者权利宣言》及《残疾人权利宣言》为出发点,制定了西班牙《残疾人社会融合法》(General Law o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Social Inclusion),保障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和各项权利。
美国在残疾人保障方面存在着的政策观念的转变及发展,主要体现在主体身份的转变上,联邦政府从原先的主要负责者逐渐转变为决策者和监督者,把更多权利和发挥的空间留给地方政府和社会,促进参与主体的多元化。1961年,美国制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障碍标准》(Uniform Federal Accessibility Standards),实现了无障碍设施最低标准的统一,随后无障碍设计的要求被纳入到法律体系之中。此后,英国(25)英国于1967年出版了《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建筑标准》,随后于1978年颁布了《英国残疾人房屋设计标准行业法规》。、日本(26)日本于1982年发行了《无障碍化建筑设计标准》,并在1993年颁布的《残疾人基本法》中规定国家、地方团体等部门应采取的公共设施无障碍化。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制定了无障碍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1990年,美国颁布了《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禁止在就业、教育、交通、商品服务等方面歧视残疾人,特别是其也一并对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制。在残疾人融合教育领域,美国也出台了《障碍者教育法》(The United States Special Education Legidlation)、《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为残疾学生创造平等的、无差别的教育环境。
而英国政府实行“平等、多样性、融合”战略,于1995年通过了《反残疾人歧视法案》(The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为了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法案条款明确规定,在就业、社会服务、教育和交通方面歧视残疾人是违法行为,并在英国议会专门设立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融合教育方面,英国侧重于扶持残疾人教育中的高等教育部分,并以其为突破口推动整体融合教育的发展(伍琳,2017)。
5 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的原则及思路
5.1 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的原则
5.1.1 平等原则
“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残疾人平等地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与发展是实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真正繁荣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27)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三十三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称的“平等”首先指的是形式上的平等,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就是“机会平等”或“机会均等”,是指每个人作为抽象的人是平等的,也就是把人具体的个性全部舍弃,只保留作为人的属性(林来梵,2011)。就这个意义来说,平等原则也可以被置换成不得歧视原则。
在《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平等对待和不得歧视占据重要位置,比如其明确阐明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便是人们所拥有的尊严、价值、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强调需要保障残疾人不受歧视地充分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28)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序言。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61-106.shtml,2020年12月18日最后访问。在《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中则明确规定“机会均等”,要求社会各系统和环境都能够为所有人特别是残疾人享受和利用,同时也表明了其负有同等的义务。(29)参见《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48-96.shtml,2020年12月18日访问。消除对残疾人存在的偏见与歧视,使残疾人顺利融入社会,摆在首位的便是让残疾人享有和健全人同等的权利和人格尊严(覃有土,韩桂君,2004)。如果不能保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那么残疾人本应获得的支持与帮助就会被误认为国家和社会的施舍和恩惠,这并不是将残疾人当作平等的、有尊严的主体对待的表现。
我国过去将具有身心缺陷的人称为“残废人”(30)“残废”这一称呼在我国82宪法中仍然保留。我国现行宪法第45条规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而“残废”实际上是以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是否能够就业、是否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为尺度作出的一种评价,这折射出人们以创造经济价值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观念。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程度上是被歧视、缺乏尊严的人。过去的“个体型残疾理论”也认为,残疾人自身伤残的结果是导致其所经受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性质认定上仍然存在着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不正常”与“正常”的二元区分。残疾人应该去主动适应社会,克服诸多不便,而社会没有义务去适应和方便他的要求——而假使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了方便,那也只是出于一种怜悯和施舍,而非基于他的权利。
而如前文所述,现如今伴随着社会型残疾理论的普及,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残疾”这一称谓已经被“身心障碍者”取代,这种称呼强调“残疾人”个人及其面临的不便或障碍并非社会问题的源头与社会的负担,恰恰相反,“残疾人”面临的不便或障碍大多是社会造成的,即“残损在个体,障碍在环境”(何乃柱,李淑云,2013)。迈克尔·奥利弗(1983)也提出“社会型残疾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不认为残疾人自身有什么毛病,它摒弃了个人病理学模式……社会型残疾理论将目光聚焦于环境的改善,重视环境对残疾定义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强调残疾人对环境的适应。”
由此,残疾人或身心障碍者严格来说并非需要怜悯和施恩的对象,他们在人格上和健全人完全一致,因此完全没有被歧视的正当基础。他们虽然需要社会提供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条件才能正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健全人可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使之能”正常生活,而是社会通过提供条件“支持”他们的正常生活,因为他们本来就具有与健全人一样的人格,并且与大多数人一样平等地享有正常生活而不被歧视的权利。
5.1.2 倾斜保障原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2009)中提到,自然的不平等,例如出生伊始所享有的天赋、身体状况等难以通过提供均等机会的方式消除,而差别原则就是为了消除自然偶因所造成的不平等。依据差别原则,国家可以通过对教育、就业等资源方面的差别分配来对最不利者的长远期望进行改善。以受教育权为例,残疾人因其身体或者智力等原因,无法像非残疾人一样无差别地接受教育。一般情况下,对于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子女等社会弱势群体只需要在学费、餐费等方面给予补贴或者减免就可以保证其接受正常教育,但是对于残疾人,给予与普通弱势群体相同的补贴或减免虽然满足了形式上的平等原则或非歧视原则,但仍然远远不够(刘雪斌,王志伟,2018)。残疾人作为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在受教育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需要国家和社会进行进一步的给付。基于此,在残疾人权益保护与推进残疾人社会融合过程中,有必要更侧重实质正义,根据残疾人实际需要给予针对性保障。因为“如果不问个人差异,一味统一平等对待,那么越是如此,越是有利于现实中具有强势特征的人,而不利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林来梵,2011)。
也就是说,在“倾斜保障原则”中,“平等”的内涵被扩大了,它不应只局限于机会、资源获得层面的无歧视的“起点公平”,即能够使得残疾人与健全人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同时也应由残疾人与健全人的差异化现实逐步发展到实现“差异化公平”:一方面需保障残障人群与社会一般人群平等地享有权利;另一方面则应考虑其因身体机能障碍产生的特殊需要,为残疾人提供必要的机会和资源,为其实现正常生活创设出优良条件,共享全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成果。换言之,“起点公平”为“差异化公平”提供基础和保障,“差异化公平”为“起点公平”提供目标和指南,二者间共同作用,进而达到“平等”在形式和实质意义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从这个意义来说,残疾人获得倾斜性的保障和给付不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质评定意义上的展开,它也是一种残疾人享有的社会权,该权利的存在就是旨在纠正过度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对应着国家在给予公民物质、经济等方面的积极给付义务。事实上,通过过往实际操作经验表明,残疾人因残疾与健全人所产生的差距并非不可弥补,借助国家和社会的积极给付义务,残疾人在工作、教育、学习等各方面的潜能同样可以得到完全释放,与健全人并无显著差异,甚至做得更好。
因此,基于倾斜保障原则,残疾人群体有权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帮助以弥补其先天的不足,使其最大程度上平等地融入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生活,进而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满足民众对于社会正义的期待。就比如社会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教育上的资源倾斜,通过此类补偿机制来弥补残疾人先天条件的不足,使其有机会享受与健全人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从而达到实质意义上的正义。
5.1.3 充分融合原则
纵观历史,美国历史上的“隔离但平等”政策曾一度被其最高法院判决为合宪,例如1896年普莱西案(Plessy v.Ferguson)的判决中就认为对黑白种族的隔离的法律要求,并不必然隐含着任何一个种族低劣于其他种族的意思。然而可以延伸的是,残疾人与健全人一样平等地享有融入社会生活的权利,具有人之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不应在“隔离”、“限制”中接受社会关怀。否则,就如沃伦(Warren Earl Burger)所指出的,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不平等”,对残疾人的心灵和心智造成创伤,同时也不利于一般公众对残疾人生活的了解与关心。(31)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47 U.S.483)中,沃伦大法官认为即使教学设施平等,进行种族主义隔离教育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仅仅因为种族和肤色的原因,将少数民族的学生同与他们年龄和资格相同的其他学生隔离开来,将使被隔离的学生对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产生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将对他们的心灵和心智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
另一方面,残疾人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一员,应全面、深度、系统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不能因其特殊身份而受到不当限制,进而影响其基本权利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充分融合原则并不否认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存在差异,是一种多样性的体现,但更加应该强调通过创设相应条件,尽可能将二者包容在“同一个环境中”,使残疾人在实践和心理层面均成为社会的一员。例如在残疾人就业方面,其可以在相关支持设施的帮助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健全人共同参与劳动,进而为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生产的一分子创造条件。
就目前来看,在残疾人保障领域,反歧视求平等、反隔离求融合,是国际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主要潮流(汪海萍,2006),各国在残疾人保障立法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强调“充分融合”的理念:避免历史上曾经一度出现过的的“隔离式关爱”“收容型救济”,强调残疾人要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选择居所,获得各种社区支持服务等,并与健全人一道参与到教育、工作、医疗等日常活动中。在此时代大势下,我国残疾人事业必须坚持充分融合的原则,在“平等、参与、共享”理念的指引下,推动全社会向着公正、包容、惠及每一个人的可持续上发展(吴文彦,厉才茂,2012)。
5.2 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的思路
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应当以“权利”和“融合”为出发点,将残疾人社会融合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残疾人事业的相关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导下,推进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工作。这不仅要求我们建立科学的残疾人社会融合的评价体系,把残疾人社会融合的全过程分解为若干具体的组成部分予以落实,更要优化顶层设计,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调整制度、优化环境、改变社会对残疾人的观念,帮助残疾人更加便捷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最终实现社会融合。具体而言,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的社会融合事业可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加以推进和深化:
5.2.1 加强制度设计,完善制度框架
长期以来,相比个体的身体条件制约,制度因素对于残疾人的社会融入程度产生着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更是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残疾人社会融合,需要通过明确具体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搭建起有切实实施力的残疾人社会融合制度框架,使该领域内不同的法律制度形成内在统一且有机联系、相互支持的系统及有机整体(黎建飞,2010),从而充分回应现实需要:一方面,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位阶,推进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相关权利类型化、成文化、具体化,例如,可以通过探索人大立法的形式,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法规上升到法律层面,甚至探索我国的《残疾人社会融合法》,实现我国残疾人基本的获得保障权利的具体化,从更高的层次上保障残疾人社会融合;另一方面,完善法律实施机制,畅通残疾人维权途径,真正让制度保障“动起来”,例如,可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残疾人保障法》中“法律责任”规定的相关内容,赋予政府有关部门相应职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为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5.2.2 构建友好环境,健全设施建设
正如《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九条所提出的建设能够保障残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相关要求,友好完善的公共设施及社会环境营建,是残疾人充分融入社会的前提基础,相关设施设备的缺失将大大制约残疾人的社会融入水平。“十四五”期间应当更加着力去推动友好型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生活环境支撑: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无障碍设施领域的制度建设,深化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长效工作机制(吕世明,2013),同时,可以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将相关技术标准直接纳入法律规范体系中,并将无障碍设施配套作为新建建筑验收合格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鼓励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无障碍设施建设中,推动无障碍设施进一步铺开,提高我国城乡无障碍服务水平,例如,可以在总结现有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试点“无障碍城市”,并作为相应考评、督查指标,为各地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提供动力。
5.2.3 注重社会引导,实现良性互动
我们党作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各项事业中承担着重大使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体需要主动发挥引领作用,帮助残疾人积极融入社会,在全社会弘扬助残精神,自觉树立社会融合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风尚。
另外,媒体作为新闻事件与社情民意的反映窗口,在残疾人社会融合议题的信息共享、舆论引导与监督、推动社情决策与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促进残疾人与社会构建融合意识的重要媒介。实现残疾人社会融合,必不可少的就要实现残疾人群体在舆论传播领域的良性生态。一方面,应扩大现有信息媒介,保障残疾人平等获得信息的基本权利,例如,扩大手语节目覆盖面、设置专门面向残疾人的节目,多元化报道残疾人生活、工作全貌;另一方面,媒体在相关消息报道时可以从公众利益角度出发,构建平等、参与、共享的残疾人形象,形成良性互动的舆论氛围。
5.2.4 完善社会保障,促进自我认同
平等对待是法律禁止直接歧视的观念所表达的基本原则(阎天,叶静漪,2009),完善对残疾人有关的社会保障举措,促进残疾人就业等,是残疾人反歧视事业的关键所在,也是使其在新时代完成社会融入的的应有之义。例如保障其就业本身就能够帮助其建立自我认同,由内而外的认同从“社会负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又比如,在实施相应保障举措、推进其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就能促进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一方面应着力为残疾人参与社会生产提供基础条件,为其社会保障相关措施的落地创设基础;另一方面,相关单位,尤其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切实履行残疾人安置义务,充分发挥残疾人在对接弱势群体、顺畅沟通渠道等方面的特殊优势,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提供助力。
5.2.5 推动教育融合,构建全纳教育
教育对人的身心长远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残疾儿童和少年接受更加充分的教育,就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程凯,2006),教育融合也因此在残疾人社会融合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只有在学生时期就与健全人共同接受相同的教育,在培养残疾人权利观念的同时帮助其他人从小树立正确的社会融合观,才能更加避免残疾人被区别对待,与主流社会相隔离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应当加强设施与专业人员配套,为普通学校实现全纳教育提供物质与人才保障;另一方面,应大力推进宣传教育,从各级教育部门开始改变观念,将残疾人视为平等的受教育主体而非有功能缺陷的受帮助人群,从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纳教育”提供基础。
6 结语
当前,我们国家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兑现了中国“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在推进残疾人社会融合事业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在未来,也必将继续为这一事业担纲举旗。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开创出新时代我国残疾人社会融合事业发展新局面。
继续推进残疾人社会融合事业以彰显大国担当。残疾人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和能力,也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成员。我国在残疾人社会融合事业方面的制度经验、方式方案,都为全世界提供了思路和借鉴,接下来更需要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政治权利,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消除残疾人社会参与障碍,推动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谱写中国人权进步的历史篇章,为国际人权保障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继续为实现残疾人对美好的生活向往凝心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朋友的梦”。实现残疾人社会融合,需要认真研究残疾人社会融合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优化顶层设计,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残疾人社会融合的支持体系,设计科学完备的评估体系和督促检查体系,将各项残疾人帮扶制度落到实处,织密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底线,搭好残疾人发挥本领才干的平台,奋力实现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继续推动残疾人社会融合相关研究迈进世界一流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推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需要进一步理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为指导,加强法律、教育、信息、就业及社会保障、媒体、无障碍等方面与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科学认识,加快相关研究成果落地转化,将残疾人社会融合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为保证残疾人能够获得公正的、必要的机会和资源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科研成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