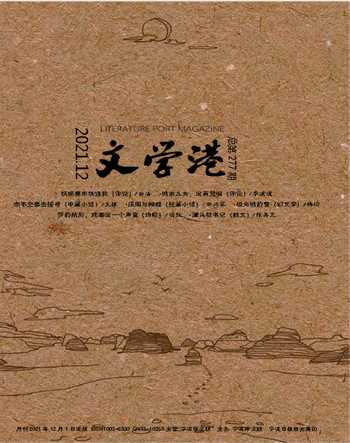两个母亲(外一题)
梁高英
孩子眼中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自己、养自己的亲生母亲;一个是生别人、养别人的别人家的母亲。这两个母亲如影相随,互相补充。
一
跟别人的母亲比,自己的母亲总是严厉一些。
“想骑自行车?不行,不行,马路上多危险,坚决不许骑!”——這种要求,常常是你还没提完,就被自己的母亲残忍拒绝,坚决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
“想吃棒冰?不行,不行,天气那么冷!吃下去对身体不好!不能吃。”——这种要求,常常是你刚说出口,就被自己的母亲果断否定,坚决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
“要钱?要钱干什么?家里有吃有喝。没有钱。”——这种要求,常常是你刚起了个头,就被自己的母亲半途打断,坚决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
……
自己的母亲常常瞪起眼睛,这个不行,那个不许。于是你看着大街上自由自在骑着自行车的小伙伴、去别人家做客看到别人家满冰箱的棒冰时,还有那口袋里总有大把零花钱的隔壁家的小孩,你就会奇怪别人家的孩子街上骑自行车就安全、别人家的孩子吃棒冰就健康、别人家的孩子有零花钱就可以……他们的母亲为什么就同意呢?
这时总是羡慕别人家的母亲。
二
自己的母亲不仅要求严格,而且总是嫌弃自己的孩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甚至越长越残都是理由。“别人家的孩子”就是所有自己的母亲创造出来的。
那天去家访,一进门,小明的母亲就告状:“小明太懒了!常常我叫他多看书、多看书,他就是懒得多看一点点。如果像隔壁的小华就好了,多乖的一个孩子啊!父母不在,他整天关起门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多自觉!”其实这两个孩子我都了解,小明不像他母亲说得那样懒,他很爱阅读,常常废寝忘食。小华也不像小明母亲说的那样自觉,他关门是关门的,但常常在里面看电视、玩手机,但小明的母亲总是看不到这些。
朋友生孩子比较早,总结出大实话:“孩子小的时候是很可爱的,白白胖胖,还有奶香味,依赖着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多棒啊!但后来越来越讨厌,最讨厌的是7-18岁之间。有自我了,有主见了,叫他做什么总是跟你顶,最讨厌。”确实大实话,主要是“有自我,叫他做什么总是跟你顶”,的确,所有的母亲总是喜欢听话的孩子,母子之间也是一场控制和反控制的过程。但直到孩子长大,长得足够大,大到离开家,所有的母亲又突然改变口径,觉得自己的孩子又变得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足够好。那些中年阿姨常常说:“奇怪,这个孩子以前那么不听话,现在怎么这么乖了呢!在工地,天天太阳晒也不怕辛苦,老板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叫他擦个地都嫌累,推三阻四。”孩子也觉得奇怪:自己的母亲以前像个超人,再后来变成了巨人,再后来怎么越老越小了呢?
三
当然一遇到事,两个母亲还是两个母亲,自己的和别人的,分得清清楚楚。
那年冬天,我看见这个背着女儿的母亲!隔着自己的厚棉袄,女儿用手紧紧搂着母亲的脖子,长得过高以致几乎垂到地上的脚打着厚厚的石膏!母亲瘦小而又年迈,常常需要踮起脚尖来增加高度以使女儿双脚不会碰地!脖子被紧紧卡住,双脸涨得通红,为使女儿能够搂住,只得把头使劲垂下去,花白的头发盖住整个脑袋,在斑驳的树影下尤其显得触目惊心!微弓着身子,不时耸着,用力把女儿往上顶!虽然如此,女儿还是不时滑下来,于是,不停地往上顶,往上顶……她背着女儿,就这样走完了这长长的林荫道,然后转弯开始爬楼梯。她先吃力地仰起头,看看高高的楼梯,吐出一口气。然后蹲下身子,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女儿的身子使劲往上一顶,最后腾出一只手,扶着栏杆,一级一级地往上挪:重重地上左脚,重重地上右脚,两脚并拢,歇会儿,吐口气,再上左脚、右脚……那放在栏杆上的手关节突出、肤色通红,疤痕累累……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快要爬完高高的楼梯了,她直起脖子,吐出长长的一口气,进到了教室。然后就在众多的注目礼中,她半斜着身子,双手托着女儿的臀部,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女儿放在座位上。额角上是大颗的汗珠,脸上的皱纹因脸涨得通红而更加明显,一条条,犹如刀刻。旁边的母亲看见了,只是在旁边纷纷说:“哟!这个女儿怎么了?”——也不过来帮一下忙!
两个母亲其实都叫“母亲”,都是一样的。
怀念大伯
这几日中的某一日应该是我大伯的忌日,但具体是哪一日已经不记得了。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毫不起眼,并且很快会被人遗忘,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但尘埃也是石头,也会硌疼一些人。
准确地说,他不是我亲大伯,他是我爸爸同母异父的哥哥,因为他是一个“拖油瓶”。五岁死了父亲,母子俩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因此经人介绍,我的奶奶、他的母亲就从外地过来嫁给了我的爷爷,他也跟了过来。新的家庭也不见得好多少,随着弟弟妹妹的出生,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很小的年纪,他就跟他的继父、我的爷爷为这个家不断劳作:插秧、割稻、种菜……农家要干的一切活他都要跟着干。农闲之际还要跟我爷爷走街串巷去卖面,卖回的不是钱,是米,给人家面,人家给米。换来的这些米他就提着、抱着。都说继母不好,但自己亲妈的偏心也是有目共睹的。听老一辈的人讲,在我奶奶的眼里,他既不像后来出来的弟弟那么聪明,也不像后来出生的妹妹那么贴心,他只是她以前痛苦生活的一个凭证,因此对他极为简单粗暴。甚至在他有一次发高热的时候也没有细心护理以致他脸上长满疹子从而成了麻子。对他的婚事也不大上心,在那个讲究父母之命的年代慢慢地他就成了光棍。母子俩在院子里大吵大闹的场景现在村里的很多老人还常常拿出来闲论,可见当时有多么惊心动魄。从来没有被温柔地对待过,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嘴里却叫着“妈,妈!”但我想,他不叫“妈”,他还能叫谁呢?相比别人,还是妈妈对他最好。
当我有记忆起,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住在两间简陋的瓦片房里,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光线很暗,一下雨就漏水,脚踩上去就“咂咂”地响,那时的我极不爱去,我总疑心那里有老鼠和蛇。所有的衣服是别人送的,有时候这件短袖领口破了,有时候这件衬衫大了,裤子的腰更是从来没有合适过,雪白的肚子总是露出一大截。常年不穿袜子,光脚穿别人穿过的各种各样的球鞋、皮鞋,太大了就拖着。村里的每个人,甚至连小孩,都叫他“麻皮,麻皮”,本名反而渐渐被人遗忘了,似乎他一生来就是麻皮的,都忘记了他也曾有小婴儿时代白白胖胖的时刻。有一亩地,是他全部生活的来源,他在上面轮流种花生、葱、芹菜之类的东西,收获后就用一辆三轮车骑到街上去卖,明明3元一斤的葱,他5角也卖,明明5元一斤的生姜,他2元也卖了,然后带着几十元的收成,心满意足地回到他的瓦房,为自己做饭、洗衣服。我妈妈常常埋怨他卖得太便宜,被人坑,他也只是笑笑,不说话。他总是买青鳣鱼、猪头肉这些便宜不健康的菜,我爸爸说他高血压要当心,他也不理睬。他就这样粗糙地度过了他的全部生活。
但在有些事情上他是很固执的,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恐惧。1998年的台风吹倒了他的瓦片房,站在一大片的废墟前,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眼泪,70多岁的男人、一米八的个子,默默地站着流泪。后来听人说,台风刮倒了,国家能帮助重建,他似乎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就一次次跑村里、跑镇政府协调重建,但后来最终没有重建,只是村里安排了住房。他很失望,总是强调自己住不惯。那时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住不惯,村里分的房子是楼房,干干净净的,不比他那原来的瓦片房好吗?但他就是说自己住不惯,因为这个房子不是自己的,这里的邻居也不好。于是我终于明白,他缺少的是归属感:他这一生孑然一身,当房子都是别人的,邻居都是新的,哪还有什么是属于他的呢?他没有位置、没有支撑,他怕。为这件事,他一直在坚持,一直在不断地找村里、镇里的领导,一直到死。虽然村里后来也给他换了很多房子,但他还是说住不惯。最终,他至死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他只能叫叫自己的母亲:妈……妈……——权当回了家。
对于人死后仪式的羡慕也是他所坚持的。人死后,乡下总有很多仪式。对于这些仪式,他有旁人无法比及的虔诚和迷恋。别人家的,他总是去帮忙,站在旁边看,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别人家的子孙如何把先人的后事做得十全十美。自己家的,他更是亲力亲为,清明、中元、春节祭祀……一个不落;烧9个小菜、上香、敬酒……井井有条。甚至在很多人劝他,反正你孤身一人,又没有子孙后代,以后不要再做时,他也不听。他说他死后很想有盏“灯”,这也是一种仪式,由女儿出钱请道士做法,据说能照亮魂灵回家的路。他没有女儿,因此在他去世后,我和我的堂妹们拿出钱给他做了一盏“灯”。当仪式的最后,我和我的堂妹们提着那盏灯,奔跑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嘴里不断念着:“大伯回家哦!大伯回家哦!”我突然深深理解了他的期盼,这么广阔无垠、全被暮色笼罩的世界,到处一片黑漆漆,没有一盏灯,还真回不了“家”。而家,是他一生的向往。他的迷恋来自他无家可归的恐惧。
最后的时日,他的脾气变得很古怪,总是喋喋不休地罵人,似乎想把前半生郁积的闷气全吐出来。他嫌弃衣服没洗干净、嫌弃邻居太吵、嫌弃菜不好吃……他把请来照顾他的保姆全部骂走,把养老院工作人员全都骂遍。他一改往日胆小的习惯,不断折腾他的兄弟姐妹,他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不停换人、换地方,甚至要求他们放下手头的事去照顾他。对的,有所亏欠的,都要带回去。他日复一日地躺在门板拆下来的床上,任由苍蝇围满全身。他只是不停地叫着:“妈……妈……”然后那天是台风天,时下时停的雨下得让人心烦,我的姑姑、伯伯、爸爸回家吃了一顿中饭后,回来发现他安静了!他去世了。死时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不知道那时他还有没有叫着:“妈……妈……”
他的兄弟姐妹把他的丧礼操持得很体面,我想他会很欣慰。他这一生,无儿无女,无财产无伴侣,甚至无是非无恩怨,赤条条地来,干干净净地走,直至最后尘归尘、土归土——倒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