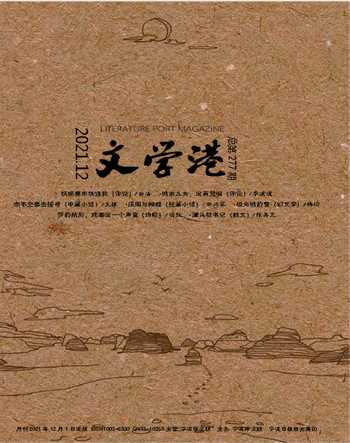场景
李世成
客车上
小男孩是世界上最恐怖的生物。仿佛是过去几年的梦境。我正在拥有一个可恨的小儿子,我无法知道他毁坏一切的冲动源自哪里。
他的妈妈为了制止他在客车站乱买东西,只好将儿童安全绳给他扣上。候车室的眼睛密密麻麻地向我们这边扫射。如果他不叫她“妈妈”,我们真像一对拐卖儿童的年轻夫妻。他越对着她喊“妈妈”,我越像一个对孩子不管不顾的可恶的父亲。先前他跑去便利店抓糖果和面包,手里能塞的都想塞满,抓一把,掉落,继续抓,他知道他的妈妈会跟上来给他付钱。他才三岁,想要的那么多。我过去将他抱回来好几次,她远远地看着她的小儿子,任由他在那里挑挑拣拣。他太相信自己的小手了,他甚至抓起一个大面包,将其举起,对着灯光,白炽灯太刺眼,他对白光失去了兴趣,将面包放回原处。他不能一次拿那么多零食,还有糖果,他在店里对着他母亲跺脚。
他母亲给他买了一个棒棒糖,还有一包手指饼。他安分了一会儿,将棒棒糖从嘴里拿出來放在椅子上,立马被他的妈妈呵斥,说放在椅子上不卫生。他看也不看椅子上的棒棒糖一眼。他的妈妈用纸巾包住棒棒糖,对我笑了笑。我接过棒棒糖,向垃圾桶走去。他吃了几根手指饼干,抖了抖食品包装,他大概想知道,还有多少根手指饼。他的妈妈在玩手机,我在看他的妈妈,更多的时间在看他。眼前的女人至少比我小七岁,眼前的小孩三岁了。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我每年都会提前一两天回贵阳。今天和我一道从村里出发的,还有母亲和父亲。她,还有她的父亲。我们乘坐村里往返县城的一辆SUV,车主大概也是春节前后在老家开车营生,过些天他也要出省打工去了。我不知道她在外省做什么工作,她秀气的面庞本不适宜在工厂待着。或许她可以在她口中的安徽或者江苏某个县城当超市导购员,或者给别人守店面,再者我可以给她安排一个令人安心的营生,比如她此行正是回去照看自己开的服装店。此前我们在通往晴隆县的乡道上,她被同村的一个大娘问过,嫁去了哪里。安徽还是江苏,我没有记下。车主将车停在了派出所,她和她的父亲下车去给她取临时身份证。我们在车上等他们。她将儿子抱着下车,她的父亲走在前面。车主出去在坝子边抽烟,我也下车在车旁站着。母亲和我说,想拿一百块钱做压岁钱给刚才的小孩,她和我说起年轻女人的父亲,她去和他拿一种难遇的草药,他分给母亲很多,并且不要她的钱。母亲说那种草药只有山崖上有,那个男人喊母亲姐,他的妻子和母亲同村,他岳母和母亲的妈妈是亲戚,要么就是她们是本家,这样的话语我总是不能记住。但母亲每次和我谈起别人,都要将他们的村寨和出身,是谁家的亲戚,若与我们家有亲戚关系的,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都要和我说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为此抱怨过,母亲说她不说我便不会知道。或者她以为,她和我介绍别人的时候,我对对方的了解会更清楚一些,这样的效果,确实让我和其他同龄人相比,记人这一块有自己独特的记忆力,只要我当时听进去的话,身边的人说起别人时,我能将他们口中的人联系起来。
母亲比去年的春节又更老一些,她正向派出所大厅走去,她将会遇到刚才那对父女,还有年轻女人的小儿子。车主和父亲在闲聊,父亲去晴隆是为了和人订一套铁门,他想先去看看,哪里有合适的。车主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向父亲推荐,派出所下面的几个做铁质门板生意的门店就有,并劝父亲在近处购买,他们负责上门安装,很是方便。
父亲等母亲回来后向院坝外走去,他们一高一矮,走在那条土路或者沥青路上……多么糟糕,那是怎样的一条路,它可能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土路了,或者镇上最近在修路,我的印象停留在土路上。我站在车旁玩手机,要么就是回到车里玩手机,我还会做点什么呢。父亲和母亲去看门板,我没有跟着去,对乘车的厌烦感,令我更加疲累。父亲回来后,说可以在镇上订门板。车主说那他们可以不用往县里赶了,等下一趟车来了直接回家。父亲和母亲感到有些歉意,车主将少挣他们两人四十块钱。
这趟车,最精神抖擞的便是在那年轻女人怀里的孩子了。他年轻的母亲,还在派出所里排队,等先于他们的人办完事情才能轮到他们取一张临时身份证。
车上的一位大娘,得知我和这对年轻的母子也去贵阳时说你们可以作伴同行,我想着我是可以给她提一下行李箱什么的。按母亲的说法,我该叫她父亲舅舅,那她自然是表妹了。到晴隆客车站,我扮演起长兄的角色,带着自己的妹妹和侄子,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和女生吃饭我最怕对方中途先去结账,我们吃饭的时候没怎么说话,她边吃边喂孩子,我看着餐室里的邻桌,想象他们如何疲累,终于能够停下来吃午餐,将自己安放在凳子上就不用管行李,将其丢在一旁。邻桌有一个孩子安分托着一碗米饭,正在将需要拉拢的米粒刨进嘴里,他吃得极为认真,他的年纪和自尊心,已不再让大人给他喂食,大人偶尔给他夹菜,他还会不好意思,扭头看看有没有人在看他。
我眼前调皮的小孩,吃一口便跑出去,到处欢。这个不安分的小牛正咧着嘴对着他的母亲笑,细小的牙齿没冒几颗。他趴在另一张塑料凳子上看着我笑。看看我的行李箱,再看看他妈妈的行李箱,他对拴在我行李箱把手上的鱼挂饰很感兴趣,我不搭理他,他料定他动手扯这条鱼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时看着我吃饭,自己倒是怎样都不开口。他妈妈百般哄他,他仍是无动于衷。我说我们吃吧,不用管他,小孩不听话就不是好小孩了,坏小孩大人是可以不用管他的。他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轻轻地笑了。她一定也察觉到,这是我开口说得最久的一段话,她看着我认真的样子,又笑了一下。她说,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我说我比她大,自然是要叫一声哥的。她叫了我一声,朝阳哥。我嘴里的饭还没有咽下去,一时无法应答。
我以前是见过她的,那时候她才八九岁的样子,年纪正好可以是眼前小孩的姐姐。她和小时候的模样变化不大,多年前的小女孩,那头青黑的马尾,跟随她的哥哥经过一口井旁。
她问我,你记忆力怎么那么好。我说,不知道。为此我会很伤心。多年后我还会记得,我今天和你同行的上午,或者即将到来的下午,还有傍晚。我告诉她,我认识的人不多,记忆也会挑人,刚好有的人有些场景,我记下来了,此后有些境遇,我会突然想起他们。她说,挺好的。她对我说,她是怎么长大的都忘了。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的在她丈夫的老家让公公婆婆带,她自己带小的这个。我看了看眼前的小孩,他终于安分了,用小勺子自己舀饭吃。我不太信任小孩,我有预感,他的安分是暂时的,等他吃饱了,我又将扮演一个不懂得带小孩的父亲了。我有些担心,我们吃完饭后,去候车室等车时,我该怎么面对眼前的小孩。我已经做好准备,我将不为所动地看他如何在人群中大哭,他的哭声把候车室的空间填满,哭声穿过陌生人的头顶,肩上,撞到离家远行的行李,不相识的人们将一同领受那喷涌的委屈,人们一同默守哭声流动。
到了贵阳金阳客站,我从客车底拿出箱子,我们打车到贵阳北站。晴隆到贵阳,两个半小时,她将手机给她儿子后,自己靠着椅背闭目。孩子终于安分了。儿童安全绳依旧扣着他们的手腕。她给他孩子打开一个动漫,调好适当音量就不再管他了。车上的电影来来回回放一部战争题材的片子,车上的音响比动漫视频音大,我便没有其他担心的了。
我们没料到在路上会堵车。车上我一直在看《菲利普·雅各泰诗选》,每次都会翻到那首《正如一个人喜欢待在忧伤里》,从它读起,随意翻阅,读到哪儿算哪儿。
正如一个人喜欢待在忧伤里
不愿换一个城市或者去流浪
我和贵阳之间的关系,我还没有找到,但我已经不想去别的地方。那次在办公室看到一个公众号推送菲利普·雅各泰的诗,读到这首,我差点流泪。之后从孔夫子旧书网买下这本绝版书。每挪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需要乘车,我在车上遇到很多人,有的隔几天或者一两个月,我们会在同一辆公交车上遇到;而每年我回家来,从没有在同一辆客车上,发现往年我们共同乘坐同一辆车的人,男人或者女人,每一年,每一个,都是陌生的。
她的孩子睡着了。她总算更加放心起来。她回过头问我,怎么不靠着睡会儿。我说不困,看看书或者想想其他事,会快一点到贵阳。她轻轻微笑转过头去。她幼时的马尾藏在我眼前这丛浅黄色的长发里,无论我怎么辨别,始终找不到。她的发丝很大部分搭在白色羽绒服上,即便如此,我还是看到了掩藏在她发间的瘦小的脖颈一处皮肤,那块肤色一直被她的头发和衣领溺爱,无论是多么糟糕的天气,它都能跟随她的脖颈无忧无虑度过整个上午或者下午,哪怕是在堵车的路途,我也没有看到那块理应被溺爱的皮肤显露出半点焦虑的神色。
我们顺利极了,至少不是堵到晚上。这是一个出门的好日子,大人们说。但依然有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事故,我们没有去想,那輛车的主人是不是想快一点躲回他所在的城市,或者仅仅只是在路上握着方向盘走神了半秒钟。下车后,我提起行李在她前面,在路边打网约车,我们即将前往北站。我坐在副驾驶位上,她和她的孩子坐后排,小孩早就困意十足,此刻正靠在他妈妈的怀里。我们又像最初从村里出发前的模样,谁也不认识谁,因此,没有交谈的必要。
我将网约车上的地址改到北站附近城区,下车后我直接去给她找住处。为了让她安心,通往酒店前台时我让她自己上前,我不可能唐突到连他们母子的住宿也安排了。她怀里抱着孩子。我只好给她提箱子上楼。孩子像只壁虎那样黏住她。她无奈地对我笑了一下,说又麻烦你了。我说小事啊,不麻烦。听到开门的声音,小孩醒了,闹着要下来,看到床就扑上去了。他妈妈对他说,还没有脱鞋。并警告他在外面给她听话点,不然她这就出门不带他了。她提议我们在附近一起吃晚饭。
晚餐时我给她回忆,她小时候如何跟在她哥哥身后,她哥哥手里拿着一根细竹枝,时不时挥手将路旁的小草小树削掉枝茎。她开心地笑起来,她不太相信她可以不声不响地只是跟在她哥哥身后,而不是去找其他伙伴玩。我说可能只是他们吃饭的时间到了,她哥哥从家里听从母亲的叮嘱,去寨中找她让她回家。她笑了笑,没有说话,举起筷子伸向离她最近的盘子,夹了一筷菜,放到她儿子的嘴里。
吃完饭,她的小儿子有些不舒服,我带她去药店买药,店主朝我问,孩子有什么症状。我看向她,她向药店老板说些什么我没有听。回来的路上,她说,你对这些地方挺熟。我说有导航啊,吃饭的时候我便开始搜附近药店。
把她送回酒店大门,她笑着说,你回去吧。
好,我说。
到了说一声啊,她说。
好,我说。
公交车上
他看着左手手链圆实的珠子,仿佛看着它们能让他心平气和起来,孩子是别人的,孩子的哭闹只能令他觉得心疼,而不再是烦躁难忍。他刚刚捂住二女儿的嘴巴,委屈的泪珠流到他手背上。他只想让她闭嘴,如果不是他手背上沾满了眼泪,他必定还想再打她手臂一巴掌。他低着头看着手链发呆,右手拨动几颗珠子,黑色的珠子像他阴郁的心情。二女儿踢掉鞋子,光着脚坐在座位上。这本不是她的位置,她先前的座位靠窗。大女儿正趴在窗口看外面车流。哭声在车内漾开,他最小的女儿听到二女儿的哭声,也在妻子的背上大哭起来。妻子无动于衷,仿佛她正是拐卖儿童的恶妇,任凭孩子在背上哭泣。她懒得拍一下她的小女儿。
他低着头看着互绞的手指,此刻他不是三个女孩的父亲,而是一个做错事的少年。他的双脚拢着一袋米,米袋上写着“稻花香米”的字样,他身上没有一个包,妻子也没有,他们的出行只是负责拖家带口这么简单。但这趟车,让他觉得很是无奈,甚至麻木。大女儿将头伸出公交车外看外面车辆和道旁树木,被他吼一句后才将脖子缩回来。大女儿一副看惯她父亲能耐的模样,一点也不惧怕他,她知道只要他们还待在公交车肚子里,她父亲的打骂就不会超出她能承受的范围。她用手指戳了一下她最小的妹妹的脑袋,她的两个妹妹还在哭,越哭越大声。
先前是她挨着她父亲坐,她的二妹挨着窗户安分坐着,她一直在逗挨着窗户的二妹,她们商量着把公交车窗户打开。两姐妹合力将窗户打开后,她们争着往窗外看,她凭着自己比妹妹壮实,仰仗多出一两岁的力气将妹妹撇在一旁,妹妹只好坐回座位上。妹妹看着她的脑袋,她看着窗外。她要和妹妹换位子,妹妹不让,她将屁股坐在妹妹的腿上,抛弃了妹妹,抛弃了她们刚才合力开窗的姐妹情谊。妹妹开始哭了起来,她想不出要告状的话,只能将不满藏在哭声里。
他一把将二女儿拉到自己身边,二女儿握住后排左侧靠窗的椅子扶手,那是她先前坐上的位子,她不愿意到她父亲这边来,继续用更大的哭腔表达委屈。他粗暴地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到自己身边。大女儿如愿坐到靠窗的位子。胜利的喜悦被她掩藏起来,她平淡地看了妹妹一眼后将目光投向窗外。她觉得发出哭声的妹妹真是太没劲了。她冷静地看着窗外,偶尔回过头确认妹妹的哭声。二女儿愈发觉得委屈,她挥动右手臂举起小小的拳头砸向她的父亲,持续砸了很多下。
做错事的他盯着公交车头显示站名的窄小屏幕,他的视力好极了,能将屏幕上的字全看在眼里,就是迟迟不出现他希望快些到达的站点。车上的人们用目光找寻哭声的发源处。他低着罪犯的头颅。公交车上的人不知道两个小女孩为什么要哭。若有人怪罪他们虐待孩童,他将毫不犹豫承认。他几乎忘了他最小的女儿的存在,那幼小的哭声,倒是很积极地制造着巨大的噪声应和她的二姐。他看不到小女儿的脸庞,她幼小的脸庞伏在她母亲的背上,她将哭声砸向她母亲,砸向公交车肚腹里的所有人。他不知道小女儿有没有流下眼泪,只要看着二女儿就知道了,他只好认为她们的泪水继承了他们族群的本能,或者别人家的泪水。三个女儿,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不出来。
妻子继续无动于衷,将疲惫的双手扒在前面女人的椅背上。她身旁坐着的女人和她年纪相仿,此时慷慨地伸出左手隔着背带拍着她小女儿的背。炎热的天气,令她有些虚弱,小女儿一点重量都没有,背着她就像背着空气,是她自身的重量将她压垮,只要孩子还在哭,她便发现,自己不会晕倒,反倒是这股恸哭的气力扶起了她,才不致昏厥在椅子上。生下三个孩子后,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胖,她不用看也知道背带将她壮实的后背勒出一个圈,如果可能,她将无比记恨这虚情假意的壮硕,她没有因这肥胖的身躯,将生活过得更好。
车厢内狐疑的眼神生出了热络的烟尘,熏得他的头颅愈来愈沉,他只好将头更沉下一些。
那袋米此刻是唯一可以给他倚靠的。先前他还曾因为羞怯,多次拒绝亲戚的厚意,亲戚说,你是嫌少是吗,他没再拒绝,从亲戚家出门时将米袋结结实实地扛在肩上。车内的眼光还在滋生热浪,车内空间,因他一家更加灼烫。他不用抬头也知道,人们不停看向他们这边。他和两个女儿坐在公交车后排,妻子背着三女儿坐在倒数第二排左侧靠窗位子。二女儿还在哭,他刚才已经将踢落的鞋稳当地套在她脚上了。
他拿她们没办法,更是拿自己没办法。上公交车前,他们没有直接从高铁站打车到市区,这一趟公交车他们坐过多次。他想起三个女儿还没有出生前,想起第一次去她家。她家坐落在一片鼓楼丛生的山区里,梯田围着木瓦房,女友家和其他人家一样,在稻田里养鱼,她们这儿的米远近闻名,每次他来到她们家,吃饭时都要说她们家的米太好吃。彼时,她向他打趣,以后你来一次让你扛一袋回去。他高兴地说,求之不得。
他将哭声置身事外,这样好受多了。他的右脚踝被一只蚊子咬了,蚊子早就飞走了,他将手里的链子擦脚踝,再次体会到手链珠子的圆实,这种感觉让他多少觉得好受一些。他抬眼看了看幼小的三女儿,她仍旧伏在妻子的背上大哭。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毅力,他只好将一切归咎于身旁的二女儿和大女儿,大女儿的沉默早就被他忽略了,像是自己从未生养过这个孩子。这样的心绪,促使他在看向妻子时,也觉得妻子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女人了,此刻她正是车厢内哪个糊涂丈夫的女人,他和她们,反正是没有关系了。
他面无表情地扫射车厢装着的其他人,站的站,坐的坐,大部分人仍在盯着他。他将空洞的眼神投递出去就没想着变换神态收回。他知道他在等什么,看着周围飘过的建筑物,他知道他就要解放了。
他终于等到车内报出最刺耳的站名。他大喊一声,下车了。他右手捏着米袋一角,他左手拍了拍正在哭泣的二女儿,以及睡着了的大女儿。他没有说话,向正在打开的公交车后门走去。他的妻子转头看了她的两个女儿一眼,她背上的三女儿感觉到她起身后停止了哭泣,伸着细小的两只手掌垫到眼睛下,幼小的女孩的额头伏在小小的手背上,她依然没有抬头。
女人从后门下车后,大声喊,下快点。她大女儿早就超过二女儿身边,一蹦就下车,二女儿颤颤巍巍在车厢内摇晃,像是先前的恸哭用尽了力气和幼小的智力,她并不知道应该扶着人们的椅背,一个青年握着她的右手臂,她才不至于摔倒。但她胆怯地抽出自己的手,继续哭,经过后门前,是几个年轻的女孩扶着她,看着她下车。
他们一家在公交车外的人行道上向前走去,像正在完成一趟迁徙。他肩上扛着米袋,再次使他看起来像一家之主,走在他前面背着最小的女儿的女人,因刚才的一声“下快点”,她看起来才不像一个哑巴。
他们一家正在用健康的步伐踩过城市的道路。
葬礼上
在持续惧怕失礼的不安中,我从口袋里掏出车票看了一下车型,“大型高二”—— 我对“大型”两字心生疑窦,我的右臂酸极了。
我借玩手机或校对稿子的正经模样弯曲手腕,尽可能收缩右臂,双手搁置腹前。右座女孩紧临在侧,我自觉垂下手臂与她紧贴无疑,哪怕隔着两件羽绒服。女孩始终以围巾蒙住鼻口,左手捏着细心折叠过的纸巾,偶尔抵住鼻端。我们都感冒了。
窄小的空间让我玩手机或者看稿子都极为不便,我只好将双手环抱胸前怀想往事。那道长长的有坡度的石梯就在这时出现了,事后我才确证,多年前我就爬过这道石梯了,其中有一次,我和外公去看人们敲铜鼓。
但那次我们是在迎接新年的夜晚前去等待,大人们说,这一天叫除夕。三外公家这道石梯至少近百年了。在小王寨的日子,在我还不懂得和大人们打招呼的年纪,遇到比爸妈大的人都喊外公外婆是不会错的。这儿的人都无比疼爱我,是我遇到过最好的人们。小王寨是不多见的最有团结心的村寨,一家有事,周围的人家都前来帮忙。这和一些大寨子不一样,寨子大了,人们奔忙于生活的方式百变,各有各的难,一有事情,很难再召回村人来互相照看了,本家间,每家出一两个人便是最难得的了。小王寨不一样,一家有事,能回来的人全都回来。
我很多年没有参加一场本民族的葬礼了。
三外公,我叫他三公。我在镇上上一年级,遇到赶集日不上学,或者上午学结束午间回来吃饭,我趴在外公在镇上供销社分到的房间窗口,偶尔会看到三公拿着带有表格的本子和他的几个同事一道经过楼下,他们在和街道上的店铺主人核对一些东西。现在我不知道以前的自己是先看他肩章還是先看他的面容,才知道那是三公。他是否抽烟,我已经想不起来。他清瘦的面容像极了其他热爱抽烟的长辈。他们那一代人很少有肥胖者。我们后辈只好认为,他们的青年或者中老年,都是勤俭节约惯了,舍不得对自己更好。
我留守在小王寨的岁月,三公定居在镇上,很少回到小王寨来,他在小王寨的老家建在小王寨大寨的石头山上,他家挨着大寨那块庞大的独立岩。独立岩旁是一幢幢木瓦房。每家都有长长的石梯通向宅院。三公家的铜鼓是小王寨唯一的铜鼓,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三公家是小王寨的老房子,里面住过一代又一代人。
铜鼓被视为吉祥的圣物。每到除夕夜,守岁的时候,村里人会请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去敲铜鼓,人们因为这个夜晚的到来感到欣喜。铜鼓的声音能让人忘记一年的琐碎,人们寄望于明年一切会更好,日子过得更踏实,田地丰收依旧,村寨人畜出行顺利,诸事大吉。
关于这个铜鼓,还曾遭遇一段波折,有人家和三公家打官司,对方说铜鼓是他们家的。他们拿不出证据,三公家的长辈告诉对方,那位长辈说,就由他来告诉大家,铜鼓上的纹饰都是些什么,鼓上有多少个圆点。对方哑口无言,这场官司的结果显而易见。
那个夜晚我跟随外公去三公家。屋里已经围有一帮人。大人们在抽烟叶子,年轻一点的人抽过滤嘴香烟,没有人说话。烟雾缭绕,人们如同置身梦中。古老的房子由古老的木材和石块建成。我看屋里没有和我一样年纪的小孩,只好独自靠着一根柱子,看他们神情肃穆地听铜鼓声。三公表情严肃地手持一根木棒,木棒沉默,只有击向铜鼓时才跟随铜鼓发声。
人们何时散去已经无法回见。这个夜晚的人们都在想什么,再没有人去回想。只要将心绪向这个夜晚靠拢,隔着一层虚空,当晚在场的人仍然能够清楚地看清铜鼓所在位置。铜鼓挂在一根粗绳上,垂落在房间里,当晚人们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听三公敲铜鼓。人们离散后,相继从长长的石梯走下,他们不用打手电筒,年纪大一些的人凭着记忆和经验,早已练就摸黑走夜路的本领。何况这是大年三十的夜晚,每家每户都在门外点上一盏灯,灯罩是玻璃制成的,大多数人家用当时常见的长管波浪流体形的灯罩,这样能够给灯芯挡风。借着这些光亮,回家的人愈加放心,就算他们已喝了些酒,这些灯光足够鼓舞他们信任醉步。
我再次走向这道长石梯,依然是向三公家走去。而此时,他已不能再在屋里为我们敲铜鼓。父亲喊来十几个本家,跟随一道前来祭奠。我是队伍里的一员,手上拿着我能拿的供品。进门前,我们已先在门外点燃爆竹。爆竹声响起,三外公家族的女性后辈,便出来候在院门旁等待客人。她们没有同往日般穿布依族的黑色服饰,而是出于敬意或者缅怀,穿上白色的孝服。
在部分我认识的亲戚中,我一眼看出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不是人群中最年轻的,她是我的娃娃亲,已嫁人两年多。我默默地从她身旁走过。我在想,稍后再过来和她打招呼。在等待父亲祭拜前,我们先去安置饭点的人家吃饭。
我还在找她的身影。二十年来,我还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到院子时我遇到了她,但母亲看到我,向我走来。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和我曾经的娃娃亲说话。
这次又错过了。
晚上,我还是想再去碰碰运气,兴许,在我的三外公、她的三爷爷的葬礼上,我能在这个夜晚碰到她呢。我找了个借口,跟随我的舅舅,从小寨送东西去大寨。在车上,舅舅双手搭在方向盘上,对我说,以后还是娶个布依族姑娘吧,你看你哥哥,他已经娶了一个汉族姑娘了,你再娶一个汉族姑娘,以后你妈妈想找人说布依话时,就找不到了。
我动用我向来对长辈惯用的小心语气说,好。我清楚,我的神情一定是那种一眼就看出的顺从或小心模样。我不清楚这种表情,是与生俱来,还是继承了基因的怯懦,父亲在外人面前,一向内敛,在自家亲戚面前,也百般客气。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爷爷,也是如此。而我的表情,我是否可认为,我只是在模仿书籍或者影视,藉以自我感动。
我已感知到一种即将降临的落寞。
我没有遇到她,那个比我大三个月的表姐,我的娃娃亲。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三公的母亲问我的母亲,她孙女的小儿子是否和人家订娃娃亲了,母亲说没有。我后来叫她太婆的老人,以一種斩钉截铁的口气说,用得着去哪里找。从那以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的娃娃亲,是太婆的曾孙女,是母亲的侄女。她比我大三个月,我记得她的名字,记得她家在镇上的位置,记得我为数不多的几次遇见,都未曾和她打招呼。
而她,在三公的葬礼上,根据我们村庄一行人判断,应该从人群中看到了我。一个在她婚前,名字多少和她有些关联的异性,那个陌生的名字,或许偶尔会被她的亲人提起。
胆怯的少年长成青年,依然没有和那个女孩说上一句话。
在三公的葬礼上,这天被我们这边的人称为“开堂”,我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人们的哭声。我想起我的表妹,她刚出生的夜晚,我没有听到她的哭声。因为那个下午或者傍晚,我和一个幼时玩伴,企图去等待我姨娘生孩子,被大人赶走了。我已经想不起,那是三公分到的房间,还是姨娘自己在那个院子租的房子。那个院子基本上住的是鸡场镇税务所职工。我们还想继续等下去,但大人们已经嫌弃过我们了。我身旁的小女孩闷闷不乐地说,不让看就不让看,有什么稀奇的。
之后我在某个高中女同学的面容上,寻找到那个遥远的小女孩的容貌。某一刻我终于在网络聊天工具上问她,你是否在鸡场镇上过小学?她说她没有去过鸡场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