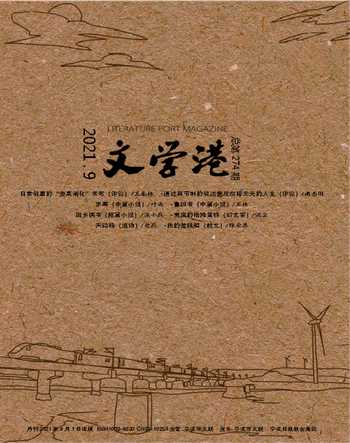岛上影剧院
虞燕

一
岛上的影剧院四面皆是台阶,这座庞大的建筑物被高高抬起,众人望向它,不得不微微仰视。在影剧院正式开放之初,少女时的小姨就带我去过,小人儿惊诧于里面的空间之大,脑袋拨浪鼓似地来回转。很快,灯熄了,嘈杂声消失,像有谁把黑暗撕开,露出巨大的长方形“豆腐块”,光影扫过密密麻麻的人头,明明灭灭。我的新奇劲撑不到四分之一场电影,遂将脸蛋埋进小姨怀里呼呼大睡了。
我得以真正亲近影剧院,是上了小学之后。每年六一节,学校都会组织去影剧院看演出,看电影,那个广阔的空间被稚嫩的身影和声音充盈,闹哄哄,乐淘淘,空气一直在膨胀。顶上所有的灯开着,光线四处散射,每一张脸都那么明媚。大家紧攥着粉色或浅蓝的电影票,找寻自己的座位,找到了却又不好好坐下,像一只只松鼠那样窜来窜去,地上的影子重叠又跳开,欢腾得任性。
老师吹响了口哨,尖利的声音戳破了膨胀的气体,孩子们自然心领神会,纷纷各就各位,如一颗颗散落的棋子终于回归到棋盘的合适位置。我早就瞥到角落里提着筐的老师们,筐里是儿童节的福利,每人一份奶油面包加果汁露。叫奶油面包,其实见不到一滴奶油,应该算一种最普通的软式面包,但在当时的我们看来,那简直是珍馐美味,那么松软,那么香甜,令人愉悦的气味分子迅速渗透、扩散,彼时的影剧院竟如此亲切而温柔。直至今日,我见到与之相似的面包,就会想起儿童节,想起岛上的影剧院,想起那微小的妙不可言的幸福感。
舞台是高傲艳丽的贵夫人,只可欣赏,难以接近,其左右两边各有台阶,仅供演出者及相关人员通行。绛红色丝绒帷幕上镶了金黄色流苏,每一回的拉开与合拢,都是流苏的起舞。帷幕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就那么一拉一合,便生生将影剧院分成了两个世界,台上流光溢彩备受瞩目,台下灯光幽昧面目混沌,却又是联系紧密的两个世界:台上报幕完毕,台下掌声响起,台上表演结束,台下掌声再响起,那种自觉的呼应总能让气氛热烈起来。
节目由每个学校选送,表演者几乎全是学生,即便那些演出并不專业,也并不盛大,甚至还有点拙劣,但每次都充满期待。之所以期待,其一,在我的童年和少年里,能坐在影剧院看演出的机会实在不多,有得看当然不想错过。另一点显然更关键,那就是表演者里有我熟悉的人,确切地说,是我的同学,原本和我一样普通的人摇身一变,成了舞台上的明星,是的,明星。化了妆,穿了表演服,往台上那么一站,自信而耀眼,我会把目光牢牢地粘在她们身上,从那个节目开始到结束,舍不得开一点小差。
在当年的那些演出里,《手拿碟儿敲起来》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我心里闪亮了许多年。表演者七八人,统一的粉色衣裤,黑色镶金边肚兜,个个手持盘子筷子,画得脸白唇红。我的同学巧燕和克男也在其中,巧燕是领唱者,站在中间位置,“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一开口,声音清亮,感情饱满,一双灵动的眼睛顾盼生辉,再配以恰到好处的敲击盘子声,简直艳惊四座。我完全忘了啃手里的面包,身子与脖子最大限度地前倾,恨不得整个人贴到舞台上去。周边传来夸赞声,来自老师和大人们,我才顾不上他们呢,我正被一种轻微的眩晕感攫住,如梦似幻,仿佛所有的声音已汇成了江河,我在其中沉沉浮浮,晃来荡去……
一曲终了,我迟迟回不过神,直到巧燕和克男下台来,两个粉雕玉琢般的人儿如此熠熠生辉,在我眼里。那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跟她们隔着跨越不了的距离,羡慕和沮丧同时袭来,令人发慌,令人无措。究竟为何沮丧?没法说清。也许是因为羞怯的灰扑扑的自己,也许是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更没有机会上台“辉煌”一把。
的确,直到多年后影剧院成为危房被拆除,我连舞台的边都没碰到过,倒是我那个胆大粗莽的弟弟曾像模像样地上了回台。那年的国庆汇演,他和另一个少年表演霹雳舞,戴着黑色半截皮手套,穿着当时流行的旅游鞋,又是太空步又是疯狂打转又是遭了电击似地扭摆抽搐,看得人心惊胆战,生怕他一轻狂就出了糗。他呢,偏偏无所畏惧,卖力炫技,我挺起脖子紧抿嘴唇,一动不敢动,舞台的灯光像是打在了我身上,闪得晃眼,又辐射得人微微冒汗。喝彩声突如其来,这一惊吓,害我原本跳得好好的心脏猛地栽了一跟头。直到表演顺利结束,我才舒了一口气,弟弟这个节目真是漫长啊。
似乎做过一个在影剧院献唱的梦,梦里的舞台异常的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我怯怯地拿起话筒,却怎么也唱不出声,嗓子和身体都跟我拧巴着,令我动弹不得。而台下开始骚动起来,嘈杂声愈演愈烈,海浪般涌过来,涌上了舞台……醒来时,我的身体正绷成一张弓,再用点力,就要拗断了一样。恍惚间,想起刚刚的梦,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忧伤。
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岛,精神生活相对匮乏,影剧院一出现,自然就成了炙手可热的福地。鼎盛期,基本上每天都放电影,有夜晚场,也有白天场,影剧院外墙及台阶下的某些特定位置,一张张电影海报如花枝招展的姑娘,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赚足了眼球。
《南北少林》《黄河大侠》《海市蜃楼》《黑楼孤魂》《妈妈再爱我一次》《青蛇》……那些电影像神奇的调味品,竟让一个个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而隽永。到影剧院看电影从赶时髦变成了一种常态:闲来无事,去看场电影;过节过生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看电影;渔民海员好不容易上岸休息,陪家人看个电影;客人来了,要不请看电影好了;羞于向心仪的人表白,那委婉点,先从约看电影开始吧;正式谈恋爱就更不用说了,不看上十来场都显得不够甜蜜不够有诚意……
影剧院的繁荣让很多人看到了商机,周边开起了各种店,形成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小商圈。有个别脑子活络的,在边上随便支了个小摊,生意居然不错。这下好了,引得一些原本沿街叫卖的摊贩,还有在轮船码头等地摆摊的,也都不甘落后,纷纷赶了过去。摊位犹如顽强的可移栽的花儿,一朵朵一簇簇地盛放于影剧院台阶下的空地上,一时之间,那里喧闹如菜市场,麦芽糖、炒瓜子炒花生、糕点面包、爆米花、水果等美食摊位是主力军,若是夏夜,当然还会有冰棍雪糕和木莲羹,此外,还有修鞋补鞋的,卖玩具和生活用品的……经过时,常常可见遍地的甘蔗皮、桔子皮、瓜子壳、糖纸,这个场景好像有点向人炫耀的意味:看,生意还行哦。
那会没有收摊位费这一说,今天你去摆,明天我也去摆,生意嘛,来一笔是一笔,赚到才是真实惠。在很多人眼里,影剧院大概就是一颗大蜜糖,凑上去,总能尝到甜头。
母亲也动了心思。家底薄,过日子从来精打细算,若有增加额外收入的机会,不抓住难免不甘心。父亲是海员,具备在外采购的便利,那些年,父亲从全国各地运过大白菜、螺狮、海蜇、芋头、莴笋等到岛上,而后跟母亲一起去菜市场贩卖。那些东西要么是岛上稀缺的,要么价格低廉,总之,须得有赚头。去菜市场卖货,凌晨四五点就得出发,冬日的海岛天黑如墨,寒风似冰冻过的刀片,刮到身上,寒气一下子沁进了骨头缝里,冷到发疼。好几次,借着屋里的灯光,我在门口目送父母亲或挑着担或推着木头手推车走出院门,他们脚步坚定,说话声不大却透着难掩的兴奋,一忽儿就消失在转角。
去影剧院那里卖什么好呢?不能任由自己选,得看父亲是否能采购到合适的。也亏得父亲活络,找到了金桔和柿饼。当时,岛上还没有柿饼这种食品,那么甜糯可口,我跟弟弟吃了还想吃,被母亲拦下,她把装柿饼的大塑料袋用布条紧紧扎起来,而后拍拍塑料袋,把我们搂了过去,说等赚了钱,让父亲专门买来给我们吃。
木头手推车又派上了用场,一大袋柿饼,一竹筐金桔,还有一杆秤和一把小凳子装于其上,母亲头戴新毛巾,握住手推车的两个手把,向影剧院进发。在那块空地的小摊圈,母亲属于后来者,她有点难为情地挤了过去,推着车,小心翼翼地挪动,生怕碰到别人,然后,在一个不大起眼的角落停下。那里的摊位都是不固定的,谁早到谁占,但好多次,母亲就算去得早,也依然老老实实地守在边边角角,她说,抢占好位置搞不好会成为众人眼中钉的,就是做点小生意,伤了和气就不值当了。
影剧院里,上演着各种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影剧院的台阶下,是真实人间的一角,每一张脸多多少少透露了其生命的本相,平静,沧桑,热忱,悲苦,从容,隐忍,坚韧。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小摊中,有个补鞋的男人尤其显眼,棕黄色的围裙裹住了半个肥胖的他,围裙下露出的一条腿向外翻,且比另一条细小,他补鞋用劲时,小木凳偶尔会发出“吱扭”声,真担心会因承受不了他的体重而散架。男人是那里出勤率最高的一个,修鞋技术不错,积攒了一定的口碑;他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仿佛面部表情一放开,皮肤会破裂一样。
母亲的摊位跟她的为人一样,不事张扬,静静候于角落里。多数时候,她就倚着手推车,微笑着看眼前的热闹,那块边上印有碎花的毛巾戴在她头上,既遮了阳,又平添了几分俏丽。也许是母亲长得漂亮又和善,也许是货品着实吸引人,反正,每天不至于空跑,总能卖出去一些。
有一次,老天突然变了脸,一场大雨下得猝不及防,各摊主如受惊的小动物,纷纷逃了开去,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得跟密集的雨点比速度。母亲推着这么一辆车,哪里跑得动,只得把备着的雨衣盖在货品上。柿饼虽有塑料袋装着,就怕万一出现破洞,哪怕是小小的一个,水一渗进去就完了。母亲到家时,浑身湿透,走一步,水泥地上就出现一小摊水,她匆忙抹了把脸,揭掉雨衣,紧张地查看,挂了霜的柿饼一个个在塑料袋里躺着,像躲在全封闭式帐篷里,很干燥,很安全。母亲这才长长吁了口气,去洗澡换衣了。
那场雨让母亲感冒了一场,她护下来的那些柿饼后来都卖光了。母亲兑现了承诺,让父亲出海时特地买了柿饼,让我们姐弟俩吃了个够。而母亲,在影剧院存在于岛上的那么些年里,却从未想过要进去看一场电影,电影票得花钱买,舍不得。可她曾离它那样的近。
三
影剧院的衰败和某些新事物的兴起仿佛是一眨眼的事。
录像厅、OK厅、舞厅、闭路电视,相继盛起,好似海风从哪吹来了它们的种子后,迅速在岛上各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从此,海岛的夜晚颇有了点灯红酒绿的味道。
喜新厌旧也好,逐新趣异也罢,反正,影剧院终究是被冷落了。某天,我去轮船码头,经过影剧院时,竟有些不敢认,它是趁我不備急速老去的吗?变得灰败、颓靡,“长涂影剧院”五个字像被谁用力搓洗过,旧旧的,软软的,让人担心风一吹会“啪嗒”掉到地上,原先那么气派的台阶看着低矮了不少,细长的裂痕弯弯扭扭爬了上去。曾经,那可是岛上最气势恢宏的建筑物啊,在我心中高高耸立,睥睨而向,这样的落差让人伤感。
影剧院也在寻找出路,开始承接一些专业或半专业的演出活动,演出团队均是外面来的,具备一定的水准。酒香也怕巷子深,好酒还得勤吆喝,在当时,贴海报是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不但影剧院周边,各单位大门、菜市场、商店、路边、村口等也都张贴了演出海报,图片和广告词做得相当抓人眼球,以吸引人前去一观。那些演出委实为影剧院短暂地拉回了点人气。
那年,在本岛上高中的弟弟放了暑假,闲来爱去街上转悠。某日,他对海报上关于小矮人的演出产生了浓厚兴趣,非怂恿我一起去看。想了想,我还从未看过正儿八经的演出呢,且真的有很久没进影剧院了,那就去瞧个新鲜吧,票价也不贵,十块一张。
白天,看演出的人还真不少,黑压压涌进去一大片,小矮人这种特殊群体引起的关注度总会高一些。待坐定,我随意抬头,心里蓦地一惊,影剧院墙上和顶上竟出现多处裂缝,有两处尤其醒目,长而宽,像丑陋的扭曲的疤痕,张牙舞爪的,又像被武侠片里削铁如泥的剑狠狠劈过,总感觉那半个墙要倒下来。我有些恐慌,死盯着那条裂缝,越看越觉得其幽深,且正在慢慢扩大,真怕有什么东西会突然从那里面跳出来,我的背上一阵发凉。而头顶的灯,坏的坏,破的破,亮着的那些,发出的光也不透亮,蒙上了很多灰似的。要不是有那么多人在,我肯定要逃走了。
老人说过,房子长期无人居住就没有人气撑着,容易坍塌。影剧院也如此吧?那一刻,我就有预感,这座1200平米左右,可容纳700多观众的影剧院恐怕撑不久了。
演出开始了,台上的热闹暂时消减了我的恐惧。不知道演出团队是怎么找齐那些个罹患侏儒症的人的,六七个小矮人呼啦啦一字排开,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一出场就来了个火辣辣的劲舞,他们短小的四肢踩着音乐节奏卖力地伸、蹬、跳、挥,自信又滑稽,台下顿时如开水烧沸了般,热烈,喧嚣,尖利的口哨声刺得我耳膜发疼。小矮人们表演经验丰富,很会调动场上的气氛,出场舞过后,他们或两人一组,或三个成团,唱,跳,相声,小品,弹奏、小杂技、换装,无缝衔接,如陀螺般不停歇地转。惊叹于那些小小身体里竟蕴藏着如此大的能量,我莫名想到了河边常见的一种草,茎细而韧,擅蔓延,看起来那么微弱,一不留神,却占领了一大片土地。
其中一个节目,又是他们合体表演的舞蹈,看得好好的,忽地,前面的人约好了似地全站了起来,随之,哄笑声四起,整个影剧院回荡着“嗡嗡嗡轰轰轰”的声响。我懵了一会才搞清,是小矮人们整齐划一地倒下去了,打转打滚,各显神通,原本体积就小的他们一打滚,人们怕看不着,索性站了起来。他们表演得尽心尽力,鲤鱼打挺,简直能听到肉身与舞台相击的“砰”,听着人一阵发疼,而丑化自己以逗乐观众大概已是必备法宝,无论是扮作乌龟爬来爬去,还是翻各种搞怪型的跟头,观众很开心,他们看似也很开心,昂着泛满油光的脸,堆着笑接受那些善意或恶意的笑声和掌声。他们身上的白衬衫几乎被汗水浸透,好像舞台是游泳池,他们刚游了一圈上来,舞台的灯光恶作剧般散射着,晃耀着,我看着台上的人,身高一样,装扮一样,面目似乎也一样,让人怀疑是不是批量生产出来的,他们如若不是聚集起来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又会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下场时,他们也不走寻常路,本能地拿出了逗乐的各类小绝招,台下果不其然响起一片起哄声,声浪汇聚一起盘旋而上,撞在墙上和顶上,碎得七零八落。我再次看到了那些裂缝,弯斜着,沉默着,幽昧又忧伤。
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进入岛上影剧院。此后,陆续传来它越来越不景气的消息,最终,电影票甚至卖到了一块钱一张。影剧院被拆除时,好些人去现场看了,都挺兴奋的,说马上会建一个鲜亮的大超市。我没去,我在心里默默送别,就像送别一位伤痕累累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