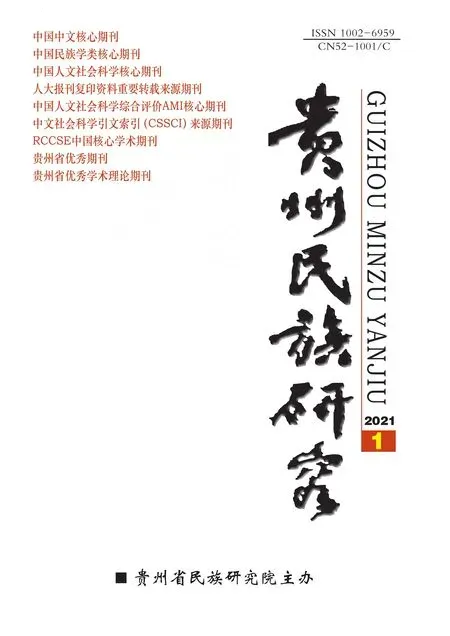侗族古歌创作观念研究
王 红
(广西大学文学院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同步发展”是21世纪民族文艺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1](P71),民间文艺思想虽然还不具备独立的理论形态,“大都蕴含在民歌、传说、故事之类口头文学作品之中”[2](P39),但学界越来越关注其研究,涌现了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王佑夫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批评卷)》、宝音达《简析少数民族文论中有关文学功能的论点》等成果。作为桂、湘、黔毗连地区的侗族先民“以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方式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和生产生活的诗歌创作”[3](P2),内容极其丰富,目前学界仅研究了一些古歌作品所呈现的宗教信仰、集体记忆、社会价值等,而对侗族古歌的艺术创作规律、创作观念相对涉及较少。侗族古歌[4]特别是一些古歌的歌头、序歌、尾声歌等集中体现了侗族人民的创作观念,侗族古歌在艺术本体、编创传承、文本构成等方面的理念是侗族人创作观念的呈现,又是这些观念的运用。
一、诗缘史论:古歌的发生学观念
诗歌本质是中国古代文论较早探讨的问题之一,一直存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主要观点。就创作观念的呈现而言,侗族古歌涉及到古歌的艺术本质问题即“古歌是什么”,包含古歌的创生过程及其规律。
侗族古歌的产生有三大特性,其一是缘事而发,侗族古歌大都是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体事件,结合创作者的亲身经验,融会其感受、体悟而形成;其二是集体性创作,侗族古歌的形成是族群的集体性智慧,这决定了侗族古歌中的事件对象并非私人事件,而是族群共识性的普遍性事件;其三是时间锤炼,侗族古歌的集体性创作并非一次性行为,而是立体与连续线性时间相统一的艺术行为,侗族古歌中的事件对象是一些有长度的已发生的事件,或者是一些业已发生的、具有发展持续性的事件。综合此3点,侗族古歌中的事件对象本质上就是历史的呈现与展演,侗族古歌源于史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历史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事件,这也是侗族古歌的核心构成。族群历史成为古歌表现的主体对象,即侗族古歌创作审美情感的发生源于“事”,如《盘古开天》点明古歌唱述是为了“追溯往事”。《侗族祖先哪里来·祖公上河》指出古歌唱述可缅怀祖先:“高山泉水润心胸,喝水不忘老祖宗,侗族祖先哪里来?古歌里面有传诵。”侗族古歌因为事件而产生,留下了侗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复杂因素制约的印痕”[5](P19),事件存录在古歌中,事件是古歌的本源和逻辑发生起点,体现了古歌起源于族群史的创作观念,类似《嘎斗莎》 (《祭祖歌》)“在尚未发现文献专载侗族社会历史的情况”[6](P85),呈现了古歌所具有的记史、存史价值。感事而发并不是社会生活事件的复制,其中史蕴诗心,展现出侗族族群对历史事件的体验与认知,一是事件的选择性及对事件发展动态性的关注。如古歌书写了烧烟火、滚磨盘、奔跑追逐等兄妹婚考验的世俗化场面来呈现血缘婚历史,呈现侗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同胞友好相处、族际和谐的传统以及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品质,“体现了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精神”[7](P103)。古歌的历史主要以人们的生活遭际为叙事,叙述重大历史事件也侧重展开生活细节的叙写,而这指向的是对历史宏大叙事的背离。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显著特征,同一题材的古歌会有不同异文,《侗款·恢复祖先俗规》唱述“同是一支耶的底,各人的歌词不相同”,如迁徙古歌在侗族地区形成了来源广西梧州、江西吉安等不同的迁徙源头记忆。古歌所构建历史不是单一的叙述,而是多个文本的反复言说、唱述,形成了对同一段历史较为多向度的呈现,侗族古歌书写的历史事件是侗族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践,是有长度的事件的复数集合。二是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侗族古歌的认知源于生活经验,它并非先验的、逻辑的,而是立足于自身对于事件的感受体会之后的经验理性。所以历史是古歌情感体验认知的对象,而古歌反过来又成了侗族认知的实践形式与艺术显现,充分显现了心灵史与社会生活史的融合。具体说来,侗族古歌致力于建构侗族历史,记录事件,呈现侗族人的思想情感。就表现对象而言,古歌事件描摹动作行为,如《萨玛耶》描述了杏妮数次挥刀对抗地主、官兵的举动,塑造为民请命、不懈斗争的女英雄形象,后被尊为萨玛神,“是祖先崇拜与英雄崇拜的复合体”[8](P92)。侗族古歌在明确人物的民族精神、事件的意义取向基础上,塑造、还原人物代表性的行为动作,这些行为动作成为侗族文化精神的具体展现,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举止的模范与标榜。就表现本质而言,古歌事件表现精神情感。侗族古歌反映了古歌的事件记叙实际上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显现,内心情感是古歌的本源、母体。同时,由于没有文字也无法掌握文字,侗族先民诉诸口头传统表达情感,古歌成了他们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古歌的事件就寄寓着他们的情感,“以人生体验传达情感,以生命之旅通达人生之真”[9](P118)。《歌师传》提出诗歌要以情动人,要有“吸引人的力量”,使人“心服肠软”。古歌还要表达内心情感,且多表达悲情, 《卖女歌》 《秀银吉妹歌》《吞烟崖》等指出古歌是侗族人“叹苦情”“诉苦情”的表现。历史事件是侗族古歌最本源的因素,基于生活的思想情感活动是古歌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侗族古歌是侗族民众生命活动的产物与体现,呈现出古歌情性本体、生命一体的建构原则。就表现功能而言,古歌的事件诠释具有价值意义,呈现出实践精神的思维方式,《朱郎娘美》希望侗族人反思历史:“朱郎娘美悲欢离合破镜重圆多难苦,恩恩怨怨冤仇悔恨谁是祸由根?一件奇事从流传到今世,是非功过真假虚实有谁评!”古歌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据清末怀远侗汉民众抗击政府事件编唱的《刘官乱三江》指出唱歌可“解心闷”,“唱支歌来解心闷,唱唱清朝年间的苦情”。开堂歌《饭养身来歌养心》指出歌谣涵养人性:“饭养身来歌养心,草养羊群水养鱼。”古歌具有精神食粮的价值,与人对生命的思考紧密联系,彰显出侗族歌谣的“民间性”和“神圣性”[10](P153)。
其次,古歌中事件的长度与连续性意味着古歌表现历史的纵深度及其规律。侗族古歌中的事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民族之事如人类诞生、事物起源、民族诞生与迁徙及风俗生活等,如《天根地根》 《人源歌》 《侗族祖先》 《九十九公破姓开亲》等篇目;一类是个人之事如个人英雄业绩、爱情婚姻,如《吴勉歌》 《吞烟崖》等篇目。这两类事件往往以民族之事作为唱述的主要内容,个人之事的唱述基于民族历史背景,或交织着一些民族之事,如《吴勉歌》 《妹道》等篇目。一方面,从鸿蒙之初到人生初创到阶级社会的进程,从生产生活到物质生活到风俗生活,古歌唱述了侗族发生与发展史,链条式地展现侗族人的人生画卷,如《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形象地反映侗族的来源、制度、迁徙等,堪称“侗族口碑相传的、诗体的《三皇本纪》 《五帝本纪》”[11](P3)。《侗族祖先哪里来》唱述侗族人的“往事”“根底”,从神话想象逐步接近史实,各部分相对独立又可串联在一起,历史叙写呈现出连续性、涵盖性与包容性。另一方面,在历史书写的选择性传达出侗族人的情感意志和思想观念,侗族古歌主要选取了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代表性事件,如《吴勉歌》 《吴金银歌》唱述明、清时期侗乡抗击朝廷、争取自由的典型事件,《歌师传》涉及清末黔湘桂地区13位歌师的16部作品,是一篇“侗族诗史诗评性质”的作品[12](P102)。古歌的历史呈现主要是以点带面,并在古歌记叙中,投射侗族人的思想情感、人生反思。侗族古歌建构历史、陈说事实,“自我形成、自我书写、自我参照,不以任何他者为中心或边缘”[13](P253),涉及侗族的历史进程、众多领域,显示了侗族古歌的表现长度与宽度,且在历史叙事中以代表性、典型性事件深入探讨民族发展、人文精神,显示了古歌的表现深度。
因此,侗族古歌体现出了诗缘史论的发生学观念,可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古歌蕴含的历史论观念。历史是基于业已发生事件的体验与认知,不仅在于社会生活的宏大叙述,也体现为对于生活琐碎的刻画描摹。情感体验是历史理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构成了历史的活性要素,意味着历史发展的非理性特征,表现了历史自身的生命本位与立体有机性。二是古歌蕴含的艺术观念。以历史论观念为基础,侗族古歌从民间底层生发,古歌在事件的书写中呈现侗族民众的内在精神活动,或是激烈情感的强烈迸发,或是细腻情感的娓娓诉说,呈现了情、事、史结合的宽度与深度,是侗族人生命自然变动的外在呈现。在这个意义上,侗族古歌是侗族人的生命韵律节奏的艺术表达,具有生命精神涵养的艺术属性。古歌是心灵史,也是社会生活史,呈现了古歌可以感发历史进而建构历史的创作观念,是以生命时间为基础的历史论与审美论的结合。
二、根茎生长论:古歌之创编观念
侗族古歌与侗族文化是双向式建构的,侗族文化是古歌创作的生成语境和艺术给养;侗族古歌又反哺文化,是侗族文化的构成要素与发展动力。因此,侗族古歌的创作——改编就必然关涉到两个方面:一是侗族文化的形成规律及其族群文化思想;二是侗族古歌自身创编的艺术规律及其艺术思想。它们呈现为古歌的生成语境、生成方式与创编规律等内容。
首先,在特定的族群社会文化语境下,侗族民间艺人的创作是为事而著,他们基于其民族文化身份,根据自己的见闻、业已发生的事件即兴、即时编创,且很多古歌初创之时往往以第三者全知视角展示事件的始末,如歌师在《李源发带兵》指出其唱述是“听人言传”,根据传说在侗族人争取自由的传统中即时创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彰显。《侗族祖先哪里来》指出古歌在事件“刚刚发生过”就全景展开侗族族源、迁徙等唱述,强调内容的及时性与体验性,又凸显古歌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侗族古歌的创编是在侗族文化母体之中,侗族文化滋养了古歌,古歌在侗族文化中即时创编、生成,是侗族文化的呈现与演绎,同时古歌又反哺侗族文化,丰富侗族文化的人文精神涵养,而这呈现出了古歌较明显的民族文化即时性生成观念。
其次,侗族古歌的编创是稳定性与动态性的融合,即侗族古歌是族群面对社会环境之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的继承与主体即时性创造的融合。民间艺人往往会结合侗族的地理、社会、人文环境,致力于从文化根性上建构某事件/事物的来源、发展,在唱述中既有侗族人传统民族风俗、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的显现,也有侗族人的主体性创造发展。《歌师传》赞颂歌师记个的歌腔创新,“更编了十二种不同的歌腔”,而这种主体性创造一是表现对象的创新,如《禾谷耶》唱述黄狗给人类带来谷种的起源神话来解释尝新节中祭祀喂狗的习俗,反映了侗族人在从事山地农耕之时形成悠久的稻作文化,稻作生产规律的唱述“直接反映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14](P65)。 《歌师传》反映清末琵琶歌发展“黄金时期”涌现的歌师及其作品。二是表现技巧的创新,如《人源歌》异文以款词形式演述,增加了讲述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妹道》异文以妹道、老蛇等人物对唱推动情节,出现了类似人物台本的戏剧化因素。三是观念的创新,如《九十九公破姓开亲》反映款首们订立“破姓开亲”的盟约,实现了男女青年就近婚配。《吞烟崖》注入歌师对婚姻自由的赞同态度、对民间信仰的批判意识。古歌在侗族文化母体之中,会反映侗族文化的历史与变动,民间艺人在侗族古歌的创编中即时创编,呈现出表现对象更丰富、技巧更多元、观念不断更新等特征,这使古歌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这说明了古歌具有明显的动态融合发展观念。
再次,侗族古歌的编创有着相对明确的社会实践功能指向,在强调古歌之审美性与伦理道德相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其艺术价值功利性与去功利性的辩证统一。侗族古歌是侗族人思想情感的表现,民间艺人的思想情感、创作动机关系着侗族古歌的创编、展演的思想内蕴与审美取向,《吞烟崖》是清嘉庆、道光时期歌师智过因为同情悲剧人物的命运、批判愚昧的民间信仰而编创的。清道光、光绪年间歌师吴国宝的《石咸珠告官》没有全景式展演石咸珠的人生经历,而是集中编写石咸珠抗粮抗税,为民请命的举动。侗族古歌反映了歌师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基于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信仰问题的认识来编创古歌,而这些伦理道德观念不是以生硬、教条的方式,而是通过鲜明的形象、曲折的情节来刻画、显现,在情绪感染、美学熏陶以及价值认同的条件下凸显了古歌艺术的社会和合功能,“在实践的演练中将描摹性语言与日常行为、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编织成侗民族的“权力文化网络”[15](P72)。这种编创是民间艺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良好的艺术涵养的集合,是有文化根基的艺术创作,呈现了古歌较为明显的伦理美学原则。
可以说,侗族古歌编创之根茎观念的“根”主要指向文化与社会生活。在此之中,文化并非逻辑的先在存在,它立足于社会生活,诉诸于侗族人在面对生活时所激发出的情感意志与思想才华,并依次显现发生的创造性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历史的沉淀与筛选发展演变为族群社会生活的构成要素,是一种族群社会生活生态的自然循环。古歌编创的逻辑起点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双重根性。而“茎”是指编创人在植根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主体性创作。前者维系了侗族古歌编创的稳定性,后者支撑了古歌的动态发展性,二者协调共生,决定了古歌是具有相对自足、自主发展的生命有机体,也潜在地呈现了侗族古歌之“根茎生长”论的创作观念与丰富的文化观念。
三、生命本色论:古歌的文本构成观念
侗族古歌作品的构成观念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二是古歌艺术内部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侗族民间艺人依生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之间,以生命为艺术本位和核心枢纽,因而能用生命的本色言说来形塑古歌的文本构成。
首先,侗族古歌表现出生命主体对环境的自适性。黑格尔指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周围现实环境是一幅“有定性的图画”[16](P312),侗族古歌呈现了侗族人在这样的“有定性的”环境中对环境的适应,一是古歌要书写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地方性、民族性的环境是古歌中人物的活动场所,同时特定人物的活动会对环境形成能动性影响,如《根猪》唱述了养殖猪是侗族人适应环境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这是侗家捉猪喂猪的根由”。在《金银王》中,拜王滩、勇士坡、黑白路口等地名来源于吴金银起义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事迹。侗族古歌呈现了古歌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侗族地区自然环境的补给,又折射出侗族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与作为生命母体的自然有着血脉相连的契合关系,展示了侗族原初生存状态和生命感觉。二是古歌文本书写要与展演环境相适应。侗族古歌反映了古歌主要是在祭祀、婚礼、节庆及娱乐等场合展演的,如广西三江侗族人农历正月初三或初七、二月初七和八月初七要祭祀萨岁[17](P51),唱述古歌,“唱出了萨岁的劳苦功勋古根由” (《萨岁殿》)。《张良张妹》表明这首古歌在婚礼场合唱叙,“我们祝愿新婚夫妇,像张良张妹那样和睦相处。我们祝愿新婚夫妇,为人类创造文明幸福。”古歌系统的博大及其生活实践形态使得古歌在展演场域需求上具有了量与质的优势和能满足的先在性,同时古歌能够在文体学领域进行及时的符合性创造,这在本质上是古歌展演机制的艺术实践化显现。
其次,侗族古歌是生命情感的个性化自由表达。在此方面,古歌的音韵形式表现得最为突出,音韵是生命的语言镜像,它的物理性运动直接呈现出生命的情感轨迹。侗族古歌往往以音乐感极强的侗语演唱,以生命间的直接碰撞、天然和合来构建文本,进而建立歌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如开堂歌《抖一抖老虾公精神》指出“侗家唱歌有严密韵律”, 《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唱道:“让我们哟,放开丽楼那样的歌喉,追溯漫长的历史,颂唱先祖创业的盛况……我的歌声像山泉一样……”通过“丽楼那样的歌喉”即有节奏、声律的语言来颂扬祖先创世的举措,歌声如山泉的流动一样有生命律动感。古歌又将韵味视为其重要的美学特征,以韵味打动人心,如琵琶歌开堂歌《笋未长枝未成竹》指出句子“不相押韵”不是好歌。《莽随刘美》唱述:“整晚唱歌韵味来搭配,今晚摆完莽随列美故事献给大家听。”音韵律动变化更好地呈现了侗族古歌的生命情感,如《嘎茫莽道时嘉(侗族远祖歌)》 唱述“古老的歌句啊,已在我的琴板卜卜地跳荡”。《妹桃歌》唱述:“火塘烧火鼓楼暖,弹起琵琶叮咚响。妹桃嘎锦代传代,世世代代永传唱。”无论是在琴板上“卜卜地跳荡”的歌句还是在琵琶“叮咚”弹奏的嘎锦,古歌注入生命力与灵气,且有壮大雄健的“力”感。
再次,侗族古歌反映了生命群体意志的存异趋同。侗族古歌充满了生命情感的图式,探索与追问生命意义即“人之维的生命存在意义与宇宙之维的生命价值意义”[18](P119),且生命意志必须在集体认同中找到归属感方能圆满自足,是以侗族古歌尤为注重表现生命差异之后的共性和鸣,又契合于古歌源自族群而用之族群的互构理念,古歌中的集体生命意志演变为伦理道德与古歌展演的仪式化。第一,古歌呈现伦理道德。侗族古歌依托于生活,力图表现潜在的民族精神品格,寄语侗族人牢记并传承处理人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关系中所持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刘美莽子》要求侗族人不忘修心养性:“‘人勤变富、人懒变穷’这是正道经一本,奉请各位拿去常讲常做相劝众乡亲。”《风公耶》“大家都敬风公四季讲和气……风调雨顺五谷长,六畜兴旺人欢喜”的唱述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敬与祈祝。古歌呈现的是侗族人个体内在的精神操守,和与之相对应的外在价值诉求的关系的建构,以此为基原点,衍生出其道德伦理整体的多层内涵,并向社会关系、宇宙自然的和谐论进发。第二,古歌展演仪式化。侗族古歌的文本往往由文字文本与展演文本构成,《歌师传》指出“歌的本身它有吸引人的力量”,文字文本是古歌文本的基础,展演文本是文字文本的演绎与艺术魅力的追加。古歌文本的展现是歌乐舞一体的,“耶歌不论长短大家舞又唱”(《琵琶歌选·劝散场》),古歌从文本音节呈现与展演表达建构了自身结构,是音节表达和行为动作相结合的艺术结构,显示了侗族古歌的口传文学质性,同时,古歌的展演活动往往是在集体的仪式场合进行的,“同人们的一定共同生活具有直接的联系”[19](P429),在这种集体氛围中实现民族文化的反复言说,从个人展演进入集体记忆,促进集体接受,建构族群生命共同体,在侗族古歌中,伦理道德和仪式均是生命集体意志诉求的强化表现,它们是生命的规则,但因其生命的自我设定与自觉遵守而消解了其中的强制性,演变为生命归属的精神家园与强力保障。
最后,侗族古歌反映了古歌中的生命传达与文体跨界。侗族古歌的文体要素丰富,具有“跨形态性”特征[20](P39),有意象等诗体构成的要素。表现为意象描写如《猪的起源》从根源建构猪的生成,也表现为某个意象在古歌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如《娘梅歌》唱述的“鼓楼”即是娘梅带着助郎尸体去击鼓许婚葬夫来骗取银宜的地方。还表现为古歌运用意象为烘托、起兴等修辞目的,如迁徙古歌运用葛麻与根、斑竹与笋之间的关系起兴谈及溯源、追忆诉求,这些民众所熟悉的、地方化的意象通过感物、移情、移转等模式,“人的情感通过诗歌的内在节奏和意象运动得到升华”[21](P111)。古歌又注重故事情节及其完整性、行为动作及其矛盾性,但无论是哪种艺术表达方式,古歌都需要语言来传达生命情感,“编歌全靠心灵的人把语言提炼”(《歌师传》)。侗族古歌的语言特征、言说方式以及文本内部结构都以生命传达为核心,生命意志的托举高扬消解了文体学的逻辑限制,文体边界的解域消融将古歌回位于母体艺术,生命与古歌艺术互为表征,相互镜照,显现出古歌文体学的生命本体论思想。
通过对侗族古歌艺术的研究可以发现,人、历史、文化、艺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联系中,社会生活是人类事件活动的全部构成,经由时间长度与时间线性运动形成历史,历史是人—族群活动的选择性记忆与情感性认知。文化是历史的审美化表征,也是人—族群思想意志具有特定载体形式的社会实践。而以古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则是族群依生于历史、文化,在族群对社会生活经验之后,以事件行为为核心表现对象的艺术创造,历史、文化经由族群创作者给养古歌,古歌反过来创生历史与文化。而人—族群在历史、文化、艺术的哺育中定义自我,形成生命的自足与圆融,并通过相应的社会实践行为产生历史、文化与艺术。以此为基础,侗族古歌产生过程中所内蕴的诗缘史论、根茎生长论以及生命本色论等创作观念就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充满生命活性的逻辑理性。这些创作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显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