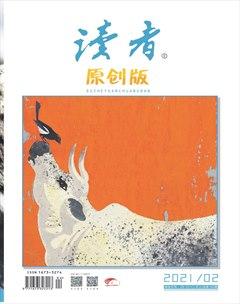向生活许愿
柴岚绮

一
在我老家,每到冬天,人人家里都要腌一些咸货—就是把新鲜的鸡鸭鱼肉用盐腌渍入味,再挂起来晾晒。住平房的时候,咸货挂在家里朝南的屋檐下;搬进楼房了,咸货就晒在朝南的阳台上。每每入冬以后,行走于街市之中,仰头一看,家家阳台上都会挑挂几串沐浴着阳光的肥瘦相间的咸香肠,以及被冷风吹瘦、吹透的一整只咸鸡、咸鸭,这是本地每年冬季必不可少的风景。
这些丰盛的咸货,一部分是寻常人家冬日厨房常备的应季风味,另一部分则被细心储存到过年,成为年夜饭的必备菜品。
从记事起,我家的年夜饭一直传承着本地的固定菜式搭配—几个热菜,几个蒸咸味,一大盘炸圆子,一锅老母鸡汤。咸味大抵有这么几样—咸鹅、咸鸡、咸鸭,再有一碟比较讲究的咸味拼盘,由切得薄薄的咸鹅肫、香肠以及咸鹅爪组成。
那时每到腊月二十九,我妈就着手清洗历经了这个冬天风霜的几样咸货,准备把它们烀熟。咸鹅身形大,肉也丰厚,即使一半也是不小的体积,所以,烀咸货必须刷净一口专门留在过年期间使用的大锅,里头加上咸鹅肫、咸鹅爪,添上足够淹没食材的冷水,将其稳当地放于炉灶之上。
烀咸货是家里的大事情,表示年夜饭已进入倒计时了。锅里的冷水渐渐煮开,开始咕嘟咕嘟冒出热气,肉食的咸香味儿也渐渐飞出锅盖,扑鼻而来,家里所有的角落都会被这股特别的香气瞬间填满。
把烀熟的咸货切好、摆成漂亮的一盘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年夜饭讲究食材,也讲究刀功—这时候,就该我爸出场了。那是大年三十上午,木制大砧板和磨过的斩骨刀都已洗干净且被开水淋烫过,拿到桌上,我爸还会取一个小锤子来,再端来大盆烀熟的咸货,对照着手写的年夜饭菜单,把需要派上用场的一样一样挑出来切。
我爸会对着咸鹅端详一会儿,寻找合适的部位下手。一刀下去,往往只能切到一半的位置,这时他就会很有耐心地用小锤子敲刀背,一点点把刀刃敲下去,确保斩出来的切口整齐美观。咸鹅切好以后,码在有红色花边的瓷碟里,鹅皮朝上,一块儿压一块儿地码好。此时,他会站远几步,就像他平时写毛笔字那样,搁笔后会离得稍远一些再瞧一瞧,这些都是他的“作品”。
咸味特别下饭,年夜饭的前半场,它们往往是“摆设”,等到上主食后,它们才是备受瞩目的主角。我和哥哥会各夹上一块儿早已看中多时的肉多骨头少的咸味,一口咬下去,唇齿间立即渗出一股美妙的咸鲜味,赶紧追一口甜丝丝的白饭,这大抵就是过年的滋味了。
二
再后来,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扩张为八口人—我和哥哥各自成了家,且都有了孩子。此时我们的饮食主张也随着观念而改变。受本土饮食口味多年熏陶,我们都挚爱家乡这一口咸味,但还是会频繁对爸妈宣讲“咸的东西不宜多吃,最好吃清淡一些”。我爸那张手写的年夜饭菜单就这样被我们改良了,咸味的分量减少,增加了鱼虾和各种蔬菜。但每每吃到最后,压轴出场的咸味拼盘还是年夜饭桌上最受青睐的“明星”,仿佛只有它们上桌,才是完整的年夜飯。
我家传统的年夜饭菜谱虽有所改动,但也有永恒不变的三道菜:一道是青菜豆腐,取俗语“青菜豆腐保平安”的寓意;一道是炸糯米圆子,图一个“团团圆圆”的好彩头;还有一道红烧鱼,表示家里“年年有余”。一年一度的年夜饭,是借由食物虔诚地向生活许愿。
我丈夫的老家在外地,自成家后,我和丈夫就约定好,两边轮流过年,今年在他家吃年夜饭,那明年就去我家—毕竟是一年到头最受重视的一餐饭。我与我父母住在面对面的两个小区,离得近,常在一起吃饭,但每到快过年时,我爸也会突然发问:“今年是不是轮到在我们家吃年夜饭了?”“哎,爸爸你忘啦,去年我们是在这边吃的啊。”“哦,不记得了!”他一脸认真。
三
在我家,年夜饭的掌勺大厨一直是我妈—从进九后忙着腌制咸货,到腊月开始预备年货等,围绕着大年三十儿这餐团圆饭的事,几十年来,都是她操心与忙碌着。即便我有了孩子,即便我早已年过不惑,在她眼里,我还是“不会忙年夜饭”的孩子。
这几年,妈妈渐渐开始“忘事”—忘了按下电饭锅的煮饭键,或者等吃完饭才发现锅里还有一盘热好了没端上来的大菜。这位总嫌弃儿女不会做事的老太太终于在某一天服老了:“有时看着那么多菜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好,以后的年夜饭就给你们做吧,我们老了,吃一口热的就行。”
平时只晓得七嘴八舌提意见,真等到全权做主,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手忙脚乱—糯米圆子是怎么做的?青菜烧豆腐里的豆腐要先煎吗?老母鸡买哪里的正宗?常责备妈妈不懂得让自己歇一歇,等到自己亲手操持,才知晓三餐不易,做一桌既传统又有新意的年夜饭更不容易。
每年,无论我们在哪边吃年夜饭,虽然吃的是不一样风味的饭食,但环绕着的是相同的氛围—满桌好菜,酒杯斟满,身边俱是至爱的亲人,这一年的奔忙且统统抛置一边。那一刻,坐在桌前的我总会有片刻的出神。从我归属的这个叫作“家”的小小窗口望出去,大地之上,万家灯火,每一扇亮灯的窗户后面都有一户平凡的人家,都拥有这样一张叫作“团圆”的饭桌,每一个家庭都怀着同样的心情和同样的祝愿—那种心与心强烈共鸣的奇妙感觉,是每年吃年夜饭时最触动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