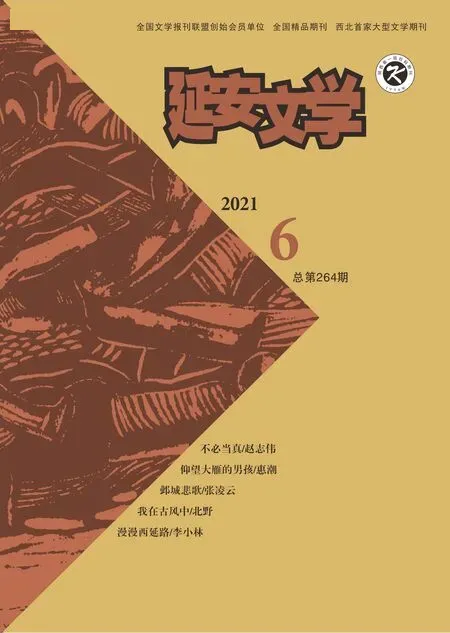运移是一种素养
——简析崔完生诗集《所有的可能都叫运移》
田永刚
“我手写我心”是写作者最基本的特质,是“诗言志”由动力转化为显现的“发乎情、止乎礼”的过程与结果。在现实的大背景下,这种表现力就是一个诗人该有的素养。而在崔完生的诗集《所有的可能都叫运移》(以下简称《运移》)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素养,就是记录时代、关注生活。
一个文本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一首诗歌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其最核心的,永远是作者的立场、情感和思想。从文本上讲,《运移》作为一部石油题材的诗歌选集,对抽象的工业术语、科技名词、现场存在进行诗意的书写,意象序列中的设备、器械、技术、工艺与情感、情怀有机融合,让物与我在诗行内外彼此相关,又彼此相忘。在熟悉与陌生的临界点上,把工业化、现代化与普通人的日常同轨并线,让诗歌一次又一次触摸到地层的温度和地表的激情。如果说文学是我们思想的化工厂,那么工业就是现代文明的催化剂,把生活这个原材料加工成为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必需品。尽管文学质涵万事万物,但在具体的结合中,受限于题材、文本、环境、意象等等因素,尤其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歌,与工业的结合有先天的间隙,甚至带着些许牵强和空泛,即使刻意溶解中也大多因为形而上而备受质疑与白眼。作为一个浸淫诗歌多年的诗人,崔完生并没有忌讳这些,因为和写作同龄的,是他在石油工业中更深的沉入和敏感,他有足够的火候和功夫,来探索、寻找、驾驭石油工业和诗歌之间的切口,并从中发出牵一发动全身的穿透力和观者同吟的感染力。
第一个切口,便是工业中的人。一百多年的石油开发历史,诞生了诸多名留青史的人物,比如《梦溪笔谈》的作者、第一个命名石油的沈括。
他知道石油很重要
有一天会“大行于世”
他却没有预测到石油以后会成为
大地上巨变的根源
他也没有预测到
自己仅仅是多看了石油一眼
就成为了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
尽管那一眼
只有发现
没有贪婪
——《沈括》
还有毛泽东曾亲笔题词的陈振夏……但更多的,是那些支撑石油的普通人,比如小媳妇大姑娘组成的女子采油队,比如井场种菜的人,比如父子或夫妻石油工这样的特别群体,还有那么多我们身边的“巨人”赵根、宋杰、米强、雷东虎等等,他们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他们微小的表情和经历,都成为了诗歌的语言和情感,而这些日常的或欣喜或疼痛或纯粹或慌乱甚至微不足道的人物,阳春白雪中嵌入下里巴人诗意的光芒,定义里枯燥、干涩的工业被鲜活的人物在诗歌里解构、重组,然后以一体化的方式呈现表达出来。
第二个切口,是工业中的事。没有一个个事件,就没有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石油工业中那些广为人知、不为人知的事件,譬如夜晚的井场、油区的慰问、巡线的工作、想家的女工,还有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的诞生、怀想中的革命战争年代、扶贫的故事等等,一件事和时间的化学催化,一群人和一座座山的对话,一个个情景通过文字的诗性再现,让我们感受到时代里石油工业的变迁、石油人的变迁、与石油相关的我们生活的变迁。诗歌记录生活反映思想的艺术追求和文化传承,也得到了重现。
把时光的电池卸下
让时间停在1907年的秋天
停在一个名叫延长的县城边
……
我来拜谒这地下的火焰
刚刚一低头
就听见铁器的摩擦声自地心传来
抬起身子
阳光的雨瀑就刺痛眼底的渴念
这是大河流水的拍岸
还是我追逐浪花的晕眩
我每一次瞻仰后
都要把那块取出的电池安上
让最先运动的秒针
去跑着告慰刀耕火种的祖先
——《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
第三个切口,是石油工业的力量。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既可能是隔行如隔山的阻碍,也可能是因为深处此山中的迷障,尽管,它们已经很深入地融合进了我们的世界。石油,就恰恰拥有这种力量。石油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它的存在,但大多数人对它的认知仍然处在概念之中,知其大不知其所以大,而在《运移》中,读者可以形象化地了解什么是储集层、渗透率,也可以生活化地理解油藏、勘探,甚至还可以动态化地明悟岩心、岩石,至于油井、井喷、计量等等词汇,工牌号、螺丝刀、钳子这样的工具和小物件中,都能感受到一种情感和思想在微小处的触动。
这是又一个人体标本
躺着,活着
在最小的空间,说
让时光在石头的中间停下来
等我,等你
九窍闭关
世中世外有谁能还原初心
心若抽空
缘分孽债也不再互相抵近
天堂与地狱不知道有没有门
其间一定有过渡的厅堂
我们可以停留、可以穿过
却不能言说
一座火山被熄灭的疼痛
——《储集层》
一首首诗读下来,一个个片段流淌过,石油这个行业,石油这种风物,都开始活泛起来,原来啊,这些抽象的事物,居然可以具象成心中的波澜,而我们走过的岁月,与石油在诗歌里居然有如此的关联。
还还有一个切口,是诗中浸透的原乡情结。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从普通石油工人到石油报编辑,从诗歌写作到石油开发志、石油史的编纂,多年与石油为伴,诗人与石油、诗歌与石油史、原乡情感与石油物态等等,共同构成了他心中“挚爱者的大地”。同时,专业的认知、熟悉的领域给予了石油诗歌写作丰厚的底蕴和空间。阅读的过程,能感受到诗人对石油、对与石油相关的事物已臻至“灯下黑”或者说视而不见的境地。石油融入生活、骨脉、精神甚至灵魂之中,诗歌书写中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不见其形心有其意的触动,但有风吹草动,便有刻骨铭心、难舍难离之感油然而生。所以书写石油,就是他重新界定生活、再返本真的一次历程,与诗歌、与石油、与自己保持疏离,然后重新认识、熟悉、接纳、包容、享受,让生命在书写中得到不止于浅层的凝练与升华。
是的,世界是宏大的,但组成世界的,是微小的事物,而串联其中的,是自然中微妙的规律和生物富含的情感。“历史是一种假象,铺陈在地下,一动不动”,诗歌与诗人,就是将历史、文化,将万物的演变,以诗歌运移在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这其中,有真实之美,有语言之美,有生活之美,更有共鸣之美。
事事关石油,“每一滴都是语言,每一方都是诗篇”,但运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素养。而这种素养,既是物理的,也是化学的,变与不变的双重意象、诗歌与石油的双重交叠、我与生活的双重解构,尽在其中,就像石油的问世,静则潜移默化、安沉地下,动则石破天惊,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