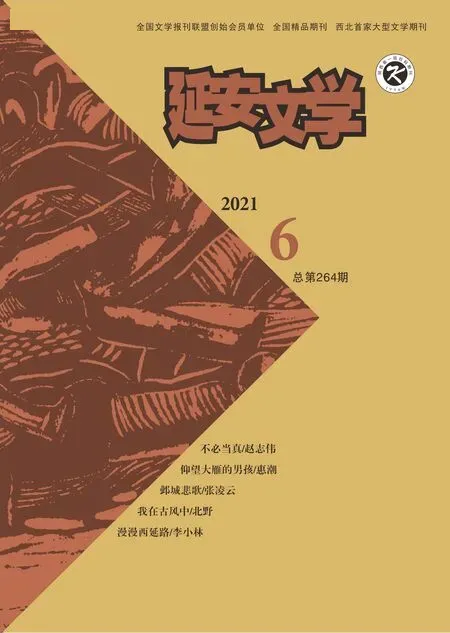讲故事的人,与我们日渐疏远
——狄马《歌声响处是吾乡》读后
惠雁冰
在阅读尼古拉•列斯科夫的作品时,本雅明曾言:“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能够把故事讲好者及愿意听故事者更是稀少,即使开讲也容易陷入“四座尴尬”的情状。本雅明的困惑,当然是出于现代工业文明整体兴起后传统艺术形态急速凋敝的现实,体现出对“现代”这一时间维度、现代性这一精神品格、现代化这一物理性景观的深沉反思,内含着与传统艺术光晕被动惜别的特殊况味。其实,这种反思也同样渗透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民间艺术如何存在与怎样保护不但成为文化热点,也成为时代难题,由此引发了知识界人士集体性的呼告与守望行动,并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形态、不同民间艺术中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索与艺术实践,为民间艺术的复归、重释与传承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中,在陕北民间文化的行吟者行列中,狄马显然是不容忽略的一位。其新著《歌声响处是吾乡》就是在文化现代性反思的前提下,对陕北历史文化饱含锋锐的钩沉与新掘,同时又伴随着一种无言无解的忧思。说其锋锐,是指他在言说陕北历史文化时不是线性梳理历史的页面,而是聚焦最能表征地域性格、地域精神和地域血性的历史片段,以此来打通地域、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言说方式看起来是散点透视的,却有一种直抵文化内里的光芒。说其新掘,是指他在解读陕北民歌、陕北说书、陕北方言、陕北艺人时,始终灌注着真切的生活体验与深重的悲悯情怀。其中,真切的生活体验让民间艺术从橱窗或舞台真正落回它所依存的烟火人间,还原了艺术发生的原始场域;而深重的悲悯情怀则让民间艺术背后的鲜活个体一跃而出,从而使纸面上、口头上的艺术具有了生命的质感。归结起来,其实彰显的还是以“人”为中心的意识,为底层生命立传的意识,为民间艺术正名的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人的意识的始终在场,陕北民间艺术的汁液开始涌动,陕北的苦难历史浮现出了英气勃勃的面影。说其忧思,是指他在面对市场化背景下民间艺术影响力日益缩微的状况所发出的阵阵感慨,又是指他对非遗保护过程中民间艺术渐渐滑入商业性演出现象的种种反思。这副愁容如秋露一样渗满这部书稿的边边角角,映射出一个陕北民间艺术守夜人的复杂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与他笔下的韩起祥、张俊功、贺四一样,狄马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经验和交流中讲黄土地上的历史文化,讲底层艺人的生命故事,讲陕北民间艺术不被年轻人认同的窘状,也讲他从中看到的某种不太明朗的希望。尽管他以特定的视角来呈现自己的观感与迷茫,也以一种有选择性的叙事手段来刻绘这个时代的表情,但通过这部书所反映出来的“陕北”无疑是有地域骨血的陕北,也是有生命体温的陕北。
在阅读的过程中,狄马的部分论述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如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问题。狄马对于小传统的解读甚为精准,用“静水深流”来指称,并言“大传统不大,小传统不小”。就我看来,所谓的“小传统”是指一种相对封闭的自足性的文化结构,用威廉姆斯的话来说,则是特定历史场景下特定族群的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置于陕北,就是与深沟大山、苦难生活相关联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地理样态,如忙时田头唱曲解心焦,闲时扭秧歌闹社火,晚时围坐炕头听说书,喜时唢呐横吹酒曲声起。至于过年过节、生老病死,更有一定的文化仪式。正因为其覆盖了这块土地上个体生命延续与终止的全程,并作为一种重复的经验不断在代际之间伸延,这才体现出文化本身的世俗性,也坐实了小传统之“大”。但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其实又并不清晰。尽管大传统在封闭的区域影响不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何况小传统中部分环节对大传统也有呼应之处;尽管大传统以规训话语为主,似乎难以涵盖小传统注重个体生命张扬的特征,但小传统中又同时存在着对个体生命张扬限度的规训与劝诫。这种同时在场的抑扬态度,又足以把小传统视为区域化的大传统。这样来看,作为自然分割的地理有边界,作为文化结构体的大小传统之间并无严格的边界。
又如如何看待民间艺术的生态问题。面对舞台上日益走红的陕北民歌,狄马敏锐指出“一首歌的旋律可以搬上舞台,生态怎么搬上舞台?”此言我深表认同。但我由此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理性看待这种商业化演出爆热、民间生活遇冷的现象。正如狄马一再强调的,陕北民间艺术依存于传统农业时代,是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符码。现在这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归,舞台上不断翻唱的民歌只是一种旋律的再现,至于民歌的原始生态及其中关联的个体生命意识早已消亡,何来原生态之说?所谓的原生态民歌不过是对某种未受现代音乐体制明显规训的原生嗓音、歌词、情感的综合表现而已。这样的诘问扣准了本质,的确值得反思。不过,现代社会的发展已如东流之水,不可逆回,要让陕北再次复归到那个封闭艰困的状态更属枉然。换句话说,我们也不能单单认为只有让陕北孤绝于现代社会之外,重返“七笔勾”的状态,陕北民歌才能真正回到寄生的土壤,并保留其鲜活的原质。相反,在顺应时代变迁的前提下,正视当下陕北民间艺术的生路问题,才是较为理性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以为以舞台表演来显现陕北民歌的存在,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尽管舞台的间隔使讲故事的人与受众之间缺少一种经验的传递与交流,甚至“观众也成为一位心不在焉的主考官”,但起码能激活陕北民歌的生命力,也能使之保持与当代生活的联系,还能通过广泛的流布影响与培养一代新人。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痛感电影、照相艺术对传统艺术的断裂性影响,但又不能不接受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彻底覆盖及技术性革新这一严峻事实。那么,在针对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的现状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在有本雅明这种现代性忧思的同时,对传统艺术光晕的消散持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陕北民间艺术的出路问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人民戏剧》杂志曾提出“京剧向何处去”的话题,一时争鸣不断。当时,刘厚生提出了“四条路”的论断,即“第一条路是进‘八宝山’,就是竞争不过别的艺术形式,衰亡了……第二条路,往博物馆去,就是类似日本歌舞伎的路……第三条路,向自由市场去,国家不管,爱怎么演就怎么演……第四条路,经过我们大力革新,大力推陈出新,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走上一条适应现代生活的新路”。如果将这一答案推及今天陕北民间艺术的话,前三条道路无疑是不可取的,只有第四条才是真正保护、发展陕北民间艺术的必由之路。但怎样保护,谁来保护,保护什么,保护得怎么样,依旧是个问题,我想这也是包括狄马在内的所有热爱陕北民间艺术、并期望它能一直伴随自己心史、心路的所有陕北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此,我无力来解答,只能寄希望于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及非遗保护者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