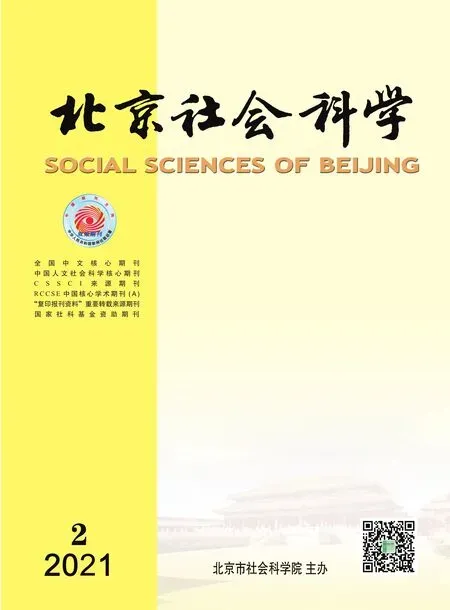论宋代宰辅词人群及其与主流词坛的关系
宋 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
宰辅是宰相和辅政大臣的总称。宋代宰辅不是指宰相个人,而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整个决策集团。[1](P317)一般来说,宰辅包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宋代个别时候不拜枢密使,以枢密副使为枢密院最高长官,这个时期同知枢密院事亦在宰辅之列。宋代宰辅副职名称变化不大,宰相名称略有变化。宋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任,又以他官加同平章事者为宰相,其本官身分高下不一,从三师到承务郎皆可加同平章事为宰相。元丰改制后以左右仆射为真相,宋徽宗时期更名三公为真相之任。建炎三年(1129年)在吕颐浩的建议下,以左右仆射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任,至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又改左仆射为左右丞相,此后宋代宰相名称再无重大变化。宰相的人数大概在2人到4人不等。常规而言,以左相为大,虽然同时都作为宰相,如从右相进为左相,则视为升迁。
词人的标准按照王兆鹏先生所说“存词十首以上即为词人”。[2](P95)在研究考察中看到,两宋有词传世的宰辅共有76位,存词共计1916首,其中存词10首以上的宰辅词人,北宋有4位,南宋有17位,共计21位,这些词人被确定为研究重点。同时一些宋代宰辅虽然存词较少,但他们的创作却往往开启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或者作为某种创作风格的重要补充而具有考察的意义,因而并没有将那些存词较少的宰辅的创作排除在外,仍然将其纳入宰辅词的范畴进行考量,这些词人本人也被目之为宰辅词人。
对宰辅词人的界定,基于以政治地位作为考察的着眼点,拜为宰辅的经历是划分宰辅词人创作前后期的标准。由于创作主体的不可分割性,不同的人生际遇对同一创作主体的创作风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止宰辅在拜为宰辅以后所作的词是宰辅词,在位登二府之前的词也是他们创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考察宰辅词人创作的重要参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创作与作家具体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相关,词人的创作往往集中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并不是全部宰辅词人的创作都可以截然按照拜为宰辅的时间点来划分前后期。拜为宰辅之前、之后,贬谪之时、闲退之际,都可能成为宰辅词人创作比较集中的时期。宰辅作为士大夫群体中官位最高的一类人,无论拜为宰辅之前还是之后,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考察的意义,因而结合宰辅词人具体的创作情况,考量拜为宰辅的经历对宰辅词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的影响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一、宰辅词人创作概述
宋代宰辅词人的分类可以按照时间的标准,分为北宋宰辅词人和南宋宰辅词人;亦可以政治地位为标准,分为拜为宰相的和仅为副职的宰辅词人;还可按照存词数量的多寡,划分为存词较多的宰辅词人和存词较少的宰辅词人。文章综合考量以上划分标准,主要依据纵向的时间变化和宰辅词人的创作特色,揭示宰辅词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发展的动态过程。
北宋宰辅词人以晏殊、欧阳修为主,另有王安石、苏辙、曾布、王安中等人存词较多。从整体上来看,北宋时期宰辅词人虽然存有一定数量的词作,但相比较南宋而言,数量少,有模式化倾向,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宋代词体繁兴之初,以宰辅词人为主的高官群体是宋词的主要创作者。笔者根据《全宋词》对宋代词人按照政治地位进行整理,宋仁宗在位前后,宋词创作高峰期出现之初,词人官职构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宋代词人身份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柳永、晏殊登上词坛以前,词坛较为沉寂,北宋前期70余年仅存词数十首。这20位词人中,9人进士及第,2人赐同进士出身。可见在晏、欧、柳永开始大量创作宋词之前,词作者的身份主要以进士及第的文人士大夫为主。其中林逋是隐士,出身儒学世家,颇好古;杨适是庆历五先生之一,归鄞讲学,具有儒家士人身份也是宋初词人的普遍特征。从表1还可以看出,高级官员所占比重较大。宋初百年20位词人中有9人官至二府。同时非二府成员和岘,其父和凝为后晋宰相;李遵勖为宋初大将李崇矩之孙,后来为驸马都尉,皆为贵胄或世家出身。可见宋代词人身份以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为主,随着宋词词体地位的提升,词人身份具有自上而下流动的特点。南宋以后,随着诗词一体趋势的形成,低级官吏和布衣词人在词人身份构成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
第二,北宋宰辅词人的创作存在一个薄弱期。宋词勃兴之初,宰辅词人的创作十分令人瞩目,在宋真宗、仁宗时,涌现了寇准、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著名宰辅词人。他们的创作内容较为丰富,不仅涉及政治题材、边塞风光、歌舞酒宴、相思怨别等内容,风格上也兼有晏殊的含蓄清雅、欧阳修的深婉俊逸、范仲淹的豪迈洒脱。及至宋神宗熙、丰年间,当苏轼等人登上词坛以后,词体地位得到提高,词人的创作也逐渐增多,但宰辅词人的创作反而走向沉寂。除王安石以外,仅苏辙、曾布、司马光等人有少量词作传世。曾布、司马光的词

表1 宋初词人身份构成表
在风格上延续宋初宰辅词人所开创的创作范式,以艳情柔婉之作为主;王安石和苏辙的词则寄寓了明显的禅学意味。这一时期宰辅词人的创作虽然较少,却也透露出北宋宰辅词人对词体功能的多元化认识。
熙、丰时期,宰辅存词较少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更与词人的社会身份相关。熙丰时期在朝堂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王安石,是新学代表人物,元祐时期在朝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司马光,则是洛学代表。彼时二程也在朝中为官,尤其程颐又在经筵为侍讲,宰辅大多是理学家,他们对词的创作抱有疏离的态度,自己也很少作词,自然传世词作较少。新学代表王安石的词作相对较多,也比较有特色,其中宣扬佛教义理的作品,在词体诗化的道路上具有客观上的引导之功。同时这种创作也是对宋词晏、欧所开创的词体雅化道路的一种跳脱,反而更像是对词体产生之初佛教“经呗”演唱活动的发扬,与苏轼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之际有意区别词体的现象不同,王安石改造词体的主观意图并不明显。
宋哲宗亲政后不久便去世,宋徽宗即位之初也做出励精图治的姿态,朝中曾布、章惇等新党人物主政,这个阶段的宰辅存词较少。宋徽宗中晚期,由于皇帝艺术才华的显露,大晟府的建立,宰辅中涌现出一些词人,他们多有与皇帝的唱和词传世。如范致虚、王安中,这些宰辅的创作走入宫廷,与帝王相酬唱,词体地位也因之得到进一步提高。此一时期宫廷宴饮活动较多,宰辅词或许也较为可观,但靖康之变以后,或因战乱而失传,或因词作过于淫靡而被销毁,这其中或许也有大量宰辅词一并失传。
第三,北宋宰辅词人的创作推动了词的“尊体”进程,这一过程与宰辅对帝王意志的承继有关。在“尊体”的道路上,宋词发生发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帝王的参与,诸葛忆兵先生在《论帝王词作与尊体之关系》一文中称:“从带头创作淫靡歌词,到有意识倡导高雅,帝王的影响是其他因素所无法替代的。帝王作为国家的形象代表和人们心中的伦理道德典范,在歌词创作领域,推尊词体,使词走向高雅,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3]帝王的引导是宋词“尊体”的重要原因,帝王的态度对词体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宋初词坛的沉寂,与宋太祖对词的态度有关。相传他对亡国之君以词名世的状况曾报以蔑视,据胡仔记载:“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艺祖云:‘李煜若以做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4](P96)太祖对李后主的批评带来上行下效的影响,宋初整个文坛都对词的创作提不起兴趣。宋代建立以后,为了改变晚唐五代的浇薄士风,士大夫渴望重建儒家道统,砥砺名节,拒绝浮靡,诚如学者所言:“北宋初年诗风文风的改变,‘文章还正统’的创作风气逐渐形成,非常不利于‘主乎淫’的词的创作。”[5]所以宋初词坛较为沉寂,这种沉寂状态的打破还是以帝王的默许甚至引导为突破口。
宋仁宗、神宗均有词传世,尤其是北宋末年徽宗的参与,客观上推尊了词体。南宋君主参与词的创作则更加明显,如高宗自作渔父词,孝宗亲自唱词,都促进了词的“尊体”进程,南宋词坛词人大量涌现,宰辅作词也较多,且较有特色。《古今词话》载“宋初帝王不以词见”条云:“词盛于宋,而国初宸翰无闻,然观钱俶之‘金凤欲飞遭掣搦’,为艺祖所赏。李煜之‘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太宗所忌。开创之主,非不知词,不以词见耳。嗣则有金珠乞诗之宫嫔,有提举大晟之官僚,按月律进词承宣,命珥笔宠诸词人,良云盛事,奚必宸翰之远播哉。”[6](P1139)宋初太祖因钱俶“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楼云雨隔”而心生怜恤,称“誓不杀钱王”,宋太宗因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而鸩杀李煜,都是因词而得福或遭祸的例子。及至后来,宣和年间宫嫔偷窃金杯后因词获释,徽宗时期大晟府词人按乐律向朝廷献词等事,都昭示了帝王对词体发展的影响,王奕清称之为“盛事悉必宸翰之远播”,上行下效,是宋词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与之相类似,宰辅词人在词坛起作用的方式也具有这种上行下效的特点,因而虽然宰辅词人创作实践不多,也并不一定是传词数量多的词人,但他们却往往是后代诗话、词话绕不开的人物,他们的词作更容易被记录、模仿和传播。
同帝王的影响方式相类似,宰辅词人与词体相关的活动、事迹也展现出宰辅在词体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据载:“皇祐中,吕夷简致仕,仁宗问:‘卿去谁可代者。’夷简荐陈尧佐,上遂召还大拜。吕生日,陈携酒过之,作《踏莎行》词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双飞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轻拂歌尘转。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吕笑曰:‘只恐卷帘人已老。’陈曰:‘但得公老于廊庙,莫愁调鼎事无功。’二公相推,何等蕴藉。”[7](P10)吕夷简推荐陈尧佐为相,陈尧佐作词表达对老丞相推荐之恩的感念,使词的功能不仅仅限于佐酒应歌,在应酬词中打上了政治际遇的烙印,客观上有推尊词体的作用。
钱惟演的事例也具有代表性。据《词源萃编》言:“钱惟演,吴越王俶之子,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坐擅议宗庙,且与后家通婚,落职为崇信军节度使。其《玉楼春》词云:‘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岩。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悉肠先已断。情怀渐觉成衰晚。莺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此公暮年之作,词极凄惋。”[8](P1829)钱惟演是吴越王之子,出身帝王家庭,一生追求宰相之位,并曾拜枢密使,其词中所寄寓的那种伤时之感带有浓烈的政治感怀,在酒宴歌席间表现严肃政治主题的意义,也是对词体摆脱小道诗余的有益尝试,有助于宋词的尊体。
南宋宰辅词人的创作数量较多,内容也比较丰富,各种题材类型和艺术形式都有尝试。小令、长调、大曲、导引等皆有涉及。词史上最长的词牌《莺啼序》就是出自宰辅词人王淮之手;最完备的大曲出自宰辅词人史浩之手,南宋宰辅词人的创作也独具特色。
如南宋宰辅词人的创作主题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以富贵主题的表达为例,北宋词人以晏殊的“富贵气象”为主要追求,但也被批评陷入清寒,南宋宰辅词人在创作富贵之词的时候,则融合当时词坛的重气思潮,使之具有一种“壮雅”的特色。在政治感怀词的创作上,北宋词人援引政治题材入词,南宋宰辅词人则在此基础上,于政治感怀词中加入对现实政治的议论,以此团结具有共同政治主张的士大夫,使词具有可以“群”的功能,同时也通过在词中寄寓政治感怀的方式,将南宋末年的权相政治与战争实况引入词的创作中,扩大了宋词的表现领域,进一步推尊了词体。在援引禅理入词方面,南宋词人也能够一改北宋宰辅词人生硬说理的弊病,融“理趣”与“禅思”入词,追求禅悦之风,展现出宋词多样化发展的痕迹。
又如,南宋宰辅词人的词体诗化观念具有动态变化的倾向。在南宋诗词创作趋于一体的词坛背景下,宰辅词人的创作实践却向我们展现出另外一种倾向。宋初之际,宰辅词人将士大夫意识烙印在词的创作中,促进词体的诗化。在南宋,宰辅词人的创作则体现出对词体本色的复归。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宰辅词人,追求风雅,清人江立评曰:“石湖词跌宕分流,都归于雅,所谓清空绮丽,兼而有之。姜史高张而外,杳然寡匹。”[9](P119)范成大词以风调娴雅而为世人所称道,在南宋词逐渐走向案头化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词以和婉可歌为主要特色,周必大在《与范智能参政》中引陈无己云:“妓围窈窕,争唱舍人之词。”[10](P2092)陈廷焯亦有“石湖词音节最婉转”(《云韶集》卷六)之论。冯金伯将蒋竹山词和石湖词对举,突出其风雅之韵,曰:“读秋屏词,尽洗铅华,独存本色,居然高竹屋、范石湖遗音,此有井饮处所必欲歌也。”[11](P688)与此同时,《白石道人歌曲》中亦载范成大向姜夔求新曲,姜遂作《暗香》《疏影》二阙以献的故事,都说明了范成大对词体和婉可歌特色的追求。
当然这种和婉可歌,也是在诗化的背景下进行的。邓乔彬先生《石湖词叙论》中称:“沈曾植谓石湖词有‘诗人旨格’,盖指范成大以诗人身份游戏乐府,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诗家笔法用之填词,进而使其词呈现出诗的旨趣,有诗的意格。”[12]宋人以诗为词,主要是指在词的写作内容上援引诗歌的内容入来,以此改造词的艳情特质。石湖词的和婉可歌,追求诗歌的风雅,消弭词的艳情特质,同时这种风雅追求与当时词坛“崇苏”的风气相照应,而与辛弃疾等人的豪迈之风相疏离,在疏旷之外追求典雅含蓄,体现出范成大在以诗为词的大背景下对词体本色的坚持,这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中是值得重视的。可能正是范成大的引导,促进了以姜夔、史达祖等人为主的江湖派词人风雅之旨的形成,使之与辛派词人的粗豪分庭抗礼,形成了对明清词学影响深远的风雅词派。
总之,体裁越是成熟就越容易走向规范甚至僵化,在以诗为词的问题上,宰辅词人的创作具有二元化的作用,从一开始通过以诗为词的形式改造词体,到词体成熟以后,又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在词的佐酒伴宴、和婉可歌等特质上维护词体的独特性,避免词落入诗歌的窠臼,一味摹写诗歌内容学习诗歌风格,走向案头和僵化。
二、宰辅词人交游唱和活动
所谓群体,也即社群和共同体,指由有某种共同特征、从事某种共同活动或处在某种相同环境下的两个人以上组成的集合体、集团或组织。一般的群体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每个成员都受其制约和影响。由于宰辅是一个历时性的群体,他们虽然受到与宰辅这一社会身份相关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要求的影响,但宰辅词人群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词人群体,讨论宰辅词人的结群问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衡量宰辅词人是否有结群的倾向,主要依据两个标准。首先是宰辅词人群体内部是否拥有旨趣相投的创作个体,其次是创作个体之间有明确的“分题”“次韵”类酬唱活动。通过笔者的考察,可以看出宋代宰辅词人并不具备结群的明显特征。从群体的概念上来说,他们仅仅是在一定文学环境中有着相似的艺术理想和追求的一个文学创作群体。宰辅词人群体按照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代表了立于庙堂之上的士大夫群体的创作风格。与江湖词人倾向于结群不同,宰辅词人作为士大夫中的成员,虽然也往往会相互唱和甚至结社,但他们并不具有明确的结群意愿,也没有产生实际意义上的词人群体。
在宋词发展过程中,宰辅词人可能会根据创作环境的不同,产生短暂的唱和行为。如南宋由于权相政治的影响,建炎绍兴时期,李纲、李光、张元干、李弥逊曾经相互唱和;宋末由于贾似道当权,对外战争形式严峻,吴潜、吴渊、吴泳、魏了翁等人又相与唱和;再如宰辅退居后,洪适与叶宪、洪景裴等人组织真率会,史浩与汪大猷等人组成尊老会,范成大与姜夔、杨万里等人相互交游唱和等,形成了一个个小型唱和群落。与那些真正以词名世的词人群体不同,宰辅词人间的唱和群落,可能会以宰辅的个人审美趣味为标准,但这些唱和活动或受某一具体的政治事件影响,或因退居后志趣相投的诗酒悠游,他们的唱和并不具有明确的文学目的。这其中宰辅的审美趣味虽然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却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词学理论,围绕宰辅所进行的唱和活动也并没有形成流派。但这种唱和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又确实真实存在过,作为宋词流派发展的补充,在词史的流变过程中也是具有价值的。
北宋时期宰辅存词较少,传世史料也不丰富。以晏殊为中心,欧阳修和范仲淹都是晏殊门人,王安石又是晏殊同乡,史料中也每每透露出他们相互之间曾有雅集唱和活动,但具体记载其唱和状况的史料却并不多。比较详细的有庆历间晏殊西园赏雪,《苕溪渔隐丛话》中载:“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欧阳学士修陆学士经,元献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也。’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是时西师未解,欧阳修句有:‘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元献怏然不悦,尝语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韩愈也会做文章,但言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恁地作闹!’”[3](P174-175)这则记载虽然是记录了一次不算愉快的聚会,亦可知他们之间围绕着“未尝一日不宴饮”的宰相晏殊而时常有雅集活动,可惜由于史料的缺乏,当时结群唱和的盛况难以窥其全貌。
这一时期晏殊和欧阳修的审美旨趣成为士大夫所趋奉的目标。除了晏殊的富贵气象受到后人的推崇外,欧阳修的创作也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赞誉,《六一词跋》称:“荆公尝对客诵永叔小阕云:‘五彩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曰:‘三十年前见其全篇,今才记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数词人求之,不可得。”[13](P1026)酒宴唱和之际,欧阳修以文坛执牛耳者的身份创作的小歌词,自然成为士林争相传诵的对象,这也是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生命力之所在。如同魏晋年间,文学自觉,左思作赋,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一样。但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词又为小道艳科,大臣作词亦往往自扫其迹,酒宴中的创作大多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到熙丰年间,苏轼、秦观、晏几道等人大量作词,他们的词也在都下盛传,但他们都未曾拜为宰辅,宰辅词人又大多不是一流的文学家,不以文学创作的进步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这也是造成北宋宰辅词人结群现象不明显的原因之一。
南宋初年以李纲为中心,周围存在一个以李光、李弥逊、胡铨、张元干等人为主体的唱和群体,他们在政治上秉承主战思想,坚决反对和议,视秦桧若仇雠,提醒朝廷勿忘国耻,积极呼吁当政者使用李纲这样名臣主持抗金复国大业。他们的词以抒发对故国的怀念、壮志难酬的苦闷、遭贬处穷的悲凉为特色,唱和主体多为豪放词人,在词风上具有上承苏轼、下开辛弃疾的特点,留下的词作较多,唱和活动也有迹可循。如李纲和李光之间的一次围绕李白画像的唱和活动,李纲寄一首《水调歌头》(李太白画像)给李光,李光以《水调歌头》(李公伯纪寄示《水调》一阕咏叹李太白词采秀发,然予于太白窃有恨焉,因以渊明为答水调歌头)为答,二人的词作通过对李白的不同态度,表达了对各自人生际遇的感怀。同时期张元干有寄给李纲的《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李弥逊有《水调歌头(次李伯纪韵趣开东阁)》《水调歌头(次李伯纪春日韵)》《蓦山溪(次李伯纪梅花韵)》《洞仙歌(次李伯纪韵)》等词相与唱和。作为李纲的坚定拥趸者,李弥逊和张元干之间也有唱和活动,如李弥逊有《沁园春(寄张仲宗)》《永遇乐(用前韵呈张仲宗、苏粹中)》,张元干有《宝鼎现(筠翁李似之作此词见招因赋其事,使歌之者想象风味如到山中也)》等词相互唱和。从这些唱和词的内容来看,李纲和李光的词尽管也围绕当时的社会环境抒发感慨,有政治影射的意义,但政治倾向不是很明显,而张元干、李弥逊的创作则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倾向,主要歌颂了其主战观念。
宋孝宗时期,围绕宰辅词人范成大的唱和活动较多。宰臣如洪适、周必大、丘崈、京镗,高官如杨万里、韩元吉、陈造、尤袤,名士如姜夔、陆游等人都与范成大有交游唱和活动,形成了以范成大为中心的文人唱和群落。他们生活在南宋最为承平的时期,宴会雅集活动较多。但这个群体的唱和比较松散,主要围绕范成大的仕宦交游活动而进行。范成大本人词集里明确指明唱和对象的极少,仅《满江红(始生之日,丘宗卿使君携具来为寿,坐中赋词,次韵谢之)》是与丘崈的唱和词。但其唱和对象本人却多有词传世,如宰辅词人丘崈的《满江红(和范石湖)》《满江红(余以词为石湖寿,胡长文见和,复用韵谢之)》、京镗《醉落魄(观碧鸡坊王园海棠闪范石湖韵)》。士大夫如吴儆《浣溪沙(次范石湖韵)》、陈三聘《念奴娇(和徐尉游石湖)》以及布衣姜夔的《石湖仙(越调寿石湖居士)》《暗香》《疏影》等词。范成大交际比较广泛,早年进入仕途曾受到洪适的点拨,学习吏事,与周必大、杨万里为至交;在四川时亦颇得蜀人之心,周必大《神道碑》中称:“三年春,公大病求归,上令先进敷文阁直学士,明日乃下诏命公列上兵民十五事,上曰,范某已病,尚为国远虑,可趣其来,公疾愈而行,送客数百里,不忍别,后公谢病,吴门往来者,伺候谒舍或经月,必一见乃去,其得士心如此。”[14](P609)以范成大为中心的创作群落,其创作时间在孝宗、光宗时期,是南宋政治经济最为发达的历史阶段,这个唱和群落的集结是以范成大的名望和个人道德魅力为核心,他的审美取向也对这个唱和群落的风格有一定影响。
南宋中晚期,出现了两个以宰辅词人为核心的创作群落,分别以魏了翁和吴潜为核心。这两个唱和群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叉和融合。魏了翁的唱和群落,以四川籍贯或在四川为官的士大夫为主。如其唱和对象范子长、范良辅、高嘉定、高瞻叔皆为四川人。他与四川籍参知政事李壁之间存有15首唱和词,与简阳籍官员许奕、刘光祖分别有11首和25首唱和之作。魏了翁词中还有大量与四川籍家人的唱和词作,如有与绵州表兄唱和18首、与荣州表兄唱和11首,还有与茂叔兄15首、西叔兄17首。这些词的创作与魏了翁在四川成长、为官、后又退居的生活经历相关。由于其理学家的身份,这些唱和词的理学倾向也很明显。
另一个是以吴潜为中心的唱和群落,包括吴泳、吴昌裔兄弟、赵葵、赵范兄弟以及吴潜的兄长吴渊,江湖词人吴文英、高观国等人。社会地位从高官到布衣,创作内容较为丰富,大多与他们共同的生活经历相关,词中尤其以仕途际遇、政治感怀等内容为主。如吴潜与吴泳兄弟之间的唱和词,有《祝英台近(和吴叔永文昌韵)》《八声甘州(寿吴叔永文昌、季永侍郎)》等。又有与赵氏兄弟的唱和词,如《贺新郎(寄赵南仲端明)》《酹江月(瓜洲会赵南仲端明)》等。吴泳词中也存有与吴潜的唱和之作,如《满江红(和吴毅甫)》《清平乐(寿吴毅夫)》《满江红(和吴毅夫送行)》《满江红(和吴毅甫)》等。这一群体的唱和内容主要围绕南宋末年内外交困的战争环境,抒发自我感怀,思考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当时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不同,他们的创作表现出比较积极的精神风貌,展现出宋代士大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以少胜多的美好愿望。对比南渡时期热切的爱国情怀,中兴时期浓厚的燕乐氛围,这一时期宰辅词人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所作词具有明确的理性特色。
吴潜和魏了翁之间也有唱和活动。吴潜有《满江红(送魏鹤山都督)》《八声甘州(和魏鹤山韵)》等词,魏了翁亦有《唐多令(别吴毅夫、赵仲权、史敏叔、朱择善)》,是魏了翁督视江淮军马时所作,与时事政治相关,展现出二人以相同政治目标为纽带的交往过程和政治际遇。
总之,宋代宰辅词人的创作虽然没有明确的结群现象,但是通过他们之间的唱和活动,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以宰辅词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些唱和群落,这些唱和群落与时代环境相结合,具有各自不同的创作特色,并对当时词坛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作为宰辅词人结群的判断标准。
三、宰辅词人与主流词坛之关系
宰辅词人的创作风格各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与主流词坛有时保持一致,有时又展现出疏离,按照时间顺序,宰辅词人群体与主流词坛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发展阶段进行考察。
宋初以晏殊、欧阳修为主的宰辅词人,他们引导了宋词的发展方向。历代论北宋词皆以晏、欧为始,《白雨斋词话》中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15](P6-7)陈廷焯认为晏、欧始词乃五代余续,同时认为晏、欧虽然享有盛名,但并无特别的贡献,哪怕是艳体词也并非上乘。王国维则对晏、欧的评价较高,他称:“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16](P38)又言:“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16](P42)晏、欧在宋代为一时文学之巨擘,欧阳修更是倡导古文运动变革文风的改革者,他们在宋词发展之初起到了引领词坛发展的作用,此后宋代宰辅词人或在政治上各有建树,或在学术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以文学名世者无人超越晏、欧,这或者也是晏、欧能够以其创作实践开创宋词繁兴的原因。因而在宋初,以晏、欧为代表的宰辅词人是引领宋代词人风气、促进词体繁兴的典范,宰辅词人的创作就代表了宋词的发展方向。
熙丰、元祐年间,宰辅的创作整体趋于沉寂。宰辅词人如王安石、曾布、苏辙、司马光的创作较少,但是他们的创作与苏轼、秦观、晏几道等人的主流词坛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共同致力于宋词以诗为词的发展倾向,助力于词体之成熟,是主流词坛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王安石词以清雅的诗意改造了词体之柔靡,其“平岸小桥千障抱”,写景平淡清远,与秦少游“山抹微云”有异曲同工之妙。曾布是宰辅词人创作大曲之第一人,其《排遍》的特点是化用诗句入词,以诗为词,后来南宋洪适与史浩都有套曲,但皆以祝颂为主要内容,与曾布词形式相似,但在内容上有较大区别,代表了词体发展过程中的诗化倾向和词体成熟之后复归本色倾向两种不同阶段的表现。苏辙的创作也具有以士大夫情怀入词的特点,其《调啸词》写隐居幽情也是对以诗为词的一种有益尝试。至于司马光的《西江月》《锦堂春》则是宋词一贯创作旨趣之所在,画面绮丽、情思柔婉,为柳永、张先小词创作之余续。总之,熙丰、元祐宰辅词人的创作与主流词坛的创作相融合,是词坛的有机组成部分。
徽宗末年,宰辅词人以王安中、范致虚的祝颂词创作为主,是宋徽宗时候大晟府词人创作的补充。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对王安中其人、其作有详细的记载:
毛子晋跋《初寮词》云:“履道由东观入掖垣,由乌府至鳌禁,皆天下第一。或谓其受知于蔡元长,密荐于上,故恩遇如此。”又云:“或云:初为东坡门下士,其后附蔡叛苏。”又《幼老春秋》云:“王安中以文章有时名,交结蔡攸。攸引入禁中,赐燕,作《双飞玉燕》诗。”今就二说考证之。毛跋一曰或谓,再曰或云,殆传疑之词,未可深信。赐燕赋诗,事诚有之,讵必蔡攸引入耶。《宋史》安中本传“有徐禋者,以增广鼓铸之说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东南九路铜事,且令搜访宝货。禋图绘坑冶,增旧几十倍,且请开洪州严阳山坑,迫有司承岁额数千两。其所烹炼,实得铢两而已。坑术穷,乃妄请得希世珍异与古之宝器,乞归书艺局。京主其言。安中独论坑欺上扰下,宜令九路监司覆之。坑竟得罪。时上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夤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事,当责所属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视其所经由,仍申严臣庶往还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云云。安中对于蔡京,屡持异议,再疏劾京,乃至京惧攸泣,而谓附京结攸者顾如是乎?二家之说,何与史传迥异如是。[17](P4492-4493)
该跋词详细地记载了王安中受蔡京等人引荐而入朝,侍奉禁中,并得到皇帝信任的事情。同时载王安中屡次弹劾蔡京父子、令徽宗悚然纳之,不难窥其人品中反复无常的一面,但其词却独具高士之姿,充斥着对隐居生活的歌咏和赞赏,词风亦不失清旷。冯煦《蒿庵论词》称:“词为文章末技,故不以人品分升降。然如毛滂之附蔡京,史达祖之依侂胄,王安中之反复,曾觌之邪佞,所造虽深,识者薄之。”[18](P558)冯氏认为词是小道末技,故不必以人品的高下来衡量其词品的高低,但像王安中、蔡京等人,因为人品低下,尽管艺术造诣较高,但终究为有识之士所不齿。肯定了蔡、王等人的艺术造诣,同时也指出其作品不为世人重视的原因。
王安中词内容涉及较广,既有援引庙堂内容入词的一面,如《御街行(赐衣袄子)》,同时也作有婉约词,如《虞美人(雁门作)》《浣溪沙(看雪作)》等,旖旎婉媚中不失有疏旷放达之处。据笔者看来,其大部分词作与大晟府词人创作特点类似,诸葛忆兵先生《徽宗词坛研究》中说:“处于相同社会环境当中,艺术气质相近的大晟词人,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职责之所在,其创作呈现出某些共同性。大晟词人实际上是徽宗的御用文人群,故推而广之,大晟词人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也同样存在于大晟府以外的其他御用文人的创作中。”[19](P4)因而王安中虽然作为宰辅词人,但同时也是徽宗的御用文人,他的创作与大晟府词人创作风格保持一致。
南渡时期,宰辅词人李纲、李光、赵鼎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引导了词坛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围绕着在这几位宰辅身边的词人胡铨、李弥逊、张元干等人,更是开启了宋代豪放词风之先河,具有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历史作用。这一时期宰辅词人的创作与李清照、向子諲、朱敦儒等人所代表的南渡词人的创作既有一致又有不同。如在表达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南方生活环境不适应等方面,宰辅词人和大部分南渡词人的创作没有太大区别。宰辅赵鼎的《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可谓沉郁之至,是南渡时期表达伤怀故国之感的典型作品。但在表达爱国主题层面,宰辅词人虽然大多为坚定的主战派,但他们词中的爱国情怀却与士大夫阶层展现出来的对抗金复国理想的歌唱不同,宰辅词人更多的是抒发一种壮志未酬的感慨,而较少表达具体的政治观点。李纲的怀古咏史词具有影射现实政治的倾向,但大部分词作以人生际遇的抒写为主要内容,仅《苏武令》一词直接显露出抗金复国、迎回二帝的政治主张。岳飞的《满江红》是表达民族情怀较浓的作品,这与岳飞的前线经历有关,而与其宰辅地位相关性较小。其余如李邴、张纲等人的创作皆以含蓄为主,李光的词虽颇近苏轼,但其词中直白表达抗金复国主张的也不多,仍然是以抒发个人际遇的感怀为主。
宋孝宗、光宗时期是以辛弃疾、韩元吉、张孝祥、陆游的爱国词的创作为主流的时期,但此时宰辅词人如史浩、范成大、洪适、丘崈、京镗等人的创作却较少表现爱国主题,主要以歌舞酒宴的燕乐生活为内容,与主流词坛的创作表现出一种疏离状态。虽然他们与辛弃疾等人之间也有唱和交游活动,但此一时期辛弃疾的词风并没有影响宰辅词人的创作,如洪适有《满庭芳(辛丑春日作)》表达政治失意,辛弃疾《满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韵呈景卢内翰)》所表达的也是仕途受挫的悲凉,风格沉郁,与他的爱国词壮阔豪迈的风格还是有区别的。史浩与陆游也有交游,史浩集中有《鹧鸪天(次韵陆务观贺东归)》《生查子(即席次韵陆务观)》等词,淳熙末史浩由鄞入京时,还曾到访陆游山阴老家,彼此之间亦有诗歌相互唱和,但即便作为爱国诗人代表的陆游,他与史浩间的往来之词也只是记述宴饮活动,不表达政治观点,显然是顾及史浩的身份和心情。
宋宁宗、理宗时期是豪放词与风雅词畛域互分的时代,主流词坛由两种创作风格的词人所构成:一类是以辛弃疾、刘克庄为代表的豪放词人,一类是由姜夔所开创的,以高观国、史达祖等人为主的风雅派词人。宰辅词人的创作则基本可以归入这两派中,如吴潜、吴泳、陈韡、魏了翁的创作与辛派词人风格接近,何澹、许及之等人的创作则以典雅清丽为主,近似于风雅词派。其中有两个特例,一个是吴潜,他与风雅派词人相交甚深,但他自己的创作却追慕辛派词人,格调豪迈放旷。另一个是魏了翁,他以理学家身份作词,作品中多有理趣,是理学思想对词的影响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位词人。由于二人存词较多,且当时词坛与吴潜和魏了翁相唱和的词人亦较多,这些唱和词又都表现出比较明确的理性思考,作为宋代理学影响下的一种新型创作范式,成为主流词坛的必要补充。及至南宋末年,宰辅词人的创作以文天祥、文及翁等人的创作为主,主要结合时事抒发国破家亡的政治感怀,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主流创作。
总之,宋代宰辅词人作为宋代士大夫中地位最高的一个群体,受到政治地位的影响,他们存在一种并不自觉的群体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大致相同的创作倾向,与同时代其他词人的创作具有不尽相同的风貌。宰辅词人通过对宋词佐酒伴宴功能、言情特征的坚持,在诗化、雅化等问题上,也展现出一定的群体特色。同时与时代环境相融合,宰辅词人通过一些交游唱和活动形成了一个个小型的唱和群落,这些唱和群落中的词人,社会身份上至宰辅下至布衣,他们的创作反映出宰辅词人的审美趣味,是宰辅词人创作观念的一种有效落实。宰辅词人创作的独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与主流词坛的创作倾向或保持一致,或存在疏离,或作为主流词坛创作风格的重要补充,从而在词史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具有考察的意义。
注释:
[1]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8辑)[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诸葛忆兵.论帝王词作与尊体之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4](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诸葛忆兵.宋初词坛萧条探因[J].文学遗产,2009(2).
[6](清)王奕清.历代词话·卷四[C]//.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马兴荣,刘乃昌,刘继才主编.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8](清)冯金伯.词源萃编·卷四[C]//.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宋)范成大著,黄畲校注.《石湖词》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9.
[10]吴熊和,沈松勤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12).
[11]孙克强,杨传庆,裴哲编著.清人词话·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8).
[12]邓乔彬,宫洪涛.《石湖词》叙论[J].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13](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C]//.四部丛刊(第4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14](宋) 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六十二[C]//.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15](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清)王国维著,施议对译注.人间词话[M].长沙:岳麓书社,2015.
[17](清)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C]//.词话丛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增订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19]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