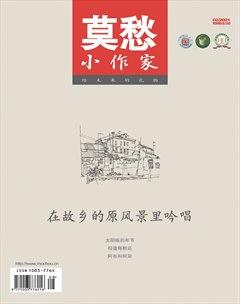南角墩的出路
我曾经步行观察过许多和南角墩一样的村庄,尤其是它们平静而安详的路口。标准化的村村通工程造就的路口改变了村庄原来的落后与艰难,它们又以一样的宽度表达着村庄的呆板和困境。路边依旧是延续了千百年的草木枯荣,所有写乡村的诗歌依旧能够找到确认,比如春风吹又生、汗滴禾下土、解落三秋叶以及万树寒无色等等,然而在这些路口你能看到一种新的情绪在滋生与疯长,往前依旧是依依墟里烟的村落,但往后却是绝城而去的车马行色,城市化在这些路口一遍一遍地提示与召唤着村庄经过这些路口的离开与诀别,这些路口是村庄情绪的出口,是村庄与过往的诀别之处,更是村庄奔向新生实质又是走向迷茫的码头,它们看似貌不惊人的设置在时间和空间上标记着一种决断,一种酝酿已久而又即将下定决心的改变。
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我隐约地感受到这种改变的开始——不过这不是我的确证,只是我确实只有那么短暂而清晰的记忆。那时候我还没有敢想象离开这个村庄是多么新奇而又艰巨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去一次集镇都是繁华和奢侈的记忆,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就足以改变清灰色的生活记忆。我说的“那个时候”,不过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是我们在课堂里盼望着“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后几年。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凛冽的寒风穿过窗户上破旧的塑料布钻到单薄的被子里来。四叔在昏暗的晨色里喊了父亲一声:“大哥哥,我去新疆‘做生活了。”父亲前一天的酒大概还没有醒来,就朦胧地喊了一声“知道了”。“做生活”在平常的话语里是一个辛苦的词,在南角墩人们的心里它就只有一个狭义的意象,就是做千百年来不变的农活。但是在四叔的嘴里,这个词已经是靠着手艺吃饭,他学会了瓦匠手艺又凭此在安徽娶回了老婆,现在他又要去更远的地方“做生活”。这个词有点辛苦和无奈,没有太多的人愿意背着这样一个词汇离开村庄,人们更愿意踞守在村庄里过着已经不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但是他们心里也隐约地感觉到,外出“做生活”可以让生活更好,这从日后四叔从外地带回来的哈密瓜干以及伊力特老酒等稀罕物品中得到了见证,于是“打工”这个词开始诱惑人们的心绪,人们开始慢慢地理解外出的辛苦对归来的幸福而言意味着什么。
于是,南角墩的村口不再仅仅是回家的记号,慢慢地成为走向好生活的捷径,他们突然发现留下来的父母姐妹以及苍老的土地确实没有那么值得留恋。与此同时,改变在村庄向外突围的同时,也受到轰鸣车辆的影响在内部发生着聚变。土地就像是已经不再安分的人们,也渴求着改变“死粥死饭”的过法。“死粥死饭”一开始是最奢侈的生活向往,吃饱了就有力气和希望,后来又称为一种科学的生活方法,人们在温饱之后已经习惯这种朴实的过法,而从“那个时间”开始,这种最为稳定可靠的方法受到了撼动。
不知道是哪一天,南角墩的干部有些神情异样地召开“社员大会”,动员大家将土地扭转给大户进行养殖。这是一次“风波级”的会议,尽管没有扩音设备,但会场的热闹依旧震撼人心。大家的疑问是确实无疑的:不种田这地用来干什么?地给了别人我们吃什么?要是亏本了我们去哪里要钱?这些疑问并不完全愚昧。南角墩的土地也并不是一直按照“水稻土”的遗传过日子。过去种过棉花和薄荷这样的经济作物。棉花种植是从外地学来的,从种苗到收货几乎延续三个季节的辛苦,即便是到了冬季也还有要整理棉花秆的辛苦,这些熬火的枝干不知道多少次戳破母亲的手掌,卖给棉花站的价格也没有彻底改变辛苦的生活。薄荷的种植和炼油对于种稻的人们而言,简直就是高科技的种植,四处树立的炼油的烟囱最终成为村庄里的遗迹,多少年后还有低价卖不出的薄荷油装在塑料壶里装在家中,几乎每一个家中都会有一个残余着薄荷味道的塑料壶,证明着试图改变生活的辛辣味道。父亲和四叔从安徽人那里学过种西瓜的本领,那些大西瓜长在地里形势喜人,可是卖不出的窘境几乎让人绝望,那时候“市场”这个地方对于南角墩而言,也还是一处遥远而不知道在哪里的秘境。所以无论怎么折腾,大家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安心的办法,稻麦两季的日子让人心安。
如今更要将土地交出来,这是一件摄人心魄的事情。胆大的声音也大,胆小的声音却也不小,但是争论了多少次之后,人们还是在提前预交的土地扭转金交付以后将土地腾让了出来,按照当时稻麦的价格与租金一起划算,人们还是认为这种不劳而获的土地出租有些诱人。养殖的内容也很新奇,过去养殖的无非是鲫鱼草鱼胖头鱼,现在要养的是一种叫作“罗氏沼虾”的外来物种,这当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但是拿到租金的人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缴械投降的土地和主人们一起观望着这场亘古未有的改变。当然,科学或者只能算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罗氏沼虾的养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南角墩这片土地及其周边地区一时间全部腾笼换鸟,成为连片的养殖基地,甚至据说成为全国第一占据大半壁江山的基地。
辛劳和沉睡了千百年的土地,真的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而由此改变的租用土地者和出租土地者的生活在改变的同时,也慢慢地改变了南角墩人的生活,作为农民他们不再是耕种者,而是成为经营者,这是比生活质量的改变更为深刻的一次改变。且不说那些承包经营的农民从“粮农”变为“虾农”,就连那些按年领租金的人们也改变了信念,他们在平时侍弄剩余土地的同时,也在塘边给虾农们打零工抓虾子做杂活,这样也有了一笔不菲的收入,这让他们沾沾自喜甚至最终在土地面前由缴械投降变为丢盔弃甲。村庄一开始对于土地的保留还是有一定的分寸的,人们按照人头预留了一定的“口粮田”,这一来是他们坚信自己亲手栽种的粮食口味亲切且安全可靠,二来他们也在考虑着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他们心里盘算着就是再不济总也会有饿不死人的保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短短几年的犹豫和观望之后,并没有需要多少的动员,南角墩的人们最终选择了将粮田悉数租给了种田大户,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租金,也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干活挣钱。
至此,南角墩的农民意想不到地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土地银行和母鸡银行转变为现代经济农业,于是在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情况下,他们成为我们公文写作中的新农民,而南角墩也转变为新农村。这种转变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然而其中的低价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根本的是人们对地和村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南角墩的土地还算是慷慨的,那不妨让我们草率而大概地回望一下她的过往,就会发现关于饥饿的记忆是屈指可数的。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是顽强和深刻的,口口相传的记忆未必不如纸本真实与稳定。和平原上的众多村落一样,南角墩大多数时候是温和的,她有着分明的四季,有丰沛的雨水,有丰赡的物产,还有性格温驯的人们和禽兽,这些让这个村庄封闭而又独特的强大。土地的封闭有自己的主观性,在无能为力介入外部世界的时候,人们选择了更为稳妥的“画地为牢”,用“有的忙就有的噇”来作为生存的第一教条,他们坚信土地不会辜负忙碌的双手,而事实上这种期待、付出与给予是平静而连续的。这样的里下河腹地的村落不得不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福地,这一点许多外来者表示倾慕,而南角墩的人们虽然不至于傲娇,但他们确实用自己静默的坚守证实着土地的慷慨。
他们信任土地并且达到崇拜信仰的地步。在除了“菩萨”这样模糊的宗教信仰之外,村庄里几乎没有一处正式的宗教处所,而土地庙却以其特别的规模出没在村庄的许多角落。因为土地的珍贵,即便是神灵也要给肚皮让位置,土地庙经常选址的则是不起眼的角落,这也让其有一定的隐秘与神奇。土地庙的功能性非常明显,体现的就是人们对土地的敬意与祈求:“公公說风调雨顺,娘娘答五谷丰登。”这副对联可以完整地表达出南角墩人对自然和土地的期盼。这种跪拜维系了很多年,人们甚至在每一个生产组都设置了土地庙,以祈求土地的慷慨给予,这恰恰已经暴露出人们对土地或者说对生活更多的野心。
——摘自《一个人的平原》,周荣池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内容有删节
编辑 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