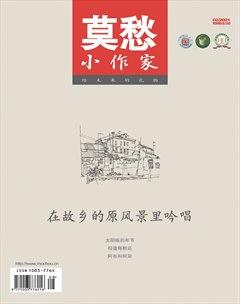种植
1
秋天里忙碌,是乡村的习惯。
秋天忙得比春天要从容。春天是紧迫的,土地像饥饿的小孩,张着嘴叫着嚷着等人用种子去喂饱,迟一步,就错过一年。春天特别让人慌张,心老是提着。
而秋天不同。
棉花白成一片,是摘的时节了,摘得从容,不必像春天下棉籽营养钵时那样抢时赶工。
稻子熟了,农人在田地弯腰挥镰,麻雀们尾随在后,欢快地在收割后的田里觅食。
谷子进仓,整个晒场,在谷子进仓后都留给了新稻草,还有推着铁环奔跑的孩子们。
秋天的云,又大又低。云下,在草垛上散步的麻雀们,小得有点孤单。
炊烟升起,鸡们闲庭信步,女人在屋内纳鞋底,男人整理春耕要用的农具。
新稻草盖成的屋檐下的生活,安逸得很。
炊烟四起时的乡村,锅里煮着新米,灶膛下燃着新稻草。收获带来的喜庆让乡村突然像变成新的一样。就连傍晚时边走边看的狗、归圈的鸡们,也在这种喜庆中变得步态从容。
以上这些,是种植类社会的生活节奏。
2
乡下的秋天,多是用来种植的。
在稻子收割后的土地,埋下大蒜头,洒下芫荽和菠菜种子,这两种植物长得爽快利落,种子入土后,下场秋雨,就长茎长叶了。
莴苣与以上两种不同,有点矜持。萌芽后,要从地里一株株重新移植到开阔的大田里。不喜欢扎堆,这便显出了大家闺秀的气质。
样子好看的莴苣,亭亭玉立,风一吹来,茎是直立的,叶是招展的。两下一比较,边上站立着的芫荽和菠菜,就显得非常普通,不比莴苣的风情。
莴苣再风情,也只是有风情而已,不像黄芽菜,那是满满的风月,盈盈浩荡。
风情与风月,差了许多距离,风情是人间的,风月是天上的。
霜冻之前的深秋,黄芽菜生长的样子像村里女孩,虽然每日里粗茶淡饭,风里来雨里去,但一样是父母爷奶的心头肉,一样的生得粉白娇嫩。
乡村女孩子的粉白娇嫩,是落在南瓜上的那层粉,粉嘟嘟的,轻轻一抹,粉就沾到了手指上,放到鼻前一闻,能嗅到淡淡的清香,那种香,若有若无。
乡下女孩子的白,也是带着植物的某种品质,像莲藕,结实、健康。也像乡下盛饭盛菜的大碗,白,不是纯白,有着陶土的色泽,阳光下一照,红润润的,让人生出许多的欢喜。
乡下的女孩子,自由自在,粉白娇嫩,只要不反了祖上留下的规矩,一切都随着你的性子来长。这就多了莴苣所没有的气韵,风月之妙就在这里。
3
秋天里栽完最后一茬油菜秧,刮过村庄上空的风就日日凛冽起来。
这是冬天来了。
阳光照在庄稼上,虫子们在深土里睡觉,等着明年惊蛰时的雷声来叫醒。地里的活渐渐稀落,男将们扛着棉花卷、拖着大铁锹去海堤边出河工了。
我的村庄离海四十公里左右,但一大半的村民没有看过海。他们过的是种植类生活,海风与河风轮流或交替着从村庄上空刮过。他们知道有海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存在着,但从没有想过去看海。只有村里的男人,他们见到过海,他们每年冬季去海堤边,挽着裤腿,甚至赤脚,流着大汗,挑河、挖沟、引水。甚至,填海。
向大海要土地,一个时期成了当地的重要任务。
村庄里的人,谈起他们的邻居大海时,带着同情,说住在海边可苦了,一年四季没有米吃,那里的地,泛白,带着盐花。那里的人,长得土气,男的女的脸都是黑的,被海風吹的。
他们把海边的人,一律简称为:海里的。
谁家有海边的亲戚来了,邻居们客气地问:家里哪来的贵客啊?对方答:海里上来的二姨奶奶。
有位亲戚住在靠海的村子里,每次来,回去时都背着大包小包。春天来,给过年腌的咸肉。夏天来,给地里长的菜瓜。秋天来,给新米,给晒好的山芋干。冬天来,给过年吃的馒头、年糕。
奶奶每次都嫌给对方带走的东西太少,她对儿媳妇说,别手太小,我们有地,吃掉了还能长,海里能有什么,有地也长不出来,泥都是又苦又咸的。
平原上的村庄,过的是河流带来的种植生活。他们善良地同情大海。
但现在,大批过着河流生活的人,涌到了海边去打工。河流滋润过的土地,基本上都不种庄稼了,建了各种工厂。
而海边,种起了西瓜。河流边年轻的女人,年初五一过,就成群结队下海,等到“五一”节左右,再成群结队回来。
邻居家的桂芳,跟我同年,她是下海种西瓜大军中的一员。返回村里时,带回一麻袋小西瓜,十个,给左右邻居几家分一分。自己家留两只就够了。桂芳种西瓜,每天工钱三百元。午饭由雇主送到田头,十分钟吃完。
海里的人,称桂芳她们这些是乡里的。越往西,离海边越远的,越是“乡里的”。乡里的人,没有地了,在外面流浪打工。
多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河流边的大男将们,坐着拖拉机,拖拉机上成麻袋地装着黄芽菜、青菜、猪肉,一路向东,去海边出河工。
在工地上白天流大汗,晚上喝白酒,吃猪血烧黄芽菜。男将们走后的日子,女人们用玉米粉子在大锅里熬糨糊,拆旧衣服,把门板卸下来摊在太阳地里,刷一层糨糊贴一层旧布。大年初一,全家老老小小就能有一双新鞋穿在脚上。
这就是苏中故乡一个村庄里的冬天。但我的父老乡亲不认为这就是冬天,他们固执地在等待一场雪。
冬至前后,会有一场大雪覆盖在苏中平原上。只有下了雪,才真正是冬天来了。雪怕羞,白天不下,使劲刮冷风,第二天醒来一推门,那雪恨不得贴着门挤进屋来。
下小雪,大多数孩子都不到校,老师也不怪,像父亲一样的笑笑说,太冷了,在家烘炉子吧。
老师们倒是不怕乡下的路难走,都到校汇了齐,也就七八个人。
操场边上有学校的自留地,种青菜、大蒜,学校食堂自用。还开辟了一块地,长红花,夏天开的花漂亮,深秋时卖给乡上的药店。
地里的活,是老师课后带着学生一起做。地窄,学校小,孩子少,师生们挤在一起像做游戏一样就把活完成了。
白雪盖住了操场和那块庄稼地。偶尔有小雀从上面飞过,很快就没入掉光叶子的树丛中。校园四周长满高大的榆树,春天,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捡榆树花,用白糖渍了当菜吃,或者摊在操场上晒干了卖给药店。
榆树花摊在地上,满满的,像下了一场雪。但比雪芬芳,比雪暖和。
真正的雪天一到,也像是榆树花开遍了天上人间。只是少了榆树花的香气。
孩子们不到校的雪天里,老师们派校工去村里买羊,一只。
再从代销店里买几瓶海安粮酒,用的是卖红花的钱。
这一天,学校里的钟不响,黑板前的粉笔灰不飞,屋檐下站着,能听到雪落在平原上的声音。
老师们这时不像老师,像同学们平时看到的亲戚或者邻居,他们快乐地围着桌子,开心地说着闲话。男老师的口袋里别着一支或者两支钢笔,女老师棉袄领口处总往外翻着一片春意盎然的假领子。那时流行假领子,表示里面穿了件好看的衬衫。像善意的谎言,为的是一份体面。
一切都是好看的。
雪后,天晴,孩子们来上课了,教室里有股淡淡的膻味。
老师们招呼一个班接着一个班的小孩排好队,轮流进厨房喝羊汤。碗不够用,几个人一组换着喝。
喝的羊肉汤上面浮着细细的蒜花,绿绿地漂在土白色大碗里。
喝过羊汤,就要期终考试了。考试结束,孩子们扛着开学时带来的板凳,回家过年。
4
春天,万物生长,苗苗们、土地们,分分秒秒都在往上冒着氤氲的热气,越生长越吸吮,人和物都相互吸吮得饥饿难忍。
真饿,虽不至于饿死,半饥半饱更难受,肚里空,嘴里发苦,胃里往喉咙口冒酸水。
别的地方开始暴发血吸虫病。生产队接到任务,给乡上的药店收集癞宝浆,说是这浆制药可以治血吸虫。
乡下人把癞蛤蟆称作癞宝,人手一只铅皮夹子,大人下田小孩上学,口袋里都带着铅皮夹子,随时随地掏出来对癞宝下手。那个春天,万物都在发育生长,刚刚熬过一冬的癞宝们却痛苦无比。
惊蛰后,逮到癞宝后,用发下来的铅皮夹子,往癞宝头上的两只小角一夹,从中挤出几滴白色的浆来,可以换到钱。
哑巴夫妇取了浆后,顺便把癞宝煮了吃,中毒,人没了。无儿无女的,上海没来人,生产队集体捐了钱,把他们埋在通榆河边。
通榆河边的田,都是肥田,埋在好田里,算是厚葬。通榆河边的地,四季长庄稼。
去地里劳作的人,逢到清明或者七月十五鬼节,都记得带捆黄草纸去坟前烧一下,作两个揖。算是把他们当作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自己人。
5
回到乡下,我能看到的田野,越來越少。
田野上盖起房子,高大的屋,成片地堆在田野上。那些是工业园区,当时建起来是为招商引资,先筑巢再引凤。凤没有引来,就空着,就关着,就锁着,就闲置着。
我站在那边,像站在陌生的异乡。
庄稼少了,田野瘦了,风就显得硬削。
在树下随意来回转着。一转就一脚踩到什么硬硬的东西,低头一看,露出一点茎,是块大半个身子埋在冻土里的山芋。
这块土地,上一季定是种的山芋。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不知是不是调皮地躲过了农人的手,还是被可怜地遗忘了?我干脆除了手套,轻轻往土里一探,山芋就跳到了手上。大半个手掌那么大的山芋,还连着一小段茎在土里。
看看手上的山芋,独自笑笑。
笑给田野看,笑给记忆中在田野上奔跑过的自己看。
那时多好,田野辽阔,奔跑自由。哪像现在,离开了田野后,我只会为生活奔波,不会为自由奔跑。
准备往回走之前,我想了想,把那山芋又埋回了土里。
同行的人不解。我说,给土里的虫子留点食吧。
走了两步,回过头来,折回去。把山芋重新往土里埋得深了点,是担心被人发现再刨回去吃了。我说,如果虫子不吃了你,你明年记得要发芽。我对这颗山芋有着天然的信心。
6
后来,过去了好久。
某天,我在开会,突然想起这只山芋,不知它后来发芽了没有?它会忘记和我之间的约定吗?
我开会时的位置,正对着一块大的玻璃。我在玻璃里看到自己的脸上突然有一丝笑容。没有人知道,我跟一只山芋有一个约定,那是我记忆中的田野给我的一份深情。
这份深情,至今还在拥抱着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人。
——摘自《意思》,韩丽晴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本文有删改
编辑 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