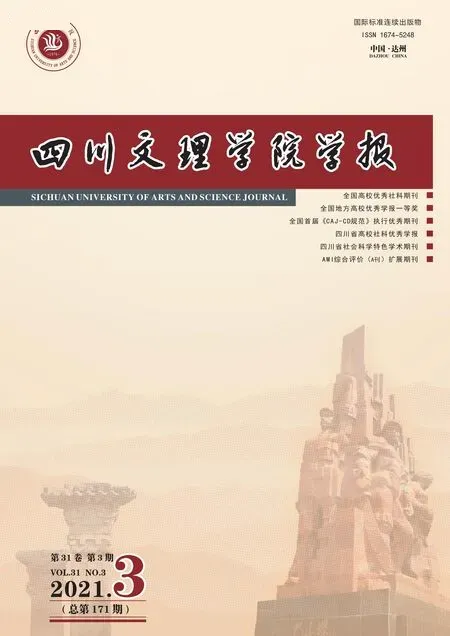乡愁、怀旧、象征与视角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主题与技巧探析
叶奕翔
(广东警官学院 基础课部,广东 广州 510230)
白先勇的《台北人》的是一部风格独具的小说集。在主题上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烈的悲剧意识,透露出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浓重的虚无情绪。这与作家独特的家世、经历有关,在该书的扉页上,作者引录刘禹锡的《乌衣巷》来表达他的人生体验:“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二,是强烈的怀旧感,对于童年记忆中的大陆,白先勇有种复杂而难以割舍的情愫。《台北人》题辞中写到:“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这部名曰“台北人”的作品,其主角其实都是大陆人,其所写的是那个已经过去的“忧患重重的时代”。在写作技巧上,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一是叙事艺术的精雕细琢,在叙事视角、时间、节奏等方面做了精心的处理。[1]在这些方面,《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都可以视为《台北人》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以下即从主题和技巧两方面对这一篇进行细读分析。
一、乡愁与怀旧:《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两重主旨
像《台北人》中其它作品一样,《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故事很简单:作为仆人的王雄(一个大陆籍的退伍老兵),畸形依恋主人家的小女孩丽儿,以致最终发狂而死。然而它的意蕴则并不简单,白先勇在台大外文系的同学欧阳子甚至认为“在《台北人》全集中,《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很可能是最难了解的一篇。”
故事的第一个层面是乡愁。王雄在湖南老家曾经有个白白胖胖的小妹仔,那是他娘从隔壁村买来的童养媳,而白白胖胖的丽儿很像记忆中的小妹仔,所以他把自己的思乡之情全都寄托在丽儿身上。王雄处处以丽儿的保护者自居,因为他过去就是小妹仔的保护者:“他那个小妹子好吃懒做,他老娘时常拿扫把打她的屁股,一打她,她就躲到他的身后去。”然而丽儿渐渐长大,离他而去,他终于发狂而死。欧阳子认为下面几句对话“非常重要”,“因为作者隐约向我们暗示,王雄为什么后来采取跳海方式自杀”:
“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的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
“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的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
“怎么不呢?”我答道,“那边时常还有饿死的尸首漂过来呢。”
“他们是过来找亲人的,”他说道。
“那些人是饿死的,”我说。
“表少爷,你不知道,”王雄摇了摇手止住我道,“我们湖南乡下有赶尸的,人死在外头,要是家里有挂得紧的亲人,那些死人跑回去跑得才快呢。”[2]271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雄之死,就是由于丽儿的离去断绝了他与故乡的象征性联系,于是不惜跳海去“找亲人”。
故事的第二个层面,是怀旧。时间意义上的乡愁与空间意义上的怀旧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乡愁不过是另一种怀旧,恰如山姆·尤因的名言:“时隔多年,你终于回到故乡,这才发现你想念的不是这个地方,而是你的童年。”对于王雄来说,这二者更是一体之两面。王雄无疑是一个活在回忆中的人,他全部的人生意义,就在于“过去”。在这个层面上,丽儿就是过去的再现。和丽儿在一起,就是和过去在一起。丽儿的离去,是对王雄的致命一击。在《台北人》中,白先勇写了大量生活在回忆中的人,多是高官,贵族,名媛,贵夫人……这些人怀念过去,是怀念那逝去的荣华富贵,青春美貌。王雄并没有什么光荣的过去,“他原来是湖南乡下种田的”,他的过去有什么值得怀念的?欧阳子认为,王雄沉溺于过去,实际上是沉溺于那种童真的,无尘世污染的世界:
王雄对丽儿的爱情,不是一般男女之爱,而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的执着(Obsession)。也就是说,他对“小妹仔”,对往日简朴生活,特别对年轻时候纯真的自己之无限眷恋与痴迷。他用全部生命力量设想抓住的,与其说是丽儿的感情,不如说是丽儿的童真气息所能给他的“回到过去”的幻觉。如此,卫护丽儿的“童真”(Innocence),使之永久存在,成为王雄生活的惟一使命,全部意义。[2]267
她认为这是王雄的“潜意识”。也就是说,王雄所痴迷的,不是丽儿这个人,毋宁说是她的未经尘世污染的童真。四十岁的退伍兵王雄,是一个不愿长大的人。白先勇借助叙述者“我”,暗示了王雄与丽儿的缘分就在于那种“赤子的天真”。可是,四十岁的人,十岁的心态——这就决定了王雄的悲剧性命运。他的悲剧就在于:一味沉湎于过去,而拒绝现实(这实际上是《台北人》的一个总主题)。丽儿终究会长大,终究会走进世俗社会,她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
如果说丽儿是“过去”的象征的话,那么喜妹就象征了现在:
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3]70
王雄对喜妹的排斥,也就是对现实的拒绝。跟纯洁无暇的过去相比,现实是令人厌恶的(“喜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全身总是箍得肉颤颤的……”),充满肉欲的、堕落的(“她放纵的浪笑了起来,笑得全身都颤抖了,一边笑,一边尖叫着……”)
同时也是强大的,王雄对这现实充满了厌恶,绝望之际,他强暴了喜妹,喜妹没死,王雄却死去了——他没有征服现实,却被现实所征服。
二、象征与视角:《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写作技巧
首先是象征手法的使用。《台北人》体现了白先勇融合中西文学技巧相的努力,使作品具有了所谓“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美学特征。象征是种古老的文学技巧,从诗三百到荷马史诗,从卡夫卡到曹雪芹,在文学的世界里,几乎无处不见象征的身影。从这个意义讲,象征是无所谓中西,无所谓古今的,文学本就是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游戏。但是,象征的使用方法还是有区别的。在中国传统的诗词曲赋中,象征常常与典故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种含蓄蕴藉之美,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美学特征。“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它与杜鹃啼血、望帝啼鹃的典故联系在一起,这是古典诗词中被广泛运用的典故,寄托的不外故国之思、漂泊之苦、思乡之情,如“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宣城见杜鹃花》)在白先勇这里也是如此,它寄寓了上文所说的乡愁与怀旧,本是极为悲苦的情愫,但是作家借用传统文学中的典故写出,并不直言其苦,真正做到了“哀而不伤”。“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是全文的总体象征,如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想必不能领会作家的这层用意。如果按照情节和人物,小说完全可以以“王雄”或“王雄之死”之类作题,作者不仅用它做题目,而且频频提到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王雄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四周“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的草坪上,被丽儿当成马骑。而这成百株杜鹃花全是王雄亲手栽种,因为丽儿喜欢杜鹃花。丽儿上中学后疏远了王雄,王雄变得格外沉默,只是“把那百来株杜鹃花浇个几遍”。王雄死后,我走进园子,“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
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3]76
其他意象,如丽儿(过去)、喜妹(现在),则是在文本世界中,根据语境而被临时性赋予象征意义,更为接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技巧,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加缪笔下的局外人等等。欧阳子认为丽儿和喜儿还分别是“灵”与“肉”的象征。王雄迷恋丽儿,讨厌喜妹,是暗示了作者白先勇对灵肉冲突的思考。她甚至认为这才是这篇小说的“核心”,这样的解读就更具现代主义意味了。
其次是叙述视角的处理。所谓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也就是由谁来看、谁来讲述的问题。叙述视角涉及两个问题,即叙述者的身份和态度。根据这两个方面的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叙述视角,赵毅衡归纳出九种,如第三人称全知式、第三人称旁观式等。[4]《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由“我”来看,而且由“我”来讲,属于第一人称旁观式。与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一样,“我”既是故事中的人物,又是故事旁观者和讲述者。下面就探讨一下其叙述者身份和态度所产生的效果。
叙述者的身份对小说叙事有重要影响,小说家往往对此颇费思量。《祝福》和《孔乙己》中的“我”分别是返乡者和小伙计,前者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潮的知识者,从他的视角写出,目的是要从外部揭示鲁镇人们的精神病苦。后者恰恰是鲁镇底层的普通一员,从他的视角来写,就从内部描绘了鲁镇的社会关系和孔乙己的生存处境。茅盾说的《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由此可见一斑。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有一段话交待了叙述者的身份:“我在金门岛上服大专兵役,刚调回台北,在联勤司令部当行政官。我家住在台中,台北的亲戚,只有舅妈一家,一报完到,我便到舅妈家去探望她们。”这样的身份,让“我”得以带领读者走进王雄的故事。王雄与“我”的关系并不算亲密,但是也能聊聊家常,在与“我”的交谈中,王雄有限度地透露其内心世界,读者得以窥见王雄感情世界,这与第一人称主角视角、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效果都不同。而由于在金门服役的经历,“我”又能够接触像王雄那样的大陆过来的老兵,并感受他们的乡愁。“我”能够接触故事中的人物,与他们交流,但毕竟属于外人,由这样一种视角来写,加以倒叙的运用,王雄的死就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而叙述者则试图带领读者揭开谜底,好像电视栏目中的情境,但与电视不同的是,叙述者最后没有把谜底直接告诉读者,他只是提示。
叙述者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小说的风格。如果“我”只是“客观地”地讲故事,并不发表评论,那么这个小说就会比较客观。反之则会比较主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叙述者大部分时候只是陈述他所知道的故事,所以小说在整体风格上是客观的,欧阳子认为这篇小说“最难了解”,就与此有关。一般而言,客观小说比主观小说费解,最极端的是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完全由人物对话构成。但是《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叙述者并不是完全隐藏了自己的态度。由他的眼睛看到的王雄、丽儿、喜妹,并不一样,描写带有倾向性:王雄木讷、丽儿可爱、昔妹可恶。他还评论那些像王雄一样的老兵说:“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地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这里就暗示了王雄对丽儿的迷恋,是以“赤子的天真”,怀念“女婴的憨态”。而当“我”看到一个在海滨月下拉二胡的老兵时,更是直接点出了他们的乡愁:
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月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3]69
“我”的联想,是一种移情,这就很明确地表达了对王雄他们的同情,并提示了小说的乡愁主题。总之,白先勇的视角处理,使得这篇小说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格:它带有神秘费解的色彩,而又并不像一些现代主义小说那样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