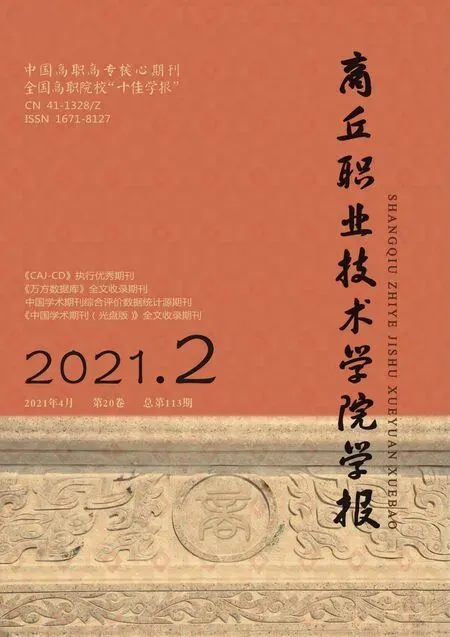“恶讼师”形象评析
杜 强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讼师行业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先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对于诉讼指导需求的客观产物。一般来说,基于“无讼”的儒家思想以及力图减少社会治理成本的政治现实考虑,传统社会的政府官员是不喜欢讼师的。[1]4他们往往刻意宣扬讼师狡诈、逐利的形象,对民间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名化,以此警示民众远离这一“危险”群体。[2]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足以影响大部分人的意志。当一两个恶讼师出现在民间,官方的号召与身边真实的案件得到印证时,“恶讼师”这一形象就被无限放大了。时至今日,人们多认为,讼师都是些鼓讼、诡辩、诈伪的小人,百姓谈及讼师多是呈现出一副嫌弃、鄙夷的面容[3]275-276,甚至今天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多以恶讼师为研究对象①。虽然我们承认个别恶讼师的存在,但单纯以个例印证整个讼师行业“善恶”的问题显然是失之偏颇的。讼师行业自春秋时期出现,至民国时期消亡,在中国存续了约2400年②,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恒久的烙印。讼师行业必然存在着某种特质,使其在不断遭受打压与非议的传统社会中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一、“恶讼师”形象的成因
“恶讼师”形象的出现是对传统社会现实的一种客观反映。中国古代必然一直存在着一些为非作歹、仗势欺人的恶讼师,然而今人对于讼师形象整体污名化的评价显然存在着某种人为力量的刻意干涉,而这股力量正是“恶讼师”形象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对传统“恶讼师”观念的继承以及对讼师行业的误解,也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讼师形象的客观评价。
(一)传统文化对讼师的打压与报复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代表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即“大传统”文化;二是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即“小传统”文化。“大传统”文化引导社会文明的走向,“小传统”文化提供民间的素材。[4]
1.“大传统”文化的打压
契合于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在西汉以后逐渐成为精英文化的代表,它追求稳定的社会环境,强调“止讼”“息讼”,以保证小农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之间尚且能够保持平衡。宋代以降,商业的发展激化了民众间利益的冲突并使得诉讼行为蔚然成风,人们的生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追求稳定的儒家文化依然是宋朝及后世精英文化的主流,这使得“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剧烈冲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精英们将儒家经典视为“天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儒家推崇仁义,反对言利,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式的诉讼因被其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而备受谴责,于是,讼师这一以诉讼谋生的行业受到“大传统”文化的打压。[5]今天能够流传下来的封建法典以及断案成例多是“大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当时的封建精英们对于讼师的厌恶之情随着传世文献流传了下来,由此也影响了今天人们对于讼师形象的认识与评价。
2.“小传统”文化的报复
在“厌诉”的大环境之下,以诉讼为业的讼师多被人们所鄙夷,“不喜无争,乐于有事,所谓讼师硬证之流也”。[1]94加上讼师的身份地位低下,收入竟多高于一般人③,这些足以引起普通民众对于讼师行业的非议了。虽然讼师行业实行的多是明码标价的买卖,求诉之人有着自由选择的裁量权[6],但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无法避免。世人多恃强凌弱,士大夫也为五斗米折腰。人们基于付出高昂诉费的烦闷心情,对于讼师形象所做的评价,必然是一种偏激的、有失公允的报复行为。
(二)官方对“恶讼师”形象的刻意塑造
1.曲解诉讼行为
谈及讼师,人们经常把讼师与“鼓讼”“挑讼”“健讼”联系在一起。虽然讼师需要处理各色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讼师喜欢挑拨诉讼,他们在面对诉讼时甚至表现出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经常劝说百姓凡事谦让,不要轻易走上公堂。[7]“讼之一道,家身所系,非抱不白之冤,不是戴天之仇,切戒轻举,以殆后患。”④然而地方官员们在总结当地好诉之风的成因时,多将其归咎于讼棍的挑拨,“民间控案,多由讼棍而起……播弄是非,挑唆兴诉,希图酒食,需索钱财。”⑤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百姓们便会止讼、息讼、厌讼。⑥地方百姓之所以好讼、兴讼就是由讼棍的挑拨造成的。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讼师群体便逐渐被当权者所厌恶。一个时代当掌权者制定的律法、民间的乡规民约、宗族的家法族规都将“争诉”视为一种耻辱甚至违法行为时,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讼师的地位低下了。但是,从取得的社会效果来看,讼师行业的出现却衔接了律法的刚性与民众的柔性,达到了平复社会纠纷的效果。于是实践中产生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当权者需要借助讼师的能力解决困难纠纷以处理诉讼[8],但又惧怕讼师的力量,使得民众争相求学斗讼之术,从而轻视农桑,干扰社会风气,动乱国基。官府似乎忘记了诉讼乃是人之常情,“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⑦。从古至今,诉讼之风就没有中断过,尤其在商品经济逐渐得到发展的宋、明、清时期,好讼之风更是盛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世人将其完全归咎于讼师的挑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2.打压讼师行业
讼师这一职业由来已久,他们通过代写呈送官府的诉状或者为求诉之人在诉讼中出主意得以赚钱谋生。客观上,强调民为邦本、止讼、息讼的朝廷对于讼师是呈打压态度的。为了彰显皇权圣明,欲缓和社会矛盾的朝廷虽然有时会默许讼师行业的存在以追求个案的公正,但讼师这一职业从来没有因此而走上升迁的正途,国家也没有专门设立研究讼师职业的官方学问。讼师掌握着游离于官场与民间的诉讼力量,可以安然地享受非耕之食,但也承受着民间的舆论压力和官方力量的打击。相比于官府,他们不具有权威,没有威慑力,所以花了钱打官司却没得到应有回报的求讼者,必然将其内心的烦闷之情有意流传于民间。⑧对于地方官吏而言,任职辖区内诉讼案件的多寡是其政绩考核的重要考量,甚至刑部还明文规定了对讼师的处罚条例。⑨“凡教唆讼者,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 与犯人同罪”⑩,因此,一些地方官到任后发布的第一批告示中往往就包含严惩讼师讼棍的内容[3]275-276。长此以往,得罪了官方与民间力量的讼师便以“恶讼师”的形象一直流传了下来。甚于明清之际,一些家法族规将讼师行业比作奴婢、优伶等贱业,并对于一些从事讼师行业的族人予以“革谱”“出族”等惩罚[9]。
(三)今人对于讼师形象的误解
讼师不同于律师、刑名师爷与讼棍,对讼师形象的合理建构应当与此三者进行区分。
1.讼师与律师
出于对讼师与律师的误解,有人将讼师看作传统中国的律师。[10]人们对于律师的不解与厌恶,由此也拓印到讼师身上。我们应当清楚,讼师行业产生于中国本土,于民国时期逐渐走向消亡,律师行业则移植自西方国家,于清末进入中国社会。讼师和律师是两种不同行业,存在较大的差别。首先,讼师生活在重实质轻程序的司法环境中,地方官员追求的是对实体真相的发现,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违背一定的法律程序,也是被朝廷所认可与肯定的;律师行业则产生于近现代社会,他们在办案过程中必须注重程序,程序价值甚至是重于实质结果的。其次,讼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他们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收入,也可以遵循自己的良心选择是否帮助求诉之人打官司;律师受到的约束则要更多些,律师的执业既要受行业协会、组织章程的统一约束,又必须借助律所的力量才能承办案件、获得收入,并且其服务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最后,讼师多出身于科考落榜的儒生,较之于今天必须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加以实习一年才有可能取得执照的律师而言,讼师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11]概言之,律师与讼师之间不存在承继关系,两者在指导思想与办案流程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将讼师理解为古代律师。
2.讼师与刑名师爷
讼师与刑名师爷虽然都是传统中国独有的诉讼力量,但两者在身份、地位、工作内容与工作对象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人们对这两类不同职业的模糊界定,影响了世人对讼师形象的客观评价。虽然讼师和刑名师爷多出身于考场失利的落魄书生,并且因从事基层诉讼行业不被社会所认可,但是,两者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不甚相同的,因此,不能因两者的职业出身与从事内容的共性而将两者混同。首先,讼师的案源来自民间,收入并不稳定,是个能者多劳多收入的行当;刑名师爷的收入则相对稳定些,他们多在幕后帮助官老爷处理地方上的诉讼纠纷,靠拿官老爷的赏钱营生。其次,讼师凭借自己的智慧帮助求诉之人谋求名利;刑名师爷则依据自己对案件的理解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帮助官老爷处理诉讼纠纷,两者多在程序上处于对立的立场。[12]最后,社会对两者的认可程度不一,刑名师爷因在官老爷手下谋生,虽不能说是狐假虎威,但较于中人更易依傍些权势,一些家法族规因此只将讼师比作优伶娼妓等下贱行当,而对于刑名师爷多是没有歧视之意的。[11]48
3.讼师与讼棍
一般认为,讼棍专指那些无端生事、挑拨离间的恶讼师。这一说法具有以偏概全之嫌。对讼棍的理解不能将其限定为特定职业的不良群体,讼棍之所以会被地方官员们厌恶,是因为他们无端惹是生非,扰乱了地方的治安,破坏了当地的民风。正是因为那些无端生事的刁民、暴徒引发了一系列诉讼行为,这才催生了讼师行业的存在,因此,讼棍的范围不能局限于助长兴诉之风的恶讼师,还应当包括扰乱社会治安的刁民、暴徒等一类群体。清朝官员王有孚指出,讼师专指帮人词讼、劝人息讼、受人尊敬的贤良,讼棍则不仅包括唯利是图、搅乱官场、劳民伤财的鼓讼者,还包括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污染社会风气的强人、刁民。他认为,“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以此例证,讼棍不同于讼师。讼棍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但不限于讼师群体之中的“恶讼师”;讼师则是一个专有概念,仅指符合帮人词讼、劝人息讼的贤良。当然,这一说法割裂了讼师与“恶讼师”的内在联系,若将帮人词讼、劝人息讼的贤良比作“讼侠”,与助长兴诉之风的“讼棍”相对应,便容易理解王有孚“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这句话的含意。在他看来,讼师不包括“恶讼师”这一群体,一旦讼师助长兴诉之风,便成为讼棍,讼师与讼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
二、“恶讼师”形象的现实内涵
对于讼师形象的评析,应当先明晰其存在的合理性,摒弃上帝视角带来的思维定式,不能局限于成文史料,也不能超越阶级特征对其进行评价。将讼师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研究其超脱于一般民众的行业特质以及社会处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讼师的行为习惯以及其品性。
(一)讼师的社会地位低下
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一方面,政府强调息讼、止讼;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结构特征使得社会在处理矛盾具有“大事化小,小事不扰”的传统。此外,“由家及国”的中国国情也使得一个个家法族规成为约束族人纠纷的初级规范,大多数矛盾在诉讼之前便早早被宗长、族老调解了。一些家法族规甚至认为“太平百姓,不登讼庭,便是天堂世界”[13]。至于那些个敢于敲惊堂鼓的“求诉”之人必然都是自认为受到莫大冤屈,并敢于冲破官府高昂讼费等诉讼门槛,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使得他们必然敢拿出自己半生的积蓄去换一个“理”字!在那个文极而治的时代,讼词多是字字斟酌的,一纸好的诉状甚至能决定案件的胜负,所以,“求诉”之人多是愿意花大价钱换取一纸好的诉状的。我们应当清楚,虽然传统社会有意对讼师进行诋毁、打压,但民间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并未随之减少。[14]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由于当事人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心中难免有些郁闷,对官方的收费标准他们不敢在明面上抱怨,至于讼师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阻止这些怨言了,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里,民众也乐于将这些幽怨之语作为床前、饭后的谈资。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会对这些个“不识五谷”“不劳而获”的讼师嗤之以鼻。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乡土社会,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15]。
(二)讼师具备一定的才学傍身
对家族难以解决必须诉诸官府的纠纷,世人多想到的是找一个好讼师,写一纸好诉状。在讼师存在的年代里,由于教育的落后,知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是说求讼之人不想自己写诉状,而是能识字、写字的人依旧只是少数,代写诉状、提供律法咨询在当时确实是个技术活。讼师们能以一纸诉状唬住不识字的庄稼汉,但对于科班出身的县太爷,甚至十年寒窗止于县衙的刑名师爷却是不够看了。“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16]所以,讼师想要谋生必然是要熟读经典、通晓律法,这样才能在一纸诉状上和当朝文人议论是非。仅仅能写一纸讼词是远远称不上优秀讼师的,并且讼师也没有资格让日理万机的县太爷陪他咬文嚼字。于是,讼师在书写诉状时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多站在县太爷的角度议论案件得失。这使得官府乐于按照他们的意图解决问题,因此也就可以顺势实现胜诉了。如清代曾六如所著《小豆棚》中疙瘩老娘对于寡妇诉求改嫁的诉状:“叔壮翁大,嫁与不嫁。”该诉状正是掐准了伤风败俗行为影响官老爷的年终考绩,使得其不敢轻视这一诉求,继而以短短八字诉状便取得了胜诉。
(三)讼师掌握一定的语言艺术
一个优秀的讼师所写的诉状必然是妙语丛生的。据《小豆棚》记载,江北连年遭逢灾害,米贩们纷纷到江南收购粮食。江南人担心大米的大量外流会使本地米价上涨,因此阻止大米交易。于是,江北地区人们就请疙瘩老娘书写诉状:“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短短两句话,江南官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大米往江北运送。究其原因,疙瘩老娘的语言是很有技巧的,原本是一国地区间的商业纠纷,疙瘩老娘的一番话,却将这一问题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颇有分地割据之嫌,江南地区的行为就值得深思了。在“文字狱”盛行的当时,这种诉状一出,官府必须妥善处置,稍有不慎便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轻则削官败爵,重则身首异处。讼师的语言应当简练、得体、中肯,切合官府的胃口。高明的讼师甚至敢于利用当时的政治风向对官府扯虎皮、拉大旗。敢这般行动的讼师必然是熟悉官场、胆大心细之流,我们不得不称赞这些讼师的智慧。
三、研究“恶讼师”形象的现实意义
讼师行业及其文化是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讼师形象的研究是了解中国传统诉讼艺术的重要途径。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观,恢复民族自信的征途中,认清传统中国法律职业工作者的客观形象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对“恶讼师”形象成因、内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指导律师行业的发展
讼师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左右中人钱财、命运的能力,当局者欲借助其力量维系统治,但又担心其势过大对于国家的治理造成恶劣影响。因其门槛太低,易成大势,中人竞相言律法而不重视农桑的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随着讼师数量的增多,社会上的争诉之风随之盛行,“神授王权”的君本位统治根基也将会变得岌岌可危。至于律师,在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背景下,社会生产力借助于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家不仅不惧怕民众竞相言法律,甚至主动普法,鼓励民众研法,以培养民众的法律意识。因此,结合“恶讼师”形象产生的政治因素,为推动律师行业的良性发展,国家既需要提高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又需要加强对律师行业发展方向的引导与规范,按需发展这股异于中人的力量,以使得今日之律师在习得讼师这一行业被中国社会长久需求特质的基础之上,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二)建立多元的纠纷调解机制
时至今日,中国民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厌诉”心理,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淡薄,普法教育、宣传的力度不到位。因为“厌诉”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内生特质,“厌诉”不代表逃避现实、回避问题,法律也不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唯一手段。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并非要求当事人一旦遇到诉讼纠纷就诉诸法庭,这样必然会引发“诉讼爆炸”,不利于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夸大法律的作用。在乡土社会的一些小额经济纠纷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或者在第三人主持下的斡旋调解,较于法律的强制干涉,不仅更具有效率,而且当事人双方的意志也会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尊重。欲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国家需要重视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机制,继续发挥传统社会中家规、乡约等一系列“软法”的调解、规范作用。多元纠纷调解机制的建立,使大量规模小、影响小、危害不大的社会行为在民间得到有效处理,那么,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便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各类复杂的社会问题了。
注释:
① 陈智超:《宋代的书铺与讼师》,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东京同朋舍1989年版;陈景良:《讼师、讼学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等等。
② 自邓析所处时期(公元前545年-前501年)到民国初年建立律师制度(1912年颁布《中华民国律师暂行章程》)止,约2400年。
③ [清]徐珂:《清稗类钞·册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6页。载:周某曾做太守,因不法之行被迫辞职归乡后,“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所入与作吏时略等。周喜曰 :‘吾今而后知绅之足以致富也,何必官 ’。”
④ [清]讼师秘本《惊天雷》。
⑤ 同治年间四川南部县发布告示《禁止教唆,以清诉源》。
⑥ [春秋]孔子:《论语·颜渊》:“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⑦ [清]崔述:《无闻集·讼论》。
⑧ 据霍存福在《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一文统计相关文献得出结论:“讼师多是被动接受请托。”那么流传于民间的“民间讼牍繁多,……全由于讼棍为之包谋 ”便值得思考其真伪了。
⑨ [清]沈书成《则例便览》卷四十七《刑·杂犯》载:“地方官失察讼师,罚俸一年;若明确不报,经上司访拿,降一级调用。”
⑩ 《大清律例·刑律·教唆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