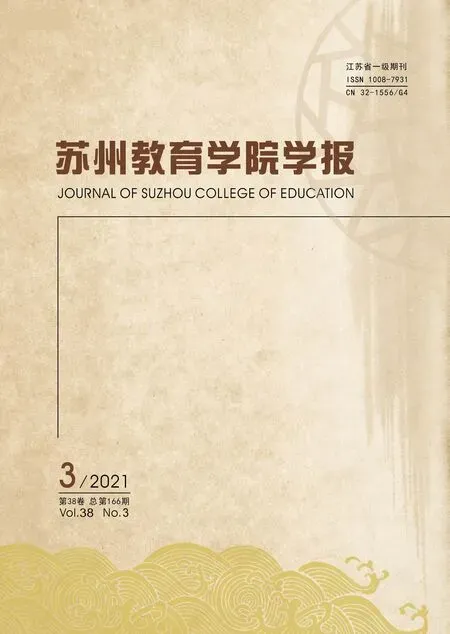张爱玲笔下民国女学生的“身体”困境
——基于教育身体史视角
周 琳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 200062)
随着近代社会对女子教育关注的增多,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传统意识形态下女性的身体枷锁不断受到冲击。因此,培养拥有独立意识和个体价值的新时代女性成为当时女子教育的重要议题。传统的史学研究往往运用正史或官修史籍史料,从宏观角度回顾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女子教育的整体状况与主流思想。然而回溯历史,近代参与教育的女子对自己的身体是如何感知的?她们在社会的种种约束中是顺从还是觉醒?又是如何尝试打破“身体”困境的?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将“身体”作为分析女子教育的有效视角,以捕捉教育参与者个体身体感知的独特性。
一、教育身体史与新史料
教育身体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史学视野的下移和教育学的“身体”转向促成了这一学科的诞生。从历史学角度来看,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将视野下移,研究对象从精英和官方转向广大民众和民间,史学的研究重点从思想史和制度史转向了活动史,即聚焦基层人物和日常活动,关注人的在场。从教育学角度来看,此前,教育学一直没有“身体”的教学。李政涛提出教育学要回归教育生活,回归“身体”。转向身体, 就是对人的体验和感觉的转向,方能将教育学中的“人”具象化,将“生命关怀”落到实处,落到每一个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身体里。[1]教育身体史专门研究和重点考察历史上教育参与者在教育乃至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身体”的生成与改变及“身体”变化对教育、社会、时代会产生的影响。根据周洪宇、李艳莉的定义,教育身体史呈现过去教育参与者在教育活动中的“身体”,包括其服饰、发型、情感等细微之处。[2]从教育身体史的角度来看,教育史就是教育参与者的身体被压制、规训或反抗、解放的历史。
国内的教育身体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周洪宇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呈现出理论建构和具体研究两大发展路径。理论建构方面,周洪宇、李艳莉阐明了教育身体史以生命关怀为精神内核,让教育回归“人”本身[2];作为教育史生长的新起点,关注教育参与者真实的生命参与和生命体验[3];从多学科角度出发,探究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给予教育身体史的坚实学理支撑[4]。以上研究明确与深化了教育身体史的学科内涵,同时为教育身体史的具体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具体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于明清时期女子的身体教育[5]、民国时期大学的“拖尸”研究[6]、民国时期学校中的女子“剪发问题”[7]等主题进行了探索,紧扣“教育”与“身体”两大关键词,具象地呈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参与者生活化的体验,揭示了其身体话语背后各种权力与自我力量的交织。由此,教育身体史为考察历史教育活动提供了妥帖的切入点,也为当代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经验。
史料的多元性是教育身体史的一大特征。随着史学视野的下移,史料的来源也随之拓宽,甚至包括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那么究竟何以成为史料?钱锺书指出:“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8]周洪宇认为,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只注重正史或官修史籍史料的运用,正史史料应当与笔记小说史料并行。[9]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将小说作为史料,用以探究校园叙事、教育改革等。就教育身体史领域而言,作为教育身体史的史料,小说作品中对于人物的外貌、神态、心理活动乃至生活环境、社会风貌的详尽描写与刻画,能够打破传统史料中人物呆板枯滞的形象,并能清晰再现教育参与者的“身体”生成和身体、文化、社会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例如,于洋就从《红楼梦》中透露出的身体符号和女子教育入手,揭示明清女性的身体意识以及身体教育对女性的奴役与暴政。[5]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张爱玲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小说对于女性(尤其是女学生)这一群体的服饰、行为、场合等一系列身体话语都有着浓墨重彩的描绘,为身体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打破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单一控诉,将女性放置在自身的地位演绎,深入女性的精神世界,进而呈现出民国时期女性的自我救赎和与男权社会的对抗。[10]本研究尝试以张爱玲小说为史料,探究民国时期女子教育参与者“在场”的“身体”困境,还原生命个体对身体约束与打破的感知和行动,从而丰富教育身体史的研究内容,也为当代的女子教育与女性身体话语的应对提供借鉴。
二、民国女学生与张爱玲作品
“女学生”是一种现代身份建构,这一群体的本土形成始于清末。女子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她们接受教育的空间是以家庭为主的,直到民国时期女子学堂的兴建,女子教育才被民众谨慎接受,从而走入公共领域。尽管近代女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识,然而遗憾的是,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还是难以真正实现女性独立和男女平等。正如梁启超在《倡设女子学堂启》中所写:“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1]女子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最终回归到了家庭和妇道上。同样,近代重要的女性报刊《女声》中提到,多数女学生最终都选择回归家庭,管家育儿,而真正成为独立的职业者实在凤毛麟角。[12]这一特殊时期的女学生群体受到了各方关注,尤其是其形象、情感和命运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呈现,胡子沛就通过对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女学生书写进行研究,考察了“五四”文化理想的价值导向。[13]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对“身体”关注的加深,女学生的“身体”特征也成为了研究对象,如周洪宇、周娜曾从民国女学生的“剪发问题”入手,窥探民国时期到“五四”时期的教育话语。[6]
张爱玲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女作家,她的贵族身份和出众的才气让她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拥有了自成一派的精致和“扭曲”,也让她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在场”那样醒目。她本身是一名教育参与者,在散文《天才梦》[14]、《童言无忌》[15]、《银宫就学记》[16]中,有她对自已“身体”生成进行的片段式描绘。纵观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对女学生的描绘,从《五四遗事》[17]到《半生缘》[18]、《小团圆》[19]等,其笔下的女学生往往被置于十里洋场中的城市现代叙事之中,在新式教育和传统命运之间迷茫、徘徊、苦苦挣扎,《沉香屑·第一炉香》[20]中的葛薇龙、《茉莉香片》[21]中的言丹朱和《封锁》[22]中的吴翠远都是典型代表。因此,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女性作家,张爱玲笔下的女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命运走向能够较好地反映出民国时期新式教育背景下女学生的生存状态,进而探寻出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目的、状态及出路。
在“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兴文化思潮影响下,城市是那些女学生开放的生存空间,但是,纸醉金迷中的道德标准也是她们的生存困境。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目的并非是将她们培养成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即便思想启蒙已经使她们有所觉醒,但是女性依旧是男性的附庸。作为受教育者的女学生的“身体话语”,从服饰、发型到言行举止,在这一时期的女性群像中都是突兀的、迷茫的。张爱玲用她独有的时代敏感,在作品中生动还原了民国时期夹杂在学校和社会、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女性无法掌控“身体”的无力感,她忠于女性身体的书写恰恰为教育身体史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真实生动的史料。
三、张爱玲作品中女学生的“身体话语”
张爱玲作品中对女学生出场的外貌、衣着、神态举止都有精细的刻画与描写,这有赖于她对金钱、服饰的毫不掩饰的钟情。她曾在《童言无忌》中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15]268作为一个七岁便能初试写作的天才少女,她急切地用“爱司头”“高跟鞋”这些身体表征来证明自己的成长和骄傲。下面笔者以张爱玲作品为例,从女学生的“身体”服饰、“身体”动作、“身体”场合三个方面,解读民国时期城市女学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观念。
(一)“身体”服饰:朴素与华美之间
服饰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征。根据周洪宇的观点,自晚清以来,女学生作为有别于中国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外在装扮有很大改变,摒弃了传统的华丽繁复,提倡西式的简约、朴素。张爱玲这样描写她并不愉快的中学时期:“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15]268服饰的寒酸带来的是心灵的羞耻与憎恶,与多数家境富裕的学校同伴格格不入。《心经》中小寒穿着“孔雀蓝衬衫与白裤子”,长着仿佛神话里小孩的脸,“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23]88她的同学们“一个戴着金丝脚的眼镜,紫棠色脸,嘴唇染成橘黄色的是一位南洋小姐邝彩珠。一个颀长洁白,穿一件樱桃红鸭皮旗袍的是段绫卿”[23]90。就算是身着符合女学生身份的服饰时,依然可以窥见张爱玲笔下女学生群像对华美服饰的追求,女主人公往往是素净简约的,但是眉宇神态之间却又充满了孤傲与不安定。
此外,女学生的“身体”服饰兼具西方殖民地特征和传统的东方色彩。《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开场穿着南英学校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她又与其他的女学生一样爱赶时髦,“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20]256现代化和清末服饰款式的拼接,女学生的形象夹在两个时代潮流之间,显得不伦不类。初入姑妈家的葛薇龙,面对为其成为交际花准备的一应俱全的服饰,“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20]267少女忍不住对华服的向往,试起衣服来一夜也不曾合眼。身处香港沦陷区,大户人家女性的华服有着英国上层阶级传统的保守派习气,显示出与女学生身份不相符的骄贵矜持。
(二)“身体”行为:规训教化和打破禁忌之间
张爱玲笔下的一部分女学生无论是身着朴素校服还是华美旗袍,“身体”行为不断在打破原有传统男女之间的“身体”距离和“身份感”。《心经》中年近二十的小寒向同学介绍父亲时,亲昵地挽着父亲的胳膊。单独与父亲相处时,“只伸过一条手臂去兜住他的颈子”[23]100。即使是母亲进来,“他们两人仍旧维持着方才的姿势,一动也不动”[23]100。小寒对于父亲禁忌而疯狂的爱,通过她逾矩的“身体”动作向众人和母亲宣战。《封锁》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乖乖女吴翠远与偶然换座位到她身边的有妇之夫吕宗桢在电车封锁时擦出了短暂的爱情火花,“宗桢与翠远给他们挤得紧紧的,坐近一点,再坐近一点”[22]94。但是封锁一结束,恍然如梦醒时刻,翠远一睁眼望见宗桢遥遥坐回了他原先的位子上,此时身体距离的拉开竟比下车更加决绝,意味着男主人公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同没有发生,一切仅是女主人公的黄粱一梦。《色戒》[24]中,爱国女学生王佳芝用身体换得刺杀易先生的机会,但最终因身体的爱欲交织,年轻的心沉沦其中不能自拔,而错失了刺杀的良机。
张爱玲在《色戒》中提及:“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24]238感性“身体”话语的最终落点是女性内心的情爱和灵魂的自由。在女性“身体”被家庭、学校和社会道德教化和严格规训的时代,城市中的新女性用稍许逾矩的“身体”行为和亲昵距离来传达自身的欲望和追求,“身体”的反叛象征着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
(三)“身体”场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
张爱玲笔下的女学生不但出现在公寓、家等私人领域,在舞会、电车等公共领域同样有她们的“在场”。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权力规训理论”认为:纪律倾向于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以便于权力规训置于其中的身体。[25]女学生的“身体”场合从封闭的家庭转向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打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频繁地出席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等社交场合,但是出席这些场合对她而言,仅仅是单纯炫耀衣服的机会而已。《封锁》中,吴翠远是更为独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形象,新兴家庭的乖乖女毕业后留校成为英文助教,自己乘坐电车上下班,电车上的短暂邂逅碰撞出爱情的火花。这些学校、家庭之外的地点也开始出现在小说中,女学生,或者说是城市女性不再被束之闺阁,她们有了自己的社交和工作,彰显了受教育女性的独立。
女学生的“身体”场合虽扩展至公共领域,但是“回归”私人领域的心情更盛。《心经》中小寒对父亲说:“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23]104她为了自己对爱的信仰,自愿圈在这公寓的一方天地里。《封锁》的结局里,宗桢将命运之思寄托于乌壳虫,最终还是“爬回窠里去了”[22]96。事实上,“回归”一词不甚准确,张爱玲作品中的“身体”在学校中的出现被弱化,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总在思想依旧保守的家庭和纸醉金迷、将女性物化的社会之间徘徊不定,如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人”一般。正如葛薇龙姑妈所说的:“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20]290她们不再甘于沦为男性的附庸,社会也尚未给她们合适的出路谋生,“出不来”又“回不去”,这成为民国时期现代城市女性的“身体”困境之一。
四、民国时期女性的身体困境:审视教育目的
自女子教育被列入学制系统以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女性数量不断上升。在接受近代学校教育的同时,女学生在外形上也一定程度接受了西方的服饰装束。当时的《女学生杂志》对女学生的装扮有这样的描述:“女有长辫流传近,帽结襟花香坠粉。乌膏注发发似泥,两髻垂垂覆额低。金珠百货饰辫服。”①转引自杨玉洁:《民国女报视域下的早期中国女学生——以〈女声〉杂志报道为例》,《青年记者》2017年第17期,第112——113页。因此她们成为新型淑女的代表,其时髦装扮也引发了一股模仿之风。然而,女学生受教育之后的出路依旧狭窄,她们眼高手低,始终无法摆脱男人的附庸地位与家庭的束缚。曾越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女学生群体形象,发现女学生从清纯少女走向摩登女郎的形象路径,实则反映出女学生物欲渐强而内涵渐弱的特征。[26]
首先,在民国初期能够进入学堂学习的女性大多来自家庭条件优越、父母思想开明的新式家庭,但是家庭对女子教育的结果期待却多是结婚。其次,即便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足,社会民众守旧的偏见却未曾改变。《封锁》中的翠远的教书能力在学校里被质疑,在家庭中也得不到理解,曾经竭力鼓励她用功读书的家长已经对她失去兴趣,宁愿她当初匀出时间找个有钱的老公。以翠远为代表的这一类女性深受家庭守旧观念的束缚,她的电车情缘更像是一种赌气般的叛逆:不妨找一个不但有钱、还有太太的男人气气他们罢了。新时代的女性也要面临这样的窘境,张爱玲不由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20]291在这种境况之下,不再有郎才女貌的爱情,仅剩下物质与精神不相匹配的悲剧婚姻。
此外,男性与社会将女子接受教育看作一种规训手段,女性接受教育是为了取悦男性。在《封锁》中,宗桢絮絮叨叨地向翠远抱怨自己的妻子连小学都未毕业,多么差劲。男性是希望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是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和生活的趣味。有趣的是,在散文《银宫就学记》中,张爱玲写到了自已观看的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渔家女》,影片中的美术家坚决地说自己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但随后他却不由自主地教渔家女认字。中国学者以往便有教小妾读书的爱好,因为他们鲜少有机会教女学生。因此,女子教育虽然被社会所认可,但目的却是出于对男性趣味的迎合,女子教育沦为男性或社会对女性进行规训的手段。
当时的女子教育未能帮助女性实现自我解放,或是让她们有机会为改变国家命运出力,而仅仅成为了女性谋求“美满婚姻”的装饰品。[26]归根究底,民国时期的女性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目的的偏离,导致女性自身的身体解放举步维艰,最终大多数女性还是回归了家庭和婚姻。无怪乎在《天才梦》中,张爱玲的母亲说出“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14]202这样决绝的话来。外界进步的冲击无法撼动人们内心的守旧,只是徒增女性的苦痛与挣扎。社会将她们视作取悦男性的“花瓶”,家庭把她们能够嫁给有钱人视作最好的人生出路,最终她们已经不知自己“身体”的价值和位置何在,而处于无处可依的困境。
五、结语
作为教育的参与者,张爱玲笔下的女学生为我们展现了属于民国时期的城市的最生动的“在场”。女子教育和新思潮的兴起,使这一群民国女学生得以走出家庭,在学校和社会上占得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守旧观念和家庭的束缚形成的现实困境,使“身体”徘徊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怯懦之间进退两难。如今,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然不同往日,但是相较于男性,社会生活中依旧透露出对女性更为严苛的身体审视和约束。女性应当对自身的身体形象有正确的认知,对女性的教育期待和教育目的应当被进一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