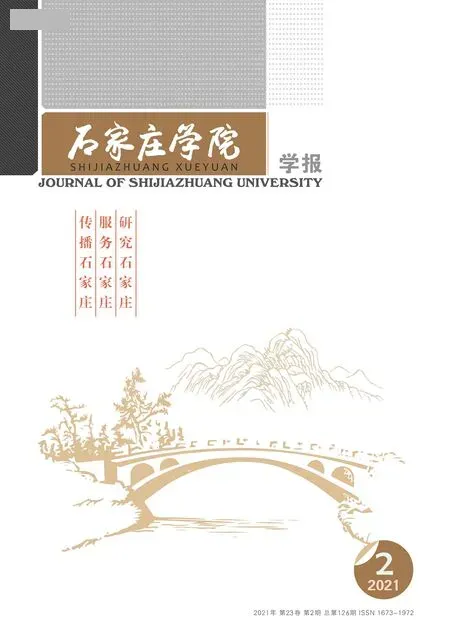“异态”时空下的“苦难”叙事
——论《中国文艺》的“写实小说”
高姝妮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000)
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人实施严苛的文化统制,但为了转移民众的政治视线,也鼓励文学创作,以期为建设“大东亚文化共荣圈”提供相应的文化基础。《中国文艺》便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由旅平台湾文人张深切在北平创办的,从1939年9月创刊至1943年11月终刊,共出版9卷51期,是华北沦陷区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尽管《中国文艺》是日本人出资支持创办的,但其执笔的编刊者却力避日本殖民意识形态的干涉,秉持“文化兴邦”的办刊理念和“纯文学”的启蒙追求,与日本的文化政策斡旋,使《中国文艺》“纯文学”的文化立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中国文艺》的办刊原则引起了有识作家的共鸣,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艺》从重振民族文学与重振民族精神两方面探索北平文学的自救方略,所刊载的文学作品体现出其文学启蒙导向。
《中国文艺》一共刊载了243部中短篇小说,其中除一部才子佳人小说①才子佳人小说为林凤的《小姐们》,载1939年9月《中国文艺》的创刊号。、一部武侠小说②武侠小说为毕基初的《青龙剑》,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2卷第3期。和六部色情小说③六部色情小说都是公孙嬿的作品,此处称为“色情小说”是按照当时对公孙嬿描写男女情欲、肉欲小说的定论而来的。这六部小说分别为:《海和口哨》《北海渲染的梦》《流线型的嘴》《解语花》《卸妆后的生命》《镜里的昙花》。外,其余的235部小说则以现实为基点,从家庭、社会、文化等方面抒写“苦难”的“写实小说”。这些“写实小说”既有对社会暗角的暴露讽刺,也表现家庭生活的困境;既批判封建愚昧的腐朽观念,又抒怀青年人的忧郁情绪。其多元的主题开掘苦难时代民众的精神困境,展写战争背景下满目疮痍的社会图景,战争罹难、沦陷之辱、社会无序、生存维艰使得“苦”成为这个时代的共鸣。《中国文艺》刊载的小说将作家对“苦”的情感体认予以文学的表达,使文本在作者的关切、同情和理解的情感作用下拉近了作者与民众的距离,建立了作家与民众的血脉联系,由此成为了受难同胞的民族语义场,以苦难的民族书写建构了文学启蒙话语。从家庭到社会,从“他者”到“自我”,作者对“苦难”的书写与现实的反思拓展了理性精神启蒙的维度。本文以此为基点,将《中国文艺》刊载的“写实小说”的主题分为家庭小说、暴露讽刺小说和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进而解读《中国文艺》“写实小说”潜隐的人文关怀与民族情蕴。
一、家庭小说
“家庭”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根脉,情与理的交合使“家庭”形成了复杂的文化体。以“家庭”为中心建立的亲情网,既饱含血脉深情,又兼具宗法礼制。因此,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成为千年封建制度统治的基础。在传统的“家庭”秩序中,以“忠孝”为核心的等级观和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观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所以“五四”新文化先锋者以摆脱“旧家庭”束缚的方式来打破封建文化的桎梏。于是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离家”成为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解放的迫切需要,并被赋予了理性启蒙的寓意。“家庭”分割着“五四”新文化先锋者的文化教养与精神追求,他们在家庭情感和文明制度的矛盾纠葛中难以明晰“家”的去从,因而“离家”变成了“五四”新文化先锋向封建文化“宣战”的“仪式”。这是“五四”新文化先锋者决绝的反抗亦或逃避,在此,由“离家”而衍生的“五四”新文化观对“家庭”伦理道德关系的重建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深受“五四”新文化观影响的北平文人在思考新型“家庭”伦理关系的同时,亦在有意延伸“家国同构”的民族意蕴。“家”是“国”之本体,而“国”亦建构着“家”的伦理秩序,“家”的困境暗示着“国”的危难。在此,沦陷区作家不仅探讨文化代际之时“家庭”的道德伦理困境,也思忖着“国难”之时的个人处境与选择。
尽管“五四”新文化观使“离家”的进步意义得到认可,但从家庭内部关系看,“五四”新文化先锋者的“离家”产生了不可规避的道德困境:一方面,他们追求自我解放而成为家族的“背叛者”;另一方面,他们对家庭责任与角色的逃避使其成为家庭生活中的“缺席者”。知识分子的“离家”问题是《中国文艺》刊载的家庭小说中颇为关注的焦点,这些小说多从道德立场反思“离家”之举与家庭关系重建的内在关联。《妇道》①详见萧艾《妇道》,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9卷第1期。中的丈夫在北平上学,接受新式高等教育的“丈夫”越发地感受到与“妻子”在精神沟通上的巨大差距,于是这场父母之命的婚姻成为了“丈夫”无以解脱的精神重负,他既厌弃,又想逃离。所以,无论“妻子”为家庭付出多么大的心力都是徒劳,她都无法得到“丈夫”应有的尊重和认可。直到“妻子”在街上发现“丈夫”与“新欢”亲昵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成为丈夫眼中的“家奴”,而不是与他举案齐眉的“妻”。父母之命的婚姻悲剧使传统的中国女性成为时代的弃儿,陈腐的婚姻观被“新文化”解构,相夫教子、勤劳持家的“优良传统”已不再满足男性的婚恋需要,在崇尚两性精神契合的“新婚恋”时代,深谙封建家庭伦理观的传统女性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情地碾压。《离婚》②详见芦沙《离婚》,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2卷第3期。中“维”离家求学,“妻子”留在乡下忙于家务、伺候老少,为了让自己有正当的休妻理由,“维”设计让“妻子”和“长工”发生关系,妻子的忠诚和勤恳皆毁于丈夫的算计中。当计划成功时,“维”非但没有道德的自谴,反而自鸣得意于找到了“离家”的正当理由,随即便“堂而皇之”地追求城里的“杨小姐”。“维”利用妻子的负罪救赎着他对婚姻的背叛,他以僭越道德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思想解放”和“婚姻自由”;而丧失自我价值认同的妻子只能在“家庭”与“婚姻”中塑造“自我”,虔诚地以“夫”的意志为重心。不料,极力恪守妇道的妻子陷入了丈夫“违道德”的算计中,当她承受着道德自谴的碾压时,丈夫却在“违道德”的欢愉中窃取精神的自由解放,“真道德”与“违道德”的命题审视着文化代际之时传统两性婚姻关系的复杂变异。《中国文艺》的家庭小说多以女性视角探讨女性在新旧家庭关系中的角色重塑,“家庭”不仅是生活的场域,也是女性的精神场域,一方面“家庭”真切地表现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反映出“五四”新文化向旧文化冲击时隐在的家庭道德困境与女性精神危机。
男性知识分子以其绝对的社会话语权倡导新道德的重建,然而接受新文化的女性知识分子却在父权的压制下陷入新旧道德的双重困境,她们既无话语权也难以解放自我,读书让她们获得了自我的认知,即便无以改变她们的宿命,但至少她们为了确证自我做了些许的反抗。如:“林宁”③详见寒流《林宁》,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9卷第1期。为争取婚姻的自由,不顾父亲的反对与“黄诗庚”私奔;“芸”④详见芦沙《手帕》,载《中国文艺》1942年第6卷第3期。为了坚守自己的爱情,反抗家里的指婚,无奈跳窗而亡,以死抗争;“我”和“纲”⑤详见纪莹《白色的忧郁》,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9卷第3期。幸福的家庭生活因他乡下妻子的到来被打破,“纲”以“恋爱自由”之名与乡下的妻子断绝往来,并同多位女性确定过恋爱关系,“纲”的自私、滥情与逃避让“我”果决地放弃这段荒唐的婚姻……由此看来,接受新文化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独立意识,自我价值的认同使她们渴望女性的独立、自主、自尊,于是勇敢地向旧道德发起挑战,极力争取“离家”与“成家”的自由选择权。
在“五四”新文化观的影响下,“家”建构了两性婚恋自由的理想,然而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自由的婚姻观让他们在情与理、本我与自我间挣扎,家庭道德与婚恋理想分离着他们的灵与肉,继而形成了夫、妻、情人间异化的两性关系。“家”限定了道德的边界,婚姻的忠诚、责任、承诺都守护在这一边界中,而越界的爱与情愫只能潜隐地滋生在婚姻的暗角,被赋予“不义”之名。《七天》①详见侯少军《七天》,载《中国文艺》1939年第1卷第1期。中的“均”和有夫之妇“玲玲”相爱,最终“玲玲”无法承受道德的谴责抑郁而亡;《夏日》②详见吴明世《夏日》,载《中国文艺》1942年第6卷第6期。中刚刚步入婚姻的“李玫”准备去医院堕胎,因为孩子的父亲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前男友,然而面对“家庭”她又无法宽宥自己的欺骗,于是她决定堕胎来消除对丈夫的惶恐和不安。在新文化的观照下,婚姻与家庭是维系两性关系的道德约束力,婚外情背负着“不义”“不仁”“不道”之名。然而新文明与旧道德的矛盾激化了情与理的冲突,于是行尸走肉的婚姻、无以认同的婚外情、为夫不仁的丈夫、为妻不贤的妻子、为人不义的情人便构成了两性婚姻关系的异化形态。《中国文艺》的作家探讨文化代际之时婚姻家庭关系的道德困境,新文化动摇了传统的婚恋关系,使得无助的女性、畸形的婚姻成为不可规避的家庭问题。作家以文化的视角反思新旧文化的裂隙带来的道德冲突与生存窘境,从家庭的矛盾折射社会发展的文化困境。然而,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两性关系只是其中一环,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亲缘关系同样也引起了《中国文艺》作家的关注,这里既有血脉相连的亲情,也有家庭伦理维系的亲缘,通过亲缘关系展写血亲之间的人性与人情。
血缘亲情是建构家庭秩序的基础,然而这一血缘亲情网并不是坚不可催的,亲缘关系往往被企图重建家庭秩序的“外来者”打破。“后母”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家庭“外来者”,这一形象也是《中国文艺》家庭小说中常常展写的,如:“李五爷”③详见颠夫的《母女泪》,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1卷第5期。娶了“英美”为妾,为了私夺家财,“英美”将“李五爷”的女儿远嫁作妾,利用儿子骗取家财,“偌大的家私被剥落得只剩零碎之物”[1],即便最后“英美”进了监狱,“李五爷”也无法挽回家庭的其乐融融;“林宁”父亲自从娶了姨娘后,姨娘常招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打麻将,或是带着林宁的父亲整日躲在屋子里抽鸦片,姨娘的粗俗、自私让林宁心生鄙夷,原本平静的家庭因为姨娘的闯入而急转突变;“若英”④详见刘萼《幽灵》,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9卷第1期。的父亲自从娶了姨太太回家,“若英”和“母亲”的命运便被改写,在姨太太的唆使下,“母亲”的脸被油烧成了碳糊,随即“母亲”又被父亲关在了后院的黑屋里,而父亲对“若英”也由宠爱逐渐变得冷淡与疏离,原本温暖和谐的家笼罩着冷漠的阴霾,最终“若英”和姐姐被迫离开了家;“寿山”⑤详见袁素辉《八千个日子》,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2卷第5期。的父亲娶来了继母,继母对他百般虐待,他不仅要忍受继母的打骂,甚至还要承受饥饿的惩罚,无奈之下,“寿山”带着对继母的仇恨逃出苦难的家;“小蓝”⑥详见寒流《小蓝》,载《中国文艺》1942年第6卷第3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在她12岁那年父亲娶了继母“素纹”,然而“素纹”的到来并没有让“小蓝”感受到母爱,“素纹”整日纠缠于“父亲”与前妻的过往而难以面对当下的家庭生活,“父亲”和“小睿”的死又让“素纹”对“小蓝”心生幽怨,“素纹”最终因精神崩溃离开人世……由此观之,泼辣、刁钻、自私、无情、冷漠是《中国文艺》刊载的家庭小说中所呈现的“后母”的共性,恰恰是这样的性格特征冲击着家庭原有的和谐氛围。“后母”对新家庭的排斥和拒绝使得她们急切地企图重建新的家庭秩序,为此她们打破原始家庭的情感结构,以确立其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在欲望的驱使下,占有、抢夺、牟利让她们成为十足的家庭“入侵者”。《中国文艺》的作家将“后母”与“家庭”放置在对立的叙述模式中。作为一个家庭的外来者,“后母”为了确证自身的家庭地位,以恶挑衅、打破固有的家庭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着颇为相似的行为和心态,由此“后母”的形象在家国的视域下拓展了新的阐释空间。作者不仅从道德立场上批判“后母”的人性缺失,还从民族立场上探讨“后母”卑劣行径的深层意蕴,因此“后母”形象无疑有着对“日本人”的影射。“中国”是国人共同的“家”,中国同胞是祖国母亲的儿女,日侵者的蓄意挑唆、发动战争、扶持傀儡、经济抢夺、文化统制等对中国人的“家”破坏无遗,造成了“家”的混乱与同胞的罹难。《中国文艺》的作家从道义良知上谴责日侵者丧失的人性,从国家立场上批判日侵者对一个国家尊严的践踏,中国同胞不会接纳与认同蓄意侵略、占领中国国土的日侵者。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日侵者与沦陷区的有识文人建构着各自的话语圈,他们在明暗间互相抗衡,因此,“排斥”“反对”“疏离”“反拨”是《中国文艺》的有识作家为挣脱“后母”的压制一以贯之的创作态度。
《中国文艺》的家庭题材小说转换了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视角,从道德冲突和人性欲望两方面探讨家庭伦理秩序和两性关系的困境。这一困境不仅反映在“家庭”上,同样也关联着国家与社会。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即是《中国文艺》作家有意为之的民族书写。文化的代际造成了家庭关系的裂隙,情与理的冲突打破了家庭关系的平衡,两性在家庭的道德边界上陷入两难,他们的犹疑、徘徊、无所适从使得他们不得不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逃避现实,青年的忧郁显现出世纪末的情绪。与此同时,《中国文艺》的家庭小说作者注重“后母”形象的塑造。作为亲情谱系的“外来者”,“后母”往往被赋予冷漠、卑劣、自私、刻薄的性格特征。她们打破了以往的家庭秩序,强行建构新的家庭关系来确证自身的地位。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文艺》作家着力塑造的“后母”形象无疑有着对日侵者的影射。这一民族隐喻,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日侵者”的不满与愤懑,另一方面也暗示出他们的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
二、暴露讽刺小说
《中国文艺》刊载的小说多以客观写实为主,写实小说是作者的情感体验对现实的重组,文本着力描写现实生活的原貌,真实地表现人们现实生活的困境,抒怀个人的苦闷情绪,批判社会现实,“言民众之不敢言”。其中,暴露讽刺小说以犀利的文学话语揭露社会暗角,是《中国文艺》刊载的写实小说中对现实批判力度较为深刻的一类。《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与解放区、大后方的“暴露讽刺小说”是共时性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北平有识文人对解放区、大后方文学活动的关注与呼应。然而从启蒙理路上看,《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与解放区、大后方的“暴露讽刺小说”显现出不同的路向。《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反映战争匪乱、社会无序、贫穷饥饿、阶级压迫和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作家以苦难生活的书写引起民众情感的共鸣,试图从情感的认同与民众建立同胞的血脉联系,不但表达出对当权者的不满和排斥,还展现了他们的道德良知与人文关怀,从而使《中国文艺》的小说创作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呈现出“济世”的文学取向。
暴露现实小说拓展了多元化的社会书写,作者从生存的困境、人性的思考以及对官僚作风的讽刺等不同面向开掘社会暗角,现实的灰暗与无望成为作家苦闷的时代记忆。由经济萧条引发的生存危机成为时代的焦虑,生存危机不仅让百姓承受着食不果腹的煎熬,同时还带来失业、匪乱、流亡、人口贩卖以及逼良为娼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危机之中。面对现实的窘迫,有识作家在“作品要表现时代”的呼吁下创作暴露现实的小说,他们着眼于灰暗的社会现实,揭示战争背景下畸变的社会样态以及百姓的生存窘迫。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农民破产使得“饥饿”从乡村蔓延到城市,所以农民的生存问题便成为《中国文艺》作家颇为关注的问题。如《秋土》①详见步南《秋土》,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8卷第1期。中的农民“老张”颗粒无收,这不仅意味着全家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饥饿之难,同时还要承受地主“蔡大爷”的逼租。而“蔡大爷”既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教授的文化身份与政治家的社会背景让他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并成为其盘剥农民的资本:“我是地主,收租是我的权力,他们死也该还。”[2]对颗粒无收的农民“老张”,“蔡大爷”没有丝毫的同情与悲悯,用那张蛮横的嘴脸催逼着“老张”交租。在此,小说揭示了沦陷区农民的苦难生活与阶级矛盾的两级分化。战争天灾、畸形的政治体制、经济萧条以及地主盘剥的多重压迫,使得“靠天吃饭”的底层农民毫无出路可言。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变卖妻女换取口粮,如“慧儿”②详见张学勤《慧儿》,载《中国文艺》1939年第1卷第4期。的父亲将“慧儿”变卖换粮,以供全家果腹;抑或“逃”出农村,在城里谋求生路,如“马成”③详见鲁施《地平线上的人》,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8卷第5期。为躲避农村的苛捐赋税、乱抓壮丁而逃到城里“务工”,然而城市并没有改变他难以果腹的生活,复杂的城市结构不断地异化着人的生存危机和社会形态。饥民①详见慕容慧文《冬景》,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2卷第2期。蜂拥而至地围在粥厂为争得一口粥喝而互相撕扯,在生存面前人变成了饥饿的囚徒,然而政府以拯救之名供给的粥粮却掺杂着砂石,苛刻的领粥条件,让受难同胞在自相撕扯中上演“争食”的闹剧。政府的伪善不但没有解决流民的饥饿,反而把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在此,作者由生存危机反思道德危机,政府掺假牟利,而生存的窘迫却让底层民众丧失了道德理性,自私、伪善、抢夺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非理性中。“饥饿”浸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分阶级、无论贵贱。《潦倒的巅崖——忏悔录之三》②详见程心枌《潦倒的巅崖——忏悔录之三》,载《中国文艺》1942年第7卷第1期。中,饭店给狗吃的是海鲜、翅根、牛尾、鸡爪、红烧肉、面包……而街上的乞丐却连狗都不如,当他们去饭店讨要粮食时换来的是一句:“剩菜剩饭全可送到小市去卖钱,不喂狗!也不让给叫花子!”[3]作者以辛辣讽刺的笔法展写了“人不如狗”的社会病状,社会阶级矛盾的两级分化呈现出权力话语对底层民众个体价值的消泯,底层民众难以取得个体身份的认同,于是“人吃人”成为了畸形社会的“常态”。车夫“顾二”③详见唐楷《生物》,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2卷第4期。是家中唯一的经济主力,全家连一顿救济粮都吃不上,迫于无奈,“顾二”只得向以前的主顾老爷借钱,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然而讽刺的是,主顾太太虽虔诚地吃斋念佛,却不肯发善心帮助穷困潦倒的“顾二”,最终“顾二”冻死在雪地中,手里还攥着管家大哥借的一块钱,而家里等待用钱看病的孩子也难以逃脱死亡的魔掌……从穷人“乞食不得”到富人“食有余裕”,从“人不如狗”到“人吃人”的病状,《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作家以辛辣的笔法揭露社会两级的极端分化,畸形的社会体制导致社会分层的异化,特殊的政治语境下这一病态的社会造成了骨肉同胞间的厮杀,冷漠的人情与冷酷的人性涣散着民族凝聚力,小说中这一隐在的民族情感结构透露出作者复杂的心绪,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国家、对骨肉同胞、对腐朽的社会、对无力的底层民众掺杂着愤懑的、深沉的悲哀与同情。
如果说“食不果腹”是肉体饥饿的痛感,那么过劳、匪乱、失业、破产则增加了精神饥饿的重负。如:“汪六”④详见西澈《炉灰》,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2卷第1期。的父亲死后,“汪六”变成了既无住处又无生计的流浪者,最终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服毒自杀;“四嫂”⑤详见处士《四嫂》,载《中国文艺》1939年第1卷第4期。的丈夫失业在家,整天沉浸在赌博和酒精中麻痹自己,“四嫂”平静幸福的生活陷入了无边的黑暗;“王先生”⑥详见曹原《十年》,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1卷第6期。的家被土匪劫掠一空,儿子又骗走了他的财产,孤身一人的他茫然无措,任凭命运宰割;经济萧条迫使“胖老板”⑦详见汪家祉《逃》,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1卷第6期。的生意濒临破产,无法偿还的外债与难以为继的生意让“胖老板”无以生存,逃跑便成为他唯一的求生之选……《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以“饥饿”展写战争背景下民众的生存困境,既表现黎民求生不得的悲惨境遇,又着力反思由生存危机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就民族立场而言,由社会两级分化而导致的阶级压迫变成了同胞间的“自相残杀”,这不仅是社会危机,同时也是民族危机的显现。在与解放区、大后方“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共时语境下,沦陷区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涣散了民族凝聚力,在此作家对社会暗角的暴露和批判显现出深切的民族忧虑。
暴露现实小说的叙述方式是正面的、直接的、尖锐的,作家直面现实,剖析社会问题。而同样是暴露社会暗角、批判社会现实,讽刺小说的叙述方式则是间接的、夸张的、圆滑的,它以夸张、荒诞的笔法放大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丑陋,耐人寻味的讽刺意蕴鞭挞着现世丑态与人性拙劣。官场讽刺小说主要描写一些官僚营私舞弊、徇私枉法的昏庸作风,他们“吃空饷”“混日子”“谋私利”,如虫蚁般蛀蚀着社会。作家揭开他们伪善的面具,将他们的鄙俗、无知以及丑恶暴露在正义的阳光下,在道德立场上以犀利的笔法批判他们罪恶的灵魂。如:“地方领袖张局长”⑧详见凯军《张局长》,载《中国文艺》1939年第3卷第4期。无知无识,居领导之位却毫无作为;“舅老爷”⑨详见李道静《舅老爷》,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9卷第1期。依仗着自己是县老爷的小舅子就为虎作伥骗取钱财,以县长的名义卖弄权力……装腔作势、营私舞弊、目无法理、无所作为暴露了政治体制的漏洞和隐患,由此揭示出日伪政权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作家以幽默犀利的笔触塑造了社会上层的一群“丑物”,正是由于他们的“丑”才浸染了社会制度之“丑”。《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不仅揭露上层官僚的“丑行”,还批判了人性的“丑态”。如《蕉》①详见萧菱《蕉》,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1期。中的“周同”,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放弃科研,并寻求妹妹的帮助。妹妹凭借与银行经理的“干爹”关系为“周同”谋得一个银行职员的工作,然而对于“周同”来说,这是不光彩的甚至他所厌恶的。当他看见那个肥胖的男人和妹妹坐在床边时,妹妹却向那个男人喊起了“爸爸”,“周同”便爆发怒火。作者批判了在金钱名利的驱使下“任人为父”的社会怪相。人伦关系的混乱、投机钻营的畸形社会扼杀了心怀理想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努力进取非但没有改变自身的生活处境、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反而遭到了社会无情的鞭笞,而所谓的“成功人士”却是一群毫无作为、贪于私欲的钻营者。社会的倒行逆施导致了错位倒置的人才结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滞后。牟利者、投机者、伪善者、钻营者既是当权者,也是备受“重用”的“中坚力量”,这些人掌握着政治的话语权,也就注定了社会的畸形异化。而愚昧麻木、胆小怕事的民众被压抑在这异化的社会中不得喘息,他们只能成为无力的浮萍被社会浪潮放逐。可见,无论是掌控话语权的“官僚”还是听命摆布的市民,国人精神的颓废导致了社会的无序。正因如此,国民精神才有启蒙的必要,拯救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拯救国民,只有重振民族精神,才能有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作家以犀利的笔法批判社会丑态、揭露人情凉薄,展现了他们深刻的社会思考,通过“苦难”叙事唤起患难同胞的精神共鸣,促进民族向心力的凝聚。
解放区、大后方关于“暴露与讽刺”文学的讨论与《中国文艺》刊载的“暴露讽刺小说”几乎是共时存在的。解放区、大后方的“暴露与讽刺”文学发起于张天翼1938年创作的《华威先生》。该小说发表在1938年4月《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作者通过“华威先生”徒有工作虚名、毫无实际作为的官僚作风,批判了混迹于革命队伍中“专吃抗战饭”、装腔作势的不良分子。这些人在革命队伍中散播不正之风,涣散军心,动摇革命的政治信念,不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设。《华威先生》发表之初就遭到了李育中等人对“暴露与讽刺”文学的质疑,由此展开了“要不要暴露黑暗问题”的论争。以李育中为代表的批评者认为,组织的内部问题不应公开暴露,以免影响抗日战线的团结统一;而以茅盾为首的批评者则支持、鼓励“暴露与讽刺”小说的创作,他们认为,“暴露与讽刺”小说表现了“典型人物”的阴暗面,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避免对抗战文学中“歌功颂德”的片面创作方式,所以“暴露与讽刺”文学不仅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式,还通过发掘社会的暗角揭露革命政治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抗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最终,茅盾对“暴露与讽刺”的意见得到了解放区、大后方文人的普遍认可,由此推动了“暴露与讽刺”小说在大后方的发展。之后,张天翼的《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巴人的《一个老地主的故事》等“暴露讽刺”小说相继发表,并轰动一时。
尽管大后方、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暴露与讽刺”小说共时性地存在,但政治语境的不同使得沦陷区与大后方、解放区的“暴露与讽刺”小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果说大后方的“暴露与讽刺”文学批判的对象为敌人、汉奸以及革命的中间分子、落后分子,暴露的是抗日战线中的阴暗面,那么《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的批判对象则是社会的上层官僚、思想落后保守的民众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传播者,暴露的是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的暗角。从批判的目的看,大后方的“暴露与讽刺”文学是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设为核心,剔除的是革命队伍的蛀虫;而《中国文艺》的则力避政治话语,以沦陷区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重心,凝聚民族的向心力,进而抵制日伪政权的压迫。与大后方“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讨论热潮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文艺》的“暴露与讽刺”小说的创作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暴露与讽刺”小说的现实批判性显现出与日伪政权的疏离,间接反拨了日本的殖民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暴露与讽刺”小说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理路,通过对现实的反思建构民族启蒙话语,间接反戈着日伪政权,因此“暴露与讽刺”小说的启蒙话语不仅不能为日本所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遏制了殖民话语的传播。在抗战的文学视域下,《中国文艺》的“暴露与讽刺”小说与大后方的“暴露与讽刺”文学共时性存在,显示出沦陷区《中国文艺》的编者们试图与大后方、解放区建立隐在的文学对话。然而,沦陷区相对封闭的政治空间与文化语境阻隔了这一对话的实现。因此,《中国文艺》的“暴露与讽刺”小说的主题和创作导向呈现出民族启蒙话语的断裂。不容忽视的是,北平的《中国文艺》编者们与大后方、解放区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共同的民族启蒙话语。如此看来,《中国文艺》也并非是孤军奋战,在民族启蒙的立场上,有识文人仍能坚守着民族信仰去寻求文学启蒙的路径,这里没有政治的分区和文化的边界,“实现民族的独立”才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欲要实现“美”的社会理想,让民众走出现实的困境,还须从重振国民精神起步。由此,文学启蒙话语就有了既定的拓展空间。《中国文艺》的“暴露讽刺”小说是在对“丑相”“怪相”的叙述中隐含着作家深沉的民族情怀与深切的现实反思,作家以“美”的社会理想反拨社会现实的“丑”,“美”即是民族精神启蒙的动力和方向。在此,民族精神的启蒙与社会现实的黑暗在时代的结点处形成了一个话语圈。从言与意的表达策略看,“暴露讽刺”小说还包含着“笑”与“悲”的情感内涵,作家将忧郁、苦闷、愤懑以及抵抗都融贯在讽刺小说含泪的“戏谑”中,幽默所承载的却是无尽的苦闷。“言不尽意”的表达方式增加了文本的叙事张力,扩大了文学启蒙的阐释空间。《中国文艺》作家在明暗间书写时代的道德危机与精神危机,表达了对日伪政权的不满与愤怒,一定程度上反戈着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悲笑”的言说策略即是《中国文艺》有识作家有意建构的启蒙“隐言”。
三、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
在民族危难之时,欲要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就要深化民族精神的理性思考,这就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启蒙须从文化立场与国民劣根性的价值立场探寻重振民族的思想理路,《中国文艺》刊载的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便立足于此,并借鉴了“五四”小说对国民思想启蒙的创作理路。如果说“五四”文学对思想文化的批判是理性的驱魅,那么《中国文艺》刊载的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则是以民族的视域探讨启蒙话语建构的困境。前者是清除封建思想的阻障,推进民族文化的革新;后者则是倡导民族精神的重振,凝聚抵御日侵者的民族向心力。由此可见,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决定了同一小说主题不同的启蒙路向。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文化的根基,但它的残余势力仍潜隐在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成为了重振民族精神的阻碍,因此在《中国文艺》刊载的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中,以文化的视域探讨民族精神的启蒙是其中的重要一脉。《樊笼》①详见萧菱《樊笼》,载《中国文艺》1943年第8卷第3期。中的新女性“丽”被村民视为城里来的灾星,为“灭除”这颗不祥的“灾星”,村民们把“丽”打成了血肉一团,接受新思想的女性被拘禁在封建的“樊笼”里遭到原始乡村文化的打压,原始的乡村文化向城市新文明发起冲击,于是“丽”成为新旧文化与城乡文明双重对战的牺牲品。作者批判原始乡村文化的落后、封建与粗暴,是亟待被拯救的文化盲区,而启蒙的光芒势必要驱散没落文化的黑暗。《问卜》②详见陈异《问卜》,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3卷第1期。中的“二姨”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师范毕业生,即便如此,“二姨”也没有从科学理性的认知中消除封建思想的痼疾。她迷信占卜,并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寄托于算命占卜中,然而讽刺的是“二姨”听信的算命先生——王半仙却是一无所知的骗子……从无知的村民到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文化的革新并没有促使普通的民众觉醒,他们仿佛是这个时代的拟古者,愚昧的封建思想使其明显地表现出与社会文化节奏的脱节。现实生活的苦难让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于是他们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神灵”,既无心面对现实、改变现状,更无暇顾及民族前途和国家危难,可见封建思想无疑涣散了民族凝聚力精神,进而妨碍了民族精神的启蒙进程。在此,批判封建文化的余孽已出离了文化层面的考量,民族危机的紧迫让这些有识作家更关注文化形态的启蒙价值,于是他们通过批判封建思想对民众的毒害,放大民众麻木、愚昧和冷漠的国民劣根性,这既是发人深思的人性拷问,也是对民族启蒙理路的思考。
“何先生”③详见乔迁《何先生》,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3卷第3期。是个诚实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然而他的诚实不但不被民众认同,反而被视为是“疯言疯语”,无人理会又备受排挤,所以作为有道德良知的觉醒者“何先生”的苦闷即是启蒙者的苦闷。尽管以“何先生”为代表的启蒙先锋者能敏感地洞悉时局,勇敢地向民众发出启蒙的呼吁,但是他们的呐喊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回应,民众的冷漠、麻木和愚昧吞噬着呐喊者的声音。这些觉醒的呐喊者被排挤在启蒙话语的边界,他们既无力发出启蒙之音,又不甘于坐以待毙,因此这些迷雾中的觉醒者注定成为苦难时代的孤独者。《中国文艺》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一方面,揭露封建文化的余孽对愚昧民众的精神侵蚀,颓废萎靡之势涣散了国民精神;另一方面,作家由国民的劣根性反观社会现实,揭露畸形的社会体制对人格理想与理性精神的泯灭,表达了作者对日伪政权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愚昧、冷漠同胞的痛心失望。愚昧者在苦难的压抑下变成了无泣无诉的“奴”,软弱者在失落中陷于无尽的幽怨,觉醒者做着反抗的挣扎,呐喊者呼吁重振民族的希望……《中国文艺》刊载的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从多重维度探讨凝结着对民族精神的启蒙理路,在同情悲悯中展现作者的现世思考与人文关怀。
民族的崛起要靠青年。作为民族振兴的脊梁,青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群体,他们的精神成长是特殊历史时期颇为重要的时代命题。《中国文艺》的编者多为北平新进作家,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下,他们以青年人的身份体验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倡导社会对青年人“时代病”的关注,从青年人的生存危机、精神困境反思政治环境与社会体制的异化。青年“李迈伦”①出自袁犀《陷》,载《中国文艺》1942年第5卷第5期。深陷苦闷不能自拔,失业、穷困、失恋的现实打击让他无法得到自我价值的认同,他既想改变环境又不愿付出行动,既想维护尊严又拼命放纵自己,酒精麻醉着他的痛苦,赌场让他逃避现世之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让他变成了社会的“多余人”,他失落的灵魂无以找寻生活的寄托,无奈之下只能以“死”终结现实的窘迫与精神的空虚。造成“李迈伦”自杀悲剧的不只是灰暗的社会现实,其内在的精神结构与文化心理也构成了他盲动的精神动因,落魄青年受制于时代也无心自谋出路。他对现实的无望源于他对自己的绝望,听天由命的消极心态反视着他潜在的劣根性——“奴性”。“奴性”增加了忧郁青年的社会盲动性,“奴性—依赖—压抑—受伤—盲动—麻木”,这一情绪变化的连锁反应暴露出国民劣根性对青年思想的腐蚀与侵害,是涣散国民精神的罪恶之源,在《中国文艺》的“问题小说”作者看来这更像是一场爆发在沦陷时期青年身上的精神危机,它阻碍了民族精神的启蒙进程。《供状》②详见麦静《供状》,载《中国文艺》1941年第4卷第6期。中的“我”是一个刚毕业工作的青年,初来上海,没有房子,只能同一些青年租住在一间房子中,然而“我们”的关系并不和谐。“高志新”对“我”的轻视和排挤僭越了“我”的底线,加之生存压力的窘迫令“我”忧虑,于是精神的“压抑”使“我”丧失了理智,情急之下,“高志新”被“我”误伤致死。“李迈伦”和“我”的苦闷代表了这个特殊时代颓萎青年的普遍情绪,他们是接受新文化教育的有志者,然而生逢乱世的他们不仅没有找到生活的出路,反而还在现实的蹂躏中屡遭“碰壁”:失业、失语、失势让他们产生现实的幻灭感,生存的焦虑使他们陷入个体价值的失落,脆弱、彷徨、虚无、忧虑、感伤是灰暗的时代给予青年一代的精神底色。
《中国文艺》刊载的“青年问题小说”可追溯至19世纪20年代书写青年人世纪末情绪的“问题小说”,不得不说《中国文艺》的“青年问题小说”既是对20年代“问题小说”创作理路的借鉴,同时也表现了“异变”的政治环境为青年人带来的精神焦虑。无论是“20年代”的文化代际还是“40年代”的国土沦陷,这两个时间节点恰好都是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时代的变革影响着青年人的社会理想与道德追求,于是青年人的压抑、幻灭和犹疑印刻着社会现实的痕迹。20年代的“问题小说”关注文化代际之时启蒙者的思想困境,理想与现实、新文化与旧道德、启蒙与愚昧的反差冲撞着启蒙者,使他们产生了压抑和困顿的情绪,为此,他们从个人问题的表征去探讨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矛盾。而《中国文艺》刊载的“青年问题小说”关注的是政治动荡之时失落青年的精神危机,现实的灰暗不仅幻灭了他们的理想,甚至还造成了他们的生存危机。生存无着的压抑泯灭了青年人的自我价值认同,他们彷徨失措、逃避现实的苦闷导致精神的盲动,国家与民族在颓萎青年狭隘的个人视野中逐渐淡化,更无从谈及民族理想与天下己任,这令有识作家为民族的前途而忧虑。《中国文艺》的“青年问题小说”作家对青年的世纪末情绪持以批判的态度,这些疏离现实的青年是作家启蒙的对象。一方面,这些青年要从混沌中自醒;另一方面,文学启蒙者须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继而重振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体现了《中国文艺》“重振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的文化方略,这不仅是《中国文艺》作家的共识,同时也是精神文化反思小说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中国文艺》刊载的小说从家庭、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苦闷”的时代,以多主题、多角度开掘民众的精神困境,作家既忧心于亟待拯救的社会,又焦虑于国民精神的启蒙,当苦闷成为时代的底色时,《中国文艺》小说便呈现出哀伤的格调。然而,哀伤并没有使《中国文艺》的作家停止对文学启蒙的追求。他们借鉴“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方式建构民族的文学启蒙话语,无论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还是家庭伦理的探讨,都呈现出旧主题、新立场的叙述方式。在民族危难之时,《中国文艺》作家呼吁民族精神的重振,他们对抗着日本殖民意识形态,试图通过多种主题开拓文学的启蒙空间。无论是《中国文艺》刊载的“暴露与讽刺”小说与解放区、大后方“暴露与讽刺”文学的共时性存在,还是“家庭问题”小说对家国同构问题的反思;无论是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对民众精神困境的忧虑,还是写实小说对沦陷区苦难生活的揭露……从《中国文艺》刊载的作品主题可以看出,《中国文艺》的编者在有意与解放区、大后方文学建立对话,一方面是对文学理论建设的呼吁,另一方面则从文学启蒙话语中寻找重振民族精神的路径。这些编者与有识作家在《中国文艺》的阵地上共建文学启蒙话语,既是对民族立场的暗自坚守,也是对正义的文学价值取向的追求,他们在明暗中书写时代的道德危机与精神危机,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展现了有识文人的人文关怀和民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