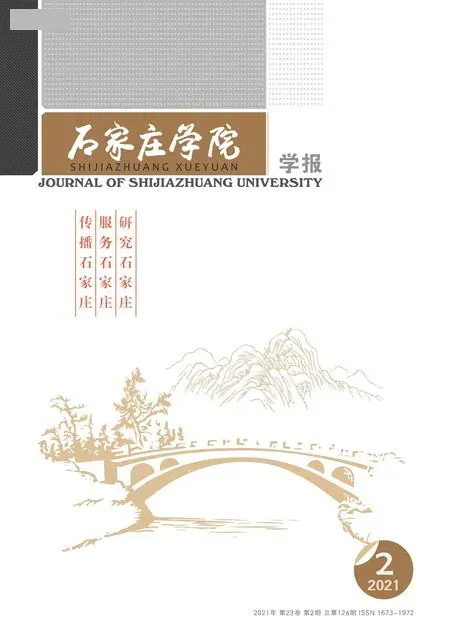汉唐时期国家对北部边疆经济治理研究
杨 丽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汉唐时期,我国北部边疆地处“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和“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交汇地带,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门户。由于北部边疆深居大陆腹地,处于中原王朝经济中心的外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与中原内地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中原王朝整合边疆的能力,甚至引发边疆危机。若单纯依靠政治、军事等硬性手段,很难实现对北部边疆有效、长期的治理。汉唐中原王朝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考虑,一直重视对北部边疆经济的治理与开发。
一、汉唐时期国家对北部边疆经济治理的实然境况
汉唐时期北部边疆治理存在着诸多困境,有来自北部边疆自然因素的限制,也有来自人文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制约。
(一)自然地理环境:北部边疆环境恶劣、资源贫乏,限制了经济发展质量
北部边疆乃北部边陲之地,以山地、高原为主的地貌特征和干燥、严寒的气候,给经济治理和开发带来了诸多不便和现实困难。
气候干燥。北部边疆地区所处纬度高,整体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加之深居内陆,向海一面又有山地阻隔,常年降水稀少,且分布严重不均。这样的气候环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经营与发展。
土壤贫瘠。北部边疆地貌以高原、山地、平原、戈壁为主,土壤贫瘠,可耕地比重小,只有长城沿线地区,如土默特平原、河套平原、西辽河中下游平原等土壤较为肥沃,其他山地、戈壁等则不宜农耕,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
天气严寒。北部边疆地理纬度高,大部分属于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常年气候偏低。在蒙古高压气团的控制下,西伯利亚寒流南下致使北部边疆冬季漫长(11月-次年4月),最低气温甚至达到零下40℃;春季(5-6月)、秋季(9-10月)短促,并常有狂风甚至大雪等突发性天气。“胡天八月即飞雪”描述的便是北部边疆的秋天情景。
灾害多发。北部边疆气候的不确定性,导致北部边疆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俗称“白灾年年有,黑灾不时来”。生活于北部边疆的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产业结构单一,对自然环境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却特别小”[1]38,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其后果就甚为严重,对游牧民族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2]
(二)人文社会环境:北部边疆人口稀少,边民不喜农桑,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
人口稀少。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劳动力,人口不足,则意味着劳动力的缺乏。汉唐时期,北部边疆一般为战争的前沿阵地,战后,游牧民族撤离,这里成为中原王朝开发的新区,人烟稀少。
交通不便。北部边疆远离中原,路况艰险,在这里维持驻军和支撑军事行动、重兵戍边或征伐平叛、运送粮草等军需困难重重。秦汉时期是“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3]1421,至唐代还是“千里馈粮,涉履艰险,运米一斛,达于边军,远或费钱五六千,近者犹过其半”[4]4830。以粮草为中心的军需供应则是战争得以继续的物资保障。而粮食供给是士卒生存的先决条件。若靠内地长途转运,会造成边防兵粮饷不济甚至断绝的危险。
边民尚武,不喜农桑。北部边疆自古以来民族关系就比较复杂。先秦之时,这里有戎、羌、氐、乌孙、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交错杂居。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之长期受战争环境的磨练和游牧民族风气的影响,生活于北部边疆的居民民风剽悍尚武,他们“任侠为奸,不事农商”[3]3263,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汉宣帝时,渤海一带民众“好末技,不田作”,太守龚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5]3640。唐代的突厥,经济还处于“随逐水草,不恒厥处”[6]1864的原始“游牧奴隶制社会形态”[7]124。
(三)军事因素:战争较为频仍,发展经济的环境不稳定
秦末汉初,匈奴趁中原内乱,势力迅速壮大,有控弦之士30余万,咸服诸国。向东,大破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3]2890;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3]2887,将诸引弓之民及北边地区的汉人并为一家。匈奴不仅控制了蒙古高原,还控制了河西和西域,并臣服诸羌,占据了青海羌族所居之地,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且“南与中国为敌国”[3]2890。匈奴胡骑经常南下,侵掠汉之雁、代地区,成为中原王朝北部边疆最强劲对手,导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8]716。
唐代北部边疆的民族比两汉时期复杂得多。北部边疆的防御中线有突厥、回纥等侵扰,西线有党项、吐谷浑和吐蕃等侵犯,东线有契丹、奚等侵扰,但威胁北部边疆安全最严重的部族要数突厥和吐蕃。
汉唐时期,由于这些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或归附后的叛乱,加之这些侵扰或叛乱还经常与边地的地方军阀集团勾结在一起,引发北部边疆的军事冲突和政局动荡,导致北部边疆民众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经济萧条,增加了经济治理的难度和风险。
二、汉唐时期北部边疆经济治理措施
汉唐时期,北部边疆具有国家安全战略屏障和亚欧大陆腹地的双重区位优势,不仅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前沿阵地,更是中原王朝边防安全的战略要地。中原王朝一直在该区域设重兵防守,军费开支浩大,军需转运不便。因而只有发展北部边疆经济,才能强边固防。
(一)屯垦戍边,保障军需给养
汉代屯垦。中原王朝自秦以来,便在北部边疆实施屯垦戍边政策,这是一项以国防为主要目的,在边疆推行的一种开发利用土地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在边疆军事要地,以驻军和移民为主,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发展农牧业生产。屯垦的管理模式是实行兵农结合制度,屯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边疆的军需给养。汉代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始于汉武帝时期,屯田从河套以东开始,后扩大到河西、河湟、西域等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结束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3]2911,匈奴势力退出漠南和漠西,汉武帝立即下令进行垦殖,拉开了大规模边疆军屯的序幕。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又遣兵卒60万到上郡、西河、朔方屯田。自此以后,西汉政府将屯田作为保卫边疆的重要手段。屯田区域有河套平原、湟水流域、河西及西域的轮台、鄯善、渠犁、车师,最西到达乌孙所在的锡尔河上游地区。其中,又以西域屯田规模最大,效果也最显著。东汉时期,继续实施屯田之策,但东汉屯田的目的是为防御塞外诸羌的掠夺和镇压郡县降羌的反抗,而采取的与军事镇压相配合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东汉屯田重点区域在西域,北部边疆的屯田主要在河湟、陇西一带的黄河沿岸广大区域,但其规模和成效远不及西汉。
唐朝屯垦。唐代,为防御突厥,在北部边疆建立了一整套驻防体系,驻军人数不断增加。庞大的军队,解决粮饷供应是首要大事,所谓“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9]2976,以达到“搜乘训兵,屯田积粟,谨设烽燧,精饰弋矛,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10]2976之效,故唐王朝一直把屯田作为巩固边疆、加强边疆军事建设的重大举措。唐代规定“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10]1840。为落实屯田安边政策,唐朝明文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草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防人等食。”[11]215同时,在中央尚书省的工部之下,专门设立指导和督察全国屯田事宜的最高领导机关——屯田司,负责管理屯田。在政府的号召下,唐代北部边疆,如关内道北部、河东道北部、河西陇右、河北道北部一带成为屯田的主要区域。北部边疆的土地得到迅速开发,出现了大片农田。
(二)发展马政,提高边防战斗力
马不仅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重要役畜,还是驿传交通、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在我国古代军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被誉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10]840,所以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征马、养马作为要政之一。马政对于汉唐北部边疆安全意义重大,故两朝都非常重视马政事业。
西汉马政。西汉一朝,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成了汉王朝的最大外患。“要最终抵御匈奴的侵扰,除了坚甲利兵,强弓劲弩外,还得有足够数量的马匹。”[12]早在文帝之时,为扭转由于战马缺乏无法组建骑兵的劣势,便颁布“马复令”以鼓励民间养马,除鼓励民间养马外,还在西、北开辟了广大牧场,以繁育军马。汉景帝时,在接近匈奴人生活的北部和西北部边疆一带设苑囿以养军马,当时全国共设马苑36所,以皇帝的侍卫和侍从人员——“郎”为苑监,使用官奴婢3万人,分养马30万匹,平均每人照顾10匹马。可见养马规模之大和对马政的重视。武帝继位后,“为伐胡,故盛养马”[3]176,马匹数量大增。但是对匈奴的战争,马匹消耗太大,仅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战役,军马死者10余万匹,于是武帝在景帝马政的基础上,又采取多种措施,设法繁殖和补充军马。汉昭宣时期,继续推行“马复令”以增加马匹数量,为补充边郡军马及驿传马匹的不足,还下诏减省皇室御用马匹。至汉成帝,内有农民起义的打击,外有鲜卑等的侵扰,马政也很难维持,“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5]3296。汉元帝时,朝廷削减部分厩马,裁撤马苑。汉平帝时,“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5]353。
东汉马政。东汉时期继续实行马政,但规模远不如西汉。光武帝时期,便将前汉设于河西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牧师苑裁撤,“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10]3582,至此,东汉牧师苑数量大为减少,36苑唯剩汉阳流马苑尚存。到了东汉后期,由于旷日持久的羌乱和南匈奴、乌桓、鲜卑的时降时乱,加上各地的农民起义,东汉马政遂走向没落。
唐代马政。从建国伊始,唐统治者就极为重视马政。唐建立了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中央设太仆寺专理马政,地方设置了星罗棋布的监牧,这些监牧由各个边防军镇保护,并专设“防御群牧使”“防御群牧大使”等职。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年),唐朝马政达到最盛,全国共设有56监。从高宗乾封至景云年间,马政事业暂时走向衰落。唐玄宗继位后,又开始重视马政,于是“马稍稍复”[13]1338。安史之乱后,唐马政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出现“臣闻平时七十万匹马……如今垌野十无一”[14]290的凄凉景象。唐肃宗以后,牧事遂废。
(三)互市贸易,促进商品流通
汉唐时期,北部边疆地区的关市贸易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关市,也称互市、胡市、合市或交市。发展关市贸易,经济上互通有无,利用中原优势物质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或部族施加经济文化影响,从而以汉族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去感召和影响匈奴等游牧民族,以缓和双方的矛盾,增加边疆对内地的向心力。
汉代关市贸易。中原王朝与匈奴进行贸易开始的较早。早在战国、秦时便与其西部的羌族以及北部的戎翟(匈奴)等草原民族保持着贸易关系,并通过贸易获得“胡马”等利益,故而西北边地一带虽“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3]3262。西汉立国之初,就与匈奴通关市,匈奴以驴、马、羊驼、兽皮等物产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等,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关市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0]2931。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西汉王朝意欲进击匈奴的马邑之谋失败后,汉匈之间进入战争状态,但汉匈之间的关市一直未绝。汉昭宣以后,汉匈关系日渐恢复,关市贸易更进一步发展。东汉时期,汉匈之间的互市贸易依然存在,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远驱牛马与汉合市”[10]2946。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北单于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还“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10]2950。可见当时互市贸易规模相当可观,中原丝绸、衣物、食品、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北边,匈奴“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騨騱騵马尽为我畜”[15]5。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也与乌桓、鲜卑发展关市贸易。光武帝时期,设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赏赐质子,岁时互市”[10]2982。乌桓主要以牛、马、羊等求市,换取中原汉地的“精金良铁”及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布、帛、缯等,还有其他“珍货”奢侈品。鲜卑也与中原王朝进行互市贸易,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10]1609。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东汉王朝“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10]2986。直到东汉末年,北部边疆的互市仍颇兴旺,如刘虞任刺史期间,“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10]2354。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主人是史籍未见记载的东汉晚期“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曾管理上谷宁城互市。其壁画《宁城图》中,在县衙和幕府前,县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一片空旷场上,有一方形墙垣,注“宁市中”三字,这就是文献所说的“上谷胡市”[16]53。壁画“宁市中”是汉代北方各民族之间频繁贸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唐代绢马贸易。唐朝与同纥、奚、突厥、吐蕃、吐谷浑、靺鞨、契丹、奚、室韦等民族开展互市。唐代前期,互市交易的商品主要是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与周边民族交换马、牛、骡、驼、羊等牲畜等,唐中后期茶叶取代绢帛成了唐朝向周边民族贸易的大宗商品。
唐初主要是和突厥、吐谷浑等进行贸易往来。武德八年(625年),开互市,“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17]5994。早期的互市,唐王朝因“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17]5994,可见通过互市换取耕牛对中原王朝有着重要价值。唐中期主要是和回纥之间的互市贸易,其时间久、规模大,双方交易的大宗商品主要为缣、马。唐玄宗时期,“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12]1335。唐肃宗时代,回纥与唐市绢“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10]5207,双方1年中就有10万匹马与400万匹绢的交易数目。安史之乱后唐代与回纥的绢马贸易,使唐王朝获得了大量急需的优良马匹,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唐代与吐蕃战争对军马的需求,增加了唐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控制力。互市不只是中原王朝一方的愿望和要求,游牧民族也同样有这一愿望和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 000匹到安西(今新疆境内)互市。
(四)完善道路交通,密切与内地联系
北部边疆多山林、戈壁和沙漠,发展交通运输困难多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北部边疆战争仅限于是陆战,兵源主要是步兵、骑兵或车兵。国防交通运输只能依赖道路,倘若交通不畅,边疆的建设和巩固就无从谈起。所以汉唐时期国家非常重视北部边疆的道路交通建设,尤其重视建设通往北部边疆的交通主干线。两汉时期北部边疆重要的交通要道主要有4条。
直道。直道始建于秦朝。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3]758。直道是汉唐期时期连接关中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要道,直道的北口与南口大体南北相对,并与长城呈丁字相交,互为支撑,有利于军情的秘密快递和辎重、兵员的及时运输,具有“南卫关辅,北御羌戎”[18]的显赫军事战略地位。一旦北部边疆有警,中原王朝可迅速沿直道征调军需物资和部队驰援长城一带防线,从而加强了中原王朝对北边和关东的防御和控制。
稒阳道,也称五原塞道,北通匈奴,南至京师长安,是中原与北部地区最直接的交通路线,更是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通道。和平时期,稒阳道车传、骑传、步传十分频繁,车马运输往来不断;战争时期,则成为交战双方集结兵力的军事线路。
飞狐道。飞狐道早在楚汉之际就已形成。飞狐道西通大同,北连张宣(张家口、宣化),东南可达河北各地,直至北京,西南可经代县到达太原,成为南通华北平原、北达千里大漠的交通要道。
丝绸之路。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在北部边疆境内的大致经行地点为:自东而西,出陇西,穿越河西走廊,或穿越腾格里沙漠,抑或沿祁连山脉南麓西进,再经张掖郡、酒泉郡至敦煌郡,出玉门关、阳关西行,进人今新疆境内。两汉时期,特设西域都护,以维护西域地区安定,并沿途保护过往商队和西域“胡商”安全。唐朝规定,如果商旅往来、贩运货物,沿途关隘不得无故阻拦,特别注重商路的畅通。
唐代北部边疆重要道路。唐时,修建了由边疆“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12]1146,这7条要道中位于北部边疆的有3条:
一条是经过营州入安东道(今朝鲜满洲),此道经汝罗守捉,至安东都护府500里,达朝鲜半岛,是横贯辽东腹地的陆路干道。此道共分南、中、北三道。[19]唐中后期,大批的波斯、粟特商人也沿此道来到营州。
另一条是经过夏州通大同、云中道。此道自夏州、代州,而后从雁门向北,经云州、静边军前往单于都护府,是唐代京师长安到单于都护府的主干道。
再有一条便是经受降城入回鹘道。这条道也称“参天可汗道”、回纥路或回鹘道。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应北部边疆地区铁勒诸部的请求,在回鹘以南、突厥以北地区(今内蒙古乌拉旗中后联合旗西北)开筑连接内地与回纥的“参天可汗道”,作为联系京师长安与北部边境的驿道,后为受降城入回纥的另一便捷之道。此路开通后,唐与西域中断的交通联系得到了恢复。通过此道,铁勒诸部每年向唐王朝贡献貂皮以充租赋,也是唐与回纥绢马交易的重要通道。它的开通与维护,密切了回鹘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有助于中央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辖。
三、汉唐时期北部边疆经济治理取得的成效
(一)减轻了国家长途运输压力,保障了部分边疆军粮供应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进行经济开发与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汉代实行屯田后取得了“益垦溉田”[5]3912“多田积谷”[5]3923的经济效益。屯田开发不仅免除了士卒长途转运粮草之劳苦,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而且解决了部分前线边防戍军的粮食补给问题。实施屯田之策,戍卒且屯且战,使军队能够长期守边,提高了边疆综合防卫能力,确保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和长远发展。唐代疆域“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12]960,这些成效的取得,与中原王朝在边疆的经济治理是分不开的。
(二)提高了边防军战斗力,增强了边疆防御能力
汉唐时期,北部边疆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他们擅长骑射,并拥有优良的战马和精锐的骑兵,中原王朝若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必须以马制马、以骑制骑。拥有强大的骑兵,才能与这些骑马民族在北部边疆驰骋角逐。中原王朝重视马政事业,马匹的供应有了保障,顺利组建了骑兵部队,使军队保持强大旺盛的战斗力。
(三)促进了北部边疆经济发展,缩小了腹边经济差距
两汉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在北部边疆被广泛使用,垦殖面积不断扩大,边疆农业得到了发展。同时,水利工程也开始在北部边疆兴修。水利建设的发展,缓解了北部边疆因降雨量少和不均对发展农业生产的影响,改善了发展农业的条件,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增加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
唐代经济治理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大唐北部边疆的屯田得以迅速发展,其地域范围从山西北部扩展到河北、河套地区和河西地区。史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20]165实际上,唐朝的军屯数量远不止此,而是共有1 039屯。《通典》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朝廷颁布诏令“隶州镇诸军者,每50顷为一屯”[17]19。按每屯50顷计算,北部边疆地区屯田面积则近43 250顷左右,年产量达430万石左右,其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因而出现了“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21]2616的丰收景象。
(四)促进了北部边疆社会整合,增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屯垦开发,有效保障军队的粮食补给,推动了北部边疆的经济开发。互市贸易,加强腹、边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加强了北部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推动了边疆经济的发展,缩小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展道路交通,保障道路通达,使得中央王朝的军队能够适应长途远征的需要,不断得到充足的兵员和物资的补充,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道路的畅达,有利于加强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央政令可以借助交通系统迅速、及时地传达到北部边疆基层,密切了中央与边疆的联系。同时,各民族在共同开发边疆进程中,促进了风俗习惯的融合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为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传播到更远的边陲地区,不仅加快了当地文明的进程,也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原与边疆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吸纳、融通和汇合,并最终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在经济开发活动中,边疆各民族杂糅相处,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了解,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共同进步,推进了北部边疆社会整合,增强了各族人民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汉唐时期北部边疆经济治理的历史鉴戒
治国必治边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北部边疆作为我国边疆的一部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屏障。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北部边疆经济治理有自己的特色与建树,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汉唐统治者自身阶级本质的限制,统治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部边疆危机,更不可能真正实现北部边疆的良好、有序治理,其治理注定会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北部边疆治理所需成本大
人口和粮食乃一个国家经营边疆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汉唐王朝为了维护在北部边疆的长期统治,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守疆拓土,也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常备军保卫国土。因此,徙民实边和屯田垦荒是汉唐王朝的一致选择。徙民实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北部边疆农耕人口的数量。但对于贫瘠荒凉的北部边疆,解决大量边防驻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困难非常大。军屯虽然解决了部分军粮问题,但开发北部边疆的经济成本较高。至汉武帝统治后期,已出现“天下户口减半”[5]1427,国家“府库并尽”“县官大空”[5]1136的局面。而屯田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军费开支日增。盛唐时期的北部边疆便出现了“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12]1370之困境,唐后期北部边疆因时局的动荡,北部边疆基本荒芜。
(二)统治者对北部边疆的治理缺乏持续性和连续性
汉唐时期,统治者往往关注的是对北部边疆游牧民族的羁縻统治,而对北部边疆的经济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导致北疆经济发展缺乏持续性和连续性。西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了高潮,但到西汉后期被搁浅。东汉时期,朝廷在北部边疆问题上缺乏长远眼光,对北部边疆的投入逐渐减少,甚至有放弃北部边疆及西北边疆的念头,并多次“悉罢边屯”[10]2368,频繁大规模内徙边民,导致北部边疆人口锐减,屯田区开始荒芜,边郡经济逐渐萧条,加剧了北部边疆局势的动荡。唐中后期,北部边疆出现了众多藩镇,藩镇之间相互攻伐,政局动荡,北部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也因时局混乱而搁浅。
综上所述,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实行屯垦戍边、互市贸易、马政、交通等举措,保证了在较低成本基础上北部边疆治理程序的运行,是“安中国之要术”[22]288。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边防士兵的后勤粮饷供应,减轻了北部边疆各族百姓的经济负担,还促进了北部边疆经济的发展,保障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加强了北部边疆与中原的联系。汉唐时期国家对北部边疆的经济治理对今天边疆治理和边疆稳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