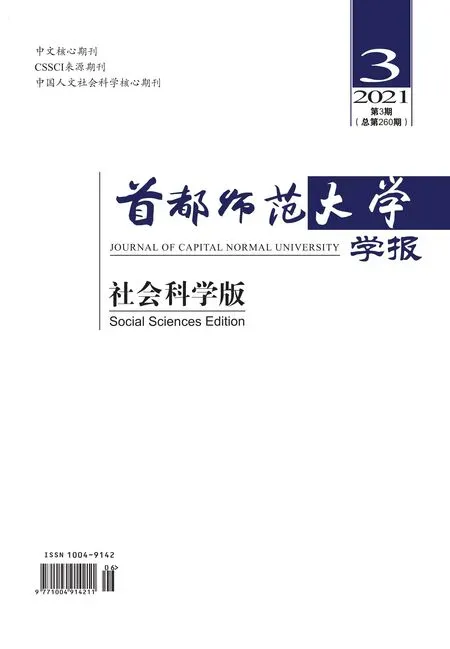早期人类的“完整性思维”对“全知叙事”的影响研究
邱紫华 余 杰
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指出:“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计其数;种类浩繁,题材各异。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遍布于神话、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①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因此,进入20世纪,随着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起,小说的叙事方法成为文学形式研究的热点。到了20世纪中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叙事学”确立。此后,约50年间涌现不少叙事学理论大家,如研究叙事线条的米勒、研究叙事视角的托多洛夫、布斯、热奈特、查特曼等、研究叙事结构的普罗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等,他们成果斐然。在他们叙事学的研究中,“叙述视角”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叙事者所采用的人称身份决定了他叙述的视角、他的叙事风格、故事结构以及叙述者的思想情感倾向。
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将叙述视角定义为:“叙述故事的方法——作者所采取的表现方式或观点,读者由此得知构成一部虚构小说的叙述里的人物、行动、情境和事件。”①Abrams M.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ms,Philadelphia:Harcourt Brace College,1999,p.231.国内学者则认为:“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无论是在文字叙事还是在电影叙事或其他媒介的叙事中,同一个故事,若叙述时观察的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②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因此,“叙事视角”是叙述的着眼点,它又往往被研究者们称为“视点”(point of view)、“视觉角度”(angle of vision)、“透视”(perspective)、“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on)等。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包含有观察者的视角、叙述人对人物、事件的观察和理解上的切入点、叙述的重点和细节的选择等要素。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叙述人称总体来说有四种情形: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以及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叙事作品所采用的“人称”和“视角”变换的叙述。20世纪后期,西方结构主义批评家开始对叙述视角的形态加以细分和深入研究,如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③兹韦坦·托多洛夫:《文学作品分析》,引自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8页。。从这些概念出发,我们集中探讨“全知视角”的特性及其形成的文化因素。
一、“全知视角”与“全知叙事”
所谓叙述的“全知视角”(omniscient perspective),直译为从“无所不知的角度观看”,也称之为“全能式叙述视角”。按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说法:当叙事者的观察视野大于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视角时,可以将其定义为“全知性视角”。④兹韦坦·托多洛夫:《文学作品分析》,引自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8页。
(一)“全知视角”的突出特点
其一,叙述者始终是同一个人、持同一个主观的角度观察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现象、人物的行为及其过程。就像一位手持一个一个提线木偶的“表演者”,他既描述人物的动作,又模仿每一个人物的对话;也像电影导演那样,一切均是他的安排,一切都由他创造。全知全能的叙事采用局外人视角。它的观察视角是“单一”的、个人的。
其二,叙述者对他所观察和描述的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即拥有“全知性”。这就是说,这位叙述者虽然是从“单一”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但却能够全面、完整地叙述整个故事的情节、各种各样的事件、各个人物的行为及其心理活动。叙述者如同神话传说中的“天神”那样是“全知全能”者:什么事都知道,什么隐秘都能够描述和揭示,还能够逼真地描述和再现人物的行动场景、思想状态、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等,如《红楼梦》原著第六回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及被删掉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等极其隐秘的情节和细节。这就意味着叙述者的“叙述”具有“无所不知”即“全知视角”的特性。亦即,“可知性”“知晓一切”是“全知视角”的重要特性。
从逻辑上讲,叙述的“全知视角”除指叙述者的“全知”之外,还潜在地规定着阅读者也应知晓的意思。作者(叙述者)知晓一切,清楚一切,并且通过他的叙述,阅读者也就能够知道、了解并理解这一切。因此,“全知视角”的“知”中,就包含着叙述者的“全知”和读者的“全知”,其目的在于让一切人都知晓,一切事实都昭然若揭、清楚明白。如果只有叙述者知晓,而阅读者不知晓,也不能称之为“全知视角”。
其三,“全知视角”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拥有叙述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一方面表现为作者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环境的一切限制,去尽情地描写或叙述。例如,《西游记》中对孙悟空的描写,从出生到当上“齐天大圣”,再到被压在大山之下,再到跟随唐僧西天取经,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作者描述孙悟空的活动范围,则是上天、入地、下海、入云。在这一时间过程和空间环境中,作者似乎与孙悟空如影随形。整部《西游记》中,作者都是自由逼真、毫无遗漏地记录下了孙悟空的全部经历和行为。另一方面,“全知视角”的“自由性”还表现为:它既可以“历时性”地从开始到结束完整表现事件和人物;又可以“共时性”地同时表现不同的对象。例如,同一时间在不同的人物之间发生的事,作者都知晓,可以采取“话分两头”等方式进行同时描述。可见,“全知视角”的自由性意味着叙述者是自由的,不受时空约束。同样,阅读者、接受者也获得了与叙述者、作者同样的自由。
其四,“全知视角”叙述者还充当着“预言家”的身份。他不仅可以对作品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件详尽地陈述和描写,而且对将要发生的事件及其最终的结果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故事中每一个人的遭遇、命运和最终的归宿都可以加以预测、暗示,并最终予以证实。例如,《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及其他女性的终极命运,早就在“太虚幻境”秘柜中收藏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中确定了!“全知视角”叙述者则是随着故事情节的线索,把这些结果一一予以叙述、展示而已。有灵气的、思维敏锐的读者,也就可以根据叙述者、作者的设定和暗示,提前知道人物的终极命运。
这样看来,“全知视角”的叙述似乎是最完备、最客观的叙述,好像它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历历在目,逼真而生动。这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的优势在于,其视野可以无限开阔,适合表现时空延展度大、人物众多、场面宏阔、社会矛盾深而复杂的题材。由于“全知视角”具有这些突出的功能,所以“全知视角”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叙事性文学中最常用的叙事视角。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史诗、寓言故事几乎都采用“全知视角”来陈述故事。例如,古代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古希腊《荷马史诗》都采用了“全知视角”的叙事方法。因此,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认为,“全知视角”叙事是传统的、自然的叙事叙述模式,采取“全知视角”写作的作家是“全知全能”的作家。①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页。所以,20世纪的叙事学理论家把它称之为“全知全能视角”“上帝视角”“神的叙事观点”。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美学把文学艺术的“真实性”尊奉为文学与艺术的生命;真实性成为了西方美学关于“艺术美”的重要审美标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都认为,那些采用“全知视角”叙事的史诗和小说都具有高度的真实性。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大多采取了“全知视角”的叙事方法。据说,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客观、全面、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现象。19世纪德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谢里曼就根据《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城海岸线准确而逼真的描写,居然寻找到了古代“特洛伊”城的遗址。
(二)“全知叙事”的“全知”悖论
进入20世纪,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富于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艺术的研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美学观念,并兴起了形式主义美学思潮。例如,法国思想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从生理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的视觉功能。他通过对传统的“六面体”概念进行考察,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个人观察任何一个事物,都只能从一个固定的视角进行;任何一个固定的视角都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而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整体。同理,任何一个人看一个六面立方体,都只能看到它的三个面。这说明:“六个面的立方体”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结果,而只是人们头脑中的知觉经验推理的结果:“有六个相等面的立方体不仅是看不见的,而且也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在我看来有一个有六个面的立方体,之所以我能把握物体,不是因为我从内部构成物体;而是因为我通过知觉体验进入世界的深处。有六个相等面的立方体是概念—界限(idée-limite),我就是通过它来表达在我眼里、在我手里和在其知觉明证中的立方体的有形呈现。”②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2—263页。简单地说,人的视觉是不可能同时感知“六个面的立方体”的;人的视觉只能直接感知看到物体的三个面。而“六面立方体”只是人们通过感觉经验而形成的“主观的观念”——概念,梅洛-庞蒂从而指出了“六面体”只是一个主观思维创造的概念,而不是视觉的事实!从科学事理上讲,“全知”的叙事被证明为“不可能”。
20世纪科学哲学的原理揭示了另一个惊人的事实:任何叙事都只能是“单一角度”的叙事;“单一角度”的叙事所传达的仅仅是“片面的真理”。同样,“全知视角”依然只是一种“单一角度”的叙事。所谓的“全知叙事”,也只不过是叙述者把个人的“单一的视角”加以膨胀、放大而拥有“无所不知”的功能而已。“全知视角”叙事其实质是叙事者把自己的主观精神加以神幻化、扩张化的结果。“全知叙事”的东西只是作者或叙述者的主观精神的展示而已。它所传达的也只是叙述者个人运用想象或幻想所编造虚构的事件、场景和情景而已。因此,作为传统的、自然的“全知视角”叙事在20世纪后期受到文学批评家们的挑剔和怀疑是非常正常的。
20世纪叙事学揭示出“全知视角”的秘密。研究文学叙事形式的学者注意到,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方法所叙述的故事“事实”严重违反了生活真实,是一种貌似真实的“伪真实”,是以假乱真的“幻影”。因为,任何一个叙事者或作者都不可能观察到一个事件完整的过程和所有人的行为;任何一个叙事者都不可能洞察到所有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的生成和变化。可见,“全知视角”叙述的东西,不是幻想就是主观拼凑,是最不真实的东西。
“全知叙事”遭受挑剔和摈弃的原因,根本上讲在于它的主观性、虚假性,即缺乏可信度。正如美国学者万·梅特尔·阿米斯在其《小说美学》中说:“写小说常用的方法就是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地插入到故事当中向读者讲述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这种步骤有些牵强,它容易破坏故事的幻觉,除非作者本人是个极为有趣的人,否则这种插入是不受欢迎的。”①万·梅特尔·阿米斯(Ames,V.M.):《小说美学》,傅志强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全知叙事”的作品中,所展现的一切都是作者主观意识和意志的体现,永远只有作者一个声音,人物都因叙述者思想情感的倾向性而染上不同的道德情感色彩,读者被叙述者紧紧地控制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中。这显然也不符合现代人张扬自我的取向。因此,“全知视角”的叙事被批评得体无完肤而惨遭摒弃!更多的叙事者转而采取“内视角”“外视角”和多种视角相结合的“多元化”的叙事角度。
二、“全知视角”叙事形成的文化原因
20世纪“叙事学”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关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今人质疑的“全知视角”是古代各民族叙事性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寓言故事)应用最多的叙事视角?为什么世界各民族都采用“全知视角”的方法来陈述故事?为什么韦勒克、沃伦把“全知视角”叙事称之为“传统的”和“自然的”叙事?为什么“全知视角”的叙事都采取强调先后次序的“线性”叙事?
上述问题涉及“‘全知视角’叙事方法形成的文化原因”这一重要的审美文化理论问题。我们认为,要探讨这一审美文化理论,应当像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主张的那样:“凡是学说(或教义)都必须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开始时开始”②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我们的研究起点应该是这些动物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③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维柯推崇的研究方法就是“追本溯源”的方法。根据维柯的主张,要探讨“‘全知视角’叙事方法形成的文化原因”这一重要问题,就应当研究早期人类诗性思维的“认识论”的特性,即为什么早期人类渴望对外部世界的“全知性”认知?早期人类诗性思维的“完整性思维”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制约他们口头叙述和文字叙事的“全知”方式的?我们认为,要解答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至少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早期人类“诗性思维”的“完整性思维”特性对“全知叙事”的影响
所谓的“诗性的思维”,就是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指出的那种“人类早期的思维形式”,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文化人类学者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原始思维”。这种思维是直觉的、充满想象的、以情感作为动力的、大量运用象征比喻的、形象(意象)的思维方式。其中理性的、逻辑的思维成分混同在诗性的思维之中,以直观的、经验的实践理性运用于生活与生产中。我们认为,诗性思维从两个方面制约并影响了“全知视角”叙事的形成。
此前,有一些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曾零星地提到早期人类叙事的某些特点,但没有展开论证,更没有从叙事学学科意识的角度,对人类思维和叙事的关系加以研究和论证。他们仅仅是把早期人类这些零星的、似乎极端的、奇特的“叙述”事例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现象来举证。例如,英国学者泰勒、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美国学者博厄斯、俄国学者普罗普等在其著作中都是这样看待早期人类的叙事现象的。
20世纪的思维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早期的“诗性思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完整性思维”。“完整性思维”表现了早期人类的一种心理倾向或心理诉求。它激发人类从整体上认知对象,要求完全彻底、细致周详地认知和把握对象。如果人们不能全面清晰地认知和把握对象,就必然产生神秘感、惶惑和恐惧感。在“完整性思维”的制约下,人们的心理必然要求或希望对于生活中所有的现象和事件都给出确切的答案。为了对现象和事件给出答案,首先就用经验来说明,当实践经验不足以解释和回答疑问时,人们就采取想象、猜测、幻想来填补思维逻辑中的空缺。人类的好奇心理、探秘心理就是要穷究原因,为自己寻找到满意的答案。人类的探秘和好奇心理促成了在认知上,凡事必须有明确的解答;在表达和描述上,必须注重细节、毫无遗漏。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解的思维特性,促成了“全知视角”的叙事特点。
在人类早期的艺术中都呈现出“完整性思维”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绘画、雕塑、民间口头叙事和歌谣等文学形式中,都表现为尽可能地展现外部世界和人物大而丰富的信息量;表现为创作者、叙述者的“全知”功能和接受者的“全知”效应。
首先,完整性思维充分地表现在人类古代的绘画上,这就是“散点透视”和“正面律”。
古代早期各民族的绘画绝大多数都遵循“散点透视”和“正面律”原则,几乎都不采用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那样的方法,即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来观察对象、来表现对象的“焦点透视法”。古代各民族往往运用“多点透视法”(又称“散点透视法”),即从物体的各个面来表现画面。“多点透视”就是把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面”都给画出来,从而明显地“歪曲”“扭曲”和改变了对象的轮廓形象。这就是著名的绘画艺术的“正面律”方法。例如,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从各个面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就成了“被扭曲”的、拼凑的形象:人物形象有侧面的脸、正面的胸、侧面的腿、正面画出来的大眼睛、无遮挡的、完整的手臂和手。同样,巴比伦和波斯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中国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和汉代画像砖中的房屋等,都是把看到的和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逐一展开,全都表现在同一个平面上。
这并非是古代艺术家不懂焦点透视,而是在“完整性思维”的制约和驱使下的“全知”表现和“全知”传达。英国艺术史家、美学家E.H.贡布里希指出:“心理学家们想测试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趣味,给他们看各种鸟的图画,结果发现了一个干扰因素:土人们‘不喜欢不完整的再现,例如为了表现透视效果而略去鸟脚的那种情况’。换句话说,他们和柏拉图一样反对错觉主义(即焦点透视法——引者)做出的种种牺牲。”①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其次,完整性思维制约下“全知视角”的叙事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口头叙述文学中。其叙事特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种叙述面面俱到、繁琐重复、绝无遗漏。古代的口头文化是原始思维的体现。古人一切思维活动和交往活动全凭口头语言表示。对口头语言的高度依赖,使古代人类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注重表达细节真实的思维习惯。
古人注重事件细节的表现和陈述,在叙述过程中决不遗漏任何鸡毛蒜皮般的细节。古人认为这是最完备最真实地再现事实的方法。所以,原始的叙事特点就是繁琐和重复,由于繁琐和过多的重复使人感到缺乏重点。对于古代叙事来说,细节就是情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指出:“多数原始叙述文学的特点是不厌其烦地交待过程,列举细节,一笔不漏。”②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匈牙利美学家乔治·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引用了马克斯·施密特描述的一个例证:“一个印第安人在答复这次旅行要多久时‘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表示太阳一天的行程,然后做出睡觉的表情,用这种表情手势重复的次数表示到达旅行目的地所需的天数。连最后一天到达目的地的准确时间也是用这种方式表示的,他用手指出太阳的高度来说明到达的时刻。’”①乔治·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这一事例说明了完整性思维制约下的叙事特征。这种叙事方法,在人类早期的口头文学、早期诗歌中是最基本的、最常见的叙事手段。这种不遗漏任何细节的繁琐重复的叙事手法,后来发展为所谓“环中环”“套中套”的叙事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典型的代表就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的叙事方式。这一特性在现代各民族的民间叙事诗或者民间故事的情节叙述中还有大量的遗存。
反之,在古代,像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那样从“事件的行进中”开始的简洁的叙事,几乎难以寻觅:“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妻子发觉了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言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只是夫妻两个,就是他们整个的家庭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②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版,第3页。可见,“完整性思维”制约下的古代叙事,就是否定或反对概括,反对简略。如果让古代人用高度概括的、简略的方式叙述一件事件的经过,就等于要求他抹杀事实,隐瞒真相。早期人类的“完整性思维”重事实、重细节、很繁琐、反对简化和概括的思维模式,在后来的叙事性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延伸。例如,中国诗赋就不乏对东西南北、上下四方的空间方位的详尽描述:南北朝民间诗歌《木兰辞》中就罗列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司马相如《子虚赋》在“子虚”盛夸楚之云梦“方九百里”的阔大时,赋文曰“其东则有蕙圃……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其西则有涌泉清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其上则有鹓雏孔鸾……其下则有白虎玄豹”③司马长卿:《子虚赋》,引自《文选》卷七,萧统编,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0页。,等等。
另一方面,完整性思维制约下的“全知叙事”严格遵循“线性叙事”来建构故事。所谓“线性的叙事”是指所讲述的事件必须有头有尾、完整有序;叙事须严格遵循时间进程;叙述过程中绝对不能有“插叙”或“倒叙”;更不允许中断故事或者从事件的中间开始叙述。这种叙事结构就是“线性结构”。中国宋代话本大多具有“线性”的叙事结构。例如,山东某地有一个张家庄,张家庄有一个张员外。张员外生养有一女,名叫娇娇,自小就同花桥镇李家二公子订亲。如今,娇娇年方二八,长得花容月貌……也就是说,“线性叙事”生成的思维根源,在于人类“诗性思维”有着强烈的秩序感。
早期的人类有着完全彻底、细致周详地认知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原始人类在纷乱的自然现象中建立一种秩序,这就是人类心理的“秩序感”。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R.Popper)说过:“我先是在动物和儿童身上,后来又在成人身上观察到一种对规律性的强烈需要——这种需求促使他们去探索各种各样的规律。”④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转引自E.H.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杨思梁、徐一维、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早期先民对外界的对象进行了非常详细、非常繁琐的分类,并加以细致的排列、比较、组合,企图把各种各样的自然事物纳入一种秩序系统,以便认知自然和驾驭自然。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引用科学家的话说:“科家们……唯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容忍的就是无秩序。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自觉地减少知觉的混乱,这种努力最初以一种低级的,而且多半是不自觉的方式开始于生命的起源时期。……科学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我们称作原始的那种思维,就是以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也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一位土著思想家表达过这样一种透彻的见解:‘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有其位,因为如果废除其位,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宇宙的整个秩序就会被摧毁。”①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列维-斯特劳斯还指出:“任何一种分类都比混乱优越,甚至在感官属性水平上的分类也是通向理性秩序的第一步。”②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页。可见,原始人善于把性质相同的事物,进行某种匹配、组合,以达到对一种秩序和规律的认识,如用啄木鸟嘴来治人的牙痛就是如此。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18]2013年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全面阐述了青年教育的重大关键问题。2018年5月2日,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第六次到北京大学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以及“青年如何健康成长”等重大问题,他强调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17]在这些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明确了新时代青年教育工作的目标定位、主要任务、重要举措和基本要求,这也是新时代高校青年教育工作应遵循的原则。青年教育观,正是习近平青年观的实践基础。
20世纪产生了很大影响力的“格式塔心理学派”强调,人类对于外界纷乱的事物有着“秩序”化的知觉要求。这种对于“秩序”的知觉,也显示出希望让形式变得简单化的趋向。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指出:“我们的知觉偏爱简单结构、直线、圆形以及其他的简单秩序。我们在混乱的外部世界里往往易于看清的是这类有规则的形状,而不是杂乱的形状。散乱的铁屑在磁场里会受到磁力的作用而排列成有规律的图案,同样,到达大脑视觉皮层的神经脉冲信号也会受到喜爱和厌恶这两种心理引力和斥力的作用而重新排列。”③E.H.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杨思梁、徐一维、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早期先民的叙事,正因为其心理上强烈的“秩序感”,才导致原始歌谣、史诗、传说在叙事上倾向“有先有后,有条有理”这一富有秩序感的“线性叙事”模式的产生。
(二)古代的神灵崇拜是形成“全知叙事”的催化剂
原始人类的“诗性思维”中蕴含着浓厚的神灵崇拜意识。神灵崇拜包括对“神的代言人”——祭师、宗教领袖的崇拜和服从。神灵崇拜是人类早期叙事“全知视角”的催化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各民族宗教中都有“创世神”、主神、大神。他们是“全知全能”的。
古埃及人心中的“太阳神”阿蒙、印度教的创世神“大梵天”、犹太人《圣经·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基督教徒崇拜的“上帝的儿子”耶稣、伊斯兰教徒信仰的“真主安拉”、中国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以及其他民族宗教中的“神”,等等,这些大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除了“全知全能”的“大神”之外,各类宗教中的祭师、诗人也都是“神的代言人”。古希腊人就把“诗人”看成是“神的代言人”,即“创造者”。
犹太人在《圣经·旧约》中描述了上帝“六天创世”“大洪水的生成”及“诺亚方舟”的故事,叙述了在西奈山,上帝耶和华秘密会见摩西时突然显灵并授以摩西《十诫》的场景。这些既神秘而又隐秘的事迹,只有神和祭师才能知晓。这些“神迹”也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和他的代言人——祭师才能够向人叙述。这种叙述必须采取“全知视角”即“上帝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够传达出“上帝知道”“祭师知道”及“广大的群众”也知道的“神圣的信息”。
印度教崇拜的大神“梵天”既有“创世”的能力,又有“全知全能”的功能:梵天通过思维、意念创生了万物。全宇宙的生命都由他身体里流出,并由他维持着生命。梵天不仅用思维和意念创造了万物和人,而且还把自己的思维智慧赋予人,使人成为能感觉和思维的生命。当然,万物所知所想、所作所为,梵天都知晓!《蒙查羯奥义书》中说,梵天的特征是:“恒常、遍入、遍在、微妙极。他是不变不灭者,是孕育和产生万物的根本。”④《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这样的神就是全知全能的神!天下之事,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伊斯兰民族崇拜的天神“真主”是全知全能的神。《古兰经》中说:“他已为你们创造了大地的一切事物,复经营诸天,完成了七层天。他对于万物是全知的”;真主还说:“我的确知道天地的幽玄,我的确知道你们所表白的和你们所隐讳的。”⑤《古兰经》(第二章“黄牛”),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中国汉民族的宗教是泛神宗教,有数量众多的大神,传说中的神仙就有“千里眼”“顺风耳”。中国佛教信仰中有“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所以,中国人常说:“人在做,天在看!”
概言之,各民族的祭师、歌师、游吟诗人都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是万能的“知情者”,他们代替天神发言和叙述。因此,早期的神话、史诗、民间故事、传说、寓言等自然而然地都采用“全知视角”来叙述。可见,对“神”的崇拜催化了“全知视角”的产生。
(三)古代哲学思维的“整体观”决定了“全体”才是“真理”的牢固信念
根据“诗性思维”的“整体思维”观念,早期的人类认为:把握“全体”就把握了“真理”;把握局部就是谬误。这样的认识和观念在各民族的宗教中有相近的表达。
基督教的“上帝”就是真理,就是宇宙、世界的全体,是“一”(太一)。伊斯兰教的“真主”就是真理,是宇宙、世界的全体,是“一”。印度教的真理观强调“至大无外”的绝对真理是“梵”。“梵”是“一”。
公元前6世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经阐发过这样的观点:任何“真理都是片面的”,任何人的“单一角度”的观察都是“主观的”观察;任何人的“单一角度”的叙述都是主观的叙述。佛教的本体观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地、水、火、风”四种细微元素和合而成的,也有另一种说法:是由“地、水、火、风、空”五种细微元素和合而成的。因此,任何“单一的因素”,如单一的“地”(土)、“水”“火”“风”都不能构成事物。既然万物都是四种或五种细微元素和合而成的,因此,万物的本质相同,只是形状、形态不同而已。这就是佛教对“世界本质”的看法。
佛教的“本质”观念决定了它的“真理”观: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一”和“全体”才是事物的真理。“单一的”就是片面的;“和合的”才是真理。佛教从多元性、整体性来把握事物的真理,也从“多角度”来观察和描述外部世界。例如,在印度佛经《南典经藏小部自说经》中,有一篇《生盲品传闻经》,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盲人摸象”。这篇佛经表明了佛教的真理观。
佛陀(释迦牟尼)住在王舍城的祇陀林园的时候,有一些不同宗教教派的沙门和婆罗门也住在王舍城。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思维方法,因此在思想观念上就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各持不同的、相互对立的见解。他们“各有所信,各有所见,各有所好,各有所乐”,“如是诸沙门、婆罗门,各有异见,争论斗诤,以如矛之口,互相刺击而各自谓:法如是,法不如是,法不如是,法如是”。①糜文开:《印度文学历代名著选》,台湾东大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31页。当弟子们向释迦牟尼请教,如何看待各派宗教徒相互攻讦的观点时,佛陀就用寓言的方式,给弟子们讲述了他的观点。这就是著名的“盲人摸象”的寓言:一个国王聚集了全城的盲人前来摸大象,并要他们说出各自感知的大象是什么样子。由于每一个盲人所触摸到的大象的部位不同,他们对大象的感觉和印象就不相同,描述也就不相同。应该说每一个盲人的感觉和判断,在他所感知的范围内都是正确的,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主观真实”即“片面的真实”。然而,盲人们各自对于大象模样的叙述,又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为此而争吵起来,互相否定、互相攻击。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那些外道沙门和婆罗门所争论的问题和看法,就像这些盲人一样,“无有眼目,不知利,不知非利;不知法,不知非法……各有异见,争论斗诤,以如矛之口,互相刺击”②糜文开:《印度文学历代名著选》,台湾东大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33页。。最终,他们都堕入了虚妄不实的见解之中。
这就是释迦牟尼所阐发的观点:“真理都是全面的”,任何人的“单一角度”的观察和感知都是“主观的”观察和感知;任何人的“单一角度”的叙述都是主观的、片面的叙述。佛陀的见解,就是佛教哲学“整体真理观”即“因缘和合”的学说:万物都是由多种元素和合而成,只是形状不同而已;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东西;事物的真相、事实的真理只存在于多种要素的组合之中,存在于“因缘和合”之中。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根据佛学“因缘和合才是真理”的原理写下这两首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苏东坡的诗具有深刻的哲理。他根据佛学“因缘和合”的理论,来说明美妙的琴声、美妙的音乐是多种元素和合而成的道理。这些元素有琴身、琴码、琴柱、琴弦,更重要的是要有会弹琴的手指等,其中任何单一的元素都不会产生美妙的音响。苏东坡《琴诗》中深刻的哲理在于,探究真理,就是要从事物的存在状态,即从多种组成要素及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看某一事物。同样,《题西林壁》也是强调只有通过多角度的观察、散点透视的描述才能够全面、客观而真实地表达对象的情态与样貌。可见,佛教哲学的“全体”才是“真理”的观念,支撑着“全知视角”和“全知叙事”观念。
(四)“全知视角”的叙事手法是古代“群体叙事”的成果
早期人类的传说、史诗、民间故事都是集体创作,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陈述本民族的传说和历史。所以,古代人的叙事活动,就是全民族每个个体共同参与的“群体叙事”。这种群体的“叙事”,是公开的、透明的,其目的是让全民族每一个人都“知晓”。
全民族“群体叙事”中的神话、传说、历史是共同认可的“历史事实”。为了达到准确传承的目的,“全民族的叙事”要求每一个叙述者毫无遗漏地描述。叙事者所知道的事件一定要表现;叙述者“不知道”的隐秘的事件,也要通过大众的想象、猜测、推理和虚构来加以完善。可以说,古代的“群体写作”“群体叙事”强化了“全知视角”的叙事功能。即,“全知叙事”中既包含着群体作者都“知晓”的东西,也包含有群体“接受者”应当“全面知晓”的东西。“全知叙事”的“全知”既是作者的“全知”,也是接受者、阅读者的“全知”。“全知叙事”是为了实现民众的“全知”,它需要排除任何“不可知”或“不知”的因素。
从叙事的本性而言,“全知叙事”表现出的确定性是人类内心需要的,作为读者也总希望从作品中获取某些确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关乎故事,也关乎价值观和时代精神。也就是说,“全知叙事”既应包含着群体作者都“知晓”的东西和想要传达的东西,也应包含群体“接受者”应当“全面知晓”的东西——从形式到内容。如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对于般度五子的身世来历,为了让大家都知晓他们的神性出身——坚战是正法神的化身、怖军是风神的化身、阿周那是天帝因陀罗的化身、无种和谐天是双马童的化身,群体叙事的代言者——神化的叙述者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强调般度五子半人半神的身份:通过护民子之口讲述,通过这些主要人物的自叙来强调,通过其他人物的提示,通过仙人或天神的警示、精灵的预言及民众评论等多次加以强调,并借助婆罗门宗教信仰共同体使之成为大家的叙事共识——五位英雄不同于常人,他们注定负有神圣使命,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及最终胜利,既是上天的意旨,也是正法的胜利;他们的故事既是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是印度人民的宗教信仰。史诗中这位“睿智的叙述者”就这样向我们表明:“全知叙事”的“全知”既是作者的“全知”,也是接受者、阅读者的“全知”,它实现了民众的“全知”,排除了任何“不可知”或“不知”的因素,它是群体的娱乐,也是集体的智慧。所以,从哲学认识论看“全知叙事”的实质,它就是一块晶莹透亮的“水晶石”,在人们的认识方式上发挥着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