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遗产法视域下的非遗保护国际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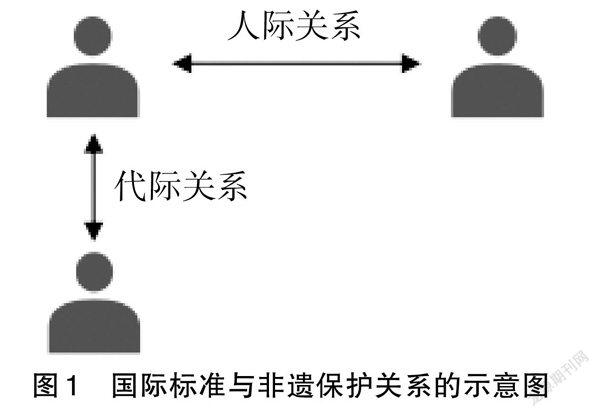
摘 要】结合国际文化遗产法这一领域的兴起并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章提出非遗保护的国际标准问题,即“人权”“相互尊重”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因应非遗传承以人为依托的特点,这三项国际标准之于非遗保护的意义分别指向人的本体、人际关系和代际关系。《非遗公约》丰富的国家实践已表明,尊重人权是公约各项原则的根本,相互尊重是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保护工作的行动目标。“十四五”规划已将非遗保护列为我国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适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十年以及《非遗公约》生效十五年,重视《非遗公约》的解释问题并使之与我国法律进一步对接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际文化遗产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标准
【作 者】王薇,法学博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讲师,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海洋法团队成员。广东佛山,528000。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6-0135-0010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下称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文称《非遗公约》)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公约之一(缔约国数量已达到180个)。公约自2006年生效至今已十五年,随着在各缔约国实施的日渐深入,近年来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称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与反思措施,如何解释公约的核心条款显得愈发重要。不少学者注意到《非遗公约》第2条明确规定“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相互尊重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正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对于如何解释该条中的“人权”“相互尊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学界鲜有答案。
本文将从整体上阐释三个非遗保护国际标准的涵义、指向意义和实施地位等,结合国际文化遗产法兴起的国际背景对《非遗公约》的多重立法目的进行分析,立足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称《非遗法》)提出衔接建议。于我国而言,我国是现任联合国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的委员国(任期为2018—2022年),2021年正是我国《非遗法》颁布实施十周年纪念。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均强调要积极做好《非遗公约》的缔约工作,进一步提高履约能力和水平,完善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在此背景下,注重国际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进一步对接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文化遺产法的兴起以及《非遗公约》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文化遗产法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新分支。就国际法的发展而言,文化遗产成为国际法的专门保护对象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二十世纪之交,1899年和1907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两次和平会议首次将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编撰进有关战争的国际公约中,但只有在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后,文化遗产才因其作为世界不同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从而逐渐成为国际保护的独特对象。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近半个世纪以来,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法迅速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已由战时保护延伸至和平时期保护,保护对象也从物质拓展至非物质、从陆上拓展至水下,涵盖遗迹和遗址、国际贸易中的文化财产、自然文化遗产、非遗、水下文化遗产以及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等。对此,《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在“文化遗产”词条中指出:在当代国际法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独立领域,且已经达到相当复杂和精细的程度,这种保护主要是由条约和一些软法性质的文件所提供。[1]
近十年来,对于这些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国外有学者开始使用“国际文化遗产法”的概念,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1无独有偶,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也开始使用“国际文化遗产法”一词,如钟慧(2018)、周刚志等(2018)、孙雯等(2018),虽不多但也说明共性的存在。相较而言,我国学者更早也更多使用“文化遗产法”一词,正如王云霞教授在《文化遗产法学:框架与使用》(2013)前言中指出,“文化遗产法学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及其社会功能的一门学问。”“近几十年来,国外文化遗产法学研究已经成果斐然,……然而在中国,……可以说文化遗产法学研究的薄弱和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文化遗产法律实践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另有些学者虽未将该领域称为“法”,但关注的也是同样的对象,如郭玉军教授主编的《国际法与比较法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2011)即是相当全面的研究。
国际文化遗产法的发展呈现出与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工作的扩展而同步的趋势。目前,教科文组织框架下共有六大文化公约:
上表所列的信息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六大文化公约中的半数是2000年后通过的。仅在踏入二十一世纪的头五年时间内,教科文组织接连于2001年、2003年和2005年通过三部重要文化公约,分别保护水下文遗、非遗和文化表现形式,且每部间隔时间仅一年,彰显了国际社会对文化保护的决心,也意味着国际文化遗产法的兴起。其二,在同期通过的文化公约中,《非遗公约》发展最为迅猛,仅十年时间缔约国数量已跃居第二,正在向全球性公约发展。
一方面,国际文化遗产法正在蓬勃发展,《非遗公约》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需要更多的学理思考;另一方面,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关注文化领域的法律问题(不论是国内法领域抑或国际法领域)属当然之举。2021年8月的两办意见也明确提出要统筹整合资源完善非遗相关理论研究体系。
二、《非遗公约》的多重立法目的及非遗保护国际标准
(一)《非遗公约》立法1目的分析
《非遗公约》最主要的立法目的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全文有4处直接提到),同时还兼有保护人权、构筑和平文化与促进发展等三个立法目的(序言第1、4、2段)。换言之,《非遗公约》的起草者们以及诸缔约国谈判代表们希望公约实施可以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为各社区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以及发挥非遗作为可持续发展保障的重要性。就序言的地位而言,它可作为解释正文各项规定时的指导方针(阐明意图或强调动机),但其主要功能不是为缔约国或组织成员国设定基本义务。
(二)与立法目的相配套的非遗保护要求
上述三个立法目的不只停留在序言中,而是进一步规定于整个公约最为核心的第2条中——“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相互尊重2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三项非遗保护要求恰恰对应着序言的三个立法目的,这三项要求将在《非遗公约》的实施过程中作为缔约国的基本义务予以落实。
从制定公约时的谈判记录可知,在非遗概念的括性定义部分(即第2.1条)采用了分层结构,由广义概念、内部标准(internal criteria)和外部标准(external criteria)三部分组成(逐层限缩了保护对象的范围)。内部标准指遗产之于某社会群体身份的价值,外部标准指国际普遍认可的规范和要求,这反映的是国际层面非遗保护政策的双轨路径。[2]“外部标准”最初只是一个共识,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努力必须建立在普遍接受的人权、公平和可持续性以及对所有尊重其他文化的文化的尊重之上”[3]。之所以将其称为“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criteria),全程参与公约制定的国际法学者珍妮特·布莱克(Janet Blake)的一段话可作注解,她认为“制定一项新的国际规范文件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一便是起草一个范围足够广泛且可行的非物质遗产定义,……新文件将是填补这一保护缺口的重要步骤。同时,它也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可以在这一重要领域进行国际合作时必然的动态中得到发展”[4]。
在进一步分析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之前,需要就存在于文化公约中的“标准”这一术语进行补充解释。
(三)文化公约中“标准”一词的含义
文化公约中的“标准”(criteria)这一概念,是为了对文化遗产进行国际保护时,根据不同的保护目的而设置的,指的是影响评判和作出判断的因素,而不是评价质量的统一规格(standard)。各项标准与不同文化公约的宗旨紧密相关,因而在文化公约的定义条款中多有“在本公约中”(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或译为本公约的目的)的限定性表述。
各文化公约在对不同类别文化遗产作出定义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規定有多种保护标准。例如:
1954年《关于在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第1条在界定“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时根据两项标准,一是对各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值得保护的文化财产类型的经验准则(empirical criterion)。[5]48
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第1条对“文化财产”的定义依赖于对各文物类别的详细描述以及按照各国国内法对这些物品的重要性标准(如对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科学具有重要价值)。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第2条亦采取同样的定义。[5]48~49
知名度较高的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3条则以“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定性标准(qualitative criterion)对“自然遗产”作出定义。[5]49
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第1条设置了文物须至少100年来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公约标准(conventional criterion)。[5]49
至于2003年《非遗公约》,前面分析了非遗定义中的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双重结构。此外,该非遗定义同时也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首要标准,历年版本的《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下文简称《操作指南》)第1和第2条均是非遗名录列入标准规定(Criteria for inscription on the List)。
三、非遗保护国际标准的涵义与指向意义
关于为何引入这三个概念,其对《非遗公约》的实施会产生何种影响,对落实非遗保护工作又提出了何种要求,笔者已有三篇文章分别论述。概而言之:
第一,非遗保护国际标准之一“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有两方面涵义,一是作为判断标准,避免支持那些违反人权的文化习俗;二是以人权方式保护人们实践非遗的权利,这属于文化权利的范畴。事实证明,非遗保护既促进了人权领域“获取和享有文化遗产的权利”的发展,同时该项文化权利亦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基础,《非遗公约》的诸多理念可依托于该权利进一步落实与完善。[6]
第二,非遗保护国际标准之二“符合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相互尊重要求”与《非遗公约》的制定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理念紧密相关。相互尊重本身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的一项抽象原则,非遗保护实践大大丰富了该原则的内涵,使其具体要求和适用方式得以明晰。鉴于相互尊重原则与《联合国宪章》中的容忍原则联系紧密,二者异曲同工、共同指向构筑和平,因而相互尊重原则可作为国际文化遗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加以巩固和发展。
第三,非遗保护国际标准之三“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意味着如何使非遗保护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也能确保非遗本身的可持续性。《非遗公约》的实施表明,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只属于环境法领域,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需要从子孙后代的利益进行考虑,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国际文化遗产法的一般法律原则。
那么,上述三个国际标准与非遗保护之间是何种关系?为何从众多国际规范中只选择这三个而不是其他作为非遗保护的外部考虑因素?《非遗公约》的缔约历史文件没有给出答案。根据非遗传承以人为载体的特点,笔者认为:三个国际标准的排列本身具有从本体到群体、从当代到下一代的逻辑顺序,且分别指向人的本体、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人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关系。如图1所示:
(一)“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标准指向人的本体
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主体。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签署之日起,促进和保护人权便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非遗公约》也在序言首段特意强调了“国际人权宪章”(即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经濟、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两者又合称“人权两公约”),足见人权因素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其中,《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推进现有国际人权文件、特别是“人权两公约”从而确立各项具体人权的依据,也是各国争取实现的共同标准。自该宣言通过后,国际社会通过多年努力已形成了涵盖防止歧视、土著人和少数群体的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健康权、工作权以及社会福利、进步和发展等方方面面的人权体系。至世纪之交,条约形式的基本人权框架已准备就绪,1993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推动人权框架的全面落实。《非遗公约》正是在2000年前后启动了可行性研究,非遗的传承和实践均是以人为载体,与人权保护的关系天然紧密,将人权方法纳入非遗保护之中自着手制定公约之初已成共识。
(二)“符合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相互尊重要求”标准指向人际关系
相互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秉持和维护的根本原则与核心价值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1945年)的序言写道:战争的根源在于“对人类尊严、平等与相互尊重等民主原则的摒弃”以及“借无知与偏见而散布并取而代之的人类与种族之不平等主义”,故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因此相互尊重原则有着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构筑持久和平的使命。它在多个文化公约及国际文件中均有体现,如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目标之一为“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和平文化建设”以及第2条规定“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非遗公约》第2条中的“相互尊重要求”正是该原则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延伸,可理解为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对所有尊重其他文化的文化的尊重,具有伦理规范的意涵。
(三)“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标准指向代际关系
“可持续发展”概念由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又称《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中首次提出,指“在不损害后代人实践和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发展”。此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可持续发展”已经从一个概念发展为规范(norms),且被载入多个条约和国际组织决议中,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一项新的国际法原则。尽管主要作用于环境领域,但凭着超强的渗透力它已拓展到诸多其他领域,尤其是所强调的代际责任、代际公平问题,更是深刻影响着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比如早在《非遗公约》通过以前,教科文组织就曾于1997年通过了《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宣言》,指出“在充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当代人应注意保护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当代人有责任确定、保存和保护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这一共同遗产传给子孙后代”。可见,在文化领域,同样需要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
四、非遗保护国际标准在《非遗公约》实施中的地位
与《非遗公约》实施的阶段性特点相对应,非遗保护国际标准对《非遗公约》实施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阶段性。在早期的非遗名录评审实践中,三个标准一直未受到重视。针对这一问题,2012年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附属机构(The Subsidiary Body,存在于2009~2014年,2015年后与咨询机构合并为审查机构)的工作报告首次予以指出:申报缔约国呈现出一种反复出现的趋势——未能对该要求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遗产项目本身的性质已足以使这一问题变得毫无意义,然而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每个申报列入名录的遗产项目均须证明其完全符合该定义。[7]2013年是转折之年,因应教科文组织的评估建议,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的重要地位在近年《非遗公约》的实施中逐步得到明确。
(一)尊重人权是《非遗公约》各项原则的根本
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在2014年常会中提醒各缔约国“尊重人权是《非遗公约》各项原则的根本”(be fundamental to the Conventions principles),并要求各国应在申报文件中提供更多资料证明遗产项目的实践如何符合现有的人权文件。[8]在此以前,人权因素在非遗名录评审中普遍受到忽视。2016年,人权因素成为非遗名录评审的重点考察事项,这在当年的评审决定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委员会不仅鼓励缔约国在申报文件中主动提供遗产项目与现有国际人权文件是否相符的资料,[9]而且在多个遗产项目的评审决定中专门提及人权问题。
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09年所设立的“文化权利领域的独立专家”研究成果的影响,2017年的非遗名录评审较为集中地表现为对文化权利范畴下“获取与享受文化遗产的权利”的关注以及行使该权利时与习俗做法之间的冲突。这说明,非遗保护工作受到国际人权文件约束的同时本身也在促进文化权利这一基本人权的发展。
(二)相互尊重是《非遗公约》的基本原则
通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2012至2015年数次常会的决定,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相互尊重已从“要求”上升为“基本原则”,而且是《非遗公约》实施以来唯一明确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原则。最早,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在2012年“提醒缔约国注意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相互尊重要求是《非遗公约》的基础”[10],2013年再次“提醒缔约国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中相互尊重是《非遗公约》的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11],2014年又一次强调该要求基本原则的地位及其与促进对话之间的联系,[12]而后在2015年的项目评审中直接称之为“相互尊重原则”(principle of mutual respect)[13]。全球首个被除名的遗产项目比利时“阿尔斯特狂欢节”(2010年列入代表作名录)正是因为不再符合相互尊重要求以及不能促进对话而于2019年被除名,足见相互尊重原则的重要性。
在非遗名录评审中,是否符合相互尊重原则主要通过文化敏感性方法进行分析。截至目前,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曾对申报缔约国提出的要求有:应极其谨慎地对有关战争、冲突或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行表述,避免引发社区之间任何方式的误会;应慎重描述甚至应避免提及他国境内的做法和行动,以免无意中削弱了尊重或妨碍了对话;避免在申报文件中使用与《非遗公约》精神不符或可能引起社区之间任何方式的误解的表述或用语,甚至对遗产项目的名称都应给予最大的谨慎;提供口头传统类遗产项目的歌词和诗句的翻译,以获得更广泛听众的理解、超越国家和语言边界。[14]
在规则完善上,2015年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通过的12条《保护非物质文化遺产的伦理原则》(下称《伦理原则》),对有关社区的权利、政府与他们的互动行为、非遗的本质等多方面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大大丰富了相互尊重原则的内涵。而早在十五年前,促成《非遗公约》得以启动缔约工作的“全面评估《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的国际会议”(1999年,美国华盛顿)对此亦有论及。当时,中亚、亚洲、中欧和阿拉伯国家等四个区域性研讨会均提出要在新的国际规范文书中纳入伦理准则,这些准则须明确尊重传统文化和民俗及其传承人的相关原则,该项建议在华盛顿会议时被提炼为“尊重原则的伦理准则”(a code of ethics for principles of respect),会上有学者注意到对伦理准则的呼吁,指出缺乏对传承人知情同意权的关注,[15]39,272,119也有人类学教授建议,新的国际规范文书中应有保护当地社区和土著从传统知识商业利用中获益的条款。[16]143~148后来,这些对非遗相关社区的尊重和保护的强调不仅成为《非遗公约》的核心理念,而且在实施中得以规范化,例如《伦理原则》第4条即规定了传承人的自愿、事先、持续和知情同意的权利,第7条则规定了有关社区应从保护中获益的权利。
(三)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保护工作的行动目标
将国际社会主要政策目标之一的可持续发展引入《非遗公约》、尤其是认为非遗保护能直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想法,被誉为是《非遗公约》所采取的富有创造性的方法。[17]11早在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概念正式纳入国际议程的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也肯定了传统知识和经验所具有的价值,认为其中蕴含着大量对复杂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传统技能。[18]143
然而在概念提出后的近三十年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构成要素和基本要求,国际社会也一直在探索和讨论之中。由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非遗之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未能在《非遗公约》早期实施中得以凸显。如今,可持续发展概念已经从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最初涵义,演变为倾向于以人为本且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多元概念,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三要素和一系列法律原则。[19]194尤其是直接指引2015~2030年全球行动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更是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从1987年抽象的“需要”和“限制”两个方面以及经济、社会、环境三个要素扩展到2015年具体明确的17类大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几乎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健康、科技发展等方方面面,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事项范围高度重合,直接渗透、影响和引导了国家相关的战略、政策与法律的制定,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深入到新的层次。[20]369可以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命运与未来。
关于《非遗公约》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宋俊华教授将其区分为“本体性可持续发展”和“语境性可持续发展”。1鉴此,对《非遗公约》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除关注“本体性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外,还应当扩展视角紧跟国际社会的最新进展。2016年修正的《操作指南》也增设“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专章,以28个条款对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细化。在该可持续发展专章出台后,自同年起非遗名录评审即呈现出对可持续发展要求前所未有的关注,2018年列入代表作名录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可谓是重要代表。22021年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踏入行动十年(2021—2030,The Decade of Action towards the 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起始之年,这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十年。《非遗公约》各缔约国也应当采取行动,通过更好的机制落实《操作指南》可持续发展专章已经建立的框架,从而发挥非遗作为可持续发展保障的重要性。此外,联合国大会也自2015年起,在题为“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议程项目下列入“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分项,[21]反映了国际社会希望更好地巩固和释放文化的推动作用的意愿。
五、启示:重视《非遗公约》的解释问题,将其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进一步对接
尽管相较于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3年通过的《非遗公约》还很“年轻”,但它已拥有180个缔约国,代表着广泛的国家实践。在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非遗公约》已然证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采用与人权法、环境法等相兼容的互动立法模式的可行性。尤其是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在近年《非遗公约》实施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这提示我国须注意作为公约核心条款的第2条的解释问题。
任何一项国际公约的研究均离不开缔约材料、评注和国家实践。前文提到的珍妮特·布莱克教授,她于2006年独著以及2020年与Lucas Lixinski合编的两版《非遗公约》评注(A Commentary)即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在对《非遗公约》第2条解释时,2006年版评注侧重于参加谈判的缔约国代表们对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的考虑和表述选择,布莱克教授认为定稿文本使用的“要求”二字(原草案曾用“原则”)具有模糊性,留下了许多开放的解释空间,也使之更像是推广某些具有积极作用的非遗类别的目标而不是硬性要求。[22]36 2020年最新版评注则明确指出:与国际人权、相互尊重和可持续发展不符的非遗将不被公约宗旨所考虑,这一对非遗的国际考量既代表了重大利益,也是公约实施的挑战所在,毕竟许多非遗表现形式若从性别平等、保护身体完整性、尊重儿童权利和其他人权、或者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角度看均可能存在问题,这些非遗将被排除在《非遗公约》的保护范围之外。[23]52两版评注对比可知,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在公约实施中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朝着更具拘束力的方向发展。
于我国而言,以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非遗法》为中心,经过十年发展如今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非遗保护法律和政策框架。而且,非遗保护已成为我国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第十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部分专门一节规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4]
今年,针对《非遗法》实施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反思成为热点。事实上,《非遗法》中亦有保护标准的类似规定,如第三条规定“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第四条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其中提到的“优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可理解为非遗保护的中国标准。
在国家层面上,既然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是《非遗公约》国家实践的重要代表,那么进一步落实我国《非遗法》须具有国际视野,不妨将《非遗法》中的保护理念与《非遗公约》中的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进行对接。具言之:
其一,借助《非遗公约》的人权要求丰富我国《非遗法》第三条中“优秀”概念的内涵。人权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已成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引入人权因素可帮助甄别符合当代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优秀传统文化。我国自加入《非遗公约》以来一向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已在非遗保护、传承和利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不妨将这些方面的经验转化为推动人们“获取和享有文化遗产的权利”这项新发展起来的文化权利的国家实践,从而促进国际文化遗产法的发展。
其二,我国《非遗法》第四条中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要求可结合《非遗公约》相互尊重原则,从构筑和平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比如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肯定了相互尊重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25]。这说明在非遗保护中强调相互尊重原则有助于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符合我国民族政策。
其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直接规定于我国《非遗法》第四条中,可依据《非遗公约》丰富我国非遗保护中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根据公约《操作指南》(2016年版)“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专章,非遗保护将在包容性社会发展(涉及食品安全、医疗保健、优质教育、性别平等、获取清洁水资源)、包容性经济发展(涉及创收和可持续生活、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旅游业)、环境的可持续性(涉及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环境影响、基于社区的抵御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能力)以及和平与安全(涉及社会凝聚力与公平、预防和解决纠纷、恢复和平与安全、实现持久和平)等四方面发挥作用。而两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也明确将主要目标之一设为“到203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这说明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国际层面上,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规范向文化领域的渗透,继而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引。我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国,有责任参与并推动《非遗公约》相关规则的完善。实际上,早在《非遗公约》草案文本的谈判阶段,我国在肯定“公平、可持续性和文化社区之间相互尊重”(即第2条的历史谈判文本之一)的表述以外,认为该条款草案所规定的价值观仍然不够广泛,提议增加“尊重自然和非人类生命的整体性”(respect for the integrity of nature and non-human life,又译“天人合一”)的道德和价值原则。[26]不过,该修正案作为非遗保护标准未免过于抽象。对此,建议我国在细化非遗保护国际规则时,尽量做到既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兼顾世界性,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全世界不同民族、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均能理解。
六、结 语
国际文化遗产法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积极效应的肯定和认可,然而并非所有文化都是积极的,文化多样性的负面效应同樣客观存在。为了抵消这种负面效应,《非遗公约》引入国际公认的规范作为非遗保护的外部评价标准。“人权”“相互尊重”“可持续发展”,这与非遗保护本是两个轨道上独立运行的领域,如何实现二者的融合是《非遗公约》抛出的一个命题。
经过十五年的发展,三项非遗保护国际标准的内涵在《非遗公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其重要性也得到一再重申。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三个标准仍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有赖于后续实践进一步明晰。这就启发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从重申报转向重保护以后,还要注重《非遗公约》的解释问题,主动把握国际规则的解释权,将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转化为促进国际文化遗产法发展的国家实践,进而引领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我国软实力。此外,鉴于非遗保护与联合国三大支柱性议题(人权、和平与安全、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进一步落实非遗保护国际标准亦是我国在文化领域积极履行《联合国宪章》关于保护人权、促进和平与实现发展等国际义务的重要体现,能够以小见大赋予非遗保护工作更高的国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Francesco Francioni. Cultural Heritage[M/OL]//Anne Peters(ed).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2013-02-10)[2021-08-15]. https://opil.ouplaw.com/home/MPIL.
[2] UNESCO. Final Report of the UNESCO Expert meeting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iority Domains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C/OL].(2002-01-24)[2021-08-15]. https://unesdoc.unesco.org.
[3] UNESCO. Action Pla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pproved by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Round T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ing Definitions[C/OL].(2001-03-17)[2021-08-15]. https://unesdoc.unesco.org.
[4] Janet Blake. Preliminary study into the advisability of developing a standard-setting instrument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Round Table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ing Definitions[R/OL].(2001-03-14)[2021-08-16]. https://unesdoc.unesco.org.
[5] Francesco Francioni. Article 2(1): Defin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 Janet Blake and Lucas Lixinski (eds.). The 2003 UNESCO Intangible Heritage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6] 黄瑶,王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引入人权因素:缘由、功用与对话机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
[7] UNESCO. Report of the Subsidiary Body on its work in 2012 and evaluation of nominations for inscription in 2012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R/OL].(2012-12-05)[2021-08-02].https://ich.unesco.org/en/7com.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 DECISION 9.COM 9.a[EB/OL].(2014-11-28)[2021-08-02].https://ich.unesco.org/en/9com.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DECISION 11.COM 10[EB/OL].(2016-12-02)[2021-08-02].https://ich.unesco.org/en/11com.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DECISION 7.COM 11[EB/OL].(2012-12-07)[2021-08-02].https://ich.unesco.org/en/7com.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DECISION 8.COM 8[EB/OL].(2013-12-07)[2021-08-02].https://ich.unesco.org/en/8com.
[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DECISION 9.COM 10[EB/OL].(2014-11-28)[2021-08-02].https://ich.unesco.org/en/9com.
[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DECISION10.COM10.b.15[EB/OL].(2015-12-04)[2021-08-02].https://ich.unesco.org/en/15com.
[14] 黄瑶,王薇.《保護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相互尊重原则及其适用探析[J].文化遗产,2020(3).
[15] Anthony Seeger. Summary Report on the Regional Seminars ; Final Conference Report; Bradford S. Simon. Global Steps to Local Empowerment in the Next Millennium: An Assessment of UNESCOs 1989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M]//Peter Seitel(ed.).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s: a global assessment, Proceeding of the UNESCO Conference on a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1989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 Local Empower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
[16] 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 The Role of UNESCO in the Defense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M]//Peter Seitel(ed.).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s: a global assessment, Proceeding of the UNESCO Conference on a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1989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 Local Empower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
[17] Janet Blake. Introduction: The Convention, from Inception to Young Adulthood[M]// Janet Blake and Lucas Lixinski (eds.). The 2003 UNESCO Intangible Heritage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8] 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9] [荷]尼科·斯赫雷弗.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法中的演进:起源、涵义及地位[M].汪习根,黄海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0] 宋英.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之路[C]//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年刊:2018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21] 联合国大会.Resolution A/RES/70/214[EB/OL].(2015-12-22)[2021-8-10].https://undocs.org/en/A/RES/70/214.
[22] Janet Blake.Commentary on the UNESCO 2003 Conven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 Leicester: Institute of Art and Law, 2006.
[23] Francesco Francioni. Article 2(1): Defin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Janet Blake and Lucas Lixinski(eds.). The 2003 UNESCO Intangible Heritage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4]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001).
[25]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02).
[26] UNESCO. Compilation of amendments from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ing document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f Experts on the 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R/OL].(2001-01-24)[2021-08-10]. https://unesdoc.unesco.org.
THE INTERNATIONAL CRITERIA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AW:
With Comments on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aw
Wang Wei
Abstract: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aw, plus the promulgation of UNESCO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criteria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at is, human rights, mutual respec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ue to the human-center characteristic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se three international criteria respectively point to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bundant state practices of UNESCO Convention have shown that human rights have been the fundamental rule of all principles in the Convention, mutual respect has bee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action goal.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has been list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y. The year of 2021 i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Law and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ESCO Convention, and it is of obviou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o promote its further connection with the law in China.
Keywords: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aw;the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human rights;mutual respe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criteria
〔責任编辑:李 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