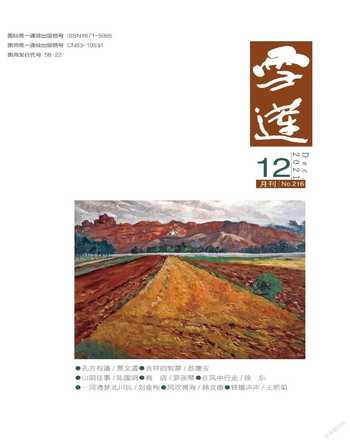如烟成河
1
记不清是什么年头的事了,好像是过年之后的几天,农历初二三四拜年的时候,老人们嘴边念叨的声音越来越稀的那种:往年啊,采买去的是老街。
老街不大,街面宽约两米,一横两竖,像个不带钩的“冂”字形。从村子出口往南,走过弯弯曲曲的田间小径,穿过一条大水塘埂,进入老街所在的村子,大约十来分钟的路。
村里,农舍,篱笆墙,菜园,鸡鸣狗吠。一样的农家小院,一样的建筑格局。顺着长长的筒子街,从西一直到村东头,绕过一棵粗壮的老槐树,向南,一条泥石路直通老街。
老街路面用大大小小的青石板铺就,其建筑与村舍有同有不同,墙面有小青砖砌筑,有土坯砌筑,有用石头垒一截墙脚。屋面清一色的青灰色小瓦。如何区别住家和铺面呢?很容易,住家的大门不管大小,都是两扇对开门。铺面则是用木板拼接,有四开的、六开的,最多是八开的。
站在北街口,向南,一条街,长200多步;向西,一条街,长300多步。但走进去,长长巷道,悠悠曲折,1000步怕也是还踩不到头。不过,那不能算街,是连街的住户。这些住户里有一个老街最高大的店——大合作社,专卖各色布匹和脸盆水瓶之类日用品。
往南,有一个南街口,东为进口,西是铺面,得走上一阵子,背心上渗点碎汗的那种。街南、北、西三面一层一层扩展开去,围成方圆两公里的村落。如果从横切平面看,老街的位置像一把扇面的轴心。
街区大大小小住了百来户人家,用于生意的铺面只有十几家。这十几家,有烟、酒、百货、杂货、典当行、餐饮、澡堂、铁匠铺、布店、裁缝店……当年的生产生活所需,麻雀虽小,可是啥都不能缺的。
也不知是谁定下的规矩,老街双日逢集。单日街上特别冷清,不管是四开,还是六开八开,最多只拆开两块拼板,用于出入。逢集日,一大清早,所有铺子门板全部拆开来。买的、卖的,来来去去,进进出出的,挨挨挤挤,喧喧闹闹。
也有不买也不卖的,只来回转一转,看一看。见到老乡邻、老面孔,打个招呼,拉拉呱,一声声亲昵着,其实也就是几次集子没见上,顶多十天半月,哪能那么热情呢?倒也想起平时,街上的人稀稀落落,但比起乡下,还是有人气得多。
除了店里的百货,周边村民也把自己地里种的,一古脑地兜了过来,什么米、黄豆、绿豆、花生呀,家里养的鸡鸭鹅,积攒的鸡鸭鹅蛋拿去卖,换些盐、酱油、煤油、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品。好在是自家产的,价钱也不贵,碰到故交旧友,甚至拱手相送,全没有那种讨讨争争的场面。偶尔弄个半红脸,也一定是双方推来推去的谦让。来买农产品的大都是没有地的公家人,像供销社、医院、粮站这些国营集体单位,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熟了以后,有的自然成了老主顾。
常常有卖不出去的,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家。有时,碰到“收货”的贩子,就像偶尔得了一颗糖一样幸运了。老街人叫收货的为“贩子”,收米的叫“米贩子”,收雞的叫“鸡贩子”。“贩子”从老街便宜买去,再去十里以外的大集市卖,小本生意赚取差价。来了哪种“贩子”,哪样农产品必成了紧俏品。收的时候也看“货”成色。好在,老街上的人心眼实诚,拿到街上卖的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不好的都留着自己家里吃。
即使是这样,因为街小,那些“贩子”一个月只来一趟两趟。时间长了,倒让这些乡民心里挺惦记的。
2
晨光起,天色亮,一踏入街北巷口,就有袅袅的油香绕鼻。
街北,左边第一家是住户,第二家是油条店,是老街唯一一家早点兼饭店。店很简陋,却使每一个去老街的人流连忘返。
店里炸油条,也蒸馒头,但只有油条卖得特好,一斤面粉十来根油条,逢集日,十斤面粉很轻松地就卖出去了,馒头却很少有人问津。农家面粉,枯枝柴火,自家地里长的,哪能不香?想吃馒头,从油条店里要块“面头”自己在家也能蒸出香软蓬松的馒头。
至于饭店,有时,一个月来个三两回外地人,也只粗茶淡饭,图个肚子饱。来客多是街上人家亲戚,主人图面子,才到饭店。店里灶火“呼呼”生风,店师傅炒几个家常菜,主人和客人你来我往,喝上半天酒。即使这样,能请客人到店里的,都会听见路人稍不注意闹出的咂咂声响,弄不好成了村口一连多少日子的炫耀。到了自家来了客人,好歹也拼个脸面,请客人去饭店嘬上一顿,出来时红光满面,豪声大气的嚷,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油条店有两间铺面,一间整面墙的门,一间半截墙的窗。天才刚露一点亮色,门就“吱吱呀呀”开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身着白大褂,虽然油污斑驳,却洗得干干净净的。他不急不忙地拆门板,一块一块,搬到后院,再拆窗户板。
人们往老街聚集而来,走过的,路过的,探头向店里张望。迎窗口一口大油锅,油锅后面一块两张大桌面大的案板,一个膀阔腰圆的老师傅很投入地忙碌。他个头不过一米七,肚子跟箩筐一般粗,胸前一块肚兜样的大围裙撑得老高,胳膊又粗又短,手背如发酵过的大馍。
大人们说,他是让油给熏的。
老师傅和小伙子是一对父子,但从他俩身材和面貌上看,很难扯到一起去。
揉面、扑面、搓面、拍面、切面……油锅里沸腾的油等不及了,鱼眼一样冒着热气,老师傅从案板上抓起一根切好的面条,又捏起一根,两条相叠,一条小木条轻轻一按,拎起轻巧地一扭,转身扔进油锅里。一整套动作,老道熟练,连贯有序,且一招一式干净利落。
一根扭扭面下锅,另一根已经操在手中了。就这样,扔了十根,老师傅停下手。油锅里翻滚着,伴着“滋滋滋”声,扭扭面从油里慢慢浮了上来,一点点膨胀,扭曲的身体涨大了足足有五倍,仿佛在油里扎了一个猛子,再一现身就长胖了,染上灿灿的黄,变成一根大油条。
老师傅站在油锅前,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眼皮忽上忽下。一会儿,瞅一眼油锅里的油条,一会儿,瞟一眼街上的来人,搭上一两句俏皮话。
炸油条的香味飘得很远,很远……到街上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走到窗口前,脚步好像都重了。大人们算是有自制的,一步一步,如蹚水;孩子们脚底下像抹了强力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就如镶进那胖胖的油条上似的,嘴里不住地咽口水,任大人怎么拉,就是挪不动步。
油条店中央有两张大桌,是农家里最普通的大桌,四方摆着长板凳。去店里吃油条的都是工夫闲的人。他们上街,基本不买也不卖,专为吃油条。一来就钻进店里,坐在大桌边,跷起二郎腿。店小伙送来两根油条,再拎起大茶壶,倒一盏茶,双手递过去,放在来者面前。来者不紧不慢,吃油条品茶,边看着街上来往的人。
茶是大碗茶,油条是最正宗的老手艺,人是老面孔,话不过是家长里短,春种秋收,天气寒凉炎热。
如烟的话儿,散在空中,又落下来,淌成了一地的河,流淌在老街,似乎从来没有潮湿过一回似的。
有时,母亲也会买油条,但她从来不舍得吃,而是放进篮子里,用毛巾严严地盖着,带回家里给我们吃。
那时,家里大人上街回家,孩子们老远就迎上去,掏一掏荷包,翻一翻篮子,如果能得到糖或者油条,心里美滋滋的,好几天里碰到了树桩,都想着得瑟几句。
3
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趟老街,置买日常用品。
前一晚上,母亲从房间里搬出一个瓷花坛,里面装着平时积攒的鸡蛋。母亲一个一个拿出来,再一个一个很小心地码在竹篮子里。母亲每做这些活时,我都待在旁边,嘴巴咂巴咂帮着数数,手忙不跌地帮着比较大小。我知道,母亲第二天要上街。
时间长了,我发现,母亲每次码的时候都很有技巧,她先把大一点的鸡蛋挑出来,小一些的放篮子底下,挑出来的大的放篮子上面,再盖一条干净的毛巾。母亲忙完了,我就跟在母亲后面,央求带我一道去。农忙时,母亲一口回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农闲时,母亲满口答应,并嘱咐我早点睡觉。
朝阳初升,田埂上,露珠在草尖上碎钻一般闪着灼目的光。脚踩上去,露珠滑落,湿了鞋,湿了裤管。到了街上,湿鞋踏着青石板,能清晰地听到“啪嗒啪嗒”的声响。
母亲随着熙攘的人群,走走停停,我跟在母亲后面,停停走走,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瞅瞅这个,摸摸那个。我特别喜欢看灰瓦青砖店铺里那一扇扇窗格。窗格的油漆斑驳暗淡,但窗格里透着的花纸却多彩艳丽。
百货商店生意是最好的。即使是诱人的油条店,也只是清早那一会儿,八点多后,街上人空了,油条店也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只有师徒两人。
百货商店与油条店斜对门,在街口转角处,门对油条店窗子。商店两间铺面,里面没划没分,却自然形成两个区域。靠门一边,一顺溜摆放着三口大缸。一缸酱油,一缸盐,一缸白酒。买酱油和酒,都是自带空瓶。那时,最精贵的是医院打吊水的瓶,售货员拿起缸边的漏斗,插入瓶口,再拿起特制的提子,扎进缸里,慢慢提上来,对准瓶口上的漏斗,提口微微一倾,倒入瓶内。售货员心里有杆秤,什么样的瓶装到哪儿,一秤,八九不离十。
秤盐简单些,商店里有手工糊的纸包,三面封口,盐装进去,敞口那面两角一折,再往折縫里一塞就收了口。店后门那里,有一只大桶,里面装着煤油,虽然家家都装了电灯,但每家都备些煤油,预防着停电时用。
另一边,一排一米多高的柜台,透过柜台玻璃可以看到各种商品:有作业本、铅笔、橡皮等学生用品,有针头线脑之类的生活品。但吸引我们孩子们的是两分钱一块的硬糖,寸把长,深褐色,我们叫它“狗屎糖”,名字不雅,却特别甜,得到一颗,慢慢地吮,小半天时间,嘴到心里满满的都是甜。
踏进百货商店,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酒香味儿。喜欢喝酒的人,闻一闻就醉了。老街歪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时,别人打牌聊天,他去商店。磨磨蹭蹭老半天,就为讨那一口酒香。对于不会饮酒的我,特别讨厌那味儿。母亲在商店里打酱油买盐,我捂着鼻子站在商店门槛外,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对面的油条店。如果母亲买了糖,叫一声,来吃糖。我便一个闪跳,跑进店里,那时,什么讨厌的味儿都闻不到了。
售货的男人年近四十岁,每次母亲买了糖,他都拿着装糖的纸包,在高我头顶的空中,唬着脸,引逗道,不给,不给,糖是我家的。我伸出手,边叫着,给我,给我,边跳着脚去抓。他呢,不急不躁,糖包就在我头顶盘旋,我高,他高,我低,他低,就是抓不到。母亲见了,解围道,叫伯伯好,快叫伯伯好。我才不叫呢,母亲明明已经花了钱,还说糖是他家的,真是个坏人。
上小学时,发现他是我同桌的父亲。我们学校和老街所在村子只隔着一条机耕路,每次去商店买学习用品,同桌都陪着我一起去。他父亲也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有时,还拿糖给我和同桌吃,真是羡慕极了。如果我家也有这样的商店多好啊,那样,每天都有糖吃了。
后来,听同桌说,商店是公家的,他父亲只是拿工资的大集体工人,他们家里吃的酱油盐都要花钱买。
4
北街口向西,走过十来家住户,是布店和日用品店。那时,人们喊顺口了,叫什么来着?哦,“大合作社”。
大合作社坐北朝南,高大,气派,跳眼。屋顶两边有飞檐高高翘起,犹如两只飞燕轻盈展翅。迎街和其他店铺一样,一式的木板拼接,是墙,也当门。不过,因为铺面宽,自然显出不一样的气势。大合作社东西与住户相接,南北与住户相对。对于不熟悉老街的人来说,它有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余韵。
本地老一辈都知道,大合作社以前是本地大地主李家的,解放后充公。早先用于人民公社办公场所。后来,公社选址街北另建,这里改做了布店和日用品店。
店里豪华大气,带有几分古色古香。从东到西相当于农家五间屋的开间,迎面立着两个醒目的大红色柱子,粗壮,敦实,一个大人环抱不过来。墙面间隔镶着镂空雕花物件。店里从西往东,五分之四一排木板柜台,一米多高。柜台里,靠墙一排货架上,扎着一卷一卷的布,花花绿绿,密密匝匝,鲜艳多彩,惹亮每一个去店里人的眼。
卖布的人不固定,换来换去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子,杨柳细腰,一副弱不禁风的小女儿态,穿着打扮时尚潮流,是老街的一道风景线。来人了,口吻有点儿怯生生的,指定了一种花色,卖布的抱起一卷布,只听得柜台上“哐咚”一响。然后,那女子高高地站在柜台后面,一手扯布,一手翻动布卷,放布。
柜台上蓬松着一堆布,软软绵绵的,散发着清新的香气。女子一手拎着布角,一手拿着直尺,从布角顺着布边量,一尺,两尺,三尺……大人一件衣服六尺,小孩子三尺五尺……不等。量好了,布对折,边对齐,一只手紧紧捏住,一只手拿起剪刀在布上剪一个小口。然后,两只手各捏住一边,向两边一使劲,只听得“滋——”的一声脆响,像是谁吊起了嗓子,布的裂口像安了滑轮往前滑溜。两手交替往前,捏到裂口处,再向两边使劲……那姿势,怎么看都有些像《红楼梦》里的晴雯撕扇,既俏皮又俏美。
那些年轻女子还有一个技能,就是算盘打得特别娴熟。算账时,微低着头,嘴里轻轻念着,随着手在算盘上一阵“啪啦啪啦”響,一笔账就算出来了。不过,从春天到夏天,布店里生意都显得冷清。只有到了秋后,庄户人家卖了地里收的,家里养的鸡鸭猪羊,手头有了钱,布店才红火起来。
布店东边有一个区间,一间玻璃柜台,里面摆着碗、碟、盘子、茶缸、毛巾、手帕、脸盆之类。柜台后面坐着一位男售货员,四十多岁,很清闲,也很少说话,手里常常捧一本厚厚的旧书,好似很认真地读。
母亲很少光顾那边,不是家里不需要,而是碗、碟、茶缸、脸盆这些用品,一用好几年,连一条毛巾、一块小手帕,有时都要用上一两年。烂了,补一块补丁,直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换新的。因此,虽然摆设上也是花花绿绿的,但相对于卖布这边,要冷清很多。
乡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娶媳妇、嫁女儿这些大事,一般定在秋后,手头活儿闲了,新婚的被子、床单、衣服,水瓶、脸盆,摆宴席碗碟、茶缸,采办的采办,添置的添置,对于布店和日用品店,都是一笔大收入。
岁末年关,喜气氤氲老街,平常人家也要奢侈一次。有条件的,大人到小孩,大到棉衣、外套,小到内衣、短裤,都重新添置一新。
大年三十,里里外外换一套新衣。喜庆的气息,便如一阵春风,吹暖每一个角落。
5
裁缝店在老街南,坐南朝北,夹在一排农家屋里。
门面不作标记,不挂牌,但和老街里的其他店一样,迎街是木板拼接。
师傅姓张,大家都叫他张裁缝。平时,有人想去裁缝店做衣服,直接说,去张裁缝那里做。张裁缝既是师傅称号,又是店名。
进店,一切陈设都是农家式的。厨房、卧室、堂屋。厨房烧饭,卧室睡觉,堂屋东,板凳围着大桌,东山墙上挂一幅中堂画。中堂也是年年换,今天挂年年有余,明年挂富贵牡丹,后年挂松鹤延年。不同的是,堂屋显眼位置,一张裁衣服的大案板占据了小半间屋。案板后面,一台有些年月的缝纫机,一架摆放布的货架,一条挂着花花绿绿衣服的铁丝。
父亲说,张裁缝跟我家沾上亲,算起来,长我两个辈分,但印象里,我家难得去做一回衣服。
那时,乡间有上门做衣服的裁缝师傅。一般人家请裁缝师傅到家里做衣服,也是当时风俗。一天管三餐,工钱两块。手艺好的师傅有人赶着去学徒,师傅不带多,一般带一个,最多带两个。用师傅的话说,收了人家为徒,要让人家有饭吃,也就是有活做。
平日里,裁缝师傅跟乡里人一样,耕犁打耙,播粮撒种。一到冬闲,就被人家请了去。我们村子请的是邻村王师傅,村里人都看得上他的手艺活。
一早,王师傅带徒弟到了请他的人家。师傅站大桌边,量尺寸、裁剪布料,徒弟坐缝纫机前,踩动脚踏板,埋头做衣服。
王师傅到哪家做活,哪家像办大事。起上大早到老街,买菜、买肉、买烟、买酒、买早点。中午,还要邀请四邻,或亲朋好友作陪。
一天做下来,摸点黑,褂子、裤子、内衣、短裤,大大小小能做十四五件衣服。一般人家也就一天的活,人多的,也有做两三天的,一年的衣服都有了。
张裁缝店里做衣服无需这样的排场。扯一块布料到店里,现场量尺寸。一件衣服根据大小款式,工钱三毛、五毛、八毛、一块不等,谈好工钱,也不用提前付,到约定时间,衣服做好了,上身试穿,合适,付钱,拿衣服走人。
裁缝做的衣服,多半宽松肥大。孩子们穿上,一个个嘟着嘴,嫌难看。大人们却喜笑颜开,直夸师傅做得好。因为这样,可以多穿些时日。偶而也有撒泼的女孩子,隔壁家的晓花,做了一件春秋衫,晓花穿在身上,又肥又大,像戏台上跑龙套的,她甩了甩衣袖,顺势往地上一倒,打滚哭闹,说什么也不要。弄得张裁缝很没趣。晓花妈妈真有办法,去油条店,买来一根热气腾腾的油条。晓花一见,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鼻涕眼泪没有擦,捧着油条,喜滋滋地走了。
张裁缝家祖传做衣服,自他爷爷时,就在老街开裁缝店。早些年裁缝店叫裁缝铺,张裁缝十四岁跟着父亲学裁缝。说到他的手艺功夫,用他自己的话说,衣服穿上身,就像站在身上一样,缝有缝,角有角,无形中人也显得精灵灵的。
我第一次去裁缝店是准备上学那一年夏天。事儿不大,却特别隆重,父亲和母亲一起带我去布店,扯了四尺白底大红花哔叽。其时,我只有八岁,人也瘦小,根本用不了四尺布。母亲说,做大一点,一来,长得快,二来,冬天可以做棉袄罩褂。
去裁缝店。张裁缝边给我量尺寸,边满面春风跟父亲聊着新闻趣事,母亲则拉着我配合张裁缝量尺寸,嘴里不住地提醒,做大点,孩子长得快。张裁缝一手尺头,另一手很随意地滑过皮尺,接着,轻轻一掐,手腕轻巧地一翻转,眼光直扫过去,尺寸就记在心里了。不时地,嘴里回应母亲,是啊,孩子就像地里的大白菜,一场雨冒一截,不过,也不能做太大了,太大了就没形了。
肩膀、衣袖、衣长、衣围,一一量好了,张裁缝转身到案板前,拿过一本翻卷的小本子,记上尺寸,就等着拿衣服了。
因为沾亲带故,我家的衣服做得快,工钱也便宜些。三毛、五毛的,收两毛五、四毛五,八毛、一块的,收七毛、九毛。少个五分一毛,母亲总会记着,下次去老街,顺便带一些新鲜蔬菜送给张裁缝,算是还了一份情。
【作者简介】杨丽琴,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短篇小说》《作家天地》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