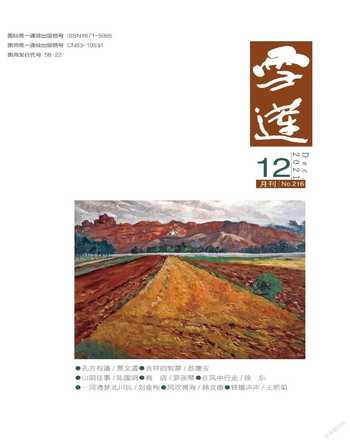吉祥的牧草
一
直到现在,父亲都没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失踪的那个傍晚,暴风雪来得毫无征兆。先是一片两片,而后洒洒落落,最后纷纷扬扬,暴躁地肆虐起来。隔着玻璃窗,雪在暮色中拥抱着寒风一起旋转飞舞,颜色极为苍白,显得特别不真实。
这时,母亲已把刚出笼的馒头端上炕桌,馒头冒着热气,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麦香。端上炕桌的还有一盆洋芋丝,那是母亲的拿手好菜,香气诱惑着我,肚子里的饥饿感又增加了几分。可是父亲没上桌,谁都不能动筷子。母亲严厉的目光一遍遍扫视着我手中的筷子,我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急切地等候父亲出现,他出门时说,要下雪了,先去马厩草场转转。两个多小时了,没见回转。
母亲焦灼地站在木门玻璃窗前向外张望,屋外除了怒吼的狂风翻卷着雪花,什么都看不到。暮色一寸一寸暗下来,屋内的灯光将黑夜紧紧贴在玻璃窗上,父亲依旧迟迟不见踪影。
母亲的眉头拧成一道绳,灯光下长久的等待,仿佛令她苍老了许多,额头突显的皱纹为那种苍老增加了一种哀怨。终于,她有些忍不住了,翻出手电筒,抓起炕上的一件棉袄,说要去寻找父亲。我跳下炕沿,扯住她的衣角。我怕一旦母亲开门,屋外的风雪会裹挟着所有的恐惧冲进家门。母亲用眼角扫视了一下我脸上的哀求,最终无奈地长叹一声,又把衣服重新扔回炕上。我知道母亲妥协了,赶紧回到炕桌边,眼巴巴地盯着桌子上的馒头和洋芋丝。
母亲拿来海碗,拨了半碗洋芋丝,将两个馒头压在菜上,重新放进锅里蒸篦上。炉里余火犹在,她铲了一铲羊粪,火的温度透过铁皮炉向外蔓延。看了看跳跃的炉火,母亲轻轻朝我说了一声,吃吧。这时候,我才发现,失去温度的馒头和洋芋丝已经没有了香味,色泽依旧却不再诱人。母亲一直没动筷子,她拿起针线箩里的鞋底,孤单地坐在窗边的土炕上,一边纳着鞋底,一边不安地朝外张望,任凭一窗之隔的黑夜和雪花在她眼前张牙舞爪。
父亲值守马厩草场已有二十多天。副业队队长照顾父亲,起初给他排的并不是夜班。父亲值了几天班后,却主动提出要值后半夜的班。队长很恼火,责怪父亲不识好歹,既然喜欢后半夜,那就一直都上后半夜的班,并且以后也不准调换。队长的这一决定,似乎更合父亲心意。每天傍晚,吃了晚饭,父亲会先出去转转,而后回来,眯上一觉,午夜闹钟响起时,揣上母亲热在锅里的馒头或鸡蛋,悄悄出门去马厩值夜班。天放亮,再早早回来,美美睡上一觉。每个夜晚,母亲手里总有做不完的活,不是缝补就是纳鞋底,直到目送父亲出门后才上炕躺下。
这个暴风雪的傍晚,父亲出去后,直到天亮都没回来。
副业队是农场场部下属一个小队,承担着农场近万人口的生活用品的生产加工。比如说,吃的方面有面粉车间、豆腐车间、红糖车间、榨油车间、酱油醋车间、蛋糕车间、烧酒车间;穿盖方面有裁缝车间、棉胎车间……大小车间生产的产品,除了直接運往场部各个商店出售,同时还运送到三十多里外县城的大小商店里销售。
父亲不是饲养员,他在副业队干的活跟马厩草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从棉胎车间被派去看守马厩草场,副业队很多职工都认为,是因为两斤棉花得罪了队长。
副业队队长是山东人,从部队转业到农场场部,后来到副业队担任队长,人高马大,性格直爽,嗓门尤其响亮。离开部队的队长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和习惯,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在家属院前面的黄土路上跑步,脚步踩在路上铿锵有力,蹬、蹬、蹬地能把整个家属院都震醒。每到这个时候,很多职工家的烟囱里也升起了青烟。在大家看来,队长就是报时的钟表,只要他的脚步声响起,家属院就必须要醒来,因为孩子们要上学,男人们要上班……也有人在私底下议论,这队长管得真宽,把副业队的车间管好就成了,干嘛还要把家属院也管起来。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想不通,平日里严以律己,作风过硬的队长,竟然也有犯浑的时候。一天下午,队长路过棉胎车间,见只有父亲一人,就顺手抓了一把棉花,约莫有两斤,说是给老婆做“鸡窝”(冬天穿的棉鞋)用。父亲当即上前制止,说,这是公家的棉花,动不得。队长咧开大嘴嘿嘿一笑,说,两斤破棉花算个啥,你每天弹棉花,飞散的棉絮都不止两斤。父亲说,这是两码事。队长又像是讨好父亲似的说,别这么认真,老苏,我还是你孩子的舅舅呢,看在这个份上,你就别犟板筋了好吗?父亲不肯“私了”,依旧牢牢抓住两斤棉花不放手。两个大男人,一来二去,善意的玩笑最终变成口角,引来其他车间的职工围观。那个下午,队长的面子就这样被父亲无情地扫在地上,他心里特不爽,把棉花狠狠砸在地上,头一扭就走了,脚步声比以往重了很多。
父亲在饭桌上提起此事,母亲心里有些担忧。母亲责备父亲,得罪谁都不能得罪队长,好歹还是干亲戚,两斤棉花有什么可惜,再说了,无论怎样,你也不好当人面让队长下不了台,当兵人脾气犟,你惹他做啥?
父亲振振有词地反驳,那是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拿呢?你看我弹棉花这么多年了,有拿过一两回家吗?
父亲说的是事实。母亲瞪了父亲一眼,毫不客气地回应父亲,就你正经,就你清高,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不就两斤棉花吗,犯得上得罪人吗?
母亲的担忧很快灵验了,没两天,下了通知,派父亲看守马厩草场,说是轮班半个月,可父亲在那里一直待了二十多天,也没接到让他重回车间弹棉花的指令。
副业队马厩里只有十匹马,平时用于驾辕送货。为统一管理,入冬后,这些马都转场到了场部畜牧队。相比副业队,场部地处河谷地带,地势低,冬天暖和。整个秋天,与副业队毗邻的农业队千亩麦地里的麦秸全都运送到副业队马厩草场,为了防止火灾和盗窃,副业队专门挑选各个车间的职工轮流看管马厩草场。副业队的马厩草场,用母亲的话来说,那可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场部马厩根本就用不上副业队的麦秸,因为场部的马厩储藏的青饲料足够 200匹马吃上两三年。也正如此,每年一到开春,小草冒出地面,副业队马厩草场上堆积一冬的麦秸,全都被拉到河滩里烧成灰烬。再好的草料,马不吃,就是废料。这个时候再用于烧炕取暖,早就过了季节,若不烧掉,反而占了太多的场地。但是宁可烧掉,队长从来都不允许家属院的职工们擅自带一根回家。
每年烧麦秸的日子,母亲后半夜早早起来发面揉面。吃了早饭,带上面盆和一块塑料布,再带上清油和姜黄,来到河滩,找个平坦的地方,把塑料布铺好,揉好面团,在面团上抹上香油,撒上姜黄,七拧八扭成一团,塞进锟锅里,盖好盖子,选一处正燃烧的麦草堆,扒出一堆过火的灰烬,将锟锅埋进灰堆。半个小时后扒开灰堆,拉出锅来,掀开盖子,面团已经在锅里开成了花,那香味飘满了整个河滩。一次,队长恰巧路过河滩,被母亲做的锟锅馍的香气所吸引。母亲很客气地掰了一块,让他尝一下。末了,见队长喜欢,母亲又塞了四个给队长,让他带给家属和孩子吃。队长性格直爽,吃了锟锅馍,过意不去,当场就表示,他姓李,母亲也姓李,干脆认了母亲当干妹子。队长开玩笑说,这样,以后吃锟锅馍就不成问题了。
母亲笑笑,不置可否,队长就这样成了我的舅舅。
看守马厩草场是个苦差事,白天一班,晚上一班。尤其是后半夜,不能睡觉,要定时巡查麦草垛。母亲开导父亲,去找队长,说几句好话,就可以早点回车间。父亲心里却惦记队长的气,死要面子地反问母亲,苦啥,不就看一堆草么,又不累,找他干吗?我又不靠他养活,他算什么,不过就是个队长,牛逼个啥。
后来,母亲偷偷去了一趟队长家。回来后,我问情况如何。母亲摆摆手,叫我别多嘴。
二
队长是一大早赶到家里找父亲的,他说马厩草场的麦草垛像有人偷过,他想找父亲问一问原因。队长还说,上半夜看草场的人说,交班时,没见着父亲的影子。在此之前,队长还听其他值守人员汇报,自从父亲开始后半夜值守后,人经常溜得没影。好几次,上一班的人把钥匙落在了马厩工棚里,返回去拿,都没见着父亲,围着草场转了一圈,也没瞅见半个人影。
队长担忧地对母亲说,妹子,他老是这样,我觉得你该查查了,人学好难,变坏易。万一出了问题,我这个当哥的就对不住你了。队长的话,让我们感到吃惊,父亲头天傍晚从家里出走后,如果没去马厩草场,他能去哪里呢?

母亲心里有些发慌。之前,她以为父亲还在马厩里睡懒觉,起来得迟。她还以为父亲一大早又去草场转了一圈,正在回家的路上。队长撵到家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母亲当机立断,二话不说,扯上我撵到马厩,父亲果然没在里面,他睡过的炕头,被子乱成一团,还扔着一条女人围的绿色头巾。母亲捡起围巾,看了又看,扯了又扯,好像要从里面扯出什么秘密。果不其然,母亲从头巾上发现了一根细长的头发,她小心翼翼地捻起那根头发,看了又看,扯了又扯,好像还想从上面发现更多的线索。令母亲失望的是,头发只是头发,哪里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母亲的眼泪开始如同断线的珠子,她把围巾狠狠甩在地上,朝上跺了几脚,头一扭,一路小跑回了家。
我连忙捡起头巾,跟在后面追赶。赶回家,母亲已经收拾好了一个包裹,似要出门。
我去找你父亲,你哪都不许去。你也十三四岁了,也不小了,千万不要学他的样子,老老实实把家看好。母亲说,箱子里有馍,热热就能吃。母亲就是母亲,即便是外出,还依然惦记着我。此刻她已经铁心离家,根本不理会我的阻拦和追问。母亲说走就走,出了家门,踩着尺把厚的积雪,头都没回一下。
出去找人,有必要带包袱?我揣测母亲这次出门后,会不会回来。父亲彻夜不归,一定伤了她的心。其实,母亲性情一直都很温和,从来没和脾气倔强的父亲发生过口角,也从没干涉过父亲的工作。即便是父亲从车间里被撵到马厩里,母亲也从未有过一句抱怨。她甚至还将自家的被子拆开,从棉胎里掏了两斤多棉花,洗干净,用手一点点扯得蓬蓬松松,新鲜的如天上的白云。瞅了个时间,连同给队长全家人纳好的布鞋一起送了过去。她说队长五十岁,要过生日了,做妹子的应该送份礼物,同时也顺便弥补下父亲的过失。母亲说,打人不打脸,父亲当时的做法的确不对,她想叫队长把父亲重新派回弹棉车间。母亲觉得父亲不该去看守草场。那种苦活是没技术的人做的。怎么能叫一个二十多年的技术工去守草场?家属院的人都在讨论,说父亲是二百五,实在没必要为两斤棉花和隊长较劲。父亲在别人眼里成了笑料,作为妻子,母亲觉得有义务去维护丈夫的尊严。
母亲出门一整天,我把眼睛望酸了都没看见她回来。风还在呼啸,雪还在飘洒,没了父母的屋子如同冰窖,我蜷缩在炕上,即便裹着厚厚的被子,土炕的温暖在一点点退去。
失踪了一天的父亲是接近午饭时到家的。他似乎是跋山涉水,从遥远的地方归来,大衣前后沾满泥水,一双大头皮鞋也沾满了泥水。一夜不见,父亲显得无比憔悴,第一眼看上去,甚至令我怀疑:这个进入家门疲惫不堪的男子真的是父亲吗?
父亲进门一屁股落到炕边就嚷嚷,我饿了,有吃的吗?我从面箱里取了一个冻得硬邦邦的馒头。他啃了一口,反问,这么硬,是石头吗?我赌气没回应。
父亲又问,你妈呢?我说,走了。
父亲嗖地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叫道,她上哪了?她怎么能走呢?我的正事还要她帮忙呢!听父亲的口气,好像母亲擅自离开家门非常不应该。
我想了想,就把从马厩带回来的那条绿色头巾狠狠扔在父亲眼前,你问问这个吧,它应该会告诉你的。谁知,看到头巾,父亲竟然开怀大笑起来,如同中了邪。
我说,你还笑?还不赶紧去找我妈?
父亲胸有成竹似地大手一挥,摇摇头,不急,先办正事。
三
父亲一定很后悔,他的错误决定导致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仅仅露出一点苗头,就被父亲掩藏起来,包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那天晚上,因为母亲离家出走,父亲放心不下我,就把我带到马厩。看看闹钟已是凌晨两点,他说,你自个睡,我去草场转转。我不肯,坚持要跟他去巡查。他考虑了半天,才勉强同意。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踩着没膝的积雪,绕着草场巡查。
雪夜里的草场,草垛上覆盖着积雪,如同一个个白色巨人矗立在雪地上,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风夹着雪,紧一下慢一下地刮着,落到人脸上如同刀割。可是转到一半,父亲“哎哟”一声,说忘带了一样东西,要回去拿,叫我一起走。我觉得这是父亲的计谋,目的是想把我哄回马厩,他一定有什么想隐瞒我。我硬是不肯,父亲只好无奈地转身,三下两下拨开身边麦草垛上的积雪,从边上掏出一人高的草窝,把我推进去,叫我安稳地待在草窝里,他回马厩拿了东西就来。父亲还煞有介事地叮嘱我,假如晚上看到了什么,天亮之后都必须得忘掉。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以为这个午夜,会发生我从来都没见过的场景,比如说鬼怪,或许它们将在这个雪夜里进行厮杀。失踪了一天的父亲一定是从别的地方带回这个消息的,他拒绝带我出来,无非是不想让我亲历这一恐怖的场景,那一刻,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既欢喜又惶恐。
父亲走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并没看见自己设想的那些场景。倒是听到几米之外的麦草垛边,传来粗重的喘息声。我以为在做梦,狠狠掐了一下大腿,证实声音并非虚幻,赶紧侧耳聆听,确定是人的喘息声。我悄悄从草堆里探出头去,果然发现前方的麦草垛边,有两个人影在蠕动,他们好像是在抽麦草。堆积了几个月的麦草垛很实沉,上下麦草紧紧积压在一起,每抽一束都很费力,以致他们喘着大气。当时,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勇气,驱使我猛地跳出去,用手电筒的光罩住两个人影。
我看见,草垛前竟然是一个老阿妈和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少年,他们身后放着两个大背篓,正伸手到覆盖着积雪的麦草垛上,一点点抽着麦草。不幸的是,他们刚开始,就被我逮个正着。
我异常兴奋,想冲上去抓住两个背篓,少年却惊慌地迎上来,拔出一把匕首,挡住了我的脚步,匕首在雪色下闪着寒光。老阿妈一把抓住少年的手,压低声音,急促地喊着我听不懂的话,像是在阻止少年的行为。匕首的寒意令我后退了一步,可我的内心并没有放弃,我用目光狠狠地盯住少年,在我看来,阻止他们本身就是一次正义的行动。
就这样,我和少年一直对峙,直到父亲出现,紧张的场面才有所缓和。父亲一把将我拉到身后,不顾我是否摔到在雪地上,竟然示意两个人继续装草。老阿妈看看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父亲忙说,别怕,他是我的儿子,没事的,没事的。说完,要拉我一起上前帮忙,我狠狠甩开了父亲的手。
那个午夜,父亲竟然在我愤懑的注视中,热情地帮助两个人装草,很快就把背篓装得小山一样高。临走时,老阿妈犹豫片刻,还是走近我,慈祥地拉起我的双手,用生硬的普通话说,孩子,谢谢你的阿爸,昨天夜里,我出来找牧草,冻昏在雪地里,是你的阿爸救了我。这次我们转场,突然遇到雪灾,牲畜缺少牧草,多亏你阿爸帮了我们的忙,我们要谢谢你,菩萨会保佑你们的。
见我气呼呼地不理会,老阿妈尴尬地笑笑,拉着少年,向父亲和我鞠了躬,这才背起背篓,艰难地在雪野上迈开步伐。父亲似乎想到了什么,赶紧追上去,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条绿色的围巾,围在老阿妈的头上。
我突然想起,母亲面对那条绿色围巾时的情形。
队长说草场有人偷草,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竟然会是同伙!
四
我坚持认为,母亲的离家与父亲彻夜不归有关。父亲为了办正事,愁得焦头烂额。但我认为找回母亲,比他的正事还重要。我威胁父亲,不找回母亲,我就去找舅舅,说出偷草的事情。我告诉父亲,舅舅已经发现有人在动麦草的手脚,只是没抓到把柄。如果我能提供线索,他肯定求之不得。
不知父亲是听了我的威胁心生胆怯,还是真想找回母亲,最终接受我的建议。次日一大早,还没等我起来,父亲就换上崭新的蓝色中山装,隔着窗户玻璃,朝我挥手,出了门。他这套衣服是母亲亲手做的,只在过年或回外婆家时才会穿。有了这套行头,父亲看上去精干多了,我怎么也想不通,队长为什么要把他派去看草场呢。外婆家在县城,距副业队三十多里,父亲能不能在外婆家找到母亲呢?如果能,如此寒冷的天,穿得如此单薄,踩着厚厚的雪,要跋涉三十多里路,我突然觉得父亲好可怜,我的威逼实在难为父亲了。内心自责的我赶紧从床头拉过一件大衣,跳下炕追出家门,想递给父亲,他却早已消失在家属院黄土路的那端。
父亲中午时分就回来了。他不像是去了外婆家,以往去外婆家回来时,父母手里总会提些外婆做的甜醅、酸奶或其它点心。这次,父亲却两手空空。我堅信,父亲一定没去外婆家找母亲。我朝父亲身后张望,期望母亲是被他缩小了,装在口袋里带回来的,在我不经意的刹那,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给我一个惊喜。可这个中午,父亲不是魔术师,他最终没能实现我的期盼。
我问,我妈呢?
父亲说,找了,没找到。你外婆家也去了,说你妈没回娘家。你外婆连家门都没给我进,说队里派我看马厩草场应该是犯了不小的错误,外婆家的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都在议论这事,忒丢人了。你瞧瞧,这是哪门子的事啊,我看草场,跟那些街坊邻居有什么关系?
父亲有些生气,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似乎又想到什么,转手把烟头掐灭,扔出很远,摆摆手说,算了,找不到就不找了,办了正事,再去找。父亲如此对待寻找母亲的事,就好像母亲是他的佣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有些不高兴,把坚硬的馒头丢进锅里热,馒头落在蒸篦上,发出啪啪响声。
父亲坐在炕桌边,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见我有些生气,表情无奈地说,别急,等正事办完,一定再去找你妈。
父亲写完几页纸,认真地折叠好,塞进中山装的口袋里,兴冲冲去了一趟队长家。
回来时,却耷拉着脑袋,蔫巴巴地直接上了炕,衣服也没脱就躺下了,好像突然生了大病似的。我猜想队长舅舅肯定没给他好脸色。
我把热好的馍馍端上炕桌,又泡了缸茶,喊父亲起来吃饭。父亲欠起身子,睁眼瞅瞅炕桌上的馍馍,又重新躺下。
我说,你别嫌弃,找不到我妈,只能是这样的伙食。
父亲叹息一声,我不是嫌这个,我是发愁,正事可能会泡汤了。
你到底想帮谁的忙啊?我不高兴地问,你连自己的忙都帮不了啊。
父亲看了我一眼说,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懂。
我说,肯定是麦草的事。这有什么难,你网开一面,只管让那两个人拿好了,麦草那么多,不拿,开春也是烧掉。缺少人手,我也可以去帮忙。
父亲急了,你想错了,每次就那么点牧草,还不够牲畜塞牙缝,若是队长开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鄙视了一下父亲,你还嫌少?你都把人家得罪了,傻瓜才会答应你。
父亲说,不会,有一个人只要肯帮忙,队长一定会答应。
我问,谁?
父亲说,你妈。
父亲的答案令我更加生气,明明出去找了,却不到半天就回来了,没能把母亲找回来,如今又提到母亲才能帮他的忙,这明摆着是哪壶不开掀哪壶。父亲丝毫不在意我的态度,他说,队长是你妈的哥,是你的舅舅,你妈出面,他肯定给面子。我心怀不满,责备父亲,早知道这样,你干嘛顶撞队长?每天后半夜跑出去,都不给我妈一个交代。你知道吗,暴风雪那夜,我妈在窗边足足守候了一夜。
我不是回来了么?不是好好的吗?女人都那样,气量太小了。很快,父亲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又添了一句,不过,你妈度量其实要比别人大。父亲讨好地对我说。我的心软了下来。问,那你现在咋办?
父亲犹豫地望着我,像是在讨主意。要不,我再去求下队长?我使劲儿点了点头。
五
父亲第二次从队长家回来,不用他说,我已经从他脸上看到事情的结果。他显得有些忧伤,一声不吭地在炕上躺了一个多小时,突然翻身跃起,说是要“背水一战”,决绝的样子像是电影里赴汤蹈火的英雄。我说队长若没答应,你就打消念头吧。父亲来气了,冲我吼叫,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怎么看得下去。当初队长不叫我看草场也就罢了,可偏偏又派我去看草场。我要是聋子瞎子就没事了,可偏偏又遇到转场的牧民,风雪天里,谁忍心看着牲畜在雪灾中死去?那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啊。父亲的口气听来,好像这雪是有人故意让下的一样,一心在打抱不平。
父亲焦灼的样子让我难过,可我跟队长舅舅又搭不上話,他若肯理我,我一定会抱着他的大腿,哀求他帮帮父亲。
那天下午,父亲睡了半天的觉,他睡之前满怀期盼地再三叮嘱我,若是队长来找,要及时叫醒他。他说队长这人脾气犟点,人还是不错的,说不定他想通了,还是会同意的。整个下午,我暗地里观察,父亲并没睡着,他一直都在悄悄地盯着挂钟,一直捱到夜里 10点,父亲的美梦最终落空,队长连个影子都没出现。不能再等了,父亲看看挂钟,失望地起身,长叹一声,一言不发,推门而出,说是要去看草场了。
临出门前,父亲再三叮嘱我,晚上会有暴风雪,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能出门。鬼才相信父亲的话,我猜测父亲可能要去办他所谓的正事了。既然队长都没给他好脸色,没答应他,那父亲嘴里所谓的正事肯定是有风险的。替父亲的安危着想,我认为母亲不在家,只有我才能阻止父亲的行动,尽管这个阻止有多少把握,我也没底。但是固执的父亲显然已决意一口气要走到底。我不阻拦,谁阻拦?
我一直迷迷糊糊等到凌晨两点多,一阵隐约的狗叫声惊醒了我。风雪夜里,狗的叫声极不真实,像是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只是偶然闯进了我的梦乡。我套上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拿起母亲常用的手电筒,我知道父亲此刻在哪里,我想探究父亲到底在办什么正事。
一点点地接近马厩草场,一个杂乱的场景慢慢呈现在眼前:马厩草场边上,二十多头牦牛一字排开,背上搭着架子,十多位穿着长袍的牧民男女,正轻手轻脚捆扎麦草,将它堆放在牦牛背上的架子上。来回穿梭的人影中,我找到了父亲,他像一个将军,正站在麦草垛旁,有条不紊地指挥那些人搬运麦草。我诧异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安静,我好像身处在一个无声世界里,看着眼前的牧民们在默默地装载麦草,夜风寒气逼人,装草的牧民们脸上却盛开着微笑,那是绝处逢生的微笑,是充满希望的微笑。那些微笑一点点融化了麦草垛上的积雪,让我内心渐渐变得温暖。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开始帮忙搬运起麦草。
天渐渐放亮,雪又开始在天地间轻舞飞扬。白日之下的雪,如同玉屑晶莹。
二十多头牦牛背负着如同小山似的麦草,一字排开,连成一条“山脉”。父亲忙完一切,回头发现了我,嘴角笑笑,想问我什么,却没问出口。他只是朝我点了点头,目光里充满歉意,我也朝父亲点了点头,用目光送给他一份支持。父亲却没能接住,因为他的目光此时已经掠过我的头顶,跑向我身后,很快变得有些慌乱。我赶忙追随父亲的目光扭过头,突然发现,队长就站在距离我和父亲不远的地方,他似乎已经来了很久,我们谁都没发现。
队长用犀利的眼睛扫视着我、父亲、十多位牧民、二十多头牦牛。他的目光里隐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以为属于父亲的暴风雪即将来临,我甚至为父亲担忧,怕他会收不了场。
我甚至想好了,万一父亲被责骂,我一定会冲上前抱住队长舅舅的大腿佯装亲热,让他无法放下面子指责父亲……出乎意料,沉默片刻,队长笃定地扫视一圈在场的人群后,最终坚定有力地挥挥手,用他在部队里练就的雄厚声音,吐出两个字——出发!
起初有些忐忑不安的父亲,听到那两个字,脸上顿时开满了花,他感激地望了一眼队长,坦然地回过头,手一挥,也学着队长的样子,大声地喊了一句——出发!
我看到那条“山脉”开始缓缓移动,十多位牧民朝我们深深鞠躬。人群中还闪出了那天夜里我遇见的牧民老阿妈,她踩着积雪,步履蹒跚地走到父亲面前,双手颤抖地把一条洁白的哈达搭在父亲的脖子上,深情地凝望父亲片刻,而后双手合十,转身尾随着运草料的牦牛队伍远去。我还惊喜地看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了队长身边,他们望着披着哈达的父亲,会心一笑,那笑里似乎藏着什么秘密。
天地之间,白雪苍茫,就像一条宽大的哈达,搭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我知道上面一定写满了吉祥,写满了祝福。
【作者简介】苏康宝,浙江温州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07年以来,先后在《西北军事文学》《西南军事文学》《黄河文学》《辽河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文学与人生》《雪莲》等刊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80余万字,2011年出版纪实文学集《守望非遗》,2013年出版中篇小说集《河镇纪事》,2015年出版散文集《送你一束腊梅香》,202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寻找李慕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