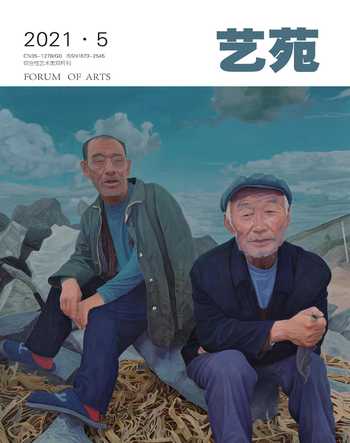汉画像的美学式研究路径
李新
摘 要: 《方花与翼兽:汉画像的奇幻世界》从美学、图像学等角度对汉画像中的六个专题展开综合研究。作者注意到汉画像中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成像方式,重视从想象力、比兴思维等方面分析造像的思维方式,从层累的传统文化、多元的外来文化和地域性文化等方面总结汉画像的审美特征,还借助图像辨识、形式分类和还原方位等方法,重点阐释了六类图像的象征内涵、审美精神,呈现出“点—线—面”的阐释路径,突出了“飞升化仙”的共同主题。
关键词:汉画像;美学式研究路径;想象;象征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朱存明主编的《方花与翼兽:汉画像的奇幻世界》作为《汉学大系》丛书的一种,2020年12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汉画像中的图像为中心,选取汉画像中的“方花纹”“灵芝草”“云化鸟”“虹”“翼兽”、《列仙传》与汉画像中的神仙形象对比等六类专题展开研究。作者们重视“经典阐释与主题研究并重,历史的考据与新出土文物的互证,古典文献与出土简牍对读”[1]4的研究路径,不仅仅基于图像所处的“原境”[2]7展开研究,而且借助图像学、符号学、象征主义等方法,聚焦汉画像创造的思维方式和成像的审美特点,从美学角度(1)探究了汉画像的象征内涵、审美精神和美学意义,对于汉画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基于汉画像创造的思维方式
汉画像是汉代艺术的重要遗存,是创作者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借助想象力和比兴等思维、 立意于象的结果。朱存明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汉画’一下子把漢代的天与地、神与鬼、人与兽、美与丑、善与恶、吉与凶、灾与异等展现在人们面前。”[1]1概括出汉画像题材的丰富性和以象表意的创造性。从本书的论证方式和研究角度可以看出,作者们重视从思维方式角度对汉画像展开研究。
作者们注意到了灵芝草、“云化鸟”“翼兽”等图像中包含的现实因素,以此为出发点发掘图像的内在意蕴。如“灵芝草可以致幻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菌类含有的裸盖菇素——赛洛西宾。”[1]106“云化鸟”图像是汉代人看到鸟儿或隐或现地飞行于云气之间,激发了创作者的想象。[1]138“严格说来,虚拟想象的动物也是以自然界的动物为原型的。”[1]292这表明,汉画像中不仅写实、叙事的图像,如庖厨图、乐舞图、狩猎图、历史故事等是现实世界的表现,而且非现实的图像在某种程度上也寄寓了现实的因素。作者们探索汉画像的现实因素,有助于理解图像创造的原理、目的和功能等,是探究图像的象征意义和美学内涵的重要基础。
本书还注意到了这些图像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特点,重视主体想象力在创造图像中的作用。第二章中指出灵芝草之所以表现为三种形态,是因为“任何图像的创造首先来自于创造者内在心灵的需要”[1]70,突出了主体心灵在汉画像创造中的主导地位。汉画像创作中,主体借助想象力组合符号的过程,是“立意于象”[3]822的过程,也是象征意义生成的过程。第五章作者认为翼兽是“作为人们想象化的形象,把符号不同而文化功能相同的动物图像进行了拼接组合”而创造出来的。[1]319创作主体以“意”择象,但每一符号或图像都不是随意刻画的,而是为“意”所制约,为“意”服务的。朱存明在《汉画像之美》中就指出汉画像是汉代现实、精神和文化等的“镜像”,“人只能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死后的世界,但却可以幻想一个死后的世界”[4]21。汉画像中翼兽的“羽翼”大部分是为突出表现翼兽的神性而有意添加的,寄寓着羽化飞升的内涵和意义。主体借助想象力使多种符号集于单幅图像中,以表达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作者在论证灵芝草、虹、“云化鸟”“翼兽”等图像时,根据形、音、义等方面的相似性解读汉画像中的图像,是一种基于比兴思维展开的研究。文中指出,灵芝因“T”字的形状,而被类比为昆仑山、仙台或“华盖”,与西王母成为固定配置[1]86;“虹”与“桥”同形同构,汉代人便将其类比为登仙之桥[1]247;受传统鸟图腾崇拜的影响,汉代人认为人或者兽生出双翼就可以羽化飞升。[1]322这些都符合汉代人的艺术创造思维方式。汉代人是借助譬喻取象、依类象形、立意于象等方式创造的艺术意象,体现了先秦比兴思维在图像创造中的应用。这也是汉画像的象征意义得以生成的重要方式。作者们从形、音、义等象形、类比的思维方式出发,对汉画像展开分析,有助于拓展汉画像的象征意义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书作者们在研究图像的过程中,从现实因素、想象力、比兴思维等角度对汉画像中的图像展开研究,属于美学式的研究范式。从这三个角度解读汉画像中图像的象征意义,对于研究汉画像的审美意识、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这三个角度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汉画像的创造规律,对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汉画像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二、聚焦汉画像创造的审美特征
本书选取的六类专题在体现汉画像创造的审美特征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从图像志溯源或跨文化视域等不同角度对图像展开分类、比较和阐释,体现出汉画像创造的层累性、地域性和多元性等特点。
本书作者们重视从历时的角度对图像的形式和意义展开溯源,发掘图像中积淀的、层累的文化元素。书中将“方花纹”远溯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史前陶器上的花瓣纹和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花朵纹饰。本书还认为“云化鸟”图像远承新石器时期的云纹、鸟纹,近续商周器物上云鸟纹结合的纹饰图案。作者们一方面溯源了这些图像的形式演变,构成了关于它们的美术研究和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探索与图像内在意义相关的文化、思想和观念的源头,进一步深入分析图像的内涵和意义。如作者根据“云化鸟”意象的地域分布特点,认为它与早期的东夷文化和鸟图腾等有关,这就为解读“云化鸟”意象中的再生、飞升等意义提供了理论依据。[1]157这种研究方法致力于发掘图像的演进脉络,在古今比较中,凸显汉画像的审美特征和独特的时代意义。
本书对比同一图像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深入研究它们的审美精神和美学内涵。第二章、第三章主要是以地区为依据对图像做出分类,如各地区的云化鸟图像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卷云形态的云化鸟集中于山东地区,蔓草云形态的云化鸟集中在陕西地区,流云形态的云化鸟散见于徐州部分地区。”[1]158这种区分属于图像志的、艺术学的方法,为进一步探究图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特征提供重要依据。同一类的图像之所以表现为不同的风格、样式,与墓主人、创作者(工匠)的审美意识有直接关系。巫鸿就指出:“作为个人‘纪念碑’的装饰,图像母题又反映了主顾赞助人或工匠的思想、品味和个人喜好。”[5]12因而,根据汉画像的地域性特点,分析各地区的表现方式和创造观念,研究造成差别的审美意识、艺术观念和文化因素等,从整体上把握该图像的形式和内涵,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和阐释该图像在汉代的文化意义。
本书还重点关注了汉画像中的外域文化,从跨文化的多元性视域研究汉画像。作者认为两汉时期是翼兽受外来影响而发展的关键期之一。[1]283-284“汉画像中翼兽造型特征与羽翼的具体形态,受外来的狮首格力芬或带翼狮的影响。”[1]268这是因为汉代打通丝绸之路,促进了与西域等外域文化的往来和交融,外来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大大激发了汉代人的想象力。汉代人从中吸收了羽翼等符号,用来表征飞升化仙等意义,是突破层累、彰显创造的重要方式,丰富了汉画像中图像的表现形式。本书作者是从美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汉画像中“翼兽”图像的象征意义展开分析,发掘出汉代翼兽文化不同于汉以前翼兽文化的独特之处。
本书从历时层累、地域性和跨文化的多元融合等三個角度,各有侧重地对“云化鸟”“翼兽”等图像展开了细致研究。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机地体现在各个专题的研究中。如翼兽的研究,既注意到了“翼化”现象的层累性,同时侧重从跨文化的多元视域探究汉代翼兽中体现的西域、中亚等新元素。汉画像中的图像是在多元层累的基础上,结合地域性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内涵,创造出饱含象征意义的艺术意象。聚焦汉画像创造的审美特征展开研究,较为合理、细致和全面地对汉画像中的图像作出分类和分析,丰富和发展了汉画像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其他图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集中汉画像的主题展开研究
本书各章分别选取了方花纹、灵芝草、“云化鸟”、虹、翼兽和列仙图等六类图像展开研究。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相似的主题——“飞升化仙”。这种基于某一类图像,从整体上对这类图像的内涵、图式和意义等展开研究的基础上,重视由单类图像的专题性研究与多类图像的谱系式研究相结合的路径。
本书作者们重视图像志、艺术学和美术学等研究的基础作用,结合图像的辨识、形式分类和还原方位与配置等方法,对图像展开细致分析。如第一章以“方花纹的名实之辩”为始,第二章以“灵芝草的图像判定”为端等。这种图像辨识研究增强了主题立论的说服力,为图像的分类研究等提供依据。作者们在比较、归纳中总结各类图像的独特规律,从不同角度对它们作出分类。如“云化鸟”图像分为卷云化鸟、蔓草化鸟、流云化鸟等三大类,又详细划分出多种类型。[1]158“虹”图像分为龙首龙身、双首一身、单道、双道等类别。[1]206-215这种“微观研究”有助于分辨同类图像之间的异同,发掘它们的形式特点和规律。作者们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结合图像的方位和配置,还原图像的“原语境”。如第一章根据方花纹出现的方位——藻井、棺盖、墓室顶盖、祠堂顶盖、铜镜钮等位置,总结出它的“顶”和“中”的特点;第二章总结出芝草与西王母、伏羲女娲、羽人和四象等的配置规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依据单幅图像解读它们的美学内涵和象征意义带来的误判,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体现了严谨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本书作者更加重视汉画像中图像的表征功能,探究图像的象征内涵和审美精神,从而提炼出共同的主题。他们认为,不仅芝草、翼兽等图像具有象征性,方花纹和云化鸟纹等具有装饰性的图像也具有象征意义。“汉画像中的方花纹就是用抽象简洁的符号来表达汉代人对生命永恒的追求。”[1]45“云化鸟这种纹饰在汉画像中具有宇宙不同层次分界线的意义。”[1]138这就将装饰功能和象征意义统一起来了。这是由汉画像的创造方式决定的。汉画像是创造者借助想象力和比兴思维等立意于象的成果,是为死者服务的现实世界的“镜像”,其中每一个图像和符号都具有它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朱存明在《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中就提出了汉画像的“宇宙象征主义”,认为汉画像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体”,其中包含着汉代人思想文化和审美意识等,是汉代人认识、表现世界的重要方式。[6]76但是每一类图像的象征意义又不是唯一的,如灵芝草图像包括“不死仙药”“有德瑞应”“升仙凭证”等;虹图像包括“司雨之神”“升仙之桥”“龙宫之门”“天穹之盖”等象征意义,体现了汉画像内容的丰富性和汉代文化的多样性。本书作者以具体图像为中心,从“象征”的角度更深入地研究图像的象征功能、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等,区别于从艺术学和美术考古等方向对图像的形式和创造规律的研究,是探究汉画像和汉代的美学观念和审美精神的重要方面。
在单类图像的象征意义的基础之上,突出多类图像的共同主题和谱系,是本书的重要特点。本书选取的六类图像尽管在图像形式、图像配置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表现为各自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象征意义,但它们并非是零散的和随意组合的,而是共同指向了“飞升化仙”的主题。“方花纹”寓意炼形飞升、“灵芝草”是服食升仙的仙草、“云化鸟”是汉代气化飞升思想的表现、“虹”是登仙的桥梁、“翼兽”表征着汉代羽化飞升的观念、第六章则是从图文互释的层面研究汉画像中的列仙形象。六类图像分别从升天式、登仙式、羽化成仙式(2)三个角度表现了两汉祈求飞升化仙的时代主题。但由于主体、地域、时期等不同,其表现同一主题或相近主题时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会有差异。这种主题性的研究以具体的图像研究为基础,比较、归纳多类图像所表征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发掘其中蕴含的共同主题,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汉画像的美学内涵、象征体系和时代意义,也为研究汉代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书各章的研究体现出从“点”到“线”再到“面”的阐释路径,是一种围绕主题展开的专题性、谱系式研究。作者们以汉画像中的同类图像的辨识、分类、配置等为基础,聚焦“象征主义”的视角,由象揭意,通过解读单类图像的象征意义、审美精神和美学内涵,总结多类图像中共同蕴含的主题和意蕴,鲜明地體现了美学式的图像学谱系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对其他主题和专题的汉画像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 语
总而言之,本书从美学、图像学等角度对汉画像中的六类图像进行综合研究,体现为从分类研究到整体研究、从形式分析到内容分析的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旨在通过解读汉画像,发掘其中蕴含的审美意识、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等,实现多类图像的主题研究和谱系建构。这是基于金石学、考古学、文化学和艺术学的研究之上的美学式的研究范式,,探寻汉画像的美学意义和审美境界。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表明,汉画像中蕴含、融汇了早期文明和外域文明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元素等,体现了汉代文化绵绵不断的继承性、生生不息的创新性和多元交融的包容性。汉画像基于传统,开拓进取的创新品质,对当下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反思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精华,结合新的时代因素和外来文化,创造出凸显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优秀文化和艺术。这也凸显了汉画像研究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巫鸿、朱存明等学者们都详细了汉画像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演进历程。如巫鸿在《武梁祠》中,提到了金石学的研究、19世纪以来的综合研究、艺术学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等方法,他采取的是在图像志基础上,展开图文互释的研究方法。参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2006年,第39-80页。朱存明提出了汉画像研究的四种历史范式——金石学式、考古学式、文化学式和艺术学式等,他在《汉画像之美》中采取基于四种研究范式的美学式研究方法。参见朱存明:《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48页。
(2)朱存明认为汉画像中的升仙有三种样式:升天式、登仙式和羽化成仙式。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方花是炼形升天的工具、灵芝草属于服食升仙的仙药;虹桥等是登仙的媒介;云化鸟、翼化则是羽化成仙的方式。
参考文献:
[1]朱存明.方花与翼兽:汉画像的奇幻世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
[2]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6.
[3]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7.
[4]朱存明.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巫鸿.公元2世纪的天界图像[M]//郑岩.陈规再造: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6]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林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