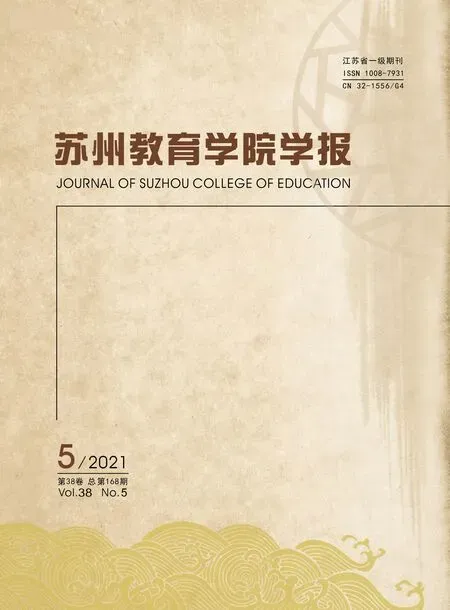从“天雨粟,鬼夜哭”到敬惜字纸
——论古代神话和民间习俗中的汉字崇拜
陈连山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仓颉造字”是中国古史传说的一部分。从神话学立场看,“仓颉造字”也是文化发明神话的一部分。本文从神话学,而不是历史学的立场出发来分析“仓颉造字”,并通过分析敬惜字纸习俗,来阐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文字而获得的优越感,以及民众对于文字的崇拜。
一、汉字发明人的选定
文字是呈现书面语言的基本工具。文字本来是口头语言的记录,但是由于它本身的数量和书写成本的限制,导致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记录口语的所有内容。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因为当时使用的文言文跟口语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当然,文字这种书面语言也具有口语所不具备的优越性,那就是它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在没有录音设备的古代,文字记录可以超越空间,传播给更远地区的人们,也可以跨越时代流传得更久。文字在保存和传播文化知识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因此,文字是古代高等文明的标志,也是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柱。既然文字如此重要,那么,古人崇拜文字、崇拜文字发明人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汉字的发明与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由某一个人突然发明出如此完整的文字体系。迄今为止,古典文献和考古材料都没有可靠的汉字发明人的任何信息。假如把仓颉看作确实可靠的历史人物,那么从历史学角度来探讨“仓颉造字”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是本文采用神话学立场来研究“仓颉造字”的原因之一。
可是,古人似乎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汉字发明人,而且不止一个。在神话中,苍颉、沮诵、伏羲都曾经被视为汉字发明人。《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1]这里的“一”是指一心一意、专心致志的意思。爱好文字的人很多,但是只有仓颉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仓颉专心于文字。在荀子眼里,仓颉是众多文字创造者中最好的一个,或者说是最有功劳的一个。荀子的上述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仓颉造字”的说法在古代各种造字神话中是最为普遍的。《世本•作篇》则说汉字是两个人发明的:“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之史官。)”[2]30还有一种说法是汉字是伏羲发明的。《尚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3]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沿袭了此说法:“太皞庖牺氏(即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2]16
以上三种说法各不相同,特别是第一和第三种说法完全对立,如果从历史学角度来判断,根本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古人出于崇拜汉字的实际需要而创造出的神话,三个人物都是神话中的人物。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人物,并最后将汉字发明人归于仓颉一人呢?我从他们的身份入手来分析。
根据《说文解字•许慎序》的说法,仓颉是“黄帝之史”[4],宋衷亦有此说[2]30。这个身份是很神圣的,因为黄帝一直被看作华夏文明的始祖。《史记•黄帝本纪》说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5]6。张守节解释说:“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5]8黄帝作为神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其部下自然也都是文化发明人。仓颉作为黄帝的史官,出于记录历史的需要而发明文字是顺理成章的。《春秋元命苞》把仓颉的地位提升到古代帝王:“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2]30这个说法不见于其他古籍,可见流传不广。但是,这个身份的神圣性比其他古籍所说的仓颉为黄帝史官要高出很多。因此,《说文解字•许慎序》《世本•作篇》所讲的仓颉为黄帝史官的说法与《春秋元命苞》中仓颉为仓帝的说法是互相矛盾的。古籍中关于汉字发明人的三种矛盾说法,以及仓颉身份的不同记录表明,仓颉只是后人出于崇拜汉字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历史人物”,其实质是古代神话中的文化发明英雄。
《世本•作篇》说汉字是沮诵和苍颉两个人共同发明的,这不太符合一般文化发明神话的规律。即使真的如此,其中也存在谁的功劳更大的问题。按照《荀子•解蔽》的说法,还是仓颉最为专业。另外,沮诵与仓颉的身份存在雷同,所以,沮诵在该神话的流传过程中就逐渐被仓颉吞并了。或者说,这两个黄帝史官在神话的不断发展中合而为一了。
作为古史传说中时代更早的帝王,伏羲的主要事迹在于画八卦、制嫁娶。绝大多数谈论八卦起源的材料都称八卦是伏羲发明的。同样,普遍存在的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交尾的图像则是表明了伏羲和婚姻制度的关系。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云:
太皞庖牺氏(即伏羲),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2]16
上述神话的核心仍然在于画八卦和制嫁娶,发明文字只是伏羲的众多成就之一。而仓颉只有这一项功绩(这就是荀子所说的“一”),所以,伏羲的“造书契”就很容易被“仓颉造字”取代。我们在晚期的史料和民俗资料中很少再看到伏羲“造书契”、发明文字的神话。由此可见,随着神话的发展演变,仓颉逐步成为唯一的文字发明者。
二、汉字崇拜在“仓颉造字”神话中的表现
很多古籍都谈到了“仓颉造字”,但一般没有任何情节。有情节的早期记录首推《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云:“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豪(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6]571从这个神话本身看①《淮南子》对这个神话的态度与神话本身不太一致,待下文分析。,天(神)是完全支持发明文字的,所以他为预防人类贪图文字之利而废弃农耕,提前降下粟雨以警示人类;鬼(兔)则是担心自己可能会受累于文字。在这个神话中,仓颉的文字发明惊天地泣鬼神。这是对汉字的社会功能的极度夸张。
《春秋元命苞》叙述的神话则更加奇特:“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乃受河图、录字②录字:涵义不详。《艺文类聚》中有黄帝得到大鲈鱼赠送的录图,录字很可能也是和录图类似的东西。。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③笔者重新句读。原文参见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0页。在这里,仓颉成了古帝,龙颜宽阔,还长了四只眼睛,且聪明绝顶。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神灵佑助,像伏羲、黄帝一样接受了所谓的河图、录字。在这样的前提下,仓颉才发明了文字。根据这个神话,文字是在神灵的启示下,由禀赋异常的远古圣人发明的。所谓“仰观”“俯察”,就是仓颉发明文字的具体过程,这和伏羲发明八卦的过程“仰则观象”“俯则观法”[2]16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就是说,文字是参考了天文地理制造出来的,所以它能够表达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春秋元命苞》从文字的诞生到文字的功能,对汉字进行了全方位的神化。
这些神话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仓颉及其发明的文字的虔诚崇拜。古人创造这些神话,就是为了使文字获得合法性和神圣性。
三、汉字崇拜从神话逐步发展出敬惜字纸的民间习俗
汉字崇拜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不断发展的。从先秦时代就出现的“仓颉造字”神话经过不断发展,日渐完善,并逐步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汉字的崇拜出现在各种地方政府的《惜字条约》中,也存在于民间敬惜字纸的习俗中。
汉字最初是刻在甲骨或铸在青铜器上的,再之后书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那时候的文字崇拜是否发展到爱惜一切写有文字的材料,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证据。杨宗红、蒲日材认为道教崇拜符箓、佛教崇拜佛经、儒教崇拜圣人之书,“……儒释道三家均有字纸崇拜”。[7]但是,我以为道教符箓、佛教经书和儒家经典跟一般文字有重要区别。道教信众崇拜符箓,佛教信众崇拜佛经,儒家知识分子崇拜圣人之书,这些都只是崇拜自家的神圣经典。早期的文字载体(甲骨、青铜器等)成本很高,文字应该主要用在记录所谓的“经典”和重要事务方面。崇拜经典是不是附带着崇拜文字难以确证,但是,当纸张发明以后,文字载体的成本大为降低,文字逐步得以普及,也用来记录日常生活的需要。写着世俗内容的字纸是否依然神圣?这才成为一个问题。后世的敬惜字纸习俗是珍惜一切写有文字的纸张,包括经书和一切废纸,但不包括未用的新纸。所以,杨、蒲二位所列不能算作真正的敬惜字纸。
纸的普及大约在魏晋时期。目前已知最早的敬惜字纸言论出自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8]这段话把敬惜字纸的理由归结为尊重儒家经典和圣人,但是,经典的范围扩大到写有经义和贤达姓名的“故纸”,这就开启了敬惜一切字纸的先河。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云:“自从远公于大内见诸宫常将字纸秽用茅厕之中,悉嗔诸人,以为偈曰:‘……《长扬(杨)》并五策,字与藏经同。不解生珍敬,秽用在厕中。悟灭恒沙罪,多生忏不容。陷身五百劫,常作厕中虫。’”[9]这里所说的“字纸”不一定是经书。偈中所说的《长杨赋》是扬雄的文学作品,五策是政治奏议,当然都不是经书,但因为它们的文字与佛经相同,因此被认为是必须“珍敬”的,不得“秽用”,这是典型的敬惜一切字纸的行为了。
从《颜氏家训》《庐山远公话》可知,后来民间广泛流传的敬惜字纸习俗的确跟儒家和佛教信众崇拜经典有关系。道教文昌帝君信仰在敬惜字纸习俗的形成过程中影响也很大。据说他主要掌管文运和科举,明清时期其神职扩大到驾驭神鬼、降妖除魔、祈雨、求子等领域,跟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于是百姓也越来越崇拜文昌帝君。而在文昌帝君信仰中敬惜字纸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真诠》[10]等劝善书在敬惜字纸习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爱惜字纸就能得到神灵保佑;糟蹋字纸,就将遭受各种报应。一打一拉,影响不可小觑。
敬惜字纸的习俗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对废弃的字纸不可乱用。不能随手包东西,不可用做手纸,不可践踏等。第二,废弃的字纸要妥善保管。第三,需要丢弃的字纸要深埋于净土之中或焚化。第四,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组织,例如惜字会、敬字社等。其中天津的崇文社、德文社、广善社、拾遗社等还在每年三月初三到文昌宫焚化字纸。[11]
这里再补充一些关于如何焚化字纸的材料。各地的《惜字条约》普遍都规定了:街坊里社村墩,都应该在洁净之处,公设惜字亭一所,用来焚化字纸。其实,在文昌帝君庙和学堂中,往往都有类似建筑。其他一些庙宇也有在庙前建惜字炉的,专门供善男信女用来焚化需要丢弃的字纸。我在浙江诸暨的古代学堂内,就见到了一座惜字亭。它是当时师生用来焚化字纸的。其实具有同类功能的建筑在其他地区还有别的样子,如高塔形状。这些建筑的名字不尽相同,有“敬字亭”“惜字宫”“惜字塔”“字库”,等等。
四、文字崇拜的弊端
文字崇拜的精神实质是崇文重教,这当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其他学者对此已经有过讨论,无须赘言。我在这里转换一下视角,专门讨论一下文字崇拜的弊端。
还是从古代说起。《淮南子》在引述仓颉造字神话的时候,并不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是根据黄老思想对此有所批判:“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6]571-572按照《淮南子》的说法,人类的能力越多,道德水平就越低,发明太多,机心太重,质朴的本性就会受到损害。这种道家言论固然不足全信,但是很有启发性。
文字崇拜使得掌握和使用文字的中国古代文人变得充满文化优越感,自以为掌握了文字,就掌握了最大的能力,因此就垄断了一切知识和文化。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不识字的人叫作“文盲”,认为他们没文化。这样,古代知识分子和“五四”以来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总以精英自居,以民众导师自居,强迫民众接受他们的教育。在古代这叫“教化民众”,如今叫做“启蒙民众”。启蒙没有错,但是启蒙应该以双方的自由平等为基础,否则,无异于精神控制。我在《走出五四,全面肯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曾经说过:“说到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用科学与民主对民众进行启蒙,民众在他们眼中依然是等待教育的对象,这种启蒙与古代知识分子教化民众实质上是相同的,存在的差别只是在于各自准备给民众灌输的观念不同。从根本上说,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知识分子都从来没有把民众当作平等的人看待;更没有把民间文化当作平等的、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12]
其实,文字不过是人类语言的载体之一而已,口语是人类语言更直接、更便捷的载体。人类的知识和思想除了借用文字表达之外,还有口语表达的途径,还有实际行为直接展示的途径。不识字的民众同样能够创造文化、拥有文化、传承文化。而且这种文化还可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3]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的就是民间口头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在研究古往今来各种文字崇拜的时候不得不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