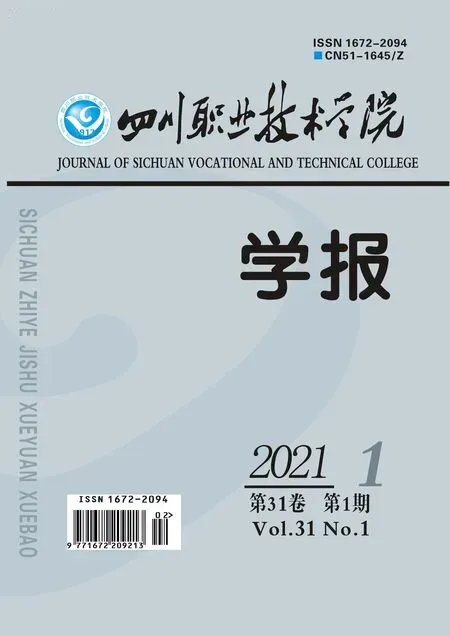安大简《诗经》与《毛诗》的章次差异初探
郑婧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2019年9月21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安大简”)第1辑[1]正式发布。作为战国早中期的抄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版本。简本《诗经》58篇中有14篇与现存《毛诗》章次排列不同。
关于安大简《诗经》与《毛诗》的章次差异,学界多有讨论。黄德宽指出:“简本与《毛诗》的章次也造成一部分异文,这些差异是否体现诗意的差别,尚待深入研究。”[2]吕珍玉认为,安大简进一步证明了《诗经》的重章叠唱,只要合乎押韵,章的安排在当时可具有随意性。[3]王化平师注意到安大简《诗经》章序与《毛诗》不同之处在于,一般是以章为单位发生变化,且很多时候是二、三章之间的变化。他表示:“这与诗歌的音乐性相关,也有可能与抄写格式相关。”[3]网友“汗天山”指出:“安大简本《诗经》章序多有与《毛诗》不同者,很多诗篇的章与章之间是并列关系,次序颠倒对诗旨并无任何影响。”[4]赵海丽《安大简本〈螽斯〉章次探赜》指出,安大简《螽斯》与《毛诗》相较,二、三章相互错置,根据诗旨梳理及章次顺序的考察分析,认为安大简是一首用于祝祷子孙众多的乐歌颂诗;从音韵方面,安大简以阳声收尾,较《毛诗》以入声收尾,在情感表达上更音调畅阳;综合而言,她认为简本《螽斯》章次较《毛诗》合理[5]。宁登国、王作顺《安大简〈诗经•江有汜〉异文的解题价值》表示,《江有汜》简本二、三章与《毛诗》互换后更符合嫡妻感情变化过程,可证《江有汜》为单纯的“美媵”诗无疑[6]。
鲍则岳在研究早期诗歌文本问题时,曾提出“构建模块”(buil ding bl ocks)这一概念,指的是相对较小的文本单元,它们可被灵活地编入不同的文本语境[7]。《诗经》中的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构建模块”,即相对于一首完整的诗而言,它只是其中较小的组成单位,可以被灵活地排列在同一诗篇的不同位置。《诗经》作为合乐的歌词,多重章叠唱,全篇各章的结构和语言往往非常接近,只有部分词汇发生变化。因此章的安排在当时可具有随意性,顺序变换后大多对诗意无影响。
安大简《诗经》与《毛诗》不同章次情况如下:
《卷耳》: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螽斯》: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羔羊》: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殷其雷》:简本第一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一章。
《江有汜》: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车邻》: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驷驖》: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小戎》: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简本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黄鸟》:简本第一章对应《毛诗》第二章,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一章。
《硕鼠》:简本第一章对应《毛诗》第二章,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一章。
《墙有茨》:简本第一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一章。
《蟋蟀》:简本第一章对应《毛诗》第二章,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一章。
《绸缪》: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鸨羽》:简本第二章对应《毛诗》第三章,第三章对应《毛诗》第二章。
以上14首诗中,绝大部分章次变换后在诗旨表达、诗意理解等方面无任何影响,《毛诗》与简本的顺序均可。当然也有例外,如《驷驖》、《绸缪》就存在一定的争议。两诗中发生变化的两章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并列关系,顺序颠倒后会对诗意的表达和理解产生一定影响。
一、《驷驖》
《驷驖》三章,章四句。简本与《毛诗》二、三章顺序颠倒。
《毛诗》作:
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
安大简作:
《毛诗序》:“《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孔疏曰:“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园囿之乐者,还是田狩之事,于园于囿皆有此乐,故云园囿之乐焉。猎则就于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调习则在园中,下章园中事也。有蕃曰园,有墙曰囿。园囿大同,蕃墙异耳。囿者,域养禽兽之处。其制诸侯四十里,处在于郊……园者,种菜殖果之处,因在其内调习车马,言游于北园,盖近在国北……”[8]481在“游于北园,四马既闲”一句后,郑笺云:“公所以田则克获者,乃游于北园之时,时则已习其四种之马。”孔颖达解笺曰:“此则倒本末猎之前调习车马之事。言公游于北园之时,四种之马既已闲习之矣……游于北园,已试调习,故今狩于囿中,多所获得也。”[8]483-484郑、孔均认为此篇出现了两个场所,即园与囿,全诗采用倒叙手法,先说公在囿中“舍拔则获”,最后解释原因,即之前公在园中早已调习过车马与猎犬,所以能够做到田则克获。
然陈奂认为二人之说有误,陈曰:“《有杕之杜》传:‘游,观也。’《书•无逸》篇云:‘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浑言之,游亦田也。古者田在园囿中,北园当即所田之地。首章言狩,此章言北园,与《车攻》篇上言狩言苗,而下言于敖,文义正相同也……《笺》以《序》‘田狩园囿’分属二事,遂谓公游北园为田获以前,并读‘闲’为‘邦国六闲’,‘四马’为‘四种之马’,恐非《诗传》之恉。”[9]327-328是以陈奂认为全诗采用了顺序手法,但其说或有不足之处。首先,陈奂质疑倒叙说,是从“游”有“田”义出发的。他举出的《尚书•无逸》篇句子,实际断句当为:“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10]《汉书•毂永传》引经曰:“继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伪孔传:“所以无敢过于观游逸豫田猎者”,“观”“游”并列,即观赏游玩,与“田猎”异义。孔颖达正义:“则其无得过于观望,过于逸豫,过于游戏,过于田猎”[11]513-514。如是,则“游”释为“游戏”,与“田猎”并不同。此外,《尚书•无逸》篇还有一句将“游”“田”二字并举:“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疏分别释作“游逸田猎”“游戏畋猎”[11]512。“游”“田”当分属两种不同的行为,即“游玩、游戏”“田猎”。因此,陈奂认为浑言之“游”亦“田”的说法不可从,且遍检古文献,无“游”义同“田”的例证。陈奂或是将田猎看作是一种游玩方式了,但很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至于《驷驖》一诗是否分述两事,还得看《毛诗》末章中“闲”“载”二字之义。历来学者对“闲”的理解不尽相同,占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练习、熟练”,经学家多从此义。毛亨、郑玄均释“闲,习也”,陈奂云:“《书大传》:‘战斗不可不习,故于搜狩以闲之也。闲之者,贯之也。贯之者,习之也。’”[9]328又《尔雅•释诂》有言:“闲、狎、串、贯,习也。《释曰》:‘闲,便习也。’庄二十二年《左传》曰:‘赦其不闲于教训。’”[12]今人高亨[13]、袁梅[14]释“闲”为“熟练”义,乃取“闲”通“娴”。若“闲”为“练习、熟练”,则《驷驖》分属二事,在前两章狩猎完毕后,言之所以能“田则克获”,是因为之前在北园中已有练习车马或车马已熟悉狩猎。二是“休息、闲暇”义,即“闲”通“閒”。《诗毛氏传疏》:“闲,古字皆当做‘閒’。”[9]327《说文》:“閒,隙也。引申,閒者,稍睱也,故曰閒暇。今人分别其音为户閒切,或以闲代之。”[15]589此义展现出了狩猎完毕后从容休息之态,若取此义,则全诗采用顺序:前两章叙述激烈的狩猎场景,后一章则言狩猎后于北园休息、整顿车马与猎犬。
再看“载”字之义。张平子《西京赋》“属车之簉,载猃猲獢”,张铣注:“猃、猲、獢皆狗也。载之以车也。”朱熹《诗集传》曰“以车载犬,盖以休其足力也。韩愈《画记》有骑拥田犬者,亦此类。”[16]朱熹训“载”为“乘”,并由韩愈《画记》中所记“以骑马者怀抱一犬”来证明“载犬于车”的合理性。后世从之者众多,如陈乔枞、牟庭、胡一桂、汪语凤、日本学者山本章夫等。但反对者亦有,如胡承珙《毛诗后笺》就曾指出:“《集传》又引韩愈《画记》为据,后世事恐难以证古。”[17]561胡说是也。此外,若如朱熹所说,把“载”释为“以车载犬”也与全篇诗旨及主题不符。从前两章内容可见,《驷驖》诗重在展示秦狩猎的强健、英勇体魄,若后一章陡转直下言猎后车马休息、猎犬乘车,或有讽刺之感,不若郑玄、孔颖达所释佳。
郑笺:“载,始也。始田犬者,谓达其搏噬,始成之也。”孔疏:“《释诂》云:‘哉,始也。’哉、载义同,故亦为始。”[8]484马瑞辰认为,“载”古训“始”……“始之”即“调习之”[18]369-370。此三人解释大同小异。胡承珙则进一步指出:“《西京赋》‘载猃猲獢’,语本在将猎之前,正与《诗笺》谓北园调习说合。后儒谓田事已毕,游于北园,以车载犬,休其足力。夫田毕而游,事所恒有,但不必更载田犬以从耳。或疑先言田猎,后言调习,文义不顺。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国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17]561此说可谓一语破的,解决了《驷驖》诗叙事手法的问题。
要之,从“游”无“田猎”之义,“闲”释为“练习、熟练”、“载”训“始,始成之也”可知,《驷驖》分属二事,前两章描述在囿中的狩猎场景,末章倒叙狩猎前于园中调习车马、猎犬之事。
简本将《驷驖》二、三章顺序颠倒后,全诗既可看作采用插叙手法,也可看作采用顺序手法。插叙是说简本将《毛诗》一、二章发生在囿中之事割裂开来,先说狩猎的装备和人物,中间插入之前发生在园中的调习车马一事,最后叙述狩猎结果——公于囿中“舍拔则获”。顺序是以“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一句为全诗的叙事中心句,如此,无论是狩猎前的装备、随从人物,还是狩猎前于北园练习车马猎犬,都可看作正式狩猎前的准备,只是时间远近的不同。
从诗旨的表达与诗意的理解出发,无论是《毛诗》的倒叙还是简本的插叙或顺序,似乎都能说得通。但是从诗的连贯性来看,当属《毛诗》章次顺序更佳。一方面,《毛诗》连贯了同一地点发生之事;另一方面,《毛诗》连贯了狩猎的行为与结果,即“狩”与“获”。
二、《绸缪》
《绸缪》三章,章六句。简本与《毛诗》二、三章顺序颠倒。
《毛诗》作: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安大简作:
早在1984年,王文君《从民俗学看〈诗经•唐风•绸缪〉》一文就曾提出《绸缪》章次错简,二、三章位置应互换,否则,既不符合上古乐歌演唱的定制,又违反了上古婚礼的一般习俗[19]。
安大简《绸缪》正好与《毛诗》二、三章顺序颠倒,但就此说《毛诗》二、三章错简还为时过早。《绸缪》章次可有三种情况:或从《毛诗》,或从安大简,亦或将各章都视为“构建模块”,章次顺序可有不同。具体属于哪种情况,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绸缪》诗旨问题
《绸缪》诗旨,从古至今,说法颇多,主流的说法有三种:
刺晋乱说。《毛诗序》:“《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也。”[8]454-456在诗序基础上,毛亨与郑玄的解释又有所不同。毛亨:“不得其时,谓不及仲春之月。”正义曰:“毛以为,不得初冬、冬末、开春之时,故陈婚姻之正时以刺之。”郑笺:“三星谓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昏而火星不见,嫁取之时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见其在天,则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见于东方矣,故云‘不得其时’。”正义曰:“郑以为,不得仲春之正时,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举失时之事以刺之。”[8]454-455
相得而喜说。朱熹《诗序辨说》:“此但为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词,未必为刺晋乱也。”[20]
贺新婚说。《诗经原始》:“《绸缪》,贺新昏也。”[21]《诗经译注》:“这是一首祝贺新婚的诗。它和一般贺婚诗有些不同,带有戏谑、开玩笑的味道,大约是民间闺阁新房的口头歌唱。”[22]进入现代诗歌研究阶段后,此说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姚奠中《释〈绸缪〉》中明确提出,“此诗应是歌咏新婚之诗。”[23]邵炳军、郝建杰《〈诗·唐风·绸缪〉诗旨补证》[24]、王文君《从民俗学看〈诗经•唐风•绸缪〉》[19]均赞同此说。
仔细梳理以上三种说法后可发现,“刺晋乱说”是宋以前的普遍看法,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相得而喜说”是在宋代理学兴起的背景下提出的,更注重从文本角度解读此诗;“贺新婚说”是在清代“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产生并流行起来的,得到了大部分现代学者的支持,并促使他们从民俗学、人类学的新角度去诠释《绸缪》一诗。
《绸缪》诗旨问题,难有定论,三说各有自己的立足点。考虑到《风》诗多为劳动人民生活的写实,而《诗序》的“美刺”二元论多为政治服务,脱离了原始的诗旨,因此,从文本本身出发,围绕《诗序》阐释得出的“刺晋乱说”不如“相得而喜说”“贺新婚说”有说服力。
(二)“良人、邂逅、粲者”所指
诗中先后出现了“良人、邂逅、粲者”三词,具体所指,历来有争议。
毛传从第三章的“粲者”训为“三女”出发,认为“良人”也应指向女性,释作“美室”[8]455。陈奂[9]284、胡承珙[17]527从之。郑笺则根据文献中“良人”多为古代妇女对丈夫的称呼,认为此处“良人”也不应例外,当指男性[8]455。日本学者竹添光鸿[25]从之。朱熹《诗集传》、陈子展《诗经直解》在郑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良人”指新婚之夫。“良人”一词在传世文献中即可称女性,也可称男性。“良”最早释为“善”,胡承珙《毛诗后笺》:“‘良’既训‘善’,则‘良人’男女皆可通称。”[17]527此说可从。《战国策》:“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良妇也。”[26]此“妇人”称“良”之证。“良人”一词还见于《诗经》其他诗篇,《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27]169“良人”为诗中从殉三位男子的代称;《秦风•小戎》:“厌厌良人,秩秩德音。”[27]166是妇人对自己丈夫的称呼语。
《毛诗》“邂逅”,韩诗作“邂遘”,敦煌伯二五二九作“解觏”,安大简作“矦”。韩诗及敦煌本在形音方面与《毛诗》可构成通假关系,《释文》:“邂,本亦作解。觏,本又作逅。邂觏,解说也。”[28《]淮南子•俶真训》:“孰肯解构人间之事?”高注:“解构,犹会合也。凡君臣朋友男女之会合,皆可言之。”[29]毛传释“邂逅”,“志相得”也,新婚夫妇情投意合。“邂逅”一词还见于《郑风•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邂逅相遇,与子皆臧”。毛传云:“邂逅,不期而会,适其时愿。”[8]375诗经研究者大多将《绸缪》“邂逅”译为“不期而遇(的人)”或“喜爱(的人),作名词,一方面符合“见”后接名词的语法,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一、三章的“良人”“粲者”相呼应。新出安大简“邂逅”作“矦”,[1]145刘刚认为当从简本,他表示:“简本反映了诗之原貌,胜于毛、韩二家。因为‘邢侯’作为名词,与‘良人’‘粲者’词性一致,可以充当动词‘见’的宾语,无需像‘邂逅’那样随文训释……‘良人’指一般民众,‘邢侯’为小国诸侯,‘粲者’当指代大夫。三者身份层层递进,所以简本把‘邢侯’章的次序放在最后。”[30]网友“汗天山”对此持不同看法,他指出,“邢侯”仍当读作“邂逅”,因“邢侯”指具体的某个人或某类人,使得主角在同一诗篇中出现了不止一位,似嫌重复[31]。此说可从。《绸缪》作为一首婚嫁诗,蓦然出现一类具体的人,即刘说之“小国诸侯”,显然于诗不类。“邢”匣纽耕部,“邂”匣纽支部,音近可通;“侯”匣纽侯部,“逅”匣纽侯部,音同可通。因此,简本“邢侯”就目前来说,释作“邂逅”是最佳的。
至于《毛诗》第三章的“粲者”,《广韵》、《玉篇》均释“粲”为“美好貌”,“粲”古字作“ ”。《说文》:“三女为 , ,美也。”[15]622可知,此字多形容女性之美。“粲者”于《绸缪》诗中指女性,即新婚之妇,历来无争议。但刘刚为了使安大简“邢侯”为“小国诸侯”的解释说得通,从毛传释“粲者”为“大夫一妻二妾”出发,指出本词的重心在“大夫”,而不是“一妻二妾”,从而认为“粲者”指代大夫[30]。这一解释未免过于牵强。
要之,《绸缪》一诗中,“粲者”指代新妇,“邂逅”指向新婚夫妇二人,若将“良人”一词释为“美室”,继续指新妇,则与“粲者”重复,全诗缺少重要的主人公新郎。且毛亨将“良人”释为“美室”,是从后句“三女为粲”这一解释出发的,目的是将全诗叙事主人公统一为新郎,以表达不能在良时娶妻的无可奈何,从而附和《诗序》的“刺晋乱说”。但从“良人”一词在《诗经》中的常见解释和保持全诗协调性出发,将其看作对新郎的称呼似乎更加允洽。据此,也可进一步看出“刺晋乱说”的不合理性。
(三)“子兮子兮,如此……何”句式之义
“子兮子兮”句中,“子”分别对应“良人”“邂逅”“粲者”,马瑞辰:“此诗设为旁观见人嫁娶之辞,‘见此良人’,见其夫也;‘见此粲者’,见其女也;‘见此邂逅’,见其夫妇相会合也。”[18]346因从古无自称“子”者,所以第一章的叙述者或为妻或为旁人;第二章的叙述者只能是旁人;第三章的叙述者或为夫或为旁人。考虑到全诗的统一性,叙述者为旁人的可能性更大。这就不免联系到“贺新婚说”,“旁人”即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如何”在《诗经》中多释为“奈何”,但《绸缪》一诗的“奈何”不是表达无可奈何之感,而是旁人对新婚夫妇的戏谑之词,“你呀你呀,看你拿这个夫君/美妻怎么办?”“你们呀你们呀,看你们这对恩爱夫妻怎么办?”
王文君认为,按照贺婚习俗,客人们应该是先提及夫或妻,最后才会提到夫妻二人的,再从《诗经》音乐中的“乱”章出发,也可证二、三章错简[19]。《诗经》作为合乐的歌词,诗、乐、舞本为一体,孔颖达云:“诗为乐章,诗乐是一。”[32]《诗经》乐曲有“乱”,可证之古代文献,如《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33]何谓“乱”,主要有五说[34],其中阴法鲁从艺术创作的心理层面剖析,认为“乱”位于一首诗的卒章,从文字上来说,是歌词的主题部分;从演奏上来说,是音乐和舞蹈的高潮部分,往往采用合奏的方法。他指出:“把‘乱’安排在作品的末尾,一方面企图使人们当时得到艺术欣赏的最大满足;一方面企图给人们留下一个深刻的鲜明的最后印象,长期缭绕在记忆里,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35]阴法鲁对《诗经》“乱”的解释,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同。《绸缪》诗中,众人对新婚夫妇情投意合的赞美和戏谑一章,即《毛诗》第二章,相较于其他两章,是全诗的高潮,用来表达众人对新人喜结良缘的美好祝福,可以看作是“乱”章。但也不排除全诗无“乱”章,因三章同属祝福之语,章序变化后只是祝福对象出场顺序不同了而已,对诗旨与诗意影响不大。
要之,若从婚俗和《诗经》音乐的“乱”章来看,简本章次顺序确实更加严密,较《毛诗》略优。但因诗、乐早已分离,我们目前无法获知《绸缪》篇的音乐,自然也不能轻易否定《毛诗》章次顺序存在的合理性。
三、小结
安大简与《毛诗》除章次方面有不同外,在词句、用字方面也存在大量异文。黄德宽曾指出,安大简《诗经》异文为战国时期《诗经》的流传和语言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汉语史、文字发展史和《诗经》学等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2]。安大简的出现,无疑为我们研究《诗经》提供了更多新角度、新材料。相信通过简本与《毛诗》的对比研究,《诗经》史上一些长期的疑难问题也将得到进一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