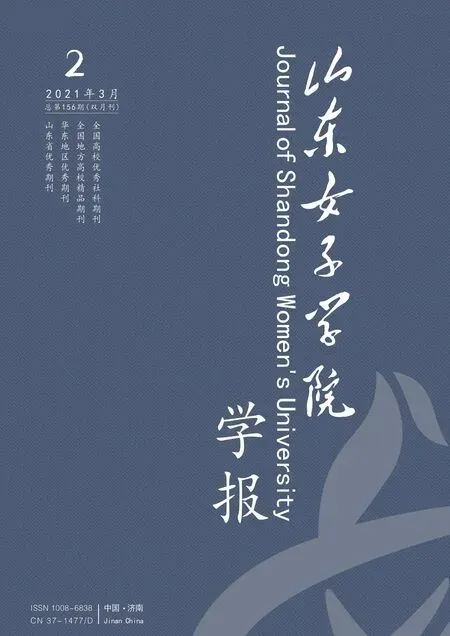女性体育电影:女性身体建构与现代性表达
李 月,李 攀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在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电影创作格局日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体育电影开始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就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历史来看,从1934年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女篮5号》(1957)、《排球之花》(1980)、《沙鸥》(1981),再到2020年的《夺冠》(原名“《中国女排》”)、《李娜》,女性运动员成为我国体育电影中常见的重要形象。女性身体作为女性体育电影最为重要的表达手段,在近百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由不同历史阶段所决定的现代性内涵。本文通过对女性体育电影的历史性分析认为,电影中的女性身体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性表达的重要媒介。
一、白话现代性:身体的对象化与都市摩登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含义丰富的概念,“从概念所涵括的范围来说,它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它就已经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再从空间的广度而言,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争论,也早已超出欧美的西方世界,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1]1从概念产生的历史来看,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代表,他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大力宣扬“理性”与“自由”,这被福柯视为“现代性态度的纲领”。黑格尔则在康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性作为世界的本质并且为自由寻找现实基础(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对现代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性的理性化特征、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对立与冲突、现代性作为一个世界祛魅的过程,以及现代性导致的诸神不和与自由的丧失等结果的分析与论断上”[1]96。福柯则“从疯癫、监禁、性等历史事件的考古学调查与系谱学研究,来解释现代社会的规训性质”[1]187。吉登斯从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制度与传统关系等角度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制度性的转变,哈贝马斯则有“现代病理学理论”……由此可见,关于“现代性”概念的论述是从哲学的宏观层面逐渐深入到了世俗微观层面。马泰·卡里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将“媚俗”确定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且主要用来指涉现代性的世俗内涵[2]。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则将涉及日常、平庸层面的社会现实称为“白话现代性”(vernacular modernism)或“白话现代主义”,并且身体被其视为这种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3],而中国早期的女性体育电影正是通过遮蔽女性主体意识的方式将女性身体构建为被男性所凝视的对象,展现着这种新兴的现代性内涵。
1934年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问世。在这部反映“孙瑜的进步”[4]的影片中,黎莉莉饰演的来自乡村的女孩林璎在摩登上海的运动场与舞厅之间往返,当身体在这两种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空间中穿梭时,健康充实与颓废堕落的能指也在不停转换。张真在分析《体育皇后》中林璎所经历的身体旅行时指出:“女孩们在宿舍、跑道或是舞厅里面炫耀年轻的大腿——电影中频繁出现的这些夸张镜头,表现了女运动员们身体中所蕴含的活力和摩登性。”[5]正如米莲姆·汉森提出的,“随着摄影机对体育活动及健康体质的强调,明星的身体,包括身体的局部,不管化妆与否,都成为视觉快感和形象展示的特享区域,从而提供了一系列欲望的中转”[3]。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张真与米莲姆·汉森的观点就会发现,二者都认为在《体育皇后》中林璎的身体无法避免地成为了欲望的对象,而这种欲望在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看来显然是来自男性。在她看来“女人作为形象,男人作为看的承担者”[6],女人始终处在被“凝视”(gaze)的地位。这种将女性身体客体化的观看模式在张真与汉森的分析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前提:镜头对身体的强调。《体育皇后》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场景,林璎为了去观看花花公子胡少元的比赛而精心打扮,林璎精心挑选了一件旗袍,并且在镜头前大方展示自己年轻的大腿。在这个场景中,大腿显然是作为视觉中心而存在的。虽然孙瑜想通过本片传达“体育救国”的理念,但是在上海的都市消费语境中,很难避免观众对于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习惯。林璎充满活力的女性身体在影片中事实上归属于以胡少元为代表的男性群体。
在《体育皇后》中,林璎的身体除了作为一种现代性视觉对象之外,其身体旅行所串联起的上海都市摩登空间也让其承担了现代性展开线索的作用。影片中上海外滩、高档餐厅、舞厅、汽车等现代性景观在事实上为银幕前的观众构建了一个摩登都市的视觉意象。通过身体运动,一种都市摩登文化在影片中浮现出来。林璎在取得成功之后沉迷于物质享乐,影片展现了林璎庆功宴装修奢华的高档餐厅、舞厅等空间,尤其是舞厅,更是上海摩登都市文化的重要表征。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专门研究了上海舞厅的现代性内涵:“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经常出入那些头等舞厅和有歌舞表演的卡巴莱,像华懋公寓顶楼、国际饭店的天台、百乐门戏院和舞厅。”[7]所以对于当时的上海市民而言,舞厅同电影院一样属于现代性空间的典型代表,跳舞本身就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社交方式与生活方式。1932年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对舞厅与跳舞有着极具现场感的描绘: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萨克斯)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舞着,华尔滋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滋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
从这些意象化的描写中不难感受到现代都市生活给人带来的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特殊感受。林璎的身体就如同一条连接线将混杂(hybrid)状态的都市空间与身体实践串联在一起,共同向观众构建起一道都市世俗生活的风景线。在丹纳看来,“要了解一件艺术品……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8]。《体育皇后》诞生的时代正值国民党政府的“大上海计划”(1)1929年7月,上海市政府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划定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的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及周南十图、衣五图以西的土地约7000亩,作为新上海的市中心区域。8月,成立了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以后由该委员会陆续提出了市中心区域的分区计划、道路计划,黄浦江虬江码头的建造计划,以及上海市分区和交通计划等。这些计划构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大上海计划”,也称“大上海建设计划”或“新上海建设计划”。建设时期,道路、体育场、图书馆、医院等现代建筑不断涌现,这些现代性空间的出现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世俗生活的发展,二者不可分割。所以,如果将《体育皇后》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时空坐标中就不难发现,林璎的身体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国)现代性内涵的重要索引,通过对其身体表象与内涵的梳理与挖掘,一种白话世俗的现代性维度浮出水面。
二、革命现代性:身体的规训与惩罚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革命”(Revolution)本身就可以被归纳到“现代性”的范畴之中,尤其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来说,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革命”甚至构成了本土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正如“现代性”一样,“革命”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指涉。《易经》中讲“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这里所谓的“革命”其基本含义是以暴力手段实现改朝换代,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话语的主流逻辑。英文“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运动,后来与“revolt”(叛乱)词根相同而产生出政治含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表征出和平与激进两种不同的革命模式。陈建华则认为,“革命作为一种话语形态,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数年里才出现的”[9],作为一种本土语汇,它的复活“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日语的翻译,也即受了某种西化的洗礼”。从历史实践来看,不论哪种意义上的革命,其所涉及的范围都非常广泛,绝非仅限于政治领域。其中,“身体革命”通常是“革命”的重要表征。“身体革命”不仅意味着社会审美风尚的转变(如裹足与放脚),同时更是一种政治宣示(如蓄辫与剪辫),所以身体作为革命话语实践的重要场域,通常被加以修饰和改造以配合革命进程。而且,当剧烈的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之后,革命逻辑自然将由外转内,聚焦于革命群体内部身体与思想的改造与控制,而这也就构成了本文意义上革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当然革命现代性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身体既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对象,也是民族国家自身的隐喻。”[10]33一个国家人民身体的强弱往往与国家自身的力量大小相联系。按照历史规律来看,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塑造强健的形象,战争和体育是两种常用途径,二者之间在深层逻辑上互通,“体育竞技是国家间象征性的对抗,军事冲突则是国家间事实性的对抗……当军事和战争行动尚未获得恰当机缘的时候,人们发明了体育竞赛,以此来替代性地满足征服和战斗的欲望”[10]36。所以,对国家或民族来说,体育赛场上的身体对抗通常很容易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这种身体—国家的喻指关系同样也延伸到电影创作领域,一些体育题材的影片往往通过再现或想象的方式来完成民族认同感的提升。个人身体对国家而言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这不仅体现在形而上的象征层面,而且体现在最细微的社会活动中。国家对身体进行着最为细致的管理与控制以生产出符合要求且被规训的身体,同时国家还发展出一系列对于身体的惩罚技术作为最终实现驯顺身体的保障,其最终目的就是“制造有用的人和有用的个体,并服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11]28。
1957年谢晋导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彩色体育故事片《女篮5号》问世,影片主要讲述了两代篮球运动员在新旧社会中不同的生命轨迹。片中主角林小洁在教练田振华的教育下,转变观念,最终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国争光的篮球运动中去。在《女篮5号》中谢晋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构建出了对于林小洁等人身体进行规训与惩罚的有效体系,而最终效果也正实现了对林小洁身体的规训,其身体的现代性特征也最终被革命话语所编码。影片中对于女运动员的身体规训体系首先表现在女队员们在比赛登记处测量身体指标,正是在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测量中,“身体成为国家权利的焦点,成为国家目光紧盯着的对象”[10]34。通过这种对身体指标的测量与登记,女队员们相关的身体数据(身高、体重、年龄)、技术特点等被记录下来,这些数据既能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教练进行配置的直接参考,同时又能帮助其在整个团队系统中获得相应的位置分配。为每一个身体确定具体存在的位置是确保国家权力控制身体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被登记、检测过的身体才能在国家机器运作的时候被检索和调用,所以看似不起眼的入队体检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微妙的政治意义。其次,住宿空间的分配是影片关于身体规训系统的重要手段。女队员们所居住的集体宿舍一方面是能够确定身体所在的空间坐标,另一方面还是福柯(M·Foucault)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具象化。在这个杜绝了私密性的集体空间中,每个人都实现了一种最为直观、彻底的相互观看,虽然这种观看往往是非刻意的,但是对于置身其间的人会产生心理上微妙的暗示与强化,即每一个人都是被镶嵌在固定的位置上,“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12]162,从而保证整个集体的和谐运作,这一运作逻辑在处理林小洁与汪爱珠之间床铺纠纷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从林小洁的角度来看,对床铺选择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个人任性而为,更是在进入集体时,面对身体归属问题时的焦虑潜意识(对于身体的焦虑则更是现代女性所面临的重要生存问题,在这一点上《女篮5号》更具有相当的现实启示)。正如列斐伏尔(Lefebvre)所讲,“空间看起来好似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13],影片中的女运动员宿舍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身体进行长久规训的空间,但是颇为吊诡的是宿舍窗外却是上海的高楼大厦,这或许也体现了谢晋导演潜意识中将现代性与革命性相对接的尝试。再次,影片中关于篮球技巧的身体性练习以及比赛场上的身体对抗也是一种精确的规训手段。女队员们在田振华的指导下在运动场上跳高、练习移动脚步、演练战术等行为都是对身体动作的精确规定,在这种不断重复的练习中,“身体、四肢和关节的位置都被确定下来。每个动作都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连接也预先规定好了。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12]11,与身体形成肌肉记忆一起形成的是对这种身体控制技巧的认同。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权威的存在是这一规训系统能够有效运行的主要保障。
惩罚系统是当规训系统受到越轨身体挑战时保持效力的重要手段。在对身体的惩罚上,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着明显区别,后者常诉诸各种肉体惩罚技术,而现代社会的惩罚体系则带有明显的非身体性特征,虽然这种惩罚仍然是以身体为最终目标。在现代社会,“惩罚的对象不再是身体,而是灵魂。惩罚不再是折磨身体,而是改造灵魂;不再是消极地否定,而是积极地干预;不是镇压,而是疗救”[11]29。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现代社会惩罚特征的相关论述与《女篮5号》中的身体惩罚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刑罚中,“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刑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力的经济机制”[12]11。在《女篮5号》中林小洁因不能首发出场而闹情绪,队友汪爱珠因前嫌而隐藏了林小洁留给队长的请假纸条并最终导致林小洁没有及时赶上与工人队的比赛,田振华无法容忍林小洁这种不遵守纪律的行为,即使在下半场在球队处于被动时也坚持不让林小洁上场,最终球队输掉比赛。在此,不难发现作为团队权威的田振华为了维护团队纪律所施加的惩罚,也就是田振华剥夺了林小洁的比赛权利。林小洁坐在场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队一点点地输掉比赛,赛场上一分一秒的时间对林小洁来说都是煎熬,这正表现出了影片中存在的身体惩罚体系的具体运作:由集体权威所发起,剥夺个体作为群体构成的权利的同时作用于个体内在的道德体系,内疚与自我谴责是其常见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谢晋所构建的惩罚系统“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充满策略地运转”[11]29,其最终目标不是损毁而是疗愈(林小洁焦虑情绪最终被解决),这实际上也正应对了现实政治中有关革命性的身体政治逻辑。《女篮五号》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它的出现实际上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该片创作始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所以从题材上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林小洁作为一名女性运动员的银幕形象在当时银幕上占据主流的工农兵形象中也带有很大辨识度。同时谢晋对林小洁采取的福柯式的形象建构,同时也是在创作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松动的情况下一种既往文艺为政治服务创作逻辑的习惯性延续。所以《女篮5号》在历史时空中体现了一种时代要求与个体偏好之间的对话、协商关系。《女篮5号》在展现革命现代性的历史主调的同时,实际上也潜在地涌动着个体表达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最终将随时代的发展迎来释放的历史机遇。
三、启蒙现代性:自我身份的认同与构建
“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1]4。在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Kant)看来,所谓的启蒙(enlightment)就是使人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陈嘉明认为以消除蒙昧、开启民智为目标的启蒙运动是由理性主义精神与自由主义思想这两大支柱共同构成的。理性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一种“自我认识”的能力,即笛卡尔式的“我思”,这逐渐被演绎成为对某种权威、传统的怀疑乃至挑战,韦伯(Weber)称之为“祛魅”(disenchantment)。自由主义思想认为人的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并且这种思想后来被表现为一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其在处理个人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为个人的生存空间提供了理论依据。个人主义实际上与自私自利无关,它的精神实质是“以人为本”,在个人与国家、集体的二元关系中,个人主义伸张个体理想、追求个体自我实现,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个体理想不是由宏大崇高的国族理想、需求所召唤的,而是个人自身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自然生发出并与崇高国族理想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体育电影的梳理不难发现,在如《沙鸥》(1981)、《夺冠》(原名“《中国女排》”)(2020)、《李娜》(2020)等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中,女性身体具有了新的现代性意义,这些女性身体实践在承担民族理想的同时,还构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整个思想领域开始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在电影领域则体现为一种“伤痕”创作风格,而这种伤痕风格自然也延续到了体育电影的创作中。1981年由张暖忻导演的电影《沙鸥》以“文革”后重新投入到排球事业的女运动员沙鸥为主角,表现了沙鸥为了参加“文革”后第一次国际锦标赛不顾伤病而努力拼搏的励志故事。与《女篮5号》中的林小洁不同,沙鸥是经历过“文革”之后重新走上了排球赛场,其对于排球运动的热爱与执着不仅是出于国家荣誉感,更是有着其自我实现的必然要求。排球运动对于沙鸥来说是其社会身份获得的现实保障,所以沙鸥即使面临着全身瘫痪的风险也不肯放弃排球运动,因为对沙鸥来说只有将身体全部投入到排球运动中去才能治愈十年空白所造成的“自我认同焦虑”。影片中多次展现了沙鸥刻苦训练的场景,始终保持运动的身体成为对曾经失去的自我身份进行追寻的重要媒介。沙鸥的形象可以说是代表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整个失落的群体对曾经自我身份认同的重新构建,其身体实践更具有了明显的个体意识,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国家荣誉而奋斗,更是为了证明自身价值和抚慰心理创伤。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经对历史进行反思、对伤痕进行治疗的身体实践也发生了明显转向,女性身体开始摆脱历史的负重,更加轻松地面对自我需求。新时代的女性体育电影中的女性身体开始呈现出新的启蒙性质。与《沙鸥》中从历史困境中挣扎出来而伤痕累累的身体不同,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为现代身体构建提供了一个宽松、开放、多元的实践空间。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女性身体成为《夺冠》《李娜》这类影片的主要视觉意象。《夺冠》虽然也是以中国女排为创作题材,但是与《沙鸥》不同的是,片中主人公不再纠缠于历史伤痛,而是以自我价值实现为重要目标。影片在表现女排运动员的日常训练以及世界大赛的场景时,将女性身体实践构建为一种青春热血式的自我实现。这种强烈表达欲望的原动力并非来自于外在苦难或挫折,而是青春躯体自然生发出的生命能量。片中白浪饰演的青年郎平与中国国家女排运动员朱婷构成了一种拉康式的“镜像”关系,但与以往体育电影中的镜像关系所不同的是,《夺冠》中的身体归属已经发生了质变。在《女篮5号》中,身体最终经过规训被国家所征用,而在本片中,女排运动员能够大声喊出“为自己打球”的口号,并且郎平对她们而言不仅是为国家荣誉奋斗的英雄,更是个人想要触及的未来。自我权利意识由《沙鸥》中的萌芽与潜意识形态发展为《夺冠》中的显在形态。影片中女排运动员经年累月的训练,身体一次次地冲击极限实际上正迎合了当前年轻人的生命观。她们不再徘徊、迷茫于历史的漩涡,而是自始至终都有着明确的生长方向。而且尤为可贵的是,跃动的个人身体不仅没有成为挑战主流权威的叛逆力量,反而与之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对话关系。个体理想与国家荣誉在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个人身体与国家身体之间的张力关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可以说,从《体育皇后》到《女篮5号》再到《沙鸥》,始终存在的个人身体观的悖论在《夺冠》中获得了更为宽阔的讨论空间。
如果说《夺冠》因为其排球的群体性运动而依旧存有集体对个体进行编码的话,那么对另外一部以女子网球为表现题材的影片《李娜》而言,片中的女性身体有更为彻底的个体身份认同与建构冲动。影片以我国著名网球运动员李娜的运动生涯为线索,重点展现了李娜成名前的艰辛付出与情感线索。从影片几个重要时期李娜的情感状态中不难看出,影片重点将李娜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而没有将之塑造为为国争光的英雄形象。李娜在少年时期被父亲送去学网球,这在李娜看来是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未完成的理想的无奈之选。而十年后的李娜则将网球视为自己最大的梦想。片中李娜在不同的时空中留下孤独训练的身影,身体不断地挑战极限,但她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不再是国家理想和民族荣誉,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是她前进的动力。如果说《夺冠》展现了青春的活力热血的底色,那么《李娜》则展现了青春的另一种底色:孤独。所以影片中提到,“人们往往以为走自己的路是最容易的,恰恰相反,因为这是一条最孤独的路”。在具体身体写作的呈现中,影片没有过度展现人物近景或特写,而更多是以远景展现李娜在夜晚的训练馆、在雨中的网球场等孤独的时空间的身体存在。巫鸿(Wu Hung)在《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中提出了“女性空间”(feminine space)的概念,将女性空间理解为“以建筑、氛围、气候、色彩、光线、气味、声音和精心选择的居住者及其活动所营造出来的世界”[14]。通过采用巫鸿的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李娜》中的场景空间而言,这种女性空间是由运动的单个女性身体与空旷的环境(训练馆)、非常态气候(雨夜)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女性身体则是这种孤独女性空间唯一活动的视觉形象。对比性的视觉设计强化了人物内心的心理活动,空旷的现实空间造就了充实的心理空间,独自训练的身体实践强化了人物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人物能够更多地思考自己努力训练所追求的价值与意义。与《夺冠》的最大不同正在于此,《李娜》通过展现身体的自我放逐而为人物提供了更多个体性思考。从启蒙现代性角度来看,《李娜》无疑有着最为强烈的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冲动。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改革开放对社会思想领域产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莫过于思想的巨大解放,而这种大解放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集体与个体关系的重新定位。从《沙鸥》到《夺冠》,个体自我实现的渴望逐渐显扬,这也正是对这种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的具体回应。沙鸥、女排群像、李娜等银幕形象不再被塑造为一种承载集体理想的体育迷思,而是具有更明确个体诉求的自我启蒙者,而这种人物塑造范式转型背后体现的是新时期、新时代到来的历史性变革。
四、结语
从《体育皇后》到《女篮5号》,再到《沙鸥》《夺冠》《李娜》,不难发现在近百年的女性体育电影的创作中,女性身体不仅仅是活跃在训练场上的视觉对象,更是现代性内涵在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具体展开。女性身体成为现代性书写的重要媒介,从最初作为被凝视的客体,到被革命话语所改造的对象,再到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女性身体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演绎着现代性历史书写的不同阶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体所经历的重要变化,从曾经被消费的视觉快感而逐渐成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这一方面体现出随着历史进步所产生的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女性身体中所展现出的现代性内涵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脉络。从林璎到李娜,自我实现的个体诉求变得更加明确、合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体育电影中的女性身体不仅仅是女性命运的写作支撑,更是能够映射近百年中国现代性发展内涵的多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