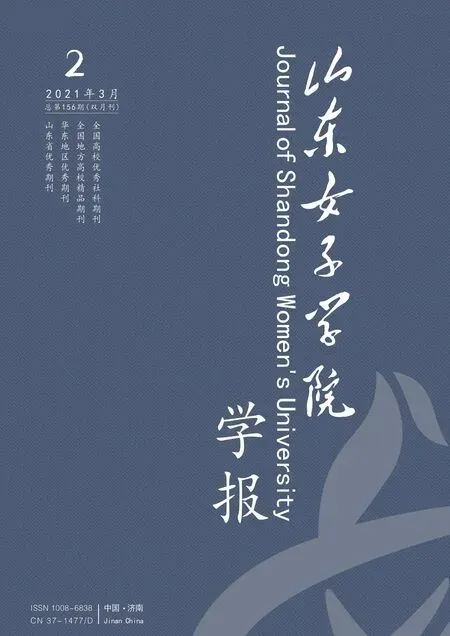创伤、记忆和超越:论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创伤叙事
于春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一、引言
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于1940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是美国华人的二代移民,也是华裔美国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1976年,汤亭亭出版其处女作《女勇士》(TheWomanWarrior)。此书一经出版,便获赞誉无数。《女勇士》中汤亭亭以非线性拼贴的方式将母亲讲述的故事和过去“我”自身的经历和见闻,以及东西方神话的改写融入本书,包括“无名女子”“白虎”“巫医”“西宫外”“胡笳怨曲”五个彼此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故事。因为书中情节多取材于旧中国社会,出版社为迎合西方读者东方主义趣味,增加销量,将《女勇士》列入“自传”类别,出版当年,此书就问鼎美国全国书评界非小说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Nonfiction)。对《女勇士》学术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于东方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身份方面的讨论。学者詹妮弗·格里菲斯(Jennifer Griffiths)曾说:“《女勇士》还继承了从创伤遗产中获得的艺术视角的发展。”[1]
通常来说,创伤记忆理论多用于精神分析,尔后有学者将其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分析创伤记忆对个人和集体文化身份建构的作用。近年来,创伤记忆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汤亭亭作为早期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再现了美国华人创伤记忆的形成、传递和超越。自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实施后,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被孤立了半个多世纪之久。长期的“隔离”不仅造成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华人发声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美国主流文化中已经建构起蔑视华人的话语霸权。之后,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的话语霸权在历史语境中不断强化并日渐强大。事实上,“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的写作”[2]。汤亭亭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即是通过对个体、家庭和社会记忆的回溯,重现了以“我”为代表的美国二代移民的精神创伤,不仅具有文学研究的意义,还兼具跨文化研究的价值。
对于《女勇士》中的创伤叙事研究,国内已有相关探讨。其中胡小玲2013年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女勇士〉的创伤叙事论略》一文最具代表性,它指出汤亭亭以隐喻的叙事策略将不可叙述之事进行描述,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式叙事策略,颠覆了传统女性形象[3]。整体来说,国内对于《女勇士》的创伤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身份的解读,尚有许多研究空白。本文将借助创伤记忆理论,从创伤的代际传递、创伤和身份危机、创伤和文学创作三方面解读《女勇士》中主人公“我”的创伤。
“创伤”一词的基本含义为身体或精神受到的破坏或伤害,“既可以指代有形、显性的创伤,也可以指代无形、隐性的创伤”[4]。最初,创伤属病理学范畴,后发展为精神病学术语。弗洛伊德对“创伤”的定义如下:“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5]卡鲁斯(Cathy Caruth)在她的经典著作《无主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中给出的“创伤”定义是:“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个体原有的经验被覆盖,对这些事件表现出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意识的现象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反应”[6]。结合学界对于创伤的论述,创伤可大致分为性别创伤、种族创伤、历史创伤和文化创伤四种。在《女勇士》中,这几种创伤彼此交织、难以割裂。杰弗瑞·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在《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论文集中就曾提出,“创伤并非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社会建构的”[7]。在《女勇士》一书中,主人公“我”的创伤也并非生来就存在和被感知到的。随着“我”不断成长和对家庭记忆的深入了解,在社会环境的挤压和社会观念的浸染下,“我”的创伤开始形成和深化。
二、创伤的代际传递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常把自己经历范围之外的事物也纳入自己的感知之中。换言之,“记忆不仅充满了个体对自己经历的事情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回忆”[8]12-13。《女勇士》的开篇以母亲英兰的叙述开场:“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9]3母亲向“我”讲述了“我”的一个姑姑的故事,这个姑姑的名字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所以在文中被“我”称为“无名姑姑”。在丈夫漂洋到美国数载后,无名姑姑与人通奸,怀了身孕。村里人深知此事有辱民风,于是强烈谴责姑姑的通奸行为,他们在姑姑临盆之际,闯入“我”的老家,大肆破坏,宣泄不满。最终,姑姑在猪圈中诞下了腹中的婴孩。翌日清晨,母亲井边打水时,发现了井里无名姑姑和婴儿的尸体。承受了太多世俗的白眼和责难,无名姑姑的心灵遭到了重创,走投无路而被迫投井。这份折磨人的心灵创伤,给“我”们家族也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自此之后,“我”们全家“当她从没来到这个世界上”[9]5。
多利·罗伯(Dori Laub)曾提出创伤事件见证的三个层次:“第一层,经验之内自身的见证;第二层,对他人证词的见证;第三层,对见证过程本身的见证。”[10]也就是说,第一层次主要指个体经历创伤事件,获得经验;第二个层次可以指讲述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受众即听者追随幸存者的讲述,重新经历创伤事件;第三层次的见证则重点落在了“我”自身作为听者,获取经验并寻求真相的过程。无名姑姑的遭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男权社会观念对于女性的恶意和迫害。在姑姑的故事中,母亲英兰既是性别创伤的幸存者,又是家族创伤的亲历者。在无名姑姑的创伤事件中,母亲英兰首先是第一层次的见证者,她见证了姑姑的离经叛道之举和令人不胜唏嘘的结局。在此基础上通过向“我”转述,将他人创伤经历及自身创伤经验传递给“我”,实现了第二层次的见证。“你现在已经开始来月经了,你姑姑的遭遇,你也有可能遇到。你可千万别给我们丢脸……镇上的人都眼睁睁盯着你呢。”[9]5母亲的教诲看似向女儿灌输了规避社会唾弃的行为规范,实则强调了男性权威对“我”的约束。母亲通过叙述,让“我”了解到旧中国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卑微,“我”意识到“在饥荒年月,生为女人,生个女儿,就已是十足的浪费”[9]7。而且母亲在叙事中数次强调“别对你爸说我告诉了你这些”[9]5,由此可见,在这个家庭中,父亲是绝对权威,母亲身为女性则沦为男性权威的附庸。在“父亲—母亲—女儿”的三人关系中,母亲成为父亲意志管控“我”的帮凶,而没有为女儿“我”争取更广阔的话语空间和发展自由。母亲对于姑姑投井丧生的寥寥叙述并未实际还原姑姑悲剧的全部事实,从而将“我”引入了一系列的设想和推测中。“我”想象姑姑是一个“野女人”[9]11,但是很快又被自己否定,在“我”的想象中,姑姑最多是一个“爱打扮”的女人,而“女人爱打扮,就会落下不守妇道的名声”[9]11,最终她对美的追求招来了男人的目光,埋下了送命的祸根。无论如何,在“我”的各种设想中,姑姑的所作所为都不至于让她付出被千夫所指、自绝性命的惨痛代价。“我”还设想,如果姑姑生下的婴儿是一个男孩,那“倒还有被宽恕的希望”[9]17。姑姑投井,母亲重述,“我”的演绎,实现了对这一创伤事件三个层次的见证,而上一代遭受过、见证过的创伤也经叙述传递到了“我”的身上,“姑姑的亡灵纠缠着我——她的魂附在我身上”[9]18。
学者王欣认为:“创伤记忆通过见证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传递给下一代。结果是,从未直接经历过创伤的个体或集体继承了死去已久的先人的创伤回忆。”[11]57在无名姑姑的故事中,似乎不检点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也间接成为“我”和母亲英兰受创的原因。实际上,从宏观层面来看,无名姑姑的悲剧深植于中国旧社会男权压制的大环境中。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女性话语丧失,被迫消声。这在文本中体现在:一方面,母亲对“我”讲述的故事是父亲不能知道的秘密,母亲不仅向“我”传递了姑姑事件承载的创伤,更警示了“我”要沉默;另一方面,整个故事没有姑姑说过的只言片语,即使是在讲述者的设想中,姑姑也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形象,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作为“家族之耻”,甚至连名字都不能被提及。开篇母亲讲述的无名姑妈的故事成为“我”性别创伤的萌芽,也成为“我”家庭记忆中创伤的一部分。
《女勇士》一书的副标题为《一个生活在群鬼之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鬼”是中国传统鬼神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在书中“我”对于“鬼”的观念的了解,源自母亲给“我”讲的鬼故事。在母亲的故事里,中国社会里有形形色色的鬼:墙头鬼、替身鬼、溺死鬼、吊死鬼、口袋鬼……林林总总,名称各异。在《巫医》一章中,母亲英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医科学校求学时组织同学们与“压身鬼”搏斗的经历,不仅如此,她还向“我”讲述了鬼如何附体在婴孩身上等,这些在“我”看来简直荒唐的超自然故事,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而母亲讲的鬼故事“常进入我梦中——那些婴孩反复出现在我的噩梦中……”[9]96在弗洛伊德的定义中,噩梦是主体遭受创伤的重要表征之一,“我”在噩梦中多次经历创伤,相信自己生活在“群鬼”之中,这些鬼是中国来的,“那些梦是用中文做的,中文是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的语言”,“我清醒时的生活像美国人生活那样正常”[9]96。母亲给“我”灌输的鬼故事和鬼怪的观念,成为“我”文化创伤记忆阐释的基本框架,在“我”看来,“中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中国文化是丑陋的梦,是令人费解的语言,是扭曲的生活”[12]。创伤记忆的框架“解释了故事中人物行为的动机”[11]186,在文本中,“我”对中国文化很难形成认同感,由此铺垫了“我”对于接受美国社会文化的转向,但是,在“清醒”的美国社会中,“到处都是机器和鬼——的士鬼、巴士鬼、警察鬼、灭火鬼、查表鬼、剪树鬼、杂货店鬼”[9]135。美国在“我”看来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鬼国家”,“我”在社会生活中迷惘、失落和无所适从。由此可见,母亲传递给“我”的关于鬼神的创伤记忆,使“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鬼和异端的世界中,“有时候我讨厌洋鬼子让我们不能说实话,有时候我讨厌华人那样鬼鬼祟祟”[9]202。“我”在中美两种社会文化中无从选择,找不到文化根基。
在《女勇士》中,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主要有以下特点:(1)代际传递主要依靠母亲向“我”讲述的方式进行,成为“我”家庭记忆的一部分,“我”在家庭记忆的阐释框架下展开思考,赋予“无名姑姑”和“鬼”以创伤意义,成为“我”创伤记忆中的基本叙事原型,并在脑海中固化。(2)倾听者“我”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母亲传递的家庭记忆,通过相关的材料进行补充,丰富了讲述者所提供的信息,比如“我”在母亲给“我”讲过“戏蹬鬼”后,主动查阅中国人斗鬼的资料,书中呈现的故事加深了“我”的创伤体验。母亲的创伤证词触发了“我”的创伤经历,加深了“我”所恐惧的性别创伤,并促成了“我”在两个“鬼国家”进行文化认同的意识分裂,突出了文化创伤对“我”的伤害。
三、创伤和身份危机
创伤记忆“成为家庭中时代的重要内容,成为下一代身份构成和自我认识的重要部分。”[11]180无名姑姑的故事给“我”笼罩了家庭和时代的阴影,而月兰姨妈的故事让“我”开始意识到自身身份的挣扎。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曾讨论了记忆的基本区别,他定义了“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两个概念。他认为:“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13]43《西宫外》一章讲述了月兰姨妈首次造访美国的经历。在之前的三十年里,她都是靠在美国当医生的丈夫定期汇款度日。许多中美文化的差异都在月兰姨妈的故事里被呈现和放大。英兰与子女和外甥女在机场接从中国漂洋而来的妹妹月兰,外甥女只要看到门一打开,就大喊“妈妈”,这一举动“让她的美国表姐表弟都不好意思了”[9]129。英兰让自己的孩子也一起喊姨妈,可他们害羞地急忙溜走,如叙述者所言,“大概这就是美国式的教养吧”[9]130。外甥女出生于中国,生长在中国,五年前才来到新大陆美国,她的身上渗透了“中国式”的教养,母亲在此处也代表了“中国式”家长的形象,而“我”和兄弟姊妹们接受的是西式的社会教育,行为表达自然不同。由此可见,在“我”的家庭内部,两种文化暗潮涌动。在中美文化交织的家庭中,月兰姨妈无疑是其中最“中国化”的代表。月兰到姐姐家后许多行为都令人费解:她“冲某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说一堆话,送给姐姐和孩子们淡绿色丝绸旗袍、玉镯和耳坠。这些在姐姐英兰看来都是华而不实的,只是将“那些有用的、实在的东西放进后面的卧室”[9]135。学界认为母亲英兰是美国社会里中国文化的代表,但此处细节则体现了母亲英兰长期浸润在美国社会中,深受美国实用主义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妹妹月兰产生了文化观念上的裂痕。还有月兰姨妈诸多的生活细节,在已经“美国化”的外甥、外甥女看来,简直要把他们逼疯了。母亲英兰安排月兰姨妈美国此行的目的是,夺回她在美国另组家庭的丈夫。然而在“美国化”的丈夫面前,月兰姨妈一言不发,俨然成了一个失语的形象,她不仅没有勇气去捍卫自己“正宫”的地位,还对自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我应该回中国去,我压根儿不该来”[9]159。同样的话也由姨父说出,“你来这儿是个错误,你适应不了”[9]168。在姨父所代表的强势的美国形象面前,月兰姨妈的境遇体现了华人在美国社会被边缘化和排斥的生存状态。在寻夫失败后,月兰姨妈甚至都无法在美国社会生存下去,她连洗衣房最简单的工作都无法胜任,后来变成足不出户,只窝在房间里的人。她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过去的事情,慢慢地,她成了一个疯子,被送进精神病院,彻底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最后精神崩溃而亡。创伤研究指出,重复、闪回和幻想是创伤的重要症状,月兰姨妈就在这种往复的创伤回溯中走向灭亡。
“传递让过去和现在发生了联系”[8]179,月兰姨妈自我身份认同的创伤也反映到了“我”身份建构的焦虑中。在美国社会中,“我”同样是失语和沉默的身份,“我喜欢沉默。最初我没有想到应该说话,……当我发现自己必须讲话的时候,上学才变成煎熬,沉默也开始变得痛苦”[9]182-183。老师建议“我”和妹妹进行语言障碍治疗,但每次一到医院,失语便不治而愈,“我”痛恨沉默和无声,厌恶自己的不争,但究其根源,却发现“我们沉默,是因为我们是华人”[9]183。不说话就没有身份!“我”深刻意识到,人不能离开身份而存在,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求与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我”挣扎着从沉默走向发声。原文中有近七页讲述了“我”要求一个沉默的华人女孩发声的经历,从最开始命令她必须说话到循循善诱、以理规劝,“你要是不说话,就是棵植物。你要是不说话,就不会有个性”,劝说无果后,“我”歇斯底里地咆哮,“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头都哭晕了”[9]194-200。“我”之所以会竭尽全力地劝诫小女孩发声,是基于华人同源的种族认同感。“集体创伤,影响到一个有明确成员的群体,必然也会与该群体的集体身份有关。”[13]163沉默是华人无法建立身份的缘由,这不只是“我”的身份建构创伤,也是所有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无法规避的生存困境。尽管“我”努力克服了像月兰姨妈一样无声的窘境,但这只是“我”获得身份的第一步,“我”依然对自己的身份存疑。我不理解英语中的单词“I”(我),这一问题其实反映了“我”在英语世界身份建构的终极困惑。“我”渴望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获得一个美国身份,又囿于中国人的出身和中式家庭文化的浸染,“我”的种族和文化创伤遭遇使得身份建构过程十分艰难。
“我在白鬼和他们的车之间跌跌撞撞。这也有黑鬼,只是他们都睁大着眼睛,满面笑容,比白鬼更容易看清。”[9]107作者借由“鬼”的意象,以小女孩的视角表现了“我”作为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生存感受到的压迫感和与美国白人群体的疏离感。在美国,非裔与亚裔同属于边缘群体,是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极力排外的对象,他们之间同病相怜,自然惺惺相惜。“汤亭亭在美国文化熏陶下长大,说着英语,长着中国人的相貌,既是中国文化的他者,又是美国文化的他者,在两种文化中无所适从。”[14]汤亭亭借此表达了“我”在双重社会文化背景夹击下无所归属的苦闷和屈辱。
韦尔策提出:“记忆传递过程中讲述和接受的历史框架形成了每个人的身份。”[8]185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华人一方面身体里流着故土的热血,被中国文化思想的家庭所影响,另一方面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陷入了中美文化双重边缘化的困境。也就是说,“她的身份焦虑来自于中国和美国对她的不同期待,来自于两种文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12]165,是顺从还是抗争?中国还是美国?边缘还是中心?这些都成为“我”当下不得不思索的问题,身份建构何其艰难。
四、创伤和文学创作
心理学家认为:“能够讲述自己或自己生活的故事常常意味着创伤的治愈。自传式的回忆和关于一个新的自我的概念界定了叙事的形式。”[11]299创伤的经历者或幸存者在讲述过程中将创伤经验重新认识和整合,尝试获得新的解释,与世界建立新的联系。可以说,叙事也是受创者寻求创伤疗愈和创伤消解的方式。既然《女勇士》在出版界被归入“自传”之列,对此汤亭亭也从未极力否认,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文中叙事者即汤亭亭本人,汤亭亭讲述的方式同时又是她对于创伤记忆的文学创作。因为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对记忆的重新审视和艺术加工。全书皆是“我”在讲述记忆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尤以第二章《白虎》和最后一章《胡笳怨曲》的文学创作痕迹最浓。诚如华裔作家赵健秀所言,写作即是对抗。汤亭亭痛恨华人“宁养呆鹅不养女仔”重男轻女的观念,也不甘长大后就嫁人,沦为丈夫的仆役和附庸。为了对抗这种性别创伤,汤亭亭创造性地改写了中国历史中花木兰的故事,创造了一个新的花木兰形象。这个花木兰即是“我”:七岁上山求学问道,以期与强盗对抗,为村民复仇,是百姓赞扬的女勇士。这个花木兰不同于北魏替父从军、恪守孝道的花木兰,汤亭亭将岳飞的故事与花木兰拼贴,将岳母刺字的情节移植到花木兰身上,而且花木兰背上的字变成了“报仇”“誓言”,以及一桩桩“冤情”、父母的姓名和老家的地址。可以说,汤亭亭的花木兰是自我实现的英雄,她期待自己作为木兰可以与世间的灾难和不公斗争。“而履行孝道——这一父权制的道德,则成了一个附带的话题。”[15]国内著名学者张子清教授曾评价汤亭亭为“最有实力的女性主义作家”,因为她给消音的女性发言的机会,而且让她们可以成为英勇斗敌、冲锋陷阵的英雄。不仅如此,上世纪70年代,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也尝试消解了传统认知中男女的差异。一方面,汤亭亭颠覆了读者对于婚配的认识:在“我”作为花木兰的故事中,“我”和丈夫是青梅竹马,因爱而结为连理,而非传统中国婚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强行组合,甚至在“我”生死未明的情况下,“我”的新郎都答应下了与“我”的亲事。另一方面,汤亭亭还重新组织了婚姻关系中的分工:“我”是率领一众士兵的将军,奔赴在杀寇前线,在与丈夫重逢后,他成为“我”麾下的一名将士,“我”们在战场上并肩杀敌……如此,汤亭亭在她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分工和“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再之,汤亭亭的花木兰形象兼有女性气质和男子气概,寄托了“她对于理想中的‘异性同一体’的厚望”[15]:在“我”怀孕的最后几个月,“我”仍坚守在抗敌一线,驰骋疆场;在诞下婴孩后,一改传统女性生育后羸弱不堪的形象,“将婴儿包在我宽大的盔甲中,随后催马上阵,冲入战斗最酣之处”[9]44。成为花木兰的“我”突破了男女的性别对立结界,塑造了一个女勇士的形象。第二章文末,“我跟那位女剑客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木兰以武复仇,而“记录本身也是复仇,不是砍头挖心,而是用文字复仇”[7]59。“勇士的传说让马克辛(汤亭亭)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重新确立自己——战斗和写作都是传统意义上男性的职业。”[16]从这个逻辑来说,汤亭亭不仅通过叙事者的成长经历消解了男女差异,更在叙事之外以写作的形式僭越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可以说,文学书写是汤亭亭对抗性别和历史创伤的重要方式。
第五章汤亭亭也改写了蔡琰的故事。蔡琰是东汉末年的女诗人,20岁为南匈奴的一个单于所掳,在匈奴生活了12年,生下两子,但是孩子们并不会说汉语,甚至听不懂汉语,“只会像唱歌一样模仿,还嘻嘻哈哈地笑”[9]230。语言,作为文化的基本载体,承载了母亲对于故土文化的怀念,而出生在胡地的孩子并不理解母亲的故土之念。既然言语无法共通,蔡琰只能以吟唱共情。
蔡琰在歌唱中土,歌唱她在中土的亲人。歌词似乎是汉语,可其中流露出的悲伤与愤懑,胡人也听得懂。有时他们觉得听到了几个胡人的词语,唱他们无尽的流浪。她的孩子不再嬉笑,当她走出帐篷,坐在冬夜的篝火旁,坐在胡人中间时,孩子们终于开始和她一起唱起来[9]230-231。
尽管语言不通,蔡琰一曲却唱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所以,汤亭亭借由蔡琰的故事改写表现了语言不通也可以实现沟通和互相理解。在《西宫》一章中,母亲英兰评价姨父之所以能融入美国社会,是因为他能讲英语。此处母亲的观念反映了美国华人群体的共识,母亲为了让“我”说好英语甚至给“我”割了舌筋,“我”在沉默无法发声时,也曾想过学好英语,去上英语学校……在《女勇士》的多个细节中,作者默认了语言相通是异邦人沟通的必要前提,但在全书末尾作者借助改写蔡琰的故事,表现了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的民族间沟通的可能性。
滞留匈奴十余载后,蔡琰被赎回中原,“她从胡地带回自己写的歌,三首之中有一首流传至今,名为《胡笳十八拍》。汉人用自己的乐器为这首歌配上曲子,如今依然在演唱,歌词也译得凄切动人”[9]231。这首在胡人和汉人看来都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得以在两地流传,“曾经被视为障碍的种族现在却成了她的优势……她的曲子不仅是一种融合,还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创造了一个新知识产生的文化界面”[15]。在“我”的心目中,蔡琰俨然成为一个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使者,深刻表现了汤亭亭对于跨文化交流互通的美好愿望。虽“胡与汉兮异域殊风”,但“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蔡琰以歌吟唱,“我”以文字“吟唱”。“我们现在属于整个地球啦……要是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就属于整个地球。”[9]118通过对蔡琰这一人物故事的变形和改写,文化对立被悄然消解,勾勒出了“我”所向往的中美文化融合的和谐之境。
有学者指出,汤亭亭在援引中国故事和历史时并不严谨,杂糅了西方文化的元素,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亵渎。其实不尽然。阿斯曼认为,“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17]。在这里,中国历史故事成为汤亭亭消解性别、种族、文化、历史差异的利器。记忆研究学者厄尔(Erll)在书中这样表述:
个体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在叙事中结构化。重新讲述自我的故事会引起这个结构的变化。注意力的重新分配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贡献,也促成了心理和心理治疗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一种回看的文化。这种文化意识到,讲述过去和历史,是建立在理性和感性相对满意,对现在和将来有所规划的基础上[18]。
作者能够重述自己的故事,是历史回忆和社会现实的复现,同时又高于历史和现实。因为讲述者需要对创伤事件进行重新梳理,将创伤记忆有选择地重述并有意识地或放大或缩小其中某些方面,这些行为是讲述者重新经历创伤、思考创伤,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建立自我与社会、与世界之间联系的过程。在汤亭亭的书写中,我们能够看到经历创伤后作者认识的进步——对性别、种族、文化和历史的重新思考。诚如张喜华教授所言,汤亭亭的写作是“边缘走向中心的努力,是中心接纳边缘的期盼”[12]。女人可以成为兼具男子气概的盖世英雄,中美人民可以打破种族和文化的壁垒互动交流,那些造成创伤的历史也可以成为我们获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五、结语
长期以来,学界公认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是“东方主义的同谋”[19],认为其书中对旧中国黑暗、扭曲的描写实则是作者尝试跻身美国主流社会、构建自己美国身份的策略。从创伤角度分析,文中的叙述实则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创伤人物和回溯稀奇百怪的创伤记忆,表现了作者在创伤历史影响下,以及在性别、种族、文化几重偏见下,在夹缝中挣扎的创伤体验。更可贵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地回望创伤,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自我创伤疗愈的出路。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所呈现的创伤体验首先来自于“我”的家庭创伤记忆,尽管“我”不是历史事件的创伤经历者,但经由母亲的转述,这种创伤感受也移植到了“我”的身上,“我”开始有了成为性别弱势者和被消声的隐忧。上一代的创伤经历内化成“我”认识社会的经验,“我”在中国家庭和美国社会的来回穿梭中,陷入自我认识的分裂,上一代的经验加重了“我”自我身份认定的危机感。在现实世界里,历史无力改变,性别、种族、文化偏见难以撼动,于是“我”寄希望于文字,通过重写创伤来自我疗愈。可以说,汤亭亭以文学创作的方式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自我疗伤的乌托邦。其中,汤亭亭描绘的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文化互融的美好图景不仅抚慰了几代美国华人被边缘化的精神创伤,而且为全人类追求平等美好的世界刻画了现实可能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盛行,新冠一疫让全人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汤亭亭是时代的先锋,她“利用中国文化为资源,将美国作桥梁,通过表述来生产一种另类的文化视角”[12],在四十几年前就藉由自身和家庭创伤的回忆表达了隔阂消解、人类相惜的美好愿景。换句话说,《女勇士》是一部具有跨时代进步意义的作品,其现世意义仍值得从多方面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