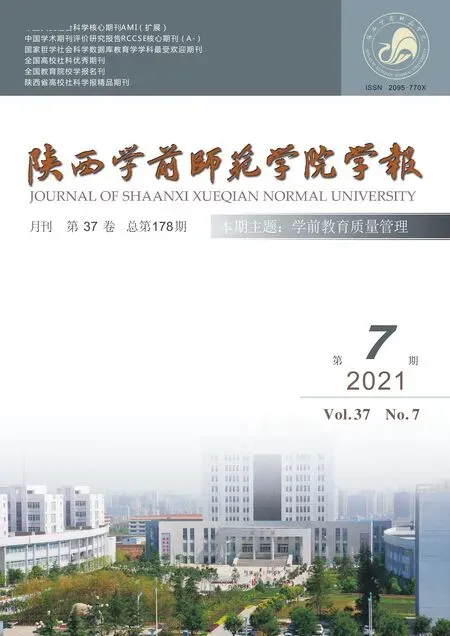译介学视角下《孺子歌图》文化信息和形象的变形
李蓉蓉
(1.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旅游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2.华侨大学MBA教育中心,福建泉州 362000)
清末留华西人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编译的老北京童谣英译本《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孺子歌图》)在西方出版并受到关注,第一次向世界详细具体地展示了清末时期北京儿童的生活,并从不同角度传递出丰富多样的文化信息,包括方言、修辞、游戏、食品、时节、职业、民俗、社会地位等。作为我国首部译介到国外的近世童谣集,《孺子歌图》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打开了民谣译介的一扇窗,译本得到了周作人等著名学者文人的肯定,对后世民国时期的民谣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童谣译介的理论背景和研究现状
翻译的本质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翻译界长期争论的话题之一。20 世纪80 年代末到90年代末西方翻译研究跳出了语言文字层面,完成了文化转向。1997 年,译介学建构者谢天振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提到:译介学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角度已从最初的比较文学媒介学转向了比较文化。他提出了译介学研究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其中就包括“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中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的变形”[1]这两个最主要的概念。在第一个概念中,“创造性叛逆”具备认识论意义,既是其核心概念,也是其分析工具,较常见的是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可分为个性化翻译(包括归化和异化)、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而对于第二个概念——“翻译中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的变形”,既可能发生在“创造性叛逆”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性叛逆”行为的结果。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文化形象”这个提法,谢天振教授之后也做了调整,例如在《创造性叛逆——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2016)一文中,他早已将“文化意象”完全取代了“文化形象”,因此我们在此亦使用“翻译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这个概念。
随着文化成为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之一,中西方文化融合加剧。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学作品走向国际的译介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得到保护和发展尤其值得译者重点关注和慎重对待。基于上述理论和认识,“童谣译介过程中的文化变形”研究应运而生,该研究建立在“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的理论基础上,经过研究者审慎地、多维度地考证童谣这种口头文学体裁在具体某部译作中涉及的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的异同,透过跨文化交际视角,剖析该童谣译作在译介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作用上的得失,由此总结经验,推进童谣译介的发展。目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以“中国知网”搜索为例,使用“创造性叛逆”为关键词的可搜索到1143 条研究成果,以“文化意象翻译”为关键词可寻到1177 条,而以“童谣文化意象翻译”“童谣文化意象变形”等类似关键词搜索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万方”、“维普”等国内大型数据库亦罕见同类研究。
二、《孺子歌图》译介中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的变形
从文化保护角度而言,《孺子歌图》童谣译本中出现的一些典型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已经超越了译介行为本身适宜突破的界限,以下笔者主要从方言、修辞、游戏、民俗民情四个方面探讨该译本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
(一)方言译介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
在《孺子歌图》童谣中,老北京方言随处可见。对比文化意向的变形,方言译介主要分为口音译介变形、异地方言或他族语词汇译介变形、词意变形三种。
第一种变形是口音译介变形。儿化音是老北京方言(又称“京片子”)中最具代表性的特点。词后儿化最常见,如“砖儿”“媳妇儿”“墙头儿”;词中儿化也很常见,常常出现在名词、拟声词和语气词(又称“衬词”)中,例如中秋节北京传统儿童玩具“兔儿爷”。对儿化音,何德兰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对个别的词后儿化,将“儿”译为“小”,如“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儿。”译为Little snail(“水牛儿”是北京土话蜗牛的称呼);对个别的词中儿化,将“儿”音译为“’rh”,如虾蟆的叫声“哇儿哌”(Wa’rhwa)、“格儿瓜”(Ke’rhkua);童谣里大部分的儿化音被有意地漏译,即直接省去不译。
第二种变形是异地方言或他族语词汇译介变形。除了北京儿化音,童谣里还出现了其他方言和他族语,如东北话、满族语言等。“爷爷抱孙子,坐在波棱盖儿”,“波棱盖儿”是东北话里的“膝盖”,何德兰采用了归化方式,直接意译为“He’s sitting on his knee.”如此,读者便难以领略原文在不同方言之间切换的乐趣。对此,笔者持两种意见:一方面,要求何德兰翻译出不同方言的味道,在当时或现今看来不但难操作,也不是很有必要;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和保留近世童谣中的有价值的方言文化信息,这个难题值得研究。
第三种变形是词意变形。“耍义”在多首童谣中出现,可推断是清末北京方言,现在已较少见,(多指小孩子)撒泼、耍横,尤其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产生的各种任性的行为。英语解释为be rude or unreasonable,and act shamelessly to others.可以使用spoiled,capricious 或petulant。然而何德兰在翻译时改变了这个词的内涵,用quarrel来取代。根据牛津字典对quarrel 常用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为an angry argument or disagreement between people,often about a personal matter.表示“吵架、争论、拌嘴、分歧”,例如They had a quarrel about money.第二种解释为(especially in negative sentences)a reason for complaining about somebody/something or for disagreeing with somebody/something.表示“质疑的理由”,例如We have no quarrel with his methods.很显然,童谣中出现的quarrel 没有传达出“撒泼、耍横”的涵义,而是令读者对童谣人物的印象产生了偏差,发生了意象错位。
(二)修辞译介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
“起兴”是中国民谣借鉴古典诗歌“兴”的一种表现手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咏之词也”,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为兴,后为咏,使诗歌产生了意味深长、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在《孺子歌图》,起兴之处频频可见,看似与后文毫无联系,却有营造环境气氛的作用。如“上轱辘台,下轱辘台,张家妈妈倒茶来。”“上去下来,萝卜要卖水壶要拿。”“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他妈。”以“剔灯棍儿,打灯花儿,爷爷儿寻了个秃奶奶儿”为例,译文是He pulled up the wick with the candlestick knife,and found he had married a baldheaded wife.“剔灯棍儿”指的是挑起蜡烛灯芯,剔除馀烬,使灯更亮。“灯花儿”指灯芯燃烧时烛泪凝结而成的花状物,寓意吉祥。“打灯花儿”本是活泼的孩子们喜欢的小游戏,即帮大人剔灯棍的时候顺便打掉灯花,作为起兴部分,本来和爷爷寻了奶奶没有多大关联,然而译者把情境设计为洞房花烛夜,将起兴部分和主题的逻辑重新理顺,使人读来合情合理,联想到爷爷在新婚之夜挑灯细看奶奶的情景。但是译者将“打灯花儿”略去不译,本是为了避免译文过于冗长而失去韵律美,却也舍弃了这一文化信息。
(三)游戏译介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
《孺子歌图》有不少游戏童谣,其中一首叫《跑马城》:“雉鸡翎,跑马城,马城开了,丫头小子送马来。“雉鸡翎”又叫“野鸡翎”或“雉毛翎”,英文pheasant's tail-feather,即戏曲中的翎子,是用野鸡的尾部最长的羽毛制成的。提及雉鸡翎,中国人会联想到戏台上头戴金冠,冠上插着雉鸡翎,英武潇洒地冲锋陷阵的武生或武旦。这是丰富的传统戏剧文化带给国人最真实的文化意象。然而对美国读者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集体文化记忆,这就需要译者寻找到文化的契合点或近似等价物。此外,仅仅通过译文我们看不出何德兰是否真正了解《跑马城》的游戏规则,而《跑马城》的游戏规则本就是译介这首童谣的一个难点。这个游戏要求一群孩子手拉着手站成面对面的两排,中间隔着约十几米。当其中一方唱着这首童谣点名要对方队列中的某个孩子来扑城时,这个孩子就要出列,猫着腰,憋足劲,向着对方的阵营冲杀过去。游戏结果有三种情况:第一,冲破了对方的防线,凯旋并带回个俘虏;第二,冲不破防线,被对方扣作人质;第三,憋足了劲冲杀过去之时,对方紧绷的防线突然间松开,这孩子一头冲了过去,扑了个空,栽了个跟头,摔得鼻青脸肿。可以看出这个游戏有着严格的规则,要求参与者具备勇气和体力。然而何德兰将“雉鸡翎,跑马城”译为He stuck a feather in his hat,and hurried to the town.这不禁令人想起一首戏谑意味浓厚的美国传统儿歌Yankee Doodle(扬基曲):Yankee Doodle went to town riding on a pony.He stuck a feather in his hat and called it macaroni.(扬基·杜多进城,骑着一匹小马。他帽子上插着翎毛,被人叫做纨绔子弟。)这样的译文表现不出这个游戏的热闹场面,也传达不出中国孩子顽强和尚武的一面,反而给童谣增添了一层戏谑嘲弄的味道。译文颠覆性的二度创作使源语文化意象完全改变,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在同一层面上对这首童谣的译文和原文进行讨论了。
(四)民俗民情译介过程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
中华民俗民情丰富多样,以下以饮食和农时方面的译文为例。
1.饮食文化
对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的东方美食大国而言,饮食方面的对外译介在清末时期实属不易。《孺子歌图》里的食品,有些翻译得比较简约,如“大花糕”,即北京重阳花糕(用黄米或糯米加上糖油干果青梅烤制),因为甜度高被译为sugar-cake,尽管不够贴切,但对比整本童谣的其他食品译文,可称得上是比较真实而简洁的;有些食品翻译得很详细,如“豌豆糕点红点儿”,对应的译文为Round bean cakes with red spots bright,可以说是这本童谣的食品译文中最为细致而完整的。然而,面对童谣里源远流长的中国饮食文化,译者使用的译介方法比较单一,导致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上的变形频繁出现,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种变形是“以他物代替”导致的变形。以“糖瓜”为例,“新年来到糖瓜祭灶”这句童谣在《孺子歌图》的译文是You’ll find whenever the new year come,the kitchen god will want a plum.这里的“糖瓜”被译者用plum取代,仅仅是为了能够押韵,而“糖瓜”这一能够带给大部分中国人温馨和甜美的童年记忆的文化意象就这样被另一种不相关的食品取代了。在中国年节文化中,“糖瓜祭灶”极容易让人联想起俗谚“廿三糖瓜儿粘”,指的是腊月廿三那天家家户户要祭灶王,人们会买些用黄米和麦芽糖熬制的糖瓜(扁圆形)、关东糖(长条形)供着,请灶王升天到玉皇大帝那儿做年度报告时多多美言,来年这家人才会得到上天庇佑。而plum(李子)在当时的种植技术条件下,无论是产于中国的还是生于欧洲的,果实成熟的季节都不在春节附近,就算几十年后将两种李子杂交后的美洲黑布林,也是在夏季成熟,因此这里的plum 除非是李干,否则说不通。然而,李干再甜也没有糖瓜甜,糖瓜蕴含的民俗寓意不是李干所能代替的。至此,腊月廿三祭灶的文化信息经过译介已变形,“糖瓜”的文化意象也不复存在。
第二种变形是“一刀切”。童谣里出现的一些民间糕点,如“切糕”(北京枣切糕,红枣加黄米面粉蒸制成)、“窝儿薄脆”(一种油煎小薄饼)、“烧饼”(老北京芝麻烧饼,咸酥口感)、“饽饽”(用粘米制作而成的食品,其颜色金黄,有粘性,味香可口)、“麦饽饽”(馒头)、“烙饼”(用麻油烤烙的面饼)等,尽管原料和制作工艺不同,但还是被译者统一译为cake。又由于西方cake 的种类繁多,外国读者对cake的印象也不一而足,这就导致更为复杂的理解偏差,致使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发生了严重的变形。
第三种变形是“置之不译”。何德兰从最初来华到出版《孺子歌图》已历经十二年,对中国的历法、节气和传统节日可能不会太陌生,然而以下这首童谣的译文中并未充分保留文化信息——“喜儿喜儿买豆腐,该我的钱,我要你见,今年腊月二十五。”译文:Debtor-The magpie sells his bean-curd dear.If you owe me,then you I would see,on just five days from the end of the year.俗话说“腊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过去人们在这一天要做豆腐,或者买豆腐、炸豆腐,主要是取豆腐的谐音“斗福”,对即将到来的新年寄予美好的愿望。何德兰在此将押韵处理得很好,但是却没能进一步将bean-curd 和on five days from the end of the year进行文化上的链接,也没有利用副文本补充说明中国腊月二十五的民俗活动,童谣背后关键的文化信息被忽略了。
第四种变形因“误译”导致。误译带来的是文化信息和文化意向的错位,例如“馍馍”。“馍馍”是用面粉发酵蒸成的食品,南方人称“馒头”,译文却是pie(馅饼);又如“油炸馅饼”被译为The cake we bake,we put in oil,or pork,or steak.若选择pie,则更符合食物带馅儿的特点。
2.历法、节气和农时
除了饮食文化方面的误译,译文还出现了历法、节气和农时等方面的误译。例如“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来了种荞麦。”译文:The Farmer’s Guide-In Spring,plant the turnip.In summer,the beet.When harvest is over,we sow the buck-wheat.这首童谣指导人们根据作物的生长条件和环境进行种植。中国夏季进入三伏天的时候,在初伏可以种植萝卜;中伏是种植白菜、青菜等蔬菜的最佳时期;在末伏适合种植荞麦。从题名The Farmer’s Guide 来看,译者概括得非常到位。然而将三伏天分别对应春季、夏季和秋收之后,很显然是译者的有意误译。译者希望避开“伏天”这个文化差异,用归化的方法使大洋彼岸的同胞们能够理解这首童谣。然而从美洲读者的角度而言,译文极有可能导致他们对中国农时产生误读,影响他们对中国农时的正确认知。
(五)其他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
以上我们探讨的四个方面的文化译介特点只能从单一的角度反映《孺子歌图》英译本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译介情况。译本中还频繁出现动物、植物、昆虫为主题的童谣,民俗类也常有地名、服饰、嫁娶、买卖等情景,甚至也会出现抽鸦片、裹小脚、重男轻女等极具时代特点的细节描写。当多种文化信息同时出现在一首童谣中,被何德兰译介到他的国家,又经过了众多的媒介评论和无数读者的解读之后,能够保存下来的120年前中国真实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还有多少呢?
译本里有一首嫁娶主题的童谣,“十八个骆驼驮衣裳,驮不动叫麻愣……小姐小姐你别恼,明儿后儿车来到,什么车?红毂辘轿车白马拉,里头坐着个俏人家……”按东北方言,“麻愣”就是“蜻蜓”,因而此处被译为dragonfly。然而,骆驼驮不动的嫁妆,蜻蜓就代替得了吗?这委实经不起推敲。在其他版本的译文中,有另一种解释是“马鹿”。马鹿又称“赤鹿”,力能载重,被鲜卑人驯化为载重工具。后来鲜卑的一支和其他族繁衍成了蒙古族,蒙古人又驯养了驯鹿,以驯鹿的肉和奶为食,并且将驯鹿驯化为骑乘工具。满蒙联姻300 多年,载重的鹿很可能就是在这一阶段进入了清朝满族人的歌谣里。因此,笔者推测,该首童谣里的“麻愣”极有可能不是东北话的“麻愣”(蜻蜓),而是大型鹿种“马鹿”或“驯鹿”。除了“麻愣”这一尚待考证的疑点,结合上下文,童谣里的“俏人家”按照常识和逻辑最有可能指的是前来迎亲的新郎。但在何德兰的译文中,迎接新娘的迎亲轿子里坐着的是a beautiful girl(美娇娘),难道侍女代表新郎来迎亲?译文留下了这两个不合理的疑点,又缺少用来解释的副文本,极有可能使这首童谣在西方人眼中成为一首荒诞歌谣。如若笔者所推测,“麻愣”确是载重工具的鹿,“俏人家”确是迎亲的新郎,那么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意象和文化信息则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没有得到正确的传递,阻碍了多少西方人对当时中国北京迎亲习俗的正确认识。
另举一例,清代男性的发型是当时最有特色的文化现象,《孺子歌图》里就有一首童谣描写了清末时期男孩的发型——“脑瓜儿上梳着个小蜡千儿”,我们就以此作为最后一个译例。“蜡千儿”又称“蜡签儿”或“蜡扦儿”,是过去烛台上用来插蜡烛的金属签,有铜制的、锡制的和银制的,常用以比喻孩童头顶上扎的冲天小辫儿。译文“On his head is a candlestick,weighing a pound”却并不提及辫子,使用的candlestick是烛台或蜡烛架子,无论如何都比插蜡烛的金属签要笨重得多,西方读者看后不但想象不出当时中国北京男孩们常见的冲天辫发型,脑海里还会产生一个孩子的头上顶着个一磅重的烛台的荒谬联想,致使文化意象发生了变形。世界万物,凡不合理就不为人理解,不为人理解就难以被接受,从这一点看,为了减少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译者须结合专业知识,加强文化交流意识,注重源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保护,充分发挥译介应有的正面作用。既然译介的高级目标是文化交流,在译介过程中导致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甚至脱落,其背后必有复杂的原因。
三、《孺子歌图》中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之背后原因
首先,译者自身原因。第一,重情感传递:对比忠实于原文,何德兰更倾向于译介过程中情感的传递。他志在将这些童谣所展现出来的温情和中国家庭生活全新的一面展现给西方孩子,并能引导西方的孩子对东方的同龄人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热爱。我们能感受到何德兰面对岌岌可危的帝都晚景,仍对这片土地满怀温情和善意。第二,扎实的文学功底:不拘小节的再度创作。何德兰有较高的英语语言功底和文学修养,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他的遣词造句不拘泥于语言文字层面,采取的创造性叛逆形式和同时期的其他民谣译作也有很大的不同,考虑的是译作是否能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感悟是否和源语读者对原作的感悟近似,译作是否保留原作的大部分艺术风貌,是否能够给予读者以艺术审美感受,以及是否能够延长在目的语国家的生命。因而在译介过程中何德兰能够做到思路开阔,手法大胆,终使译文灵动,成为何德兰本人的再度创作。而再度创作对原作就难以做到完全忠实,原作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甚至脱落也就不可避免。第三,源语非译者的母语:对非母语文化的认知和感受不能与对母语的相提并论。从何德兰有限的生平资料来看,1901 年之前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与清廷上层交往甚密,且与中国教育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童谣是口头文学,大多出自民间,而他接触的平民不会太多,搜集的六百多首童谣的来源也不一定是从田野调查得来,只知道有一部分是从佣人的转述中记录下来。如果我们将《孺子歌图》收录的一百五十多首童谣的个别童谣版本和其他相似版本比较,甚至能发现个别中文童谣就存在错误。中华文字和历史源远流长,何德兰从最初来华到出版《孺子歌图》历经十二年,十二年对忙碌的何德兰而言要完全掌握中文本就是难事一件,更何况要求他对童谣中包括民俗、历史、方言等方面的文化信息了如指掌也就难上加难了。
其次,读者方面的原因。何德兰在英译本序言中明确提出:“我们期望对这些童谣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同时又能使说英语的孩子们满意。我们关注的是孩子的接受程度而非学术需求。”[2]《孺子歌图》英译本出版之际,Mother Goose Rhymes已经在西方风行了一百多年,何德兰本人也是听着《鹅妈妈童谣》长大的,本能地对《鹅妈妈童谣》有着特殊的依恋,译者和读者之间的情感距离比起译者和原作的情感距离要近得多,因而他在译介的过程中也更容易从目的语国家小读者的视角和听觉去判断译文的走向,以归化为主的创造性叛逆方式来译介《孺子歌图》。《鹅妈妈童谣》里收录的童谣有不少夸张荒诞的打油诗,这或许能解释何德兰的一些漏译、误译和编译手法,对居住在北京多年、交往甚广的何德兰而言,想弄清楚像“蜡千儿”这样的口头用语或许并不是多难的事,但类似的误译反复出现,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何德兰的有意安排,试图营造类似《鹅妈妈童谣》的夸张和诙谐效果。
最后,文化地位的原因。清末时期中国文化相比较西方文化等强势文化群体而言属于弱势文化群体,很多译介者不知不觉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心理影响,译入外国原著以异化为主,译出中国原著以归化为主,虽然促进了西学东渐,却也导致大量中国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变形甚至脱落。
四、对中华童谣译介的建议
何德兰的《孺子歌图》英译版在20 世纪处出版之后迅速得到了海外广泛关注和认可,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取得了零的突破,瑕不掩瑜,译文中部分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的变形并不足以否定他对传播中国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笔者亦怀着欣赏与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地剖析、考证何德兰先生的译文。追古朔今,对比中国新旧社会更替的动荡年代,120 年后的中国社会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已经逐渐争取到了自己的文化话语权,让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了解中国。上文我们提到cake 在《孺子歌图》里的“广泛”使用,如今,和中华美食一样琳琅满目的菜名译文已以规范的形式出现在西方各大中餐馆菜单里,《牛津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已经收录了baozi,jiaozi 这些词条,汉源英语词汇不断增加。
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现代汉语除了普通话,又分为七大方言区,每个方言区又分为若干方言小片。方言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童谣作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和传统典籍一样历久绵长,中国童谣的译介仍旧承担着传播和保护地方文化的重任。透过对《孺子歌图》英译本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的分析,中华童谣至少应在以下四个方面构建保护文化的译介模式。
首先,对译者的要求:提高译者的双语知识技能和文学功底,译介过程中同时关注文化内涵和韵律趣味,适当利用副文本信息补充文化内涵[3],注重文化信息的保护,避免因韵害意;第二,以受众为目标:以目的语国家读者的视角和需求适度地调整译介方向和技巧;第三,童谣的出版:选择国际上权威的出版公司[4],提高童谣译介的可信度和文化自信;第四,童谣的传播:从出版物到影视作品,从网络教学到出版物数据共享平台,从公共网站到自媒体,充分利用一切媒介进一步传播已出版的童谣。
中华童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承载了每个人成长的美好记忆,更是各个民族的人们代代相传的艺术珍宝,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帮助中华童谣“走出去”,只有童谣获得更广泛的接纳,让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童谣背后的真实的文化,才是对这些民族瑰宝最好的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