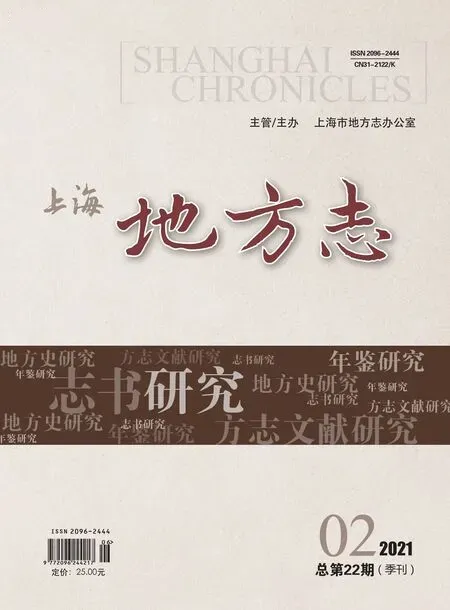近代上海市民社会与沪剧艺术的关系初探
石梦洁
一、沪剧的起源概述
(一)从“花鼓”到“本摊”
中国的许多民间戏曲起源于农村地区,沪剧也不例外。据《上海沪剧志》所载,沪剧原是在吴淞江和黄浦江两岸乡村传唱的山歌俚曲,又称为“东乡调”①汪培、陈剑云、蓝流主编:《上海沪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概述”,第1页。。起初是一种连说带唱的表演形式。到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逐渐向作为戏剧表现形式的‘对子戏’和‘同场戏’②所谓“对子戏”,由男女二人对唱对演。而“同场戏”又分为“小同场戏”和“大同场戏”。“小同场戏”演员人数在三人及三人以下,情节相对简单;而“大同场戏”表演人数在通常在三人以上,剧本情节相对复杂,变化较大。见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中华戏曲·沪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过渡,当时群众又把它称为‘花鼓戏’”③《上海沪剧志》,“概述”,第1页。。
众所周知,花鼓戏起源于安徽凤阳地区。有研究者认为,清代中叶,因淮河水灾,凤阳人从安徽流离至江苏,故而将花鼓戏带入吴地④柯如:《再论花鼓戏之起源》,《申报》1933年6月15日,第21613期,第15版。。
嘉庆年间上海南汇人杨光辅所撰的《淞南乐府》一书,有“村优花鼓妇淫媒”的词句。这首乐府后面并有附注:“男敲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笛、板,所唱皆淫秽之词,宾白亦用土语,村愚悉能通晓,曰‘花鼓戏’。演必以夜,邻村男女键户往观。”⑤杨光辅著,许敏标点:《淞南乐府》,《沪城岁事衢歌·上海县竹枝词·淞南乐府》,《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若将此视为沪剧前身,则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由于植根农村,起初花鼓戏多描写乡村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些低俗露骨的“淫秽之词”。早在嘉庆年间,花鼓戏就遭到了明令禁止⑥嘉庆十一年(1806年),官府曾颁布《禁花鼓告示》,见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6年,第10页。,但见效甚微。到了19世纪中晚期,由于花鼓戏的演出范围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拓展,地方士绅也加入了打击花鼓戏的行列。艺人们被迫将表演场地转入租界。然而,在官府的穷追猛打下,在租界的演出也受到阻碍。1872年10月15日的《申报》上所刊《请禁花鼓戏说》:
“若花鼓戏则以真女真男当场卖弄凡淫艳之态,人所不能为……穷乡僻壤偶尔开台一阙,甫终片帆已挂。盖恐当道闻风驱禁,犹存顾忌之心,而乡间妇女尚有因之改节者密约幽期,尚有因之成就者诱人犯法,已属不堪。今则倚仗洋商恃居租界,目无法纪,莫敢谁何。”①《请禁花鼓戏说》,《申报》1872年10月15日,第144号第1版。
演员们只能或边走边唱(即“跑筒子”),或在街头临时圈地卖艺(即“敲白地”)②《上海沪剧志》,“概述”,第1页。,以此躲避追查。为了长久地维持生计,他们将花鼓戏改名换姓作“本地滩簧”③滩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对产生并成长于该地的由说唱嬗变为戏曲的表演艺术的一种习惯性的称谓。见朱恒夫:《滩簧考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页。,简称“本摊”或“申滩”。由于当时的“苏州滩簧”在上海市民阶层中广受欢迎,于是本摊也借此东风,在形式上由立唱改为了苏滩的坐唱。
(二)从“本摊”到“申曲”
20世纪初,报纸上屡有关于本摊在茶肆演出、客座满盈的报道。如1904年的《申报》中就有言“马家厂旁南园小茶肆主,招人歌唱滩簧,观者如云,异常热闹”④《上海保甲巡防局纪事》,《申报》1904年10月1日,第11300号第9版。,可见这时本摊已开始为城市底层市民所接纳。该时期代表人物许阿方和胡兰卿,被视作沪剧界的“祖师爷”⑤其实,沪剧的“祖师爷”还有如“水果景唐”“麻皮雪春”“红鼻头掌生”“花鼓戏阿六”等一些只留下艺名的老先生。但因为没有真名,无档案可查,在1934年“申曲歌剧研究会”制“先辈图”时,因此未能将他们列入其中。见胡晓军、苏毅谨等著:《戏出上海——海派戏剧的前世今生》第六章,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
辛亥革命后,施兰亭、邵文滨、胡锡昌、陈阿东等一批本摊艺人主动响应政府文化改良的号召,对本摊中的“淫词秽语”进行了调整。1914年4月,《申报》上登出准予改良滩簧开唱的信息,本滩就此获得了官方认可:
南市第一区境德兴楼茶馆拟设改良滩簧,遵章认缴同捐,补助地方公费。会经呈请上海工巡捐局,给谕在案。兹经朱局长函,由第一警区查明,该茶楼附设之滩簧确系改良小说,并无淫词秽语,自当照准。故于昨日批示,给发执照矣。⑥《改良滩簧准予开唱》,《申报》,1914年4月12日,第14694号第10版。
而后,“天外天”“新世界”“大世界”等游艺场的出现,无疑又给本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⑦1917年,“丁少兰等以东乡调、本土滩簧之名,在上海天外天游乐场演出,这是本滩首次献艺于游乐场”。见《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第126页。1914年,施兰亭等人组织了沪剧史上第一个专业艺人团体——“振新集”⑧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8册第三十八卷,《文化艺术(上)》,第二章“戏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5217页;屠诗聘主编:《上海春秋》下篇,第二十七章第六节《本地滩簧—申曲》,香港:中国图书馆编译馆1968年,第59页。;同时,用“申曲”名称替代了“滩簧”。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⑨“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首次将申曲改名为沪剧。”见《上海沪剧志》,“概述”,第2页。关于这一更名,20世纪30年代时任江苏省吴县县长的吴企云写过一篇《申曲研究》:
叫申曲,便与昆曲相并肩,似乎是雅了吧,于是申曲这名称竟夺去了花鼓戏等的本名了。申曲这名称,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八日上海市申曲歌剧研究会正式成立,在上海市党部注册,可说已是正式的了。我们对于“申曲”两字,也很赞成,因为他能够表出地方性的缘故,至于雅不雅,倒在其次。⑩吴企云:《申曲研究》,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正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565页。
至此,源于农村的沪剧开始正式面对都市群众。
二、20世纪20-40年代沪剧在市民社会中的表现与接受
(一)市民社会与沪剧表演形式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概念源于西方。关于这一概念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李天纲教授在其著作《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中就大量运用了“市民社会”及“市民意识”等相关词汇。或许因为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话题,书中并未就此给出具体定义,只是指出韦伯曾对此有所论述,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民社会”一词是在18世纪产生,且“历来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欧洲13世纪的城市时都用了‘市民’的概念”①李天纲:《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页。。言下之意,所指的“城市”,是以西方城市为模型的现代城市,而非中国宋明时期的城市。②李天纲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那些高度发达的城市,比如六大古都,其经济地位都依附于政治地位,“欧洲城市后来又自己的法庭、军队和警察,领主不得入内,就是国王也非请莫入。中国的城市就不同,都邑之内历来还是皇家官府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自我权利意识的仅仅是上层的官僚、士大夫,而工商人士却无法用社会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生计。即便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尽管出现了一大批“小市民”,但他们的作为也仅仅体现在精致的物质生活上,而非对于地方事务的贡献和参与。见《人文上海》,第27—28页。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上海较早地与西方文化碰撞、杂糅,因而在市民社会的成型过程中,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得以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申曲刚刚进入城市时,主要观众集中于茶楼酒肆。在这样的瓦肆勾栏间受到欢迎,可见当时上海民众普遍文化水平有限,审美情趣充满了浓厚的世俗气息。然而,底层民众从来就不具有意见导向,话语权总是集中在有一定社会地位、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中,如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文人、记者等等。他们认为申曲并不能登大雅之堂,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申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与当时上海最受追捧的京剧和昆曲相比,申曲无论是从自身的文化底蕴还是演员的表演功底来看,也的确难以望其项背。为了在困局中找到生存空间,申曲的改革迫在眉睫。
上海人看戏对舞台效果十分重视。“(演员)长相要漂亮,服装要鲜艳,灯光要明亮”③蔡丰明:《上海都市民俗》,第八章“声色之娱·上海都市文艺娱乐民俗”,第一节“风靡上海的戏剧热”,学林出版社2001,第277页。,是讲“腔调”的上海人对一出戏最基本的外在要求。为了适应城市群众的欣赏习惯,申曲恢复了花鼓戏的站立演唱形式;而在布景、服装、道具等硬件上也不断完善,比如根据剧本内容绘制幕布、添加软景等④《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第125页。。
尽管申曲对京剧、昆曲、苏州滩簧以及评弹都有所借鉴,但为了更好地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申曲也向“文明戏”⑤所谓“文明戏”是相对于旧戏而言的,当时更多称为“新剧”,如欧阳予倩在《谈文明戏》一文中写道:“初期话剧所有的剧团都只说演的是‘新剧’,没有谁说‘文明戏’的。新戏就是新兴的戏,有别于旧戏而言,文明两个字是进步或者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正当的解释是进步的新的戏剧。”见欧阳予倩:《谈文明戏》,葛聪敏编选:《欧阳予倩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14页。而周剑云在《新剧评议》一文中认为,文明戏和旧戏的区别在于内容上的文艺美术:“新剧者,一般人士所呼为文明戏者也,此文明二字何等华丽,何等光荣……新剧何以曰文明戏?有恶于旧戏之陈腐鄙陋,期以文艺美术区别之也。”见周剑云:《新剧评议》,《繁华杂志》1915年第6期。文明戏的形式很多,过去有人认为只是早期话剧的形式,其实不仅如此,黄远生先生认为剧本内容、表现形式上的有所革新者皆为“新剧”:“今日普通所谓新剧者略分为三种:(一)以旧事中之有新思想者,编为剧本……(二)以新事编造,亦带唱白,但以普通之说白为主,又复分幕……(三)完全说白不用歌唱……亦如外国之戏剧者……”见黄远生:《远生遗著(下)》,《新茶花一瞥》,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76—379页。汲取经验。1918年,与文明戏首次融合的申曲《离婚怨》取得了成功。该戏由文明戏演员范志良与申曲“子云社”的刘子云合作改编,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真实事件,主要讲述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子,因不满于丈夫贫穷失业而与其离婚,之后被“拆白党”所骗,继而走向堕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离婚后的丈夫因勤劳致富而娶得淑女,重建了美满幸福的家庭①文牧、余树人:《从花鼓戏到本地滩簧——沪剧早期历史概述》,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2集,上海艺术研究所1986年,第8页。。《离婚怨》由丁少兰和孙是娥担任主演,上演后取得了热烈反响。1921年,该剧在“花花世界”游艺场的首演更是轰动一时。
《离婚怨》开创了沪剧时装戏的先河,也决定了后来申曲以时装戏为重的发展路线。可见,当时这类具有现代风格的表演形式更受上海市民的喜爱。30年代以后,西装和旗袍成为上海都市男女的主流服装②关于上海西装业,在《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中提到,早在1896年,上海就有了第一家“和昌西服店”。而关于旗袍的起源时间一直未有定论。据周锡保《中国古代服装史》,在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妇女照片上,数十人中还只有一人穿旗袍,要到2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流行起来,30年代以后才成为普遍的妇女服饰。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装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534页。。表演申曲时装戏的男女演员,也多如此穿着。在这样的风潮下,“西装旗袍戏”变成了沪剧的一大标志。
在申曲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市民的日常活动空间、欣赏戏剧的习惯、关心的社会事件、穿戴的衣着服饰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促进了它表演形式的改变。两者之间彼此影响、相互照见。
(二)1938年以前的市民社会与剧本题材
与表现形式的改革一样,沪剧剧目的革新也无外乎以生存为本,迎合都市人群的喜好,从而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多元的摩登都市文化下,申曲在剧目内容上也必须打破传统农村剧目封闭、保守、低俗的风格,这就对新剧本的开发提出了要求。
这样的要求使沪剧史上第一批“编剧”——“说戏先生”应运而生。这和“幕表制”的引入也密不可分。所谓幕表制,就是将戏中人物和情节以类似提纲的形式单列出来,让艺人们在演出前的几小时过目,上台之后依此发挥。宋掌轻、徐醉梅、王梦良、范青凤等人可谓“说戏先生”中的翘楚,他们在20年代后期就从文明戏转入了申曲界③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下卷第十六篇,“戏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48页。。尽管他们的“剧本”流于口头形式,但一出戏的成功与否,和说戏先生表达能力及自身文化程度都有很大关系。宋掌轻曾口述:
“演出之前,先安排好分幕分场,写出幕表。这项工作不能一个人做,一定要把担任角色的主要演员凑在一起来商量,哪场是幕外,哪场是幕里。如果全本是十一场的话,就要按五场幕外,六场幕里分好。再规定好每一场戏的主要情节。确定哪些角色在这场戏里出场,哪些演员先出场,都做了规定。每场戏不能像‘拉洋片’那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拉过去就算数,而是要按照戏剧艺术的规律:做好构思与安排。规定了每场的情节以后,戏就初具轮廓了,然后就分派角包。演员少,角色多的,就要把戏不重的角色合并起来(这也要与几个主要演员商量),然后分幕分场写出来再广泛吸收大家意见。这样,一张幕表就基本上算写成了。”④宋掌轻口述,范华群整理:《漫话幕表戏》,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2集,上海艺术研究1986年,第21页。
可见,为了让演员更好地演出,说戏先生们不但要帮他们理解情节,还要帮他们描摹、分析角色的心理状态;只有高水平的说戏先生,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演员的表演天赋。
在说戏先生们的编排下,1921—1937年间,申曲引入了大量其他戏种的经典剧目。如弹词戏的《珍珠塔》《孟丽君》,京剧的《火烧红莲寺》《十三妹》,文明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光绪与珍妃》等⑤上海沪剧院艺术研究室整理:《1916—1938年演出资料辑录》,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2集,第130页。。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戏目广受欢迎,经久不衰,为当时市民所津津乐道,申曲自然也希望从中分一杯羹;而另一方面这些戏目大都是连台戏,一连上演多日,能更长久地吸引观众。
(三)1938年以后的市民社会与剧本题材
1937—1938年可视作沪剧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战争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上海滩的娱乐行业,此前红火的电影一度停滞。包括申曲在内的戏剧艺术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适时弥补了这一时期城市市民的精神文明需求。
如上文所述,由于自身缺陷,申曲在传统戏目上的表演并不占优势,他们主动将目光转向了电影、话剧以及中外文学作品。这些剧目的内容大多需要以时装戏的形式呈现,为时装戏成为沪剧主流奠定了基础。
申曲对电影的改编相对较早。早在1924年,宋掌轻就将电影《孤儿救祖记》编排成了幕表戏①《上海沪剧志》,《大事记》,第7页。蔡丰明:《上海都市民俗》,第277页。,是为沪剧史上的第一例。1941年,“沪剧”正式定名之后,真正“沪剧”意义上的“开山之作”是改编自美国电影的《魂断蓝桥》②《上海沪剧志》,《大事记》,第68页。。对话剧的改编则有1938年的《雷雨》③《上海沪剧志》,《大事记》,第66页。、1942年的《原野》④《上海沪剧志》,《大事记》,第68页。等;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有1930年的《啼笑因缘》⑤《上海沪剧志》,《大事记》,第65页。、1939年的《骆驼祥子》⑥《上海沪剧志》,《大事记》,第67页。。1944年,还以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底本,改编成了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的《铁汉娇娃》⑦《上海沪剧志》,第二章《剧目》第二节“清古装戏”,第64页。。在原创剧本上,沪剧则借鉴《离婚怨》的成功经验,主要取材于社会时事新闻,创作了《黄慧如与陆根荣》⑧《上海沪剧志》,第二章《剧目》第三节“时装戏”,第65页。《阮玲玉自杀》⑨《上海沪剧志》,第二章《剧目》第三节“时装戏”,第66页。《阎瑞生》⑩《上海沪剧志》,第二章《剧目》第三节“时装戏”,第67—68页。等。
从这些经典的申曲戏目中,可知上海市民所崇尚的艺术风格大多反映现实、贴近生活。而像《离婚怨》《啼笑因缘》之类表现家庭伦理、男女爱情的内容,尤其受到都市妇女群体的广泛欢迎⑪《上海沪剧志》,《大事记》,第7页。蔡丰明:《上海都市民俗》,第277页。。
三、小 结
从源于乡村的花鼓戏到深入都市的沪剧变迁中,可以看到地方戏曲和近代上海市民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沪剧努力融入现代市民社会,通过在名称、形式、内容上的不断改变,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在海派文化的主流中占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上海社会的各类事件,小到家长里短、中到社会新闻、大到抗战救国均在沪剧中有所折射,依此创作出《离婚怨》《阮玲玉自杀》《魂断蓝桥》等剧目。
除本文的上述研究之外,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和沪剧之间关系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问题。比如沪剧对京剧、弹词、话剧等其他曲艺的借鉴传承有哪些表现,沪剧对周边城市的社会生活是否有所影响,20世纪的报纸、杂志、广播等传媒业对沪剧的发展有没有推动作用等等,都值得继续探讨研究。希望本文能开启一个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新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