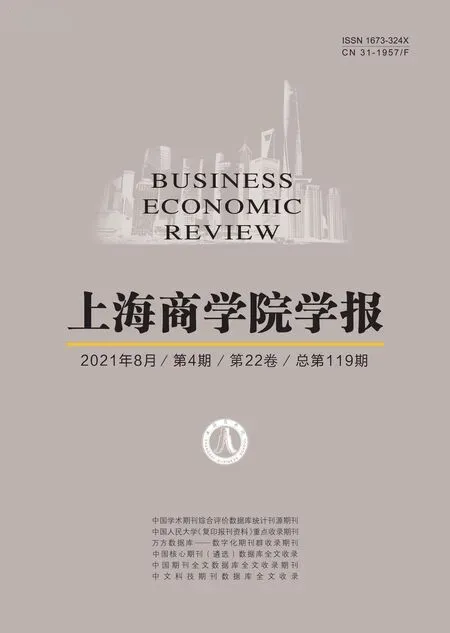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过去与未来①
[加] 唐纳德·麦克雷
胡加祥 孙安艺 译
一、国际经济法:一个国际公法视野下的新学科
国际经济法在国际公法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之下是被如何看待的呢?我并非因为精通经济学、国内贸易救济或国际商法才关注国际经济法的,相反,我是作为一名国际公法律师来关注和探讨国际经济法的。多边条约制定过程中的贸易谈判回合以及贸易协定对国际法机构和规范体系的影响都令我颇感兴趣。②McRae D M, Thomas J C,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and Multilateral Treaty-Making: The Tokyo Round”,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3, Vol.77, pp.51—83.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anada-USFree Trade Agreement,CUFTA)签订后,争端解决成为我关注的焦点,包括该协定第18章[现《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第20章]的国家间争端解决以及第19章规定的对补贴和反倾销决定的复审程序。
国际经济法领域在当时到底是如何吸引一位国际公法律师关注的呢?
首先,这要归因于律师的稀缺。就此而言,加拿大的经历的确与美国不同,因为美国国内的贸易法实践更加丰富和完善。但美国只是这方面的个例,加拿大的经历则反映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况。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时期,若美加两国发生贸易争端,加拿大会聘请美国律师来处理。涉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的事项则由贸易政策专家处理。①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在加拿大外交部法律局担任学术顾问时,我的一位同事被派往关贸总协定司,条件是她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律师!
其次,法学院没有开设国际贸易法或范围更广的国际经济法的学术课程。当时设立的课程通常是有关国内贸易管制、海关法和贸易救济等,相关课程仅用一章介绍GATT的内容。②参见 Castel J G, De Mestral A L C, Graham W C, The Canadian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Export and Im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Toronto: Edmond Montgomery Publications, 1991.美国的法学院则并非如此。
再次,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学术文献匮乏。当然,约翰·H·杰克逊(John H·Jackson)、鲍勃·胡德克(Bob Hudec)、安德烈斯·洛温菲尔德(Andreas Lowenfeld)和肯尼斯·达姆(Kenneth Dam)等学者都是笔耕不辍。欧洲也有例外,如乔治·施瓦曾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和多米尼克·卡罗(Dominque Carrerau)。国际经济法领域易于梳理的学术文献对于任何跟踪研究国际经济法的人都是一大优势,但是该领域在许多方面依然未被开垦。
最后,国际经济法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公法律师所漠视。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乔治·施瓦曾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曾就国际经济法撰写过大量文章,他还和伊格纳兹·塞德尔·霍恩费尔登(Ignaz Seidl Hohenveldern)在海牙国际法学院教授国际经济法课程③Schwarzenberger G,“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Recueil des Cours,1966,Vol.117, p.1; Seidl-Hohenveldern I,“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Recueil des Cours, 1986, Vol.198, p.1.,詹姆斯·福西特(James Fawcett)也讲授过贸易与金融的课程④Fawcett J,“Trade and Fina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Recueil des Cours, 1968, Vol.123, p.125.。但是,国际公法的主流教材仍然很少提及国际经济法,甚至不提。⑤参见 McRae D M,“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cueil des Cours, 1996, Vol.260, pp.111—113.
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
今天,如果我们再来审视国际经济法这一领域,我们不难断定:上述所有情况都已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均不乏从事国际经济法各个方面工作的律师。①国际经济法协会(SIEL)的发展以及其会议参与度之广泛都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法学院都将国际贸易法纳入了课程体系,有些还包含国际投资法。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这要部分归功于约翰·H·杰克逊创办的《国际经济法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这一平台的推动。此外,国际公法律师对国际经济法的关注度也在显著提升。
现在,有人会对国际经济法与国际贸易法之间的明显界分提出异议。有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部分,不能被视作可能或实际上与国际公法割裂的体系。正如乔尔·特拉希曼(Joel Trachtman)所指出的,国际经济法的兴起瓦解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之间的分界。②Trachtman J P,“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evolution”, 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6, Vol. 17, p.33.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研究、实践或撰写关于GATT法律的这一波人,无论是来自学界、政府部门、GATT或是律所,他们大多都不具备国际公法背景。③约翰·H·杰克逊曾经告诉我,如果他没有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工作过,他可能不会从事贸易法领域的工作。相反,他会继续专注研究他的“老本行”——合同法,并以合同法教授为职业。如此看来,尽管美国可能失去了另一个科尔宾(Corbin)或威利斯顿(Williston),亦或是另一个格兰特·吉尔摩(Grant Gilmore)(虽然我不认为约翰·H·杰克逊是一个反传统的人),但世界却在GATT和WTO法律方面收获极丰。
国际投资法领域也是如此。当投资争端提交仲裁庭时,仲裁员的人选主要来自国际商事仲裁界,而非国际公法界。仲裁案件的辩护律师也普遍不精通国际公法。这种情形在当今仍然存在,但出现在投资领域就特别令人感到讶异,毕竟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BITs)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自于国际公法,如国际最低标准(公平和公正待遇原则) 和征收。这些话题在国际法学界以及国际谈判中涉及已经有点历史了。
那么今天,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之间,或者说国际公法律师与国际经济法律师之间的关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某种层面来讲,变化是极大的。有些学者或实务工作者,或者兼具两种身份的人,被看作是国际公法与国际投资法双重领域的领军人物,例如何塞·阿尔瓦雷斯(Jose Alvarez)、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迈克尔·赖斯曼(Michael Reisman)、布里吉特·斯特恩(Brigitte Stern)以及史蒂芬·施韦贝尔(Stephen Schwebel)大法官。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例如弗洛伦蒂诺·费利西亚诺(Florentino Feliciano)以及乔治·阿比·萨博(Georges Abi Saab),他们既是国际公法专家,也是国际贸易法专家。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变化是争端解决机构发展的结果,包括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和其他投资仲裁庭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上诉机构,这些争端解决机构都亟需争端解决方面经验丰富人士的专业技能支持。
除了上述国际公法名家外,现在涌现出一代新的学者,他们拒绝“国际公法”或“国际经济法”的标签,而是将自己视为精通贸易、投资、人权和环境法等各领域的学者,并能够将每一领域的专业技能应用于对其他领域问题的分析。在2010年巴塞罗那召开的国际经济法协会(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SIEL)会议上,各论坛小组不乏这样的年轻律师,他们精通贸易法、投资法以及国际公法。①巴塞罗那会议的日程请参见http://www.sielnet.org/page-466207(2014年8月14日访问)。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渊源关系
然而,如果一代跨越各国际法分支学科的律师真的正在涌现的话,国际公法律师能否更好地理解国际经济法机构的运作以及国际经济法体系的实体规则呢?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和投资法界是否对国际公法的范围、适用和效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
以下是本人对当前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关系的一种初步的、很大程度上基于印象的进展情况的描述。首先探讨的是国际公法对国际经济法(包括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的影响和作用。国际公法的概念被用于国际贸易法已经屡见不鲜了。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协议》(DSU)第3条是有关条约解释的原则,该条款就直接把解释国际公法的原则纳入其中。虽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VCLT)第31条第(1)款(c)项[这是原文作者的笔误,实际上应该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因将任何有关的国际公法规则都纳入条约解释过程,它的确切相关性和适用范围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在解释GATT第20条规定的例外情况时,预防的概念(Concepts of Precaution)或《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中包含的诸多概念已经出现在争议双方的论点或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的裁决之中。上诉机构的部分成员(包括一些专家组成员)是国际公法律师,这无疑促进了国际公法规则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适用。②在最初的由七名成员组成的上诉机构中,有两名成员拥有的主要是国际公法方面的教育培训背景,即弗洛伦蒂诺·费利西亚诺(Florentino Feliciano)和克里斯托弗·比(Christopher Beeby),随后加入的乔治·阿比·萨博(Georges Abi Saab)亦是国际公法专家。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人们同样能见到吸收国际公法概念的现象。例如,国家责任条款所阐述的必要性概念(Concept of Necessity)。③参见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12 May 2005; Enron Corp. et 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22 May 2007.双边投资协定的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treatment,MFN)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的争论,部分也是由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④参见Anglo-Iranian Oil Co. (United Kingdom v. Iran)(1952), ICJ Rep.93; Case Concerning Rights of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Morocco(France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52), ICJ Rep.176.以及某个仲裁庭⑤Ambatielos Arbitration (United Kingdom–Greece), (1956), 12 U. N. R. I. A., p.83.此前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引起的。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ILC)关于MFN条款所作的解释草案亦经常在投资仲裁中被援引。
若检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学术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领域对国际公法概念的相关性和适用性的讨论都很热烈。一些特别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约斯特·鲍威林(Joost Pauwelyn)的经典著作《国际公法的规范冲突》①Pauwelyn J,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和伊莎贝拉·范·达默(Isabelle van Damme)的著作《WTO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②Damme I V,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当然还有约翰·H·杰克逊的著作《国家主权,WTO,与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③Jackson J H, Sovereignty, the WTO and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当换个角度看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对国际公法以及国际公法律师产生的影响时,我们会发现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其中当然不乏一些积极的影响。例如,沃恩·洛伊(Vaughan Lowe)的国际法著作④Lowe V, International Law, Clarendon Law Se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被誉为是詹姆斯·布赖尔利(James Brierly)经典著作《万国公法》(The Law of Nations)的传承之作,其中就涵盖了一章题为“全球经济”(“The Global Econmy”)的内容,这是布赖尔利或其继任编辑汉弗莱·沃多克爵士(Sir Humphrey Waldock)当时未曾设想的。《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刊载的文章也不限于传统国际法的各个领域,还包括国际贸易和投资法领域。德列夫·瓦格茨(Detlev Vagts)在该杂志创刊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指出,《美国国际法杂志》这样做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⑤Vagts D 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Vol. 100, No.4, pp.769—782.
此外,在纯粹的国际公法事项中,任何国际争端解决都会提及WTO争端解决机制。⑥参见Shaw M N,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39—941; Nauyen Q D,Daillier P, Forteau M,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que, 8th ed., Paris: L.G.D.J., 2009, pp.1241—1269.可以说,WTO争端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视为国际争端解决体系的一部分。以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的投资争端解决也被视为国际争端解决的一部分。然而,目前涉及国际贸易和投资争端解决的讨论都仅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下去。
当我们将关注点从争端解决机制转向WTO协定下的实质性义务时,会发现这些规则内容总体上仍属于国际贸易律师的专业知识范畴。虽然国际法的经典教材讲的是海洋法核心原则、国际环境法或国际人权,它们偶尔也会涉及国际贸易法的核心原则,但这只是例外。国际投资法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如前文提到的,该领域与外国人待遇有关的一些核心原则正是源于习惯国际法。
前述观点可以被国际法委员会这一典型的国际公法机构的工作所佐证。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的议题中,有一个议题涉及嗣后协定(Subsequent Agreements)与嗣后惯例(Subsequent Practice)对条约解释的影响。⑦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报告(2013年)A/68/10,第四章。该议题的特别报告员调查研究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处理嗣后惯例的做法。WTO上诉机构的争端解决实践被视为规范的做法。
然而,对于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当审议投资仲裁庭对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这样的问题出现时,委员会内部普遍认为该议题不适合国际公法律师,因为它过于技术性,应该属于WTO或其他技术性机构的管理范畴。上述观点被大多数人接受,尽管国际法委员会曾经审议过最惠国待遇条款,并且于1978年出台了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草案。⑧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报告(1978年)A/33/10,第二章。
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审议“国际投资法中公平与公正待遇”这一议题的提案同样遭到了反对,这部分归因于人们的无知——这难道不是与最惠国待遇问题同属一类的问题吗?部分归因于人们对未知的恐惧——难道没有其他机构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吗?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归因于人们这样一种认知,认为这不是国际公法律师应该研究的事项。投资法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法律体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法。
国际法委员会现在已经开始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了。令许多委员惊讶的是,当他们开始讨论这一议题时,发现该议题的核心问题都是关于条约解释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条约的嗣后惯例议题有所交叉、重叠,而后者是委员会成员眼中毋庸置疑的国际公法议题。
事实上,对国际经济法的内容和相关性缺乏认识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国际法委员会。尽管国际贸易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条约解释规则在WTO协定解释过程中的适用作了很多分析,从事条约解释工作的国际公法律师并不一定总是密切关注这些学术研究及其背后所依据的法理基础。⑨安东尼·奥斯特的著作《现代条约法与实践》(第二版)就几乎没有提到WTO上诉机构的解释实践。参见Aust A,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有一位国际法学者将解释机构在条约解释时考虑嗣后惯例的做法作为解释的补充手段,他对WTO上诉机构的解释方法进行如此评价:“对解释普遍持严格谨慎的态度,所作解释不会明显超出成员方自条款或条约的文本含义中所得出的共同意图。”⑩Nolte G,“Subsequent Practice as a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in Jurisprudence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in The Law of Treaties Beyo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44.这一论断与伊莎贝拉·范·达默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上诉机构解释过程的复杂微妙性,恐怕是见仁见智。⑪Damme I V,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为什么国际公法律师一直不愿意将国际经济法视为与海洋法、人权法或环境法同等重要的国际法体系的一部分呢?部分原因是受传统影响。如果你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国际经济法不是国际法的一部分,你以后自然也很难接受将该学科纳入国际法体系。不过这种思想上的僵化是暂时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国际经济法协会中的年轻学者很快会带来改变。
除上述传统因素外,造成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之间隔阂的原因还有很多。人们对贸易法和投资法或更广范围的国际经济法怀有若干重疑虑。第一重疑虑涉及人们如何看待贸易法和投资法。国际公法的建构历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进步,即缔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国际法律师绝不仅仅是识别和适用法律规则的技术人员,他们是在倡导采用规则体系来控制国家行为,限制主权滥用,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在20世纪初,最终促成国际联盟成立的众多有关国际组织的提议都证明了这一点。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也是受到上述目标的激励。尽管美国偶尔会质疑习惯国际法的现实存在和约束力,人们时不时也会对国际法和国际法律师的作用产生类似的看法。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国际法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ASIL)内就有过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角色的讨论,参与讨论的有学者和前法律顾问。这场讨论表明人们对于法律顾问作用的理想看法占主导地位。具体而言,法律顾问除了就国际法问题向国务卿提供咨询意见外,还应担当起国际法倡导者的角色。①“The Role of the Legal Adviser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Established by the ASIL and the ILA (American Branch),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Vol.85, p.358.
四、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分野
国际经济法未能契合传统国际公法律师改善世界的价值追求。这一点在菲利普·奥斯顿(Phillip Alston)与乌勒·彼得斯曼(Ule Petersmann)著名的学术交锋中得到生动体现。②Petersmann E U,“Time for a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for Integrating Human Rights into the Law of Worldwide Organizations: Lessons from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Vol. 13, No.3, pp.621—650; Alston P,“Resisting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Human Rights by Trade Law: A Reply to Petersmann”,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Vol.13, No.4, pp.815—844; Petersmann E U,“Taking Human Dignmity, Poverty and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s More Seriously, Rejoinder to Alston”,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Vol.13, No.4, pp.845—851.人权被认为是建立在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而贸易法则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New-liberal Economic Orthodoxy)之上的。这一无关道德(Amoral)的学科竟然与人权法这类主要关注法的核心与基本价值的领域相提并论,几乎被视为是一种公然冒犯。在投资法领域,人们也有围绕投资仲裁庭这一领域的合法性展开讨论。③参见 Franck S D,“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ternational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 in Fordham Law Review, 2005, Vol.73, No.4, pp.1521—1625.投资法还背负着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IEO)的争论以及控制跨国公司活动的持续质疑。
可见,人们对国际经济法和人权法或环境法的看法截然不同。律师之间有关人权法和环境法的争论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有约束力的原则。国际经济法是条约法,其约束力毋庸置疑,针对国际经济法的争论不在于它是否具有约束力,而是更侧重于其是否应该存在!
总之,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之间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传统国际公法理念没有为国际公法律师提供思考国际经济法问题的理论框架。国际公法律师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律师一样,往往不信任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权和环境法以实现崇高目标为己任,而国际经济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
对国际贸易法和投资法的第二重疑虑源自几乎是顷刻间发展起来的强制性争端解决制度。 20世纪60年代,国际仲裁的应用还普遍被视为是一个失败的构想,国际法院也不怎么受人待见。国际法院在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针对南非提起的诉讼中作出的臭名昭著的裁决①South West Africa, Second Phase, Judgment, ICJ Reports, 1966, p.6.引发了人们对国际法院的不满,认为国际法院偏袒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毫无益处。总之,当时的国际社会并未对通过司法或仲裁途径解决国家间争端抱太大希望。
有鉴于此,当美国和加拿大依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8章频繁诉诸该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援引协定第19章建立的双边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决定审议机制,与此同时,世贸组织成员也开始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一切都让一些习惯认为“国家往往倾向通过谈判而非司法手段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律师看得眼花缭乱。不愿就其他事项诉诸争端解决的国家为何在国际贸易法领域却欣然接受了争端解决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本不承认这一变化。②参见 Guillaume G,“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1995, Vol.44, pp.848—892.对争端解决在GATT框架下的演变缺乏了解可能是导致国际公法律师在早期不认可WTO争端解决作为类似于司法解决手段的原因;而“专家组”“上诉机构”这些容易混淆的名词以及它们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的“建议”也无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结果从国际公法角度看,依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和双边投资协定提起的争端解决的案件激增,这似乎颇令人费解。主权国家在外国国内法院被诉时会迅速援引国家或主权豁免,面对他国提起关于投资者外交保护的诉讼时会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然而它们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提起诉讼时,却为何如此情愿接受临时仲裁庭的管辖呢?这似乎完全违背了国家规避司法或仲裁途径解决争端的国际公法范式。③需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诉诸国际法院和各种形式的国际仲裁的国际争端明显增多,但仍未达到WTO争端解决或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的规模。
有观点认为,强大的经济利益是国家接受贸易或投资争端解决的首要激励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于认为贸易法和投资法是经济利益影响的产物,这使得贸易法和投资法有别于国际公法的其他领域。这引发了合法性危机——既然如此,一个WTO专家组如何能够像美国龙虾案④Report of the Panel,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85/R, 11 March 1998;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10 December 1998, WT/DS85/AB/R.和巴西轮胎案⑤Report of the Panel, 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WT/DS332/R, 6 December 2007;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12 March 2007, WT/DS332/AB/R.一样,就本质上属于环境法的问题做出裁决呢?文化和思想的冲突导致一种观点认为,贸易问题被允许凌驾于环境问题之上了。⑥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Esty D C,“Bridging the Trade-Environment Divide”,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Vol.15, pp.113—130.类似的合法性问题也在投资争端解决中被提起,尽管往往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例如结合宪法条款进行探讨。①参见Harten G V,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一个在未获国内法院那样宪法保障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临时仲裁庭怎能取代通常由国内法院发挥的角色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9章中的双边复审专家组安排也遭到了类似的合宪性挑战。②参见 Nat’l Council for Indus. Def., Inc. v. United States, 827 F. Supp.794, 800 (D.D.C. 1993); Am. Coal. for Competitive Trade v. Clinton, 128 F. 3d 761, 764 (D.C. Cir. 1997).总之,贸易法和投资法领域的争端解决就是不符合国际公法的争端解决范式。
对国际公法律师而言的第三重疑虑,或用约翰·H·杰克逊的话来说是“困惑”,在于国际贸易法中国际性和区域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种条约交错的混乱性不言自明。当前,既存在一个多边贸易机制,同时还存在数个区域机制,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方共同市场。此外,还有各种双边、三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上述多边和区域机制之间都存在交错重叠关系。由于包含着彼此重叠的优惠规定,这些协定无不蕴含着条约冲突的种子。根据GATT第24条规定,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安排在多边贸易制度下是被允许的。可以这么说,学者们广泛使用的“意大利面条碗”这个术语已经不足以表明当今国际贸易法体系的混乱程度。
在国际公法语境下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区域国际法的概念在国际公法领域向来存在争议③Lowe V, International Law, Clarendon Law Se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53—55.,而且解决条约义务冲突的机制,尤其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也非常不健全④第30条的相关规定如下:3.遇先订条约全体当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第59条终止或中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在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适用。4.遇后订条约之当事国不包括先订条约之全体当事国时:(a)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适用与第3款之同一规则;(b)在为两条约之当事国与仅为其中一条约之当事国间,两国彼此之权利与义务依两国均为当事国之条约定之。。第30条规定的“后法优先”规则(Later in Time Rule)并不能有效处理交错重叠的区域和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许国际法的某些领域也有类似混乱之处。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在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于实践、法理或学术方面尚待充分发展的领域也存在多边和区域机制的重合。⑤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附属于《联合国宪章》的论点,参见 Simma B,“NATO, the UN and the Use of Force:Legal Aspect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 Vol. 10, pp.1—22.
倘若连国际贸易法圈内的人都觉得,要厘清多边、双边和区域贸易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多么困难,那么对于该领域之外的人来说,国际贸易法体系就更加高深莫测了。国际公法律师很难将国际贸易法纳入他们原本熟悉的规则体系之内。
五、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法
当然,问题是要搞清楚上述这一切是否都重要。国际经济法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这些发展反映了最新的条约义务和国家实践,同时也在丰富和完善法学理论和学术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包括从理论构建到经验批判、从技术性规范到实践案例等各个方面。因此,在更广泛的国际公法领域,人们是如何看待国际经济法的,这一问题真的重要吗?其实,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国际经济法都将继续发展。
然而,在思考国际经济法未来面临的挑战时,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范围更广的国际法语境下进行审视,而且我们要应对更宏观的问题: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之间的关系现状是否对我们看待国际经济法的方式有所启示?是否为我们深入观察国际公法的传统思维方式提供了路径?难道上述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的变化仅仅是该委员会选举失当的结果吗?是错误的人选进入了该委员会吗?或者说,这种现象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今国际公法学者,或许还有主权国家,是如何理解和看待国际经济法的?
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公法律师对上述变化的反应源自于对国际公法的狭隘认识,而这种狭隘认识是受到国际公法先驱的影响,他们认为国际法纯粹是国与国之间的聚焦主权、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规则体系。①参见 McRae D M,“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cueil des Cours, 1996, Vol.260, pp.117—119.这样一种范式完全无法用来处理涉及外交保护和人权保护等涉及私人主体的行为。然而,这对于贸易领域却是意义重大,因为交易是私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这种范式还反映在国际法律师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点关注,他们将习惯国际法作为从事任何一个国际法领域的起点,从而将不是根植于习惯国际法而是以条约为基础的法律制度边缘化。
国际公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彰显了过于狭隘地界定一门学科的危害。国际公法的发展历史表明其正在修正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思想、新需要和新概念。一个有目共睹的例子便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个人刑事责任已被纳入国际法专业术语,这表明个人主体被国际法承认了。通过确立国际组织国际法律人格这一新概念,国际法还着手解决国际组织的法律责任问题。国际法还发展了个人权利,并建立起保护人权和少数族群权利的法律体系,推动形成国际环境法等新的领域。这些变化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国际法体系还要适应比其他国际法领域发展得更为迅速的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机构与实践。因此,各规范体系之间的整合过程相对缓慢就不足为奇了。
内部拥有多个分支学科的国际经济法体系也应当吸取上述经验教训。当前,尽管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领域的核心原则——非歧视原则是高度重叠的,但现实却是贸易法律师只关心贸易,投资法律师只考虑投资。这正是约瑟夫·韦勒(Joseph Weiler)在巴塞罗那国际经济法协会上的演讲中提出的观点。②巴塞罗那会议的日程请参见http://www.sielnet.org/page-466207(2014年8月14日访问)。从规范角度讲,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虽然律所在贸易和投资两个领域都有业务,但从事贸易法和从事投资法的执业者通常是彼此分工的。WTO专家组的成员也往往不是投资仲裁庭的仲裁员,尽管上诉机构的部分前任和现任成员是个例外。
此外,投资仲裁庭处理贸易法概念时,往往缺乏对贸易法本质和适用的充分认识。①Kurtz J, Converging System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 Vol.27, No.3, pp.865—868.同样,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处理多边贸易秩序与区域机制之间的关系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贯穿土耳其纺织品案②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Turkey-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Products, WT/DS34/AB/R, 22 October 1999.、墨西哥软饮案③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Mexico-Tax Measures on Soft Drinks and other Beverages, WT/DS308/AB/R, 6 March 2006.、巴西轮胎案④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WT/DS332/AB/R, 12 March 2007.的一条主线是,当区域贸易协定与WTO协定项下的义务发生潜在或现实冲突时,WTO协定永远优先适用。但是,GATT第24条是规定了“至上原则”(a System of Supremacy)吗?抑或“互补原则”(a System of Complementarity)?不仅如此,WTO至上是事实上最优的政策选择吗?如果WTO成员方意图追求的是WTO规则至上,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疯狂缔结区域贸易协定呢?
因此,对贸易和投资机制以及相关学者和从业者来说,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超越其学科自身的直观界限,从其他相关和重叠的学科领域中获得启示。这是贸易与环境之争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对此,上诉机构已经作出了回应。正如托马斯·科蒂尔(Thomas Cottier)在其载于《国际经济法杂志》的开创性文章中所形象地指出那样⑤Cottier T,“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Monetary Affairs”,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0,Vol. 13, No.3, pp.911—937.:“国际金融和货币事务是当代国际经济法律师所面临的挑战”。
在这方面,约翰·H·杰克逊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光辉典范——永远关注未来的挑战,试图理解学科的混乱与困惑,尝试着使旧法适应新环境。对于约翰·H·杰克逊来说,国际经济法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经济法是一个鲜活的、不断演变的机制。作为律师,我们有责任反思这种变化,解释这种变化,推动其变革,并始终向前看。这一直是约翰·H·杰克逊对待国际经济法坚守的信条。
- 上海商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势能
——双碳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