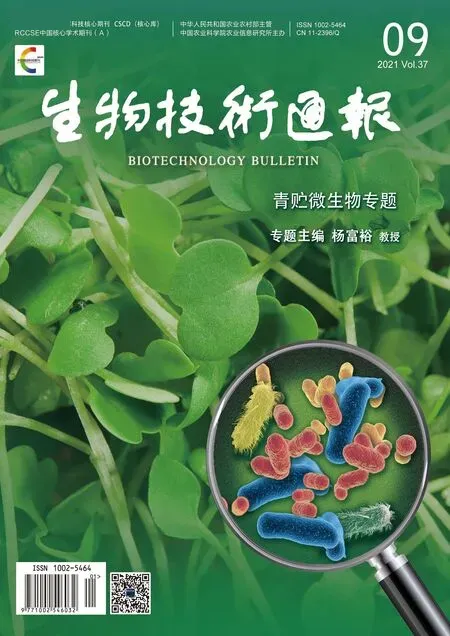植物表面乳酸菌分布研究进展
田静 张建国
(华南农业大学南方草业中心,广州 510642)
青贮是保存青绿多汁饲料营养成分最先进、最经济、最简便的贮藏方法,为草食动物提供全年优质牧草的最有效技术[1]。它是通过乳酸菌(LAB)利用牧草中的水溶性碳水化合物产生以乳酸为主的有机酸,降低pH,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从而保存牧草营养。所以,牧草表面附着的LAB菌群在青贮过程起主导作用,是决定青贮优劣、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1]。与青贮饲料发酵相关的LAB有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片球菌属(Pedicoccus)、肠球菌属(Enterococcus)、乳球菌属(Lactococcus)、明串珠菌属(Leuconostoc)、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和魏斯氏菌属(Weissella)[1-2]。产乳酸的球菌如链球菌属、明串珠菌属、乳球菌属、肠球菌属和片球菌属的一些种,通常在青贮初期迅速繁殖,使青贮饲料pH下降,然后乳杆菌属的菌种开始旺盛繁殖,进一步将pH降低至抑制不良微生物生长和增殖的水平[3]。其中,同型发酵LAB如乳杆菌属和片球菌属等的菌株发酵葡萄糖只产乳酸,能快速降低青贮饲料pH,营养损失较少;而异型发酵LAB如魏斯氏菌属的菌株发酵葡萄糖产生多种发酵产物,部分碳源以气体的形式损失,但其在改善青贮窖开封后的有氧稳定性效果显著[4],因此,LAB的种类对青贮饲料的发酵品质具有不同的意义。
通常情况下牧草表面附着的LAB数量较少,在生产实践中,常常通过添加LAB弥补其数量的不足,进而改善其青贮发酵品质[3]。但若牧草表面附着优良LAB数量较多,添加LAB则是一种浪费,增加了生产成本。此外,有研究表明牧草表面附着LAB的发酵效率高于市售LAB接种剂[5]。若能根据牧草的生长时期或生产管理改善牧草本身LAB的数量和种类,使LAB在牧草适宜收获期时的数量最大、种类最佳,如玉米的成熟初期[6],而尽量避免在LAB最少时收获[7]。因此,确定影响植物表面LAB菌群的关键因素可能对未来优化青贮饲料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对影响植物表面LAB的主要因素进行了阐述。
1 植物种类及特性
1.1 植物种类
新鲜植物表面附着LAB数量及种类差异较大,一般低于105CFU/g FM,主要是乳杆菌属、肠球菌属、魏斯氏菌属、乳球菌属和明串珠菌属的一些种[1,7]。如森地敏树和大山嘉信[8]调查了日本农林水产省畜产试验场内201点新鲜牧草的LAB数量,发现乳杆菌属、明串珠菌属和片球菌属的数量普遍低于102CFU/g FM。蔡义民等[9]发现意大利黑麦草(Lolium multiflorum)在刈割时总LAB数达105CFU/g FM,主要为乳球菌属,乳杆菌属仅为102CFU/g FM。Zhang等[10]对多年生黑麦草(Lolium perenne)的研究发现,肠球菌属的数量最多,高达105CFU/g FM,其次为明串珠菌属,为104CFU/g FM,片球菌属和乳杆菌属的数量较少,在102CFU/g FM水平左右。Stirling和Whittenbury[11]在生长植物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分离的400个菌株中,明串珠菌属的菌株占80%,其余的为乳杆菌属和片球菌属。
热带牧草较温带牧草可能具有较多的异型发酵LAB,会导致青贮过程中乙酸型发酵。如玉米(Zea mays)表面LAB主要是异型发酵的乳球菌属、魏斯氏菌属和明串珠菌属,有时会检测到很少同型发酵的乳杆菌属[12-14];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表面主要是乳球菌属,很少量的乳杆菌属、明串珠菌属和片球菌属[14-15];高粱(Sorghum bicolor)表面主要是乳球菌属、魏斯氏菌属和乳杆菌属[14,16];苏丹草(Sorghum Sudanese)表面主要是乳球菌属[14];杂交狼尾草(P. americanum×P. purpureum)和银合欢(Leucaena glauca)表面乳杆菌属最丰富[17-18];柱花草(Stylosanthes)主要是乳杆菌属、肠球菌属、魏斯氏菌属和乳球菌属[18]。而鸭茅(Dactylis glomerata)表面主要是链球菌属[19];燕麦(Avena fatua)表面主要是乳杆菌属、其次是异型发酵LAB,包括乳球菌属、魏斯氏菌属、明串珠菌属和片球菌属[18,20];披碱草(Elymus nutans)表面主要是乳杆菌属、魏斯氏菌属、明串珠菌属和乳球菌属[21];苜蓿(Medicago sativa)表面主要是肠球菌属、明串珠菌属、乳杆菌属、魏斯氏菌属和片球菌属[13,15,22];红豆草(Onobrychis viciifolia)只有乳杆菌属[23]。
在种水平上,植物乳杆菌(Lb. plantarum)、短乳杆菌(Lb. brevis)、干酪乳杆菌(Lb. casei)、乳酸乳球菌(Lc. lactis)和融合魏斯氏(W. confusa)是牧草表面最主要的LAB。陈鑫珠[24]研究了广东的13种植物物种或品种表面上的微生物,发现植物种类对LAB的影响很大,其中植物乳杆菌、乳酸乳球菌和融合魏斯氏菌分别占LAB总数的30.2%、23.9%和22.6%;大麦(Hordeum vulgare)、小麦(Triticum aestivum)和燕麦中乳酸乳球菌和乳酸乳球菌乳酸亚种(Lc. lactis subsp. lactis)共占51.9%。狼尾草属牧草表面主要是植物乳杆菌、戊糖乳杆菌(Lb.pentosus)、乳酸乳球菌、柠檬明串珠菌(Le. citreum)和融合乳杆菌[25],玉米秸秆表面附着的主要LAB是植物乳杆菌、戊糖乳杆菌和短乳杆菌,占LAB总数的85.6%[26];苜蓿表面主要是食窦魏斯氏菌(W.cibaria)、植物乳杆菌、戊糖片球菌(P. pentosaceus)、戊糖乳杆菌、赫伦魏斯氏菌(W. hellenica)、短乳杆菌、布氏乳杆菌(Lb. buchneri)[22],燕麦主要是耐酸乳杆菌(Lb. acetotolerans)[27]。Minervini等[28]发现硬质小麦从分蘖期(4月初)到生理成熟期(7月初)均有植物乳杆菌的不同菌株存在。以上LAB具有较大的基因组,包含许多附属基因,且在菌株的水平上似乎已经多样化,具有保守的核心代谢途径,且大多数植物性食品的发酵都受其控制[29]。
1.2 植物表面营养组成及含量
植物表面附着LAB的数量和种类在不同茬次、部位和生长期存在差异,如紫花苜蓿、王草和象草表面LAB的数量随生育期的推进而增加[7,24];幼叶上的细菌多样性指数高于老叶[25];第二茬和第三茬王草和象草表面的LAB数量多于第一茬[24];玉米茎上存在的LAB种类比叶上的多[24]。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叶片特有的物理和营养状况引起的,而叶片的化学特性对其影响更大[30-31]。Wilson等[32]研究表明叶片上碳源的可用性是附生细菌定植的主要决定因素,其次是氮源。Tang等[31]研究也表明LAB种群大小与植物的水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且葡萄糖、果糖和蔗糖是LAB生长的优选碳源,在碳源选择上也有较大差异[33],如明串珠菌属的菌株只能利用葡萄糖、果糖、蔗糖、海藻糖、麦芽糖、甘露糖、核糖、木糖、阿拉伯糖、蜜二糖、棉籽糖和纤维二糖[34],戊糖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首选蔗糖和果糖作为碳源,屎肠球菌(E. faecium)首选蔗糖和木糖,而发酵乳杆菌(Lb.fermentum)首选棉籽糖,融合魏斯氏菌首选蔗糖和果糖,其次是木糖和葡萄糖[24]。此外,LAB的附着部位与其营养利用也有必然联系[24],如嗜果糖乳酸菌属(Fructobacillus)仅能从富含果糖的环境中分离到,如花蜜和水果表面[35]。因其基因组中编码碳水化合物运输、代谢基因的比例低于葡萄糖代谢的菌种[35]。戊糖乳杆菌和短乳杆菌能在富含半纤维素的小麦秸秆上生长良好[36],可能由于其具有参与半纤维素降解的基因,如α-葡萄糖醛酸酶、多糖脱乙酰酶、内切木聚糖酶/内切葡聚糖酶和乙酰酯酶[37]。除此之外,植物表面的总酚、游离氨基酸、可溶性蛋白和磷含量等对LAB的定植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38]。
各种养分在植物表面分布并不均匀,如叶片的大多数区域仅包含少量营养,且可能仅在少数区域相对丰富[39]。但若局部外渗,如腺毛或损伤部位,会形成大型细菌聚集体,如链球菌属主要出现在鸭茅的开花部位[40]。片球菌属和链球菌属菌株在未受损的植物表面稀少,甚至在植物的完整花序或种子未检测到,而在被昆虫破坏的叶子、草根的鞘和枯萎的草叶上能检测到[11]。此外,在牧草收获和青贮作业期间,植物材料上的LAB数量会显著增加,作物收获期间使用的机械设备和手持工具中也检测到许多微生物[1]。陈鑫珠和张建国[41]的研究表明王草和甜玉米的LAB数量从收获到切碎阶段显著增加,主要是乳酸乳球菌、柠檬明串珠菌和融合魏斯氏菌的增加。
1.3 植物叶表面结构
除叶片表面渗出的养分影响外,叶片特有的物理结构对LAB分布也有较大影响。如阔叶植物(豆类)中可培养细菌总数明显大于禾草或蜡质叶片的植物[42]。有些植物叶片有厚厚的蜡质表皮或较大的接触角,表现出较强的疏水性,不仅限制营养物质的扩散并会抑制叶面的润湿度来干扰细菌的定植[43]。Tang等[31]对不同象草品种叶片的形态结构进行观察发现:叶表面LAB数量与叶表皮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一方面表皮毛可能为微生物提供了附着的位点[44];另一方面,表皮毛可能影响叶表面的润湿性,短而密集的绒毛会增大叶表面的接触角,如紫花苜蓿下表面和玉米叶片上表面的长而尖的表皮毛可能会刺破小水珠因张力而形成的薄膜,导致叶表面形成的水滴极容易铺展开,导致接触角剧烈减小,叶片亲水性增加[45]。有些细菌产生具有表面活性剂特性的化合物提高叶片的润湿性,可能使营养从叶片组织内部更易扩散和外渗,从而为叶表面微生物提供营养[46]。
2 生长环境
2.1 温湿度
由于日间不同时间温度、湿度的变化,以及降雨等的影响,植物表面的温、湿环境变化较为剧烈,从而影响乳酸菌的附着、生长。当植物生长环境温度较高而相对湿度较低时,叶片蒸腾作用减弱,气孔关闭,叶片表面变得相对干燥且限制了叶内营养扩散到表面,减少了叶际微生物可利用的水分和营养,从而影响微生物数量和活性[43]。但若植物长期处于干旱,植物叶片将会水分亏损,细胞膜受到损伤,内容物外渗,尤其是脯氨酸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增加,使植物表面的微生物数量急剧增加[43]。LAB对外界温度的适应性广泛,但最适生长温度不同,如乳杆菌属的菌株最适生长温度为30-40℃,明串珠菌属为20-30℃,肠球菌属和链球菌属为37℃,而片球菌属为30℃[47]。研究表明高温下植物表面LAB的数量少于低温下的植物[47-49],陈鑫珠[24]研究表明10℃、15℃和20℃下生长的植物表面LAB数量明显高于25℃下的植物。肠膜明串珠菌(Le.mesenteroides)在10℃和15℃最多。植物乳杆菌和类肠膜魏斯氏菌(W. paramesenteroides)分别在20℃和25℃下最多。10℃和15℃时LAB种类较丰富。环境湿度会影响植物表面的水活度,从而影响微生物对植物表面水分和营养的利用率。通常,外界环境湿度越高,牧草表面LAB数量越多[33,38]。唐国建[38]研究表明一年生黑麦草在50%湿度下的LAB数量为4 lg CFU/g FM以下,而90%湿度下接近5 lg CFU/g FM。
2.2 季节、降雨和干旱
季节、降雨和干旱会显著影响植物表面的微生境。Stirling[50]报道LAB数量不受季节的影响,而有研究表明LAB的数量在整个季节中是变化的[6-7],且植物表面附着的LAB数量夏季(6-9月)比其它季节多[11],LAB种类春季(3-6月)比夏末秋初(9-10月)丰富[51]。陈鑫珠[24]研究表明植物乳杆菌和融合魏斯氏菌主要出现在2-4月种植的植物上,而乳酸乳球菌和乳酸乳球菌乳酸亚种主要出现在12月种植的植物上。关于降雨对植物表面LAB影响的研究很少,Guan等[49]从四川、重庆和贵州的五个主要生态区收集了48个处于乳熟期的玉米材料,LAB数量为2.9-6.4 lg CFU/g FM;魏斯氏菌属是这些玉米中主要的LAB,其次是乳杆菌属和明串珠菌属;玉米表面的乳杆菌属、醋杆菌属(Acetobacter)、乳球菌属和明串珠菌属的相对丰度与平均降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唐国建[38]研究表明不同干旱胁迫处理一年生黑麦草后,其表面的LAB数量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而显著下降,干旱程度很强时又显著上升。Daranas等[52]报道植物乳杆菌PM411可诱导编码干旱胁迫相关基因的表达,且多糖的合成有助于LAB承受干旱胁迫[53]。
2.3 氧气
通常,LAB被认为是兼性厌氧菌,依靠发酵代谢生长,但许多植物表面依然有LAB存在,这就使得其耐氧并具有抵御活性氧的能力。许多LAB都具有由cydABCD操纵子编码的基本电子传递链,但只有当植物表面的其它微生物产生血红素或甲萘醌时,才能激活其有氧呼吸[54-55]。LAB产生有氧呼吸的关键酶,如NADH氧化酶、NADH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细胞色素氧化酶等。Golomb等[56]研究表明植物表面的乳酸乳球菌KF147缺失了非核糖体多肽合成酶/聚酮化合物合酶,导致了其对H2O2和超氧化物自由基的高度敏感。目前,有关LAB呼吸代谢在植物组织上的生长和存活研究很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2.4 光照
通常光照也会影响植物表面LAB的分布。唐国建[38]研究表明16 h光周期条件下的一年生黑麦草表面LAB数量显著高于12 h和22 h光周期的。光周期为22 h时,同一成熟叶的上表面LAB数量显著低于下表面的,这可能是长时间光照显著改变了叶表面蜡质的晶体形态,使得上表面更加疏水,营养渗出更难[57]。尉志霞[58]研究表明中午刈割的紫花苜蓿表面附着微生物的数量小于早上或傍晚刈割的。紫外线较强会严重影响LAB的生长甚至致死[59],强的紫外线辐射通常是植物表面微生物必须适应表面环境最突出的特征之一,Sundin和Jacobs曾报道能忍受紫外线辐射的细菌能产生色素[60],而有关LAB产生色素的研究未见报道。
3 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植物表面的微生境,从而影响其表面菌群。陈鑫珠[24]研究表明黑麦草喷施少量尿素后LAB种类和数量显著高于不喷施或喷施较多的处理,且主要是植物乳杆菌。李春江[61]曾报道在一定范围内小麦表面的LAB数量随施氮量而增加,但施氮量进一步增加则减少LAB数量,原因可能是施肥造成的C/N比变化影响了微生物活性[62]。此外,施肥种类也不同程度地影响LAB的分布[15],但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牧草的刈割茬次和高度也不同程度地影响LAB,如陈鑫珠和张建国[63]研究表明热研4号王草的第二和三茬LAB的数量显著高于第一茬,且植株在2 m高度的LAB数量较多。第一茬、第二茬的1.0 m植株和第三茬1.5 m及以下的植株表面植物乳杆菌占优势,而第一茬1.0 m植株有少量的乳酸乳球菌,1.5 m及以上有少量戊糖乳杆菌;第二茬1.5 m及以上植株分离到融合魏斯氏菌;第三茬2.0 m植株有大量融合魏斯氏菌(84.1%)和少量食窦魏斯氏菌(15.4%)。Torriani等[64]连续研究了玉米收割前35天,及紫花苜蓿第二茬至第五茬附着LAB的变化,发现玉米上的LAB数量变化范围为1×101-3×105CFU/g FM,紫花苜蓿为2×101-4×103CFU/g FM;LAB数量与天气状况、生长时间无关;两种植物上的优势LAB都是植物乳杆菌和假肠膜明串珠菌(Le.Pseudomesenteroides),而紫花苜蓿上布氏乳杆菌也较多。最近,有研究表明混播或间作收获的混合材料附生的LAB多于单播或单作材料[65-66]。
4 其它因素
除以上影响因素外,海拔高度和表面其它微生物等也会影响植物表面LAB[29,59]。如在台湾海拔约800 m的两个农场中,最常见的LAB是异型发酵的明串珠菌属和魏斯氏菌属,而海拔约1 200 m处,乳酸乳球菌乳酸亚种是最常见的LAB[67],海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温度和紫外线等因素综合作用。因此,影响植物表面LAB的因素较复杂。若利用高通量测序、核酸分子杂交等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绿色荧光蛋白基因(gfp)与针对影响因子有响应的启动子连接起来,可能有助于了解LAB的一些特性以及它们耐受与植物相关的理化胁迫。
5 展望
提高对植物表面LAB的了解,根据草种、生长环境、利用时期等事先预测其上LAB的存在状态,或通过一些管理技术提高优良LAB的数量,可减少青贮饲料生产中LAB添加的盲目性。这不仅可以丰富青贮研究理论,促进低成本、高效率生产优质青贮饲料,也可更好地促进其他领域中LAB的利用,如发酵植物食品和饮料、植物促生剂、生物防治剂或服务于人类和动物健康的益生菌等[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