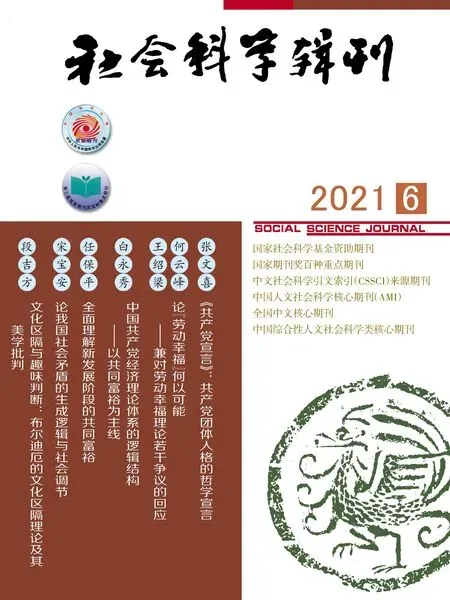袁世凯《戊戌纪略》版本源流及其写作时间考述
李永胜
袁世凯作为戊戌政变当事人之一,其所写的《戊戌纪略》(又被称为《戊戌日记》)是研究戊戌政变史的第一手资料。厘清《戊戌纪略》刊布、流传过程不仅本身即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戊戌纪略》写作时间的问题。罗家伦、刘凤翰对于《戊戌纪略》版本源流进行了探讨,并对《戊戌纪略》的写作时间作出了判断。罗家伦推断《戊戌纪略》为宣统元年补作。〔1〕刘凤翰认为《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2〕
罗家伦见过的《戊戌纪略》源自《申报》排印版本。而除了《申报》刊本外,刘凤翰还见到了另外一种《戊戌纪略》版本。刘凤翰没有亲眼见过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戊戌纪略》。他误以为袁世凯的《戊戌纪略》最早由翰墨林印书局于1909年印行。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发现了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戊戌纪略》,用实物证明南通翰墨林的《戊戌纪略》印行于1925年,并非1909年。〔3〕然而《戊戌纪略》的版本源流问题并未完全厘清。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戊戌纪略》是否为最早的刊本?还有没有可能找到更早、更多的抄本、刊本甚至稿本呢?经过多年查找,笔者迄今陆续发现了《戊戌纪略》的一种回忆版本、一种转述版本、两种抄本和多种排印版本(包括一种稿本的排印本)。笔者所见《戊戌纪略》版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罗家伦和刘凤翰所见过的版本。本文将系统梳理《戊戌纪略》诸多版本的源流关系并对《戊戌纪略》的写作时间问题加以进一步讨论。
一、《戊戌纪略》的源头及流向
笔者见过的《戊戌纪略》除了两种版本外①这两种版本包括一种排印本和一种抄本。排印本参见袁世凯:《戊戌日记(摘录)》,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上海:光华书店,1947年,第336-341页。抄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戊戌纪略》抄本。这两种版本没有标注足够的信息,无法确定其上游版本,但其内容与其他版本无任何歧异之处。,都可以确定其源头是袁世凯家藏的《戊戌纪略》。袁世凯家藏《戊戌纪略》通过下述相互独立的四条途径从袁家流向社会。
(一)《戊戌纪略》回忆版:袁克文《戊戌定变记》
1921年3月,上海《晶报》主人余大雄得见一份被误称为《戊戌纪略》的文件,将其交给袁世凯次子、时任《晶报》主笔的袁克文(字寒云)辨别真伪。袁克文认为这份所谓的《戊戌纪略》全是空论,没有记述事实,与他曾抄录的《戊戌纪略》内容不同。于是,他回忆自己曾看过的《戊戌纪略》,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写成《戊戌定变记》一文,刊发于《晶报》,全文如下:
戊戌定变记 寒云
戊戌之变,外间无由窥其真。党徒记述,则自饰非信。先是,使京侦者返报云:“康有为梁启超辈,内挟天子,而间慈宫,号云变法,施其宄图。”盖景帝童騃,但知挝鼓为乐耳。天下大计,本非所晓,况入有为等之侫言,遂不觉自堕术中。外则结纳新进,援引私好,排除异己,屏斥老成。以此觇之,其包藏叵测可知矣。时慈宫归政,不问朝事,居颐和园,放乐山水。先公正忧之,忽拜候补侍郎之命。闻为有为疏荐,益深煌虑。一日,报谭嗣同衔密诏至。先公亟延入。嗣同请屏侍仆,合门,自怀出一纸,皇皇朱谕也。中谓慈宫与直督荣禄误国,命先公率兵,先至天津,斩荣禄。后入都,围颐和园,废慈宫而幽之。即以先公任直督。先公捧诵沉吟间,嗣同忽出手枪,指先公曰:“公从,则富贵不可喻,否则流血五步之内。”先公笑曰:“君胡相戏耶?厥定大计,且有上命,某焉敢违?君先返命,某部署立至。”嗣同改容谢曰:“同以王事,未敢苟疎。特以试公。亦知公忠勇,必无异议,请恕愚昧。今内事已无虑,专赖公发于外耳。”先公曰:“比阅邸抄,有斥长素之诏,且令出京,何耶?”嗣同曰:“此康公自拟者也。意恐居京,转不利大事,故暂走避天津。下此诏者,掩后党耳目,使不疑有变,事定即归,非帝意也。”先公已心知有为谲策。盖成则居功,败则祸人耳。嗣同既去,先公轻车简从,犯夜而驰,自小站达天津七十余里,方曙即至。立谒荣禄,谓有机密,须密晤。禄即延先公入。先公请退左右,出诏授禄。禄读竟,汗颜失色,伏地待罪。先公亟扶起,曰:“公勿如此,某若遵此诏而行,今即不来密告矣。公一人生死事小,国政与太后事大。奸宄逞谋,妄托圣意,此岂真帝旨耶?公胡不辩哉?”禄再详审,恍然曰:“非帝书也。然将奈何?”先公曰:“公持此诏,立赴颐和园叩阍,陈于太后前。太后如令遵旨,公即归待罪。太后曰否,必有睿断,勿劳小臣虑也。祖制,太后不临朝,百官例不得直请觐诣。今太后于归政后,有内外大臣,遇有大事,可直诣颐和园叩请训示之诏。公往叩觐,无违于制也。太后圣明,赖有此诏,否则不堪设想矣。”禄曰:“善。公返小站,候我音告。”先公辞归。禄即密行入都,直赴颐和园。慈宫闻有大事,立召禄。禄入,跪上帝诏。慈宫阅竟,从容顾禄曰:“汝速返任所,予自有处置。”禄退出,慈宫即传旨返跸。夕抵禁宫。帝闻慈宫至,亟出跪迎。慈宫顾帝曰:“好!好!”即下诏,仍垂帘亲政,放帝于瀛台。复敕九门提督,严缉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党徒。时启超久已南下。有为则避处大沽口夷舶中,以观成败。闻讯亦遁矣。惟诛有为弟广仁及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人于菜市口。此六人,除广仁外,皆慨愤衰弊,亟欲自见。遂惑于有为之煽诱,而实未察其隐谋。心则忠贞,行亦挺特。惜少年未历事故,所遇非人,致杀其身。哀哉!若有为者,既陷君于不孝,复祸君而远引。坐使手足朋好,沦于刑钺。己则思安享其功,独逃其祸。诚善自谋,其如几希于禽兽何?〔4〕
“戊戌之变,外间无由窥其真。党徒记述,则自饰非信”一句中的“党徒”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一句是袁克文回忆《戊戌纪略》的引语。“禄即密行入都,直赴颐和园……惟诛有为弟广仁及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人于菜市口”一段话是袁克文根据后来发生的史实,加上自己的演绎,对政变过程所作的补叙。“此六人,除广仁外……其如几希于禽兽何”一段是袁克文对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评价。从“先是,使京侦者返报云”到“先公辞归”,是对袁世凯《戊戌纪略》内容的回忆,其篇幅相当于《戊戌纪略》的1/4。
谭嗣同携带光绪皇帝密谕夜访袁世凯,要袁杀禄围园。袁向荣禄告密,荣禄赴京向太后告密。这是袁世凯涉身戊戌政变最关键的情节。对此,《戊戌定变记》与《戊戌纪略》两者所记大致吻合,只是在细节上存在很多差异。
《戊戌定变记》有与《戊戌纪略》完全歧异的记述。比如,谭嗣同访袁地点,《戊戌定变记》称谭嗣同访袁地点在天津小站,而《戊戌纪略》记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地点是北京法华寺。①袁克文在《洹上私乘》里写道:“谭嗣同至小站,劫先公,假帝诏,命先公囚孝钦后,杀荣禄。”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卷1上,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第3页。袁克文《洹上私乘》和《戊戌定变记》两处说法相同,当属袁克文记忆错误。《戊戌定变记》有袁世凯与谭嗣同讨论“令”康有为“出京”之诏书的描述。《戊戌纪略》完全无此记述。另外,二者引述光绪密诏内容不同。
《戊戌定变记》与《戊戌纪略》某些记述略有差异。《戊戌定变记》说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的是朱谕,而《戊戌纪略》说是墨谕。谭嗣同提出的对于慈禧太后的处置办法,《戊戌定变记》记述是“废慈宫而幽之”;而《戊戌纪略》则是谭另觅人“除此老朽”。
总之,《戊戌定变记》作为《戊戌纪略》的回忆版,所记关键情节与《戊戌纪略》大体相同,若干细节描述与之存在歧异。《戊戌定变记》作为袁克文多年后对《戊戌纪略》内容的回忆,与《戊戌纪略》有所歧异是难以避免的。袁克文作为袁世凯儿子,叙事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称颂袁世凯,谩骂维新派人士。这也是《戊戌定变记》与《戊戌纪略》产生歧异的原因之一。
(二)《戊戌纪略》转述版:郑逸梅《政变轶闻》
著名报人郑逸梅谈起袁世凯《戊戌纪略》说:
据我所知,袁氏确有这篇《戊戌纪略》,藏在他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中,从没有在哪里发表过。记得在民国十年左右,我的内兄周梵生,在袁家当西席,教袁寒云的儿子伯崇、叔骝等读书。梵生那时已看到这篇《纪略》,录副寄给我一阅。当时我在吴中,和赵眠云同辑《清闲月刊》,便拟把它作为史料揭载。为郑重起见,先请梵生征得袁家同意。不料袁家认为不宜发表,只得作罢。隔了一年,那位曾充袁氏幕府的林屋山人步章五,在上海办《大报》(小型报的一种),他就毅然把这《纪略》公开刊出。〔5〕
郑逸梅上文说“民国十年左右”看到《戊戌纪略》,似属记忆错误。步凤藻(1874—1933,字章五,号林屋山人)所办《大报》1925年刊载《戊戌纪略》。按上文中郑逸梅得到《戊戌纪略》“隔了一年”后步林屋在《大报》刊载《戊戌纪略》的说法,郑逸梅应于1924年从周梵生处得到了《戊戌纪略》。1924年,上海《红杂志》刊载了郑逸梅所写《政变轶闻》。由此可以确定,郑逸梅在1924年得到了周梵生所抄的《戊戌纪略》,并将其改编成《政变轶闻》。实际上,郑逸梅早在1925年就说过:
《戊戌纪略》一篇,予早得副稿于内兄楚生(“楚生”应为“梵生”——笔者注),因时有顾忌,故当时未敢付诸剞劂,兹林屋觅获其稿,披露《大报》,予读之重有感焉。〔6〕
郑逸梅觉得转述与原文刊布意义不同,尽管他刊布了《政变轶闻》,仍说自己“未敢”将《戊戌纪略》“付诸剞劂”。
1924年,上海《红杂志》登载的《政变轶闻》篇幅约《戊戌纪略》的1/3,全文摘录如下:
政变轶闻 郑逸梅
戊戌政变,早彰史册。然其间尚有一段轶事,外间知者绝鲜。项城容庵老人尝有《戊戌纪略》,密交诸子。予曾辗转假阅之。原文甚详,约四千余言。兹忆其大略如下:
光绪廿四年秋,容庵奉召至京,夜在寓室,秉烛拟疏稿。忽谭嗣同来见,谓有密语……(中略——笔者注)谭云:“如不出巡奈何?”容庵谓:“可筹巨金,请内臣力求慈圣,必得出巡。此事在我,尽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在于公。告变封侯亦在公。惟公自裁。”容庵谓:“我受国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致误大局。”谭信,起揖……(中略——笔者注)。抵津,诣院谒荣相。略述内事,并道群小结党,煽惑谋危。语未竟,叶祖珪、达观察来,不得间,遂退。次早荣相来,备述详情。荣失色呼冤曰:“某若有是心,必为天诛。”越四日,荣奉召入都,临行约誓以死保全皇上。荣相曰:“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良以慈圣祖母也,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也。〔7〕
郑逸梅《政变轶闻》与袁克文《戊戌定变记》都用了第三人称转述的形式,区别在于一个用“先公”指称袁世凯,一个用“容庵”。袁克文《戊戌定变记》完全凭记忆来写,所以内容与原文差别较大。郑逸梅《政变轶闻》对照原文进行改写,其内容与原文几乎完全一致。
《政变轶闻》与《戊戌纪略》原文相比,删略了八月初三夜谭嗣同来访前,袁世凯在京活动的记述。《政变轶闻》与《戊戌纪略》除了关于两宫出巡天津一处略有出入,其他内容完全一致。关于两宫出巡天津一事,《戊戌纪略》原文是:“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8〕笔者认为,“计费数十万金”应当是指筹备阅兵事宜费用数十万金。而郑逸梅理解为“筹巨金”贿赂“内臣”,并且将“荣相(荣禄)”算作“力求慈圣”的“内臣”之一员,按他的理解对原文进行了转述改编。
(三)张一麐《戊戌纪略》抄本的流传
1926年9月2日,张一麐写给蔡元培的信中,说袁将《戊戌纪略》抄交给他的时间是袁世凯被罢免后,离京返回河南之前某一天的“翌日”〔9〕。清廷发布罢免袁世凯的上谕是1909年1月2日。袁世凯于1月5日乘车返回河南。即张一麐得到袁世凯《戊戌纪略》在1909年1月3日至5日之间。而张一麐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说,袁交给他《戊戌纪略》是在他“回南后”〔10〕。“回南”即张一麐回到苏州。张一麐1903年起任职袁世凯幕府。1909年初,袁罢官回籍后,张也离京回到苏州。张“回南”是在1909年1月5日之后。张一麐对袁交给他《戊戌纪略》的时间记忆不清,说法歧异,但都在1909年。
直到1925年,张一麐藏《戊戌纪略》抄本才公布于世。张的抄本经两种途径向社会传播。第一条传播途径是,况周颐从张一麐处得到《戊戌纪略》,将其刊发在1926年2月2日、4日、6日、8日《申报》的“餐樱庑漫笔”栏目。此刊本衍生出几种刊本,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述。
第二条传播途径是费树蔚(1883—1935,字仲深,号韦斋)从张一麐处抄得《戊戌纪略》,抄交莫棠(1865—1929,字楚生),莫棠和吴枏(1881—1942,字伯乔,又字我尊)将其对外传播。这一传播途径衍生出几种刊本和抄本,在此略作介绍。
1925年,莫棠和吴枏分别作序后,将《戊戌纪略》交上海《大报》和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大约同时刊印。关于翰墨林印书局《戊戌纪略》刊本的情况,笔者已有论述,兹不赘述。〔11〕《大报》是上海一家著名的小报,由步林屋主编,每三天出一期。1925年2月3日、6日、9日、12日、15日、18日、21日共七期《大报》,连续刊载《戊戌纪略》和《自书〈戊戌纪略〉后》。2月24日,《大报》刊载了“莫天麟序”和“吴枏序”①莫天麟是莫棠的儿子。翰墨林版和《大报》版《戊戌纪略》中“莫天麟序”的真正作者是莫棠,但不知莫棠出于何种考虑署了其儿子的名字。南京图书馆藏《戊戌纪略》抄本和《江苏文献》所刊《戊戌纪略》将“莫天麟”改为“莫棠”。。这8期《大报》除12日、24日2期外,其他6期刊载《戊戌纪略》时,文后都加了步林屋的编辑按语。
吴枏和莫棠将《戊戌纪略》交《大报》和翰墨林印书局刊出后,他们又将《大报》和翰墨林印本中的序作者“莫天麟”改为“莫棠”,形成新的抄本。南京图书馆收藏《戊戌纪略》此种抄本一件。此种抄本又由《江苏文献》刊布于世。1945年(月份不详)出版的《江苏文献》续编第1卷9、10期合刊所载《〈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刊布吴枏、莫棠所作“序”(将莫棠所作“序”改题为“跋”)和李传元所作“题辞”,并附录了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自书〈戊戌纪略〉后》。《近代史资料》转录了1945年《江苏文献》所收录的《〈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中的吴枏、莫棠所作“序”而删略了李传元所作“题辞”和《戊戌纪略》《自书〈戊戌纪略〉后》。〔12〕
(四)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戊戌纪略》稿本之刊行
1954年,荣孟源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将原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戊戌纪略》稿本公之于世。他在《戊戌纪略》前加按语:“据北京历史博物馆藏原抄本印。”〔13〕荣孟源后来说:“历史博物馆所存的袁世凯《戊戌纪略》抄本(全文见三联书店1954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盖有清政府在小站练兵机关的关防,证明这个抄本是袁世凯所存的真本。”〔14〕
荣孟源以上两处所说的“《戊戌纪略》抄本”(本文将其称作“《戊戌纪略》稿本”),应指同一物件。“盖有清政府在小站练兵机关的关防”表明,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戊戌纪略》写成于戊戌年(1898年)。这个稿本应来自袁世凯家藏,后来辗转到了原北京历史博物馆。
郑逸梅谈起袁世凯《戊戌纪略》说:“后来《纪略》的原抄本,归到北京历史博物馆,那就不知怎样的线索了。”〔15〕
照郑逸梅的看法,原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戊戌纪略》即是周梵生所抄录的洹上村所存的《戊戌纪略》原藏本。当然,如果袁世凯家收藏的稿本或抄本只有一份,那周梵生抄录时所据的本子与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应是同一本。但袁家收藏的《戊戌纪略》稿本或抄本也许不止一份。所以周梵生所抄录与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藏的并不一定是同一物件,甚至袁克文所抄录的《戊戌纪略》本子也不一定是原北京历史博物馆收藏或周梵生抄录的袁家藏本。但不管袁家藏有一份或者多份《戊戌纪略》,其内容都相同。
二、《戊戌纪略》写于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
《戊戌纪略》结尾处标注了其写作时间和地点:“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②1898年9月25日(八月初十日),清廷电令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6日,荣禄赴京。28日,清廷任命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10月5日(八月二十日)抵津。这样,至少9月26日至10月5日之间,袁世凯在督署居住。如果《戊戌纪略》确实写作于9月29日(八月十四日),则其写作地点是在天津直隶总督公署毋庸置疑。对于1898年9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这一写作时间,刘厚生、罗家伦、黄彰健都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戊戌纪略》写于光绪宣统之交、袁世凯罢官之后。〔16〕刘凤翰则认为《戊戌纪略》应写于戊戌年八月十四日前后。〔17〕
罗家伦否认《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的理由有两条。一、《戊戌纪略》所记内容是极为敏感的“秘密大计”,“按照当时一般当权大官明哲保身的惯例”,袁世凯断不会将其记录下来;二、“戊戌时期正是西太后党得意之秋,而袁复为后党荣禄亲信之人,岂敢在日记中作同情而有意维持光绪之语”〔18〕。
但这两条理由都难以成立。其一,1898年9月29日(八月十四日)朱谕中有言:“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19〕康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罪名的获得,无疑是袁世凯将谭嗣同夜访提出围园杀后一事报告荣禄,荣禄报告太后的结果。袁世凯《戊戌纪略》写成于1898年9月29日,本日的上谕已将《戊戌纪略》所记最敏感的内容公之于世。《戊戌纪略》的关键内容已谈不上“秘密”。袁将此事记录下来无须太多顾虑。更何况此种记录并不准备公开。即使其不慎泄露出去,无非是透露了谭嗣同访袁更多细节,袁不会因此招致清廷的威胁。
其二,调和太后和皇帝矛盾是袁世凯唯一可能的选择。袁世凯与维新派有一定交往,但其政治观点和立场与维新派大有不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维新派试图杀掉太后和荣禄,归权光绪帝。而袁世凯绝不可能赞成此种主张。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的光绪皇帝给杨锐等人的密谕,多多少少透露出皇帝与太后之间的权力冲突。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既不可能赞成维新派的主张,也不可能怂恿太后对光绪帝下重手。忠君既包括对皇帝的忠,也包括对太后的忠。调和两宫是袁世凯所能采取的与己最为有利的做法。离间太后和皇帝,倾向任何一方,都极易招致杀身之祸。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作同情而有意维持光绪之语”实属正常。
黄彰健否认《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的主要根据是,《戊戌纪略》所记袁世凯抵津时间与《国闻报》所记时间不符。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国闻报》载:“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20〕这段记载表明,袁世凯是下午三点到津。而《戊戌纪略》所记袁返津时间是“日已落”。黄认为《国闻报》所记袁世凯抵津时间真实可信。而袁世凯《戊戌纪略》“把他抵津的时间也记错了”,证明《戊戌纪略》“显系距戊戌政变很久以后追记”〔21〕。
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写道:“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22〕当时的文件都用毛笔竖写而且文稿中无标点。如果此处断句为“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把“日已落”作为“诣院谒荣相”的时间,而不作为“抵津”的时间,此处的记述就不存在大的问题了。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大约下午6时,太阳就落山了。从袁世凯下午3点多到天津站,到大约下午6点之间,有两三个小时的间隔。这段时间袁世凯又做了什么呢?骆宝善在《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中指出,事实上,袁世凯在车站的应酬和抵达督署路上足需花费两三个小时。根据当时官场的礼仪制度,相关的官员与将入京见皇帝或见皇帝回来的官员见面时,必须请圣安。袁世凯刚见过皇帝回津,当时天津众多官员要在车站完成“请圣安”的仪式,甚至还会进行一些热聊,为此用去两个小时,完全可能。从天津车站到位于三岔河口一带的直隶总督官署,或步行、或乘马车、或坐轿,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以上。这样,袁世凯虽然三点多“抵津”,但他到督署见到荣禄时“日已落”,完全合乎情理。1898年9月22日(八月初七日)《国闻报》“制台辕门抄”栏写道:“八月初五日晚,升候(补)侍郎袁世凯大人拜会。”〔23〕“晚”与“日已落”是吻合的。
诚然,必须承认《戊戌纪略》此处的记述不够完善。如果在“抵津”与“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之间加上一两句话,说明袁世凯在天津站下火车后,在抵达督署前做了些什么,就不易产生歧义。袁世凯此处未作详记也情有可原。《戊戌纪略》并非日记体,而是纪事本末体。正如《戊戌纪略》末尾所称“谨述大略”,与主线索关系不大的一些情节就省去不记了。无论如何,凭借《国闻报》所记袁世凯抵津时间与《戊戌纪略》所记“日已落”不相符合,不能得出袁世凯《戊戌纪略》并非写于戊戌年的结论。
罗家伦、黄彰健认为《戊戌纪略》写于宣统元年的主要理由是,宣统元年袁世凯被罢免,他有发表《戊戌纪略》为自己戊戌年的行为进行辩解的动机。罗家伦写道:
袁世凯要将这篇《戊戌日记》发表的时候,正是西太后已死,溥仪嗣位,而光绪的亲弟载沣为摄政王,继起当国的时候,也正是袁世凯罢官回籍,生命几乎不保的时候,于是急急忙忙发表这个文件,以求洗刷当时为后党爪牙的罪行……虽然张一麐先生说是他曾经“直以此事商之”,袁“翌日以此相授”。但此决非一偶发事件,乃经袁事前一切准备就绪,甚至借谈天方式,故意引张发问。〔24〕
黄彰健写道:
袁世凯是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以赵炳麟的弹劾而以足疾开缺。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当时隆裕皇太后本想杀袁世凯,替光绪复仇,而张之洞认为,宣统皇帝冲龄践祚,如让隆裕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此端一开,为患不细;遂反复开陈,袁始得保首领。袁的《戊戌日记》口口声声说,他对光绪帝如何忠诚,则他的《戊戌日记》当即在这一环境中所写。当时人认为政变的爆发是由于袁的告密,致光绪帝抑郁以终,因此袁就诡辩说,他的告密在初六,与政变的爆发无关,企图以此获得人们谅解。〔25〕
虽然载沣确因戊戌旧事对袁不满。但因牵涉帝后关系,摄政王载沣所发布罢袁谕旨不能拿戊戌旧事说事。袁世凯被罢后,康有为、梁启超以戊戌年离间两宫为词猛烈攻击袁世凯。袁世凯发表《戊戌纪略》或许能起到为己辩护的作用。但袁那时有辩解的动机却无法得出《戊戌纪略》即写于那时的结论。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逻辑关系。
刘厚生根据《戊戌纪略》的文字表达水平与袁世凯能力不符,作出《戊戌纪略》不写于戊戌年而是写于宣统元年的判断。刘厚生认为《戊戌纪略》“曾经张一麐之笔削”。因为“袁世凯自己的手笔,尚没有如此通顺。尤其‘春秋赵盾弑其君’云云,世凯脑中决没有此典故。假如把此事向荣禄说,荣禄更不会懂得。这就是张一麐笔削时,所露出的马脚”〔26〕。
刘凤翰以自己见过的两种版本的《戊戌纪略》内容差异为根据,否定刘厚生的“张一麐笔削”说。但他与刘厚生的观点相似,同样认为袁世凯文笔达不到可以写出《戊戌纪略》的水平。他推测,《戊戌纪略》有可能是由尹铭绶在戊戌年代袁世凯所写。〔27〕诚然,《戊戌纪略》长达3000多字,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叙事简明准确。短短几天时间,写出这样的文章,可能确非袁世凯的文字表达能力所能达到。但袁世凯可以自己口述,让文案幕僚执笔来写。尽管事涉机密,袁世凯亲自书写的可能性不大。不能说袁世凯自己亲自动笔书写的作品才是袁世凯的作品。袁世凯上给朝廷的奏折,基本都是幕僚书写,但我们仍然说那是袁世凯上的奏折。《戊戌纪略》必定出于袁的口述无疑,因为局外人无法写出如此详尽的内情。即使有幕友承担了《戊戌纪略》的书写和文字修饰工作,我们应当认定其作者就是袁世凯。
综上所述,《戊戌纪略》不写于戊戌年而写于宣统元年的各种理由都不能成立。对比经四条路径传播及传播路径不明的《戊戌纪略》多种版本内容,可以得出结论,《戊戌纪略》不写于宣统元年,也没有经过张一麐的“笔削”。袁克文的《戊戌定变记》基于回忆,郑逸梅《政变轶闻》用了转述形式,所以这两种版本不能与其他刊载原文的《戊戌纪略》版本精确比对。但这两种版本都证明袁家藏本《戊戌纪略》确实存在,而且其关键内容与《戊戌纪略》原文记载大致吻合。原文刊载的各种《戊戌纪略》版本,有的有《自书〈戊戌纪略〉后》,有的没有。其《戊戌纪略》部分的内容完全一致。凡有《自书〈戊戌纪略〉后》的版本,其《自书〈戊戌纪略〉后》的内容也完全一致。《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所收录的只是《戊戌纪略》摘录本,但其摘录部分与其他版本对应部分的内容也完全一致。诸多《戊戌纪略》版本的差别仅仅限于一些校对方面的差别,比如用字不同、多一字、少一字、标点不同等差异。这都属于抄写、排印过程中难免出现的问题。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戊戌纪略》稿本盖有小站练兵机关印章,证明《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戊戌政变第二年袁世凯即调任山东巡抚,离开了小站。原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戊戌纪略》稿本并不来源于张一麐的《戊戌纪略》抄本,但在内容上却与张一麐的抄本一致。这充分证明,张一麐不可能对《戊戌纪略》有“笔削”。如果有“笔削”,根据其抄本刊印的《戊戌纪略》(翰墨林版、《大报》版等)在内容上就会与据原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戊戌纪略》稿本刊印的版本(即荣孟源在《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所刊印的《戊戌纪略》)产生歧异。刘凤翰见过的《戊戌纪略》只有两种版本,他根据一种版本有《自书〈戊戌纪略〉后》,另一种版本无的情况,得出《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的结论。他的推论自然有其道理,但所述理由及证据尚不充分可靠。现在存世的多种版本《戊戌纪略》内容一致,证明《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政变发生后不久。《戊戌纪略》标明写作日期是“八月十四日”。刘凤翰认为“《戊戌纪略》成稿于戊戌政变后不久,与袁世凯所写的日期,虽不见得完全尽同,可能很接近”〔28〕。笔者同意这一判断。写《戊戌纪略》这样一篇篇幅较长的文章,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戊戌纪略》写于戊戌政变后不久,可以将1898年9月29日(八月十四日)作为其写作日期。
关于袁世凯戊戌年写作《戊戌纪略》的动机,《自书〈戊戌纪略〉后》最后一句说:“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①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555页。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上海《大报》《江苏文献》刊行的《戊戌纪略》此处为“以征事实而质异词”。“征事实而质诸词”一语准确概括出袁世凯撰写《戊戌纪略》的两个目的。“征事实”即记下事实,以便将来查证。对袁世凯而言,戊戌政变是重大历史事件,有必要将自己所经历事实记录下来,以防遗忘。“质诸词”,即如果出现对于政变过程的不同说法,可以《戊戌纪略》所记史实为准辨别真伪。早在戊戌年,尚未出现宣统元年袁世凯被摄政王罢免及康有为、梁启超党人攻击袁世凯戊戌离间两宫的情形,但袁世凯当时即担心将来可能受人攻击而需要留下记录为己辩解。不管是在戊戌年还是在宣统元年,袁世凯的《戊戌纪略》都有为己辩护的动机。区别在于,戊戌年尚无人指责袁世凯离间两宫,而宣统元年则确实发生了袁世凯被指责离间两宫的情形。因此,说袁世凯写《戊戌纪略》有将来为己辩护的动机,符合情理。但《戊戌纪略》并不存在为了掩盖出卖光绪的罪名而故意作伪的情况。光绪皇帝1898年9月15日(戊戌年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谕,谭嗣同于9月18日(八月初三日)夜带着此密谕抄件访袁世凯。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引述此密谕大意为:“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29〕这与现在学界认可的密谕内容并无歧异,其中多多少少透露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矛盾。袁世凯《戊戌纪略》明确承认自己将谭嗣同持光绪密谕夜访并提出“围园杀后”行动方案的情况向荣禄告密。如果袁世凯写作《戊戌纪略》欲掩盖出卖光绪之罪名,则不应该引述光绪密谕。引述了光绪密谕,反而有出卖光绪之嫌。袁世凯告知了荣禄光绪密谕内容,至于荣禄是否告知慈禧太后或什么时间告知慈禧太后,就不是袁世凯所能掌握的了,至今仍是一个未能证实的事情。但荣禄确实将谭嗣同向袁世凯提出的计划向慈禧作了密告,前引清廷9月29日发布的朱谕中“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一语可证实这一点。
有论者经过考证后发现,《戊戌纪略》所记的主要、次要情节真实可靠。〔30〕正因为《戊戌纪略》写作于戊戌年,才能做到这一点。《戊戌纪略》许多细致入微的描写准确无误,说明其不可能写于距离事件发生十年多之后的宣统元年。根据普通人的认识规律,经历过的事情间隔时间稍长就会有很多细节记不清楚,更别说事隔十年之久了。如果是宣统元年再去回忆记述戊戌年发生的事件,一定会记错很多情节。
三、结语
罗家伦先生和刘凤翰先生对于《戊戌纪略》的研究有开创之功。罗家伦早在1926年即对《戊戌纪略》的版本问题予以关注。时隔数十年后,他探究《戊戌纪略》源头的热情重燃,1960年撰成《一个几乎被失落的历史证件——关于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一文。刘凤翰先生花费五年时间,写就《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一文,并将其称作《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的“重心”。刘凤翰对于《戊戌纪略》的版本、作者进行考订,作了“详尽而又合理的解释”〔31〕。
尽管罗、刘两位先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他们的若干论述仍存在问题。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条件见到《戊戌纪略》的更多版本。如果刘凤翰看到翰墨林版《戊戌纪略》原书的话,自然不会作出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于宣统元年刊布了《戊戌纪略》的论断。罗家伦先生仅见过一种《戊戌纪略》版本,他推断《戊戌纪略》写于宣统元年袁世凯被罢之际。刘凤翰比罗家伦多见到了一种《戊戌纪略》版本,经对比两种版本,他得出《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的结论。他的结论与本文结论相同,但其提出的理由却与本文有别,不够充分可靠。今天有条件见到更多的《戊戌纪略》版本,通过梳理这些版本的源流关系,对比其内容异同,能够对《戊戌纪略》的写作时间作出更为可靠的判断。本文与罗家伦、刘凤翰等先辈学者的论述有较大差别,但仍然基于他们的研究基础,对他们竭力想搞清楚而未能完全搞清楚的问题做了新的探讨。
笔者所见现存于世的《戊戌纪略》各种版本(除了两种版本外),都可以溯源到袁世凯家藏的《戊戌纪略》稿本。《戊戌纪略》内容从袁家传向社会并非始于宣统元年。1921年,袁克文根据记忆以《戊戌定变记》为名将《戊戌纪略》的主要内容刊布报端。1924年,《戊戌纪略》内容又被郑逸梅以《政变轶闻》为名以第三人称转述的形式刊布于《红杂志》。《戊戌纪略》原文全文刊布于1925年。张一麐在宣统元年即从袁世凯处获得了《戊戌纪略》抄本,但当时并未将其公之于世。直到1925年,张一麐的抄本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上海《大报》刊布。1926年,上海《申报》全文刊载《戊戌纪略》。翰墨林刊本和《大报》刊本时间略早,但流传、影响范围较小。《申报》是发行量较大的著名大报,其刊载的《戊戌纪略》被多次转载,产生较大影响。《戊戌纪略》逐渐被世人广泛知晓。1954年,荣孟源将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戊戌纪略》稿本刊布于世,该稿本盖有小站练兵机关的印章,证明《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对比现存《戊戌纪略》多种版本(不包括袁克文的《戊戌定变记》和郑逸梅的《政变轶闻》),其内容毫无歧异之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而不可能写于宣统元年,也不可能被张一麐“笔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