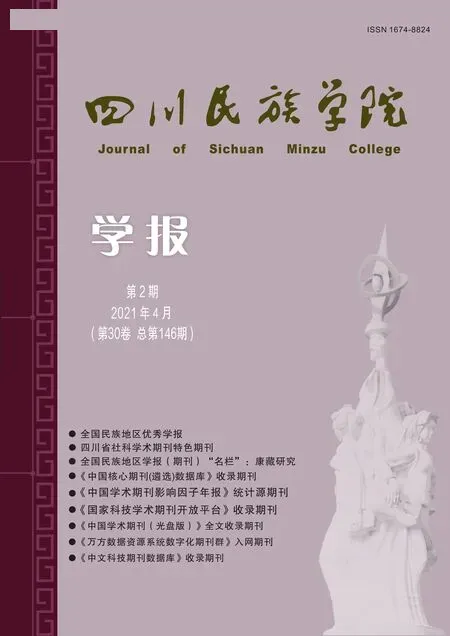论当前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困境、探索与批评立场
——以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为例
傅钱余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回顾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20世纪80—9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21世纪以来这十余年之间作品较少,进入沉寂期。如以小说创作闻名的回族作家霍达、张承志,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白族作家景宜,侗族作家潘年英,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瑶族作家蓝怀昌,土家族作家李传锋、蔡测海等等,这段时间都较少发表小说作品。其原因虽有个人因素,更重要的恐怕是社会发展因素了。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文学振奋期,也是多元文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此语境中富于激情地进行着自我民族的文化表述。随着现代化的蓬勃发展,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纯文学的社会地位有所降低,同时少数民族及其所在区域在经济发展下承受的生态、文化问题越来越多,作为民族知识分子的作家们将目光放到了现实层面,主动承担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因此会发现许多作家走向人类学散文写作、文化影视制作或其他当前社会更具传播性活动的方向。除去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更关键却常常被忽视的原因其实是在文学评价机制上对“民族特色”的过度强调造成了民族文学创作的封闭化和景观化。
一、民族文学凸显民族特色的评价标准和创作预设
在少数民族文学界有着最大影响力和导向性的无疑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后文简称“骏马奖”),这是专门以少数民族文学为评选对象的最高奖项。该奖1981年开始设立并评选了首届获奖作品,当时称之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其主管单位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这两个机构的政治权威性和文学号召力合二为一,无疑使“骏马奖”成了少数民族作家们梦寐以求的文学桂冠。
“骏马奖”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最高奖项,必然会强调民族特色。2008年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试行条例》,其核心标准第三条为:“注重作品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有学者对第十、十一届骏马奖的评语进行了关键词统计和分析,发现在49部作品的评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民族/民俗”,占比67%[1]。“骏马奖”强调文学作品的民族性,这毋庸置疑。但是,“民族性”“民族特色”其实都是内涵难以界定的模糊术语。“骏马奖”强调“历史文化”和“民族生活”,很明显更倡导少数民族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反映民族社会生活、审视民族文化传统。后来,在2012、2016年对“骏马奖”的评选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色彩,同时民族话语的表述也更模糊。
虽然术语是模糊的,但在“骏马奖”的强大影响力下,少数民族作家开始了对民族风情的片面强调。回到民族生活世界、回到民族文化传统成了作家们的创作原则,也成了批评家们的主要聚焦点。如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是1981年首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获得者之一,1982年公开发表的3篇相关评论文章中(1)详参龙长顺.孙健忠作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J].求索,1982(6):94-100;龙长顺.论孙健忠创作中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30-37;郝怀明.土家人美好心灵的歌颂者——介绍土家族作家孙健忠[J].民族文学,1982(7):84-87.,无一例外地强调其作品的土家“民族特色”;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1984年成了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获得者之一,同年公开发表的3篇论文中(2)详参孟和博彦.时代的脉息,民族的心音——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J].民族文学研究,1984(4):56-61;奎曾.鄂温克族的文学新星——乌热尔图[J].中国民族,1984(9):38-39;雷达.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J].文学评论,1984(4):74-79.,依然无一例外地强调其鄂温克族“民族特色”。凡此种种,不再累举。已有学者指出,在获得“骏马奖”的作品中,存在着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历史的追忆多于对现实的表达;二是乡土题材泛滥,城市题材太少且基本脱离民族视域[2]。显然,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作家希望得到认可,既希望普通读者认可,也希望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不得不说,在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中,在“骏马奖”的民族性强调以及学界、读者对民族特色的偏爱中,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把目光聚焦到民族文化传统,去创作具有民族风情的作品。此倾向泛滥之后,使得许多作家在看待自身文化传统时不是一种文化持有者的目光,而是自我的他者化,即为了获得主流文坛的认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口味。
正如法国文学理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所言:“民间风情、地区主义及异国情调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尽力去寻找新颖性,地区(民族的,大洲的)的特殊性……‘风俗画’和地方色彩是借助最一般的、最通常的美学手段,描绘一种特殊现实的一些尝试。”[3]在整个80、9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忙于去发现、寻找,甚至“制造”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将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在获得文坛认可的同时标榜自身文化。批评家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价动辄就冠以民族特色,而对民族特色的理解常常流于表面,导致许多批评文章将地方俚语、民俗仪式、服饰衣着等同于民族特色;作家们则以“民族味”作为创作的预设,过度追求民族特点,作品缺乏更深刻的人文内涵和审美革新。
总之,在看到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兴盛的同时,亦要注意到强调民族特色的评价机制对民族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束缚。在此背后,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薄弱,即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定位、评价标准、研究方法等缺乏深度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有较为系统的民族文学理论著作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出版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关纪新、朝戈金合著)和1998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梁庭望、张公瑾合编)。后者甚至被认为“是迄今唯一一部从理论上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著作”[4],此语虽不符合事实,但理论的缺席确实是21世纪以前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问题。21世纪以来,关于民族文学的概念、范畴、对象、理念、方法、学科建设、理论架构等方面成了此领域研究的核心议题。梳理民族文学评价标准的讨论,主要体现为三个趋向:一是不再将民族特色作为民族文学最高甚至唯一的评价指标;二是用表述更客观、内涵更丰富的民族性替换了以前的民族特色一词,对“民族性”内涵的理解也更加全面;三是将民族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倡导多元的、细致的、深层的、发展的评价模式。
在此背景下,不难理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民族文学创作的冷场。80年代很长一段时期内少数民族文学以描写民族地区生活特别是反思文学为主,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则重在展示民族文化、重述民族神话与历史等,伴随此历程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然而,21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观早已经成为共识,民族文学评价标准发生变化,同时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民族文化书写出现更多困难,文化景观式写作受到极大的批评。因此,摆在新世纪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如何写?许多作家陆续放弃了以民族特色为中心的创作,更有一些作家暂时停止了文学创作。当然,在迷茫和困境中,也有部分作家坚持探索和尝试,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便是其中之一。
二、次仁罗布的探索:人文价值、民族精神和艺术创新的统一
21世纪以来,藏族青年作家次仁罗布声名鹊起,其作品广受文坛好评,先后获得“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并两任茅盾文学奖评委。次仁罗布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有鲜明的特点,多篇小说可谓不可多得的精品。他将强烈的人文关怀、深厚的藏族传统文化底蕴与新颖叙事形式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与实践,在当前民族文学新兴与迷茫交织、作品优劣参差的复杂语境中,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杀手》:生存的意义与不可靠叙述
《杀手》发表于《西藏文学》2006年第4期,后荣登《2006年中国年度优秀小说选》,是次仁罗布受人称赞的一篇佳作。此小说为复仇题材,康巴汉子花十余年寻找仇人,真正找到后却又放弃。杀手放弃复仇的原因,成了解读的关键,有研究者从宗教角度解释,认为藏传佛教的隐忍宽容、施恩向善的宗教观念是根本原因[5]。 由此,自然而然联系到了藏族地区佛教文化氛围,从而阐释作品的民族特色。
宗教观念和民族特色当然是分析文本的一个思路,也是文本价值的一种体现,但如果忽略作者的民族身份,将其作品首先置于“文学”层面以人文价值的标准衡量,会发现宗教因素并不是杀手放弃复仇的根本原因。在长时间寻找仇人的路途中,复仇者忍受了太多的艰辛和苦痛,快到仇人玛扎家之前,复仇者去河里磨刀,把行李托放好,可见其意志之坚决。显然他曾无数次想象过激烈决斗时的刀光剑影以及决斗胜利过后的满足感,这赋予他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自我荣誉感。然而,他想象中激烈的复仇场景却在仇人花白的头发、憔悴的面容中粉碎——他可以轻易地杀死玛扎。过于容易,也就失去了复仇的意义。复仇者的哭泣是失望的哭泣,想象和现实竟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复仇者之所以“大哭而去”,实际上是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坚持了十多年的目标的虚无。与其说次仁罗布要强调宗教,不如说他是想揭示一个道理:追求意义是人的本质需求。当追求的意义突然失去,人会陷入绝望的境地。次仁罗布艺术性呈现了这一矛盾,道出了人寻找意义的悖论。
已有学者指出:意义是人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的升华需要[6]。复仇者的复仇因为历时长久,早已不是对某个具体对象的复仇,是一种符号的复仇,复仇行为也变成了对意义的寻找,是一种自我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意义正因其不可接近而具有价值,同时也让人坚持。一旦意义变成现实,意义也就不再是意义,不得不承受失去意义的痛苦。小说中“我”之所以打听复仇者的下落,甚至梦中杀人,其根源也在于寻找意义。但是,这是一种浅层次的意义,由于“我”浅表的追求,恰恰衬托出了复仇者的高大,这依赖于作品在叙事上对不可靠叙述的巧妙运用。所谓“不可靠叙述”,按韦恩·布斯的经典解释,指的是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思想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不一致[7]。《杀手》中“我”偶然遇见去萨嘎县城寻仇的康巴人,康巴人的寻仇经历由“我”来叙述。然而“我”的不在场、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对血腥结局的期待,意味着“我”其实是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我”的不可靠叙述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另外两位不可靠叙述者:茶馆的姑娘和羊倌。前者向我透露出康巴人已经找到仇人玛扎的信息,后者则陈述自己看到了康巴人在河边磨刀。三个不可靠叙述者讲述一段复仇的故事,似乎让故事变得有些扑朔迷离。
次仁罗布的用意并不在于强调真相的不可还原,作者的设计有双重的艺术效果:制造悬念和形成对比。叙述者虽然是不可靠的,但却提供了逻辑上可靠的线索,推动复仇故事的进展,一步步暗示着大决斗以及血腥结局的到来。这在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上无疑是高明而有效的,读者也期待着最后的结果。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让不可靠叙述者与复仇者形成对照。由于一直是“我”在叙述,复仇者是潜在的,对照也就是潜在的。直到文章末尾,截然不同的对比才突然呈现在读者面前:复仇者大哭而去,“我”却在梦中完成自己期待的杀人结局。读者也终于脱离故事层面,聚焦到复仇者的意识层面,终于恍然大悟:复仇对于“我”是个故事,而对于复仇者则是追寻意义。复仇者醒悟了,而“我”仍然要梦中完成故事(杀人),伦理与人性层次上的对比一目了然。
就读者而言,这一设计能极大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不可靠叙述形成一个个的“空白点”,情节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许多地方让读者去联想和补充,读者自然而然被吸引而参与其中。又因为“我”是叙述者,读者阅读时不自觉会或多或少地在感情和认知上认同“我”,所以当最后的对比出现(读者也识别出“我”的不可靠)时,读者便获得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强烈的审美感受。不得不说,次仁罗布的思考是深刻的,叙事巧妙而匠心独运,成功将生存悖论、佛教文化和新颖的叙事技巧相结合,让作品具有了人文性、民族性和文学性的多重价值。
(二)《神授》:传统危机的焦虑与空间叙事
在次仁罗布已有的文学作品中,《神授》无疑是非常成熟也广受称赞的中篇小说。该作以说唱《格萨尔王》的神授艺人为主人公,聚焦民族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放牧娃亚尔杰在草原上睡觉时,梦见格萨尔王的大将丹玛骑着骏马从云层下来,用尖刀划开他的肚子,装进一摞经文。亚尔杰醒来时就变成了格萨尔说唱艺人。此后他感觉自己真正置身于格萨尔王的身边,能看到他们的衣裳,能听到他们在战场的厮杀,能嗅到琼浆玉液的芳香,能感受到格萨尔王的苦痛……。他开始在草原各部落中自由自在地表演,牧民听得津津有味,沉浸在格萨尔王的故事中。那个时刻,时间似乎停止了,亚尔杰和牧民、现在和历史传说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是喜悦、满足和自由的。同时,亚尔杰收获了爱情,在清辉的月光中他和心仪的女子互吐情思。当研究院领导邀请他到拉萨录制说唱时,他犹豫了,舍不得牧民、也舍不得心爱的女孩,更舍不得自由自在的说唱。他以为要面对更多的现场听众去传播格萨尔故事,便下定决心来到了拉萨。然而他面对的却是冷冰冰的录音机,连格萨尔王的大将在梦中也忧郁地看着他,他很快就开始厌烦、焦虑、恐惧,甚至于暂时性失聪、失明,最后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了。亚尔杰重返草原,希望回到自由的天地,不过草原变了样,被汽车和狂躁的音乐占领了。
前后反差如此巨大,因为说唱的对象变了,在草原时是实实在在的牧民,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在拉萨却是没有反应的录音机,只有单调的电流声和嘈杂声刺激耳朵折磨精神。格萨尔说唱艺术是表演艺术,“表演是一种交流性展示的模式”[8],它由藏族人的生活世界而来,同时也活跃在藏族人生活的世界。它的对象就在现场,是活生生的人,说唱者能感受到他们,能听到他们的反馈,能从反馈中得到激励、信心和认可。这一切,却是录音机无法给予的。
作家提出的问题是:口头艺术脱离了生活世界,它还能存在吗?它将如何存在?它的存在还是本真吗?亚尔杰之所以会去到拉萨录制说唱,其原因正是研究院需要抢救、保存格萨尔说唱艺术。一个悖论在此形成:希望保留藏族文化、说唱艺术的精华,得到的结果却是脱离了生活语境的故事(语句)。而生活世界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现代化生活方式进入了原本闭塞自足的草原,收音机、电视、流行音乐取代了格萨尔说唱艺术。如此看来,对现实冲击传统的焦虑、对地方性非遗存在困境的揭示是《神授》的主题。
《神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依赖于作者采用的空间叙事的技巧。小说通过说唱表演改变地理空间从而推进故事,以空间转换而非时间变化来推进叙事进程。说唱艺人每一次表演以及表演空间的变化,都被赋予独特的意义,都参与了文本整体意蕴的表达。说唱的地理空间不断变化,伴随着精神空间的变换。游走于草原的各个部落,亚尔杰感到“喜悦”“冲动”“激动”“亲切”“快乐”“幸福”;但是,进入拉萨的研究院后,他的内心却是“孤独”“焦虑”“无助”“疼痛”“歉疚”“压迫”的。说唱艺人亚尔杰处于草原时,人与自然、精神与文化融为一体。反复出现的天神丹玛和狼体现了文化的神性空间,正是在此空间亚尔杰成了说唱艺人,身为说唱艺人他尽情游走在草原的各个场域(地理空间)。格萨尔王的故事是说唱的内容,亚尔杰的一次次表演让文化空间变得愈来愈鲜活、独特和厚重。空间的融合使神灵、祖先和说唱艺人统为一体,揭示了亚尔杰沉浸其中、自由自在的心灵状态,凸显了草原人民那种无拘无束、生机勃勃而又与环境浑然一体的生存境况。由此反观,拉萨所缺少的,正是融于自然、传统以及部落的自由完满的人性,得到的却是技术理性下苍白的、机械的生活以及对金钱的无休止追求。显然,两个地理空间有不同的文化隐喻——草原文化和现代化的技术文化。前者代表草原(也是藏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后者意味着草原的现在与未来。作品以说唱艺人处于草原时各种空间的交融和谐体现生活世界自由完满的状态和在拉萨时各种空间的分裂对抗体现现代生活中人的苍白和碎片化,这两个空间的对立,则是两种文化的对立,体现着作者对传统的依恋、对现实发展的反思以及对生存价值的感悟。
总之,次仁罗布的小说,既有丰厚的人文价值,亦有深刻的民族内蕴,还有匠心独运的叙事技巧。不止《杀手》和《神授》如此,他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特点。例如《放生羊》亦广受赞叹,小说通过不固定的受叙者(桑姆和羊)的频繁变动,将现实与想象以及多个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呈现,凸显了人对于信仰的本质需求以及拥有信仰的人的饱满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限于篇幅,不再列举次仁罗布的其他小说,但可以肯定:聚焦人的存在、关怀并重审藏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是次仁罗布作品的核心主题,而他又善于以具有独创性和个人风格的叙事技巧和语言特色予以表现。
三、结语:民族文学批评应坚持人文性、民族性和文学性的三元统一
次仁罗布创作的启示在于:书写民族文化、展现民族性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写作出发点,但必须有艺术的创新,不能一味描摹生活甚至捏造民俗,停留在描绘民俗、仪式、语言、风光等表象的景观化写作上。亦应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超越狭隘的民族视野,让文学具有更深更广的人文精神,具有“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的力量,“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这是文学作为人学的首要和必然的要求。
反观之,民族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应超越之前囿于民族特色的话语习惯,探索更全面、更深层的研究路径。粗略而言,要了解人文性、民族性和文学性才是创作和批评的核心原则。人文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评价的首要标准,其基本出发点是面对当代人的需求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民族性是文本世界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即别林斯基所谓“民族精神生活”[9],果戈里所谓“民族的眼睛”[10]。研究者亦应摒弃民族文化与文学作品简单对应的模式,重视文学艺术的特殊性,注重文学的文学性。文化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见,人文性和民族性必须以审美形态(文学性)的方式予以实现。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思考人文性和民族性价值是如何表现的?由此,便能将三个维度统一起来,形成对民族文学作品更全面的阐释。总之,当前的多民族文学研究务必从文学简单反映论的泥潭中走出来,不再片面地将作品内涵与民族文化简单对应,务必立足于人文性、民族性和文学性三元辩证统一的批评立场,方能推进多民族文学研究朝着更细化、深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