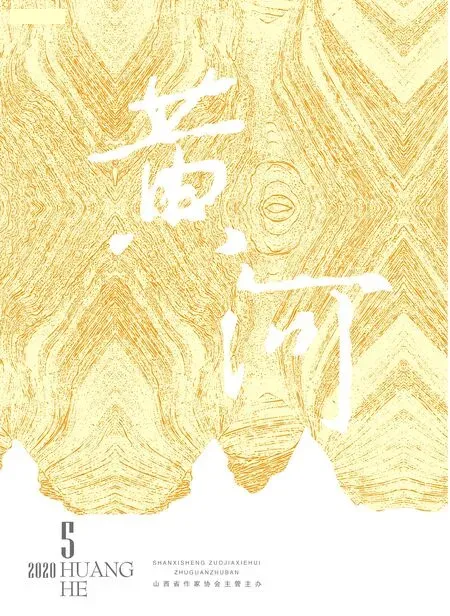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关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辩正(选载)
李希凡


蓝翎认为,他与我的合作“纯粹出于历史的偶然”,我也有同感。不过,既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那偶然的合作便早已汇流到历史的必然中去了。当事人“据实而写”的回忆录,向来极受社会的欢迎和称道,但打着“对历史负责”的幌子,歪曲事实贩私货,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个人的经历或说历史,是客观生活的真实记录,它决非可以凭人主观臆造,随意编排的“故事”,也绝对容不得别人去做任意修改涂抹。因为那伪造的细节与小事拼凑起来,也必然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格格不入。而本文与蓝文之辩正,自然也无法脱离那被不厌其烦编造过的细节与小事。如前所述,蓝翎为了强调在合作中他那道“工序”的至关重要,极力渲染我的“学历不高”和才疏学浅,以示“接受鲜花和受奖的人,恰恰是出力最少的一位”(引自“蓝文”)的不公道,甚至还越俎代疱地写了我的简史。与其让人别有用心地胡乱编排,还不如自己真真真实实地写出来,也好与“蓝文”两相对照,避免将来“死不暝目”的遗憾!
解放前,我的确有着一段辛酸的生活经历。我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华北不久,家中的经济支柱——父亲得了中风偏瘫,大哥和大姐又都去了“大后方”参加抗战,二哥患脑膜炎病逝,家里只剩下老弱的父母、二姐、我和幼弟。那时,我刚考入通县潞河中学念初中,为家境和生活所迫只得辍学,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到处谋职业找饭碗”。先后在北京宝西服店当过学徒,在白纸坊印钞厂作过童工,在石家庄市图书馆作过图书管理员。 ……抗战胜利了,给我带来的仍是贫穷和失业,我梦想上学而无门……1947年,我为了求学来到青岛大姐家。青岛解放后,军管会文教部长王哲同志(“文革”前曾任山东省副主席)亲笔写信送我上了济南华东大学。 1951 年,华大与青岛山大合并,我继续在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又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作研究生,先后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和哲学研究班学习……我想,也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才对使祖国和自己获得翻身解放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有着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感情。
我在青岛姐姐家寄居的两年,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47——1949 年。我一方面在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课程,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一方面笔录姐夫赵纪彬的著述。而决非像蓝翎所描述的那样:“料理家务”“抽空旁听”,这种本末倒置,大概也是他贬人的小花招吧!我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毛头小子能料理什么“家务”?不过是扫扫地、买买菜,送外甥去幼稚园而已!至于烧饭之类的真正的“家务”,从来都是姐姐做,老实说,我至今尚未学会。
当时山大文史系主任是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他是赵纪彬的挚友。因此,我很受优待,他发给我的旁听证,既是免费的,又是凡文史系的课程都可以去听。两年间,我听过的课程有:杨向奎的中国古代史、王仲犖的魏晋南北朝史、丁山的古史考辨、陆侃如(古代部分)和冯沅君的(中古部分)中国文学史、萧涤非的魏晋南北朝诗、殷焕先的《说文解字》、赵纪彬的哲学概论等等。学得好与不好,另当别论,借用一个时髦的词儿,当我上山东大学文史系时,虽是“不高的学历”,却有着学习过大学文科许多基础课程的“含金量”。
一个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最好免开尊口。赵纪彬根本不是“蓝文”中所说的历史学家,也从没有教过历史课,更没有做过山东大学文学院长。他只是在解放前夕,因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被地下党护送到胶东解放区。青岛解放后,又随军管会返回山大,担任过山大校委会常务副主任。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有与侯外庐、杜守素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他自己则著有《论语新探》《哲学概要》《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困知录》《困知二录》等哲学与思想史专著;前几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赵纪彬文集》。他的《论语新探》曾受到毛主席的肯定。他还是1924年的中共党员,在20年代就领导过濮阳、内黄地区的农民运动。 30 年代初,曾担任过河北地下党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开始,转向文化工作,曾以“向林冰”的笔名参加过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代表一派意见。他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在百科全书中留名。以蓝翎的“博学多才”,真不该把他是哪方面的学者都弄错的。赵纪彬的生活道路虽然累经磨难,却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自学成材,在四十年代就已应聘为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教授。他曾希望我靠自学走他的路,可惜,我的志趣在文学。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思想引路人,而他的大量藏书,也使我有了探求传统与革命文化新知的优越条件。我终生都要感谢他,不是因为有机会到他身边,还不知会走上什么道路,说不定也会像有些人那样,为生活所迫,或上当受骗,跑到什么三青团或青年军之类的去处“找饭碗”了,给自己的历史抹黑。
赵纪彬因长期坐国民党的监牢,患有神经质的手颤症,这就是他的著述需要口述由我笔录的原因。我笔录过他的《论语新探》《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中国思想通史》中他执笔的有关章节,以及两本《困知录》中的部分论著。作他的笔录,对于我这个“学历不高”的年轻人,是十分不容易的。他强迫我必须去熟读中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王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赵纪彬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著述都是在夜间进行,经常要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但也正是这“笔录”,为我奠定了古代文史知识的根基。因此,要讲读书、修养、积累,在山大入学时,有高中一年级“高学历”的蓝翎,要差得远呐!
“蓝文”说,在我们的合作中,我无书籍、无资料,甚至说我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这种贬人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姑且不说,我如果无资料积累,何由而产生对俞文的不同意见(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破旧的棠棣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那是我人大哲学班同学张钊当时送给我的)?何由而有《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前面的概括和后面的“补充、改写”?说实话,讲读马列,并非自我吹嘘,早在蓝翎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报效”的1947—1 948年,我就大量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如《资本论》第一卷、《剩余价值学说史》《马恩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斯大林选集》(马恩列斯选集均系时代出版社出版)、大连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前辈革命学者艾思奇、胡绳、许涤新、王亚南、于光远的有关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的专著。在文学方面,1948 年,我就已读完《鲁迅全集》(第一遍),以及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和胡风的1948年以前的全部文艺论集,我的老师吕荧的《人的花朵》,而茅盾、老舍、巴金的小说,田汉、曹禹的戏剧,则在我“找饭碗”时,就已读过。至于四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也包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那远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是我的读物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阅读的进步刊物,是每期都送给赵纪彬的臧克家主编的《文讯》、胡风主编的《七月》,而苏联革命文学,更是我狂热搜寻借阅的对象。为此,青岛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毕中杰同志(现已离休,在北京),曾向我提出警告,深怕因此而引起国民党特务对赵纪彬的注意。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今天要写篇文章或什么“回忆录”而追加、编造的,其中大部分“事实”都写在我1956年的入党申请书上。自然,以我当时的知识木平,很难完全读懂马列原著。但它们毫无疑问地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讲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革命,蓝翎恐怕还要迟好几年呢!这也正是王哲同志为什么要在青岛刚刚解放就写信保送我去华东大学学习的主要原因。天可怜见,“上帝”保佑我这穷孩子独有的机缘,我从此走上了“人间正道”。
也正是在这两年里,我结识了山大文史系的几位“学兄,学姐”,像今天尚在编辑《文史哲》的吕慧鹃大姐,以及在1954 年曾经担任《文史哲》责编,并大力支持和发表我们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葛懋春同志。当时他们都是山大进步的反蒋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由于在某种意义上赵纪彬曾是他们的“精神后台”,我也和葛懋春等人很接近,也谈得来,友谊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更加密切。这也算是我们那第一篇文章,在《文艺报》未加理睬,而《文史哲》却欣然接受的原因之一吧!现在,葛兄已重病偏瘫在床,或者因为有什么预感!前几年,他突然把所有我给他的信,全部复印一份寄给我保存。“蓝文”中说:《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清稿,“李希凡看后直接寄给《文史哲》,至于他信中如何说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该刊没有任何人同我联系过”。仿佛这里面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好在这封信还在,没准以后还能派上用场。何必装得那么清高,得了便宜还卖乖,合作写文章,不就是为了发表么?
在山大中文系学习的几年中,我不认为自己学历不高,就不堪造就。山大校刊《文史哲》,本是专家学者们的阵地,它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就是我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见拙著《弦外集》)。那本是我1951年写的文艺学课程的一个学习报告,是吕荧先生推荐给华岗校长,才交由《文史哲》发表的。我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如何,老师同学都在,自有公论,靠自吹自擂,只能徒增笑料。我也不必隐讳,那时有些课程已不能满足我求新知的渴望。因而,在大学期间,我基本上仍是大量的阅读。我除了担任吕荧先生的文艺学的课代表外,同学们又选我当了世界文学的课代表。这是一门新课,黄嘉德、张健两位老师过去都是教外文系的课.教中文系的世界文学,还需要摸索经验,所以经常要了解情况,以制定教学大纲。当时,我虽读完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但对整个欧美文学,还涉猎得不多;苏联革命文学虽看得不少,却不熟悉俄国文学。除果戈里的《死魂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屠格涅夫的《罗亭》外,其他就读得很少了。为了补课,只好加紧阅读。于是,就得了一个称号:“啃大本本,教条主义。 ”有的同学居然还在小组会上提出批评。但现在看来,得益的还是我。正是这段“啃大本本”,使我大量阅读了欧美和俄国的文学名著,受益终生。只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才把它啃完。 “蓝文”在叙述这样一件小事时,也要撒点胡椒面,删除“啃大本本”,只提教条主义,以示我天生骨子里的“左”,真是煞费苦心了。
我也不想隐瞒,我当时思想有点“狂”,在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和作品的评价上,与老师,甚至最尊敬的老师,都有些很不一致的看法。不用说别的,对《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评价,我就和我的姐夫赵纪彬(他长我22 岁),有着不一致的看法,常有争论。我以为这很正常。“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几十年来,无论对母校、对老师、对校友,有难处,或需要我尽力的,也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能做的我都是尽力去做的。 “蓝文”中提到了我们几位有成就的同学——刘乃昌、袁世硕、周来祥、陶阳等,那是客观存在,我希望蓝翎说的是“真心话”,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嘛!同窗好友们的著作和成就,都给我以启示和激励,我至今和他们都保持着同学间的亲密情谊,常有书信来往,真诚互助。蓝翎有么?如果说“一阔脸就变”,恐怕还是用在他自己身上更合适吧?在蓝翎未与我“相立于江瑚”之前,我也是尽已所能真诚相待的,即使在他被划“右派”之后。 “蓝文”中以不少的文字,提到所谓的“狗肉账”和“残杯冷炙”,我不想在这里多说那些跟他在信中已结过的“狗肉账”。只想问一句,我寄给你(包括寄给你妻子的)的“残杯冷炙”只这一笔么?而《红楼梦评论集》却只有过一次再版的稿费。
老师就是老师,尊师在情。但有人打着尊师的招牌,却想达到别样的目的。蓝翎在《变脸》中,就利用一位老师的一篇文章的由头,大说了一番恭维话,其目的就是要把棍子打到我的身上。有些人的“脸”确实是变幻无常,生疮的舌头也能生花。蓝翎大概忘记了他过去是怎样嘲笑这位老师的了。他大概也没有料到,老师目盲心不盲。在他那篇《变脸》发表后,我报快接到这位老师委托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的电话,劝我不必计较,千万不要同他公开论战,影响不好,我很感谢老师的关心和爱护。我让那位同学及时转告,请老师不必为这事操心,只要蓝翎不打上门来,我就不会与他公开对峙。是呵,为这事闹得沸沸扬扬,何以面对曾以有了我们这样的学生而引以为自豪的母校、师长和关注我们的校友们呢!但这次不同了,我只能应战,也请老师和校友们谅解吧!
蓝翎对我们的合作经历,有他自己的体验和感受,那是他的心思,我不予评论。但是,我在起草那篇《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路上》时,讲到党对我们的教导和培养,感情是真诚的,至今初衷不变。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那时的存在;没有共产党的思想之光,我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事业,当然有个人主观的奋斗,可如果没有党所领导的大时代的变革,“个人奋斗”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没有党的思想武装,我们不可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又怎么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而“名扬天下”(引自“蓝文”)呢?《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至今对这场“有其消极的方面”的批判运动的评价,仍然是“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接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曲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而今,当年“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陷入了怎样的矛盾啊?一面在那里力争他那道“工序”的辉煌,一面又忙着同这场批判运动划清界限。怎么就“前提变了”呢?大概是他蓝翎变了“前提”吧?为了讨好当代某种思潮的需要,赶紧往过站,赶紧洗刷自己,其实连共产党都可以不参加,免得日后有退党之烦或砍头之忧!如果说这种人“善于看风向紧跟”(引自“蓝文”),恐怕才是恰如其分的吧!我则无怨无悔。
在事业上,本来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即使在与蓝翎合作的当时,我也有自己研究的课题,从未认为,写作只有彼此相靠,永不分离,也从来未想到过躺在《红楼梦评论集》这本书上。 “蓝文”说,他为了证明“并不是依附别人的人”,“两年的时间”,“写了不少杂文和文艺评论”。而我从未认为,自己在依附别人,所以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1955 年上半年,开会任务太多,而又要抓紧时间完成《红楼梦评论集》的写作,下半年是出国了一段时间,1956 年上半年,整理《红楼梦评论集》交付出版(“蓝文”说,我在后期的写作中,只是起草,都推给他,可真是人嘴两张皮,只能随他说了),我自己又在清理思想,申请入党,完全停止了除《红楼梦评论集》外的个人写作。 1956 年下半年,工作与生活走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了。我仍继续走自己的学术与文艺问题探讨争鸣之路,与何其芳同志讨论阿Q 问题的三篇论文,与戏曲界讨论《琵琶记》的两篇论文,以及评论康濯同志小说创作的长篇论文,都是这时写的。这不是随感而发的杂文,也不是一篇作品的评论,前五篇完全靠长期的资料积累,后一篇也要靠现实资料的全面掌握。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过无任何资料,而写出的文章,我没有这种“天才”。在《阿Q 正传》的讨论中,我反对离开时代、历史、阶级而谈什么“人类普通弱点之一种”;在《琵琶记》的讨论中,我不赞成简单化地用“封建伦理说教”的帽子全盘否定这部古典戏曲名著。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在鲁迅研究界就有不同意见,但在这场论争中,我是一家之言。关于《琵琶记》,那全盘否定的意见,当时虽出自几位戏曲研究专家之口,现在却早已销声匿迹了,《琵琶记》仍活在当代戏曲舞台上,并上了电视荧屏,还得了几项大奖。蓝翎或许又说我这是“假右真左”,但我也要问一句,他在这两年间写出过这类“一家之言”的论文么?
《红楼梦评论集》于1957年1月出版,同年5月,我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评论集《弦外集》(新文艺出版社,“蓝文”说,他有过一个短文底稿本,也叫《弦外集》,我从来没看到过,也相信那“弦外”与这“弦外”,绝不是同样的“灵犀”);1959年出版了《论“人”和“现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了《管见集》(作家出版社);同年,还出版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随后,在1962 年出版了《寸心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出版了《题材、思想、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
既然是“抖裹脚”,关于《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我要多说几句。它是《红楼梦评论集》的姊妹篇。此书出版后,仅1961 和1962年,就四次重印,印数超过“文革”前《红楼梦评论集》两版的总数。“文革”后又重印过两次。我们的《红楼梦评论集》主要是写于1954-1955年间,《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除前面讲到的1954年的三篇关于《水浒》问题的文章外,多数则写于1958 年和1959 年,我自认为,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代表作。它曾是60年代国内外中文系古典小说课的主要参考书之一,1962 年日本《东京大学学报》上曾发表过入谷仙介对此书的专题评论,苏联也有过专文介绍。我想,作为“一家之言”,此书达到了我重新评价除《红楼梦》外其他三部古典小说的目的和心愿。
这些书的文章当然也有好有歹,甚至速朽的文字,或如蓝翎所说“假右真左”之类,但就《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来说,我所批评和不赞成的,则都是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和把文学作品等同干历史的简单化的倾向。我写这本书,仍像写《红楼梦评论集》一样,靠的是长期积累,而不是临时抓点材料。“蓝文”说,有人认为,他“是附骥尾以增光的人物”。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表露过这种意思,纠缠这个,有什么必要呢?但我敢说,从50 年代与蓝翎开始合作时,我自己就有个独立的存在,而且是沿着《红楼梦评论集》的路子走下去的,时刻表明着没有蓝翎,我也能行,或许更好。就从“文革”后的这段时间来说,我在编辑与行政工作之余,已写出了一百七十余万字的论著: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牡《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两本鲁迅研究专著——《〈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三本评论与研究文集:《文艺漫笔》(1985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文艺漫笔续编》(1990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1993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以“《红楼梦》艺境探微”为题旨的一本尚未完成的论著,已写出二十二万字的论题,均发表在全国学术刊物上,曾应人民日报出版杜的约稿,编选了其中八篇,题名《说情》,收入它们的《百家丛书》(1989 年出版),这些红学论文仍然坚持1954 年提出的基本观点。如果讲自我感觉,它自然比《红楼梦评论集》高明一些,我写它,也正是为了要弥补“儿童团时代”的粗糙和浅露。
研究学问,讲究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岂只对研究四部古典小说我早有自己的构想,就是两本鲁迅作品的论著,虽写于70年代末,80 年代初,却积累、酝酿于50 和60年代。我已出版了除两本选集和《红楼梦评论集》外的十四本著作,共计三百多万宇,自信并未只靠《红楼梦评论集》那“半部书”而“名扬天下”。我倒想问一句,在《红楼梦评论集》之后,蓝翎有哪一本书,能与之相比可称为“一家之言”的论著?哪怕是可称为“一家之言”的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找后账,编故事,自说自话,哪个观点是他首创,哪段新意是他写的,空口无凭,把他独立写出的真货色拿出来让大家瞧瞧。承他相赠《断续集》《了了录》《金台集》或者还有其它,但那恐怕没有一本是《红楼梦评论集》的“同类”!
为了四十年前的两篇文章,或者说“一本书”“半本书”,何至于痛苦到“哪怕为此而流汗、流泪、流血,用鞭子抽打自己”(引自“蓝文”),这么闹腾,岂不活得太腻味了!
自然,引起蓝翎“死不瞑目”的怨恨,使蓝翎非要讲清楚不可的,说开了,无非是那两篇文章,或者说那本书,没有他的“工序”不行,他出的力最多,我靠他,我沾了他的光,却成了接受鲜花和受奖的人。这是领导上不“大公无私”,无“赏罚分明”,不是“真正的伯乐”。总之,得把这个“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首先要说明的是,写最初那两篇文章时,谁也没有想到过会有鲜花和奖,它的出现,使我手足无措。我曾找过当时的领导袁水拍和袁鹰同志,说明这会使我和蓝翎相处出现困难。他们都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个人间的事。至于为什么这样决定,我无权问也不知内情。“蓝文”不是说,他和邓拓同志的关系很融洽么?邓是当时的总编辑,我当时则和邓拓同志接触很少。总不该是邓拓不大公无私,无赏罚分明,不是真正的伯乐吧?当时政协通知我报到时(1954 年12 月中旬),我能不能调到报社,还没有决定下来,我只是拿着临时出入证,被借调来写文章的,并未参加编辑业务,而蓝翎却是在十月间就已调去。所以,“蓝文”所谓的“有关领导者”的“偏心倾斜”在人民日报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在报社还是客人,并非工作人员。那么,这错选驽马的领导究竟是谁呢?我是二届政协共青团代表小组成员,组长是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后来政协开会当然就很熟了,还曾去他家吃过两次饭,听他讲长征经历,但当时却根本不认识他。他总不至于有什么偏心“倾斜”吧!不过,我倒记起一件事来,1954 年10 月,那场批判运动起来后,我们也成了忙人,好多地方请我们去作“报告”。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次“困窘”,我一向对在大庭广众场合讲话十分怯场,但又推辞不掉。大概是十一月的一天,中央团校请我们去讲,我简直不知自己在场上讲了些什么。后来听蓝翎说,耀邦同志率领团中央书记处的全体成员,就坐在最后一排听。我的不知所云的“讲演”,总是比蓝翎的“压大轴”逊色得多了!团中央书记处不会因此而错选我这驽马当他们第二届政协的代表吧?
我以为,还是不要把这样的事只归过于所谓有关领导吧!那时的组织路线就是这样,很注意干部的政治历史清楚,社会时尚和共青团又非常推崇个人道德行为,这可能就是干部路线中的所谓“左”的表现吧!其实,蓝翎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毕业分配工作时,就已如此了。否则,为什么已分配好的单位会有突然改变呢?而且改变的也不只蓝翎一人。
“蓝文”说,在邓拓同志当时对他和我的态度上,我出现了“介意”,还举了“例子”,我自问尚还不至于那样窄狭。当时我在上学,不好请假,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都是蓝翎先见,我后来才见到的。而且我那时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岗位,并非《人民日报》,而是文学研究所。为此,我曾写信给周扬同志,并收到了周扬同志的复信(原信已在1994年第10期《学习》杂志上发表)。后来还是听蓝翎讲,毛主席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要我到《人民日报》来。可不知为什幺,拖了近两个月还未解决。人民大学研究生部通知我回校参加考试,我又没有工资,很焦急是实情,但我怎能为此而“介意”蓝翎呢?他不过是刚到单位的小萝卜头,对这件事哪能说得上什么话,我再蠢也不会埋怨他。蓝翎大可不必因为自己有“介意”,也必须先给我造出一个“介意”来。邓拓同志从56 年直到他去北京市委的60 年代初,都是我的直接领导(签字付印文艺评论版),每周总有两次骑自行车送取大样。他惜别《人民日报》诸战友的诗,我至今仍能背诵,“文革”中有个别人把它作为反党诗来批判,无非是自己心虚,急于同他划清界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邓拓同志是位忠厚长者。“文革”前,我每逢春节去袁水拍家拜年,都要去看望他,他有些要查找的文艺书,也打电话来要我帮他查找,我们中间从未出现过什么“介意”,不劳蓝翎费心。
“蓝文”说他自己曾“因思想问题受到批评和帮助”,说那与划他“右派”无关,但那恐怕也反映了人品问题吧!当时(1955 年),我正在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不知情,回国后才听说。 “蓝文”还讲到,耀邦同志在信上都有批示,但批示了什么他没讲。要说那只是“在私人信件中流露过志得意满的情绪”,就太简单了吧?它们充分表现了蓝翎善于编故事的“才能”!哪是什么“志得意满”?那分明是编谎话吓人,那时你已不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而是二十四岁的成年人了,扯那样的谎,难道今天都不觉得脸红嘛?!什么“写于中央领导接见的汽车中”,哪位中央领导当时接见过我们?真不害臊!这样的编故事的信有好多封,它们寄到当时的农村会产生什么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其后还发生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事,但他既然“真事隐去”,我也不便说得更多了。只不过,看了他这次在长文中又编了那么多回顾历史的“故事”,倒使我想起了这段旧事,真是积习难改啊!
“蓝文”中所谓“鲜花和受奖”,就是两件事:一件是二届政协委员,还有一件是出席全国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不在国内,没有参加)。除此之外,我没单独参加过任何全国性的会议,所有文艺界的会都是两个人共同参加的。什么时候我也没有认为,我独得了蓝翎眼中的这两朵“鲜花”,是心安理得的。但蓝翎心里明白,决定这些事,事先既不征求我的意见,事后我也无力挽回。所以当二届二次政协会议上,宣布蓝翎为特邀代表时,我心中真有一块石头落了地的轻松之感。自然,从今天蓝翎的情绪看来,他还是认为我夺了他的“头筹”,心理仍不平衡。1956年,又发生了另外的龌龊的事,单位内反应强烈,我除去陪着挨骂,能辩护什么呢?我是预备党员,党支部给我的任务是帮助他,蓝翎已在那里写“半间房随笔”(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被分配在一间宿舍里),他感情上和我有了隔阂,我怎么帮助他呢?正如“蓝文”所叙述的,他对所谓“有关领导”的“倾斜”,有如此强烈的情绪,能接受我什么“帮助”呢?我只能在使他为难的生活问题上,为他多尽点力,谁知“反右”大潮一来,急转直下……
鲜花是要枯萎的,奖品也没有“终身制”。“蓝文”大不满意的这种什么“委员”、什么“代表”的奖励,很快也就停止了。二届政协换届,我也早已因超龄而退团。而且自1956年我辞去与华君武同志一起出访捷克后,即五七年后就再没有受委派出访。“文革”中才知道,这也是事出有因。但我当时既无自觉,也未“介意”,因为单位的历届领导都对我很好。这方面我的确比蓝翎幸运,因为我还保有工作和写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