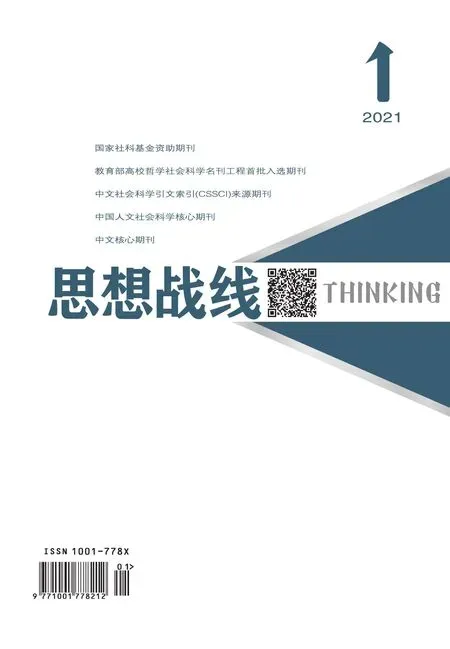族群互嵌格局下的“区域”探析
——基于都柳江流域生态与历史的人类学研究
王彦芸
一、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
区域作为学术研究概念来源于地理学,使用区域的观点“从对各种不同的自然界和它们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并存和互相影响的理解,来认识地区和地点的特性”(1)[德]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与方法》,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1页。是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所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不同学科学者围绕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展开了相关讨论。这些讨论直接导致人文地理学以及历史学发展出对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对空间现象的研究。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历史地理领域,作为一个时空连续体(Space-time continuity)的区域概念逐渐成为一种共识。(2)[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唐晓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而在人类学领域,区域最初被作为一种可以实现跨越与整合的方法被提及和实践,用以超越被“社会”“文化”等概念固化的认识及表述困境,并借由区域研究跳出小地方的局限,以面对具有交互关系的多社会体系,如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经典区域研究,其旨趣并非面对区域本身,而在于突显文化彼此参照的过程。
而真正面对区域问题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施坚雅,施坚雅将基层市场理论引入对四川盆地聚落的空间、市场分布的研究中,将区域理解为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认为区域范围就是按照人的互动为依据的空间形构,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一种对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互动的解释框架。(3)参见[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沿着施坚雅突破行政边界桎梏界定区域的思路,各学者继续进行了补充与反思,如罗威廉(William T.Rowe)提出区域并非指一个由某些关键因素,比如语言、宗教或大宗货物具有连续性或一致性而形成的地区,而是由一些变动着层级地位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4)Linda Cooke Johnson,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5.强调区域是由交换关系连接起来的相当动态的空间范围。也有学者从文化层面出发,强调区域由文化界定的性质。(5)werbner通过对中非洲区域性仪式研究,提出区域性仪式中心不仅不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也超越和模糊了行政和国家的界限。参见Richard P.Werbner et al.,Regional Cult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91.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人类学以“祭祀圈”“信仰圈”带入浊水、大肚溪的研究,将区域的关注重点放置在以民间信仰活动切入的社会联结。然而也有反思指出,这两种区域研究的取向都“过分强调了经济或文化结构层面的影响,没有呈现文化本身的转化弹性与个体作为历史能动性(agency)或行动者(agent)的创造性地位,自然也无法处理文化本身的历史化过程如何得以超越延续与断裂二元化的问题。”(6)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205页。同时,也无视了“国家”因素在区域历史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转型影响。(7)张应强:《木材的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虽然学者进行了诸多反思,但施坚雅的区域研究模式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即在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多重视野下,以人的活动为依据,对“空间”因素加以重视。
实际上,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区域进行了诸多讨论。如人文地理学中,赫格斯特兰德分析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在他的时间地理学中,区域是由人的“生活路径”(life-path)轨迹造就,强调日常活动的实践性对于社会活动构成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基于身体在时空中运动的社会构成分析被认为没有充分关照到人的主体性。总体而言,区域往往被描述成人类活动的静态场景,而吉登斯借由地理学“生活路径”的理论,提出“场景”(locale)的概念,强调人不仅在空间中停留,也不断地有意识的去运用空间,以构建蕴含意义的空间内涵。吉登斯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区域化仅仅理解为空间的局部化,区域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zoning)。”(8)[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 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对于“区域”常被用来指涉有清晰物理边界地区的分析,他认为不能将区域化完全理解为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应该特别包含了“带有社会行为跨越时空进行结构化的内涵”。(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 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这些多学科的讨论虽出发点各异,但共同之处一是以“实践”概念切入强调人的能动因素,二是提及了区域作为空间建构的过程性和时间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在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成为一个兴趣集中且持久的研究主题。在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基础上,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提出一种有着人文主义倾向、与人有关的区域概念,认为“区域是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观念”。(10)历史人类学相关研究中,强调区域是跟随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流动和作为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流动而流动的,研究者不能过分拘泥于僵化的时间或地理界限,应以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并超越所谓“国家—地方”“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之类的二元对立。参见黄国信,温春来,吴 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而人类学界也开始将视野投向历史上的他者,提出要去注意区域之中人的文化表述,将区域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11)认为区域可视为一个有意识的历史性结构,我们可以通过包含于区域构建之中的文化表述来加以把握。参见David Faure &Helen F.Siu eds.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强调历史中他者的能动性,即文化的创造力,并着重在观念层面上反思不同的时间观、历史心性之下对区域、历史之理解。(12)参见李仁渊《在田野中找历史:三十年来的中国华南社会史研究与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刊》2018年总第88期。实际上,这种着眼人群历史、关注区域社会建构过程的区域研究方法,并非仅在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领域中进行,也是当代人类学再思全球时代、跨国连接与流动之复杂关联的重要途径。(13)段 颖:《从地方、区域到全球——文思理教授的人类学之旅》,《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可以说,随着多学科的不断跨越与合作,作为概念的区域已相互交织难以条分缕析,但作为方法的区域,不同学科在各自学科脉络之下开展研究及合作,以区域为视野持续开拓和延伸。
实际上,区域研究的视野在中国运用已久,它是超越中国传统村落、认识整体中国文明的重要途径。20世纪上半叶,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开始着手中国的社区研究,目的在于不仅了解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1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94、95页。之后在几代中国人类学家的努力下,基本形成了“民族走廊”“西南民族”“珠江三角洲”等相关区域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于有着纷繁复杂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的中国西南地区而言,在一个区域整体内研究族群间的流动性与交互性,成为西南研究的关键所在。虽然西南区域研究延伸至此,但学界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持续面对,一是我们仍然面对着诸如“社会”“文化”“民族”“族群”等社会科学核心概念对现实研究所带来的限制,而这些限制使得每一个在西南开展研究的学者在面对真实社会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意难平”之感,进而需要持续在理论旨趣和方法视野上进行突破,如王铭铭提出以“关系”为核心消解概念之隔阂。(15)参见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二是学者们深感我们仍需要扎实的田野调查追寻西南社会的独特之处,能否从底层开始建立起这些区域之地方社会的架构,找出各个区域最关键的分类范畴或分析概念,才能进一步了解各个区域历史发展的独特性。简言之,当面对西南社会人群的流动与交互、身份的单一与多重,关系的联结与区隔时,是否可以突破概念之局限,追寻一种统摄多元与整体的研究路径,成为可以深入的方向。而本文则可视作在这一方向上的一种实验与尝试,以区域为核心,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探讨区域结构化过程,将不同人群纳入其中,既关注地方人群基于自身特殊的地理生态、社会关系结构对区域多层次的界定,也探讨特定时间中不同人群迁徙、交往互动对区域整体的动态性形塑。
综上所述,本文以都柳江流域多元人群互嵌的地方社会为例,以区域为切入点,力图在区域多层次的缩与展中把握多元与整体的地方图景。都柳江自清中期因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地区控制而开始了航道疏浚,最初因军需而开通水道,这不仅为国家在都柳江流域建立起统治秩序,更对都柳江流域内人群构成、经济交换、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航道疏通后,来自下游西江、珠江之闽粤商业移民溯江而上,与流域内各人群共居。都柳江水道、纵横交错的陆路网络、及两岸高坡地带不同人与物流动、活动而构织、联系,区域社会秩序与内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被建构。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对于都柳江流域来说,“区域”并非一个边界清晰、扁平的地理空间范畴。一是由于山地、河谷之自然差异,居住其间的人群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人群分类形成了地方性的区域划分。二是因人、物流动,不同族群迁徙、共居互嵌,在不同生活层面互动交往,形成了不同面向的区域社会联系。在这里观察到的区域“合而不同”的属性,正是来自于都柳江通道的流动性与文化的杂糅,从而使区域呈现出立体而多层次的特点。因此,本文以都柳江流域为切入点,试图在多种人群互嵌和多元文化类型的地带,围绕人的活动,在地方逻辑之下去呈现并理解既为特性又为整体的“区域”。
二、自然与历史:都柳江族群互嵌格局形成
都柳江属珠江流域的西江上游水系,发源于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拉林乡磨石湾,流经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黔东南州榕江县、从江县等地,而下游则于黔桂交界地带穿梭蜿蜒,直至广西三江县老堡乡与浔江汇合后称融江,融江流至广西凤山县与龙江汇合后称柳江,柳江注入西江后最终汇入珠江流入南海。都柳江流域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苗岭山脉向广西丘陵山地过渡地带,在河流的作用下,两岸山势陡缓相沿,并形成不同规模的谷地,又在若干支流地带形成坡陡底窄的沟谷,良好的水利、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得大量人口在山地或河谷地带栖息,形成了坐落于山间、河谷间规模不一的“寨子”。
历史上都柳江名称多变,如宋朝时古州(16)今贵州黔东南自治州榕江县,位于都柳江中上游。至老堡河段称“王江”,明代亦称“福禄江”,贵州官修文献中记载:“福禄江,自榕江来,直贯全境,南流广西,长八十公里,水势浩荡,舟楫畅通,上溯可达三都,下驶则至香港。”(17)贵州省从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从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6页。而在广西三江的志书之中,都柳江又被称为溶江,直至新中国建国以后才定名为都柳江。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央王朝对都柳江流域的治理也各异。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开始致力于对西南疆域的拓展。明朝初年,在西南地区“开屯设堡”,“拨军下屯,拨民下寨”,并通过“改土归流”逐步将西南地区纳入王朝国家统治秩序之下。在此基础之上,清代雍正年间始开辟“新疆”,在今天的贵州黔东南地区设立“新疆六厅”。正是在中央王朝开发西南的过程中,都柳江流域进入国家视野。
在都柳江流域,早期居住的是被称为“苗”“硐”“猺”的人群。文献中记载:“在古州之苗有硐家水家猺家黑苗、熟苗生苗各种,自清江来者仍其旧,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硐苗,中有土司者为熟苗,无管束者为生苗。”(18)余泽春:光绪五年《古州厅志十卷》卷一,光绪十四年刻本,第十八页。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控,逐步将苗民纳入流官的直接统治之下。贵州巡抚张广泗曾奏请:“都江一带,皆阻以生苗,如来牛、摆调之类,皆以一大寨领数十百小寨,甚为凶顽,最称难治。欲使都江开导,直达粤西,非勒兵深入,通□各寨。”(19)民国《三合县志略》卷5《水道·附鄂尔泰奏开都江河道疏》,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5~86页。之后则开始修凿都柳江航道“以济军需”。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调集广西军对古州地区的苗人进行镇压,并组织地方土司率士兵对都柳江航道进行疏浚。雍正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又组织清军治理都柳江独山州三脚屯至三洞段,以及古州之诸葛洞至溶洞段,不仅使舟楫可通,也在这一过程中开辟古州。
嘉庆年间,政府又先后几次对都柳江进行治理。经过这些工程,都柳江的河道得以疏通,船运也顺势展开。因政治军事因素促成的河道疏浚,从客观上加速了流域开发,特别是促使当地商业交换活跃起来。其中一重要因素,在于与粤地联通后,此区域由食川盐改食粤盐,更于乾隆五年(1740年)在都柳江上游古州设立盐务总部。因盐的流转贸易,带动了不同身份的人群进入都柳江流域。有记载称:“境内除镇标兵丁及屯军外,悉是苗人,流寓汉民绝少,自设盐埠以来,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贸迁成市,各省俱建会馆,衣冠文物日渐饶庶,今则上下河街俨然货布流通不减内地。”(20)林 溥:《古州杂记》,《黔南丛书》第五集第二册,(民国)贵阳文通书局代印,第四一五页。随着粤盐自下游向上游迁徙的,还有河流所联结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各地移民。同时,移民的进入与交通的通达,也促进了都柳江流域的木材由上游向下游交易。都柳江两岸木材资源丰沛,木材由高坡收下后在江边寨子集中扎排,可沿水道由排工放运至下游广西、广东等地市场。食盐与木材两宗货物的流动与买卖,吸引了更多从事商业活动的移民沿江上下迁徙,其中,更以广东福建两地移民为主,他们定居在水网交通便利的江边河口位置,其聚居之处,往往也成为了都柳江流域比较重要的市场节点。
航道疏浚后,都柳江流域和闽粤沿海地区的贯通,使它成为一条人与物流动性极强的通道,也成为商人进入西南腹地、苗疆地区的必经之地,而都柳江通道也成为南岭走廊上,联结海洋和苗疆腹地的重要通道。都柳江流域的变化,一方面带来的是新的人群,如汉、客家的加入;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变迁,也使得原本居住在都柳江两岸山地的本土人群开始迁徙流动。虽然这一过程因少数民族无文字记载难以追溯,但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在都柳江流域各地听到苗民被“客”赶上山的传说,以及在地方口耳相传的侗歌中,不断听到流动与迁徙的故事。(21)侗族祖源传说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侗歌的形式所唱《祖公上河歌》,此歌词中显示苗侗祖先认为自己也是沿都柳江溯流而上,其路径与上述客家移民的迁徙路径相仿,歌词中所涉及到的地名,涉及了都柳江下游区域中的广西三江县、贵州黎平县、从江县等村寨。虽然传说故事不能作为我们判断苗侗土著迁徙的确凿依据,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上述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的流动不仅局限于外来移民,地方社会内部同样也会因市场活动抑或社会秩序的变化,带来土著的流动。比如原本都柳江若干支流的部分苗侗人群,就因都柳江流域商业化的推进,迁徙至都柳江主航道上一些重要的商业集镇,进行放排、给老板打工等工作,依靠市场谋生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都柳江特有的多元人群格局。
综上所述,当下我们所见到的都柳江族群互嵌格局,与历史上王朝在西南苗疆的系列举措有关。都柳江河道的疏通,人口、商品、资本的流动,给地方社会带来新的要素,人群的居住空间也发生实质上的变化。在此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基于都柳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生态,形成了分别在河谷与高坡聚寨而居的空间格局。虽大致上以“高坡苗、河边侗”分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泾渭分明。高坡居住着苗族、侗族、瑶族、壮族等不同民族,河谷地带则以侗族、汉族为主。至今,在都柳江流域苗侗语里,村寨名称中带有“坡”和“河”的情况十分普遍,且高坡与河谷寨子之间也形成了既区隔又相互联系的关系。(22)都柳江流域高坡与河谷人群的互动关系讨论,参见王彦芸《山地与河谷视野下的族群互动与区域认同——以都柳江下游富禄乡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另一方面,也在都柳江主航道两岸,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商贸集镇地带、交通枢纽处,形成了多元人群相互交错、交织的互嵌格局。
上述这一历史背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由于人与物的流动,“地方社会由过去‘传统’的村落,逐渐扩大到区域为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或原有的区域系统之构成重组,因而有区域再结构的现象”。(23)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96页。由于都柳江河道疏浚,不仅原有的人群格局与联系延展到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不同人群之文化与观念也随之相遇,社会关系与秩序也面临着再调整。因此,随着空间、关系、观念的多重变化,区域的建构就在这一过程中发生。
三、“洞”:基于村寨关系的地域性联盟
在都柳江流域族群互嵌的地区,不同人群对于他们身处的“区域”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至今,我们在整个都柳江上下游地带仍常会听到一个与人群分类有关的空间概念,侗语称作“dangx”,在侗语中意为“一团、一帮”,它往往是若干个村寨基于婚姻或合作所形成之联合体,而它的空间范畴和内部关系,就是生活在都柳江流域少数民族头脑中的“区域”。这种由村落联盟组成的人群范畴,在诸多文献及已有研究中亦被称作“款”。实际上,侗语中“dangx”的发音,近似于汉语中的“洞”或“塘”。在都柳江上下游,带有“洞”的村寨名称亦很常见,乃至一些村寨联合体,也习惯在“洞”前加上相应的数字,表示具体的地区,如“六洞”“九洞”等。(24)“六洞”包含了柳江下游流域包括贯洞、云洞、洒洞、塘洞、肇洞、顿洞6个小“款”。贯洞小“款”辖今贯洞各寨;云洞小“款”,辖今庆云、务垦、龙图、样洞各乡的大部分村寨;洒洞小“款”,辖今新安乡大部分村寨、龙图乡干团村各寨以及独洞的伦洞等寨;塘洞小“款”,辖独洞、塘洞、上皮林等寨;肇洞小“款”,辖从江县洛香乡各村寨及黎平县肇兴乡部分村寨;“九洞”则指都柳江支流双江河上游的增冲河、牙现河、曹平江一带村寨联合体,包括现在从江县的高传、信地、增冲、孔寨、贡寨等村寨。在整个都柳江上下流域,当地侗语中有“Jus dangx jenc,Xebc dangx nyal”的说法,其意为“九片山、十片河”。靠近河边的地带分为10个聚落联合体,在文献中被记载为“溶江十塘”,今天在地方仍然流传着“溶江十塘歌”,歌中所反映出的溶江十塘范围,是由都柳江沿岸自贵州省从江县石碑村至广西三江县老堡乡的诸多村寨聚落组成。山上高坡地带分为9个聚落联合体,且每个联合体内部,又可分为更小范围的联合体。有研究认为,“塘”“洞”的地理单位,与唐宋以来在西南实行的羁縻制度有关。也有学者讨论“溶江十塘”与清代在都柳江一带所施行的塘汛制度是否相关。但在都柳江流域,羁縻制度、塘汛制度的具体实施因缺乏文献记载,从而难以理清地方所称之“dangx”与制度设置之“洞”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从都柳江流域的地方观念出发,以其内部特殊的人群关系理解这一地理空间概念。
在地方“dangx”的范畴之下,村寨之间遵循更团结的共同防御或者内部通婚关系,且这一范畴并非由单一民族构成。组成同一个“dangx”的村寨中,也可能包含苗族、侗族、瑶族、壮族在内的不同民族。即使具有不同族群界线的村寨之间不能相互通婚而形成亲属关系,但只要同属于同个“dangx”中,就要共同遵循同一套地方规约以及权利义务。这些权利义务包含了诸如防范外来入侵和盗匪掳掠、村寨联谊、祭祀及共同处理地方重大事件等。随着航道的开辟,国家力量在都柳江流域的进入,以“dangx”为核心的权力机制虽然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改变,但“洞”却留在都柳江流域诸多村寨名称之中。至今,这一地点的诸村寨也仍然保留着由“dangx”沿袭下来的村寨间人群关系和秩序。
在上述“九片山、十片河”为基础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高坡与河边有着较为清晰的界线。在当地人的头脑中,高坡与河边两种不同空间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界限,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也成为都柳江流域的一种文化表达,变成了传说故事,或以禁忌的形式被人们遵守,如高坡人不能下山居住,下山会被水淹;或者认为最先来到都柳江流域的是瑶族,住水边,苗族来了则把瑶族赶上山,而侗族来了则把苗族再赶上山,瑶族就只有再往更高的高坡走。由此可见,虽然地方社会形成了一团团的村寨联盟,但其内部,各个族群间,彼此的人群身份差异与边界,并没有被此种地域性的联盟彻底消解。基于生态和社会两个层面,高坡与河边仍是重要的分界标准,并在婚姻、市场、村寨联盟各个方面,成为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隔的两个层面。从前述下山禁忌和族群上山传说中也能看出,高坡和河谷人群间存在的这些区隔与认同,并非仅仅与生态环境、族群身份相关,同时也与彼此所持有的文化差异有关,其语言、服饰也因而不同。居住不同生态环境和关系格局中的人群,产生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意涵,并通过此种文化将各自维系在各自所认同的“区域”网络之中。
不过,山与河虽看似区隔,也并非泾渭分明。一些位于河谷地带的村寨也与高坡村寨结成同盟,成为高坡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保障。因此“dangx”背后的地方秩序和关系,也是山地人群与河谷人群互动接触的重要保障机制。本文对“dangx”以及高坡、山下不同性质空间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简单地从地理生态上划分人群,只是试图强调当我们以“区域”进行探讨时,需要看到这些地方地理空间范畴背后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也需要看到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系统地区,区域内部所呈现出的既与自然生态相关,又与人的观念文化属性紧密相关的丰富性与弹性。
虽然河道所带来的人群、物品流动,使得高坡与河谷必须在垂直空间上跨越界线形成新的联系,然而,“九片山、十段河”所蕴含的地方社会传统秩序与村寨关系,并未在河道疏浚后的区域商业化过程中逐渐式微,而是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被灵活运用。自都柳江河道疏浚之后,清政府在该流域设厅建制以执掌地方,然而在整个清代后半期,苗疆各地“起事不断”“叛服无常”。太平天国时期又受到来自下游粤地诸多兵燹骚扰,(25)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首批太平军三千余人进入都柳江六洞地区,当地一些士绅和农民加入太平军,之后约十多年间,与清军对峙的太平军在都柳江流域的永从县和下江厅都非常活跃。与此同时,贵州侗族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在都柳江一带,主要的起事地区为“六洞”和水口、古邦、南江、高岩等“四脚牛”一带。甚至在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村寨之间反而更加广泛地开展联盟进行团击。为了调整苗疆政策,清政府从咸丰年间开始兴办团练,但团练在结构上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与此种地方性组织并不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地域性的村寨联盟在上述历史过程中不但没有消解,反而借由各种历史事件得以巩固。为应对不同的历史情境,一些联盟的关系经历了重组变迁,但基于村寨的关系机制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另外,在社会安定之时,基于特定的历史关系,村寨联盟也会跟随新的社会环境制定新规约并共同遵守,或者通过“吃相思”(26)“吃相思”是一个寨子全体成员前往另一寨子做客,通常伴随唱侗歌、侗戏、聚餐等活动,并持续3天。、区域性节日等文化机制,维系彼此村寨间的关系,用文化手段明确彼此交往规范。
虽然都柳江流域以村寨关系为核心的区域看似边界清晰,然而它并非是封闭和一成不变的,相反,这种基于人群关系的区域具备兼容性和包容性。比如上文中提到,从清代陆续赴都柳江流域做生意的外来移民,要在村寨定居,必须投靠其村寨联盟,与联盟中某一家结成“兄弟”,甚至改姓以示联合,并通过举办相应的仪式进入关系结构,此关系一旦缔结则永久有效。直至今天,我们仍能在都柳江流域观察到很多此种村寨联盟、人群流动、和姓氏关系历史的延伸。正是“dangx”这样的地方性组织的性质和机制,使得因流动而汇集的多样人群得以交流互动并交错生活,既保持了内部复杂的身份差异和文化差异,又保证了不同人群可以遵循同一套村寨联盟的秩序,而形成“侗”“苗”“汉”“瑶”交错交流又为一整体的区域社会。这样的区域并非扁平、均质化的地域范围,而是由不同族群关系、文化以及人的活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交织形成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并与多种观念交织的区域。
四、市场、婚姻与复合象征体系:相互交织的整体性区域
都柳江航道疏浚之后,区域随人的活动产生变化。苗疆地区商业的发展带来新的人群和市场流动,使得山下临江而居人群的生计方式、出行方式都呈现出一种流动性,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沿着江河在更大范围内构织起来。居住在河边的侗寨开始参与水运贸易,一开始从事制船、跑船运输、放排,逐渐地跑船的人和下游商人、老板熟识之后,取得了老板的信任,继续深入上游或支流收购木材参与中间交易,深度参与到市场网络中。在水路货运兴盛时期,沿岸村寨几乎都参与了上述贸易活动。一些位于交通枢纽的沿岸村寨,常有船停泊码头过夜、中转,人群关系也因此建立。由此可见,由物的流动连通起来的市场,是人群建立联系的重要要素。不同人群通过水路联系到更为广远的地方,沿河分布的村寨来往也更加频繁。以都柳江下游广西三江县富禄乡为例,富禄作为流域中一个重要的货运商镇和中转码头,与下游的产口、良口、大滩、洋溪、勇伟、波里、高安,富禄上游的葛亮、匡里、八洛、新民、梅林等村寨来往甚密,而富禄人群的婚姻关系也以此为范畴缔结。
木材贸易带来的并不只是都柳江主航道上的市场繁荣,还将各支流也整合到这一区域市场网络中。由于都柳江若干支流连接的是地势更高的山地,木材资源大大超过都柳江主干道两岸河谷,且在丰水季节,这些支流又提供了理想的放运木材通道。因此,商业移民往往会深入支流,在交通便利处定居经商,一方面方便收购木材卖往下游柳州、广州,另一方面又将食盐从粤地带往山地,再用所赚取的利润在支流地带买卖山林土地。实际上,今天人们还能回忆起,都柳江主干道两岸的村寨,更多参与到扎排放排等运输环节,而地势较高的支流地带,才是都柳江流域木材市场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在山地流域,因资源在水平和垂直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在此基础上,以人的活动所连接的市场网络并非是平面的。市场作为构造整体区域体系的一个重要面向,将山地、河谷在不同层面上关联起来。
在上述过程中,今天所称之为“苗”“侗”的人群,也借木材的栽种、买卖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并与外地商人发生接触。然而不同人群在市场中的联系各有不同,居住在都柳江两岸的侗族人因参与货物贩运而具有更强流动性,其社会关系沿河上下辐射范围也更广,相对而言居住在山地高坡的苗、侗、瑶,则多在海拔较高的高坡、支流河网地带发生联系。居住在高坡的人群,在回忆木材交易的历史时,常强调他们并不下山,把木材交给山下“老板”即可。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是闽粤籍为主的客家移民。客家移民不仅与迁出地广东、福建家乡仍保持着联系,同时,客家商业移民因依附市场而生存,沿河开设商铺或分铺,或在支流高坡经营林地,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辐射范围更广,既沿都柳江下游延伸至珠江三角洲地带,同时也深入高坡、支流河网地带的市场节点中。可见因不同人群所居住自然生态环境、在市场环节分工的不同,所形成的区域社会网络也各具差异。
在婚姻方面,出于门当户对的观念,客家商业移民大多只与汉族移民相互嫁娶,随着移民代际增加,与当地侗族、苗族通婚的数量逐渐增加,但多局限于家财殷实的地主家庭。因此客家移民的姻亲关系,主要在沿河上下重要市镇以及支流重要市场节点产生,如都柳江下游的贵州西山、八洛、贯洞、水口、广西富禄、古宜、融安等地。此种姻亲关系网络,帮助客家移民在不同市场环节中获得支持。对于地方苗族、侗族、瑶族等人群或村寨而言,婚姻关系与市场关联并不明显,其通婚范围更多与前文的地方村落联盟相关,同时也受族群边界的影响,以及因高坡—河流这一人群区隔,呈现出“不嫁高坡”“高坡不下山”的通婚禁忌。由此可见,在都柳江流域,通婚不仅与区域中的市场体系紧密相关,还受多元人群身份、地方秩序、文化观念、地理生态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从而在现实生活层面构织出复杂多面的区域人群关系。
如果说实质的区域是由前文差异性、交错性的人群互动关系建构,那么作为一种整体的区域意象,则更多的由地方复合共享的象征体系建构和表达。庙宇和民间信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一直是都柳江流域非常突出的现象。以下游广西三江县富禄镇为例,其间林立着孔明庙、天后宫、关帝庙、三王庙、萨岁等不同庙宇。这些民间信仰,本是在地方历史过程中,因人的流动、交汇被汇聚于此,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多样信仰的内涵和符号意义又被相互采借、杂糅、创造与再创造。在同一符号不同诠释的基础上,其祭祀的人群范畴,由原来的某一特定人群逐渐扩展,演变为区域内多元人群共享的象征体系,并由此产生了区域内不同人群共同参与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以都柳江流域非常重要的“三月三花炮节”为例,“三月三花炮节”是一个多村寨共同参与的区域性节日,节日活动的重点是抢花炮,背后的文化意义在于获得此花炮所对应的神灵照拂。在都柳江流域,“三月三花炮节”通常包含三枚花炮,分别对应当地三种不同的庙宇和神灵。作为一个区域节日,一方面地方各人群乐此不疲的充分参与到这一节日中,另一方面,对“三月三花炮节”及花炮的诠释,又保留了各自的文化逻辑。借此,“三月三花炮节”可视作整合区域内原本含义不同的象征符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复合方式。(27)王彦芸:《节日内涵流变与地方文化创造——都柳江下游富禄花炮节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我们观察到的都柳江流域不同人群理解各异但又共同参与的“三月三花炮节”,正是在上述人、物、观念流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节日中体现出的极富创造性和杂糅性的区域意象,也随着历史和现实被不断地修改和再创造,而作为整体的区域,也在这一动态的文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和表达。
由前文可知,都柳江多元人群因生活世界的维度不同、镶嵌在各异又交织的区域实质联系中。这种实质的联系是人群互动与整合的基础和条件,但内部的种种差异,又因复合象征系统在文化层面相互杂糅、借用,被极富能动性地创造生产。区域就在此种“实”与“虚”、“异”与“同”之间交错往返,作为整体的区域得以呈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市场、婚姻、关系、意义多样却共享的文化象征,人们在其间活动,并不断赋予区域意义,既与过去相连,又根植于当下实践。此种既包含了时间、空间,又包含了人和观念的区域,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地方社会的关键。
五、从“在区域中研究”到“研究区域”
前文从都柳江流域的人群历史出发,在地方逻辑的基础上讨论何为区域的问题。而此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关涉到我们如何在研究上实现对西南社会整体性和特殊性的双重把握,即在一个充满流动性、交互性以及多元人群共生互嵌的地带,整体何以成为可能?本文借都柳江流域特定的人群历史、社会结构,探讨这一区域的建构过程,虽不能视作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但其立意在于抛出问题并以区域概念为切入做一种解答的尝试。此前,前人对于整体西南社会这一复杂性图景已给予了充分关注,一是从人的流动性出发,形成了“走廊”学说的宝贵成果;二是聚焦于“物”的贸易流动,形成了“通道”研究的诸多探讨;而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开展的区域研究,也在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地方社会形塑方面产生了大量有益的讨论。
上述研究都在区域性的关联整合与民族间交往互动方面,进行了细化与拓展。区域本身虽较少被讨论,但作为一个有共识基础的观念和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在西南研究中,即“在区域中做研究”。然而,区域本身的动态建构过程,及其在地方逻辑之上的理解和表达,也许不仅能继续帮助我们探讨整体之形成,同时也能在整体中持有一种异质性追问,以继续细致的田野工作,把握多元人群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和并接性,深入理解西南社会的整体与多元;不仅把区域当成一种研究者的工具框架,也能通过对区域本身的理解而解绑以往概念之种种局限,即从“在区域中做研究”到“研究区域”。
前文以都柳江流域这一因水道而产生人群交往互动、互嵌的地带为例,跟随人的活动在区域多层次的缩与展中把握西南多族群地带的多元与整体,希望借此强调区域不仅是一种基于基层社会组织关系的表达,一种不同人群生活世界的多层次联结,同时也是一种经不同观念相互杂糅、再创造的文化界定。首先,都柳江流域以村寨联盟为特点的“dangx”组织,是地方族群间联合、形成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基础。同时,这种基层组织方式又具有一定包容性和弹性,历史上,流动的人群也会基于此基层组织机制在地方生存、活动,形成一套地方特有的交往规范和社会秩序。其次,围绕市场、婚姻,不同人群在不同的环节中参与、互动,在差异中相互交织,成为多层次区域社会体系。最后借由文化象征体系,多元人群将汇聚于此的庙宇、信仰符号通过极富能动性的创造杂糅与再诠释,在诸多符号中既保留了多元的意义,又通过区域性节日将诸意义囊括其中,用一种文化整合方式界定多意之区域。在上述都柳江流域人群互嵌、多元文化交织共生的历史交互过程可以看到,区域一方面具有其自然属性,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生计模式和人群交往方式,会直接影响区域的构成。在都柳江流域,山地河流自然生态环境中人们因适应、合作而产生的特殊结群方式奠定了“区域”的基础,并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观念,在这一生态意义上,“区域”不能完全被视作为外来力量改造的结果,而是多种结构得以建立、变化的基础。“区域”所蕴含的本土逻辑即是本文所强调的。另一方面,“区域”并非静态,水道的流动属性及其人的活动亦会影响区域的伸缩,而在此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作用会深刻影响“区域”及其社会生活状态。但最终,区域的结构、变化将以文化的方式,被极具能动性的地方人群创造、诠释和实践,作为一种虽多义但具有整体意涵的观念被表达,成为当下可被触摸和可被理解的区域意象。综上所述,借由柳江流域所进行的区域讨论,并非停留在诸如市场关系、身份认同等既往讨论之上,而是试图在时间、空间和人的实践中关注地方人群内部差异与并接,进而作为一种尝试提供一个对“交错互动、你来我往”的西南社会理解的视角。
另外,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领域,区域研究围绕“国家”与“地方”关系研究框架下形成了诸多探讨。在由史学延伸出的全国性研究、整体史视野下,区域研究往往更强调跨越与整合。然而,学者也逐渐开始反思这一研究框架中“个别”与“整体”、“宏观”与“微观”之对立困境。本文从人类学领域出发,意图强调,如果我们把“区域”视作一个有意识的历史结构,则必须关注“区域”的本土逻辑,关注生态自然差异、地方人群基本分类范畴、交往规范以及内在的多样性文化表达。这一意图并非是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重造藩篱,而是希望在上与下、局部和整体间建立更多可被认识的方向和可能。在此意义上,“区域”可被理解为一种带有时间意涵以及社会文化意涵的空间单元,对区域的历史过程研究,可视作一种对历史空间和历史观念的研究,而从区域中做研究到研究区域,实则强调的是一种在地方性脉络之上的整体把握,将人类学整体观放入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本土实践中,通过对镶嵌于整体之中差异性的具体呈现,从多民族社会、多元文化体系、多生态类型和社会类型出发开展讨论,既可帮助我们充分认识被历史书写所遮蔽的“个别”与“地方”之复杂性,亦能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制度在地方社会的运作互动机制,从而以具体的历史知识、本土概念出发,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无文字传统、缺乏文献资料的西南社会而言,区域历史在何种地方社会基础之上延伸?以及在观念层面如何形成整体之区域,这些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群、他者、乃至国家的丰富历史图景。
都柳江这一山地流域地带,区域并非是一个能够被清晰界定的空间范畴,在这样一个人、物流动、交错互嵌的地带,各人群基于不同的生态自然、社会结构、生活往来与历史经验,构织出多层次的区域体系,形成对生活世界之区域的不同理解。而借助此种极具兼容性和弹性的区域观念,我们才能深入认识多样人群交织关联、多元文化差异并接之可能。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与“人”有关的区域,人作为一个“整体”生活的行动者,多重意义不断在社会互动中交错、浮现及隐退,笔者不能完全认定,区域就是人们的一种情境式选择。但是,人会在不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碰撞间,对自我有不同的认识与界定,亦会选择不同属性的界线。也就在这些力量的层叠交错间,区域一再被结构再解构,解构再结构,“区域”也从未“完成”,而总是处于流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