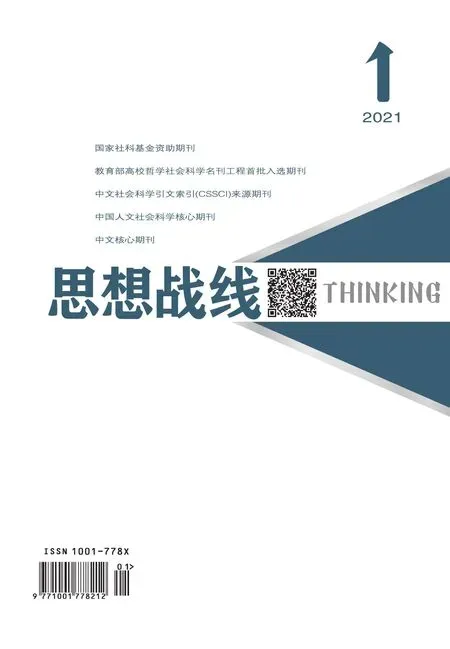“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三重实践逻辑构造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杨临宏,陈 颖
2019年12月28日,我国健康领域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颁布。该法第六条规定“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既是新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的工作方针,又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策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究竟如何实现“融入”却关乎到制度的生命力,因为“过于简化或理想化的制度,几乎也是一种‘无制度’的制度”。(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第42页。“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不能仅仅停留在立法和政策文本的原则性规定上,成为宣示性的愿景,而应当真正体现出被付诸于行动的治理效能。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探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内涵阐释、实践逻辑以及设计符合国情的“制度细节”,是建设我国健康治理长效机制的学术命题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及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健康发展迎来“机会之窗”,作为一项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机制,“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成为我国健康领域社会风险治理的“治本之策”。
一、“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发展脉络和内涵阐释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是一项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倡导的健康促进与发展战略,其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跨部门协作”。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提出,公共卫生应从过去局限于卫生系统内部运作转向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多个部门协作行动。(2)WHO,Declaration of Alma-A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1978,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declaration-of-alma-ata,2018年9月7日。第二阶段,“健康的公共政策”。1986年《渥太华宪章》将健康问题上升到公共政策的高度,认为“政府各部门领导在决策前应当有意识地思考政策的实施对健康后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健康责任”,(3)WHO,Ottawa Charterfor Health Promotion,1986,https://www.who.int/healthpromotion/conferences/previous/ottawa/en/,2018年9月7日。从而为改善健康水平和健康公平性创造全方位的公共政策支持性环境。第三阶段,“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10年《阿德莱德声明》首次使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表述。(4)Ilona Kickbusch,Kevin Buckett,Implementing Health in All Policies:Adelaide,2010,pp.4.https://www.who. int/sdhconference/resources/implementinghiapadel-sahealth-100622.pdf,2018年9月7日。2013年《赫尔辛基宣言》正式把“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定义为“一种以改善人群健康和健康公平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制定方法,它系统地考虑这些公共政策可能带来的健康后果,寻求部门间协作,避免政策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促进公众健康和提高健康公平”。(5)WHO,The Helsinki statement on health in all policies,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vol.29,no.S1,pp.i17.针对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存在的协作不力、机制匮乏和行动迟缓等症结,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三阶段配套发布《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国家行动框架》(以下简称《行动框架》)用于强化健康部门与其他部门在协作组织结构、协作机制以及共同行动上的管理。(6)WHO,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framework for country action,2014,pp.6~12,https://www.who.int/cardiovascular_diseases/140120HPRHiAPFramework.pdf?ua=1,2018年9月15日。
上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政治议程上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学术界关于影响健康的因素研究。传统上个体健康的维护也主要依赖个人保健和医学治疗,然而随着人们对“是什么造就了个体健康”的追问不断深入,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SDoH)理论逐渐浮出,(7)理论研究主要有:1974年《加拿大人对健康的新视角报告》,参阅H.L.Laframboise,“Health policy:breaking the problem down into more manageable segments”,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1973,vol.3,no.108,p.388.健康的“社会梯度(social gradient)”理论,参阅Michael Marmot,“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Lancet ,2005,vol.365,pp.1099.健康决定因素的“彩虹模型”,参阅Dahlgren G,Whitehead M,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promote equity in health,1991,p.11.https://core.ac.uk/download/pdf/6472456.pdf,2018年10月10日。试图回答为什么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费用的增长并不能有效改善个体的健康状况。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涵盖生活方式、生活环境、职业行为、社会网络在内的诸多‘非医疗因素’在不同程度地影响健康习惯的形成和健康保障的获得。”(8)WHO,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 Health equity through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2008,pp.3~12.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9832/WHO-IER-CSDH_08.1_eng.pdf?sequence=1,2018年10月12日。虽然这一理论的研究出发点是对影响个体健康因素的探讨,但是“个人对这些社会性因素能够选择的空间和潜力非常微渺,所有促进健康条件的因素都取决于集体决策,取决于社会集体分配(或再分配)资源的方式”,(9)Evely de Leeuw,“Health in All Policies-Why and How”,收录在王陇德:《健康中国,策略为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49页。因此在该理论的指引下,个体健康问题的解决思路不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诉之于调整公共政策,表现出个体健康在实现机制上的“公共性”。它与经济学视角下个体健康的“外部性”(10)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指个人或人群的行为会使他人受损或者受益。在健康领域,个体身染传染性疾病会对社群健康产生直接危害;罹患非传染性的慢性病会对社会财富和国民素质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两者常常成为公共卫生直接干预的对象,个人有时需要放弃与公共健康相冲突的个人行为方式自由来换取更健康、更安全的社群所能带来的保护与生活满足感。一起,揭示出健康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从而将个体健康问题推向更广阔的解决空间,实现个体健康与公共健康在增进人类福祉的总体利益上的内在统一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第一个内涵元素“健康”意指“公共健康”,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的集体行动,满足人们对社会环境条件的诉求,实现人人能够拥有获得健康的条件”。(11)参阅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在《公共健康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公共健康经典定义。Institute of Medicine,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8,p.19.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第二个内涵元素是“政策”,即公共政策,是政府为实现公共健康目标采取的政治行动或行为准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战略规划、法令、措施、办法等。这些政策以一定的健康价值观为基础,调整涉及健康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并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公共行政领域对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做出的有力回应,具体而言,表现为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两大学科在实现人口健康问题上的研究范式转变。
一是公共健康的实现策略从“公共卫生干预”向“公共健康政策促进”的范式转变。传统公共卫生的思想和方法“形成于欧洲和北美工业化时期,关注的是通过传染病防治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环境卫生问题,其主题是卫生运动”;(12)Richman J,“Holding Public Health Up for Inspection”in John Costello and Monica Haggart eds.Public Health and Society,Gordonsville:Palgrave Macmillan,2003,p.4.而现代公共健康则从自然环境转向社会环境,关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健康不公平背后的政策原因,此时公共健康走出自然科学的领地进入一个高度“社会化”和“政治化”的领域。在这个与政府和公众行为紧密联系的公共领域中,“人口健康更多地是由良好的公共健康措施与社会经济条件所致,而非生物医学技术发展的结果”。(13)Daniel Callahan and Bruce Jennings,“Ethics and Public Health:Forging a Strong Relationship”,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2,vol.2,no.92,p.169.
二是健康权益保障从“个人权利的消极保护”向“人群健康的积极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变。传统的个人健康权益保护基于他人负有无正当理由不得侵害个体健康的义务,当不法侵害发生时,个人有权请求来自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公力救济,但是这种保护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事后救济往往造成健康受损后果的不可逆转;个案式救济难以消除妨害健康的危险因素,从而导致损害重复发生;遭遇立法空白或者政策失当时,个体可能面临救济无门的窘境。(14)例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15年校园毒跑道事件以及2018年长生疫苗事件,据相关的新闻报道,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存在,但是个人和某些群体的维权行为无法杜绝侵害行为的再次发生。随着《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校园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颁布,史上最严的《疫苗管理法》出台。我国健康权益保障水平提升呈现出“社会”关注事件引发立法和政策转变的路径依赖,然而在大健康理念下贯彻预防为主原则应当尽量避免这种保障方式带来的被动性和过高的社会成本。这种“将健康侵权中不可知的风险归由当事人承担的做法,使得健康权保障期待落空”。(15)陈云良:《健康权的规范构造》,《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建立在侵权责任基础上的消极保护模式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逐渐走向以国家责任为基础的“积极公共政策”保护模式。政府主动排除影响健康权实现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并致力于改善维系公共健康的基础性社会条件。“积极的公共政策”不仅被视为健康权保障的“新议题和新框架”,(16)唐贤兴,马 婷:《积极的公共政策与健康权保障》,《复旦政治学评论》2018年第1期。还被认为是公共健康领域“最好的社会投资”。(17)Evely de Leeuw,“Health in All Policies-Why and How’.收录在王陇德:《健康中国,策略为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50页。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第三个内涵元素是“融入”,它被视为健康领域的“横向决策和执行机制(horizontal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18)Ilona Kickbusch,Kevin Buckett,“Implementing Health in All Policies:Adelaide”,2010,p.12.https://www. who.int/sdhconference/resources/implementinghiapadel-sahealth-100622.pdf,2018年9月7日。或者“整合型治理(integrated governance)”。(19)Shankardass et al,“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in All Policies initiatives:a systems framework for government action”,Health Research Policy and Systems,2018,no.57,pp.16~26.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打破了健康问题囿于卫生部门解决的部门壁垒,促使除参与卫生政策的决策者之外,其他部门的决策者也应当关注健康状况,从而“推动公共卫生知识转化为政治行动”。(20)Michael Marmot,“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Lancet,2005,no.365,p.1099.“融入”是政府各部门间基于共同价值目标形成一体化行动响应机制并分担健康发展责任的动态过程。
二、“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三重实践逻辑构造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付诸于行动远比设定这个目标困难得多,理论上关于该目标有效实施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影响实施效果的情境和关联要素的研究也非常少”,(21)Shankardass et al,“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in All Policies initiatives: a systems framework for government action”,Health Research Policy and Systems,2018,p.16.因而围绕这些因素构造“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逻辑可以弥补理论不足导致的实践匮乏。本文基于健康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出发点,在梳理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报告和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存在“政治—科学—行政”三个维度下的以“健康优先、健康评价和健康协同”为基本内涵的三重实践逻辑,在每个逻辑中又有各自运行的微观机制性要素。三逻辑间关系详见图1。

图1:“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三重实践逻辑
在三重实践逻辑中,健康优先是前提条件,“我们应该赋予人群健康以政治上的优先性,为此勾勒出清晰的目标并阐释其基本原理”。(22)[美]劳伦斯·戈斯汀:《公共卫生法的理论与定义》,收录在[美]马克思韦尔·梅尔曼等:《以往与来者——美国卫生法学五十年》,唐 超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健康评价是保障机制,“卫生保健政策领域率先付诸实践循证决策,这是因为以循证决策的方式进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人们就能够借助证据来证明哪些问题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举措需要实施”。(23)胡业飞:《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循证决策——一个文献综述》,《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8期。除了保障公共健康问题被及时关注外,健康评价还能保障健康治理中“公域”不对“私域”越界,比如论证诸如为什么某个健康事项需要进入公共政策的领域,实现对个体或者群体自由的干预?这些强制性干预是否果真降低了总体的健康风险?健康协同是执行过程,“协同机制有助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独立的组织资源,协助建立协调性框架,促进治理主体以互利的方式调适行为、开展合作”。(24)郁建兴,张利萍:《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协同机制及其整合》,《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提出的初衷,是改变传统官僚体制的碎片化政策手段,实现多部门合作共同应对健康不利影响因素,因此,协同的过程就是融入的体现,协同是制度实践中最具生命力的环节。
(一)政治逻辑:健康优先
健康在社会发展目标中具有优先地位是由人类的健康风险观、经济发展观和健康人权观决定的。首先,人类身处风险社会之中,尤其“健康威胁的普遍化产生了无所不在的和永久的对生存的威胁,它们现在正以相应的严酷性贯穿经济和政治体系。”(25)[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都会在不同的时空中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次,健康与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性。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减少疾病负担在客观上有助于财富的积累。“良好的健康促进经济增长,反之恶化的健康状况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26)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1.转引自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重要文献及国际案例汇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14页。不断改善健康状况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在《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中表述为“享受可获得的最高标准的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它不仅包括个人获得医疗护理的权益,还涵盖在疾病预防、卫生防护和健康促进方面的权益”。(27)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constitution-of-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8年9月20日。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健康权是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团结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载体,国家通过履行保障公民健康权的积极义务来体现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因此,健康权已经成为“国家政治讨论和社会政策制定的中心议题”。(28)John Tobin,The Right to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3.
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经验分享中,健康优先的实现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政府内生主动型。政府通过制定健康发展战略确定健康领域短期、中期、长期的优先发展事项、行动和目标,然后围绕这些目标解决在结构、机制和能力建设上的需求,其意义在于做出政府履行保障健康的政治承诺。例如,厄瓜多尔推行的《国家美好生活计划》成为该国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路线图,政府各部门工作都要围绕国家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开展。(29)WHO,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framework for country action,2014,p.4.https://www.who.int/cardiovascular_diseases/140120HPRHiAPFramework.pdf?ua=1,2018年9月15日。
二是健康危机倒逼型。每当风险和危机产生时,健康被纳入各项公共政策的考虑之中,以便形成部门间对健康危机的共同应对,许多悬而未决、久拖不久的健康问题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政策上的突破与改变。例如,欧盟在恐怖袭击、SARS等事件后加强健康安全委员会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的建设,将公共健康上升为健康安全战略。(30)Brussels,European Commission,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on Generic Preparedness Planning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t EU Level.COM(2005)605 final.2005.
三是民主监督促进型。“单纯意识到公共健康的重要性并不够,一个国家需要不断进行关于公共健康的民主辩论与实践才能真正促进公共健康的发展”。(31)Dan E.Beauchamp,The Health of the Republic:Epidemics,Medicine and Moralism as Challenges to Democrac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8,p.4.由于健康问题常常受到科学认知局限、产业利益干扰、社会旧习陋俗的影响而变得真相模糊和极具争议,推进健康政策容易发生“执行变形”,因此,建立涵盖信息发布、议题公开讨论、健康大数据报告等机制,实现对健康优先承诺的监督势在必行。例如,芬兰采用《国家健康报告》制度确保健康政策的透明度,该报告由各部门提供信息说明该部门的行动对政府健康项目的贡献程度,供公众评价。(32)Ståhl T,Wismar MOLLILA E,et al,Health in All Policies:Prospects and Potentials.Helsinki:Finish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2006m,p.174.https://ec.europa.eu/health/archive/ph_information/documents/health_in_all_policies.pdf,2019年1月15日。德国以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为代表的多个地区采用区域健康会议和公共健康报告相结合的方式,为公众尤其是地方健康利益相关者参与解决区域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平台。(33)David V.Mc Queen,Intersectoral Governance for Health in All Policies,2012,p.10.https://www.euro.who.int/_data/assets/pdf_file/0005/171707/Intersectoral-governance-for-health-in-all-policies.pdf,2019年1月20日。
(二)科学逻辑:健康评价
基于卫生循证决策传统发展而来的健康影响评价(Health Impact Assessment,HIA)是“对不同部门政策、规划和项目在人群健康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的一系列程序、方法和工具”。(34)ANN Fosyth,Carissa Schively Sloterback,“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for Planners:What Tools Are Useful?”,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no.24,2010,pp.231~245.泰国《国家健康法》、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加拿大《公共卫生法》等都以立法形式确立了该项制度,并赋权国家健康委员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公共卫生机构等机构执行。(35)梁小云等:《国际健康影响评价的制度建设:从政策到法律》,《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9年第9期。
开展健康影响评价的方法较为多元,有“法律和政策环境分析、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分析、利益相关人和关键知情人(受影响地区的代表、项目支持者、学科专家和卫生专业人士等)分析、确定和测量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成本收益分析等”。(36)Grant S,Wilkinson J R,Learmonth A,Occasional paper No.1:an overview of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Northern & Yorkshire Public Health Observatory,2001,pp.1~14.https://core.ac.uk/download/pdf/65512.pdf,2019年1月25日。健康影响评价主要适用于立法、公共政策制定、公共项目规划、公共活动等领域。例如,泰国国家健康委员会对《国家知识产权计划》草案中的健康敏感性问题进行健康影响评估。(37)WHO,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framework for country action,2014,p.11,https://www.who.int/cardiovascular_diseases/140120HPRHiAPFramework.pdf?ua=1,2018年9月15日。南澳大利亚采用“健康棱镜分析”机制,为公共政策的健康产出提供依据和建议。(38)Ilona Kickbusch,Kevin Buckett,“Implementing Health in All Policies:Adelaide”,2010,p.12.https://www. who.int/sdhconference/resources/implementinghiapadel-sahealth-100622.pdf,2018年9月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专责小组评估执行“健康社区计划”对提升健康、社会平等和经济福利等方面带来的益处。(39)Linda Rudolph el,HEALTH IN ALL POLICIES:A Guide fo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Public Health Institute and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2013,p.119.http://www.itup.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Pittman-Health-in-All-Policies.pdf,2019年1月20日。
虽然健康影响评价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控制机制越来越得到法律和政府部门的认可,但是这一工具性要素的实施却离不开“人”的因素,实施的成效取决于官僚、专家和公众的作用机制发挥。
首先,官僚发挥知识与决策的桥梁作用。“危险在增长,但它们在政治上没有被改造为预防性的风险管理政策”,(4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5页。究其原因与官僚的专业背景和决策思维有关。传统行政型官僚善于上行下效地执行政策,缺乏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证据决策的自主性,然而“在组织高层的工作中,前提控制是最重要的,因为那里的管理工作很少是例行的”,(41)[美]戴维·H.罗森布洛姆等著:《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张成福等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技术型官僚则具有运用专业知识和循证决策的意识和主动性,面对新问题、新情况时更能弥合专业认识与公共决策之间的断裂。
其次,专家科学社群发挥循证决策的支撑作用。健康治理本质上是科学精神和知识的治理,仰赖科学研究获得的成果,然而由于存在科学证据受到政治性因素干预而无法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操作空间,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主张科学领域的“协商民主”,即“建立专家和政治家之间取长补短的密切合作关系,统治要从整体上接受以科学为指导的批评与建议”。(4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 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第三,公众和社区发挥健康合作产出的促进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行动框架》中提出:“确定政策影响到的目标群体和社区,让他们为政策潜在的健康收益或者弊端以及替代方案建言献策。支持社区成员参与‘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过程来构建社区能力,包括健康政策知识、参与决策、项目执行和评估的能力。”(43)WHO,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framework for country action,2014,p.12,https://www.who.int/cardiovascular_diseases/140120HPRHiAPFramework.pdf?ua=1,2018年9月15日。
(三)行政逻辑:健康协同
“推进‘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卫生当局是否有能力积极寻求与其他部门合作和施加影响”,(44)WHO,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framework for country action,2014,p.18,https://www.who.int/cardiovascular_diseases/140120HPRHiAPFramework.pdf?ua=1,2018年9月15日。所以实施起来会遇到诸多困难。芬兰的一项调查显示,阻碍健康领域跨部门合作的因素有:“增加部门工作负担、健康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目标矛盾、其他部门没有将健康列入优先考虑事项、健康部门才应该对健康负责的认识、对是否有健康效果缺乏证据支持等。”(45)Ståhl T,Lahtinen E,Wismar M,Report of the policy dialogues.The Finnish EU Presidency project on“Europe for Health and Wealth 2006.”,2006,p.5.https://ec.europa.eu/health/ph_projects/2005/action1/docs/2005_1_18_frep_a2_en.pdf,2019年1月25日。此外,健康部门的影响力还受制于官僚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欧盟推行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各国健康部及其部长一般都不是政府内部最强势的部门和领导。政府在政策制定时,不是考虑经济、工业和贸易政策如何促进公民的健康和福祉,而是反过来审查健康政策是否对它们做出贡献。”(46)Ståhl T,Wismar M,OLLILA E,et al.,Health in All policies:Prospects and Potentials.Helsinki:Finish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2006,p.10.https://ec.europa.eu/health/archive/ph_information/documents/health_in_all_policies.pdf,2019年1月15日。
面对健康问题多部门协同的困境和挑战,世界卫生组织《行动框架》中提出“建立支持协同的结构和程序”,其核心是形成健康问题的扁平化管理结构和中枢型连接组织。扁平化管理结构将健康治理目标和责任分配到不同政府部门,打破部门间以“条块”为基础的线性管理所产生的权责壁垒,促使各部门重视健康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形成“健康意识”的行政文化,成为健康协同的共同价值基础。如芬兰制定《各部门在促进人民健康与福利的政策、活动上的优先事项(2002年至2005年)》,涉及农业、环境、教育、工业贸易、劳动、交通等11部门的健康发展事项。(47)Ståhl T,Wismar M,OLLILA E,et al.,Health in All policies:Prospects and Potentials.Helsinki:Finish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2006,pp.178~179.https://ec.europa.eu/health/archive/ph_information/documents/health_in_all_policies.pdf,2019年1月15日。
中枢型连接组织是推进各部门政策与行动协同的领导力。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实践发现中枢型连接组织具有多样性,“在健康促进行动中,由健康部门发起,多部委或者机构参与;在健康危机事件中,由政府首脑发起,所有部委共同参与;在解决公共健康的重点问题中,由新机构或者已有政府部门赋权增能来监督和促进相关部门在该问题上的协同作为;在健康城市治理中,由社区开展促进公众健康行动。”(48)WHO,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framework for country action,2014,pp.6~11,https://www.who.int/cardiovascular_diseases/140120HPRHiAPFramework.pdf?ua=1,2018年9月15日。其中,在建立部门间甚至是议会级别的健康委员会新机构中较为成功的典范是芬兰公共健康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Board for Public Health),由国务委员会设立,职责是监测公共健康的发展和健康政策跨部门执行情况,有权制定促进多部门合作的国家健康政策。(49)Ståhl T,Wismar M,OLLILA E,et al.,Health in All policies:Prospects and Potentials.Helsinki:Finish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2006,p.177.https://ec.europa.eu/health/archive/ph_information/documents/health_in_all_policies.pdf,2019年1月15日。
作为重要的中枢型连接组织,健康部门在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表现为:健康治理常态下,建立健康科学知识和证据的储备、实施健康服务质量和国民健康素质监测,推动和支持部门间商议健康事项等。有的国家通过立法保障健康部门的协同领导力,如2002年加拿大《魁北克公共健康法案》规定:“健康和社会服务的部长是政府在公共健康问题上的顾问,在法案法规制定中涉及到可能对人口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措施时都必须与之协商。”(50)Linda Rudolph el.,HEALTH IN ALL POLICIES:A Guide fo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Public Health Institute and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2013,p.68.http://www.itup.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Pittman-Health-in-All-Policies.pdf,2019年1月20日。在健康危机应对的非常态下,健康部门在健康风险识别、健康风险转化为公共危机的可能性论证、健康风险预警等方面的领导力不容小觑,直接关系到健康风险能否快速上升为国家政治议题并启动多部门协同应对机制。
三、三重逻辑下中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模式,每个‘融入’的实践都具有独特设计和管理,很难照搬套用。”(51)Shankardass et al,“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in All Policies initiatives:a systems framework for government action”,Health Research Policy and Systems,2018,p.17.我国自2013年芬兰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后引入了这一概念,在健康城市(村镇)建设、慢性病防控领域进行了先期探索;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被正式提出;2017年我国开启促进地区及全球卫生安全的健康外交;(52)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备忘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11.htm,2020年1月19日。2019年被写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短时期内从舶来词成为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基本方针。考察我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如何将具有普适性的健康优先、健康评价和健康协同三重实践逻辑与国家制度体系和优势相结合,是诠释健康中国推进速度与力度的一个侧影。在近年来我国健康治理大事件中,中国战疫、健康促进县(区)、医养大部制改革三个案例较为典型地体现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三重实践逻辑,而且每个案例都具有实践的侧重点。限于篇幅,本文将对这些侧重点进行讨论,为探索“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国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实践之路奠定基础。
(一)健康优先确保“疫情防控”融入所有政策
2020年初,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的重要批示,显示出党中央在重大公共健康危机应对上秉承和贯彻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健康优先的治疫总方针指引下,各级政府才能够在经济运行和疫情防控之间果断做出选择,“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改变了疫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进程”。(53)《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站:http://www.nhc.gov.cn/xcs/fkdt/202002/87fd92510d094e4b9bad597608f5cc2c.shtml,2020年2月29日。全国治疫过程中“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切实推进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54)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求是》2020年第5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规定,开创了在重大健康问题上突破部门立法的局限性,进行立法目标“健康化”的价值引领,从而推动动物源性传染病的源头治理。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各部委以单独或联合形式发布涉及疫情防控的全方位支持性政策,形成“疫情防控”的政策协同网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规范公众防疫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以上我国“将疫情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不仅显示出健康优先在国家主义的制度优势下所具有的强大执行力和保障力,而且还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间通过职能响应、联合决策和共同执行等方式迅速形成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体系。
(二)健康促进县(区)开启健康评价实践
“‘健康中国2030’能否真正落地最大的挑战在于:地方政府能否将健康真正地融入所有政策中”。(55)徐书贤:《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中国医院院长》2016年第22期。县(区)处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社会稳定的承上启下关键位置,是施政决策的发力点和着力点。2016年我国选取县(区)作为试点区域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出台首个“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国家级文件,(56)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县(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工作指导方案》(国卫宣传健便函〔2016〕22号)。将公共政策健康审查制度作为我国健康影响评价制度的先期探索。首先,健康促进县(区)的政府成立健康(促进)委员会和健康专家委员会。第二,县(区)政府各部门梳理本部门的公共政策是否有利于人群健康。第三,在所有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增加健康审查程序。第四,明确政府各部门开发新政策时优先考虑的健康事项,例如发展改革部门是健康基础设施规划和投资,民政部门是发展健康社会服务组织,农业部门是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业等。
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公共政策健康审查的基础上,在部分健康促进县(区)开展健康影响评价试点。健康影响评价范围包括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重大工程和项目。健康促进委员会为领导协调机构,健康影响评价专家委员会较之公共政策健康审查更为正式,对来自卫生管理、公共卫生、临床、康复领域的卫生专家和外地专家明确比例要求,确保评估更加专业和客观。公共政策健康审查制度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健康促进县(区)试点中取得明显成效,(57)第一批两年中梳理出2 683条与健康有关的公共政策,其中1 013条在试点期间进行补充和修订。第二批两年中梳理出3 293条与健康有关的公共政策。新政策制定中共开展716次公共政策健康审查,平均每个县(区)11.2次。数据来源: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影响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年,第31页。而健康影响评价在第三批试点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有部分县(区)未能开展健康影响评价”。(58)石 琦,姜玉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健康促进县(区)建设中的应用》,《中国健康教育》2019年第6期。
(三)医养大部制改革发挥健康部门领导力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和医疗基本上是平行的两条道路,直到生命的末期才交汇在医疗机构的“长期押床”中。“医养分离”已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疾病负担加重和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社会变迁,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也认为,“照护体系薄弱,加剧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不平等”。(59)《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中文版)》,2016年,第5页,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94271/9789245509318chi.pdf,2018年9月10日。在意识到养老支持如果不能成为制度化的公共服务体系,那么在未来就会演变成为影响医疗、社保、就业、治安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后,我国政府将促进健康老龄化放在重点人群健康服务的优先发展地位。
然而,我国医养结合的短板在“医”而不在“养”,所以起步阶段多个国家政策是由卫生部门牵头,但是由于老龄工作和养老资源配置职能属于民政部门,而且两个部门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卫生部门强调健康服务体系,民政部门则关注救助与保障,因此卫生部门发挥主导权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央设定的公共政策决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高于‘部’的责任范畴。当这种决策的任务与以‘部’为基础的责任结构不吻合时,中国时常面临严重的部际‘协调难’问题。部门合并使不同专业系统的决策者可以在‘内部’解决问题”。(60)王绍光,樊 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7页。2018年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设“老龄健康司”,承担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职能。这是一次健康部门在老年健康服务职能上的“扩权赋能”,形成健康老龄化的“治理中枢”,一方面原来需要跨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在调动健康部门内部资源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如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进行适老化改造,方便老年人就医;另一方面,在不能“内化”解决的问题上发挥协同领导力,寻求与其他部门达成“共识型决策”,如老龄健康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国开金融等单位进行研商,拟出台开发性金融支持医养结合发展,培育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及龙头企业的政策文件。(61)《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召开“开发性金融支持医养结合发展”协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nhc.gov.cn/lljks/s7786/201902/d446771e177c4f7fb71728607cca54c5.shtml,2019年2月22日。
四、三重逻辑下中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发展策略
无论是上述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建设短板,或是尚在试点阶段的健康影响评价制度推进缓慢,还是健康发展职能部门整合化目前只限于医养大部制和国家医疗保障局改革的现实,无不印证“我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卫生’‘大健康’工作格局尚未形成”(62)《发扬优良传统 建设健康中国 谱写爱国卫生运动新篇章——刘延东副总理在爱国卫生运动65周年暨全国爱国卫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nhc.gov.cn/jkj/s5899/201705/07e06589b14440fa81b63c55be681c88.shtml,2017年5月12日。的论断。因此,处于后疫情时代公共健康治道变革的契机中,如何在三重实践逻辑的指引下,制定我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发展策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实践机制,构建一条“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国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发展之路,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向世界交出的健康治理中国之治答卷的一部分。
(一)健康优先:从发展意识提升到危机意识
2009年我国施行新医改方案,重点放在依托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促进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近十年的改革在基本医疗服务水平、重点人群慢性病防治、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健康中国战略”是在新医改实施的基础上对国家宏观健康政策框架与系统战略的整体性布局,标志着健康政策在国家公共政策议程和权力结构中从边缘地带走向核心位置。以上事实表明,我国政府内生主动型的“健康优先”社会发展战略已经形成。然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倒逼型”健康优先发展态势,促使人们反思钟南山院士所说的“为什么SARS之后,很多研究就不搞了?”以及地方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地位被边缘化、职能被弱化的趋势。(63)徐毓才:《省级以下疾控、卫监被撤销!辽宁机构改革“有点乱”》,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0242253_452205,2018年7月10日。疫情的突发和扩散昭示“健康不仅是社会发展问题,更是公共安全问题”。正如芬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研究首席专家Timo Ståhl所言:“因为医疗卫生部门无法独自管理所有的健康威胁,需要在人群发生健康风险之前尽早采取行动,所以我们需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64)Timo Ståhl:《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构建“健康城市”健康促进能力的途径——2018年健康城市国际研讨会暨健康嘉定论坛演讲实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9年第1期。
健康风险和危机意识下的健康优先更加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导向:一是财政投入的健康优先。为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局面,中央政府强化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并且在疫情后时代各级财政将优先支持过去一直处于医改短板的医疗物资储备、传染病院区扩建、应急性医院建设等。二是公共资源规划配置的健康优先。为实现医疗卫生服务与公共健康危机应对的无缝衔接,促进公共健康服务水平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和协调,城市人口增长和人员流动将与医疗资源规划配置相适应,避免发生医疗挤兑;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将实现医疗资源在数量、功能、分布上的均衡;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将在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中提升托底能力等。三是问责事项的健康优先。中国战疫成功的背后,对疫情防控失职失责官员的严厉问责发挥了震慑警示作用。长期以来,健康发展职责属于政绩考核的“软指标”,对官员的约束力较弱,造就了再多的健康战略、健康规划也被束之高阁。因此,国家安全战略下的公共健康治理将依赖于健康优先发展职责的制度化和完善的追责机制。
(二)健康评价:从任意性选择转变为制度化践行
目前我国健康影响评价制度还只是政府行政决策前的“选择性动作”,“各部门对‘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解差异较大,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很少,严重影响预防为主方针的落实”(65)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会建设的思考与建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第4期。,导致大量公共政策、工程建设项目和产业发展规划中的健康风险没有被准确评估,要么实施前引发群体性事件,要么实施后严重损害公众健康。作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循证来源和推动“证据”转化为“政策”的重要环节,健康影响评价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嵌入我国现行的行政决策评估程序中。首先,我国的健康立法以部门立法、管理型立法为主要特征,部门之间存在较大争议的事项往往久拖不决。例如全国性的控烟法规、健康建筑法规、生活垃圾处理管理法规等立法动议或者法规草案早已形成,但是迟迟未能出台。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第三方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可以增进科学证据在弥合行政立法分歧中的作用。其次,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风险评估”中增加健康影响评价的内容。在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22条,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中增加“公共健康”,赋予决策者组织评估决策草案中的“公共健康风险”可控性的法定义务。完善该“制度细节”,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规定的承接落实。第三,保障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在健康影响评价中“能参与”和“敢表达”。“在公共卫生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中,要明确建立规范的综合性风险研判机制,确保不同领域的专家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意见”,(66)薛 澜:《加强重大疫情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光明日报》2020年3月25日。而且还应当对专家、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及不良健康影响事件的“吹哨人”采取开放性、容错性的免责保护。
(三)健康协同:从分而治之重塑为整合中枢型大协同
如前所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改变健康问题在各部门间分而治之,无法形成改善健康行动合力的困局,因此实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协同组织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既有核心枢纽组织又有机构与职能整合的框架体系。协同组织中各要素关系可详见笔者绘制图2。

图2:我国实践“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协同组织框架图
从国家权力配置的宏观角度,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需要构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机构“链接式”的健康大协同格局。立法机构是健康大协同的顶层设计者,应当改变过去健康问题立法局限于卫生行政部门“单一问题单一立法”的碎片化形式,收紧健康问题的基本立法权,制定关涉健康问题的各项基础性立法,对健康发展的方向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统筹规划,实现立法价值“健康化”取向的高位引领。立法机关还是健康大协同的监督者,通过审议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公共健康报告》,监督政府履行健康发展职责的情况。司法机关是健康大协同的法治守护者,在健康侵权诉讼、健康公益诉讼、健康保障行政给付诉讼等司法救济中实现保障健康权的“个案正义”,还可以采用司法建议的方式推动行政机关矫正妨碍健康公平性实现的行政行为。
从政府部门的中观角度,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需要构建组织整合、职能统一的健康管理中枢型行政部门,发挥健康协同的领导力。在政府层面,组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倡导、协调、评议机构——健康委员会。以国务院为例,在整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等议事协调组织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健康委员会”部际协调平台,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高层领导出任,不仅协调部委的政策和行动,还重在对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中国行动任务分工的责任落实。国家健康委员会定期发布《国家公共健康报告》,由国家健康委员会各成员单位(部委)提交在改善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方面的部门工作或者部门间联合行动情况,旨在“整合各子体系的健康职责,把卫生体系改革由个别政府部门的业务工作转变为全社会共治的事情”。(67)李 玲,江 宇:《一切为人民、一切为健康》,《求是》2017年第7期。
在卫生健康委员会内部层面,重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组织体系与行政职能,成为“平战结合、医防协调”的中枢型行政机构,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提供循证决策信息来源和实施效果监测评估。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例,整合其内设的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的主要职责有公共健康发展规划权、国民健康状况监测与评价权、健康影响评价与风险调查权、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项目实施监督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与处置权等。同时,在该局下设国家公共健康研究院(直属事业单位)承接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科学研究、技术支撑和咨询建议的职责。
从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微观角度,各级医疗机构实现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融合是在社会体系末梢端传递“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机构绝大部分仅仅还是做疾病诊疗,很少参与危险因素的筛查和控制”,(68)王陇德:《健康中国,策略为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7页。缺乏承载以“健康”为中心,提供系统、连续、防治深度结合的健康服务提供主体。因此,依托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基础和福利性保障,在各级医疗机构建立健康教育的窗口和健康促进的阵地,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科室”;社区全科医师、公卫医师相结合的基层医疗服务团队。“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归根到底还是要依托社会基层力量通过群防群控、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实现公共健康的社会效益产出。
结 语
人民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人民最大的财富。作为一项通过跨部门卫生行动和公共政策调适与互补来促进健康公平、实现社会正义的发展策略,“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不能仅仅停留在写入立法和政策的语言和修辞层面,而应当重视实践逻辑与实现机制的探讨。中国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践刚刚起步,恰逢健康优先发展“内生主动”和“危机倒逼”的双期叠加,因此未来发展策略将呈现“社会发展系统性思维”和“国家安全战略性思维”的二维竞合。尽管中国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制度反思与制度自信是相互协调的,在健康优先、健康评价、健康协同三重实践逻辑的指引下,中国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践必将嵌入国家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变革中,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