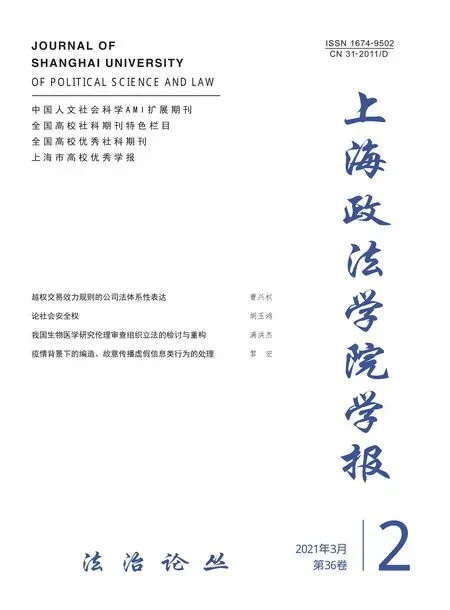人体基因科技的规制:问题、路径与原则
就内涵而言,基因科技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伴随着人们对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组学等生物科学的认知而发展。概括而言,人体基因科技囊括了探索人体基因对蛋白质表达的影响、利用或者修改人体基因变异、在不同宿主之间进行基因转移等一系列的活动。基因科技可能在物理层面对于人体是干预性的,也可能是非干预性的;就基因工程手段,包括DNA 拼接和DNA 重组,核酸凝胶电泳、核酸分子杂交、细菌转化转染、DNA 序列分析、寡核苷酸合成、基因定点突变和聚合酶对链反应皆是支撑技术;就应用范畴,基因鉴定、基因制药、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和基因克隆都隶属这一范畴。在科学研究领域,基因科技被称为分子生物学层面的“哥白尼革命”;在社会层面,基因科技带来医疗与制药、刑事侦查与司法、就业与保险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并引发对生命个体行为和群体现象的进一步解读。基因科技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社会伦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问题,涉及法益纷争与程序性救济。
一、基因科技带来的制度冲击与问题聚焦
(一)遗传学发展与基因科技的进步
遗传现象并不为人类社会所陌生,它伴随着繁衍的需求,逐步形成了经验性的知识积累。人们最早开始通过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似性来研究遗传问题。毕达哥拉斯学派曾经长期致力于三角形几何学,但是他们关注到精液对于后代的作用,并提出父母是生物三角形的两条直边,而孩子是在已知父母作为直边情形下,长度固定的斜边。①参见[美]悉达多·穆克吉:《基因传:众生之源》,马向涛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3 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如果人类社会可以根据父母特征去推算孩子的天性,那么便可以通过对父母的挑选去塑造完美的孩子,于是在政治乌托邦与遗传乌托邦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对遗传领域的重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强调了父亲和母亲在遗传当中的共同作用;二是发现有些特征的遗传在子代中消失,而在下一代又出现,即我们所说的隔代遗传。但亚里士多德对于遗传的贡献绝非停留在生物学领域,他还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非生物学”的相似性,比如姿势、语言与神态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遗传学肇始于孟德尔的发现。在孟德尔生活的年代,分类是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目标与研究方法,相似性是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的研究话题。从基因作为特定的遗传因子被发现,“瑟顿-波佛利理论”被提出所引起的生物学革命,到薛定谔著作《生命是什么?》,1953年DNA 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和证明,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再到科恩伯格分离了DNA 复制需要的酶,坎布尔发现了细菌攻击病毒,以及细菌抗药性的发现,让基因重组成为可能。如今,基因编辑技术已历经ZFN、TALEN、CRISPR/Cas和Prime Editing 四代发展②参见卢俊南、褚鑫、潘燕平、陈映羲、温栾、戴俊彪:《基因编辑技术:进展与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11 期。,并被寄予提高癌症治愈率的厚望。从DNA 分子生物科学理论的进步,到技术应用,人体基因科技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它意味着人们不仅仅可以了解DNA 的分子结构,掌握生命密码脚本,还试图通过人为的复制或者积极的创造,产生不属于自然界的DNA 信息,通过基因细胞外的运作而对遗传产生干预,成为真正的信息编码者。遗传科学的发展伴随着曲折的探索、怀疑、证伪到共识,其在社会学领域同样引发了基因歧视、基因海盗等不当利用行为,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长期围绕着基因问题展开“先天与教养孰轻孰重”的论证,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成为人们在处理基因科技发展时利用平衡的重要依据。
(二)基因科技与思想论争
伴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和对社会制度的广泛冲击,西方学者从政治学、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甚至美学等诸多角度进行了探讨,虽然学说林立且方法论各异,但主要集中在基因科技与伦理和法律制度的互动性考察,并由此产生了应当鼓励还是限制基因科技发展的论证。有关科技发展与人性价值的考察源远流长,萨顿、波兰尼、马斯洛、格里芬等思想家都曾论述过科技人性化的命题。③参见吴文新:《科技与人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 页。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认为科技会造成人格异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会沦为科技的工具;库尔特·拜尔茨的《基因伦理学》指出基因科技对人的本质性动摇,以及基因科技与伦理的争议与平衡将持续存在④参见[德]库尔德·拜尔茨:《基因伦理学》,马怀琪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 页。;哈贝马斯坚定地反对基因科技对人性的改造,主张基因科技不应当被适用于非医疗领域⑤Har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UK:Polity, 2003.p15.;迈克尔·桑德尔无论探讨正义的标准,还是探讨人性,都关注了基因科技问题,但是他倡导尊重人的自然和偶然,尊重经验的价值。人可以通过基因工程让自己变得完美,“但这不代表完美的人生”⑥参见[美]马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政治之战》,黄慧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3 页。。西方的学者还关注了诸如基因权利的属性⑦Lee.M.Sliver, Remaking Eden: Cloning H, Harper Collins, 1997.p141.以及基因技术引发的具体法律制度细节问题,比如,讨论基因科技在法律上的概念范畴和程序规范。⑧Honorable Louise McIntosh Slaughter, Genetic Testing and Discrimination How Private Is Your Information, Stanford Law and Policy Review, 2006.经过长期的论证,学者们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即人的价值不应当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被消解,但是,作为实然层面的问题,有关基因科技的规制往往与立法进程密切相关,而对基因科技规制的方法也主要采用了从隐私保护和平等保护的角度进行探讨,这既是一种立法进路,也是一种保护原则。我国的基因科技立法与学术探讨带有明显的技术发展驱动,及对社会事件的回应性特征⑨参见罗玉中:《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中外法学》1998年第1 期。,诸如《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体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较之于技术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互动,有的学者研究基因科技对传统哲学观的影响①参见樊浩:《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 期。,有的学者试图从基因权利的属性寻求保护的路径②参见郭明龙:《人类基因信息权益的本权配置》,《法学》2012年第2 期。,有的学者试图从部门法领域解决基因科技带来的法益纷争。③参见王康:《基因权的私法规范:背景、原则与体系》,《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 期。这些探讨大多试图建立一种风险控制的模式,并试图通过私法分析的方式,解决基因科技涉及的权利内涵和外延问题。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再次让基因科技问题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基因科技法律问题研究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有的学者再度重提科技与伦理的哲学思辨④参见朱振:《反对完美?——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道德与法律哲学思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 期。,也有的学者强调基因科技的立法体系完善⑤参见王康:《人类基因编辑实验的法律规制——兼论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的法律议题》,《东方法学》2019年第1 期。,还有的学者探讨基因编辑规范在诉讼法领域的实践。⑥参见陈姿含:《基因编辑法律规制实践研究:以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法学杂志》2020年第3 期。基因科技问题不仅体现在生殖问题上,也体现在对成年人的基因改造上,进而影响社会竞争的结果。比如,在较为突出的体育赛事方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以明确的态度,率先在WADA Prohibited List,2004年的禁止名单中预先禁止基因改造,即“基因兴奋剂”(Gene Doping)对体育赛事公平比赛环境的影响,在2017年的禁止名单中阐明基因改造技术被扩展到CRISPR 技术,而在最新的WADA Prohibited List,2020 禁止名单中,基因和细胞兴奋剂(Gene and Cell Doping)被禁止,禁止通过任何机制改变基因序列或者改变基因表达的核酸或者核酸类似物的适用,这项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基因编辑、基因分裂和基因转移技术,同时禁止转基因细胞手段对运动员表现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基因科技失范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否能够避免?基因科技的底线思维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建立在对基因科技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其自身发展、制度冲击与回应,以及制度本源性反思的基础上予以考察。
(三)基因科技带来的制度性问题
回顾科学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有关人体基因科技在法律层面引发的问题首先存在于风险层面,具体包括:第一,人体本身能否成为基因科技的客体?是否会导致人体的工具化?第二,人类基因特征的共有性和特殊性如何区分?同代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隐私与知情权,人类遗传资源的整体利益应该如何判断?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比如父母的选择权和孩子的自主权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第三,人体基因科技是否会导致不可逆的风险?比如,对人类基因的污染或者多样性的破坏是否会引发失控的结果,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体基因科技对于法律的冲击,还存在于数据层面,具体包括:第一,对基因信息的特殊性问题,立法采取的界定标准宽严不一。狭窄的基因信息必须是基因检测的结果,宽泛的基因信息可以囊括一切与人的基因特征有关的家族遗传病史和家庭成员的健康信息,甚至肤色、头发等一般性的生物特征。第二,基因信息是否能够脱离其物质载体而存在?其法律属性应该如何界定?法律是否得依人格属性而确保数据主体的自主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或者财产权利益?第三,基因信息是否能够专有?如何平衡个人的基因信息、家庭或者社群共有的基因信息、国家或者民族的基因信息,以及全人类共有的基因信息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因为基因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数据,应当秉持怎样的原则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通和分享?
作为一种分子生物学,基因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还指向公平观和人性问题。人性确保物种延续的稳定性,并参与界定价值观的形成。尽管对于人性的概念历来存在争议,但是人性被作为权利和正义的基础已经形成共识。然而,在人性与规范的问题上,存在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少数人的优越意识在规则中被予以强化。人性是差异化与多样化的个体寻找共性、彼此沟通并建立精神联系的基础。将基因问题特殊化所面临的问题是,先天的缺陷不应当被歧视。那么,先天的基因优势是否应当被特殊对待?如果基因干预可以作为修饰先天不公平的方式,是否应当被尊重?越来越广泛存在的基因检测技术和大规模的算法应用,可以更为精确地识别具有更强表现力的基因携带个体。如果提前选拔这些基因携带者从事特殊的行业,是否可以构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基因干预”?
二、基因科技规制途径
(一)国际立法中的伦理趋势
基因信息的爆炸,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对法律和政策、社会道德、隐私和机密、刑事公正和知情同意、歧视、知识产权与风险评估,以及疾病和健康的概念等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See Weeden, Jeffery Lawrence.Genetic Liberty, Genetic Property: Protecting Genetic Information.Ave Maria Law Review, vol.4, no.2,Summer 2006.基因突变在人群中的广泛存在,让每个人都可能面临遗传性疾病的易感性,这让基因检测在预防性决策和干预性治疗层面受到重视,尽管存在广泛的社会期待去支持基因检测对医学研究与实践的推进,但是人们依然担心基因检测的结果会被不当利用。基于基因信息的特殊性,有学者曾主张给予基因信息无形财产的地位,以财产权的性质,确保这一个体关系密切的信息得到保护。但是,基因信息可以与物质载体相互分离,如果某人不拥有自己的生物样本,那么他既不能拥有,也不能保护自己的遗传信息。最初的法律文书目标是协调国际组织成员之间的数据保护的标准,并且倾向于将基因信息作为敏感数据予以特别关注。比如,1964年的世界医学会,1995年的世界卫生组织,以及2005年的欧盟委员会指令,都尝试通过一系列原则和建议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式虽然意义重大但是收效甚微。
《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虽然没有明确,但它从两个方面有助于基因信息的保护:一是在广义上奠定了一系列可以强制性的全球人权文书的框架,并通过国内法、国际条约和协定将人权概念转变为法律;二是UDHR 在具体的条款中奠定了全人类免受基因缺陷而被歧视的基础,比如第1 条平等权、第12 条隐私权。有关人类遗传特征的国际公约主要是《世界人类基因组和人权宣言》。该宣言在第2 条和第6 条中明确了权利和尊严平等受到尊重,且不因遗传特征而受到歧视。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人类遗传数据国际宣言》强调在基因科技研究与人性尊严之间的平衡问题,开启了自此之后国际组织对于科技研发与权利保护问题的关注,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7年强调基因检测的质量问题,世界医学协会(WM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强调医务工作人员的道德行为和原则,及知情同意在基因检测时的重要性。尽管这些国际文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依然被视为只是提出了伦理原则的价值,而不是行为强制性规范。
(二)欧盟立法中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
有关人类遗传性特征的保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体现在《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以下称为“《奥维耶多公约》”)的颁布。《欧洲人权公约》获得其区域成员国全面遵守,并得到欧洲人权法院受理个人在国内法未经保护起诉的保障;《里斯本条约》强化了欧盟的基本权利原则,并通过《欧洲联盟运作条约》明确强调不歧视原则,其尊重人权的基本核心价值在《奥维耶多公约》中予以贯彻。该条约第1 条明确人性尊严和人的特征平等地受到保护,并且人在生物和医学方面的完整性以及权利和自由受到尊重。第10 条同样明确了人的健康隐私。它在消除基因歧视和确保科研和医疗活动中人性尊严及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有关基因信息和基因科技所产生的数据问题,《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3 条、第7 条、第8 条、第21 条载明了人基于遗传信息的完整性、平等权以及隐私权,强调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应当受到尊重。《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e Protection Regulatin,GDPR)的通过对于基因科技和由此涉及的人体遗传数据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规定了数据处理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最低标准,并设立专条保护基因信息、生物识别和健康数据。其中所载明的权利,在医疗器械指令(933422EEC)、医疗器械法案(MOR)和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法案(IVOR)有关基因检测的事项中予以明确。②Patel, Seema, and Ian Varley.Exploring the Regulation of Genetic Testing in Sport.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Law Journal, 17, 2019.GDPR虽然对个人信息的界定较为概括,但是明确了特殊的信息类别,有关健康、基因信息以及生物识别数据,都被作为与自然人身份信息密切相关的敏感信息。GDPR 以及欧盟53362014 号决议①Regulation (EU) no.536/201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April 2014 on clinical trials o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1/20/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158/1, 27h of May 2014.采用了对科学研究比较广义的范畴,并将临床试验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同时对临床试验依据不同的目的和试验场景进行划分,比如,以对人体的影响划分为干预性研究和非干预性研究,以研发对象分为创新药、特效药以及通用药物的研究,以研究目的分为研发新产品而进行的商业性临床试验,以及为了检测已经授权上市的医药产品而进行的非商业性检测等。《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数据主体身份是决定处理任何数据是否合法的关键因素”。基于该原则,数据处理者必须遵守获得受试者明确协议的义务,并且以明确和可以理解的方式告知其试验的目的;而受试者也必须明确表示接受数据处理,GDPR 就数据使用过程中,对数据主体权利克减的内容作出规定。
(三)英美法中的技术保护倾向
美国的《基因信息非歧视法》(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INA)在开篇即明确保护个人基因信息免受就业与保险领域的歧视。这一立法的通过存在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联邦层面的立法之前,美国已经有40 多个州立法禁止健康保险对基因信息的使用,30 多个州禁止雇主用基因信息对雇员进行歧视。GINA 法案在一以贯之地贯彻平等权保护精神的同时,立意消除个体对于歧视的担忧,其目的在于促进基因检测和基因技术的发展。②Louise Slaughter, 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50, no.1 (Winter 2013).在美国和加拿大,设备监管机构历来忽视实验室开发的测试,而欧洲市场则将基因检测的风险界定在低风险。在实践中,由于提供基因检测的机构具有多样性,设备与技术应用较为复杂,检测方法与解释方法也可能较为多样。基因诊断属于体外诊断,因此基因检测隶属于管制医疗器械领域,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受到监管,面临上市前审查,但是,这些制度并不像药品上市前审查那么严格③Hogarth, Stuart, et al.Closing the Gaps: Enhancing the Regulation of Genetic Tests Using Responsive Regulation.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vol.62, no.4, 2007.,其主要的检测事项是测试基因检测性能和临床数据支持的产品预期,以及向用户强制性说明的事项和对用户性能有限性的警告。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当时美国NIH-DOC 的基因检测工作小组曾提出,对基因检测的法律监管框架应当囊括四个维度的问题,即分析基因检测的有效性,分析临床的有效性——即生物采样与临床状况之间的关系,分析临床用途——即基因检测将带来好的结果,考虑伦理、法律和社会效果。④这一监管设想后来被称为ACCE 监管框架,是NICE-DOE 基因测试工作组在1991年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并由基因检测秘书咨询委员会在2001年报告中采用。遗憾的是,这一全面的监管框架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实现。目前的法律依然只侧重于技术的安全性。技术层面即检测结果是否准确,美国、加拿大、英国皆有法律规定。关于临床的有效性问题,即基因检测是否必要,美国和加拿大法律上都有要求,只有美国强调基因检测应该带来临床上善的结果;而对于基因检测的伦理、法律与社会评价,目前并未在各国的基因检测规范中予以量化。对于安全性的监管,美国对医疗检测风险划分为三级,将基因检测视为中级或者高级;加拿大在四级检测风险指标中将基因检测作为第三级,仅次于最高级的风险;欧盟则在三级风险评价中一直将基因检测视为低风险。
(四)基因科技规制中的数据产生和保护
公众对于基因科技的态度目前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人们更加关注是否因为基因信息而受到歧视。这源自技术的安全性进步,基因编辑技术已经改变了基因工程领域。从基因打靶技术,利用细胞DNA 自然的修复能力即同源重组对细胞基因组进行改变,再到Meganulease,ZFN 和TALEN 科学家们寻找可以切割特定DNA 序列的核酸酶,直到现在每个生物实验室都不可或缺的CRISPR 技术,可以在DNA 任何分子位置,进行精确的遗传改变,较之于“基因决定论”“基因例外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共识,尤其是在基因信息的使用层面。虽然在人类整体性发展问题上,“先天”和“教养”,或者是“基因”与“环境”任何单一维度的表述很难给出充分的论证,作为个体也可能排斥纯粹的基因决定论,但是,基因信息能够精准识别个人,并且能够揭示更多的个人敏感信息。与其他的生物信息重要的区别是,基因信息不仅可以定位到个人,还能够揭示与此相关的家庭成员的部分敏感信息,即所谓的家族和社群关联性特征。另外,在已知的生物数据中,基因信息具有最强的稳定性。①Paor, Aisling, and Ferri.Regulating Genetic Discri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Europe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vol.17, no.1, 2015.这些被称为例外论的客观依据,恰恰也是基因信息饱受污名化和歧视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在定义或者调查基因歧视的时候,规范治理更加强调因为基因信息的筛查和诊断而对个人“种类”或者“价值”的定位。法律强调的是,基因信息作为敏感信息的披露或者访问方式,但是作为隐私权的保护模式,虽然可以在保证人的主体性价值,维护信息安全性方面发挥作用,却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个体必须有能力证明基因信息的非决定作用,才能防止个体价值基于信息时的不公正待遇,这对于那些单一的基因型疾病尤其困难;二是隐私权的保护模式往往是通过征得同意的方式来维持信息在私人或者更广泛空间里运作,但它无法防止因为基因歧视而导致的潜在风险,比如通过偶然的方式、已经公开的数据、个人的披露或者其他合法情形获取的基因信息。
过去,基因检测主要存在于诊断领域,法律旨在消除获取权利信息并进行研究创新的障碍。但是,随着基因检测消费市场的广泛出现,必须由法律对基因信息的产生、控制及其流通进行规范。这一转变既预示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也对权利制度产生了新的需求。基因诊断包括医学专业人员的检测前与检测后咨询,而商业诊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利用好奇心及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参加测试,但是消费者可能面临捆绑销售,或者被提供未经允许过滤的检测结果,测试者的自主权与平等权可能面临挑战。较之于医学专业人员的检测,未经过滤的基因检测结果,受试者缺乏专业性的解释与医学指导。尽管基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健康,基因信息也有助于改善身体状况,但是信息通常是一种概率性解释,个体的消费者并不擅长对概率进行解读,还有可能造成心理负担,过度地强调基因检测结果可能忽略治疗中的其他因素。
目前的基因检测法律监管程序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被囊括在医疗器械领域中的法律过多地集中于事前评估,其有效性的评估不仅仅是一个上市前样本分析的过程,而且还应该随着适用规模在人群中不断扩大而进一步观测。近年来,上市后监督的重要性被反复提及,但是,有效的售后监督需要系统的数据收集,以及多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一些公司通过报销或者费用减免的方式实现有条件的设备覆盖,以换取系统的数据收集,因此产生了透明度问题。第二,全面定义风险分类系统,建立多个风险控制预测机制,是对人体有关的基因检测和基因诊断的比较妥善的措施,但是风险分类与风险特征复杂性认知尚不明确存在矛盾。
从自主权层面来看,仅仅因为遗传的特殊性而对其保护,是遗传决定论吗?基因信息对个体身份识别具有独特价值,但是如果把遗传性作为排他性标准,个体身份的识别本身就是在故意强化基因信息的社会意义。从知情权视角来看,知情权包含选择不知情,与遗传病史这一传统的健康信息不同,基因信息具有家族和社群的管理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家庭倾向,即在个人权益与家庭利益之间造成冲突。诸多的疾病可能在家庭成员之间传播,比如,HIV 病毒,而社会对HIV 认知的加深,并不是将HIV 病毒检测信息特殊化,这也正是对疾病恐惧与污名化减少的真实反映。因此,既有的经验应当是对法律现象进行独特但并非例外的规制。基因信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但是,却无法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因为行为差异被归结为生物的决定性或者家族的遗传,而非意思自治的结果。这将造成对法治理念多维度的冲击,比如,将亲权关系归结于共同的基因,由于家族倾向而弱化个体的存在或者预判个人的行为。因此,无论是对个人隐私权还是家庭成员知情权的伤害,本质都是对意思自由的挑战。
三、基因科技法律规制的本源性反思
(一)基因科技制度设计指向人性的认知
我们要防止动物行为学、生物进化学、神经认知科学对于人性的定性和改造。因为这些生物科学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危险:第一,人被物化,人的概念被完全消解在客观世界当中;第二,陷入先天决定论而导致种族主义、优生主义,夸大自然人暗含的社会等级,限制人后天的可塑性;第三,让人们相信有能力对人的意识和行为进行探知和干预。否认人性对人的行为决定论,并非能够带来构建论的优势。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人类就被视为可以从经验获取知识,并在个体对文化的适应当中去推进社会进步的种群。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并非完全由遗传所决定或者处于自然进化的支配之下,而是应当考量具有选择和塑造的社会决定力量。然而,社会塑造一旦走向极端,比如,杀婴行为、弗洛伊德主义、行为改造等,就会存在过度压制任性甚至反对任性的行为。极端的构造论除却对个人的忽略与消解,对社会组织同样存在威胁。如果只将人类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那毫无疑问较之于动物数量更庞大的人类行为差异中,将很难获取人类思维与行动中的共同准备,或者说难以形成普世价值,而这将直接损害社会构建的基础权威和赖以生存的秩序。
基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是关于人性讨论中的两个重要对立面,基于统计上存在的极大误差,因此很难完全说服对方,比如,证明相同基因的人面临文化的决定力量,或者跨文化的人所存在的共同的行为特性。与其乐观地说二者都从宏观层面关注人的共性,毋宁说他们都注意到了基因与人的行为之间有待论证的因果关系。基因决定论,很可能走出的误区是将动物尤其是高阶哺乳动物与人类身上共同的“动物性”界定为“人性”;而环境决定论则必须证成本性在相同文明下不准变异的可能。从总体上讲,决定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略人的行为是多重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二是利用还原论的方法解释复杂的生命系统。诸多物理现象的确通过还原方法寻求到原因与条件,整体的进步也的确有待部分条件的实现作为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充分必要性的实现。
(二)法律监管基因科技带来的负外部性和群体价值
生物学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改变,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生物数据的庞大曾经让人焦头烂额而难以捕捉其中的规律,计算机被用以处理基因组与蛋白组释放的数据,并且发现人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的计算,并发掘其中微弱的联系,人类基因组排序的提前完成和基因图谱的绘制就是典型代表;第二,利用基因技术对人类的胚胎进行控制,比如胚胎着床前进行的基因诊断与筛选;第三,将基因编辑分为体细胞编辑和生殖细胞编辑。前者通过生物技术促成经过改造的基因传播,从而改变目标基因的DNA;后者则有助于部分遗传疾病的治疗。目前在动植物身上取得成功,尤其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但是,基因科技本身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在已知的疾病预测与体细胞治疗领域,基因技术之所以效用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些疾病的发生是基因缺陷或者错误问题比较单纯,只需改变单一基因中的等位基因或者纠正其排列错误即可起到良好效果。然而,人类对于基因信息有关的知识掌握还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诸多的疾病是多个复杂的基因导致的结果。还有的基因与周围环境产生了敏锐的互动关系,或者一个基因功能复杂,它可以抑制或者激活其他基因的致病功能,有的基因可能导致一种疾病又有助于防御另外一种疾病的发生。比如,导致地中海贫血症的等位基因就有助于对抗疟疾。因此,单一基因的剪除或者修复,或者收效甚微,或者可能导致其他的疾病。基因治疗的安全性问题,还在于基因数据与蛋白质表现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有些还可能在人体的终极表现与代际遗传之间被放大。
长期以来,基因技术被作为可以延长寿命的人类福利被广泛倡导,并获得社会共识。但解决“全人类获益”的问题必须面对庞大的人口数量,个体的基因编辑很难影响到人类群体。毋庸置疑,基因技术对人类群体发生作用的前提是技术手段的安全、有效且价格低廉,否则将有违当代人的平等问题;同时,个体性或者少数人的伤害可能比人类群体等位基因改变而长寿到来得更迅速与直接。基于生物数据而实施的生育决策,过去常常与优生学和种族灭绝结合在一起而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20世纪初的基因选择在今天可能跟“优生行为”存在巨大差别,生物数据的应用可能拓展了个人生育权,而不是作为国家对个人的强制。因此法律介入应当是对个人选择“负外部性问题”的调控,即当契约的代价或伤害完全归于没有参与交易或者缔结契约的第三方主体的时候,国家应当进行管控。一个鲜明的体现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尤其是全球范围内对生殖细胞的基因工程所采取的禁止态度。
(三)非功利性规制确保生物安全
生物数据的安全性问题可以基于数据自身的特性,也可能是引发的外部性问题,但归根到底在于对人的本质性特征的影响。许多今天看来可能带有价值判断上的否定性评价的特征,却有可能维持甚至推动深远的人类延续。比如体现在群体成员之间的竞争状态,如果作为成员的人类个体只存在合作倾向,那么在对抗压迫的情形下个体也是脆弱和无能的。同时,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基因的自私的特质,比如作为母亲通常情况下只钟爱自己的孩子,以至于在社会群体当中自然人对于亲戚的偏私行为一直饱受社会学的关注。但是,恰恰是自私的基因确保了人类的每一个后代都公正地得到了无私的爱,且能够强健地发展。
这里涉及对生物新技术的规制态度,不应当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在本质上倾向于一种成本收益的计算,其优势是可以获得像科学一样在追求最优过程中清晰可辨的法律设计倾向,但随着人类认知人性的自然科学知识群体性的增长,公共制度的设计也更为复杂。
纵观人类制度设计的长河,权利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起源:君权神授,即权利来源于上帝;天赋人权,即权利来源于自然;实证主义,即权利根植于法律和社会规范。西方描述与实现人性的哲学传统,在卢梭和康德那里发生了转型,即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如卢梭所认为的人性是可以改变并且日趋完美的;康德则认为,道德准则与自由意志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人的行为的核心是理性而非人性。行为的主体必须是理性的,包括人类和理性的非人类。这一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因为进化让生物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人类被紧密地联系并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系统。在社会内部,价值并非被任意地构建,而是从整体上有助于共同的行动,并有利于物种的延续。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人类的冲突在更高的团体层面表现出正当性,因此诸多的社会规则是团体外部竞争的需求推动了内部秩序建立的结果。第二,人类群体的边界冲突虽时有发生,但共同体的概念在不断扩大,并且法律制度逐步完善以妥善解决共同体内部的冲突。这两点趋势,一方面推动了近代以来形成人性的共识,即寻求共同的文化认知,并予以固定,另一方面也推动着自主价值的觉醒,即人有能力认识自己,并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而不需要获得更广泛的群体认同。这一主张在卢梭、康德、尼采那里都得到了深刻的印证。第三,人有自由拒绝更大团体范围内的道德准则对于自身价值的压迫,但并不具有“先天形成某些价值的自由”①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 页。,也就是人的价值不是被肆意创造的。
四、结语
基因科技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内涵伴随着理论探索和技术实践而日渐丰富。在具体的制度措施层面,立法应当精细化。但是,应当注意到,基因科技对于制度的冲击是多方位的,有来自技术层面的风险,这一领域所蕴含的是安全性的需求,伦理、道德以及技术准备与立法精神相互渗透,并日渐形成国际共识。基因科技的发展在当下日益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相互结合,基因检测、基因诊断、基因编辑等技术应用带来物理层面的创伤日渐缩减,而由此产生的数据问题,在个人、市场和国际社会层面的流动性日渐重要。所以,基因信息是一种可以脱离其生物样本和物质载体的特殊性信息。从国际性立法的趋势而言,个人信息和生物数据安全的保障未来将成为发展的重点。基因科技的独特性得到规制应当是结合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客观的理性思考与客观环境基础之上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这其中不乏利益的衡量,但这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选择。虽然哲学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长期贯穿于社会管理领域,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价值论证对于基因科技法律规制同等重要,但是法律制度必须维护基本的人性价值,才能实现从个体到不断扩大的共同体概念的共识性凝聚与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