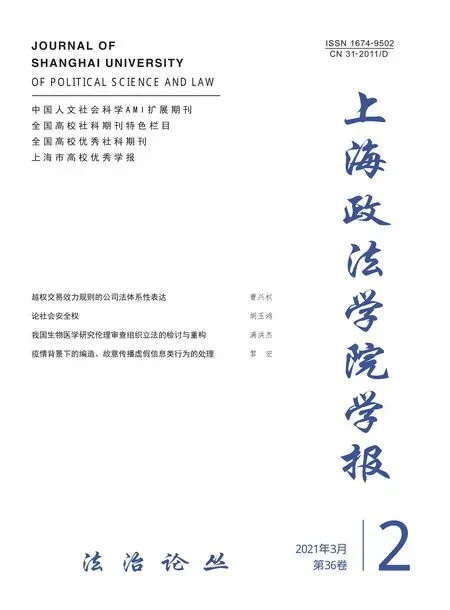《民法典》时代股东主体制度的革新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在民事主体方面,《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三种类型。自然人当中存在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两种特殊类型。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同时《民法典》第125 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文义解释的结论是所有民事主体均可以成为股东。但是现行《公司法》仅仅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两种股东类型。特殊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能否成为公司股东,《公司法》态度不明。经过商业主体和工商登记部门的共同实践,合伙企业能够取得股东资格,但不能成为一人公司的股东,因为《公司法》第57 条第2 款规定,一人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公司。合伙企业不能成为一人公司股东的理由何在?将来是否要承认包括合伙企业在内的非法人组织的一人公司股东资格?这算是一个《公司法》的老问题。《民法典》时代的新问题是:自然人中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非法人组织中的个人独资企业能否作为公司股东?以上关于股东主体资格的新老问题应在《公司法》修改中一并解决。
一、股东主体资格:开放外延还是封闭外延
从法律适用顺序上而言,特别法有规定的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一般法。股东主体资格方面有着两组法律关系:一是民法与公司法之间,民法是一般法,公司法是特别法。《民法典》确认了民事主体范围,承认民事主体享有股权权利,此时如果公司法没有特殊安排,应当适用《民法典》关于民事主体享有股权的规则,即所有民事主体均可成为公司股东,但这个结论显然难以被简单接受。二是公司法和证券法之间,公司法是一般法,证券法是特别法。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57 条规定,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应当持有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合伙企业身份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只承认了公民、法人、合伙企业的证券市场投资者资格,换句话说,上市公司股东只能是公民、法人和合伙企业。其他类型公司的股东资格证券法并未调整。《民法典》与《证券法》关于股东资格的中间地带有待公司法加以明确。此问题并非理论的空想,实践当中,《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准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意见》渝工商发〔2006〕37 号和《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市场主体准入中若干问题的通知》洛政〔2008〕104 号均规定,除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允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投资能力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股东或者发起人投资设立公司。村民委员会投资设立公司,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作出决议。两个城市承认了个人独资企业的股东资格,其他省市的具体做法尚不明确。如果重庆和洛阳的做法合理,则应当在公司法上承认非法人组织的股东主体资格,如果两者做法不合理,则应当在公司法上对个人独资企业的股东主体资格予以明确排除,或者步子更大一些,认为两者将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限定在非一人公司场合没有必要,非法人组织也可出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但无论采股东主体资格的狭窄还是宽泛立法态度,均应在立法上加以明确,以免出现不同省市不同做法的情况。因此,从法政策的角度而言,摆在立法者面前的抽象问题是:股东主体资格应当是一个开放外延还是封闭外延?易言之,公司法在确认股东主体范围时,应更靠近《民法典》还是更靠近《证券法》?
确认股东主体资格的范围应首先解决一个前置性的问题,即股东主体资格范围的立法价值追求是什么?《公司法》第1 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股东主体资格范围有关的,可能是债权人保护的问题。在公司法上隐而不彰的一个价值追求是鼓励投资,这在2013年修改公司法资本制度时得到了极大体现。保护债权人和鼓励投资之间存在角力。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股东主体越简单,其需穿透的层级越少,发现实际控制人越容易,判断交易风险也越容易,但排除了一些主体成为股东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投资。从鼓励投资的角度出发,股东主体越丰富,各类民事主体投资于公司的热情就越高,《民法典》第125 条的规范目的,就是通过保护股权和投资性权利,激发私人的逐利动机和创新动力,促进民间投资,实现财产在流动中的增值,裨益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条件的改善和社会总体的进步。①参见陈甦:《民法总则评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70 页。但对于债权人来讲,股东主体越多,其获知公司的真实信息就越难,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交易安全。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恰如合伙企业取得股东主体地位的过程。现行公司法并未明确承认合伙企业的股东地位,仅能根据第57 条第2 款得出一个推导的结论,即公司法并未考虑合伙企业的股东地位问题。但随着私募基金等领域商事实践的发展,在公司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工商登记实践承认了合伙企业的股东地位,此处利益衡量的结果是承认合伙企业的股东地位并不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又因应了私募基金的投资需要。这可以说是现行公司法仅仅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的股东主体资格的不良后果,合伙企业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取得了股东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司股东主体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因此除非法政策考量上有足够的理由,否则应保持股东主体制度的开放性,以免出现不得不承认“脱法”现象的窘境。
另外一个决定股东主体制度是封闭还是开放的要素在于,成为公司股东是基于主体地位还是基于投资行为。如果是基于主体的话,是基于广义民事主体的身份还是基于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如果基于投资行为的话,是否所有的民事主体都能够拥有财产并实现投资。我国公司法上的公司只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成立纯赖于资本的结合,对外信用的基础也是其资本,而非股东身份。有限公司虽然具有一定的人合性,但我国法上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主要体现在内部关系上,而非对外信用上,有限公司对外信用的基础也是其资本或资产①我国公司法学界就公司到底是资本信用还是资产信用有争议,但即使在有限公司场合,也无学者主张公司为股东信用。参见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2003年第5 期;陈甦:《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的学说分析与规范分野》,《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1 期。,而非股东身份。故德国法上将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均置于资合公司概念之下。既然公司对外信用的基础是资本,那么只要股东具有出资的能力,就应当承认其股东主体资格,而不应考虑组织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特殊自然人也是同理。这是成为股东是基于投资行为得出的结论。如果成为股东是基于广义的民事主体身份,既然《民法典》规定了民事主体的范畴,自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无论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从权利归属或财产流转的角度均应具有一席之地,否则《民法典》也无须设置诸多民事主体类型。为法律体系周延计,就应当承认所有的民事主体都应当具有股东主体资格,个别民事主体的股东资格剥夺或限制,如非营利法人能否成为股东,交给不同的法人法来解决即可,无须公司法作出一般性规定。如果成为股东是基于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非法人组织问题上会复杂得多。现行公司法只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的股东主体资格,似乎是基于这点考虑。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则牵涉到复杂的民法基础理论问题,即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资格的关系问题,德国法上的无权利能力社团②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 页以下。、无限公司等理论或制度均与该问题相关。限于篇幅与主题,本文在此不予展开。公司法上有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如果股东必须具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则股东只能是自然人和法人,股东主体应该是一个封闭的集合;而如果股东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行为能力即可,无须具有权利能力,则股东主体资格也应具有一个开放的外延。可见,当股东资格的取得是基于投资、基于普遍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基于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时,股东主体资格应具有一个开放的外延。仅当股东资格的取得是基于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时,才具有一个封闭的外延。而合伙企业股东资格的取得似乎消灭了股东资格的取得基于权利能力的结论的合理性。当然,如果反对者认为合伙企业取得股东资格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应该予以纠正,上述结论显然也站不住脚。但是,立法应当尊重实践还是矫正实践,可能更多取决于这种实践是否侵害了某种利益或危害某种秩序,合伙企业成为公司股东除了上述损害了现行公司法的权威性以外并无其他危害,那么就应该尊重这种实践并修改立法,而非强令实践顺应法律。新修订的《证券法》即为例证。综上,股东主体资格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非封闭概念,在此前提之下讨论特殊自然人的股东主体资格、非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才具有意义。
二、特殊自然人的股东主体资格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规定在《民法典》第二章自然人部分,两者属于自然人似乎为当然的结论。但是,第二章前三节规定的自然人显然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人,其存在着出生、死亡、监护等问题。第四节规定的“两户”不存在生物意义上的出生和死亡,也不存在监护等问题。此外,一户之内可能有多个自然人,所以其虽处自然人一章之中,但与自然人有着本质区别,是故称其为特殊自然人。在公司法上有意义的问题在于,特殊自然人能否成为股东。“两户”能否成为股东涉及诸多问题:拥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能否以字号登记为股东?“两户”成为股东的话其代表或代理权限如何安排?如果以户主或户中其他自然人的名义登记为股东,该自然人死亡时是否引发股权继承问题?“两户”成为股东,当发生股东责任时其责任财产的范围如何确定?下面就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分述之。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8 条规定:“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应当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注册登记。申请人应当提交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明和经营场所证明。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包括经营者姓名和住所、组成形式、经营范围、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使用名称的,名称作为登记事项。”如果个体工商户未使用名称,同时经营者出资设立公司,自然没有法律障碍,只是此时无法分清是以该自然人身份还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身份。如果是以该自然人身份设立公司,则该自然人同时作为一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和一个公司的股东,并无法律问题。但是,即便工商登记上毫无体现,如果认为是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设立公司,则出现疑问:当出现股东责任时,公司或公司的债权人能否主张以个体工商户的财产承担责任,而不主张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自然人股东的责任。因为按照《个体工商户条例》第20 条,个体工商户可以凭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明,依法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账户,申请贷款。个体工商户可以在银行开立账户存贷款,此时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债权人主张执行个体工商户账户的财产,自然人股东能否以其名下的账户为个体工商户的账户而提出抗辩?《民法典》第56 条第1 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但未规定,经营者个人债务能否以个体工商户财产清偿。从资产区隔理论角度而言①也译作资产分割理论,由美国学者汉斯曼和克拉克曼提出,认为企业财产独立性的意义在于将企业财产和投资人个人财产分离。参见:Henry Hansmann and Reinier Kraakman, “The Essential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aw”, 110(6)The Yale Law Journal,387(2000).,个体工商户显然不具有资产区隔功能,个体工商户的财产无法独立于经营者个人资产,理论上一般也认为,个体工商户财产和经营者个人财产无法区分,应视为一个整体,故经营者个人债务应该能够以个体工商户财产清偿。如果是以经营者个人姓名登记的股东,也就不存在代理人身份问题,但是如果该股东死亡的,发生股权继承问题,自不待言。
如果个体工商户使用名称,能否以该个体工商户的名称登记为股东?目前重庆和洛阳的规定当中并未承认个体工商户的股东地位。从责任承担的角度来说,个体工商户是否使用名称与其股东资格无关,以经营者个人名义注册和使用名称注册处理规则应当一致。如果允许以个体工商户的名称登记为股东将使得判断公司股东身份的时候多了一重外观,但从结果上来说未必导致其他主体利益的损害。所以,否定个体工商户使用名称登记为股东的理由并不充分。至于《民法典》第56 条规定的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与其是否使用名称之间并无关联。即使个体工商户使用名称,也需要登记经营者姓名、组成形式(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对外显然以经营者为全权代表,其他经营成员意见无须考虑,所以当以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为股东时,无须考虑代理人问题。当登记的经营者死亡时,是否发生股权继承问题存在疑问。如果登记的组成形式是个人经营,发生股权继承问题,如果登记的组成形式是家庭经营,则属于家庭内部股权行权主体变更问题,不属于股东变动,不发生股权继承问题,无须受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约束。
如果说个体工商户的股东资格问题更多是理论的假想,立法上可能更倾向于否定个体工商户的股东资格的话,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股东资格问题则是公司法必须直面的问题。按照《民法典》第55 条,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只能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并且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形式。《民法典》第339 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也有类似规定。将以上法条提炼出一句规则,就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可以将经营权入股。《公司法》要回答的是,入股的对象是否包含公司,如果答案为否,农地经营权入股是否还有其他企业的可能性?分析我国现有各类企业法可以发现,农地经营权能够入股的对象主要应当是公司。②参见陈彦晶:《“三权分置”改革视阈下的农地经营权入股》,《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3 期。如果公司法拒绝了农地经营权作为出资财产,《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所确立的农地经营权入股制度将落空,这似乎背离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初衷。因此,农地经营权应当能够作为公司出资财产,一个当然的结论也就产生了,农村承包经营户能够成为公司股东。传统公司法制度是以自然人和法人股东为模型设计的,当农村承包经营户成为股东后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第一,农村承包经营户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形式,而家庭成员通常并非一人,农户家庭范围内谁来行使股东权利?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角度来讲,农户的登记主体为户主自然人姓名,故行使股东权利的主体也应为户主,户主无法行使股东权利的,应委托户内其他家庭成员或他人作为代理人行使权利。从公司角度来讲,农地经营权入股后,应以承包经营权或经营权记载的自然人主体为股东,而不应以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全部家庭成员为股东。第二,登记的户主死亡时,不发生股权继承问题,而应由家庭内部新产生的户主取代原户主成为新的股东代表,此处涉及股东制度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衔接问题,未来一定会出现,应予以考虑并事先作出制度安排。第三,农地经营权入股通常不发生认缴和实缴的时间差问题,但理论上也存在认缴以农地经营权入股,后未能实际缴纳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农地经营权入股股东承担责任的其他情况,故存在农村承包经营户股东的责任承担问题。此时,不论登记的股东姓名是谁,应按照《民法典》第56 条第2 款的规定处理,即农地经营权入股产生的债务,属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以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的农户财产承担;事实上由农户部分成员经营的,以该部分成员的财产承担。
《民法典》虽然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规定在一起,但两者可能还是略有差异,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主体地位并不等同:个体工商户以“户”为单元,并非旨在创设“户”的主体地位,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商自然人的概念。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86 页。而讨论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主体地位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都规定了“户”是承包合同的主体,当发生土地承包纠纷时,户就应该是诉讼主体,由“户”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而非个人。②同注①,第291 页。显然,个体工商户的“户”更多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尊重,并非要创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而农村承包经营户则是实在的民事主体,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当下改革进一步确认和强调的主体。从制度供需上来说,个体工商户成为公司股东的制度供给意义并不显著,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股东主体地位则是公司法不得不确认的。
综上所述,应当承认特殊自然人的股东主体资格,但其毕竟并非普通自然人,在股东资格处理上应予特殊对待。为了省却麻烦,公司法可以无视个体工商户的股东资格问题,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股东主体资格应充分考量,以免“三权分置”改革的目的落空。
三、非法人组织的股东主体资格
《民法典》第102 条第2 款规定,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民法学理认为,本条所称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主要包括律师事务所,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专利代理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且未注册为合伙企业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清算事务所、评估事务所、鉴定事务所等。③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 页。还有一些法律未例示的非法人组织,包括:(1)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2)企业集团;(3)合伙类、个体类民办非企业单位;(4)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5)职工持股会;(6)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宗教活动场所。④同注③,第299-303 页。这些专业服务机构能否成为股东,与非营利法人能否成为股东的问题一样,应当由各自专业领域的法律法规安排,公司法无须加以规定,只需考虑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股东主体资格即可。个人独资企业的股东主体资格在重庆和洛阳得到了承认,其他省市态度不明,公司法应当予以明确。合伙企业的股东主体资格被商事实践裹挟而得到了承认,但合伙企业能否成为一人公司股东在公司法修改中应予回应。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虽然从财产和责任承担角度来讲,个人独资企业的独立性较弱,但个人独资企业也必须开立银行账号,进行税务登记,增值税的缴纳主体为个人独资企业而非投资人,税款的扣缴也是在企业账户而非投资人个人账户进行;与个体工商户不同,个人独资企业必须起名称。综合以上因素来看,“经营实体”一词反而得到了完整体现。承认个人独资企业的股东主体资格不会带来公司内部治理的混乱和损害债权人的后果。从公司内部来说,既然个人独资企业作为经营实体,其财产所有权虽属于投资人,但不妨碍其投入公司作为出资,个人独资企业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该个人独资企业承担并无不妥,当出现应由股东承担财产性义务时,由其投资人承担即可。当然,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8 条,如果在申请设立登记时就明确是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当出现应由股东享有身份性或财产性权利时,由该个人独资企业享有亦无法律上的障碍。由于有着个人独资企业法上关于投资人无限责任的规定,承认其股东主体资格也不会损害债权人利益。和上文提到的两户略有不同的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死亡时,发生股权继承问题,因为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7 条,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所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形成的股权,属于投资人所有,当其死亡时,股权可以继承。因此就应受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有关股权继承的规则的调整。至于为何在“两户”和个人独资企业股东资格继承方面区别对待,一方面在于这是法律解释的当然结果,《民法典》《个体工商户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①《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 条规定了收益的继承,第54 条规定的是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经营权的可以继承收益,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并非户内经营权继承。均未规定户内继承;而《个人独资企业法》明确规定了有关权利的继承,自无排除继承的道理。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概念差异。“两户”强调“户”的概念,而个人独资企业强调“个人”。《民法典》中“两户”的规定极大地体现了“户”的特殊性,即将“户”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立法体例上也将其置于“自然人”一章,因此对外代表该“户”的自然人变动,不应属于公司法上的股权继承,此时公司的人合性应让位于民法上“户”的概念内涵。个人独资企业既然强调其个人,除法定的责任财产外,自无须考量其他。《民法典》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在责任财产推定方面的不同规定也体现了法律更加注重“户”还是更加注重个人,“两户”的责任财产均推定为家庭财产或部分家庭成员财产,而个人独资企业的责任财产则推定为个人财产,除非其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
现行《公司法》第57 条第2 款规定的一人公司股东只能是自然人或者法人,导致实践中合伙企业无法成为一人公司股东。否定合伙企业一人公司股东资格的理由何在?实难回答。《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规定合伙企业的法人资格,但在司法实践中,除了没有法人资格之外,合伙企业在对外关系上与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等无异。德国学者也提出:德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合伙是民法合伙的特殊形式,因此,它们也属于财产共同共有社团。对于司法实践而言,这种分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它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德国商法典》第124 条、第161 条第2款和《有关自由职业者合伙企业法》第7 条第2 款已经授予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合伙足够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在法律权利能力方面,它们已经与法人没有任何区别。法国法已经确认:合伙具有法人资格。这也表明,各种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内在固有差异已经越来越少。②参见[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 页。尤其是合伙企业能够作为非一人公司的股东,唯独不能作为一人公司股东,实在找不到理由来论证这一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合伙企业的一人公司股东资格反而会造成一个很荒唐的局面:当公司只有合伙企业和另一个股东时,另一个股东如果转让股权,合伙企业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果行使,就会导致公司只有合伙企业一个股东。这对于该合伙企业股东来说恐难以接受。故未来公司法修改时,应明确承认合伙企业的股东资格,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上也没有排除合伙企业的道理。
四、不同民事主体股东在公司法中的体系安排
《民法典》在民事主体上采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三分法,公司法应予尊重。如果公司法承认非法人组织的股东主体资格,在设计有关股东规则时应该分别考虑股东为三种不同民事主体类型时的不同情况。现行公司法在这点上不尽人意,主要表现为未能考虑非法人组织成为股东的情况,还存在着大量的自然人假定规则,未能考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情况。
(一)未考虑非法人组织股东
除了《公司法》第57 条规定的一人公司股东主体身份限定之外,《公司法》还存在其他未能考虑非法人组织成为股东的可能性的规则。例如,《公司法》第92 条规定:“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创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下列文件,申请设立登记:……(六)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第129 条的股票种类规则,也仅仅规定了公司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可见公司法只考虑了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两种可能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条文产生的时间均早于《合伙企业法》修改和《民法典》制定的时间,彼时公司法的立法者未能考虑到这些情况,自然也就无法作出预先的安排。时至今日法律环境已然发生巨大变化,《民法典》确认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商事实践推动了合伙企业成为公司股东,此时公司法应当对于以合伙企业为典型的非法人组织的股东地位做出回应,并且在规则设计上体现出非法人组织股东的特殊情况。
(二)《公司法》个别规则的股东自然人假定
现行公司法仅仅设计了自然人和法人两种股东类型,即便在这一设计方案上,其也并非完美,还存在着诸多股东自然人假定规则,即法律行文中明显将股东想象为自然人,没能考虑其已经明确规定的股东为法人的情况,更谈不上考虑股东为非法人组织的情况。例如,《公司法》第38 条的首次股东会规则,第40 条、第101 条的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规则,第41 条、第61 条的股东会会议记录签名规则。司法解释也延续了公司法这一自然人假定,将股东当然地想象为自然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0 条第2 款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法人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尚可行,法人股东如何主持股东会?主持这一活动应仅限于自然人方能开展;股东会记录的签名也仅仅指向自然人,若考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当像《民法典》第490条一样,签名之外并列一个盖章行为才行。“股东在场”的表述对应的股东应是肉体凡胎之自然人,而不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等拟制主体。
(三)股东主体规则的体系化处理方式
在《民法典》框架之下,股东可能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公司法在设计有关股东规则时应当将这三种民事主体类型均考虑进来。涉及股东意思表示时,应像《民法典》第490 条那样规定,即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盖章针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股东,签名、按指印适用于自然人股东。涉及专属人自然人的行为时,应明确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代表或代理规则。例如,当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行使股东会召集权时,该股东会的主持应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有代表或者代理权限的人来实施。司法解释的相应规则也应一并调整,自不待言。
具体到法人,应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法人行使股东权利,法定代表人无法出席的,法人应按照普通民事代理规则或公司法上的股东代理规则,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具体到非法人组织,因涉及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两种企业类型,两种企业对外代表主体不同,个人独资企业的对外代表称为投资人,合伙企业对外代表称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而《民法典》并没有为它们确定统一的上位概念,其第105 条仅仅规定,非法人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或者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民事活动,称为非法人组织的代表容易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混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 条的规定可资参考,该条的主语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对于非法人组织而言,可以将其代表统称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无法代表非法人组织行使股东权利,则仍由代理制度来解决。而关于特殊自然人股东主体资格的处理前文已经交代,无须赘言。
五、结论
《民法典》时代已经开启,上一轮《公司法》的修改发生在《民法典》之前,值此《公司法》再次修改之际,应加强公司法制度与民法典制度的体系协调。《民法典》确立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三种民事主体类型,还概括性地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在没有充分理由否定特定主体股东资格的情况下,《公司法》应当承认《民法典》所规定的所有民事主体的股东资格。原本《公司法》上仅仅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的股东资格,如今需要考量的是特殊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股东资格。因个体工商户与其经营者密不可分,是否承认个体工商户的股东主体资格影响不大,制度需求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烈,故无须特别强调。但由于《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了农地经营权入股,在《公司法》上有必要承认农户的股东主体资格并予以相应的制度安排。个人独资企业既然被称为“经营实体”,作为一种民事主体也应当可以成为公司股东。合伙企业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股东主体资格,但却因为公司法的阻拦而无法成为一人公司股东,这种阻拦并无法律和经济意义,应明确承认合伙企业的股东主体资格,且在一人公司股东身份上不应与自然人、法人区别对待。未来《公司法》修订中应注重不同民事主体股东的差异,充分考虑到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作为公司股东的情况,在立法语言和制度设计上追求严谨,以提升《公司法》的体系化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