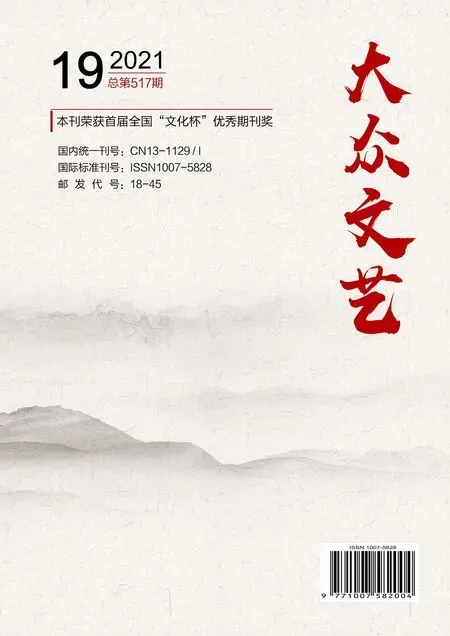浅析维柯对形象思维的理解
——兼涉与我国形象思维论之比较
赵 欣 贾若楠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们通常将维柯视作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其研究范围涉及法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由于思想复杂以及语言翻译的晦涩难懂,国内对维柯的研究起步较晚,朱光潜先生晚年花大力气翻译了《新科学》全稿并在译后记中谈到了他研究维柯的渊源:他在留学期间研究克罗齐的美学思想时,意外了解到维柯对诗性智慧中形象思维的相关论述,并对其中的一些论点十分欣赏。本文将重点对维柯笔下的形象思维进行探讨,并且尝试与我国对形象思维的解读做出对比分析。
一、形象思维的诠释与运行过程
《新科学》共分五卷,维柯从共同人性论的基本点出发,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探究多个方面的内容,意在阐明“人类如何从原始的野蛮动物逐渐发展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1],其中近半篇幅详细探讨了“诗性智慧”,这也是全书中最能体现维柯美学思想的部分。我们应当区分,维柯所探讨的“诗”并不是通常理解的狭义上有关文学的论述(包括但不限于诗歌、词),它是作为想象的产品出现的,那么相应的“诗人”也不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在想象中认识世界并且留下原始民族文明成果的人,此举显然把一般情况下“诗”的定义扩大了;另外,本文虽然意在研究维柯对形象思维的看法,但实际上维柯并未在《新科学》里明确定义。维柯认为,形象思维源于一种必要性,是基于原始人没有抽象概括的逻辑能力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另一种相对的方法,即转移或嫁接来实现认知。
维柯叙述了一些事实:最初由于生产资料受限,建造房屋时只得使用草、木等简陋的材料,这时“顶”和“木段”只是单纯用来指代房屋顶或柱子,而到城市兴起时,其可用于泛指一切建筑器材及装饰;再如屋顶不单指建筑物上方部分,后来可指整座房,其实类似的词义我国也存在,“但求片瓦遮身”中片瓦就是房屋的指代;还有关于工具的表述:“尖”可以指刀,“铁”同样可以指刀,前者是由于刀本身包括侧锋、刀身、刀柄(刀把),而只有前端尖锐的部分能够刺伤人,给人恐怖的感觉;后者则是由于无法从材料(铁)中抽出单独的形式(刀),因此能够作为隐喻或指代的部分。
维柯承认今人若需表达对精神事物的体会要显得比从前的神学诗人容易些许,像画家一样画出形象,借助想象来加以理解即可;但原始人没有这样的理解力,他们无法在抽象思维中准确捕获到两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形式并且完成置换,于是不得不采取相反的办法,仅仅将物体机械的叠加或是通过毁掉一个主体来使主体的形式分离。这是人类心灵的特点之一,即对待遥远且未知的事物时倾向于根据面前熟悉的事物进行相应的判断,因此会自然地认为一般物体也有感觉和情欲。接着他举出了很多语言上的例子:“首”(头)能够表示顶或开始,针是可以有“眼”的,壶“嘴”指器皿的一个具体部位等。
由于无知和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不自觉地把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面对抽象的、未可知的概念(或事物)时“诗人”们习惯用具体已知的事物来指涉,以上种种都表明维柯认为早期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是依靠形象思维来进行的,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祖先相比亦在不断进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原始的语言习惯却因此保留下来并成为文明的见证。
二、从诗性人物性格看形象思维的运用
我们应当有所察觉,维柯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截然对立地看待,这是维柯从早期人类思维特点出发来决定的。维柯认为原始民族相当于人生阶段中的幼年时期,逻辑思考的能力近乎处于缺失的状态,日常生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则是形象思维;不但“诗”起源于形象思维,神话、英雄人物性格、历史中一切有用的创造发明皆取自形象思维;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心智开始逐渐走向成熟,抽象思维能力越来越强,相应的形象思维的占比则逐渐减少,维柯对于两种思维的理解带有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看法。
在《新科学》中,维柯用梭伦来举例,在希腊历史中,雅典贵族党认为自己继承了神的某种天性,继承天神的占卜权;来源于野兽的平民,只有运用自然的权力。但梭伦却向普通民众传达一种平权理念:所以梭伦成为雅典平民中的“典型”。形象思维在制造某个理想的人物典型或范例的过程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原始人)将同类别中与这些范例相似的部分或者是具体人物都归纳其中,这属于一种惯用的方法。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维柯举出更多相关例子:“以同样的方式,一切关于社会阶级的法律都归到罗慕路”“一切与宗教制度和神圣典礼的法律都归到弩玛身上。”“一切关于军事训练的法律和制度都归到图路斯.霍斯提略。”[2]……
提道德拉柯时,维柯用中国的相关历史作为对照。赫拉克利族人在斯巴达建立的柏修斯国王盾牌上绘名为德拉柯的蛇发女妖,当人们盯着这蛇看时,他们将会变成顽石,于是“蛇”成为一种有象征意义的可怕刑罚。在“现今仍在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现今’的实际时间截至维柯写作的18世纪)”,“龙”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旗帜。维柯惊异于这样的巧合,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与荷马时代之初的雅典不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距离都相差甚远,却不约而同使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这不失为一场成功的创造。
事实上各个原始民族都习惯将各种制度、条文(法律)的创造,以及人类生活的有益发明都归功于一个人身上,形成所谓的诗性人物性格。它不像哲学那样抽象,但是维柯多次赞美这种智慧,它不仅反映历史上真实的动态实践过程,并且形成了早期人类文明认识世界的成果,是一座理想思维形式的丰碑。维柯回溯到历史源头看到形象思维中诗性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恰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维柯研究美学问题(主要是想象问题),不是过去美学家们就某一个静止的横断面,而是就发展过程的整体去看”[3]。或许维柯的初衷并非如此,但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确实就诗性智慧的论述扩展了美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路径,以潜隐的角度为这门学科提供新的精神启迪。
三、维柯与我国文化语境下形象思维的比较
“形象思维”一词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初从俄国传入,属于舶来词的范畴,但确实是我国熟悉的思维方式,因此一经传入就被国内迅速接受。当时许多参与讨论的学者在构建“形象思维”概念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借鉴了我国古代文选的相关思想或论述。李泽厚先生更是直接将《文心雕龙》中的“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似理应”作为《试论形象思维》的引言。
时至上世纪80年代后,其内涵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开始与意象相重合,齐效赋认为意象符号是“作家思维的主要媒介。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实质上是意象,形象思维的功能也应当是意象思维的功能。”[4]丁峻更是明确指出:“形象思维之定义应当得到完善与深化,用‘意象思维’取代之。”[5]
“意象”最早在《周易》中是出于哲学层面的溯源而非文艺范畴。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象”是指具体的事物或现象,它源于客观世界,也能够作为特殊媒介通过具体事物反映“意”的本质和内涵。魏晋时期王弼借老庄之道重新说明意、象、言三者之间呈现出的阶梯式次序:“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及:“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时他将艺术家和形象思维联系在一起使“意象”真正进入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围。在这里“意象”具体指涉两个概念,一是动态的思考范畴,主要指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二是处于静态的具体形象,即意象的生成。
意象的基础是客观实在的物体,在被迁入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带上个体情思。作为整体的概念意象显现出独特的民族质性,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将它拆成两部分,“象”是同一个物体,“意”在特定情境下其内涵将发则生相应的转换。比如,同样是桃花,在古诗中表现出了多种意象。《诗经》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最早将桃花和爱情联系到一起的诗句;唐寅慷慨吟诵道:“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借桃花隐喻隐士。此外桃花还有隐喻春天或显示悲愁苦恨等完全相反的情感等……创作者将主观情思迁入客观物象中形成意象,赋予意象更丰富的内涵并与形象思维一道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思想阐述与演绎。
要论及维柯与我国文化语境下对形象思维的分歧,首先是两者的目的有所区别。所谓形象思维,多是迁移的过程。我国的“形象思维”是将人的抽象情感迁移到具体事物中,使其成为承担思想或情感的载体,主要在于侧重表现;而维柯是将具象的概念(事物)迁移到抽象未知的概念(事物),作用是帮助理解,实现认知。其次两者指向的对象有所区别,维柯从广义上对“诗人”进行考察,实际表示的是早期创造文明成果的人,而我国由于主要在文艺领域展开讨论,因此具体指向艺术家、文学家等特定群体。最后,两者在形象思维的运行结果上亦走向不同的方向,如前文所述,维柯笔下形成了典型人物性格,而我国则归属意象的范畴。
维柯与我国对形象思维的研究都各有立足点,但两者相比较更有助于我们在广阔的视域中构建学科本体与方法论,正如韦尔施提倡的那样,应该让美学成为“一种更宽泛更一般的理解现实的方法……它使美学超越了传统美学,成为包含在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和伦理之中的全部感性认识的学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