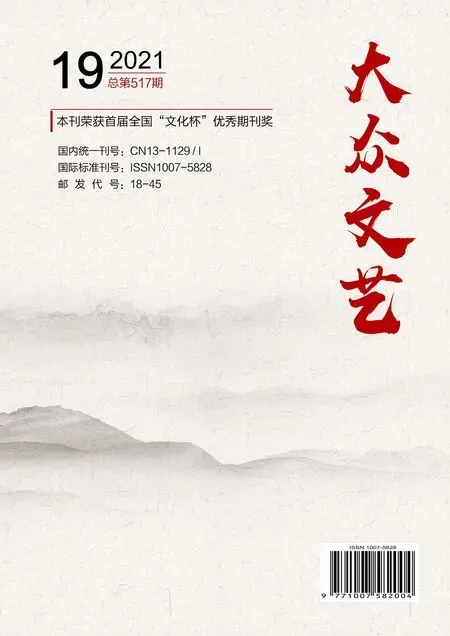略论创作中的灵感
陈梦希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00)
在长期的创作之中,常遇到的这样的状况:在绘画素材的搜集中,对景物的感受很平淡,没有创作的欲望,苦苦思索却仍无心创作。虽然殚精竭虑,却仍然在原地打转,绘制不出令人惊喜的作品,只能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技巧去完成一张画。然而,突然在某一个场景或是某一个闪念之下,茅塞顿开,对绘画无比热情,信马由缰地就能创作出极富感染力的作品。这时文艺创作的才能是从哪来的?这在柏拉图的理论中将其归因于灵感,灵感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1]。
创作者的灵感是如何产生的?在解决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的问题时常被提及。柏拉图的文艺理论就此做过深入的探讨,就灵感这一问题进行理性思辨的过程被后人总结为灵感说。灵感一词在柏拉图美学理论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概念,在西方美学的发展上影响深远。他用理性的思辨抽丝剥茧地揭露问题,将错误的见解驳倒之后,而推理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创造性工作离不开灵感现象,深入分析解读灵感与创作的关系,更能够有助于理解思维上出现的混沌不清的状态,从而以理性的态度合理的分析、指引艺术创作方向。
那么灵感和文艺创作有什么关系呢?创作者产生灵感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灵感的产生和创作者有什么关系呢?就此问题本文将在柏拉图的文艺理论中探寻答案。
一、灵感说
在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将灵感说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并进行深入的探讨。灵感在《伊安篇》的对话中被具体提出:“诗人是最初的环节,旁人都悬在这上面,有人从俄耳浦斯或缪赛俄斯得到灵感,但是多数人是由荷马凭附着,伊安,你就是其中之一。”[2]灵感通过神传给了诗人,诗人通过作品将其获得的真知和感悟传播给更广泛的大众。在这篇关于灵感的对话中,谈到了凭附一词(一如“赫剌克勒斯石”之链)。其中磁石代表着灵感,它凭附着第一层的诗人,诗人的作品凭附着诵诗人,而诵诗人的创作最后凭附住大众。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的理念中,文艺作品在创作者与观者之间起到了凭附作用,让每一层的人借此获得神所赐的灵感。
灵感带来的艺术创作有着很显著的特征。例如伊安在听到荷马的作品时就会滔滔不绝,而在听闻别人的作品时就会昏昏欲睡。这在柏拉图看来“原因在你宣扬荷马,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神的灵感。”[3]技艺在此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灵感在此时对于创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此,灵感在此时的文艺创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创作者体验到的灵感是什么样的呢?
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谈到“对所谓灵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4],在《伊安篇》中提出“第一种解释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他处于迷狂状态,把灵感输入给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伊安所体验到灵感的正是神灵凭附的迷狂。在《斐德若篇》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5]在此,迷狂状态和灵魂回忆是获得灵感的途径。
二、创作者产生灵感的状态——迷狂
迷狂是一种出神的状态,是来自灵魂的直接关照。如在文艺创作中,诗人在没有各种技艺的情况下,却能描述各种技艺,并且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感染,而此时创作的动力是从灵感而来。柏拉图认为灵感是神所赐予的,在文艺创作中,在迷狂状态中产生灵感,使得创作具有感染力。那么如何进入了这种迷狂状态呢?
在《伊安篇》中谈道:“当你朗诵那些段落而大受喝彩的时候,你是否神志清醒呢?你是否失去自主,陷入迷狂,好像身临诗所说的境界,伊塔刻,特洛亚,或是旁的地方?”“请问你,伊安,一个人身临祭典或欢宴场所,穿着美服,戴着金冠,并没有人要掠夺他的这些好东西,或是要伤害他,而他对着两万多等他友好的听众哭泣,或是浑身都表现恐惧,他的神智是否清醒呢?”灵感产生时,将诵诗人带入一个虚构的情境之中,这个情境不同于现实世界。
在灵感产生时,人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斐德若篇》中迷狂主要有四种:一种是预言的迷狂,一种是教仪的迷狂,一种是诗神凭附的迷狂,一种是爱情的迷狂。而不管是哪一种迷狂,都是达到这种状态的路径,在《伊安篇》中柏拉图把文艺创作的感人力量归结于诗神的迷狂,是柏拉图所认为的艺术创作的方法与灵感的重要来源。
首先,柏拉图在谈论创作中的灵感问题的时候,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不管在创作还是在欣赏,并没有人要破坏创作者的状态,而他为什么还会随着剧中人的命运而喜悦、悲伤、哭泣?这就是文艺作品中的世界并非现实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来说,纯粹的艺术作品是脱离现实本身的。就像诗歌通过吟诵,去除掉文字本身带来的影响,使其变得纯粹,以借助纯粹抽象的声音达到迷狂的状态;巫术通过纯粹的舞蹈肢体的动作,以动作为通道进入迷狂的状态。这种迷狂的状态脱离出对自我的认知,从而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其次,将通向迷狂状态的原因归为神赐,而此时的神力并不代表着迷信,而更像是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如祭司在祭坛上精神迷离地向大众宣告阿波罗神谕,在诗人为获得灵感进入迷狂之时,并没有像祭祀时处于精神迷离的状态,而是“进入了虚构的世界”。在古希腊文学中,神话又叫“Mothe”,在这一文学体裁中,神并非代表着迷信。而对于神的描写实际上是运用了夸张的首发深刻地表达了人们的思想和对世界的理解,神即是被夸张了的人,被神秘化了的人。而在迷狂状态的时候,实为人的特殊虚构的场域,而诗人就是人性中某一突出特点的代言人,是为了表达这一特点的工具。
我们继续在古希腊文艺理论中探索迷狂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其源自更原始的宗教和巫术之中。在古希腊更早的作品中,荷马的《奥德修纪》和《伊利亚特》、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等作品中都提道了需要诗神的凭附来获得灵感。古希腊的节日庆典上,酒神祭者在醉酒后吟唱出即兴诗,正是柏拉图总结出的这种迷狂状态的雏形,他从古希腊的宗教和巫术行为中总结出灵感说理论。而迷狂与灵感的关系在这种界定下逐渐清晰。
所以,迷狂的状态实为断绝与自身的联系,进入一个虚构的空间,在其中深入真切的感受人性的特征。而艺术作品就是将这种特征具象化、现实化的载体,所有在迷狂状态中的感知,最后都要以现实世界中所能理解的方式落实,以便让他人感知并理解。而此时虚构的空间中不必遵循现实世界中固有的观念及行为准则,这正是迷狂所体现的特征,即忘记物质性的我,不过分执着于自身。
三、灵感产生的第二种状态——灵魂回忆
柏拉图认为灵魂可以回忆起理念的知识,在其文章中解释称,灵魂在降入尘世之前就已经在非物质世界中看到了纯形式的东西,获得了有关万物的知识。但是在降生到肉身后又把它遗忘了,所以当灵魂在物质世界中又一次看见形式的事物之时,便回忆其被遗忘的形式。灵魂回忆时,创作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认为“人必须按照被称为理念的事物去运用理智,通过推理,把杂多的感觉统摄成一个统一体。这就是对我们的灵魂所曾见到的事物的回忆。那时灵魂随神周游,无视我们现在称作存在的东西,昂首观照真实的存在。”脱离自我对事物的认知,从而再去关照世界,这里所看到的世界是客观真实的存在。
柏拉图说:“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 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在此的“凝神观照”是一种理性的直观体现,它体现出几个特征:一、它是摆脱肉体的认知,去除对对象的杂念,纯粹的关注真实的对象本身,关照主体的灵魂,也就是关注纯形式本身;二、它是纯粹理性的认知过程,在漫长的认知下最后达到认识对象的本质;三、它是脱离经验世界到本体世界的过程,完成了对超验的主体世界的彻悟;四、这是一种审美的重置,用理性探寻对人性本能的理解。
脱离对主体的关照,对理性世界的认知在纯形式之下体现,即是脱离了主体的意志而关注客体世界的物性,理性认知客体世界中物的本质。理智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剥离开对对象的杂念,回到对象本身中来。
四、总结
艺术创作中的灵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复杂现象,但凡与创造有关系的领域,都脱离不了对灵感的把握。创作者通过灵感,脱离自我意识下的经验世界,进入超越经验认知的状态。这种对灵感的探究,不仅解决灵感的本质问题,通过灵感获得的途径让创作者清晰的了解获得灵感的目的是什么。不论是迷狂的状态还是进入灵魂回忆的状态,都是获得灵感的途径,如诗神的迷狂通过吟诵时产生的声音以接近迷狂的状态,巫术的迷狂通过肢体动作来接近迷狂的状态;在灵魂回忆中前世关于形式的记忆被唤醒,以形式关照世界,脱离经验世界的眼光去看待自身及万物。而不论途径如何,其最终的目的是殊途同归的,最终都是为了脱离自身的物质性,客观真实的感知现实世界。
在其中创作者能做什么呢?通过丰富自身对外物物性的理解,而消解经验世界所带来的偏见和障碍,通过不断的学习以达到创造所需要的追求。而学习目标并不是创造的根本目的,创造的目的在于先脱离自我意识,以自身的感受去寻找所要追求的形式,再用物性去吻合所追求的形式,继而选取创作所需要的技艺,最后以完成创作目的。其中的任何一环都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并不代表这是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而创作应服务于感受。作为创作者,灵感是创造中必不可少的存在,通过灵感可以感受脱离现实世界以外世界,从而完善艺术创作。艺术就是在创造,灵感说的最终目的解决了创造的方向上的问题,希望自己能在今后的创作中沿着艺术方向不断探寻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