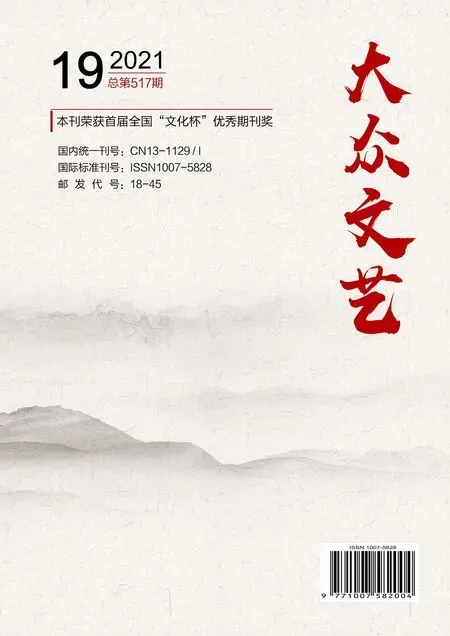从沈从文的五四精神看《边城》的生命意识
刘 斌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在中国,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可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以追问生命个体内在的主观意识、生命价值、生存和死亡的意义为主要线索,注重作为生命主体“人”的自我发现,并把“人”的本质力量提高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巨匠的沈从文,其创作无可避免地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无论是人生理想还是创作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可视为是五四精神的余波。先看人生理想方面,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边境地区参军的沈从文并没有直接地投身于革命浪潮中,但是五四运动的余波——“新书报”“文学革命意义”“新的社会理想”都给予了他“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从而为沈从文进京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改变了其生活环境和人生走向;再看创作风格方面,“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使沈从文意识到要创造出“适合与大众幸福的新的”和“适合于大众理解的”[1]作品,选择一种平易近人,贴合大众的写作方式,这种审美标准促进了沈从文具有个人特色的乡村抒情体的形成;最后,再看审美趣味方面,经五四文学精神洗礼后的沈从文认为文学应该坚持独立自由以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所以作家不仅需要有“清明合用的脑子”,还需有“自由运用的笔”,即秉持自由、独立与诚实的写作态度面向社会。沈从文代表作之一《边城》中的生命意识便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审美趣味。一方面,沈从文描摹着自然,纯真,质朴的乡村形态,展现人类原始的生命情感、力量、欲望与张力;另外一方面在挖掘乡土生命之根的同时,重新审视乡村城市化和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异变,试图重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可见,没有“五四”,就没有巨擘沈从文。只有考察了五四文学精神与沈从文作品的关系,我们才能对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一、自然景观的静穆构建
伴随着五四精神的蓬勃兴起,沈从文大量地汲取了“五四”民主、独立、科学、人道主义的理念,并将理念与他独特的生命经历相结合,对现实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溯源。表现在具体创作中,便是他在写作城市“问题小说”以反思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试图回归人类最原始的形态,将传统文化和记忆里的山水相结合,构造出一幅幅田园牧歌式的群像图。
在《边城》中,沈从文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为笔下一幕幕单纯和静穆的生命形态。相比同时代的鲁迅“冷调”式的口诛笔伐,沈从文把自己对故土、对人民的悲悯、怀念、深情以温柔而独到的口吻叙述出来,质朴而不失时代感,轻松愉悦而不失厚重。以沈从文茶峒为例,这里万物格外通透性灵,可爱至极而又亲切熨帖。在沈从文看来,天地万物同属于地球这个整体,都是生物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有其独特的生存意义,并没有高低、好坏、优劣之分,因此都可以融为他笔下的主角。如《边城》里描写白河:“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犹豫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做深翠颜色,迫人眼目。”[2];沈从文对景物的描写没有太多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大肆铺张各种修辞手法,而是以一个讲述者的口吻平静叙述。在他的眼中,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深潭、雨水、翠竹等都染上唯美的色彩,甚至是布满油垢,鱼龙混杂的店铺也变得可爱起来。
沈从文并不局限于平铺直叙自然的面貌或者一味阐述自己的主观意见,而是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上将挖掘自然山水的灵魂、内在价值、潜在的审美内涵与自身体内苏醒的生命意识、天地大爱完美融合,将文字的感性外衣与理性内核无缝接洽。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一方面,既彰显了其散文、小说丰富的审美意蕴,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自然万物勃勃的生命意识。
二、现实人生的群像描摹
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湘西大环境中,沈从文塑造了一系列不朽的人物形象: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和贫富等级,个性鲜明,活灵活现,却都追求平等自由,内心充满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命运的反抗和选择,充满生命力量,自觉化为五四精神的象征符号活跃在作者笔下。沈从文通过描述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作风,抒发了对不同生命主体的思考,足见其在人格塑造时思想的丰富性与深邃性。
在《边城》中,沈从文主要从外貌与性格两个角度塑造出了一个天真烂漫,活泼娇羞,健康善良的女性形象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眸子清亮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所以天真活泼。像一只小兽物,如山上的黄鹿,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看到陌生人就到水边玩耍去了。”[3]沈从文并没有采用具体的外貌描写,而是通过“黄鹿”等意象,从翠翠身上映现融湘西女子的共用特征——活泼、灵动、善良。翠翠年幼失去双亲,与爷爷相依为命,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她健康单纯的成长,所以当她面对动物植物时始终怀有一颗温暖的心,面对爱情时又羞怯自尊、心思细腻、坚毅执着。翠翠是沈从文笔下的一面铜镜,映射出现当代女性普遍所具有的对生活的渴望和对美好的追求,对爱情的反思与选择,渴望把握人生却又无法对抗未知的命运无可奈何的悲凉感。
除了主角以外,《边城》里的配角也都生动富有个性,并且分别代表着湘西劳动人民不同的优秀品质。例如老船夫翠翠的爷爷,沈从文通过对他撑船工作、待人接物等日常细节的描写,塑造出一个尽忠职守,善良勤劳的公仆形象;再如掌管码头的船总顺顺,有钱有势,但是并不盛气凌人,而是和气待人,乐善好施;就连岸边的妓女也怀揣一颗温柔善良的心,用爱和暖安抚着穿梭再死亡线边缘的水手……
沈从文认为,五四精神表现在人性上即是“天真”与“勇敢”,具体到作品中,就是创造出“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4]正如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所说:“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及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自然便老老实实写下去。”[5]
三、生存困境的死亡探究
《沈从文自述》一书中,沈从文详细记录了他的对生命意识的早期经验与社会知识。他最初接触“生与死”的矛盾与冲突来源于乡野盲目屠杀与从军的经历,使他得出“这给我一根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该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别一个人。”[6]的结论,唤醒了沈从文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怀以及最初的生命意识——生命的脆弱,生命权利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由生存和死亡关系进而引发到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是沈从文《边城》的创作灵魂所在。生存与死亡是生命意识两个重要的维度。生存是可能性的总和,死亡意味着生命所有的失去。生命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存在,正因如此,生命问题一直是作家笔下最核心的主题,是通死生较量冲突而向读者呈现出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审美体验。
在《边城》中共有两处死亡描写,一处是天宝意外溺水,一处是翠翠爷爷的离世,两个场景的写作手法和背后蕴含各有所不同,但是都表现了沈从文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从不同层面对死亡深度思考。
在天宝的死亡场景中,对爱情有着共同的执着追求的傩送和天宝为了表达对翠翠的感情,两个人于是约定遵照当地习俗,在一个月亮之夜,满怀真诚与勇敢地为一个“初生之犊”黄花女比赛唱歌。输了比赛的天宝竟然在几天后坐下水船时失足落入滩下漩水失去了生命。故事至此本应告一段落,但是老船夫的话“从不听说有水鸭子被水淹坏的!”陡然使得天宝的死亡意蕴变得丰富起来。死亡代表着现实人生生存权利的终结,但顽强的生命意识却没有因此戛然而止。在《边城》中,天宝虽然作为个体毁灭了,但是由他映射出来的执着、单纯、勇敢的精神却得以保存和永生。
相比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交代出天宝的死亡结局,在翠翠爷爷的死亡场景中,沈从文则主要采用了详细的环境描写,以白塔倒塌为象征,暗喻了生命的毁灭、命运的无奈和人物信念的摧毁。而后文,白塔的重新建立,又寄寓了宇宙再生的轮回性和生命永不流逝的希望。通过个体生命的不断产生又不断毁灭,显出世界永恒生命的不朽,给人的美感是痛苦与狂喜交融的迷狂状态。
沈从文对这两处死亡情节处理,是同他的理想寄托分不开的,他不愿让现实生活的丑与恶去破坏湘西人民原始的美与善,他需要通过“死亡”这一必然选择,来达到调和矛盾,回归真善美的社会理想。天宝和老船夫的死亡既是沈从文对人类生命的集中思考,又是他生命意识写作的成功实践。沈从文通过生存困境下的死亡探究抒发了人类的荣耀与尊严的终极价值诉求,生命尊严的独特价值在矛盾冲突中得到彰显,使全文获得史诗般的恢宏气象和宇宙意识。
五四运动的精神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正因为有了“五四”的历练,反思,洗礼,让沈从文脱去了狭隘的传统思想,“乡下人”的稚气和蛮力,为其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沈从文开放包容的理性态度,从传统文学中和自身独特经历中汲取营养,与“五四”精神紧密融合,塑造出独一无二的圆融的艺术风格。
对比“五四”运动后的政治文学,沈从文的《边城》基本疏离于正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外,而是对传统民间文化和五四精神的内核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始终保持一种单纯和静穆的理性回归精神。沈从文对生命意识这一命题的探讨与书写,不仅是对“五四”精神的变相继承,推进了生命意识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启示了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命形态的重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