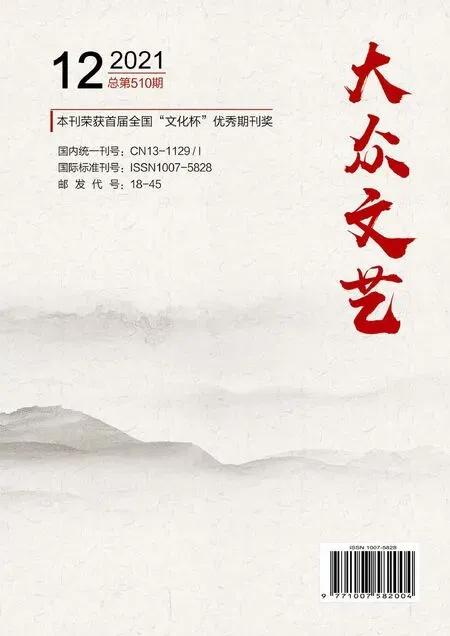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呐喊》《彷徨》中雪的意象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读《呐喊》《彷徨》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部颇具整体感和自足性的集子里,鲁迅运用乃至创造了大量“鲁迅式”意象,这些反复出现并带有强烈个人气质的意象在作品中形成独立的叙事空间。
一、鲁迅气氛:雪的情感内核
象内含意,意为象心,作为一种复杂的多面体,意象含混着自然、社会、历史、心理等多层面的意义,《呐喊》《彷徨》中的“雪”融合了“鲁迅气氛”,折射着作者的个体生命体验。
(一)雪与悲情气质
“雪”以其冰冷的物理属性弥散着浓郁的悲情气质,鲁迅小说发挥这一特质,借意象传递作者的忧郁心境。《呐喊》集内,“雪”唯一的出场是在《故乡》里,闰土向“我”讲述捕鸟的方法,因捕鸟只能借助下雪天气,“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初读此处,“雪”承载着童趣与友谊,似与悲情气质无关,实则雪景存储着“我”与少年闰土的欢乐记忆,多年后当成年闰土面色灰黄、恭敬地叫着“老爷”时,记忆与现实在隆冬交叠,加重了现时的悲哀,“我”对故乡的许多眷恋被驱散。正是鲁迅在《自序》里说的“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彷徨》里的雪则无一例外与严冬的肃杀构成一体。在《祝福》中,人物内心活动通过环境描写得以外化和加强,下雪的天气与主人公烦闷的心绪构成映射关系,反复出场后更形成“雪花意象流”,暗示着主人公的情感动向。伴着冬夜大雪,“我”回味祥林嫂饱受夫权、族权、神权摧残的生平,巨大的失落感铺展开来,最终在“团团飞舞的雪花”中,“我”仿佛看见受尽牲醴的圣众预备给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热闹的雪景是鲁镇悲剧的反讽,雪花飘落是“我”与鲁镇的诀别。《故乡》与《祝福》里的雪花承载着鲁迅深刻的悲悯情绪,既是对底层农民苦难命运的悲悯,也是对进步知识分子与故乡、故人隔膜的悲悯。
《呐喊》集内仅出场1次的“雪”在《彷徨》集中反复“飘飞”,这一明显变化更潜在隐喻了文本之外鲁迅主体情感的失落。1923年7月,鲁迅兄弟失和被赶出家门,同时肺病复发,从身体到精神皆跌入谷底,而叹“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耳”。次年春节,鲁迅连作《祝福》《 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三篇作品,显出抒情性的沉溺。
(二)雪与孤独心境
作为中华古典诗文中的典型意象,“雪”以其古典的躯壳包裹着先验的与经验的文化内涵,成为政治无意识的表征,以清冷孤寂的姿态跨越历史时空,映衬着面对黑暗开战、于绝望中反抗的先驱者形象,映照着先驱者内心的孤独。
《在酒楼上》精心织构了故人重逢的情节模式,漂泊者“我”在故乡遇到曾经的革命同道人吕纬甫,恳谈间却发觉少时眼里常闪着射人的光的他如今像蜂蝇般“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消尽了先前的锐气,仿佛一个认罪伏法的犯人。作为革命先驱,“我”与吕纬甫无疑都包含着鲁迅的自传成分,二人各执“漂泊者”与“固守者”的一端展开的关于人生状态的对话可看作是鲁迅内心两种声音的“自我辩驳”。这场辩驳是在大雪里做结的:“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寒风、雪片和黄昏隐喻着严酷的社会环境,也暗示了一场驳诘后“我”绝望悲凉的心境,但就是这看不到出口的绝望倒让“我”觉得爽快,决绝前驱——雪中禹禹独行着孤独的战士。
《孤独者》的情节模式与《在酒楼上》相似,雪的出场是在我收到魏连殳来信的夜晚.这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景象,一望无际的雪堆如同困陷在山阳县城的“我”精神荒原的对应物。在这样的雪夜,“我”想起了被孤立到走投无路的革命者魏连殳,随即收到了他的来信:“我这里下大雪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大雪穿透了时空的阻隔,将写信的魏连殳与读信的 “我”并置在同一个场景里展开了灵魂的对话,“我”最终失去了同行者,魏连殳放弃了从前的坚持,也为先前的自己所抛弃了。遥相呼应的大雪勾连起先驱者的寂寞。
二、有意味的形式:雪的结构创造
在叙事作品中,意象作为“故事的眼睛”点缀在各叙事单元,在重复出场中连缀情节片段,调节叙事作品的节奏,发挥着结构全篇的作用。《呐喊》《彷徨》中作为意象的雪出现了18次,在重复中实现着意义的递进和增添,推动小说层次感和节奏感的形成,并参与叙事模式的建构。
(一)雪的线索作用
《祝福》中雪的意象。全文虽按插叙进行,但梳理时间线索来看,第一次下雪是在祥林嫂重回鲁镇时,改嫁却夫死子夭的她被视为不洁不祥之人,在祭祀中被架空,“微雪点点的下来了”,这是悲情的预兆,在这点点微雪之前,祥林嫂已经历了一番夫死改嫁、出逃被抓、新家庭毁灭的悲剧,当雪花再度落下,柳妈和东家的避讳从精神处向她施压,神明将她的灵魂叛入地狱,肉身还要受两任丈夫的分割。微雪下落是祥林嫂走向末路的铺垫,预示了其承受神权压迫、走向精神危机的命运走向。第二次下雪是在“我”遇见形容枯槁的祥林嫂后感到不安的下午,大雪纷飞,“将鲁镇乱成一团遭”,雪势加大暗示着事态进一步恶化。最后,“我”听到了祥林嫂死去的噩耗,雪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雪花落地细微的声响仿佛就是这位旧农村妇女落地成尘的一点波澜。祥林嫂数次命运的转折都伴随着雪意象的出场,并且,当雪势越来越大,祥林嫂的生存状况就越来越糟糕。如果说祥林嫂逐渐陨落的命运是《祝福》里的明线,那么雪便成为故事发展的暗线,风景与人物之间是存在对应关系的。
同样的线索作用也表现在《在酒楼上》里,在这场感伤的重逢中,雪景伴随始终:“我”踏进酒楼,微雪已飞舞起来;吕纬甫的到来让楼上热闹起来,“雪也越加纷纷地下”,伴着废园的雪花,他向“我”讲述近况;二人别后,“我”独自朝旅馆的方向走去,走进了密雪织就的罗网。雪景闪烁在叙事的节点,不仅烘托抒情气氛,也连缀情节片段,控制着叙事节奏。
(二)雪与情节模式建构
作为线索作用的外延,反复出场的意象通常与小说特殊的情节模式相关联。在鲁迅笔下,雪意象就参与着其小说经典情节模式“封套结构”的建构。封套结构又称圆形结构,是指“把重复的因素放在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的开头和末尾,使这个重复因素起着戏剧开场和结束时的幕布作用。”[1]这是重复手法的一种特殊应用,在此种结构中,人物的行为与思想路径构成一个圆圈的循环。封套结构不仅具有结构创新的意味,更构成丰富的意义指涉。
在《祝福》中,故事的叙述在微雪中拉开序幕,交代了祥林嫂人生悲剧发生的背景,烘托了“我”归乡的沉闷心绪,而在结尾,团团飞舞的雪花为祥林嫂的人生画上句点,也终结了“我”的归乡旅程,首尾呼应间,从离去、归来到再离去,“我”对故乡人事的怀恋心态也变换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情绪,死而不僵的旧文化残影被封套在一冬的雪景里,加重了“我”与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旧人之间的隔膜感。《在酒楼上》中,故人的重逢同样是伴着深冬大雪开始的,在结尾的密雪和寒风中两人又各奔殊途,构成一个圆圈的循环,暗示着吕纬甫与周遭环境对抗而终究敌不过强大旧势力、回到原点的革命轨迹,也映衬着“我”挣扎于希望与绝望的轮回、对抗虚无的决绝姿态,深化了先驱者的寂寞形象。
三、诗化小说:雪与文体创造
诗化小说是诗歌艺术形式向小说渗透所形成的一种文体,在诗化小说中,“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色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2][4]。
(一)雪与叙事的象征化
“意象的运用,是加强叙事作品诗化程度的一种重要手段。”[3]受安特莱夫的影响,鲁迅的小说借助意象和隐喻,调和着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染上浓郁的诗化气质。
《在酒楼上》里关于“废园茶花”的描写是这方面的典型。小说对废园的描写共有三次,以第一次“我”在酒楼上独自赏雪最有代表性——几株老梅斗雪开着繁花,不以深冬为意,山茶树在雪中花开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段废园景象化用了 “红梅傲雪” 的古典意境,又融入了启蒙与斗争的时代主题。红梅和茶花是启蒙先驱的化身,它们在深冬大雪里赫然绽放、明艳如火,隐喻革命战士面对黑暗社会毫不屈服,甘于远行的游人则暗示着先驱者的孤独——启蒙对象对于被启蒙的态度是冷漠且排拒的。在小说中,大雪、老梅、茶花、游人统一于废园的意象系统,营造出红梅傲霜斗雪的审美意境,成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秘密通道。
(二)雪与行文的音乐化
“节奏作为诗歌的最原始的结构因素,是小说音乐化的先决条件”。节奏的本质是重复,密集性的重复总能赋予小说集中的主题动机、强烈的抒情效果、多样的节奏形式,“通过意象的重复,诗更接近音乐。”
在《祝福》中,雪作为一条暗线,映衬着祥林嫂的命运轨迹,随着雪势渐盛,主人公的命运渐衰。小说如同一曲主调音乐,雪意象在其中充当和声,处于衬托地位,或增强主调的气势,或削弱主调的回响,使乐章更富节奏感。《在酒楼上》《孤独者》表面上采用与《故乡》《祝福》相似的“故人重逢”情节,实则相去甚远。《故乡》和《祝福》中的“我”独处于主体位置,相对于闰土、乡民和祥林嫂,“我”在知识和思想上占有绝对优势,重逢故事是一场启蒙者对于被启蒙者的独白。而《在酒楼上》与《孤独者》里的“故人”不过是自我的分身与异化,两个主体在平等的地位中进行对话。如果把前者看作独白型的主调音乐,后者则更像是对话体的复调音乐,雪意象则联结起不同主体的感觉,使二者相互对应、产生对话,由此,小说的复调形式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在《在酒楼上》的开头有一段“我”对故乡的“雪”的评价——“我这时又忽然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尔后吕纬甫也有一句相似的话——“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这于返乡迁葬事件中宕开的一笔,或可看作是对“我”的看法的回响与反射,雪花成为双声部叙述的联结者。在《孤独者》中有类似的安排:“我”看着窗外大雪纷飞便想起了魏连殳,结果当晚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信的开头正是“我这里下大雪了。你那里怎样”,这种自然环境的呼应收到了蒙太奇的效果,将受到时空阻隔的两个主体牵连在一起,使得附于信件的精神交流顺利进行,一如两支旋律的汇合。如是,雪花的重复促进了鲁迅小说音乐性的发挥,加强其诗化特质。
论及《呐喊》《彷徨》的意象系统,研究者多关注作为社会文化符号被创造并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经典化的意象,而甚少观照自然景观意象,但细致体察鲁迅小说中的这些“风景”,我们发现,它们都或隐或现参与着作品内容与艺术的建构,这是有待继续发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