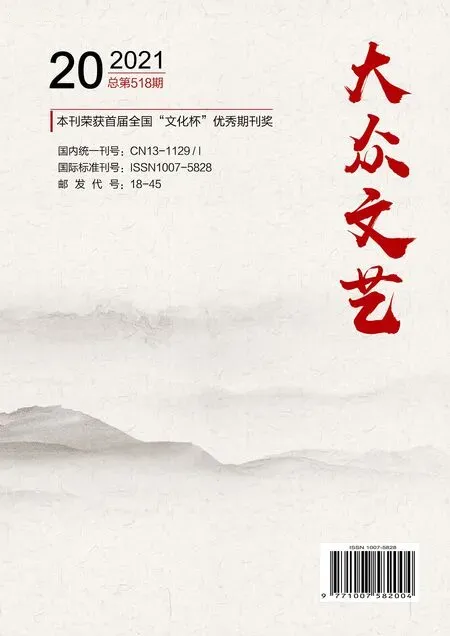从辞之“常与变”看董仲舒治《春秋》之法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徐复观评价说,董仲舒“由文字以求事故之端,由端而进入于文义所不及的微妙,由微妙而接上了天志,再由天志一贯通所有的人伦道德,由此以构成自己的哲学系统。”[1]其中文字大指《春秋》之“辞”,“辞”在董仲舒的春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将自己的观点寓于《春秋》的微辞中,他的思想体系基于对《春秋》和《公羊传》的解释,通过借事而明义,是非褒贬见微知著,创造性地诠释《春秋》的微言大义。
一、辞随事变的灵活性
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原则不是固定不变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2]它们有各自的适用范围,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看待。例如“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这四句话是对“大夫无遂事”“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闻丧徐行而不反也。”[3]的原因分析。对于大夫不可擅自行事,《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载:“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4]公子遂的任务是到京师,对“天王使宰周公来聘”的回聘,而事后他擅作主张“如晋”,这是《春秋》所贬之事。但是在庄公二十九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却解释说:“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一褒一贬形成对比。之后,对将士行军之中擅自返回之事也进行了对比,《春秋》襄公十九年载:“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而在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公羊传》解释:“其言至黄乃复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复?讥。何讥尔?大夫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公子结和公子遂同样是半途擅自行事,《春秋》没有批评公子结,因为公子结解救了鲁庄公的危难;批评公子遂,因为鲁僖公安宁无危。“故有危而不专救,谓之不忠;无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对晋国的士匄还师的行为赞赏,因为他不攻打有丧事的国家,是符合义的行为;就算父母大丧也只能徐行不返等待君命,更不用说公子遂因为生病就擅自返回了。“义具归本于忠君”,体现了君命高于一切,国事大于家事的原则。
董仲舒重视《春秋》灵活权变的特点之外,还强调权变的原则。“逢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在《春秋》和《公羊传》中,逄丑父假扮齐顷公,以自己的死换取了国君的生命,但是《春秋》却不与之。而祭仲在国家危难之际听命于宋国,将国君位让于当时的太子突,也就是后来的郑昭公。《公羊传》评释说:“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4]肯定了祭仲的权变之道。其中,逄丑父和祭仲都在为保全君主之命而行使权宜之计,但是《春秋》中对祭仲加以肯定,对逄丑父却不与之,这是为什么呢?董仲舒为此做出回答,他认为“是非难别者在此”,正是因为事件相似而情况不同,因此不可不察。逄丑父的行为是“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而祭仲却“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祭仲将其君置于贵重的地位,而不为后世所诟,“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而逄丑父却将去君置于低位,即使保全君主性命,但“《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因此,虽然“俱枉正以存君”,但“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董仲舒以逄丑父和祭仲的例子,解释了春秋之义。人非鸟兽,只为生存与利益而苟活,国君之命尤是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因此逄丑父虽然让齐顷公的生命得以保全,但是却置国君与耻辱的地位。而祭仲的做法是让忽去位,让其兄弟突继位,这样做可以使其君处于君子的地位,被世人赞许。
董仲舒对《公羊传》中四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分别做了解释。不同的行为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背景,具体环境不同,行为的合理性也就会发生变化,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得其私,知其指”所以说“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董仲舒对不同的行为作出了具体的判断和解释,他肯定了《公羊传》对《春秋》解释的变通性,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违反常经的一般原则,实施灵活性的权变。但是,权变也不是没有限定的,行为结果和动机要符合道义、荣辱才能算之真正的经权。不以生存为最高原则,而以仁义为更高标准。他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
二、辞有常义的原则性
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董仲舒提出“名伦等物”的概念,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苏舆注:“因伦之贵贱而名之,因物之大小而等之”。就是说《春秋》对于言辞很谨慎,按照名伦等物的原则。大小和贵贱不能混淆,尊卑不能颠倒。要做到大小不超越等级,贵贱遵守本分,“是故大小不踰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同言战争,天子、中国、大夷、小夷所用分别为执、获、战、伐四种言辞。首先,董仲舒认为《春秋》将天下人群分为四类,即天子、中国、大夷、小夷。“言外则小夷大夷不同辞,言内则京师诸夏不同辞”,通过用辞的不同做出夷夏和大小的区别。其次,大夷避中国,小夷避大夷,大夷和小夷有不同的回避的对象,说明大夷比小夷的地位略高。《春秋》中记载了发生在隐公七年的一件事:“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公羊传》解释:“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戎在楚丘俘获了凡伯(天子的大夫),根据小夷言伐的原则,可以看出戎为小夷。戎是己氏戎的后裔,位于今山东菏泽西南,后其地入于卫。此说明“小夷”则为“蛮夷部族”。《春秋》又在昭公二十三年载:“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髠、沈子楹灭,获陈夏啮。”陈国大夫夏啮被擒本不该言“获”而应当言“执”,但“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公羊传》曰“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吴少进也。”因吴国之“少进”,因此可以得知吴国原应为“大夷”,即“蛮夷诸侯”。从上述事例中可见,《春秋》重视在言辞上表达大小、上下、内外的等级尊卑关系。此外,用不同的言辞表达出华尊夷卑的尊卑关系,也在不同言辞的运用中起到寓褒贬的作用。
董仲舒说:“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虽然春秋之辞变换诡谲,但是董仲舒在变辞之中孜孜以求的仍是它背后所蕴含的不变的恒常真理。历史曲折无数,但董仲舒在探寻《春秋》中所展现的义利、荣辱、正邪、尊卑……这些不变的社会准则。
三、因辞见义的创造性
《春秋繁露》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董仲舒对僖公九年发生的里克杀奚齐之事进行解释。“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董仲舒解释说:“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富贵足矣,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尔!’录所痛之辞也。故痛之中有痛,无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齐、卓子是也;恶之中有恶者,己立之,己杀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齐公子商人是也。故晋祸痛而齐祸重,春秋伤痛而敦重,是以夺晋子继位之辞,与齐子成君之号,详见之也。”
这段话就《春秋》笔法而言,涉及晋齐两国祸乱。未踰年之君本应称子,但对于奚齐和公子舍都没有按照惯例。对奚齐称“君之子”,《公羊传》没有明确解释原因,对奚齐的褒贬也未明确。而董仲舒一方面为奚齐、申生、卓子无罪被杀感到痛心和惋惜,称晋祸是“痛之中有痛”;另一方面,苏舆认为董仲舒“代春秋责奚齐”,对奚齐“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给予了谴责,所以“夺晋子继位之辞”。对公子舍称“君”,是要贬斥商人自己把自己立的国君杀死的不义行为,称齐公子商人的行为是“恶之中有恶”。要“成死者而贱生者也”,所以“与舍成君之号。“《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就是对“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这一问题的间接回答。正因《春秋》无达辞,使“事”与“义”得以贯通。通过常辞与变辞的比较,可以彰显事件背后的义理,微言大义在其中显现,是非褒贬见微知著。
董仲舒认为读《春秋》的方法是要“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春秋》“精微妙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无所疑矣。”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的:“董子‘变’的观念要远比《公羊传》作者为重,对行权的范围也远较《公羊传》为宽,这与‘《春秋》无达辞’的话,关联在一起看,也是为了突破原有文义的限制,以便加入新的内容,以适应他所把握的时代要求以及他个人思想的要求而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