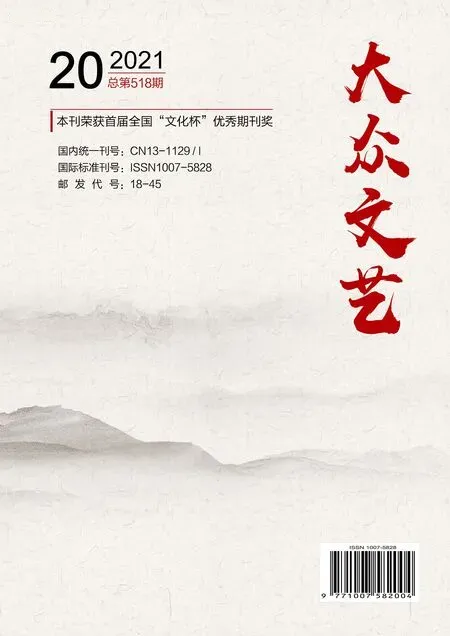三岛由纪夫《十日菊》论
——森丰子的过去与现实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十日菊》首次发表于1961年12月号的《文学界》杂志,翌年2月获得第十三届读卖文学奖(戏剧部门)。由于其以发生于1936年2月22日、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进程的“二·二六事件”为背景,所以1968年又作为“二·二六三部作”之一,与同样以此事件为主题的《忧国》《英灵之声》一起,由河出书房发行单行本。虽然同为三部作之一,但《十日菊》与事件之间,并未像其他两部作品那样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其描写的重点也并不在“起义将校”一侧。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十日菊》是三部曲中‘二·二六事件’出现的必然性最稀薄的一部”[1],以及“事件本身并非这部戏剧的主题”[2]。而在“二·二六”这一历史事件在作品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之外,《十日菊》也有着其他的解读角度:比如事件当晚,女主角奥山菊展示在“起义将校”们眼前的裸体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3];或是着眼于三岛由纪夫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近代家庭”,分析菊作为“年老”的女性,在森家如何扮演了一个从“帮助”到“支配”的角色[4]。
尽管已有的研究已经从男女主角森重臣和菊的角色出发,对作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但作品中其他的主要人物也同样值得关注。本文即拟从森重臣之女——森丰子这一角色入手,分析其与女主角奥山菊之间的联合与冲突,从而梳理出作家对女性角色“年老”与“年轻”的处理有着怎样的特征与倾向。
一、对于“过去”的直面
同样作为“二·二六三部作”之一,《十日菊》的情节和人物关系比《忧国》和《英灵之声》更为复杂。在“十·一三事件” (文中为“二·二六事件”的化用)发生的几天之前,作为“女中头”服务于森家的奥山菊从在部队服役的儿子正一处得知,青年军官们即将起义,而自己时任大藏大臣的主人森重臣也被选为了攻击目标。为了在不泄露消息的前提下帮助重臣逃过性命,菊答应了重臣对自己从其妻子进入疗养院开始便一直持续的挑逗,从而在事件当晚得以在重臣身边挺身而出,凭借自己的裸体吸引了军官们的注意,才帮助重臣逃得性命。而作为起义军官一员的正一在目睹了整个过程之后选择了自杀。此后菊便离开了森家,去乡下居住。十六年之后的当天傍晚,菊重新出现在森家,虽然本意是为儿子复仇,但在经历了一系列冲突和风波之后,菊又表示愿意留在森家,继续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情节逐步展开的过程中,除了作为“帮助者”的菊和“被帮助者”的重臣之外,重臣的女儿丰子也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第一幕第一场,在仙人掌温室中进行的父女二人的对话中,丰子作为话题的发起者,一步一步使重臣叙述了关于“十·一三事件”的过去种种,及其本人的失败的情感经历。虽然在重臣提到“你也曾有一次,对一个男人喜欢到要死”[5]时,她立即表示:“啊呀,不要说这个!”但结合丰子在接下来的第二场中的第一句台词,即可以看出她对于过去经历的态度。当家中众人从曾经的侍从长垣见口中得知菊即将返回森宅时,包括在内的重臣其他人都纷纷猜测菊的来意并对此表示担忧。而丰子的反应十分淡然:“不需要担心的呀,父亲大人。谁都会想用甜美愉悦的心情,将老旧的、恐怖的记忆重新回味一番的。”
也就是说,对于“回顾过去”这一行为本身,丰子的态度是理解和赞成的。之前对父亲提及自己过去的拒绝反应,也可以理解为作为女儿的羞涩表现。在后文中,当重高在菊出现不久便提及菊自杀的儿子正一时,丰子即刻做出的制止反应同样可以理解为对他人情绪的关怀,并非对提及过去这一行为本身的否定。
而丰子对于过去的开放态度,是促成了菊开口讲述其事发当时相关经历的关键要素。在垣见对曾经的事情表示出好奇时,也是丰子最为积极地劝说菊讲出自己的故事:“那就对我说说吧,阿菊。……我想从你口中听到。现在对我而言,唯一必要的东西就是真实。而我觉得今夜能从你的口中听见它。”可以说,丰子从结构上对情节发展的推动,正是建立在其积极面对过去、毫不回避的人物特性之上。
二、对“现在”的注视
在对“过去”抱有开放态度的同时,丰子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观察“现在”。
《十日菊》中的每一位主要人物身上,都“生活在‘过去’的威胁之下”。菊的“过去”是在“十·一三事件”中以“帮助”为目的而展开的一系列行为与后果;重臣的“过去”则是事件当晚被菊挺身相救的经历;重高的“过去”在于参加战争、最后又靠牺牲下属的性命来逃脱审判;而丰子的“过去”则在于失败的情感经历让她成了即将不如三十岁却仍是单身一人的“老姑娘”。
虽然整座森宅都笼罩着来自家中成员各自的“过去”的阴影,但其并未与社会层面的“现在”彻底断绝。在《十日菊》中,森宅被设定在湘南海边,其西侧则有群山坐落。在其中的山谷草地,经常有年轻的恋人们前往约会,或是在黄昏时分一起唱歌作乐。在前大藏大臣重臣看来,这些“T恤花哨、化妆花哨”的年轻人“都是没教养的东西”,而这种行为“恶劣”的年轻人又被其讽刺为“日本伟大的新时代”的见证。从重臣对草地上年轻人描述中,其对森宅之外日本战后社会现状的鄙夷和抗拒显而易见。
但同样对于山谷草地上游乐的年轻人群体,丰子的态度与父亲截然相反。菊到来的第二天早上,丰子做在庭院中眺望山谷时,对侍从长垣见表达了自己对远处年轻人们的向往:“那儿还有一对儿男女。……男人为什么对女人那样温柔呢?……即使离得这样远……那种温柔也会传达到这里来。……我把那片山谷草地叫作‘自然动物园’。明白吗?人类这种动物,就在那里放养,展示着最为自然的生态。有时乘着风,那些年轻动物们的麝香味道就传到这儿来。很年轻。这一个那一个都很年轻。那种年轻就像海风一样,就算吹到身上的时候还没感觉,但一会儿就要在皮肤上轻微又持续地留下讨厌的疼痛。年轻这种东西,为什么就那样了不起呢。”
虽然丰子连“散步的时候都未曾去过”远处这边年轻人聚集的草地,但她对其是不带排斥、乐于观察的。而接下来,丰子更是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我也想去看一次从庭院里眺望到的、对面的山谷的自然之美。”可以说,丰子尽管和父亲一样,都受制于自身“过去”的阴影,但对于宅邸外部目之所及的“现在”,她与父亲的态度截然相反。
三、“过去”与“现在”的连接与断裂
前文中我们已经对丰子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态度进行了梳理——丰子在并不回避“过去”的同时,对“现在”充满向往。以这种双向的积极态度作为基础,到了第二幕第十五场,丰子在脑海中终于形成了彻底摆脱“过去”阴影念头,所以才对菊有了这样的表达:“这家里的人全都腐坏了,谁也不会真正理解你的心情。他们都沉沉甸甸地坐在过去的椅子上,不喜欢你来摇晃它。……我听了你悲伤的故事之后,觉得是时候让家里的人睁开眼睛,从这过去的国度中逃脱,开始新生活了。”
为了能够“从这过去的国度中逃脱”,丰子首先强烈地要求菊的帮助:“你从什么地方拿来机关枪,将这个腐烂发臭的家里的人们杀个片甲不留就好。”但她并未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菊的帮助上。所以,在第三幕第三场,当五个年轻人为了冒险而穿越废弃的密道,从山谷草地进入重臣的卧室时,正独自一人的丰子毫不惊慌,在确认对方来自山谷之后,她主动表示:“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们。……把我从密道里带到外面去吧。……无论到哪里我都跟随你们。这个家里的人都无须在意。”而闯入者在惊诧之后,便以“测试”为理由,将丰子按倒在卧室的床上,轮流与其接吻。
就在丰子即将顺利通过“测试”之际,菊出现在了卧室中。她同十六年前帮助丰子的父亲重臣时一样,十分冷静地斥退了闯入者,从她自身的认知角度保护了丰子的安全。但对于丰子而言,菊的好心“帮助”完全破坏了自己冲出“过去”、进入“现在”的计划。菊将暗门锁上,甚至还将书桌搬去堵住门口的动作,正是代表“过去”的宅邸与代表“现在”的山谷草地之间的联系彻底断裂的象征。
四、作为“特例”存在的丰子
虽然从“过去”中逃出、与“现在”发生连接的目标最终在菊的“帮助”之下失败,但这一角色也恰恰因此成了作品中独一无二的“特例”。
正如前文中已经引用过的,森家父女三人和久违归来的菊都“生活在‘过去’的威胁之下”。但除了丰子之外,剧中的其他三位主要角色自始至终都被封闭在“过去的国度”中。重臣自从在“十·一三事件”当晚被菊挺身相救之后,虽然明知其无法重现,也一直想重温这一“立于荣光的绝顶”的瞬间。当菊时隔十六年再次出现之际,他又利用自己作为政治家的“狡智”,通过语言的“欺瞒”使菊又一次对自己臣服。而重高则一直苦于终战时出卖下属才逃脱战争审判的经历,将自己的“幸存”视为一种“背叛”,终日颓废而低落。在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重高从其死去的儿子正一身上得到了“灵感”,以上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于从笼罩自己的“过去”中得到了解脱。至于菊本人,则在重臣的花言巧语之下打消了原本为儿子复仇的念头,宣称自己要像过去一样留在森宅,为这里的人提供帮助。
也就是说,到了作品的末尾,重臣依然稳稳地坐在“过去的椅子上”,与之保持着平衡;重高在与之抗衡的过程中失败,被“过去”所吞噬;菊则在种种波折之后又回到了“过去”——唯一明确既对“过去”表示出抗争姿态,又对现实持开放态度,并将想连接二者的愿望付诸行动的,只有丰子一人。对于她这一行动的失败结局,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设定体现了三岛由纪夫的女性厌恶倾向:“没有将美的完成赋予丰子,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三岛由纪夫的。”但反过来说,虽然最终失败,但试图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抗争过程和意欲本身,即是丰子作为女性的超越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