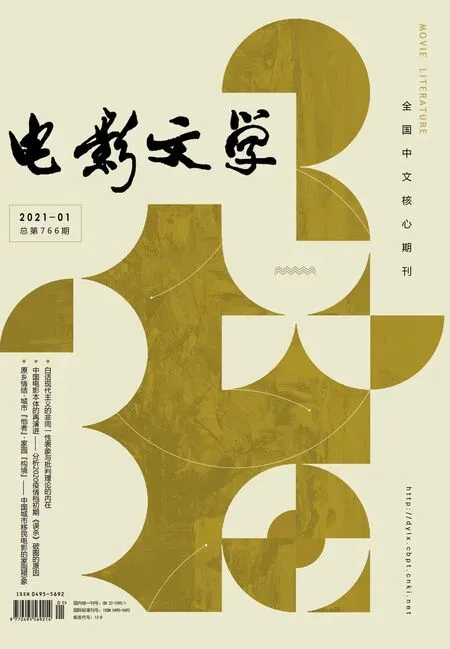图绘地缘机体
——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
刘靓婷
(中国美术学院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4)
小城镇电影作为一种亚类型的电影形式,其特有的“现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更为直接地理解为对底层现实生活的艺术化显现。小城镇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上别具一格的脉络,通过对底层社会的体察,把中国当下社会变革带来的最为尖锐的矛盾集中放置于城镇空间之中进行表述。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城镇电影创作,以“城镇化中国”的叙事路径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化的历史时空中建构了“中国”的想象共同体。随着电影创作和美学策略的不断多样化,“小城镇”作为一种空间意象被电影化之后,相较与地理意义上的城镇发生了衍变,转化为具有想象性的地缘语境存在,被赋予超越空间真实性更多的意义,进而成为带有审美倾向的虚构性能指。
一、地缘机体的集体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电影的版图中集中出现了一批以“小城镇”空间为故事背景的影片。不同于都市题材电影和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传统,在小城镇的叙事场域中找到了现代思潮与传统之间冲击与碰撞的交会点,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典型缩影:极具张力又带有暧昧色彩的文化中间带。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文化演变的基本走向,在以小城镇为叙事空间的电影中,导演们敏锐地体察到社会发展现实,以影像书写叙说小城镇空间的历史变迁与城镇人群的生命历程,用弥漫着强烈的纪实性与现实主义的批判,从不同层面挖掘、反思、想象并建构出“小城镇”的质感,从而形成了中国电影中带有明确地缘语境的独特话语空间。在小城镇电影呈现出两种面向:一种是向外的,拆解类型繁多的电影创作局面,用独有的艺术风格将自身与其他电影类型区分开来,绘制出底层群体特有的差异性生活图景;另一种是向内的,利用地缘机体语境的同一性,向内伸展出的具有话语权意味的公共文化权力空间,并形成了一个探讨群体共同生命诉求的创作路径。
如果把电影放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检视,认为不同时期的电影导演借由自身的特定观念以电影为媒介来构想现实的话,那么不同的观念就会造成不同的空间话语。第六代与新生代导演断然摒弃了第四代导演电影中乡土质朴唯美的想象,割裂了第五代导演电影中乡土的传奇化表达,秉持着对主流语境遮蔽下边缘个体的生命体悟的关注,转而将目光投注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生活境遇,构建出城镇地缘空间的艺术表述。在电影《二弟》的开头,导演运用了长镜头接镜头的组合方式,将城镇空间的压抑性填满二弟、大哥等底层人物的生活。电影中的作为静态实体的城镇景观不仅将人物的生活行径围困于其中,也构成了支配人物情感结构的空间再现。通过二弟在城镇的戏棚、码头与街道中穿梭游走的镜头,用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完成了反映生活原貌的表征效果。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地缘属性的空间实践,电影中的小城镇景观被前置,地域形态被直接作为故事的描写对象,借由长镜头不间断性的手法,将看似日常的、隐匿的、零散的城镇空间并置于小城镇人群的命运纠葛之中。在完成电影艺术生产的同时,也还原当下基层社会中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与传统意识之间抵触与矛盾的鲜活历史。
从电影叙事的角度来看,电影空间之于电影本身,并不只是作为叙事发生的场景而存在,电影空间在很多时候作为影片叙事的元素与推动力量而存在。“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行动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在《巫山雨云》中,开场即运用三种不同拍摄视角来展现三峡的平静苍茫风貌,以期与置身其中的人物躁动的、焦虑的情绪形成一种看似基于物质构成的个体经验,但是从深层次的叙事层面来看,又溢出了外在的物象与人物属性的表现,试图转化成带有强烈“中国”意味的城镇历史逻辑与集体记忆。在《秘语十七小时》的开场中,安排了一个固定镜头的段落,用夜间排档的喧嚣与人物的出场来营造出带有纵深感的小城镇空间特质。彼时,秉承着纪实美学追求的导演们运用大量的长镜头、景深镜头与固定机位,使得小城镇空间获得了纵深感日常生活的审视,获得了带有明显地缘属性的现实生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城镇电影都在讲述一个关于地缘语境下崩塌与重建的故事。在借用长镜头克制隐忍的意味,利用画面中视觉视点与听觉视点对可见空间进行立体定位,并置于纵向的时间轴上,从而制造出一种仿真的地缘空间。因此,小城镇地缘机体的出现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一次演进,具象的人类空间或共同家园的立体图景被有意识地投射在银幕之上,构成了具有逼真效果的全景影像表达。小城镇电影在获得了一种公共性的认同的同时,也完成了更为广阔而复杂的意义拓展。
二、被编码的现代想象空间
电影中小城镇地缘机体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标志性的空间呈现,借由空间中的实质性建筑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群形成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理位置,并且组合成一种集体记忆与观念认同的体验。由此,可以发现人类体验世界是基于日常生活体系下的符号编码形成的复杂运动。如果从媒介交流理论出发,电影中的空间营造使得观众不用亲临现场就可以直接感知到空间的存在。如果将空间的建构看作是“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那么小城镇电影中的空间生产正是地理学、社会学与电影学共同作用之下,在地理空间、电影空间、观众感知之间形成的想象关系,用体验与形成空间的审美方式完成了电影对社会历史记忆与集体想象的建构。

图1 小城镇电影生产关系图
这一时期的小城镇电影不仅具有类似的主题诉求,还在类似的题材中共享相同的影像术语来图绘地缘机体。小城镇的“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这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由此,也形成了对小城镇地缘机体描绘的两条主要路径。首先用概括性的表现方法,将小城镇空间中的近似的符号与细节加以选取、并归,成为特定的景观数据;其次,用符号化的方法,将空间中的特定事物加以再现,形成对物质空间的阐释,成为对电影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状态、生活状况等层面的直观表现。
爬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意象,我们发现小城镇电影中出现了极其雷同的景观符号,比如破败废弃的工厂、嘈杂艳俗的歌舞厅、昏暗狭小的录像厅、空间局促的集体宿舍等,这些其实都来自城镇灵魂的最深处,也是小城镇原有淳朴的价值观,及其伦理道德观念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侵蚀的、带有地缘意味的文化标志性符码,并为底层想象提供了镜像。如在《二十四城记》《少年巴比伦》《钢的琴》等电影中都有个重要的空间:工厂。从电影的总整体叙事结构上考察,“工厂”贯穿于整个电影情节的发展当中,作为一个特定的工业化的空间成为小城镇电影叙事的主要场景。以“工厂”为代表的异质性空间象征的是具有明确地缘属性与底层边缘属性的价值观念,抽去了关于现代化的意义,将这种工业化想象的逻辑映射为对城镇化甚至是国家意义范畴的构建,从而形成具有现代化隐喻的文化编码。在《钢的琴》中,生活中的一切都浸没在工厂的空间语境之下,对现代化夙愿以反现代的方式出现,形成对小城镇社会乌托邦式的想象。同时,又作为社会构成元素成为带有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改革风潮这一历史背景的符号特指。“工厂”的工业主义寓言与电影中小城镇人群生活的失序,通过调度与编排形成了特有的叙事空间,这也是小城镇电影从影像空间的层面坚执于其特有的人的属性、人格状态、生活方式等底层叙事,从而与都市电影、商业电影等主流电影模式保持了某种距离感。
小城镇电影的创作实践与中国当下的“小城镇”地理区位有着互为映射的内在联系。小城镇作为一种空间存在,在电影化编码之后,成为想象的景观,与地理意义上的“小城镇”发生了衍变,转化成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存在,形成对中国底层社会文化状况的症候式表达。如小城镇电影中集中出现的“街道”景观与电影中的漫游者和城镇空间形成了显形的构成关系。街道作为展现底层人群生活的微观空间,人物与象征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并置与狭小的街道之中,形成局促的视觉刺激,营造人物内心不安与焦躁的心理氛围。如《哭泣的女人》中,以“静观式”的长镜头通过王桂香日复一日地走在街道上的画面,勾勒出小县城边缘化的现状,以及与王桂香一样的底层群体彷徨而又焦虑的心理。此类街道镜头的拍摄多采用俯拍的长镜头进行具体的书写,借以形成冷静、沉重与压抑的语境空间,同时又经由电影人物在其中的活动轨迹,将带有符号性特质的景观转变成具有文化意蕴的空间呈现。在实践与编码上,电影中的小城镇成为艺术生产灌注和勾画的地缘机体,在获得额外的意义与实现导演设想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观念工具。
三、重叠的边缘性建构
将小城镇电影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发现此类电影中都呈现出具有完整意义的关注小城镇人群自我实现的愿望与困境的批判形态,不同于此前的小城镇电影创作中温情脉脉的情绪表达,90年代以来的小城镇电影采用了激烈的批判态度,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小城镇电影最为显著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指向,并表现出一种纵深的体悟。电影中的小城镇地缘机体景观所构建的叙事空间成为阐述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重要参照物,也形成对“边缘”主题的表达的重叠性路径:通过与“他者”叙述的互动关系中建构边缘化的城镇空间与边缘化的人物建构的两个面向。
首先,“他者”差异化叙述形成了对小城镇边缘空间分界面塑造中,现代与传统的重叠。通常在小城镇电影中通过极具符号性的景观表达,观众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具有明确地缘区域的经纬度矩阵。然而,在此类电影中还发现了另外一种空间建构的方式,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所产生的对比意味却惊人地相似,都以图用一个“他者”的城市意象来建立对小城镇空间的边缘性建构。在《背鸭子的男孩》中,有一段播放房地产广告的场景,用极度诱惑性的语言与画面,构筑了一个带有符号意味的现代化城市意象——“上海”,从而与故事中的小城镇空间场景形成带有戏谑意味的对比。在《米花之味》中缺席的“飞机场”一直贯穿始终。不论是喃湘露躲在门帘后偷听到大人们对“飞机场”的想象,还是置于电影后景中正在建造的机场工地,抑或是当人们去祭拜山神却被拒之门外时,头顶之上一架飞机从高远的天空中划过预示机场的建成,都与具有地缘属性的傣族村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完成了从个体空间到社会性空间建构的同时,也完成了小城镇处于破立之间所特有的人文景观。
其次,是通过对“他者”建构来形成边缘人物身份的重叠性,从个体生命历程中探求地缘机体下边缘性群体的存在意义。小城镇电影中的人物在经历了“伟大进军”的80年代、激进的90年代市场化改革和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渗透,置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的变革,内部文化重组与外来文化冲击的交错之中。在《二弟》中,以二弟的遭遇隐射全球化冲击之下传统道德范式所遭受的挑战。因为有着海外生活的经历,二弟的身份建构中同时存在着“他者”与“自我”的两个面向。在这种双重伦理困境的夹缝中生存的小镇人群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发展核心问题的缩影。在《小武》中,小武的第一次出场,穿着宽大的西装外套,戴着黑框眼镜,划着火柴,这种看似现代的装扮却与他的身型相比显出滑稽的效果,又与周围的环境呈现出不契合的状态。强烈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交错,营造出了商品经济社会中盛行的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文化状况。此时的小城镇不仅是通过电影镜头实现的空间实践,更是以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织为中介,以一种“间隙”状态呈现出来的带有强烈意识感知的、强调真实与想象并存所构成的“反乌托邦”空间。
小城镇电影的主旨是面对现代转型冲击之下城镇社群中人们共同的生命诉求,形成对民族审美体验和范式形成的深度思考。“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若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小城镇电影所指称的文化现场,显示了都市与城镇两种异质文化空间的对抗与糅合。导演们带有强烈纪实性的拍摄方式形成了某种目击式的、客观的、冷静的甚至近乎冷酷的影像风格。小城镇电影的边缘性表达形成的代码指称也出现了转变:一种是指代了在与地理学观念连接下,电影创作中所形成的新的底层叙述空间;另一种是在新的社会形态作用下,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中创造出极具空间化的社群,并以此完成电影人物形塑的现代性转变。因此,电影中明确的地缘机体界定了空间与人物的边缘性,这绝非是仅供消遣娱乐的艺术话语,而是面向时代断层时,与“当下”形成关照。
结 语
随着宏大历史叙事的坍塌,电影产业体制的全面转型,第六代与新生代导演已然无法再产生出具有宏大叙事架构的电影创作。他们将自己从现实中汲取的对于小城镇的理解不间断地灌注于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并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多元的生活经验。电影将散落在中国各处的小城镇以影像的形式搬上银幕,用图绘的方式完成了一种“地缘”的写作。因此,电影中的小城镇地缘机体并不是一个给定的实体,它可以被看成是地理学领域内的空间观转向想象空间观的介质,是基于真正的地理空间中人类事务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一种由文化建构的以多种形式被展现的时空产物。
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小城镇地缘机体的建构与表达路径,不仅是考察中国电影通过怎样的图绘方式来完成城镇空间的影像生产,更是在电影美学与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学等跨学科的交流中分析电影的文本内外,在辨析指意的过程中勾勒出对小城镇地缘空间的文化构建意义。通过对小城镇电影的研究与梳理,获得了地缘机体是如何形塑理解小城镇过去与未来的理解方式,这既形成导演们力图以一种趋近民族志的内在视点来表达小城镇世界观的实践手段,也是体认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认知范式,同时也探究了构建国家感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通过反复梳理与鉴别小城镇电影创作经验的同时,导演们致力于呈现怎样的地缘机体建构;基于当下经验的发掘,考察不同层面的力量如何将特定时空关系中的小城镇塑造为一个具有“中国”属性的地缘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