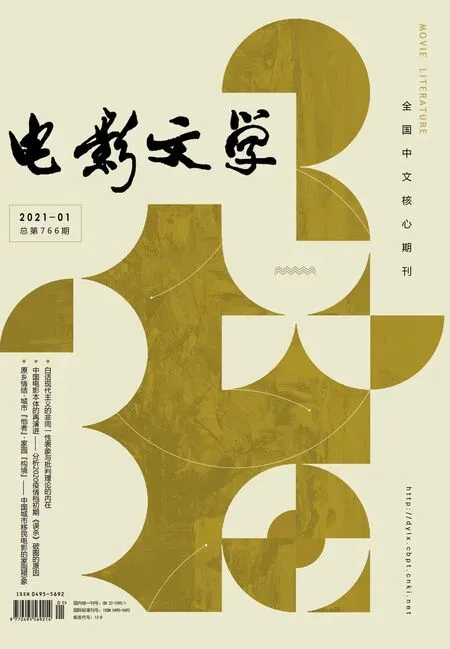从杨德昌的《恐怖分子》看电影的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
张 文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在无所不包的后现代艺术和文化中,叙事媒介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同时还包括影视、音乐、建筑等,电影也是一种叙事。本文所探讨的叙事审美形态,指的是从后现代主义观念出发的叙事审美类型,或者说是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电影文本中出现的叙事审美类型。新的叙事审美类型无疑是后现代主义的症候,同时也是对当下消费群体审美需求的回应。之所以选择杨德昌的作品《恐怖分子》来探讨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恐怖分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它聚焦于都市,影片中的台北不仅是台湾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这部影片可以被视为台湾语境中地方性与全球性交织的最佳例子。另一方面,《恐怖分子》(1986)产生于台湾的跨时代时刻,也就是戒严令解除的前一年。彼时台湾文化发展出现分水岭,政治高压下的文化生产即将结束,受制于市场和全球化影响的新文化领域出现,处于过渡时期的《恐怖分子》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种不同文化秩序的到来。
一、对传统叙事结构和主题的解构
杨德昌在《恐怖分子》中建构了颠覆传统的叙事结构,这种反叛性主要体现于非线性的交叉叙事以及多重寓意的开放式结局,这是电影典型的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之一。传统的电影叙事强调冲突或矛盾的情节,具有清晰的因果逻辑关系,强调戏剧化的效果。然而,《恐怖分子》以多线交叉叙事为主要特征,并不存在一条贯穿全片的叙事主线。杨德昌利用交叉剪辑以及平行蒙太奇的技巧,通过一起枪击犯罪事件将一组人的命运偶然联系在一起:欧亚混血妓女淑安在逃离枪战犯罪现场时被业余摄影师小强抓拍,之后爱上淑安的小强与女友分手,寻觅淑安的踪迹;淑安与母亲隔阂至深,被母亲囚禁在她的精神牢笼中;被禁足在家的淑安随意给陌生人拨打恶作剧电话,对李立中的妻子周郁芬谎称自己是其丈夫情人;周郁芬是一位作家,早已厌倦婚姻生活的她终日把自己禁锢在书房中,最终与初恋情人旧情复燃,家庭破碎的李立中陷入绝境。四条叙事线索,即有关李立中、周郁芬、小强和淑安的情节相互交织,同时平行叙事由此展开:李立中夫妇危机四伏的婚姻生活、周郁芬与情人的情感纠葛、小强与女友的纠缠、淑安与母亲的隔阂等。这种多线交叉结构具有各自叙事的轨迹,但又会在某个交叉点上结合在一起,呈现出立体的网状结构特征。《恐怖分子》也没有设定明确结局,结尾呈现出模糊性和多义性的特征。观众无法确定最后的枪声究竟为谁而鸣?是绝望的李立中枪杀了淑安和妻子的情人,致使恐惧的妻子瑟瑟发抖,还是李立中自杀身亡,似有心灵感应的妻子惊醒并开始呕吐?影片没有提供答案,因此,观众可以做出不同诠释,这正是后现代电影叙事的特征:“后现代电影叙事典型特征就在于情节最终拒绝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
《恐怖分子》还颠覆了主流社会的英雄叙事,或者说解构了英雄的主题。这部影片没有贯穿始终的英雄人物,也没有为英雄设定的重大任务,只有处处碰壁的中产阶级、游戏人生的底层妓女、无所事事的摄影师,每个人都是主角,都有各自的烦恼。杨德昌重视每一个角色的日常生活状态,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传递出的意义发人深省。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淑安为例,这样的底层人物竟然改变了其他人的命运:摄影师深深地爱上了她,与女友分手;她的恶作剧电话不仅加速了李立中婚姻的破裂,而且给予了周郁芬写作的灵感并使她一举成名,最终李立中陷入绝境。正是这样的小人物让我们注意到底层人物的心态,同时多角度地看到了物质发达社会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
杨德昌在《恐怖分子》中颠覆了传统电影的叙事结构,采用了多线性的复调叙事和不设明确答案的结局。这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多线条交叉复合叙事没有中心情节,其间断性、破碎性和异质性的特点会使习惯了因果联系的观众不知所措,但非线性叙事也能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有意地将不同的人物和空间串联起来,特别是各条叙事线上的独立故事能够形成富有张力的叙事网,为观众创造出多元意义空间,延长了观众的审美体验。同时,对英雄主题的解构有助于塑造形色各一的人物角色,放大社会和人性中的黑暗面,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对现实社会展开批判。可见,无论在叙事结构、故事主题和人物角色等方面,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都颠覆了传统叙事,打破了时空的统一和因果的逻辑顺序,创造出了更加多元的表达空间。
二、占据主导地位的空间叙事方式
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打破了传统的以时间为主线的叙事方式,突出了空间在叙事中的主导地位。鲜明的空间特征是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的典型要素。与时间相比,空间范畴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曾将这一现象追溯至19世纪的历史决定论以及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发展。米歇尔·福柯也曾指出,与时间的丰富性、多产性、鲜活性和辩证性相比,空间在过去常被视为僵死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然而,时间的优势地位在后现代时期已不复存在。时间性逻辑向空间性逻辑过渡,空间成为理解后现代主义经验的关键,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恐怖分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部影片从本质上而言是有关空间的,或者说共时的而非历时的,这不仅体现在多线并置的叙事结构上,还体现于影片描绘的每个人物的狭小空间中。空间在影片中不再是简单背景,而是关键角色,这使杨德昌的叙事方式显得更为立体化和空间化。《恐怖分子》中“空间”所传达的意义非常清晰,所有空间都显现出“囚禁”性质。无论是影片中男性还是女性的空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拘押囚禁的空间:李立中的洗手间、摄影师的暗房、妻子的书房、禁足女孩的家……空间的封闭性特征体现在每一个作为空间活动主体的都市人身上,他们相互隔绝,拒绝他人进入,被困在各自的精神牢笼中。可见,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并不能带来精神的自由。詹姆逊对《恐怖分子》空间性特色的分析显得更加高屋建瓴。他在《重绘台北》一文中另辟蹊径地指出影片中出现的各类空间与都市空间具有互文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影片中封闭的空间将台北再现为一套互相叠加的盒状住宅,里面囚禁了各式人物,这是对台湾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争取发展时面临种种局限的讽喻。詹姆逊从空间这一意义上对台北本身所做的讽喻性评论,是针对某种类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一个评论,即对“属于第三世界或太平洋边沿地区(日本除外)的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或者最近正在工业化的第一世界层次的国家和地区”的评论。在他眼中,《恐怖分子》是一部有关高度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都市的电影。且不论詹姆逊的寓言式解读是否出现了有意忽视台湾自身历史语境的误读,就空间这一范畴在电影叙事和文本阐释中的地位已可见一斑。
《恐怖分子》中的各色空间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具有多样性、重叠性和渗透性等特征,这些包含了物理的、文化的、心理的形形色色的空间形成了丰富的人物角色和城市形象。这些空间不断地交叉出现,反映出混乱无序的都市秩序以及现代人焦灼的精神状态。传统电影对空间的叙述多为背景叙述,但电影的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以空间化为主导特征。在空间叙事中,传统的情节和人物逐渐淡化甚至不复存在,线性叙事被各种巧合的时刻和交叉点所取代。或者说,空间对时间和历史概念发起挑战并占据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化”所指的空间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而不是那种旧的空间形式,也不是材料结构和物质性的空间形式,而是排除了深层观念的文字纯表面之间的捉摸不定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那种关系”。电影中的“空间转向”打破了时间性叙事的传统,模糊甚至取消了事件的因果联系,实现了叙事的同时性、多样性和延伸性,使观众不得不更加积极地参与作品解读,尝试从空间的角度寻求隐匿于影片中的联系和意义。
三、碎片化的影像拼贴
《恐怖分子》中的摄影师小强拍下了淑安的照片,恋上淑安的小强总是在暗房中欣赏她的巨幅照片(见右图)。那一张张拼贴的照片被风吹起,若隐若现的淑安形象早已拨乱了小强的心绪。这幅拼贴而成的巨幅照片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无论是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还是空间化的叙事模式,《恐怖分子》呈现出偏离传统叙事的碎片化特征。纵观整部影片,很难说清《恐怖分子》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影片开头的枪击事件一直没有发展成一个特别的叙事单元,这一单刀直入的事件也没有被赋予一个明确的结局。杨德昌的兴趣显然不在于揭开这个悬疑故事,因为对他而言枪击事件不过是发生于都市中众多事件的其中一个,它与中年夫妇婚姻不幸、底层女孩苦苦谋生、年轻人大胆追求艺术的事件同等重要。于是,枪击事件只是作为一个导火索引出了多条叙事线索。影片没有深入讲述李立中与周郁芬结婚前的爱情发展故事,没有交代摄影师与女友情变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揭示淑安与母亲之间出现隔阂的原因。这些通过拼贴被安排在一起的故事没有显示出因果统一的逻辑联系,人物形象的并置也没有产生任何明确的意义。可见,杨德昌没有过度依赖情节,他更倾向于依赖各种角色的并置来创造情感。
《恐怖分子》中被拼贴在一起的镜头没有暗示任何因果关系,这使观众无法将各个镜头联系成一个完整故事,这显然是一种取代了情节性的叙事拼贴: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许多拼贴在一起的片段,这些碎片使观众无法明白事件的前因后果,在认知上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拼贴是后现代主义的鲜明特征,詹姆逊曾用安迪·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来形象地描述这一特征。在《钻石灰尘鞋》中,单只摆放的高跟鞋毫无顺序地拼凑在一起,没有传递出任何意义。这些鞋是失去了所指的能指,纯能指之间的嬉戏产生了拼贴。后现代主义只是将没有关联的对象无端地拼凑在一起,无意产生新的内容,不过是一堆“东拼西凑的大杂烩”。作为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的拼贴经常出现在当下电影中,且表现出愈演愈烈的倾向,甚至出现了色彩、音乐、造型等各种形式的组装和拼贴。在飘忽不定的影像碎片中,意义被消解殆尽,失去所指的“后蒙太奇”效应由此形成。

(《恐怖分子》中淑安的巨幅照片)
《恐怖分子》多线并进的交叉叙事结构、对英雄叙事的质疑、对都市中平凡人物日常生活的关注、叙事模式的“空间转向”以及碎片化的影像特征,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传统叙事的颠覆,造就了这部影片在台湾新电影中的独特地位,它所蕴含的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发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先声。当然,这并不是说《恐怖分子》就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电影,更不是将之作为后现代主义电影的教科书,也不是要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要分析框架,因为这样的出发点会产生问题。《恐怖分子》具有自身的历史语境,它产生于新旧交替的戒严令解禁时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彼时的台湾都经历着重大变化,台北随即进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旧有的台北已经完全淡出,而是呈现出本土性与全球性互相渗透、叠合和杂糅的倾向。也就是说,当时转型中的台北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社会仍然具有本质差别,即使台湾已经非常开放且现代化,它依旧具有以本土文化和情感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如果将台湾自身的历史语境搁置一边,将《恐怖分子》定义为一部仅与后现代性相关的电影,只会使这部影片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注脚。严格地说,《恐怖分子》中只是蕴含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叙事审美形态。我们应该意识到,杨德昌并非有意在《恐怖分子》中卖弄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影片中的偶然性仍然属于现实的一部分,与偶然事件本身相比,杨德昌更关注的是偶然因素产生的现实影响和意义。忠实再现台北以及这座城市中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才是杨德昌创作《恐怖分子》的最终目的。这也是杨德昌一直以来的创作宗旨,即用电影来替台北画肖像。概言之,杨德昌在影片中所采用的后现代叙事审美类型是为了实现创作目的,而不是目的本身。
然而,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恐怖分子》来了解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当代电影文本中出现的一些新型叙事审美形态。后现代叙事审美类型无论在叙事结构、主题还是方式上都对传统叙事发起了挑战。非线性的交叉叙事结构打破了观众的观影习惯,但也创造出了多元意义空间;对平凡人物特别是边缘群体的关注解构了英雄叙事的宏大主题,拉近了电影艺术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叙事模式的“空间转向”使叙事不再依赖时间,实现了叙事的共时性、多样性和延伸性,促使观众积极建构作品意义;拼贴的镜头取代了情节,拒绝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这些审叙事审美类型的出现与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密切相关。大卫·哈维把20世纪70年代后期视为一个跨时代的时刻,此时后现代主义介入人们所能设想到的每一个领域,电影艺术亦不例外。电影的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作为一种新的叙事策略是主流文化适应后现代语境的结果,它在回应创作者创作激情和当代观众情感需求的同时,也在调整中不断演变和发展。虽然中国并未进入后现代状况占据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但某些艺术文化形态中已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后现代特征。我们不能无视和拒绝电影中后现代叙事审美形态的出现,但也要注意新叙事类型也应具备理性内容,正如《恐怖分子》仍然具备一定的现实指向,否则拼贴的影像呈现的只是碎片化的、高饱和的、偏离了传统叙事的符号,沦为一堆嬉戏的“飘浮的能指”,成为一场自我分裂式的视觉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