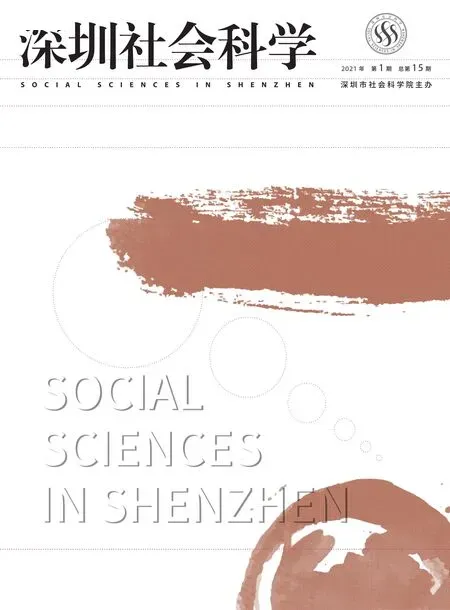非人类病毒:人类世的生命同伴与历史主体
阳小莉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10)
自2019年末潜伏到2020年初大规模爆发,继而演变为全球流行病的新冠肺炎病毒几乎成了2020年以来至今唯一的全球性事件,并且不可避免地主导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生命议题。与之相应,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封境、封城、封社区和个体的居家隔离,让我们在一种似乎前所未有的封闭物理空间和缓慢心理时间里开始思考和反思。从对国家治理和政策的反思,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合作与区隔,到野生动物保护更加完善法案的出炉,再到对后疫情世界经济、文化、政治格局等的演变的预测和讨论,它们都共同构成了此次疫情文化的主体。同时,对新冠病毒本身的生物学、医学、传播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也正在全世界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对病毒本身——而不仅仅是此次的新冠病毒——的文化和哲学意涵的探究以及病毒与我们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还尚付阙如。本文旨在从病毒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病毒的人类世特性,以及病毒如何形塑了一种新的历史性、时间感和速度感这几个方面对病毒与人类共生的生态伦理做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病毒与人类:敌人与同伴的辩证关系
(一)病毒作为非人类敌人
不可否认,当前围绕着我们与病毒的遭遇的话语充满了战争修辞。以笔者所在的美国为例,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对病毒的称谓都是将病毒视为敌人,对抗病毒所用的动词都是战争性语汇。这表明,人类与病毒的遭遇通常被人类理解为是与非人类的交锋和对决。从媒体上泛滥使用的诸如战役、攻防、战斗、阻击等战争/军事语汇可以看出,新冠病毒是被当做带给我们生存威胁的非人类敌人来看待的。更糟糕的是,随着病毒的爆发,人们甚至开始将野生动物统统视为我们的敌人。野生动物在抗击疫情期间惶惑、焦躁和不安的人心中俨然已经成了病毒的携带者和人类健康的破坏者。不止如此,很多人似乎也成了另外很多人的敌人。比如,人们将疫情震中的人,尤其是全球范围内将中国人或东亚人视为病毒的仇视和敌意至今也未曾减退。特朗普政治化、种族化病毒的所谓“中国病毒”更是让种族主义、仇视主义和国际政治等问题雪上加霜。在一定意义上,那些不知何故被染上病毒的人,那些被隔离的人,甚至那些还没有防范病毒意识的人,几乎都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正如电影《生化危机》系列表现的那样,电影中的人被病毒感染后突然就变成了有害物,他们没有权利再生活下去,而应该被消灭。
除此之外,我们日常性使用的诸如“战胜病魔”“打倒疾病”等语汇也是充满战斗性意涵的。尽管这样的战争/军事性语汇,从国家治理层面上,可以调动全民抗疫的积极性和团结性;从个人角度来看,可以起到增强意志、战胜疾病的效果。但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即在面对其他物种或自然灾害等非人类因素对人类的卫生、健康和生存造成威胁的情形下,我们总是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这些非人类因素视为我们的敌人。从这些被使用的战争语汇中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进化的“律法”下走在了这个星球进化史顶端的自信与狂妄。然而,也正是在同样的语汇中,我们作为人类也暴露了我们自己在面对非人类力量时的挣扎与无能为力。
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文明的生存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病毒的神秘和未知时产生的同样的自信与狂妄、挣扎与无力,也经常体现在我们对外星人和外星文明的想象之中。在电影《降临》(丹尼斯·维伦纽瓦, 2016)中,当12个贝壳状的不明飞行物悄然进入地球,悬浮在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上空时,人类立即进入警戒状态,各国军队严阵以待。对新冠病毒的未知和恐惧,如同电影中对外星人七肢桶的未知和恐惧一样,让人类立刻掀起生存保卫战。在语言学家路易斯和物理学家伊恩想尽一切办法破解外星人语言的奥秘,并试图理解它们意欲传递给人类的信息过程中,战争的神经愈发绷紧,几乎是一触即发。颇为有趣的是,在路易斯翻译出七肢桶外星人给人类的第一个词是“武器”的时候,人类以为外星人是在挑起战争的想法似乎被戏剧般地证实。为了阻止这场战争,路易斯与美军上校争辩,认为或许在七肢桶的语言中“武器”一词还有别的意义。也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遭遇外星人的时候,人类对于对方的未知和恐惧,便立即被转化为一种接近“敌我交战”的想象。不止人类自己这么认为,人类也同时认为外星人的目的也是一样——即它们的目的是入侵地球,消灭人类。《降临》中面对外星人时人类表现出的末日般的惊恐和全面备战的局面,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对抗与误解,与我们如今必须闭门不出,昔日繁华街道上只剩稀疏人影的科幻末日景象何其相似,又与媒介宣传中随时都可能升级的国家冲突何其类似。即便在个人层面,如齐泽克者在疫情早期表示想要站在武汉街头,去体验一番真实生活中的后末日电影场景,此刻或许也不得不隔离在家体验另一番后末日场景。[1]当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时,曾经的旁观者们此时已经成为亲历者。可以看出,病毒像一把双刃剑,它让全人类快速地凝聚起来,也在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我们之间的分裂。
病毒让国家、社会和个人,让人类与动物,让人类与病毒在不得不共同合作中发生接连不断的对抗与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类群体之间的隔阂,也加深了人类视病毒为非人类敌人的看法。这在保存人类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本无可厚非。但在人类与病毒对抗中形成的话语并不能完全被这样一种人类生存主义所解释。不可否认,病毒已经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而这一生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将病毒作为共同敌人的那个敌我范畴,而是更深地揭示了人类群体内部的分裂和我们对于病毒作为他者的无知。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换一种角度去思考病毒与我们之间可能的关系。试问,病毒真的就只是我们的非人类敌人吗?
(二)病毒作为非人类同伴
事实上,尽管我们目前对病毒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HIV病毒、SARS、埃博拉、新冠病毒等病毒性病毒上,绝大多数的病毒并不是敌人或杀手,而是在地球生命的起源、发展和维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病毒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它们无处不在,分布在海洋、环境、动物、细菌、空气和宇宙中,在我们的身体之中,甚至是我们基因组的一部分。[2]让我们暂时回到我们的身体上来。从已经是常识的生物学事实来说,我们的身体很大一部分是由细菌、病毒、微生物等非人类生命和物质构成的。病毒的数量通常以万亿为单位计,但由于体量实在微小,所以它们仅占我们身体体量的1%-3%。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构成“我们”的绝大多数生命和物质并不是所谓的“我们”,也并不属于“我们”,那么,什么是“我们”呢?“人”又是什么呢?
生态哲学家蒂姆·莫顿(Timothy Morton)在《人类:与非人类团结一致》一书中认为,我们应该从一种“内爆整体论”(implosive holism) 的角度来看待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己。“内爆整体论”从我们的身体内部出发,去尽可能地认识那些构成我们的非人类物质和生命,去发现我们与非人类的它们无法真正地区分开来。进而从根本上反思我们,或者是作为“人”的我们可能是或者原本应该是什么。[3]从“内爆整体论”的理论视角来看,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区别遭到了质疑和挑战。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内爆的多物质聚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就是非人类,非人类就是人类。而那些真正构成我们作为 “人”的生命和物质本身就是多样且丰富的。人之为人本身就意味着成为一个多生命体和多物质的集合。人并不是一个拥有独特智力、情感和意识的单一实体,而从来都是一个多重生命的聚集。因而,即便从生物学意义上,人与病毒无法切割,也无法区分。人类与非人类从我们作为人这个事实上来说,从我们的身体构成上来说,并没有界限。
对莫顿而言,“内爆整体论”形象地展示了人类与非人类在人身体之中的一种美妙的共存和团结。这种团结,在莫顿看来,不仅仅只有生态伦理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于一种“生态共产主义”(eco-communism)的理解。莫顿整本书的基本论述就是用一种生态哲学的共存和团结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要指出的是,莫顿的“生态共产主义”是一种更加美学和体验意义上的,而非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尽管“生态共产主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意涵。作为对象导向本体论者(object-oriented-ontology)的莫顿,坚持对象导向本体论者代表人物格雷厄姆·哈曼所提倡的理念,认为“美学是所有哲学的基础。”[4]因而,莫顿的“生态共产主义”并不是一般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治行动或者社会理想,而是一种美学、体验和情动意义上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体验。病毒存活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并作为构成人类之为人类的非人类物质,这本身所唤起的对于生命和美学的体验和感受就是一种共生愿景的实现。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生态共产主义”业已实现的蓝本。尽管我们目前还继续遵从现代生物学分类将自身视为一种“智人” 的有机物种,但人与病毒的共生现实,从根本上已经颠覆了这种生物学分类法。诚然,人与病毒在生命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但这差异本身,对莫顿来说,不能构成理解我们作为人的本质的唯一基础,也不是区隔人与病毒的鸿沟。
事实上,从人类与病毒遭遇的历史来看,即便侵入性、带有强病毒性的病毒最终也并不是为了消灭人类。我们目前往往诉诸的最惨痛的关于病毒的历史记忆是中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尽管当时黑死病杀死了欧洲将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病毒却并没有完全消灭人类。因为从病毒本身的生存来看,永远需要宿主的它们,必须学会与人类共存。它们本身无法离开宿主而单独存活。因而,为了自身的保存,病毒也必须保存我们。反之,对于人类也一样,我们保存自己的一个方面其实也是保存了一部分病毒在我们的身体之内,让它们与我们共存。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和生存有益,如这次的新冠病毒。但我们作为似乎更有力量的人,也没有能够阻止病毒进入我们的身体,并听任它们与组成我们身体的其他生命和物质碰撞、结合并发生无数次我们并不知晓的反应。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又必须承认病毒本身具有强大的生机力。它们能够从动物的身上转移到我们的身上,这种跨物种生存的能力是应该让我们惊叹的。病毒的生机力也正体现在它们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上。
对物质的生机力(vitality)的理论探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政治哲学家简·本尼特(Jane Bennett)。在她那本著名的《充满生机的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中,本尼特提出了“生机物质主义”(vital materialism)这一概念,认为“物”不能被简单粗暴地视为呆滞物质或是消极事物。相反,“物”拥有自身的“物—力”(thing-power),而且具有自身的习性、轨迹或是倾向,并拥有可以参与政治行动的能动性。[5]在本尼特的政治生态学中,任何一种物质,不论它是有生命的或是无生命的,都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政治潜力。比如,一段木板,一堆垃圾,或是一条虫子,一个病毒,作为非人类的物质,它们长期被排除在政治能动性和参与的考量范围之外。本尼特反对长久以来以人类行动和事务作为政治哲学表述的唯一中心,希望通过对于物的政治潜力的肯定,去认识到非人类物质对人类的政治和生态意义,也将它们纳入我们对于政治思考的范围之中。
尽管在该书中,本尼特的理论探讨基本未涉及病毒。但笔者认为,本尼特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生态学理论有助于理解我们与病毒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与新冠病毒博弈的这几个月中,我们无法不承认病毒本身所具备的超强生机力。作为一种在生物学意义上或许并不那么成熟的生物体,病毒在一定程度上以其强大的生机力极大地暴露了我们作为生物体的脆弱性。不仅如此,病毒也暴露了我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在应对它的降临时的无所准备和不堪一击。似乎是大多数人生命体验中的头一次,一个非人类病毒搅乱了人类社会长时期以来建立的一种看似牢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看,病毒本身的生机物质力和政治能动性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已经完全展露出来。病毒,作为一个长期被我们置于政治参与考量之外的他者,却在我们意想不到的今天构成了我们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体。这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本尼特的政治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人类已经不再作为政治生态学的主要或是唯一主体,而是已经与非人类物质构成了一个拉图尔式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其中,非人类他者与我们一样具有政治行动和参与的能动性,并同样构成具有政治参与能力和具备政治影响力的一个行动者。从新冠疫情的发展来看,认识到这一点也变得极为迫切。因为这将使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对于非人类因素参与我们的整个社会建构的可能性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也需要为此做出很多必要的准备,也即,将非人类物质对我们可能的影响考虑到比如政治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组织合作等政治行动和规划之中。
另一方面,在保存自身生物体生存的情形下,我们却又不得不将病毒作为我们的敌人来对抗和打击。而这一点也暴露出了本尼特政治生态学理论内部的局限性。因为在她的生机物质理论中,对非人类物质生机力和政治潜能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是要释放人类对于非人类的爱和价值的肯定,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将具有生机活力的物质认为是好的或值得被爱的。在该书发表两年后的一次访谈中,本尼特特别提到HIV病毒。当面对HIV或新冠这样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病毒时,她说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爱HIV,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爱HIV。它和人类的痛苦太过密切相连。尽管如此,它的生机力仍然值得尊重,比我们直接杀死这个病毒值得更多的尊重。更有效的疗法可以将它的病毒性降低,使得人类和非人类的共生成为可能。”[6]为此,她提及很多具有生机力的物质都可以对抗HIV, 比如避孕套、实验器材或者调整人的身体进行性行为的具体方式等。“本尼特这种完全拥抱式的 ‘生机物质主义’需要我们拥有巨大的感受力和同理心,在判断善恶、好坏、痛苦与快乐之前,我们或许最应该做的是去尊重物本身,去尊重它们的生机力,用尽可能好的办法去维持人与物共生的事实和愿景。”[7]对病毒所怀抱的感受力和共生之感,显然也无法抹除病毒对我们造成的痛苦和死亡。我们在看到生态共生理论令人欣喜一面的同时,也在实际生存中遭遇到无法完全经受伦理检验的困境。
总体而言,不论是莫顿的“内爆整体论”,还是本尼特的“生机物质主义”,都让我们去反思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我们,非人类物质与生命与我们的关系如何,以及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一种与非人类共生的方式。我们与病毒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敌对的,又是共生的。正是在这种人类与非人类、人类与病毒的辩证共生关系之中,病毒是我们的非人类敌人,却也在同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同伴。病毒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携带着它们,被它们护佑,同时也被它们威胁。因而,与病毒遭遇,并不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零和博弈,而是寻求相互成就、相互共生的一个物种间的合作过程。
二、人类世病毒
在本体论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与病毒处于敌人与同伴的辩证关系之中。然而,从SARS到新冠病毒,我们都意识到它们的到来,与其说是它们入侵了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而不如说是我们逾越了限度,首先招惹了它们。由于我们大量且无度地买卖、消费野生动物,病毒就不断地进入我们。①尽管最新研究已经表明武汉华南生鲜市场或许并不是病毒的发源地,但病毒与其可能的野生动物之来源的关联尚未解除。因而,我们与病毒的遭遇是显著的人类世时刻。仅从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几次大型疫情爆发来看,SARS,埃博拉,寨卡,中东呼吸症,H1N1和新冠病毒,都无一不是从病毒从动物到人类的一次次溢出(spillover)。这种动物传染性疾病(zoonotic diseases)尽管在流行病研究中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的加速流动和商贸的频繁所带来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连接,也拓宽和加大了病毒扩散的渠道和可能性。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表明,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是森林采伐的加剧和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会导致很多动物性疾病向人类群体传播。[8]再加上,很多失去了原本栖居地的动物被迫涌入我们的城市环境中与我们共存。但不友好的城市环境,也会进一步加速动物性病毒往人类群体中跳跃和扩散。事实上,尽管没有完全直接的证据表明是气候变化导致了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但正如很多报道者和研究者都表明的那样,引发疫情爆发的原因就跟生态环境本身一样复杂。这里面或许并没有一个所谓一对一的因果关系,但诚如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所说,新冠病毒只是我们破坏自然的后果的冰山一角而已。因为人类活动,诸如修路、采矿、捕猎和砍伐,都会造成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平衡的打破。[8]
恰如罗布·尼克松(Rob Nixon)所说,生态灾难往往是极其缓慢且通常是不可见的,可它所带来的很多后果却是充满暴力的。而且这种“缓慢的暴力”是极度深入和持久的。[9]尼克松所称的这种“缓慢的暴力”在新冠疫情上也有所体现。尽管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传播速度极快,但它却是生态环境长久遭到破坏的一个症候。毫无疑问,新冠病毒是人类21世纪以来加速活动的后果之一,而它的暴力性在那些已经死去和正在经历痛苦和死亡的人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除此之外,疫情对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暴力冲击也还处在正在进行时。而这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心力去弥补还尚未可知。
我们必须很悲哀地承认:人类世,这个用来命名人类的活动和生产已经超越了地质力量、并自身构成一种地质力量的世代,并不是用来恭维我们自身的强力的。恰恰相反,人类世也意味着人类必将在一个由人类强力主导的地质时间和历史中遭受同样、甚至是更大强力的反噬。这个反噬或许来自病毒,或许来自地震,也或许来自几千亿只已经在亚非大陆迁飞了一两年的沙漠蝗。而病毒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人类世病毒。
人类世病毒已经和将要带给我们的人类世时刻,在可预知的将来,必定是连绵不断的。此次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或许需要面临的一个更可怖的事实是,更多的未知病毒会全面进入我们的身体和生命。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高纬度高海拔寒冷地区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显然,冰川融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很多国家和人群必将流离失所,全球人口必将发生大规模迁移和重新安置。除此之外,更可怕的是永冻层的融化。永冻层融化释放出的甲烷、二氧化碳和无数未知的、甚至是史前病毒、细菌和真菌都会变成潜在的病原体。[10]而它们一旦被大规模地释放出来,就会感染并威胁我们的生存。人类或许有一天会最终毁于病毒,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世病毒呈现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极度悖论的意涵。当人类的强力足以改变整个生物圈的物理化学状态,而同时,我们将注定遭受与我们的强力同等或者更大的来自这个生物圈的反击。
三、病毒作为历史主体:逼近一种病毒的历史性、时间感与速度感
后殖民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在他关于历史的气候的论文中指出,将人类考虑为地质力量就会打破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之间的区分,进而强迫我们进入一种新的历史性。他认为,将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区分开来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是斯大林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1939)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解读。尽管斯大林承认,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一个持续且不可分割的条件,但认为它的影响力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力。查卡拉巴提指出,斯大林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历史的理解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中非常普遍。也即,查卡拉巴提总结道:“人的环境确实改变但改变如此缓慢,以至于人类历史与他的环境的关系基本上是永恒不变的,因而,人的环境完全不构成历史学的主体。”[11]但如今,问题已经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单纯互动”,而是“人已经被认为是地质意义上的一种自然的力。”[11]换句话说,关键已经不再是人类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幻,而是人类对环境改造的影响已经可以与促使环境自身改变的地质力量相当,甚至是更大且更有破坏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可能再依循长期以来以人类社会、文化为核心的书写,因为人类历史已经镌刻进地质的岩层和活动之中。因而,如查卡拉巴提所言,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不可分割。而这,便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的人类历史书写和人类对于时间的感知。在这种新的历史性中,自然(地质)时间、人类文明时间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时间交叠在一起,无法剥离开来。
这种颠覆性的历史性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新的时间感的产生。在我们为了对抗病毒,将我们自身、社群与外界隔离,进而让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几乎停止运转的时候,病毒时间开启了。当病毒在全世界扩散时,全人类不得不处于同一种时间:病毒时间。这种病毒时间,被延长成人类煎熬的每分每秒,也同时被缩减为病毒肆虐的争分夺秒。这种病毒时间的强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悬置了人类构建的生活、社会和历史时间。后者几乎已经完全被前者取代和改变。在病毒进入我们身体和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入了一种由病毒塑造的时间感和书写的历史性中。我们无法拒绝,也无法逃逸。因此,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不可分割,不仅仅是人类活动构成了自然历史和变迁的一部分,而自然历史及其变动也反过来塑造人类活动,构筑人类的时间体验,并书写人类历史。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
病毒时间所创造的时间感,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或群体独有的,而是全球性的、地球性的。这也可以说,人类世病毒为我们重新设置了一个行星时间(planetary time)。这个行星时间把人类拉入一种星球存在。其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只不过是偌大星球上的一个物种而已,哪怕我们看似暂时位于其中的高位,这个星球上仍然有那么多的生命、物质和地质力量可以轻易地伤害乃至摧毁我们这一物种。对人类来说,这也毋宁说是一种末日时间(apocalyptic time)。 齐泽克在讨论我们在末日时代的生存时提出末日时间和末日节点。他认为,“有三个末日节点:生态崩溃,生物基因技术将人类降格为可操作的机器,以及我们生活的完全数字化控制。在所有这些水平上,事物都在接近零点,‘最后的时刻正在逼近’——此处,是爱德·埃尔斯(Ed Ayres) 的描述:‘我们正在被某些事物所撞击,因其完全超出我们的集体经验之外,我们看不见它,即便种种迹象已经相当明显。对我们来说,那个‘某些事物’就是一阵闪电般的生物和物理变异,它们正发生在一直供养我们的世界之上。’”[12]齐泽克引用的埃尔斯恰切地描述了这样一种变幻莫测的临界状态。同时,这也是一种极度迷茫状态,它超出我们的集体经验之外,我们似乎也并没有看见它潜伏着的危险和它不时发出的警告,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与我们面对病毒的入侵一模一样,看不见病毒在何处,因而茫然无措。病毒先是寄居于非人类动物身体,进而走进人类的躯体和社会,而这只是星球性生态崩溃的冰山一角。或许我们最需要反思和担忧的是,在与病毒的每一次交锋中,我们不一定总是那么幸运。我们的科学和医学不会完全真的杀光它们,它们会像幽灵一样环绕着我们,等候着更好的时机,再次降临人间。
病毒不只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时间感,也创造了一种新的速度感。目前,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不得不被同质化成同一种速度:病毒速度。对病毒变异、扩散和蔓延速度的感知超越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交叠了我们生活世界的各种速度,比如新马克思主义加速主义[13],全球化信息网络传播速度,甚至是地球污染的速度。[14]而后面这些社会和政治速度都在此时受到病毒速度的制约,并被病毒速度所形塑。不仅如此,病毒速度也在,更准确地说,是在加速一些速度形式的兴起。比如,机器人送外卖、快递小哥送包裹的速度。这些存在于病毒突然降临之前的社会生活秩序中的速度,被病毒速度带动着加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病毒速度进一步带动了科技速度统御我们生活的节奏。这也是病毒速度本身的悖论之一。因为病毒速度让我们愈加蜷缩在狭窄的物理空间里,让科技速度带着我们愈加隔离我们与外界、与自然的关联。如齐泽克所说,“科技发展让我们越来越独立于自然的同时,也在不同层面上,让我们越来越受制于自然的心血来潮。”[1]病毒就是自然的心血来潮,是自然根本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而讽刺的是,病毒速度并未让我们去亲近自然,反而让我们愈加依赖于科技,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独立于自然。这因此让我们陷入一种由病毒速度和科技速度合并的双重速度的怪圈里,不得而出。
在另一方面,病毒速度也紧密地勾连着一个更大的速度:“人类世加速度”。[15]一部分地球系统科学家将人类世描述为“人类世加速度”,也即,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工业对环境破坏性影响的急速增长。作为国际地质圈—生物圈计划的合成项目的一部分,“人类世加速度”被用于理解地球在过去几十年整体的结构和运转状况。科学家发现,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明显增加。工业化畜牧业、煤矿开采、石油经济和全球运输与交通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甲烷和硝酸盐等,它们的速度便远远超过了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节奏和速度。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和生活被网络、全球旅行和电子媒介所带动的加速度,从根本上带动了人类对环境损害的加速度,也即增长了人类世加速度。[16]因而,人类世加速度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对地球系统影响的速度,也更应该被理解为一旦跨越地球系统的承受点,地球系统反扑人类的速度。而病毒速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世加速度密切相关。我们曾经和正在施加给整个地球的破坏,尽管看上去缓慢且不可见,现在都在以各种各样的加速度反噬我们自己。病毒速度只是人类世加速度中极其微小、同样不可见、却又极其强大的一部分。病毒速度与人类世速度看似在规模上有天壤的差异,前者微小且无边蔓延,而后者庞大且极具系统性。然而,正是病毒的微小和无边蔓延,才显示出了它的庞大和系统性。因为就目前病毒对我们整个社会、政治系统造成的影响来看,它是极具系统性和威胁力的。正如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是漫长的、全方位的积聚,反过来,地球环境对我们的反击也会是由局部逐渐扩散至整体的。其中,这规模的差异来源于人类世加速度的强度如何。
在病毒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性、时间感和速度感之中,我们真切感受到病毒作为生活和历史的主体在疫情当中展现出的这一非人类物质自身的强力。病毒从改变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来形塑我们对于生活的感知和想象。这一次是病毒作为主体在支配着我们。正如美国顶尖传染病专家福奇常常面对媒体提问疫情可能什么时候结束时,他总是回答,这不是由我们,而是由病毒说了算的。很明显,整个疫情过程中对于时间,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主导权和控制权。而这一切,正如“人类世病毒”这个语词想要提醒我们的一样,更多的并不是来自病毒,而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过错。
四、结语
从病毒与我们既是敌人又是同伴的辩证关系,到病毒的出现带有的明显人类世特质,再到病毒作为主体从历史性、时间和速度维度方面启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在人类世时代交叠的思考,本文主要从以上这三大方面尝试去理解病毒与我们之间的话语和伦理关系,以及病毒如何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生态和历史。与野生动物相比,病毒在物理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并不那么具象。而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和物质相比,病毒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一种特殊的生命和物质形式与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病毒有毁掉我们的能力和生机力。同时,它们也构筑了我们作为人类的身体和生长。身处新冠病毒给我们创造的这样一个“此时此刻”和“此种速度”中,我们有责任,同时也出于保存我们自身生命和文明延续的必要,对病毒进行哲学和文化反思。因为,这不单单是关乎病毒的问题,其中勾连出的时间与速度问题,都将促使我们重新反思我们与自然的总体关系,并深刻意识到自然正在且即将对我们展开的巨大反噬。人类的时间感和历史书写,及其延展开来的速度,都迫使我们必须将病毒视为要与之对抗和共生的生命同伴。病毒强大而有生机力,并且注定会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们的身体和社会。尽管人类与病毒纠缠的惨痛历史仍历历在目,我们仍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冠病毒绝不会是我们与病毒之间最后的遭遇。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当人祸越来越以天灾的面目出现,再叠加更多人祸的时候,或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回想起2020年,会发现这也许是自然开始猛烈反击人类的一个可能的元年。
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整个人类目前仍然很缺乏对超级灾难的思考。超级灾难之所以是超级灾难在于它很难预测。这也就意味着它随时可能发生,就跟这次的新冠病毒爆发,或与2008年的汶川地震一样。刘慈欣认为,目前人类所有应对灾难的应急方案都是建立在有外部救援这一预设之下的,而超级灾难是全人类、整个地球级别的灾难,并没有外部救援。他说,“目前人类社会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该考虑这个问题,面临超级灾难,外部没有救援,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怎么办?目前人人都有保险,但面临超级灾难,整个人类都不能有一个保险,我们生存的宇宙其实是很残酷的,我们应该做好超级灾难的准备。”[17]如果新冠病毒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开始思考未来可能有更大的超级灾难在等着我们,并为此做出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准备的话,应该是值得庆幸的。毕竟,这意味着,自然还没有决定一次性就摧毁我们,而是愿意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可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机会去认识到我们生存之中的宇宙环境其实是很严酷的。而新冠病毒直接将这个现实裸呈在我们面前,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社会的应对能力。除了这些,本文从思考我们与病毒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而阐发出的一系列伦理和历史问题,旨在希望这次新冠疫情除了带给我们伤害与苦痛之外,也能促使我们从病毒出发,去反思我们与整个生态环境和非人类物质之间的相互连接、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我们,作为人类世这个地质世代的主体与非主体,如何能够跳脱出我们自身携带的人类中心主义,去拥抱一种病毒式的共生思维,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