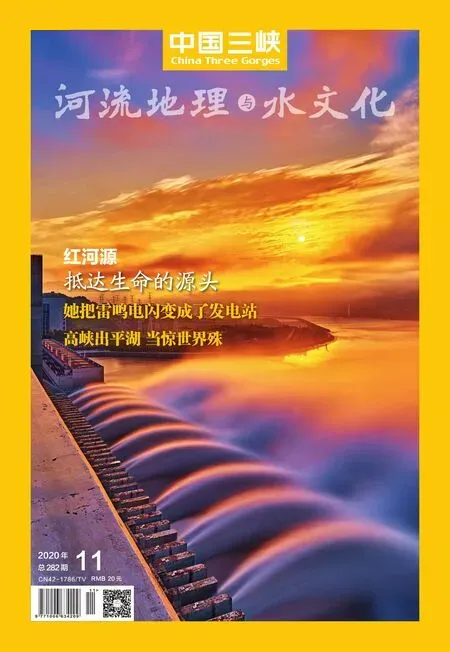江南秋实
◎ 文 | 叶梓 编辑 |吴冠宇
梅酱桂花
起风了。
风,是秋风。沉浸于秋日高远的光福古镇,仿佛在浓烈的桂花香里一梦不起。光福古镇的桂花,真多,窑上村、香雪海、铜观音寺、司徒庙,处处可见桂花树,处处闻得桂花香。但桂香持续的时间却不长,就那么一小段日子就没了,要是运气不好碰上几场秋雨的话,就像是失踪似的,消失得更快。好在光福人创造了无数与桂香有关的美味,比如桂花糖芋艿,再比如桂花糖藕,他们试图用这一道道美味对桂香进行一次次深情地挽留。
然而,这都是桂香与时令美食的相遇,最多也只能吃一季。桂花太难保存了,常温下不出几天,桂花的色泽、香味就会迅速减退,甚至发霉。面对易逝的桂香,聪慧的光福人还有别的创意:梅酱桂花。
梅子和桂花,怎么扯一起了呢?
在光福古镇,流传着一句古老的谚语:种桂必种梅。也就是说,梅与桂花都是光福的特产。坐拥无数梅与桂的光福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发明了梅酱桂花,可谓是味蕾世界的神来之笔。经梅酱腌过的桂花,能够保存5 年左右的时间,而且风味依旧——科学证实梅酱中的柠檬酸起到了保鲜的作用。而梅酱桂花的做法,首先要制梅酱。夏天,将成熟的梅子清洗干净,加入适量的盐,入缸,腌渍一个月左右,捞出梅子,将其打烂成糊状,滤去梅核,复将糊状的青梅肉曝晒数十日,待其呈黄褐色,梅酱算是制成了。而腌渍青梅时的汁液,光福人称其为梅露,经过滤后可以腌制桂花——梅酱桂花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新采来的桂花先置于竹箩里,用清水浸透后即捞出,滤去水分,与梅酱一起倒入缸内,搅匀,放置一夜,使桂花酱梅酱充分融合,次日捞出,沥去水分,充分搅拌,待入缸后,于顶部撒上盐,用竹片压牢,就可以长期贮存了。
如此制作出来的梅酱桂花,宜久存,宜随食随取,且香味犹存。
2017 年的秋天,我在光福的窑上村,见到了一瓶保存了15年的梅酱桂花。这么多年过去了,吃起来仍然鲜美如初。制作这瓶梅酱桂花的老人,据说经验很丰富。他介绍说,虽然金桂或丹桂的名称听起来更加“金贵”,但最适合做腌桂花的品种其实是银桂和白吉,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花瓣更肥厚,香气更浓郁,不易变黄。采花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有的花枝上还留有上一批没掉落的残花,这样的残花不要去采,因为黑色的残花花瓣会影响整批桂花的品质。

桂花酱制过程 摄影/图虫创意
光这些还不够,就连“拆花”也很学问的。
所谓拆花,就是把桂花花瓣从花枝上“拆”下来。据说,拆花的时候,一定要逆着花枝的方向“捋”,这样就可以连同花柄一起拆下,整个花形看起来更加漂亮,而且,相对完整的花朵也更易保存。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每年做几十罐梅酱桂花,送亲戚朋友。
真正的风雅,在民间啊。
东山白果
近一两年来,我熬杂粮粥的水平越来越高。可妻子喝完粥,还是要吃几粒白果。当然,这是秋天的事。她把七粒白果装在牛皮信封里,放入微波炉,烤四十秒,听到有啪啪的响声,差不多就好了。取出来,一粒一粒地剥开,颇有庄重的仪式感。然后,出发上班。
入秋以来的每一天,仿佛是从七粒白果开始的。为什么是七粒?好像是老苏州的传统。这恰好是我对东山白果产生好感的地方:一款美味,往往隐藏着风俗之美。

左:东山秋色 摄影/图虫创意
白果,是东山的特产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苏州特产。
之前去过泰兴,那里的白果好像颇有名,入住的宾馆大厅整齐地摆放着一排白果礼盒。后来才发现,滋味上泰兴白果略有苦味,东山白果并无苦味;颜色上泰兴白果果肉偏黄,东山白果果肉呈碧绿色,色泽亮丽;口感上东山白果更加糯软,仿佛吴中的这方山水。而且,东山白果种类繁多,有大佛手、小佛手、鸭屁股等数种。我喜欢大佛手这个名字,不仅让白果有了丝丝禅意,而且,大佛手壳薄、浆足、仁满,香中带甜,果形好看,是东山白果里的极品。鸭屁股的果形偏小,但产量高。东山人喜欢把白果做成各种菜肴,煮、炒、蒸、炖、焖、烩、烧熘等各种手法皆可使用——江南美食的精致,由此可见一斑。
旧时的苏州,大街上有人吆喝卖白果,是一道清嘉之景。小贩把白果装在铁丝笼里,放到火上烤,噼里啪啦地响。小贩还在旁边唱着这样的谣曲:

右:还未成熟的银杏果 摄影/图虫创意
烫手炉来熟白果,亦是香来亦是糯。
要吃白果就来数,一分洋钿买三颗!
也许,这是旧时苏州的特色之一。
叶圣陶专门写过一篇《卖白果》,直言“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之所以不如苏州,“声调不怎么好自然是主因,而里中欠静寂,没有给它衬托,也有关系”。他还记录了一首当年曾经唱过的谣曲:
烫手热白果,
香又香来糯又糯;
一个铜钱买三颗,
三个铜钱买十颗。
要买就来数,
不买就挑过。
白果,就是银杏的果实。
一粒白果,虽然小,却让人能联想到茫茫一片银杏林。银杏的高大树冠,宛似一把巨大的伞,赐大地荫凉,而秋深时的金黄叶片,仿佛片片黄金在空中舞蹈。我喜欢这样的景致,所以,常常会在深秋时节寻找一片银杏林发呆,做白日梦。
吴中的银杏,是值得一看的。
东山有不少银杏林,北芒村有一棵银杏年逾两千年,它和村子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相传,北芒村以前叫“北望”,吴越争霸时期,吴国为防止越国偷袭,在太湖一带设立南、北两个“望哨”,村子故有此名——只有古老的村子才会有如此古老的树。推而广之,东山槎湾、杨湾、上湾以及雕花大楼附近年逾百年的银杏,都是东山这座古镇的见证。
顺便说一下,包山寺里的两棵银杏树,也不错,堪称镇寺之宝。倘若从寺顶望去,掩隐在银杏黄里的古寺,极其江南,煞是好看。
宛似马眼
我有十八年的乡村生活经历。
现在回想起来,见过的月夜、数过的星星、踩过的露珠几乎都发生在这十八年里,所以,我一直对家乡杨家岘满怀感恩。那时候我还给邻居家的一匹马喂草。我家缺劳力,无人养马,但邻居家有。当然,不是草原上可以射箭、骑玩的马,而是下田犁地的马。每年农活一忙,我就和那匹黑色的马厮混一起,颇有交情。我还给它取过一个极好玩的名字:铁蛋。
一晃,数年已去。
我现在的生活,被汽车、演出、评委费、场务、串词以及忽涨忽跌的股票包围着,几乎与马无关了。奇怪的是,当我在三山岛见到马眼枣时,立刻想起了喂马的乡村经历。
我反复端详手里的马眼枣!想起来了,马的眼睛,大,呈三角形,饱满得像是要凸出来。据说,马与马之间的交流会使用眼睛,这真是神秘的事,不知它们会不会和人一样,也会暗送秋波呢。因形似马眼而命名的马眼枣,个大,味甜,约二寸许,是三山岛的独有之物。这与它生长的环境有密切联系,在太湖生长,有洁净的水滋养,有习习的湖风照料,哪能长不好呢。
马眼枣的背后,有一则传说——相传,宋朝有一批从北方押解到苏州的犯人在三山岛挖凿太湖石,他们将随身携带的枣子食完后,枣核丢到了三山岛,后来,三山岛渐渐有了枣。这种北方的枣由于受太湖水土的影响,结出的枣与一般的白蒲枣相比,果粒大,水分多,口感清脆鲜甜,又因形似马的眼睛,遂名马眼枣。
据说,现在的三山岛,年逾百年的枣树有六百多棵,株株苍虬,叶冠葱绿,可谓一景。
每年八九月份,马眼枣由青变黄,再由黄转为暗红,及至成熟。今年秋天,我得空去三山岛的枣园。抬头看树,一颗颗枣子挨挤在一起,极亲密的样子,这与陕北的枣树颇有不同。太湖之水衬着一颗颗饱满的马眼枣,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与岛上的枣农闲聊,他们个个闲淡从容,隐隐有古风,三山岛还真是一处世外桃源。
大画家吴冠中喜欢去三山岛写生,见了这里的马眼枣,也是赞不绝口。可翻阅他的画集,却找不到马眼枣的画作——倘若他画过,一定像他笔下的粉墙黛瓦那般,很江南很诗意吧。
采橘东山下
陶渊明的一句“采菊东篱下”,写尽人间悠闲之境。
但这是古代的情景,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映衬着,也有不高不低的古朴篱笆横在眼前,不诗意也难。而现在楼高了、路宽了、车多了,生活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以至于悠闲之境渐行渐远。其实,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若有一颗悠闲之心,生活处处充满诗意。比如在橙红橘黄的好景之际,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去东山采撷橘子,几乎就是“采菊东篱下”的当代翻版。

橘红秋色 摄影/苏州东山 /图虫创意
东山的橘子早在唐代就是贡品之一,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太湖备考》载,“橘出东西两山,所谓‘洞庭红’是也。《本草》云‘古人矜为上品,名播天下’”。再后来,看过在东山陆巷取景拍摄的《橘子红了》,让人对橘林心向往之。于是,寻一周末,驱车从吴中大道向西,很快就到了东山。
东山处处是橘园,随便找一处就能度过一段愉快时光。此行,我们去的陆巷村,是有“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之誉的明代宰相王鏊的家乡。这是太湖边的一个古老村落,粉墙黛瓦,青青的石板街,古意盈盈。顺着王鏊故居往后山走,漫山遍野都是橘林。
新鲜的橘子伸手可摘,方知“一年好景君须记”的忠告是多么妥帖。绿树丛中,一颗颗成熟的橘子仿佛一盏盏高挂枝头的小灯笼!犹记得春天时来过橘林,彼时春暖花开,橘子树抽出了新的枝条,长出了嫩绿的叶子——东山蜜橘,就像是时光写在大地上的一首长长的叙事诗,需要你慢慢地解读。中秋过后,早红橘就开始转红了,寒露后其它橘子也相继上市,再往后,黄皮橘也上市了,而料红橘立冬后才成熟,采摘下来,保存在竹筐里,可以一直藏到春节时食用。
在东山的橘园里,翻翻旧时的《橘录》倒是件挺应景的事。这册由我的西北老乡韩彦直悉心撰写于温州任上的书,是古代中国最早的柑橘专著。此书分三卷,上、中卷叙述柑橘的分类、品种名称和性状,下卷讲述柑橘的栽培技术。可惜,此书里对洞庭红的描述,竟然说“韵稍不及”其他,也许,有些失之偏颇吧。
采毕,在朋友的细心安排下,又去了东山杨湾村的一户人家品尝两款跟橘子有关的美味,一款是蟹酿橘,另一款是洞庭饐。蟹酿橘是将大个的橘子截顶取瓤,留少许甜汁,再将太湖蟹的蟹黄填入,用橘叶封口,加入数滴醋、酒,隔水蒸熟,待吃时揭开,新鲜无比;而洞庭饐则是将橘叶与荷叶切碎,取汁,与蜂蜜和米粉和在一起,制成米饼,入笼蒸熟,即可食之,这也是太湖人家常见的一款斋供点心。我是第一次尝到如此精致的美食,这也是姑苏人家在美食上考究、精细的一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