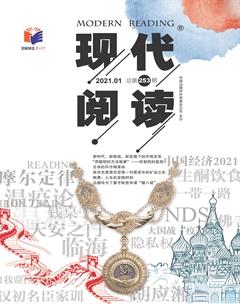爱国实业家胡应湘:港珠澳大桥“动议”第一人
周强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长约55千米,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大桥开通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018年10月23日这一天,83岁高龄的胡应湘应邀在珠海出席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这一天,也是胡应湘提出伶仃洋大桥构想35年后第一次看到完工的港珠澳大桥。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实业家之一,胡应湘1935年出生于香港,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企业陆续落户广东,伴随而来的则是电力供应不足、通信不畅、运输不便等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
胡应湘就是在那时决定要向珠三角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他先后投资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广深高速公路、广珠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沙角电厂等标志性项目。
广州中国大酒店建设期间,一次糟糕的体验让伶仃洋大桥计划进入胡应湘的视野。考虑到中国大酒店将来的运营及客流来源,一天傍晚,胡应湘决定沿着珠江西岸去澳门,然后再乘轮渡回香港。一番舟车劳顿再加凄风冷雨,让他深感交通不便的痛苦。
在高耸入云、雄伟别致的合和中心64楼,回到办公室的胡应湘来回踱步,硕大的工作台面上铺开的是一张珠三角地区地图。他开始畅想,要是整个珠三角西部与香港相通,物畅其流、人享其便,是何等快意。
“何不規划一条从香港到珠江西岸的大桥,形成整个珠三角环状高速路网?”胡应湘随后在美国展开调研,发现旧金山湾区已经修建了5座跨海大桥。
在多次实地踩点后,他发现,伶仃洋中有两座天然岛屿——淇澳岛和内伶仃岛,从珠海到香港最西面的一片海域水较浅,凭借两个岛修桥可以连接珠海与香港,加起来总长不到3千米。
1983年,胡应湘提出了《兴建内伶仃洋大桥的设想》,大桥西起淇澳岛,跨过内伶仃岛,跃至香港屯门烂角咀,全长27千米,按照双向三车道标准建设,静态总投资为134亿港元。由此,胡应湘成为提出港珠澳大桥具体兴建设想和计划的第一人。
双面“夹击”下的珠海遗憾
在珠海市委大院1号大楼一楼大厅的显眼位置,曾长期摆放着伶仃洋大桥的模型。实际上,珠海至香港建跨海大桥是珠海人20多年来的梦想。
梁广大自1983年开始先后担任珠海市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在他的心中,为珠海修建的机场、港口、铁路等,是珠海长远发展的“命运工程”。在当时,珠海一个集装箱要依次绕道中山、顺德、南海、广州、增城、东莞、深圳,才能转到香港集装箱码头,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要摆渡过七八道河流,一个集装箱运输费用就是五六千港元,而深圳、东莞只需要两千多港元,奇高的运输成本让外国投资者望而生畏。没有打通与香港连接的通道,成为珠海经济特区发展落后于深圳经济特区最大的瓶颈。
1986年11月20日,胡应湘应邀访问珠海,向梁广大详细介绍了修建伶仃洋大桥的方案。珠海方面非常重视,双方还就方案细节进行了深入交流。
1987年底,中共珠海市委、珠海市政府作出一项重要决策:打通对外开放通道,建设伶仃洋大桥。
对珠海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
1991年上半年,建设伶仃洋大桥各项研究工作全面启动,《伶仃洋跨海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1993年10月,国家计委批复,由广东省自行审查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技术与经济论证,包括资金筹措等立项前期准备的工作。
拿到批复后,梁广大也开始着手争取港英政府的共识。然而,面对香港民间的建桥呼声和珠海市政府抛出的橄榄枝,港英政府并未给予热情回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基建潮中,伶仃洋跨海大桥始终不在港英政府工程名单之列。
“当时香港还没回归,港英政府不希望香港与内地走得很近,对大桥的反应是冷漠的,回应也是被动的。”胡应湘回忆说,“港英政府在香港回归之前的方针是将香港与内地隔绝,最好不要与内地有任何瓜葛,因此当局委托英美顾问公司作了研究报告,该公司建议港英政府20年以后再考虑此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梁广大在7月下旬便赶赴香港与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会面,当面提出建设伶仃洋大桥方案,获得董建华支持。与此同时,胡应湘也在与董建华交流时提出,将1983年接驳香港屯门的原“内伶仃洋大桥”方案,改为东接位于大屿山的香港国际机场,西接澳门及珠海的“粤港澳大桥”方案。
当时,这座跨海大桥建设方案面临两种选择:南线方案是从香港大屿山至珠海与澳门之间的海域设人工岛,由该岛分两路分别入珠海和澳门,类似现在所说的“Y”形路线;北线方案则由珠海金鼎至淇澳岛,跨过内伶仃岛至香港屯门烂角咀。
由于南线方案更靠外海,要有更强的抗台风能力,深水海区长度比北线方案大,其中水深5至10米的有12千米,水深10米以上的有4千米,均比北线长。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后,交通运输部公路规划设计院(现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在完成的预可行性报告中推荐北线方案。
正式公布的伶仃洋大桥方案为北线方案:西起珠海淇澳岛大王角,跨过内伶仃岛,跃至香港屯门烂角咀,全长27千米,其中桥长23千米,大桥引道4千米,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桥宽31米,设计行车时速为100千米。预计总投资约134亿元。
伶仃洋大桥项目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准生证”,在后续推进中却无疾而终。
从1998年到2001年,粤港方面总共只开了3次工作会议,合作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伶仃洋大桥因此被严重拖延。屯门登陆点也面临异议:屯门一直是香港的交通瓶颈,若要在屯门登陆,除非香港整个新界道路系统都加以改造。
对此事,澳门也未等闲视之。
尽管当时澳门尚未回归,但澳门方面一直非常关注港澳之间修建跨海大桥的规划方案。
“当时澳门还在葡萄牙政府的管辖之下,所以这些论证和研究都是澳门的民间学者、专家,以及商界组织的。”港珠澳大桥澳门关注小组成员黄汉强说,“澳门本就是微型经济,经济能量不足,对内地与香港的依附性较强。大桥建设澳门不能缺席。”
1998年6月1日,部分澳門民间专家、学者,以及商界人士联名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并附上《港珠澳大桥与伶仃洋大桥的比较研究报告》。信中表示,跨海大桥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不仅牵动港澳和珠海三地的利益,更是关系到国家全局和“一国两制”实践的工程,而兴建伶仃洋大桥考虑澳门的意见和利益不够,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容易挫伤澳门人的感情和信心,希望中央政府从各个建桥方案中找寻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随后,澳门各界代表在多个场合发声,认为伶仃洋大桥关系到澳门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允许澳门人参与研究兴建,以不损害澳门利益和不影响港澳关系为宜。
香港冷、珠海热、澳门堵,在港澳的双面“夹击”下,珠海单方面主导的伶仃洋大桥修建工作步履维艰。在2001年建成连接珠海市区和淇澳岛的引桥——淇澳大桥后,主桥工程最终搁浅。
20年弹指一挥间,曾经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深圳以一骑绝尘的姿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而珠海的地区生产总值在珠三角九市中倒数第二。
珠江口再起风云
时间有时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有时也是推动发展的一剂良药。
随着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香港特区与珠江西岸、澳门特区的沟通与交流日益频繁,交通运输压力越显突出。
两地同胞常年往返港珠澳三地,坐轮渡转汽车,饱受舟车劳顿之苦,建设一座从香港穿越伶仃洋到达珠海的跨海大桥,成为珠三角两岸有识之士的共同梦想。
遭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香港也意识到,制造业转移是全球产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而香港要进一步保持竞争力,就必须依托内地广大的经济腹地,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珠三角西岸地区,有着大量的土地和富余的劳动力。
看着伶仃洋大桥降温、冷却,直至封存进历史,胡应湘从未放弃自己的大桥梦想。他秉持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再次走上游说的道路。
2001年,胡应湘任香港港口及航运局主席。他再一次向香港政府提议修建跨海大桥,陈述建桥的必要性。
他说,香港目前的港口集装箱虽多,但收费却很高,要想维持香港地位以及珠三角制造的竞争力,就要提供服务,降低成本,方便快捷,而这座桥可将海运、陆运、河运和空运联系起来,扩大香港的物流腹地。
董建华立刻指派运输局局长研究胡应湘的提议,但得到的回应是,根据英美顾问公司作的研究报告,在2020年前没有建桥的必要。
2001年4月,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欧广源带团赴港招商时表示,既然香港认为2020年才有修建跨海大桥的需求,而广东有沿海高速公路要接驳,所以广东计划建设从深圳至珠三角西岸的跨海隧道,并在2002年4月举行的广东银行同业公会第二届理事会上公布了海底隧道计划。
此时,围绕跨海大桥的建设,香港内部各大财团也分为航运派(反建派)和公路派(主建派)。究其根本,是各自利益,特别是港口利益之争。
反建派认为,珠三角西部货物用船舶运输到香港比较经济,建大桥需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缺乏成本效益,并且大桥建成对香港葵涌码头、深圳盐田港的货源构成分流。
主建派则强调,香港若迟迟不兴建大桥,可能让广东捷足先登,在珠海、澳门和深圳之间兴建隧道,跨越香港进行货物贸易,香港的地位将被边缘化。
2002年2月,胡应湘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把一份名为《关于兴建由香港大屿山至澳门、珠海的粤港澳跨海大桥的建议》的文件带到北京,罗列各方案利弊,从珠三角经济体系、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香港经济战略转移等方面,历数建桥的迫切性,可谓用心良苦。
胡应湘始终对兴建跨海大桥保持一种坚持不懈的热忱。
在2002年8月26日举办的构建珠三角物流平台研讨会上,胡应湘当场宣布,合和集团已经决定打破香港政府在港珠澳大桥问题上的长期沉默,拟牵头联合新鸿基地产、信德集团,以及另一家金融机构,集资150亿港元,希望以民间资本力量,推动兴建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跨海大桥。
“对香港来说,土地与劳动力价格上升引起的生产成本增高导致了发展空间的缩小,而离香港较近的珠江东岸城市深圳、东莞等由于类似原因,吸纳香港辐射力的能力也在变弱。而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将打破伶仃洋的阻遏,把珠三角连为一体,使香港在物流、金融、国际贸易方面的优势和珠三角制造业的优势形成互动,使物流、资金、服务进入发展较慢的西岸地区,将整体提升珠三角‘世界工厂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实力。”胡应湘表示,竞争带来的淘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是很快的,20世纪40年代全球最大的机械制造业中心是美国,60年代是日本,70年代是“亚洲四小龙”,珠三角已经不是成本最低的地方,亚洲还有更便宜的印度、越南,如果香港和珠三角抓住这个机遇,就可能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面对内地“大齿轮”的高速运转,“小齿轮”香港必须加快转速才能跟上内地发展步伐。反对之声越来越小,修建跨海大桥渐成香港各界共识。
2003年1月8日,董建华的施政报告中提到,兴建连接香港与澳门和珠三角西部的大桥,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珠三角再起风云,“大桥动议”重新提上日程。自此,从香港到珠海的“伶仃洋大桥”理念,被连通香港、珠海、澳门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取代。
(摘自广州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虹起伶仃:逐梦港珠澳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