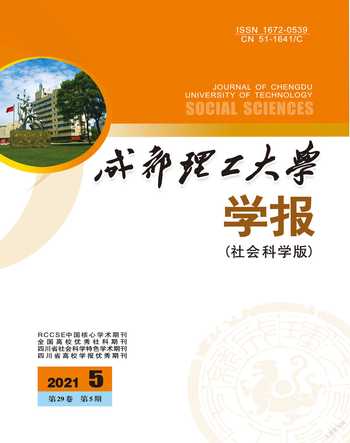情绪主体性的表现
作者简介:鄂建华(1996-),男,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摘 要:向培良认为,情绪表现贯穿在戏剧中,从剧作家创作、到演员表演、最后为观众接受,这是情绪主体性表现的完整体系。情绪是经由内心深处的性格而发出的,以动作为中介,直到观众被情绪所感染为终结。情绪的传达是中介,最后趋向于内在的生命力,使得人生获得向升的生命力,可以促成人格和德行的形成,情绪的表现更贯穿着一种教育的功能。
关键词:向培良;戏剧;情绪;生命力;戏剧教育
中图分类号: I20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5-0067-06
向培良是湖南省黔阳县沙湾乡寨头村人,是莽原社重要成员、狂飚演剧运动主要负责人、青春文艺社创始人和负责人,曾任怒潮剧社戏剧部主任、教育部巡回戏剧教育队第一队队长、国民党中国万岁剧团团长。向培良积极活跃在现代戏剧历史上,创作过戏剧理论、戏剧作品、艺术论等著作。他以独特的视角“情绪”去切入戏剧这座大厦,提倡一切为了“情绪”,“情绪”也为了一切,向培良的戏剧理论是“情本位”的,以情绪的传达为最终目的。这种要求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一套思维逻辑的,他的情绪主体性理论不是一蹴而就,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情绪”为主体的,以创造和传达这种情绪为本位的戏剧理论和戏剧作品。
一、情绪说的伊始及嬗变
在20世纪中国话剧史上,对于戏剧批评的理论是一片空白。向培良是一位刚登文坛不久的剧作家,初生牛犊的他撰写了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戏剧批评的著作——《中国戏剧概评》。该书回顾了新兴话剧发展的2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断代的话剧史。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回顾了胡适、汪仲贤、陈大悲、熊佛西、丁西林、郭沫若、田汉、余上沅等人的作品,发现剧作中存在“社会问题”“趣味”“教训与感伤”等问题,并不是“忠实表现人生,忠实地传达情绪的”[1]50。这时的戏剧不是真正的艺术,因为“真实的艺术,表现着真美的人生及其情绪,是要有真实的、坦白的心的人才能够领受的”[1]49。在向培良的眼里真正的戏剧是“一种艺术,创造和传达人底情绪的艺术。戏剧的使命在于创造和传达情绪的,不在于显示事件”[1]91。以情绪表现的标准来看,目前话剧史上基本没有一部戏剧是成功的。因为剧作家们的焦点发生偏差,首先剧作家只关注剧本,而忽视了演出的重要性;剧作家只关注事件,而忽视事件所要传达的情绪。这里可以看作是向培良“情绪表现说”的一个雏形。此时的情绪,我们要有所区分,话剧中的“情绪”与平时所讲的情绪,是有所区分的。平时所讲的情绪,是包含喜、怒、哀、乐在内的感官上的刺激反应,这里的“情绪”,是一种由剧作中传达出的幽微、隐蔽、细腻的情感,向培良强调的是内心的心理状态。所以向培良也在剧评中提到《黑衣人》和《尼庵》,其中描写的孤独、寂寞、恐怖等心理活动和含有的神秘、美丽、向往的心情是值得称赞的。
20世纪20年代的话剧作为一种新兴艺术门类,既想方设法努力挣脱于旧剧的襁褓,同時又积极向西方寻求戏剧艺术的理论。向培良是极力反对旧剧的,所以他的戏剧理论也向西方汲取营养,他曾在序言中写道:“介绍到我国来的最早的艺术理论书籍,为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两部书都使我大受感动。厨川氏主义看似太狭,而托氏的宗教意识说也不能使我满足。”[2]2这表明,西方的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向培良阅读过很多理论,虽不能十分使他满足,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乔治·贝克认为,戏剧中的剧本之所以为剧本是因为“它能在观众中创造感情反应,这个反应是剧中人物的感情所引起,或者是剧作者由于观察这些人物所得到的情感而引起的”[2]41。而动作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是“激起观众感情的最迅速的手段”[3]20。剧本对动作有明显的依赖也就不足为奇,“戏剧从一开始,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极其依靠动作”[3]15。乔治将“动作”又进行细分为“形体的动作”和“内心的动作”,他认为最能激起观众情绪的动作,亦或最能传达戏剧性的动作是“内心的动作”。而向培良举出“动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动作本身所引起的官能刺激,一是动作所表示的情绪。当下“动作”所传达的“情绪”,就如同乔治的“内心的动作”,此时的情绪是由内心的动作所生发出来的审美情感。此时的“情绪”与前文的“情绪”是有所区别的,是剧本中所生发的剧作家、表演者体验后再度创作产生的,是剧作家对于剧中人物的观察后所创造的情感,同时也是表演者对于剧本中角色人物的体验把握后创造的一种情感,还是观众从观看演出后所获得,经过内心酝酿过后的审美体验的情感。
向培良有关“情绪”理论的积累,和内心的运筹,最终集成一部著作《艺术通论》。向培良在《艺术通论·前言》中说过,“我的艺术论是从我的戏剧论出发的”[4]。向培良的戏剧理论和创作对于艺术观的形成是有影响的,这就解释了向培良为什么用“情绪”来取代托氏的“情感”一词。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把自己体验到的情感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只要作者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了观众和听众,这就是艺术。”“艺术是生活中以及向个人和全人类的幸福迈进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际的手段,它把人们在同样的感情中结成一体。”[5]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表达和交流感情的工具,是促进人类不断向上的原动力,是达成人类团结一致的精神源泉。向培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对于托氏把艺术的表达最终落脚于宗教意识这一论断,不甚满意,而以人类“情绪”取而代之。这里“情绪”的内涵较为丰富,可以概述为以下:①情绪是艺术的所传达的媒介,即情绪作为艺术传达的内核而存在,其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认识的意味;②情绪是不要被现实所压抑的,起源于实物,依附于具体的事物,最终要达到一定的行动作为发泄的终点;③情绪代表着人类相互联结的一种生命力,一种人类趋于向上的一种生命的内驱力。最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是情绪之物质的形式。向培良以本质论、假象论、内容论、形式论、材料论、探源论、创作论、鉴赏论、思潮论和效果论,架构了整本《艺术通论》,其中要求“艺术是在情绪上要求互相了解的活动,也是人类精神扩大超升的途径”。其中可以看出“情绪”在向培良的理论框架中的地位尤为重要,不仅是作为内容“情绪第一”,而且形式的千变万化也是为了引起必要的情绪来。再有甚者,创作论中其归结点在于“不仅是情绪传达的手段,而且应该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外物不断刺激创作者,而逐渐达到情绪完整的程度”[2]99。此时的情绪是一种创作的原动力。
综上可知,艺术是情绪之物质的形式。情绪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中国戏剧概评》中的幽微、内敛的心理描写的情感传达,到以《剧本论》中论述情绪是一种与动作精密联结,是剧作家或演员创造的审美效果,最后到《艺术通论》中情绪成为艺术传达丰富的内涵,以及作为一种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媒介,它既需要去发泄,又可以成为推动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更可以成为人类相互联结的一种生命力的表征。
二、情绪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
(一)戏剧创作中情绪表现的“生命激情”
向培良在写下“我离开十字街头,人的潮流在我后面奔走”之后,就开始迈上戏剧艺术的道路。其戏剧创作的过程中无形的会渗透着他的戏剧理论,从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不忠实的爱情》中的龙英男和陶亚文在爱情漩涡中的打转,一次次的被那爱情中幽微的情绪所左右,主人公感到生活的疲倦,内心的煎熬和对爱情的迷茫与怀疑,都是对于“情绪”理论创作的前奏。到《沉闷的戏剧》中充满着“疲惫,忿怒,爱之牺牲,迷罔矛盾,心底苦闷,以及追求着的理想底破灭”[6]1的幽韵内敛而又难以抒发的情绪。向培良关注的是剧中人物内心的世界,所以剧本中有详细的心理描写。在《生的留恋与死的诱惑》中,向培良描写“白色恐怖”的医院背景,到战士与护士这两种在战场和生命最后“战场”上奋斗的人,就是内心情绪隐忍后,需要极度的释放的人群。两个人的对话中“我的精神,支持着我生命的精神,我觉得已经消失了。并且我没有气力”[6]12看出护士的极力支持,直到“死神”的到来,才终结了战士生的希望之光,剧本落幕。而《冬天》之中,是充满着象征和隐喻的,情绪的传达更加的隐蔽而幽深。如同雪莱在《西风颂》讲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阮宜均和陆若华之间的爱情从怯懦走向勇敢,最后虽然以死亡终结,但是内在蕴含着一种生命力,“我离开春天,勇敢大胆向冬走去。我要同冬天奋斗。我要同寒冷奋斗,我要同黑暗奋斗,我要同残酷奋斗”[6]42。这里情绪内容饱满高涨,与剧本刚开始的那种怯懦形成鲜明的对比,饱含生命力的激情。
最具典型特征的是《暗嫩》,《暗嫩》被誉为中国的《莎乐美》。剧本是依托《圣经·撒母耳记下》的故事,暗嫩在行不轨之事之前的心理描寫堪称一大妙笔,到后来暗嫩的情感得到宣泄后一种极度失望和痛苦也是点睛之笔,其实这正是也是向培良“情绪”表现后的代价。暗嫩是一个“对美的追求表现个人的旺盛生命力,将其描述为具有激昂向上的生命力的追求理想的‘新人’”[7]。这是向培良早期的作品,整体上看有这种“情绪”主体性表现倾向的不只是向培良早期的著作,《白蛇与许仙》剧本,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经过向培良的再创作,白娘子不再是一个只有妖精法力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一个具有人类感情的女子。白娘子不是对爱情盲目追求,而是体会到了爱情的滋味,是一位正常倾诉自己情绪的女人。许仙是一个充满“内心动作”的人,许仙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思索着该何去何从时,即思索去寻妻还是去追随法海,许仙是一位在寻求内心的情绪并做出决定的“墙头草”。剧末的结局虽然是个悲剧,但是白娘子“面向太阳”的激情及向上的生命力是为我们所折服的。与此同时我们聚焦《母亲利巴的哀歌》中利巴在失去儿子时痛苦的咆哮“以色列的妇人谁比我更苦?以色列的妇人的眼泪谁比我流得多?我唏嘘如风,如秋天吹死一切有生之物的西风,我的眼泪如不息的溪流”,“我诅咒你们,也诅咒你们大王,就是把我的儿子夺去了交给基遍人的王大卫呵!”[8]内心所表现的悲痛欲绝和愤怒的情绪,正是向培良一直强调的演员要传达给观众,并在观众之中激起反应的“情绪”。
向培良在戏剧创作中会营造一种唯美而不颓废的氛围,剧中人物尽管有羸弱的现状,但是他们都是在现实中表达自己的生命诉求,在事件中塑造自己的情绪,最后展现一个人生命的激情,表现出一种奋发向上的生命力。
(二)戏剧理论中的“情绪”说
向培良以“情绪动作”说有机架构了戏剧这门综合的艺术,使剧本、导演和演员分别以情绪表现为核心得到重新阐释。戏剧是向培良最为看重的一种文学艺术样式,他认为戏剧艺术是与图画、音乐等艺术门类相等同的艺术。“因为没有一种艺术是比戏剧传播得更广的,没有一种艺术对于观众的关系更密切的。”[9]同时戏剧也是传播最为广泛与民众联系最为紧密的艺术。戏剧传达“情绪”能激起民众的反应和反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情绪”在戏剧艺术形式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向培良在《戏剧之现代底形式》一文中将戏剧分为剧本、演员、导演三个部分,“情绪”主体性的表现的“触手”伸到向培良戏剧理论的各个角落,统领戏剧理论各个部分。《剧本论》中重点谈的是编剧的问题,分别从题材、结构、人物、对话等方面展开论述。“剧本首先得有一个故事,故事必须是关乎人的活动,活动是以动作表现出来的。”[10]5然而,“动作的归结在于显示情绪,则情绪自然是剧中主体了”[10]5。戏剧最直观的方法是以动作来示人,所以在戏剧中的人物动作设置和性格特征都得巧妙地安排,动作的表现和性格的塑造最好要借助对话来安排,因此结构的安排巧妙指出就是要以剧中情绪的起伏为依托。“情绪”的触手有力地解构了题材、人物、对话等主要的剧本元素,为表演前导演的调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向培良认为,戏剧是集体的艺术而不是个人的艺术。在这个集团之中,导演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统帅,“他是剧本和演员的中介,联合舞台各部分工作成为一个联合的,联合演员的思想与力成为一个,最后,达到他工作完成的地步,联合舞台工作和剧本成为一个,而且他也是戏剧进展中事业的领袖”[11]13。导演的工作除了这三个“一个”之外,舞台上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事物,导演在戏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舞台表演是在戏剧中间重要的一环,因为观众所接触的事实的血与肉是人类的呼吸和颤动。人类此时的生命力是与观众之间息息相关的。向培良认为,戏剧真正的生命是在舞台上,一切的组织活动都应该以此为目标。舞台演出的准备工作中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是选择剧本,一是角色分配。剧本的选择应当集思广益,不能导演一人的独断,剧本选择要考虑时代、地域、受众等综合因素。角色支配不能以个性为标准,因为“舞台上需要的是表现能力”[11]33。向培良认为,一个好的演员应该知道动作、表情、声音等姿态里要与情绪的韵律相谐和。更有甚者,舞台的布景、灯光、服饰等要与舞台整体的情绪、情调相互之间配合,最后能达到激起观众情绪的结果。此时,应当注意与那些专注感官刺激的手段相互区别,不要堕入浅薄的写实主义,因此“舞台上的角色也是,而且还要情绪和韵律的调和及心和生命的调和”[11]44。导演还要分析每个角色的个性、环境、风格,他的理想,他的希望和梦等一系列事件,其前提条件是着重把握角色的心理与情绪之变迁,舞台艺术上的角色之间互相关涉,导演还要在乎角色之间的位置的变化,一个动作接着另一个动作都息息相关。随着灯光和服饰之间的变化,直接前提是为了显示这个角色的风格和情绪的变迁。导演的调度和指导都是为了“情绪”的显现,确保演剧活动正常进行,所以正如格·托夫斯托诺戈夫所言“没有导演,便没有戏剧”。
“演员底表演是舞台的中心。”[12]同时,演员也是戏剧艺术的主人,而演员的表演则是这艺术的中心。所以,从演员的角度,他平时应当要做些基本训练,锻炼自己的喉头和胸腹,能够发出必须的音调,和别的演员相互之间的契合能够产生出相当的情绪来,还必须研究自己的手和脚的动作,充分利用肢体的活动和面部表情及其舞台上动作之间的变化造出各种情绪从而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审美效果。平时刻苦的训练就是为了日后上台表演,“我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引起情绪是多么差异。表演是直接以事实之骨与肉给观众的,你要沉着考虑所创作的东西是否会发生你所预期的情绪”。在那两三个钟头中以最饱满的情绪将表演呈给观众。戏剧表演分为两个派别:“体验派”和“表现派”,体验派强调演员要真实地创造角色,必须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在舞台上表演时强调忘我,要求演员与角色合一。“演员应先产生必要的情绪,就是那个角色所有的情绪。他演玛格波斯就必须燃烧起野心和嫉妒,他受情绪的指挥。”[11]39表现派讲求理智的作用,演员只要在舞台上演出角色的性格即可,要保持自我和理智,不需要真的变成剧中的人物。“另一个派别反对这种,所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情绪。首先需要理智去寻求表现那些情绪的方法。……艺术所要传达的是情绪,但所以创达的途径却是理智。”[11]39所以向培良先生偏向于“表现派”的艺术表现观点。演员需要直接从社会从自然取得他的灵感,这要求演员去观察自己,观察别人和观察社会。人的情绪受到身体的行动和环境的影响。我们的动作在某些环境中才能表现出来,所以演员最好是在专门的场所去训练和休息。演员在排练的过程中,应当顾忌别人的情绪的变化,台词之间的时间长短的衔接尤为重要,要有张有弛,井然有序。最后是注意服饰和灯光以及幕布的位置对于演员的影响,演员衣服的变化要符合情绪的变化。不同的服饰来自于不同的种族、时代和环境,需要与角色的身份保持一致,同时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情绪,戏剧中灯光和服饰的色彩应该与演员的身份和情绪的起伏相协同。例如,在《茶花女》中“茶花女是舞台上的主角,她的衣服的色彩应当是主要颜色,不要使任何别人比她更触目,更鲜艳”[11]66。茶花女的主要颜色是桃红色,其次是高洁的白色和高贵的青色。到了第四幕中,衣服变成了青黑色和沉重的线条,这是象征着死亡的前兆。随着剧情变化和人物的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灯光也要与剧中人物的心情相契合,红色有时象征着人物内心的亢奋,青色代表着一种沉静等。
总之,向培良的“情绪主体性的表现”体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的是一种激越的生命力,而在戏剧理论中则处处以“情绪”为主体,借助“动作”的媒介得到充分表现。
三、情绪表现的教育功能
戏剧的教育功能,是指演员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用写意或写实的动作能传递出他要表达的情绪,进而这种情绪对观众情感和精神的渲染和教育。观众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领略一个戏剧人物浓缩的一生。戏剧人物情绪中会有时光易逝的叹惋,也会有功成名就的豪迈,也会有复仇之后的迷茫……种种戏剧情绪,其中蕴含了一种教育的意义,这里的教育意义不是为了教育才写的戏剧情绪,不是说戏剧沦为教育的工具。这里的教育功能是戏剧情绪爆发的过程中所包含的伦理色彩、战争激情和直接展示的生命激情对于观众的感染和教育。在戏剧创作的过程中蕴含了教育的因素,具有教育的功能。
戏剧是一种运动艺术,情绪是运动背后的推动力,这种情绪是由剧作家、演员体验后再度呈现后产生的。剧作家会以观众的接受能力和欣赏维度塑造戏剧人物的形象,会影响到演员对角色的体验和表现。演员对所塑造角色的沉浸与内在情绪的体验,情绪的高涨和生命力的张扬,是演员借助舞台艺术的手段而产生的。演员的舞台生命体验会对现场的观众产生情绪上的影响,演员的情绪包含着他对于人生所处境遇的体悟和表现,对于台下观众之间是有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共鸣。如果教育可以分类,可以分为思想的教育和行动的教育两类,“戏剧是行动的艺术”。戏剧就是对人的行动上教育的直观性的艺术。情绪可以通过演员的动作表现出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观众可以游历和领略人生的缩略过程,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观众的情感得到渲染和发泄,对于观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产生影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著作中说道:“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13]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在这里表现得要适度,既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要合理适当,因为过度的怜悯和恐惧会给人的身体带来伤害。向培良的伦理剧《不忠实的爱情》中龙英南和陶亚文二人相恋,陶亚文是对爱情执着而坚贞,面临着吴梦茵的追求,她断然拒绝;但是龙英南是因为生活的忧郁和空虚而想躲避到爱情中以便解开心结,他把爱情当作寄托,最终解开心结开枪自杀了。这部戏是在告诫年轻人不要轻易触碰恋爱的大门,其后果有时是难以预料的。还有向培良的抗战剧《民族战》,剧中讲述了东北底层人民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诈,王家堡、绿里村和下林村的村民,在反抗压迫和抵御外敌的过程中展现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英雄主义精神,底层同胞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那种高涨的情绪,给观众传递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也谱写了东北人民抗击侵略的事迹。总之,不论是面临爱情认真的态度,还是描写家国情怀的抗争史诗,在戏剧高潮部分中戏剧情绪都是饱满而富有张力的,都是演员对于观众精神方面的一种洗礼。
在戏剧舞台上情绪的表现有时是欢乐、激动、幸福的,有时是悲傷、忧郁、痛苦的。在剧院的音乐、灯光和色彩的渲染下,观众很容易沉浸其中,常常在戏剧结束之后,久久才能从那个氛围里走出来。甚至由于演员表演过于逼真,台下的观众会分不清现实和虚幻,随着剧情叫喊出来。“观众对台上的戏是非常轻信的,他们兴高采烈地自愿成为戏剧的艺术魔力的俘虏。”[14]观众会随着剧情发展,情绪随之发生起伏,他们甚至会和演员同笑同哭。在观剧之后,自己面临某一困难或障碍时,会受到剧中人精神的渲染,努力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在戏剧中,情绪表现的教育功能是能量巨大的,这种情绪的传递能产生很多正能量。
综观,向培良戏剧中情绪主体性的塑造是十分明显的,从他严肃的戏剧批评中初现端倪,到戏剧理论体系之中的建构,无意识地使用情绪的概念,再到戏剧创作中的尝试,都是为了情绪服务和编排的。情绪的编排不是无目的的,而是合目的性的。在战争年代,高涨的情绪可以迅速渲染人的情绪,人体验到生命的激情,完成一次生命的愉悦。
参考文献:
[1]向培良.中国戏剧概评[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2]向培良.艺术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3]乔治·贝克.戏剧技巧[M].余上沅,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41.
[4]向培良.艺术通论·序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2.
[5]托尔斯泰.艺术论[M].丰陈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11-412.
[6]向培良.沉闷的戏剧[M].上海:光华书局发行,1927.
[7]王云霈.唯美而不颓废——向培良综论[D].开封:河南大学,2014.
[8]向培良.母亲利巴的哀歌[J].北新,1930,4(13):81-90.
[9]向培良.戏剧艺术的意义[J].现代文学评论,1931,1(2):1-6.
[10]向培良.剧本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
[11]向培良.戏剧导演术[M].上海:世界书局,1938.
[12]向培良.新的舞台艺术[J].矛盾月刊第2卷,1934,(6):34-42.
[13]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
[ 14]波波夫.论演出的艺术完整性[M].张守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280.
编辑:黄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