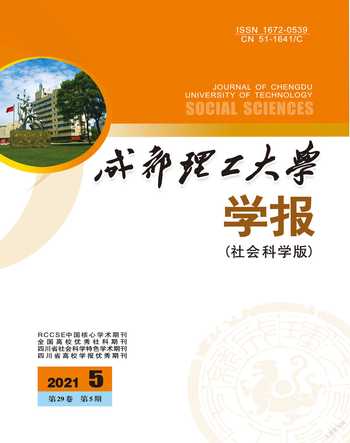论职后受财行为的认定
作者简介:汪豪(1996-),男,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摘 要: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常常具有“期权化”的特点,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其日益成为职务犯罪中预防和打击的重点。面对此类新型受贿方式,司法实践困境的“症结”在于过度重视客观的危害结果,而有意弱化甚至忽视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对于双方不存在“事先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是否成立受贿罪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及行为人是否具备受贿的故意,避免客观归罪。具体操作上,为避免不当扩大打击范围,需区分事先有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并且对受贿罪的实行行为进行严格解释,以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相结合。
关键词:受贿罪;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职后受财行为;事先约定
中图分类号: D924.3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5-0036-07
一、问题之提出
随着国家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传统受贿模式发生了变化,司法实践中逐渐出现不少新型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其中“期权化”的离职型受贿常常由于时间跨度之长、空间变化之大而表现出极大的隐秘性和复杂多样性,如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为降低权钱交易的风险,逃避法律制裁,其在职时未收受财物而是在离职后收受。与之相呼应的是,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拓宽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相关司法解释也逐步对离职型受贿作扩张解释,以期囊括更多逃避法律制裁的职后受财行为。诚如有学者所言,近年司法解释对贪污贿赂类犯罪和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足以说明当下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与颁行进入了非常频繁的时期”[1]。我国刑法虽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作了规定,但对于其中职后受财行为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该类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仍有待检视。
2016年4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规定(1),国家工作人员事先未接受他人请托,但事后基于相关的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同样成立受贿罪。该条所规定的行为模式是“未约定事后收受他人财物—履行职务—收受财物”,将其归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之一,从而认定此种情形成立受贿罪。问题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的,在双方没有事先约定或事后确认的情形下,这种对价交易关系在外部上是难以识别的,此时一律将其认定为受贿罪在正当性上不无疑问。对此,有学者指出,此种情形由于已经履行完毕职务行为,在事后收受财物之时,不可能再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目的[2]。进一步认为,“这种做法虽然满足了时下社会整体强烈的反腐要求,但也引起了偏离受贿罪的法条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担心。”[3]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的入罪法理,是通过缓和事后主观故意的认定,将贿赂犯罪由要求具备明确的对价交易约定,扩展到“可能知情”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顺应贪污贿赂犯罪打击的需要,为实践提供了一种规范依据。但是,仅仅为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而将职后受财行为具有可能的对价交易就认定为受贿罪,有违反罪刑法定要求之虞,使得司法适用受到了正当性的质疑。因而,有必要对职后受财行为的性质进行深入分析,严格把握职后受财行为成立受贿罪的标准,避免离职型受贿范围的无限扩大,以期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相统一。基于此,本文在梳理现有刑法关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行为性质认定的基础上,以《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为切入点,尝试对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关于职后受财行为性质的争议进行归纳;接着,就职后受财行为的主观故意和法益侵害进行证成;最后,在具体操作上,认为应区分事先有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并对受贿罪的实行行为进行严格解释。
二、职后受财行为性质的检视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或称职后受财行为(2),是指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在离职后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4]。对于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形,由于通常很难证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导致对于该类型情形入罪的认定标准不一。是否有必要区分有無“事先约定”,以及关于事先没有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是否一律构成受贿罪,我国刑法学界的立场也不乏争议,历来存在着否定说、肯定说和区分说的不同观点。
(一)职后受财性质的争议和评述
1.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有必要区分有无事先约定,由于行为人通常在主观上不存在受贿故意,而只有收受财物的故意,故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不构成受贿罪[5]。该说的理由主要如下:
(1)不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必然会存在交易的对价关系,即双方交易的“职务”和“财物”,而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没有职务行为可以“出卖”,请托人也无法再“收买”已经过去的国家职务。因此,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无法体现交易的关系。
(2)不具备受贿的故意。受贿罪是故意犯罪,其要求行为人在收受财物时至少要有主观上的认识,即行为人要具备接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和明知他人是基于之前的请托事项而给付财物主观意图[6]。该种情形下,由于行为人履职时未被请托,主观上不具备受贿的故意。因此,从严格逻辑上来讲并不构成受贿罪。
2.肯定说
肯定说则认为没有必要区分有无事先约定的情形,因为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一旦认定职务行为与财物具有对价性,事先没有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同样成立受贿罪[7]588。该说的理由主要如下:
(1)职后受财行为侵犯了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任何犯罪的实行行为都表现出侵害法益的危险,如果某种行为并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它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的实行行为,更谈不上构成犯罪。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仍然关注的是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情形,若职后受财行为存在“交易”的情形,同样成立受贿罪。
(2)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该说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一旦将职务行为当作收受他人财物的对价时,就可以认定其具备受贿的主观故意。
3.区分说
除了前述两种观点外,还有学者认为应当采区分说,即对于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是否成立受贿罪并未持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不宜简单地将所探讨的对象一刀切。该说认为,事前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缺乏受贿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原则上不构成受贿罪。但同时指出,职后受财行为并非绝对一律不能成立受贿罪,若存在以下情形,可认定成立受贿罪,即行为人在为请托人谋利益之前,双方并没有约定事成之后有“酬谢”,但是行为人具有获得对方酬谢的主观期待,且事实上请托人确实也送予行为人酬谢[8]。
本文赞同区分说,对于事先并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分析。职后受财行为要成立受贿罪原则上仍需坚持“事先约定”的要件,同时,对于没有事先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不能简单认为双方就不存在权钱交易的合意,只有在能够明确行为人有获得对方酬谢的主观故意情形下,才能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进而构成受贿罪。否定说中较为有力的理由是认为受贿罪是故意犯罪,故意内容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故意及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故意,只有同时具备这两者才符合受贿罪的故意内容,若缺少其中一者都不能认定其构成受贿罪。但是该观点人为地将受贿的整个行为过程分割成两部分,要求两阶段都具备故意才构成受贿罪,认定范围明显过于狭窄。此为其一。其二,肯定说容易造成客观归罪,同样存在缺陷。按照该说的观点,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行为,无论是否有“事先约定”这一条件,只要收受了财物,就构成受贿罪。并非所有的职后受财行为人都具备受贿罪所必备的构成要件,肯定说的观点突破了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显然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二)职后受财行为的司法规制
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指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与受托人是否有“事先约定”,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们谋利并事先约定离退休后收受财物的,才成立受贿罪(3)。
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十条重申了这一立场,同样采纳了否定说的观点,这一点从起草单位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关于《意见》中的“事先约定”,起草单位有关人员解释道:“《批复》的立场应予坚持,若没有‘事先约定’的在先条件,将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行为一概当做受贿罪处理,容易造成客观归罪。”[9]
2016年4月两高发布《贪污贿赂解释》,该司法解释摒弃了一直以来坚持的否定说立场转而采取肯定说,意味着今后对于职后受财行为,即便事先没有约定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事先约定,也构成受贿罪。该司法解释起草者对该项规定背后的起草原因解答时明确指出,适用本项规定时应注意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收受财物的情形,成立受贿罪需坚持双方存在事先约定的先决条件。本项规定同样受此约束,不能认为本项规定修改了此前文件的规定[10]。理论上也有观点认为,司法解释将“权钱分离”的交易方式拟制为“权钱交易”, 将事后受贿行为的违法性从司法的角度上予以认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1]。上述观点主要是从司法实践办案需要的考虑出发,意图弱化受贿罪主观故意的证明负担,但是,这样的解读极大地虚化了受贿罪主观故意的构成要件。如有学者从该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正当性出发,认为司法解释企图将“未约定事后收受他人财物—履行职务—收受财物”这一模式纳入事后受贿的范围,但又碍于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关系,于是退而求其次,将这一模式强行解释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认定行为人入罪[12]。陈兴良教授进而指出,这一规定不适当地扩张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抵牾[13]。可见,学界对司法解释中职后受财型受贿规定的正当性存在诸多质疑,认为第十三条的规定偏离受贿罪刑法教义学的解释,有悖离刑法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嫌。对此,应对《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进行严谨细致的教义学论证,对其中职后受财型行为的性质认定进行厘清和证成。
三、职后受财行为性质的证成
按照《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即使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未对他人的请托事项作出明确回应,但离职后国家工作人员也同样可能明知对方给予财物的目的,此时就被视为为他人谋取请托事项的相关利益,进而表明,双方就财物与职权之间对价关系達成了合意。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往往在实践中被直接适用,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清晰的阐释。在刑法教义学上,职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关键在于该类行为主观上是否具备受贿故意以及客观上是否侵害了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由于行为人履行职务过程中尚未产生收受财物的意图,通常很难证明主观上有收受贿赂的意图,此时,一律认定其构成受贿罪在正当性上面临着质疑。同时,判断该类行为是否成立受贿罪,还要关注受贿罪成立的客观构成要件,在此基础上分析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对此下文将予以证成。
(一)客观上有法益侵害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仍存有较大差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廉洁性说。廉洁性说主张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14],该说自诞生以来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起草的相关人员采职务廉洁性说的观点,沿袭了之前的立场,认为“只要收受财物与其先前职务行为存在关联,其收受财物的行为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10]。第二,公正性说。该说认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为黎宏教授所提倡,其认为受贿罪所要规制的是收受他人贿赂这种行为引起的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侵害及危险[15],因为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正常职务行为,同样可能侵害国家职务的公正性。第三,信赖说。信赖说主张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民对职务行为的信赖利益。有学者认为,一般国民对国家职务行为存在某种关系上的信赖,若这种信赖受到贪污贿赂的侵害,很可能会引起一般国民对国家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国民对国家信赖感的丧失,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无疑是十分危险的[16]。第四,不可收买性说。该说的倡导者认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刑法规定中的职务行为廉洁性应是指其不可收买性[17-19]。
目前我国刑法学上关于受贿罪保护法益的争议,学者们基于各自的理论立场采取了不同的观点,或从现行刑法的规定进行分析,或积极回应现阶段反腐败形势政策的需要,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本文在对受贿犯罪侵害法益做进一步的分析基础上,赞同受贿罪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观点,具体理由如下:其一,不可收买性说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协调。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有获得工资报酬的权利,这意味着公務员不得再通过其职务上的行为获取其他不正当报酬,或将其作为一种获利的手段在他处获取相应的对价。反之,公正性说与刑法规范的表述并不协调,因为若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话,其关注的重点理应是对职务公正性的侵害,而不应是收受贿赂,但实际上存在公正履行职务且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20],而这正是公正性说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其二,不可收买性说能更好地界定受贿罪的范围,避免刑法规制范围的扩张。公正性说的不足之处在于与其他渎职行为的处理不相协调,因为受贿罪与渎职犯罪的都可能会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公正性。因为渎职罪同样存在对公正性的侵犯的可能,如果说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正性,那么同样可以说公正性也是渎职犯罪的保护法益[7]475[21]。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之下,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所主张的观点比其他观点更具经验实在性。其三,不可收买性说更加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我国刑法理论上大多都认同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其关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有无被收买的可能。是否成立受贿罪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履职行为和收受财物的交易性,即使是在收受财物后合理履行职务的行为,由于此种情形已然具备了“职务”和“贿赂”的交易关系,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同样可能构成受贿罪。
学界当前普遍承认受贿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的对价,立法机关在解读受贿罪立法规定时就指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贿赂,进行权钱交易,是严重的腐败行为。”[22]受贿罪所保护的国家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法益正是权钱交易背后所展现出的实质,这也是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范性评价。具体到受贿罪的法益侵害层面,刑法所规制的并非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不被交易,这表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仍然关注的是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情形。就职后受财而言,其并不排除有交易的可能性,虽然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与离职后收受财物的行为存在时间上的间隔,但是两者在时空上的分离并不能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其在职时谋利和离职后受财的对价关系,造成了对职务行为的出卖,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符合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
(二)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
如前所述,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则是需要双方对此存在明知且形成合意。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事前或事后都没有表态,只是在离职后收受了他人财物,此时仅仅表明了一种存在权钱交易对价关系的可能性,还达不到受贿罪要求主观故意确定性的要求。《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实质上意味着只要双方存在形成交易对价关系的可能性,就可以视为达到构成犯罪所要求的明确的交易对价合意,将受贿罪主观故意的确定性要求扩大到可能性,此时就具备贿赂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对于受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从认识因素的角度来看,要求行为人意识到利用该职务上的行为作为对价,对于行为人事先有约定的情形,双方对离职后收受财物达成合意,说明其已经认识到权钱交易的性质以及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从意志因素的角度看,行为人明知他人给予的是交易对价,其已经侵害了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却对此危害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此时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受贿的故意。实践中越来越常见的职后受财行为,“尤其是涉及一些位高权重的受贿案件,这些人往往既要面子又爱钱财,权钱交易往往以一种彼此默契的方式进行,根本不需要事先的商量或者暗示”[23]。这类行为很可能就会因为双方没有事先约定而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被行为人想方设法规避掉。职后受财行为是否表明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其结论具有不确定性,不能无需证明地就直接推导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因此,如何准确界定受贿意图显得尤为重要。
在无事先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的场合,对于受贿的故意要严格认定。通常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并未有收受贿赂的意图,此时很难说其就一定有受贿的故意,但在离职后行为人已经认识到此时请托人给予财物的性质,很大程度上能够判断出其可能认识到已经侵犯到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此时能够认定行为人具备受贿的故意。如在万曾炜受贿一案中,被告人万曾炜在职期间并未与相关人员约定事后收受相关财物,后在离职及退休后分别收受了相关人员的财物(4)。在案件审理期间,法院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对于事先未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主观上并不具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收受财物的行为,认定其受贿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故不能以受贿罪定罪处罚”[24]。然而,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受贿故意并非一定形成于在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之时,即便是在职时没有收受贿赂的故意,但离职后收受财物时只要意识到该财物与先前的职务行为存在对价关系而收受,表明此时行为人将财物作为先前职务行为的对价,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形成了受贿的故意。仅仅因为受贿行为时间上出现了间隔而将整个行为加以割裂,进行分别评价,这并不严谨[25]。从整体上看,行为人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明知其是基于先前的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自然可以认定具有受贿的故意。换言之,双方的行为即是一种默示约定的具体表现,没有事先就报酬达成具体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没有约定。就社会一般人而言,行为人都会首先将曾经实施过的职务便利行为与其接受的请托人的财物联系到一起,此时很难说行为人没有认识到他人赠予的财物是由于自己曾为他人谋利过从而没认识这种对价关系,那么一旦行为人可能认识到这种交易的对价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完全符合受贿罪主观方面要件。
综上,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原则上不构成受贿罪,对此需要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和主观故意两个角度严格把握。结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无论是在离职之前还是之后产生了受贿的意图,只要基于该履职事由,将职务行为作为收受他人财物的对价时,就足以认定当事人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至于职务行为是何时实施的,不影响其构成受贿罪[26]。国家工作人员在离职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约定之职后收受的,当然具有前述所说的受贿故意,但对于事先并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不应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只要能够肯定其具有受贿故意,同样构成受贿罪。
四、职后受财行为认定路径的完善
(一)区分事先有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职后受财行为入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可能知道具体请托事项,而不能仅仅根据收受财物和感情联络的内心意图来推定。否则,就是按照行为人“可能知晓”来拟制存在故意,因为在认定对价关系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建立在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基础之上。司法实践在对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进行解释时,应当弱化司法解释中对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约定”的要件色彩,回归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从客观保护法益和主观受贿故意综合认定,从而将更多类似的“隐蔽”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当中。
如前所述,对于事先并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不应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只有肯定行为人主观上具备受贿故意,才应认定构成受贿罪。因此,可以将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其在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且主观上具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意图,并在离职后予以收受的;另一种则是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并不存在收受财物的主观意图,但在离职后同样收受了请托人送予的财物。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事先有收受财物的主观意图的行为,很明显前者的可谴责性大于后者,应予以重点关注,而后者只有在行为人具备主观上具备受贿故意以及客观上侵害了受贿罪保护法益的情况下才成立受贿罪。
(二)对受贿罪的实行行为类型严格解释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犯罪形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两高出台的任何司法解释都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当一种新类型的行为出现并且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定时,应当通过解释刑法予以明确,这样才符合法律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在反腐长期保持高压的背景下,受贿犯罪呈现出演变、升级的态势,典型的“收钱办事”的传统受贿模式发生了变化,贿赂行为的手段和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职后受财这一行为类型作了明确规定,但结合当下贪污贿赂犯罪的背景,“期权化”的受贿模式已经较为普遍,其可以看成是与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并列的另一类受贿罪的实行行为。诚然,刑法既要保持稳定性和安定性,也要适应社会从而不断发展,正如著名法学家庞德所言的“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滞不前”,但直接要求从立法上更改或者增设新法条都显得有点鲁莽,并不是最合适且最经济的解决办法。因此,本文认为,面对刑法条文事先未规定或未明确规定的情况,有必要通过解释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受贿罪的事先無约定的职后受贿行为囊括进来。对职后受财行为进行扩大解释,这不仅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而且有利于我国职务预防制度的完善。
五、结语
《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三条虽然从字面上取消了“事先约定”的条件,这无疑有利于扩大对贪污贿赂等不法行为的打击面,对这类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该解释的出台,并未解决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尤其是职后受财的范围、职后受财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等问题都尚存疑问。若这些问题无法得以明确,不仅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准确界定一些非典型的受贿行为,而且可能有违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和主客观一致原则。刑法的机能不仅在于保护法益,还在于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严格把握职后受财行为成立受贿罪的标准,对权钱交易本质在刑法上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阐释,避免将部分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入罪化,如此更容易实现司法公正和合理的目标。对于双方不存在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事先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是否成立受贿罪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认定构成受贿罪需要从行为人是否侵害了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以及是否具备受贿故意的角度出发,避免客观归罪。因此,在界定职后受财行为时,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证成,并遵循主客观一致原则,以期做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相结合。
注释:
(1)参见《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2)对于本文所指的职后受财行为,有必要在此予以说明。我国传统通说和司法实践中,职后受财有两种情形:第一类是事先有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这类情形属于普通受贿罪的范围;第二类是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这种事先没有约定或者无法证明事先有约定的情形,通常很难证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由于事先有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构成受贿罪当前并无争议,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提及到的职后受财行为都是指无事先约定的职后受财行为。
(3)参见《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4)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刑初字第102号。
参考文献:
[1]刘宪权.贪污贿赂犯罪最新定罪量刑标准体系化评析[J].法学,2016,(5):79-92.
[2]陈兴良.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刑法教义学的阐释[J].法学,2016,(5):65-78..
[3]黎宏.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与事后受财行为的定性[J].中国法学,2017,(4):227-245.
[4]郭竹梅.受贿罪司法适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279.
[5]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642.
[6]陈兴良.规范刑法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198.
[7]孙国祥.贪污贿赂犯罪研究(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8]边学文,马忠诚.“事后受财”行为能否构成犯罪——解一道商业贿赂的法律难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5-18.
[9]刘为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7,(15):17-24.
[10]裴显鼎,苗有水,刘为波,等.《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应用),2016,(19):17-24.
[11]紀康.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将何去何从——以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视角[J].德州学院学报,2017,33(1):71-75.
[12]黄伟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探讨——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刑法教义学评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38-48.
[13]陈兴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与认定——以两高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中心[J].法学评论,2016,34(4):1-9.
[1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7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09.
[15]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条的解释[J].法学研究,2017,39(1):66-79.
[16]郑泽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贿赂之范围[J].兰州学刊,2011,(12):61-70.
[17]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27.
[18]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17.
[19]刘艳红.刑法学(下)[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49.
[20]张明楷.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J].法学研究,2018,40(1):146-166.
[21]孙国祥.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实践意义[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36(2):131-142.
[2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80.
[23]杨兴国.贪污贿赂犯罪认定[M].2版.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191.
[24]周芝国,费晔.事先未约定回报离职后收取财物构成受贿[J].人民司法(案例),2016,(5):26-27.
[25]赵秉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6.
[26]孙国祥.“职后酬谢型受财”行为受贿性质的理论证成[J].人民检察,2015,(1):16-22.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