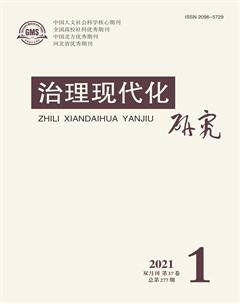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
唐任伍 孟娜 刘洋
摘 要:“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乡村中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动力,其成员是乡村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内涵和特征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新乡贤”在引领现代乡风民风家风的文明价值建设,推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基层治理模式建立,营建现代化的乡村经营体系,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乡村振兴战略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1-0036-08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资本的力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与生产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指人、群体之间的一种紧密联系,以无形的状态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表现为社会规范、信任、道德、价值观以及社会网络,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社会整合程度。乡村中关系型社会资本是由长期的社会个人往来、互利合作、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因此,农村社会共同体的信任、互利以及集体合作构成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尽管农村社会资本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发展而呈现出各种形式以及变化,但它为组织农村社会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的变化以及确立个人行为依据提供了非正式制度基础。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是现代乡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凝聚“化身”或者“人化”,构建了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及互惠互利网络,增强了乡村振兴的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内外动力。研究作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乡贤”到“新乡贤”:
内涵、职能的嬗变
“新乡贤”一词是“乡贤”在现代社会的表达,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国家迈进过程中,从“乡贤”到“新乡贤”,其内涵烙刻着历史的轨迹和时代的变迁。
传统的“乡贤”指的是村镇中多才多能、有较大作为、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社会贤达人士。“乡贤”一词连用,最初出现在东汉。随着时代变迁,“乡贤”一词使用日盛,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际,一些为躲避政治,退隐乡里过着闲云野鹤日子的为官者和士大夫,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1](P65),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乡贤”转化为“乡绅”,获得功名而不为官的儒生和告老还乡的官员成为“乡绅”或者“乡贤”的主要成员,“乡绅”或者“乡贤”成为介于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层,“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诫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2]。
“乡绅”“乡贤”群体的出现与封建制度密不可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行政管理层级多、信息传递层层衰减,导致中央集权的势力不断被削弱,到达乡村一级时官府便成了强弩之末,以致宋代便有了“皇权不下县”之说。为了弥补政府势力在乡村的弱化,保甲制应运而生,一方面协助朝廷征收税赋徭役,另一方面维持地方安定,保甲制也因此被执政者沿用至民国时期。传统的中国农村的“乡绅治村”现象诞生于保甲制。“乡绅”“乡贤”常年生活于此,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多是大家族中有威望、明事理、敢于决断的族长,或是拥有财富且对当地作出贡献的声名卓著的士绅。这些“乡绅”“乡贤”上能向官府表达民意、下能了解百姓心声。随着时代的发展,附有职业等级味道的“乡绅”一词逐渐被附有道德评价的“乡贤”一词所取代,并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
“乡贤”既学识渊博又身居高位,即使退居乡里仍然具有极大的威信,其公道正直的品德,都让乡民们信服。因此,在当地化解乡里各种矛盾,处理乡民之间各种纠纷,“乡贤”在为乡民百姓谋取利益的基础上,从而获得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到了明清之际,人才的作用日益彰显,“乡贤”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各州各县都设有乡贤祠,用以表彰与纪念对本地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历代“乡贤”都会协助官府处理诸如挖渠筑坝、抢险救灾、架桥修路等当地事务,还会发挥个人影响淳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3]。在基层社会发展进程中“乡贤”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鸦片战争后,由于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加之外国列强侵略,乡贤不愿继续在台前服务乡民百姓,转而选择隐退,“乡贤”群体衰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被新型的平等关系所替代,人与人之间尽管有职业不同、分工的差别,但地位、人格、身份上都是平等的,农村的社会结构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才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有知识、有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壮年,是乡村中的优质生产力,更是乡村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青壮年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流失,留在偌大乡村中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人们俗称为“三八六零六一”“部队”,乡村的土地、工具这些死的生产力无法与活的生产力“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因而无法生产出物质财富,广大乡村急剧衰落,严重空心化,变得死气沉沉。因此,在乡村发展面临着困境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接连出台新型城镇化战略、美丽乡村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村振兴战略是事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战略。而要使这一战略实施获得成功,人才是关键。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救赎乡村衰落之时,“乡贤”成为大多数有识之士的热切期盼。
按照《词源》的释义以及“乡贤”原意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演化,“乡贤”指的是在“乡”这一中国古老行政单位中“多才多能”的人,后来逐渐成为国家或社会对一些道德品质高尚、具有儒家学问、有所作为的官员,或是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在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1](P65)。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始终是联结统治者、治国理政者与乡民百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当统治者的公共决策与地方民意产生冲突时,“乡贤”利用自身威望代表乡民百姓与统治者进行沟通交流。“乡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各方利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因此“乡贤”能得到官府、地方宗族、乡民百姓的多方支持。“乡贤”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的人生价值、道德品质乃至学问的一种正面肯定。
传统的“乡贤”发展到新时代,内涵更加丰富,失去了传统作为“表彰的荣誉称号”的意义,仅保留“多才多能”的评价,因此被人们称为“新乡贤”。所谓“新乡贤”,是指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本地乡土有联系的,有知识、有能力、依靠较高的道德素养和感召力,对乡村振兴发挥建言献策、出谋划策,为乡村振兴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贤达和精英。“新乡贤”完全超出了“乡贤”局限于“士绅”的范畴,涵盖的范围更广更宽泛,组成群体更多元,包括各种类型的精英人才,诸如技术能手、致富能人、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等,他们有的在当地生活、工作,有的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或其他形式回到家乡,为当地的乡村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要是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人,无论是在体制内工作的离退休返鄉的官员、教师、医护人员、军人,还是文人学者、企业家、海外华人华侨,甚至返乡大学生、在外打工经商的村民,都成为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贤”。“新乡贤”这种多元、包容的群体结构,这种成长于乡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经历,既保障了资源的丰富性,又保障了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质。
正是因为“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新乡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界也引发了热烈讨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新乡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新乡贤”建言献策;2017年、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阐析。“新乡贤”文化传承并发展了传统乡贤文化中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并赋予“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的新时代特点,不单是传统中国文化在新时代乡村社会的表现,还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更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最终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二、“新乡贤”成为新时代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动力源
中国社会随着农耕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关联逐渐取代原有的地缘关系,村民之间的关系功利性增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村进城务工,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老人农业”成为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课题[5]。加之农民自身对乡贤的认同感降低,因此传统意义上那种一呼百应、既是桥梁纽带又能掌控大局的乡贤很难再出现。大量优质的代表着农村中先进生产力的青壮年农民的外出,造成了农村人才的空心化,大量土地撂荒,乡村逐渐衰落。
在乡村逐渐衰落的同时,中国的城市一片繁荣,城市化获得了大的发展,到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文明逐渐代替乡村文明。传统的乡村建设模式被打破,乡村村落呈现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层叠社会形态”[6](P74)。面对如此乡村困局,中央自2004年开始,连续十多年以“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的方式,重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村建设现代化,为此还发布多项政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增加惠农、强农专项资金。党的十九大又专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解决“三农”问题的议题推向新的高潮。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城乡差别始终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道难题,是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一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人才匮乏,有的乡村出现“刁民”群体化现象,继而演变成主流,替代农民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策者[7](P31)。因此,为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乡村亟须探索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协同共建之路,“新乡贤”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新乡贤”作为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是乡村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新乡贤”,至少包括下列五类人士:
一是体制内工作离退休返乡的官员、教师、医护人员、工人、复转军人等。这些人可以称为“五老”,即老干部、老教师、老医生、老工人、老军人,他们长期在体制内工作,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专业技术,见多识广,社会关系多,离退休以后,有的回归故土,将自己拥有的知识、资源与技术奉献给家乡,为家乡的振兴贡献才华和智慧。例如,曾经担任过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将军解甲归田,带领全家人返回江西老家农村,做了一名“将军农民”,利用自己的见识、威望以及社会影响等社会资本,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造福于家乡的老百姓;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后回到家乡,22年间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发展了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并将之无偿捐给国家,带动家乡人就业。
二是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和老基层干部。这些人有“三老”之称,即老支书、老主任、老党员,他们长期工作在乡村基层第一线,在位时公道正派,没有私心,为老百姓谋福利,说话有分量,村里人信服,深得老百姓拥护和爱戴;退位后威信仍在,鉴于对村里事务了如指掌,仍受到村民们信任发挥自身的余热。这类人有德有为有位,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宝贵财富、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心骨、乡村发展的稳定器。民营企业碧桂园在广东清远农村开展精准扶贫时,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发挥乡村中“三老”的“新乡贤”作用,有效化解了扶贫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拆迁、搬迁、公共设施建设等各种矛盾,减少了阻碍,降低了扶贫过程的交易成本。
三是当地各类模范人物。这些人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肯读书爱思考,关心国内外大事,视野比较开阔,有乡村土秀才之称。再加上长期在乡村建设中摸爬滚打,奉献付出,可耕可读,在各个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成为当地的精英、致富能手、劳动模范、文明榜样、道德楷模,在认识与见解上高出他人一筹,说话做事有一定高度,为百姓排忧解难、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尤其在百姓关心的“家长里短”“红白喜事”上有很大的话语权,愿意为乡亲们办实事,在百姓心中享有崇高威望,是新时代乡村的社会贤达,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贡献智慧和才干。
四是在城市务工创业的“新市民”和回乡建功立业的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有一定文化的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去务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他们经历了城市文明的洗礼,受到市场经济的熏陶,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掌握了一技之长,成为经济建设的能手,有的甚至自己创业成功,成为“小老板”,掌握了先进的管理技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他们心系家乡,致富不忘本,带着改变家乡面貌的愿望和技术资金回乡创业,承包家乡的土地、荒山、鱼塘,开办纺织厂、养鸡场、养猪场,搞特种种植业、养殖业,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带领家乡人民脱贫致富,改变家乡面貌。如江苏句容唐陵村支部书记刘树安,在城市打工创业成功后,回到家乡,利用家乡典型的丘陵岗坡地特点,发展苗木产业,形成了以苗木种植销售为主以及苗木经纪人包装运输、劳务编织和住宿餐饮一条龙产业链,振兴了家乡,富裕了老乡。这类人越来越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新乡贤”。
五是从乡村中走出去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这些人从家乡走出去,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虽身在异乡,但心系桑梓,希望看到家乡的变化,看到父老乡亲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因此愿意通过自己的知识、技术、资金、项目,为乡村振兴出钱出力、建言献策。这类“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虽然并不一定亲力亲为,但他们通过项目投资、专利出让、技术支持、出主意、给点子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广东、浙江、福建一带有很多的乡村,侨胞和华侨支持修桥修路,开办企业,这些依靠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支持富起来的侨胞村、华侨村,就是“新乡贤”的贡献。
“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新”,不但表现在他们对家乡振兴的期待,更在于他们回报家乡这片土地的殷殷之情,愿意通过自己的知识、才华、资金、技术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贡献,无论是“在乡”的乡贤和“不在乡”的乡贤,都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更丰富的资源,为乡村振兴贡献出更多财力、物力和智力,譬如传承乡村民间文化、资助乡村教育发展、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经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调解邻里矛盾纠纷等。
二是“新乡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族长,他们具有民主素养,身上散发着现代文明气息,致力于率先垂范、多做实事,以自己的言行感召村民,在村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从不居功自傲,更没有倚仗权势和实力干涉乡村治理事务,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为人处世,与村民保持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将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三是“新乡贤”群体广泛,类型多种,包容性强,政治精英、道德精英、文化精英、技术精英、商业精英等,有在乡的不在乡的,有国内的国外的,有離退休后叶落归根的,有外出打工创业的,他们具有不同的资源,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构成不同的类型,但都满怀乡土情结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中,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作出独特的贡献。
四是“新乡贤”普遍具有较高的品行和声望,他们以德化人,孝老爱亲,道德情操高尚,富有奉献牺牲精神,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内在的动力。“新乡贤”群体由退休返乡的政府官员、德高望重的基层老干部、榜样模范、贤人志士、业界精英组成,既是风气教化的实施者,又是公共事务的建设者,同时还是纠纷矛盾的调解者,是政治体制之外的“魅力权威”。正是因为有他们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文化传承、风俗教化、价值引领、出钱出力,大大增加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实施阻力,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更有效率。
三、“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的作用发挥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尚贤”“重能”,使乡贤文化具有独特的地方魅力和特色。乡贤文化的主体是乡绅,他们在乡村的宗族治理、民风淳化、道德伦理维系等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乡贤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乡村、扎根于乡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维系乡村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复兴乡贤文化[8](P11),不仅承载着联结家族血脉、传承族群文化,还是全世界华人华侨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精神归属和栖息家园。这种根植于血脉的精神内核成为“新乡贤”回归、实现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同时乡村社会也成为“新乡贤”的根之所在、魂之所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村是人们的根,历史上的“乡绅治村”对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促进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9],使得德才兼备的乡村精英和反哺乡村的各界乡贤开始出现。“新乡贤”和传统乡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体现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乡村稳定和繁荣中的重要地位。但传统的“乡绅治村”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借助乡绅的力量对乡村社会实施的控制,实质上是为封建政权服务的;而“新乡贤”涵盖的范围更广泛,不仅仅是政界、商界、学界及各类成功人士回归乡里、反哺家乡,而且是带领村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中国农村走向“善治”的“借力”[10]“借智”举措。
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封闭向开放全面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场域内的利益主体结构发生重整,基层政权退化[11](P32)导致乡村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快速衰落,村庄共同体迅速解体[12](P42),个别地方的乡村甚至出现黑恶势力入侵和乡镇基层政权退化。因此,吸引“新乡贤”回归乡村,实现“乡民”与“新乡贤”有机融合,形成乡村民众和乡村精英结合起来的新的治理模式,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9],整体上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破解乡村治理中面临的种种治理困境,使乡村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环节。
(一)引领现代乡风民风家风的文明价值建设
作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化身的“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价值引领上弘扬乡村振兴战略的正能量,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沿着一条正确的轨道进行。
乡村振兴首先要在乡村中引入现代文明,破除腐朽封建迷信的落后习俗和价值观,使现代文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正能量的推进作用,从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新乡贤文化”本身是一种有着榜样力量的文化,“新乡贤”作为乡村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崇德向善、致力于公益事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先导者。封建社会的乡绅阶层垄断各种资源,所以他们才得以推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乡贤”拥有丰富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需要的资源。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很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从政从军,或创业经商,或从事教育、科技、医疗和其他行业,且在各自的领域中卓有成就,成为“道德精英”“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又都怀有浓厚的桑梓情、故乡意。“新乡贤”身上的文化道德力量可以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有利于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传统乡村文化,更有利于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智力、有效运用财富的能力,而且需要“道德精英”维系文化传承和维护社会和谐。“新乡贤”是“道德精英”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地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口碑好,深受民众尊崇,一直在乡村振兴中承担着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民风家风等重要责任,扮演着重要角色。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同时,中国的乡村社会在精神道德层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广大乡村民众在传统心智还占据主导地位之际,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冲击使他们无所适从,功利主义色彩愈发厚重,继而出现乡村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村民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危机,公共精神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村民的乡村归属感降低;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性降低,乡村认同感下降[13](P100)。因此,向民众推行文明、和谐、法治、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而“新乡贤”正是传播这些价值的积极力量。
“新乡贤”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把离开家乡的人和留在家乡的人重新黏合起来、凝聚认同,并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让乡土社会更好地黏合起来[14]。乡贤作为连接本土传统乡情和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14]。“新乡贤”无论是作为“黏合剂”还是作为桥梁纽带,都是基于对家乡和国家的强烈认同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者,需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蕴含的内在潜力,使之与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中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起来,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要求,构建起包括“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群众”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重评价机制,打造出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学识卓越的“新乡贤”队伍。同时通过招募教师、医生、村干部、企业家、志愿者、爱乡爱村模范等系列活动,把那些德行好、口碑好的“在乡”和“不在鄉”的“新乡贤”推选出来,开展“新乡贤”评选表彰,并向他们颁发最美“新乡贤”证书,授予荣誉,建立荣誉墙,竖立荣誉碑,举办“新乡贤文化节”“新乡贤文化研讨会”等主题活动,通过报纸、广播和各种新媒体,向群众弘扬“新乡贤”文化,使“新乡贤”的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情操内化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有效激励广大村民,涵养积极向善、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增强“新乡贤”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更有责任感地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和手段回报家乡,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二)推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基层治理模式建立
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是在乡村建立一个良性、文明、现代的治理结构。当今中国乡村贫穷落后、“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的乡村美景逐渐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有效解决乡村复杂局面的治理体系和科学的治理结构。乡村振兴,亟须回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从中寻找出破解之道。因此,“乡绅治村”的模式对于目前乡村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乡村秩序和谐的实现单靠外力干预难以持久,村庄的内生性才是实现乡村秩序和谐的动力之源。其中内生的村庄秩序通过村庄内部人与人的联系而形成的行动能力进而为乡村社会提供秩序基础[15](P124)。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力量、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两种不同性质和向度的力量。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16](P89)。因此乡村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乡村精英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整个中国治理体系薄弱环节的乡村中实施这样一个巨大战略,要面对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务多、基层自治要求高、任务重等大大小小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新乡贤”参事会,利用熟人社会的集聚效应,为村级治理配好智囊团,推动基层组织协商民主,探索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17](P101)。
“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推动者,是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建立的中坚力量,在乡村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者,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一要建立起对“新乡贤”鼓励引导的机制,包括履职激励机制、荣誉授予机制和公益捐建冠名机制。以对家乡的感情为纽带,吸引本地的、外地的、在乡的、不在乡的企业家、党政干部、学者、医生等各行各业的技能人才等回归,壮大“新乡贤”队伍,鼓励“新乡贤”通过投资创业、行医办学、捐款捐物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二要给予“新乡贤”恰当的参与身份,使他们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这个大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干和价值。鼓励并引导优秀的“新乡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第一书记、村主任等,为他们提供服务群众、服务乡村振兴的舞台。三要建立有政府、村“两委”、群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对“新乡贤”的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以确保“新乡贤”队伍的纯洁性和公信力。建立内外部精英流通和外部精英内部化机制,既重视本土“新乡贤”培育,又加强在外“新乡贤”的发现和选拔,不断充实完善“新乡贤”结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人才短缺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的强力支撑。
(三)营建现代化的乡村经营体系
“新乡贤”大多是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纽带,因求学、经商而走向更广阔社会的精英。他们道德品行好,才学出众,视野开阔,又有公益情怀。地缘、人缘和亲缘将他们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吸引和凝聚他们用其学识专长和经验等各类社会资本反哺桑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因此,“新乡贤”将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本加以优化,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在乡村中营造起现代化程度高、市场能力强的乡村经营体系。经营型“新乡贤”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经营企业、种植业、养殖业或其他经贸活动方面的优势,营建起规模化的农业合作社,发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把乡村振兴经济基础做扎实,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技能型“新乡贤”可以发挥自身在农业种植和养殖、加工制造、建筑装修等方面的技术特长,为村民提供生产管理、产品包装、农产品销售中的各种咨询和服务,提高农民的收入。文化型“新乡贤”可以发挥自身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和特长,推进乡村文娱设施的建设和乡民文娱生活的改善,整理传承乡村民间文化,组织提供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既可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又可以提高村民的收入。公益型“新乡贤”发挥自身组织能力强,活动范围广,联系人口多的优势,通过做公益、做慈善,筹集资金,在村容村貌整治、通村道路建设、水电网改造、乡村文化广场修建、养老助学等方面,贡献力量,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发展。
(四)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
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升乡村中的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上说,中国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城市。一般来说,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都应该由政府來提供,但由于20世纪末期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现象严重,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18](P26),国家从200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废止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种田交税”模式的终结,中国农民从此挣脱了压在身上几千年的沉重枷锁,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结构进入了一个转型期。接下来国家通过种粮直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村村通公路、在农村实行厕所革命、自来水革命和垃圾革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幅度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国家尝试建立起一套惠民利民的面对面关系,因此以往“乡政村治”模式过度压制村民的自治模式在实际运用中逐渐式微。
废止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但是由于废止农业税切断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联系,乡镇基层政府无法再从农村提取资源,也就不再参与农村的公共事务和农业生产,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村级组织在村级事务中的功能日益弱化,在事权上收、工资统发状态下,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只从事一些次要的、从属性的工作。基层政府治理功能严重弱化,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上也越来越捉襟见肘,这也就意味着涉及农村公共事务的道路整修、公共水电设施等诸多事项就需要依靠乡民自己来完成。另外,随着乡村日益严重的空心化,留在村庄的都是老幼妇孺,劳动力缺乏,土地抛荒,市场经济浪潮把传统的守望相助的乡村淳朴风气冲刷得荡然无存,乡村治理难度加大,乡村社会各类“社会病”涌现,缺少共同利益联结的乡村集体无法展开互助合作,公共服务设施老化,乡村道路失修,而基层政府无力维护,依靠村民个人自发自觉的组织能力来进行集体活动已不再可能[19](P14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寻找一种连接基层政府与乡民之间的媒介,“新乡贤”就成为这一纽带的最佳嫁接者。
参考文献:
[1] 江丹,魏贤梅.唐宋时期乡贤对文化传承的作用——以 徐州地区为例[J].文教资料,2016(8):65-66.
[2] 王先明.乡贤:维系古代基层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N]. 北京日报,2014-11-24(19).
[3] 李金芳.“新乡贤”未来大有可为[EB/OL].(2016-03-17) [2020-05-05].http://www.rmlt.com.cn/2016/0317/420693. shtml.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6-03-18(1).
[5] 张冰歌.“老人农业”凸显农业发展隐忧[EB/OL].(2011- 07-19)[2020-05-06].https://hnrb.voc.com.cn/hnrb_ epaper/html/2011-07/19/content_368155.htm?div=-1.
[6] 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 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04):74-88+ 205-206.
[7]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 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J].哈尔滨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1):30-41.
[8] 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J].行政管理改革, 2012(11):11-18.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10] 唐琼.新乡贤是乡村治理的“黏合剂”[N].四川日报, 2016-09-14(6).
[11] 陈云松.乡政村治的总体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32-38.
[12] 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J].经济 社会体制比较,2005(3):42-50+15.
[13] 辛宁.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建设[J].四川行政 学院学报,2016(4):100-104.
[14] 张颐武.重视现代乡贤[N].人民日报,2015-09-30(7).
[15] 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 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134+207.
[16] 李强彬.乡村“能人”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J].经济 体制改革,2006(5):89-92.
[17] 刘超,胡伟.内卷化与小城镇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以官 镇为例[J].社会主义研究,2013(1):101-106.
[18] 张厚安.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J]. 政策,1996(8):26-28.
[19] 王丹.村庄公共精神复兴与社区整合[J].甘肃理论学 刊,2009(3):143-145.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New Rural Sage” Promo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NG Ren-wu,MENG Na,LIU Y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As the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new rural sage” is th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s member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have typical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new rural sage” is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value of modern rural style,folk style and family style,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in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of rule of law,rule of virtue and autonomy,building a modern rural management system,and improving rural public services levels and other asp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new rural sage;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責任编辑:赵 哲
收稿日期: 2020-1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18ZDA012)
作者简介: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管理思想史;孟娜,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刘洋,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